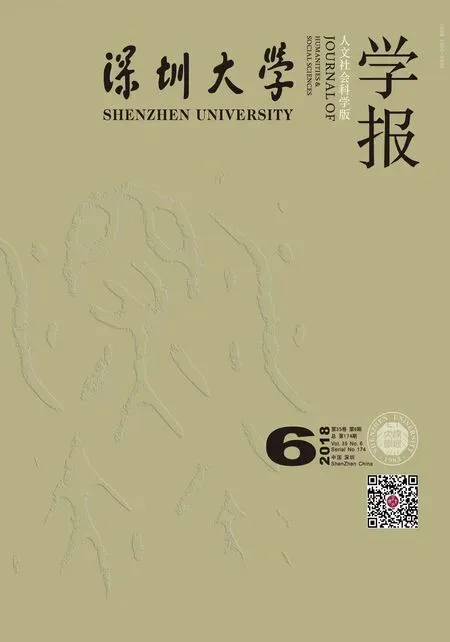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中国印度学脉络总述
2018-03-16郁龙余
郁龙余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2015年11月21~23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在总统府(Rashtrapati Bhavan)召开“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印度总统慕克吉 (Pranab Kumar Mukherjee)在致词中说:“印度学不仅仅指对印度的研究,印度学更是对人类知识重要成分的一种追求,它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由之诊断并缓解人类生活复杂性问题的一种科学。对我而言,印度学的普及正因它所蕴含的广阔的领域,以及提供揭示人类深思的所有问题的可能性方法。”①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洛克希·金德尔(Lokesh Chandra)在《印度学和印度的复兴》一文中指出:“印度学不仅是揭示过去的学问,它也是催生新印度的催化剂。”②两位知名学者对印度学的界定,大大超越了自18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们开启的以梵语文学为基础的,包括巴利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在内的以古代印度语言、历史、宗教、哲学文献为基础的古典印度学,而为现代印度学以及关注当代南亚区域③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南亚学”(South Asian Studies)提出新的追求与使命。正是印度学在印度和世界的重要性,促成了“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印度总统府高规格地召开。
2016年11月 “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印度学不仅在世界印度学花苑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别开生面,枝繁叶茂。中国印度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佛学始,继而梵学,然后印度学。中国对佛学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国现代印度学的一大来源。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留洋深造,他们分别与欧洲印度学和印度的印度学相遇,将西方重梵学的治学理念与印度重亲证的方法带回中国,形成中国现代印度学的又一来源。在这两大来源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金克木等老一辈印度学家筚路蓝缕,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印度学的格局,而且逐步打通佛学与梵学的内在关系,形成了善用中国资料、独具方法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梳理中国印度学的发展脉络、现状和发展前景,是值得我们思索与回答的问题。
一、佛学:印度佛教东传的产物
佛学、梵学、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虽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但都与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佛学、梵学、印度学这三个概念不同程度地和中国人的命运相关。
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诞生、成长、发展、壮大、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而中国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中国用了一二千年的时间,引进、消化、吸收了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化,极大地滋养、强壮了自己。
梁启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门楼。他说:“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1](P191)引进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取经求法及传经送宝的人。在这些人中,玄奘功推第一。“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1](P15)其实,玄奘的功劳,不仅体现在学界,而且体现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佛教、佛学及两者关系
佛教这个名称,是外国人叫出来的。印度人包括佛教徒原本只称“达摩”(Dharma),即“法”,中国常译为“佛法”。中国原本没有道教,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道”,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等到佛教进入中国,为了比肩,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道教”,并奉老子为教主。可以说,道教之名是受佛教启示、激发而产生的,是外力推动的结果。
佛学是佛教东传的产物。佛教和佛学是两个有关联而又并不相同的概念。一般来讲,佛学是指对佛教的研究。但是,在中国佛教和佛学又常常等而用之,尤其是在学者著作中,往往用佛学指称佛教。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心目中,认为佛教是一门学问,称为佛学。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曾说:“我喜欢研究佛教。 ”[1](P58)又说:“夙好治佛学史。 ”[1](P330)在他这里,佛教与佛学是同义的,即“夙好治佛学史”就是“夙好治佛教史”。
在佛教研究中,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蜕化”的现象。“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 ”[1](P145)梁启超所说的蜕化,指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正是这种转化,使佛教不但在中国站住了脚,而且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代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按照梁启超的观点,隋唐之所以能 “文化昂进”,正因为有佛学这个“时代思潮”。
梁启超对中国学术的分期得到了当代学者的继承。尹继佐、周山评价称:“《中国学术思潮史》是一部以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学等八个主流学术思潮为研究主体的长篇通史。”[3](P2)对于禅宗,冯友兰亦有精辟之论。他说:“禅宗盛行以后,其他宗派的影响都逐渐衰微,甚至消灭,‘禅’成为佛教和佛学的同义语。”[4]
佛教、佛学的内涵一而二、二而一的情况,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如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丁福保的 《佛学指南》、《佛学起信论》、《佛学大辞典》等等。若将这些著作的书名中的“佛学”改成“佛教”也无不可。在实际使用中,佛学的含义要大于佛教。
(二)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具有完全的印度属性,为何能在中国站住脚,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学者中是比较有共识的。梁启超说:“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佛教传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1](P145)
文化交流有一良性规律,便是优势互补。佛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互补关系,史学家张星烺说得到位而简明。他说:“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诸说,大为昌明。而展转轮回,尤娓娓动听。补秦以前中国圣人所未言之阙。予人以心理上一大安慰。加以自汉末至唐中叶,佛教书籍,译成汉文者,几于汗牛充栋。其内容如何,姑不必论。其量之多,已足惊人。文人学士,于年老倦政以后,辄喜披览,以度残年。印度哲理,自有其圆密之处,可以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细绎不尽。是以佛教入中国,至唐时已根深蒂固,虽数经摧残,而始终无损于其流行。”[5]
佛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格。中国文化也因此而长寿。诚如梁启超所说佛学输入的隋唐时代最能发挥中国文化的容纳性。梁启超是现代人,他的这句话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种总结。佛教在中国的昌盛,还有佛教它自身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圆融精神的倡导,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隋唐佛学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融合印度佛教的教理而自出于手眼、独创新意。……禅宗则是将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与中国哲学尤其是老庄思想融汇贯通而结出的成熟之果,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象征。第二,圆融精神的又一体现是,在各宗派彼此问难、势同水火的同时,又有相互取资以充实发展各自思想的举措。 ”[3](P13)
正是佛教的这种圆融精神,在和儒学、道教的交流激荡中,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主潮体现为佛教的中国化创新上,别具特色的‘中国佛性论’是佛教般若智慧的民族结晶。 ”[6](P10)
简而言之,根据信史记载,印度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内地;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激烈的交流互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期;至隋唐,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其标志是慧能的禅宗渐渐变成一宗独大,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佛教成了中国的主流思潮;隋唐之后,佛教虽然不再是中国的主流思潮,但是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释道的“合金钢”。正如张立文所说:“宋明新儒学完成了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的融合而和合转生,把三教的兼容并蓄的学术整合到‘天理’上。 ”[6](P11)
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中印佛教之间的差异。中印佛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宗旨与教体上。中国佛教的宗旨与印度佛教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反对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也无须再反对种姓观,只须觉人度人。二者在觉人度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又表现出很大不同:印度佛教的侧重点劝人多积善业,为了来世解脱;中国佛教的侧重点是劝人为善,为了祈福避灾,追求现世现报。早期佛教乃至整个印度佛教的教体就是音声,不是文字。随着佛教东渐,佛教教体发生变化,由音声而变为文字。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佛教虽然自成体系、自成特色,但它保存了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2014年9月17日,印度总理莫迪曾对来访的习近平主席说:印度和中国,是一种精神,两个身子。这句话,不但有历史渊源,而且有现实依据。早在印度古老经典《梨俱吠陀》中便有“二鸟同栖一枝”的偈颂。第二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演讲中引述了莫迪总理的话,指出这些话道出了中印两大文明和平向善的共同本质和心灵相通的内在联系。
(三)中国佛学与中国佛教文化
中国佛学这个概念,主要在中国学者群中使用。普通老百姓更多使用和接触的是中国佛教文化这个概念。关于佛教文化,中国出版过许多书籍,仅是以“佛教与中国文化”为书名的出版物就有多种。文史知识编辑部曾出版 《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作为“文史知识文库”的一种,由赵朴初、任继愈、季羡林等几十位学者的66篇文章结集而成。这套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真实内涵,言简意赅,极具代表性。
由赵朴初等撰写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代表中国人文大家对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真实地反映了佛教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印度学家薛克翘撰写的 《佛教与中国文化》,是王树英主编的《中印文化交流丛书》中的一种。它是作者“把分散于不同刊物中的文章选编成册,整理成书”[7]。此书代表一位中国印度学家对佛教和中国文化关系的学术视野和认知水准,显示了专业的深度。此书介绍了佛教对中国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技、民俗、文化交流六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大量事例说明佛教与中国小说、中国诗歌、中国艺术、中国民俗的紧密关联。
2015年,由薛克翘担任主编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问世。这是中印两国重大文化合作项目。全书分上下两卷400万字,共有2 159条词条和2 310幅图画,“对两千多年来中印两国的贸易往来、科技交流、佛教交流、宗教哲学交流、语言学交流、文学交流、艺术交流、民俗养生健身交流,交通往来、外交往来、学术交流等进行全面总结与描述。”④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和阐述中印文化关系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典集,足以让中印人民在全世界感到光荣与自豪。当然,这份光荣和自豪的大部分来自三千年中印文化交流,来自佛教对中国文化持久、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典籍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二、梵学:民族复兴的一大动力
随着佛教的东渐,一系列带“梵”的称谓和词汇在中国流行开来,如梵刹、梵文、梵书、梵钟、梵音、梵呗、梵天等等。《法华经·序品》有“常修梵行”句,“梵行”指佛教徒的功课和作为。在中国古代,梵学和佛学也常常是混用的。进入现代,随着国人视野的不断开阔,认识到印度除了佛教、佛学之外,还有以印度教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于是,梵学这一个概念就流行起来了。
黄宝生在其自选集《梵学论集代序》中,给“梵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梵语是印度古代语言,仿照‘汉学’一词,我在这里用‘梵学’指称古典印度学。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语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深度与广度也就可想而知。”[8]这个定义,将梵学指称为“古典印度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饶宗颐先生1993年出版《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收26篇论文,也是“古典印度学”的范围。
(一)救亡图存与佛教“三大革命”
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扩大和深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和真切。中国,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这既给中国带来机遇,也造成了冲击。这种冲击,自1840年以后变成了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出现了所谓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的志士仁人从各个方面提出救亡图存的方案,并付诸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成了一支重要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鲁迅、杨仁山、苏曼殊、太虚、谭嗣同、欧阳竟无等等,纷纷提出复兴佛教、佛教救国。1912年,太虚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由敬安任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敬安去世后,太虚在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1918年成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第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他大力倡导“佛教复兴运动”,在中国各地及日本、英、法、德、荷、比、美、南洋、印度等地演讲。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太虚1940年访问国际大学时,对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及其将佛经译汉为梵的工作,大加赞赏,题诗曰:
中华孔老释三家,次第曾开福慧花,好译大乘还梵士,菩提树再茁灵芽。
太虚的教理革命,从世俗意义上说,是将“民主、自由、博爱、平等”思想融入佛教教义;从宗教教义上讲,是将佛学变成动的人生哲学,将佛教变成人间佛教。太虚的教制革命,主要是保持寺产公有、集体劳作、自食其力的丛林制度,恢复民主、平等、互敬、互悦的僧伽制度,是创办佛学院,提升僧众素质的教育制度。太虚的教产革命,主要是护产和兴学两大方面。太虚毕生为佛教改革奔走呼号,贡献殊大。“从社会实践的意义讲,太虚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也是当之无愧的。”[9](P516)
(二)治佛学成晚清一大潮流
除了佛教界,整个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都在传统佛学向现代梵学转型中活跃起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佛教及佛教文学的催发、滋养作用,无与伦比。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佛教被抬到立国、兴国的空前的理论高度,被维新派视作‘最高尚’的‘新信仰’。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有时竟满纸梵语,通篇佛理,理胜于辞,质而不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可谓是佛教驾驭文学,同时又是文学宣传佛教的时期。就诗坛而言,则是佛学驾驭诗歌和诗歌宣传佛学。”[10](P383)
麻天祥认为:“晚清,佛学研究在社会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中心内容也各自不同。寺僧佛学重在护教,不得不实现自身的入世转向。居士佛学意在弘法,促使近代佛教文化的勃兴;而主要由思想家奉行的佛学,这里也称之为经世佛学,其宗旨则在于利生,它不仅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而且推进了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革。”[9](P96)这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一体,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政治家、诗人、佛家三位一体,造成了变法、诗歌、佛学三位一体”[10](P149)
解玺璋认为:“治佛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是一大潮流,但梁启超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焉。’”[11]谭嗣同和梁启超肝胆相照,他研究佛学是受梁启超启发,之前他不知有佛有孔,而只知耶稣。梁启超对谭嗣同评价极高,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称赞谭嗣同 “才识明达,魅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并认为他是当总统的人才(“伯理玺之选也”)。而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 ”[12](P301)他又说:“能为仁之元而神于元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 ”[12](P289)当他喋血北京菜市口,为国杀身成仁之后,梁启超称他:“为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13]。
综上可知,无论是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还是谭嗣同等知识分子治佛成为晚清一大潮流,都说明佛教不但在历史上为维护中国社会和人心安稳作出过贡献,而且在近现代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挥过重要作用。
三、印度学:中印西交流的结果
黄宝生用“梵学”指称古典印度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笔者在此基础上,用“现代梵学”指称印度学。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中,笔者指出“季羡林创建中国现代梵学”,并认为“中国现代梵学的先驱是陈寅恪和汤用彤,季羡林受到二位的教泽与提携,以毕生的努力和五大学术文化贡献,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梵学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现代梵学名至实归的创建者。”[14]这样,在逻辑上十分清楚,季羡林创建的现代梵学就是印度学。
印度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印度的自我觉醒以及中国对印度新的认识紧密相关。在西方殖民主义闯入之前,印度人心目中的印度是自我的印度、自在的印度;殖民主义闯入之后,自我和自在的印度变成了自觉的印度,变成了亚洲的印度、世界的印度。此时中国也变成了自觉的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也从“西天”、“佛国”、“净土”,变成了亚洲的印度、世界的印度。对印度的研究,也从佛学、梵学变成了印度学。
(一)北京大学是中国印度学的摇篮
中国印度学的诞生有两个源头,一是纵向的,自古以来的佛学、梵学研究传统;一是横向的,来自欧美和现代印度的印度学研究。这一纵一横的两个源头,在北京大学交汇融合,催生出了中国的印度学。正是这种纵横两个源头的交汇,北京大学成了中国印度学诞生的摇篮。交汇的时间在1946年,这一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季羡林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应有两个标志或要求:一是在大学里有正式建制,二是连续不断地招生。北京大学在1946年后逐步具备了这两个标志或要求。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诞生,必有前兆和先声。早在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24岁的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⑤,这在中国高校首开先河,是中国高校印度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从梁漱溟开始,中国大学开设印度学课程逐渐增多。被称为“哈佛三杰”的汤用彤、陈寅恪和吴宓是中国印度学先驱。1921年2月17日,他们的梵文、巴利文老师蓝曼先生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说,陈寅恪和汤用彤为“出众的优秀研究生”、“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15]。同年6月5日,蓝曼又给中国留学生监督严恩槱写信,告知“陈寅恪有着高超的智慧(与他的同学汤用彤一样),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16]“哈佛三杰”没有辜负蓝曼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学者”(陈寅恪语)的期望,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印度学的相关课程,为中国印度学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还有周一良。他在1939年入远东语言学院,以论文 《中国密宗》(Tantrism in China,后改名为《唐代密宗》)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世界史、中国史多个研究领域有重要收获,但对佛教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在十卷本《周一良全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第三编 《佛教史与敦煌学》收有 《论佛典翻译文学》、《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壁画与佛经》等著名论文。他的博士论文英文原稿以及中译本《唐代密宗》收于卷首。周一良是中国当代佛教研究和印度学研究的又一重要学者。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对中国印度学的贡献不应忘记。他是一位流亡者,在中国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器重。胡适称“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所公认的”(1921年9月25日胡适致蔡元培信)。他的论文《论对十世纪汉字音译梵赞的重新构拟》(载 《燕京学报》1935年6月),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
1934年,印度中印学会在印度国际大学成立,泰戈尔任主席。1935年,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主席。1937年,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谭云山任院长。从此,中印教育、学术交流有了可靠的桥梁。1942年,中国第一个印地语专业在云南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设立,教师即由国际大学派出。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1949年之前,印地语教育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发展,但是培养了一批最早的印地语师资,如彭正笃、殷洪元。1948年,金克木从武汉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他和彭正笃、殷洪元以及印度外教一起,开始了印地语专业本科教育。从1951年开始,我国印地语文学在教与学、教与研的进程中逐步发展。195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开始招收印地语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全国开设此专业的唯一一所大学。到1956年,印地语专业已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大的专业之一,在校学生人数达83人[17]。
到1960年代,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师资力量总体而言,梵语巴利语专业少而精,一共4人:季羡林、金克木、马鹏云、张保胜。印地语专业,师资较强,1960、1970年代,处于印地语专业的黄金时期。这两个专业,加上乌尔都语专业,合起来称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在东语系资格老,力量强,代表着那个年代中国印度学教学和研究的最高水平[18]。
2000年以来,其他院校也纷纷开设南亚语种专业。据统计,“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持续快速发展。语言教学方面,北京大学于2004年开设孟加拉语课程。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于2006年和2007年开设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专业。西安外国语大学于2006年开设印地语专业。云南民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1年开设印地语专业。”[19]研究机构方面,北京大学于2003年成立印度研究中心,2005年深圳大学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梵文研究中心、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杭州佛学院等等,都有学者在进行印度学研究。
(二)1925~2016年中国印度学成果丰硕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虽然遇到巨大困难,但总体上出现了百业兴旺、文教昌明的局面。印度学(印度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现代印度学研究一方面起步晚,一方面又自我小视。不少人对这个辉煌成就视若无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进行深入研究,在“辉煌成就”和“辉煌成就研究”之间出现了差距。
我们将中国在印度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做了初步统计,从1925年至2016年,已经出版的广义印度学领域的中文著作有近700部。按印度学主要涉及的学科分类,可分为文学、哲学、宗教、历史、语言、艺术、文化、关系史或交通史等。其中,印度文学类著作至少有163种,印度哲学类著作至少有155种,印度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其他宗教等)类著作至少有15种,印度历史类著作至少有86种,印度语言(包括梵语、巴利语等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语、于阗、佉卢文语等西域语言在内)类著作至少有44种,印度艺术类著作至少有32种,印度文化和人文社会类著作范围较广,至少有64种,印度与中国、西域关系和交通史著作至少有21种。
2000年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人员在增多,速度在加快,成果在加速扩大。仅对2000至2016年成果的不完全统计,重要者已超过420项,其中包括论文、译著、专著。根据这些材料,可知中国印度学研究在21世纪初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学者对印度学研究怀有越来越大的积极性。应该说,中国印度学的兴起,是学术自觉的有力彰显。文化学术的强大,首先应该文化学术自信,和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划清界限,屏除不少人心灵深处存在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语)自卑心理。同时,仍要正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印度各领域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之处。中国学术既不允许妄自尊大,也不允许妄自菲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以公允的史识,进取的史胆进行研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印度学研究将取得比现在更加辉煌的成绩。
开放的学术研究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探讨,对印度学这样一个国际性话题更应如此。中国印度学研究是个全新而重大的课题。中国印度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现代印度学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如何与同样古老的印度文明相呼应,又如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它的意义在于,始终提醒我们不要闭门造车,应以追求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为己任,这是当下印度学研究的主旨。
注:
① 印度慕克吉总统致词原稿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提供。
②洛克希·金德尔教授致词原稿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提供。
③南亚区域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阿富汗、不丹等。
④ 《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前言》(详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⑤1914年许丹(字季上)曾短暂讲授印度哲学,他的讲稿为1919年梁漱溟著《印度哲学概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