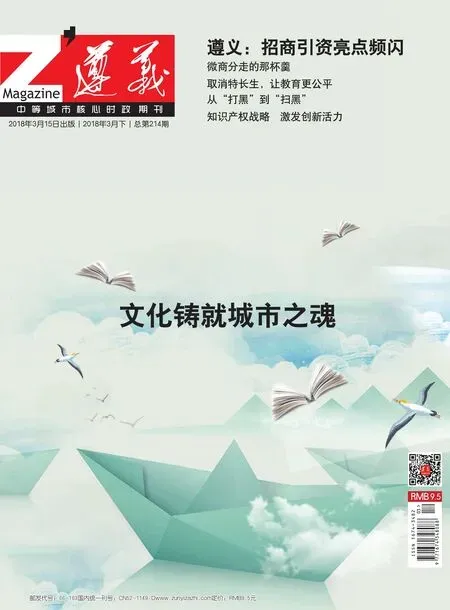拢匠与清明
2018-03-16丨郑
■丨郑 雕

90岁的老拢匠骆弟彦
“一束白花千坟秀,十里乡土尽思亲”。
清明时节,遍野的坟头上挂着随风摇曳的纸花,点缀逐渐变得翠绿的山野。入春的阳气,尚不够旺,凉风阵阵,纸花簌簌作响,似在倾述逝者的远去的情怀,也似在叹惜亲人离别乡土的伤感。“三月里,是清明,手提白纸去挂清。白纸挂在生基上,眼泪汪汪转回城。”世人对逝世先祖和亲人的眷恋情感,是清明节在华夏大地传承上千年而不衰的动力源泉。
清明节,与寒食节相伴而生,前后一天,自春秋时期的介子推割股奉君,国君重耳下令实行禁火寒食的寒食节,已有2000多年历史。拢匠的产生,与祭典相伴,与清明相随,作为一种折纸技艺与老旧行当,把清明作为一席舞台,展示其具有浓烈忠孝色彩的民间工艺!
清明前后,在亲人的坟头挂起的一束束的纸花,叫“清”。专门制作清,糊制各种冥品的为职的人,叫拢匠。
为什么称“拢”匠?
拢匠制清时,把一张白纸裁着条状,短则尺余,长则数尺,用圆弧开口的钱钻将纸条打断,数张纸条一头,用棕叶丝穿着一束,将打断的纸条往反方向撕拉下来,就是一片一条向上、二条下垂的纸片,将5—8片不等的纸片汇串成束,就是一束散乱的清。把一束清的腰间,用纸条“收拢”捆成一束,“拢”匠,大底由此而来。有了腰间的“带子”,一束清就散而不乱,像一束纤细漂亮的纸裙。
清的形样很多。一张长条形的白纸,用钱钻凿顺着长的方向打两条对称的波纹,就形成了三条未断的纸条,把两边纸条的一端撕断,往反方向垂下来,就得一束。一束清,中间的纸条像若干个“8”紧串起来,称“长钱”,这种清最简单又最常见。也有的纸条要用圆环状的竹圈横向串起来,形着灯笼样的;有的串起来,中部大,两端小的,呈腰鼓形。灯笼、腰鼓样的清,有时就需要用竹篾圈将每张穿过,串拱起来,就像纸球或圆盘,这种清更加好看。
清是由白纸用钱钻打断而成,所以叫打清。打清和打钱一样,不能打“半钱”。将纸条用钱钻打断,一般像打钱纸一样,一整叠地打,打完后再将数张串成一束,这样效率较高。可是,如果太贪心,纸叠太厚,把下面的纸打断,上面的就会被打烂、打过了头。相反,用力过少,就打不穿,给撕的时候带来麻烦。用力过小,下面没有打穿打断,就称为“打半钱”。打半钱,在撕、分的时候,返起工来,影响速度。
拢匠手艺,需懂纸剪,又要会花竹篾,懂点篾匠活儿。
竹条弯折成圆环,接口需要相扣固定,可用春天树的小枝来作连接。春天树的小枝,是中空的,将竹条弄弯相对,两端插入一小段枝条中,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圆环。想想匠师们把一根小小枝条的都用到极致,是因为在实践中凝结出来的智慧!
现在的白纸,有一定标准尺寸,折法不同,样式上也有差异。过去的白纸则尺寸不太统一,如果不注意打折的方法,就打得不统一,不美观。一张白纸对折,称对开;再对折,称四开;以此类推,称八开、十六开……无论纸的宽窄,要让清打裁得好看,拢匠有一句顺口溜:“宽留边,紧打圆”。如果纸比较宽,可以把两边留宽些,只要中间的纸条两边的钻印形成一个满满的圆形就行。有了“满圆”为标准,宽窄约有不同的纸,都可以让上端保持宽度一致,即使束成一束,也显得协调好看。
用纸片给清束腰,少不了要用浆糊。过去用的浆糊,除了面粉、糯米面,最经济实惠的就是采集苦楝子树成熟的果子煮烂捣碎,它的果肉就有很好的粘性。苦楝子的果肉很苦,也不易变腐,放在锑瓢里,可以随时加水、加果重熬,不用担心生霉变坏。
旧时打清,用的是皮纸,皮纸并不很白,而是灰色,称白纸;用来打纸钱的纸,称草纸或烧纸。实际上是,白纸还有“空白”的意思,写过字的纸是不能打清的。比起烧纸,皮纸算是比较“金贵”,是用“贡(中药:了哥王)”皮舀制,韧性极佳,是旧时抄书的好纸。现在的清,用各种白纸、彩纸、塑纸制成,色彩绚丽,款式多样,如今祭典亲人,似乎更加隆重。但说实在的,人情比以前淡了。
现在,专门以拢匠为职的人甚少,但乡村民房、集镇巷内,还有那么一些业余时间从事拢匠职业的人,在清明时节,他们制作成出堆的清,以及各种各样的纸质祭品。一些小店的主人利用空闲时间,自己动手,把白纸打制最简单样式的清,在别人祭奠亲人中,分得一羹生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传承着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的习俗。
打清,要讲方法。挂清,也有规矩。挂清,选在清明节前后十天左右,不固定,哪天都可以。但上了年纪的人,都希望家人能尽快到坟头,为亲人挂上一束白纸,表达一种祭典、表达一种孝道。“清都不挂,叫哪样孝道?前十天挂清的是勤快人,后十天挂清的是懒人。”老年人总爱这样唠叨,动员家人早早挂清去。如果借口事多,东推西推,清明节都快完了,才去挂了上几束,敷衍了事,老年人是很不高兴的。
据说,节前挂清,即使风吹雨打,清被吹断吹掉,仍会留着最后一小节,挂在枝头。节后挂清,往往是风大季节,清被大风卷走,一丝不留,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老人们这样说,目的是督促年轻的子女,在清明节即临之前,早点为死去的亲人挂上一束白花花的清。
春节外出烧香,除了亲人的坟头,别的坟前也可以插几支,但清就不行了,不是亲人、祖宗,是不能乱挂的。烧香就像装烟,装的是礼节;挂亲,就是思念、怀念,不是自己的亲人,哪能随意怀念? “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树青”。一座坟头清明是否挂清,似乎成了一个家族是否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父慈子孝的标志。一个坟头上“挂清”越多,说明墓主家族人丁越旺。
如果有儿有女,也不挂清,等同没有,就会让人闲话。“有儿坟上挂白纸,无儿坟上屙狗屎”。清明节到了,如果家人仍然没有挂清的行动,老年人就如此唠叨,作出最后的“通牒!”
在一堆堆,一束束清的纸堆中,我想起了我的幺公。幺公是老家出了名的拢匠。我记得幺公时,他已经七八十岁了,虽然身材有魁梧,留着山羊胡子,但背有些驼,由于长期糊制灵屋(给死人烧的纸房子)、打清、打钱纸,他的四个指头总是拼在一起,与大拇指形成单一的钳状,显得有些僵硬。糊起纸来,十分迟缓。
幺公对人非常友好,一年都在糊制他的人人马马、灵屋、金山银山等冥品,在厚厚的木墩上用钱钻打袱子(成叠的纸钱),也用老式的印板印是阴票子(冥币)。幺公印板图案是反的,非常精致,他印的时候,我总喜爱在旁边看稀奇。
幺公的清打得非常的好,每条钻打成的断线,连贯而规范,撕开后的清,就显得整齐、整洁。所以,到幺公那里买清的人特别多。“虽说‘烧钱化纸,以免阳人’,但孝敬祖宗,要真心诚意,给老祖宗挂的清,不能随意。”幺公总是这么说。
幺公的灵屋扎得非常的好看。他先将竹子花成细细的篾条,扎灵屋等冥品的篾条,不像打席子的篾条那样薄,只要去掉易折断的黄篾就可以。然后用花成的篾条,搭成屋子的骨架。骨架的篾条,有时要转过弯,那是不能直接折弯的,因为那样不直,如果强折成直角,就形容弄断。幺公用手将篾条扭转一下,把拐弯处弄破,篾条转角处就顺着竹丝变柔顺,不会折断。
骨架搭成,幺公拿出印好各种代表瓦、栏、窗等图案的纸,由内到外,糊在骨架上,一幢纸糊的房子就摆在眼前,有凉厅、回廊、天井、花窗、栏杆、青瓦、梁柱,宛如一座漂亮的别墅。灵屋的门上,还歪歪斜斜写着对联,什么“山清水秀非凡地,窗明几净是仙居”,什么“乐国于斯多至宝,冥居从此不忧贫”,还有“洞天福地,瑶岛琼楼”“拔云寻古道,玩景异凡尘”“自在不闻黄鸟唤,清闲哪管白云忙”等联句,儿时的我似懂非懂,觉得幺公抄上去的联句里,有一个与阳世不一样的幸福世界。
每年春节,大人安排我打袱子,少不了要去麻烦幺公,向幺公讨借他的工具——木墩和钱钻。我在幺公那里打袱子,幺公老是夸我是读书人,将来一定是一条“龙”,并乐哈哈地教我打袱子。袱子上面,用钱钻打的弧形,过去人说是铜钱。我的脑壳老是转不过弯来,称它为“括号”——因为那个图形,真就是“()”样。我一说括符,幺公老是笑,说,读书人就是读书人。
幺公用苍老的手指在旁边指点:“金、银、铜、铁、锡,打一路钱,就是金,最管钱,打二路,是银,可以。不要打成铜钱和铁钱就一般了,打成锡钱,就不起作用了……打第六路又是金,要记到起……”
幺公逝去多年,我因为多年离开老家,繁忙的工作,老是忘却了清明挂清的传统,没有为祖宗挂上一束清,以至后来,干脆不再提挂清的事了,想起来有些愧疚。
我想去幺公坟头,挂上一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