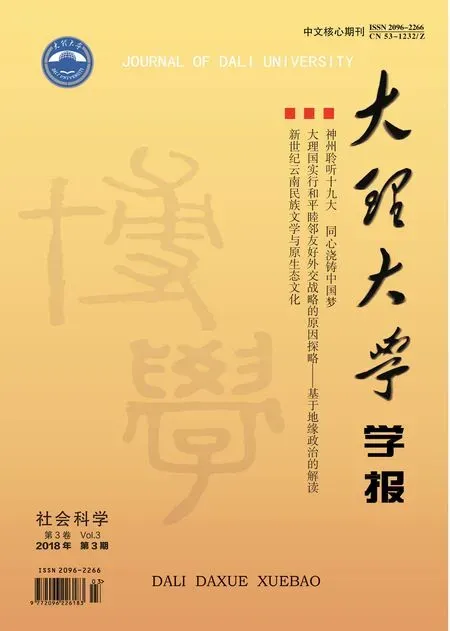从劳伦斯的作品发展析男女性属平等的观点
2018-03-14杨文新
杨文新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云南芒市 678400)
戴维德·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涉猎面广,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有诗集、散文、翻译、戏剧和画作。但与同时代的艾兹拉·庞德、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比,劳伦斯在文学上的地位“有时,似乎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稳定”〔1〕3。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自由表达关于政治、婚姻、社会、教育、宗教以及男人和女人的一些极端看法。因此,正如托格夫尼克一语道破:“每个人在一开始,都会感到这样的需要,要么喜欢劳伦斯,要么讨厌他。”〔1〕33对于喜欢劳伦斯的人来说,如E.M.福斯特、F.R.里维斯、雷蒙德·威廉姆斯和理查德·霍加特,就认为劳伦斯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或者文化偶像。而对于不喜欢劳伦斯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作家。如艾略特就表示:“劳伦斯的生活就如一个故事,充满着精神上的骄傲、情感上的病态、自我式的欺骗和某种无知。这些缺陷即使是剑桥学者,也无法弥补。”〔1〕257此外,作为 20世纪的作家,劳伦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被主流作家们,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看作“现代主义的边缘”。但正是这种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反而促使劳伦斯成为“评论中心”〔1〕179的作家。到目前为止,关于他的书籍和册子就达650本之多,而论文已达数万篇。对于这个现象,艾略特早就评论说:“关于谈论劳伦斯的各种书籍所给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通过阅读要去了解的人而不是一个要去阅读的作家。”〔1〕220原因就在于劳伦斯的作品一直都与他的经历和哲学分不开,它们就像一个三联体。
劳伦斯的三联体特点使其作品和形成的哲学思想带上了浓郁的个人经历色彩,尤其是对男女性属角色的观点研究备受争议。他是“双性同体”的赞成者,也是男女性属角色极端两级化的提出者,同时也矛盾地两者兼有。本文将从他人生经历所形成的四个阶段的作品和哲学思想出发,分析作者所持的性属观点的变化,来探讨性属平等的问题。
一、影响劳伦斯作品和思想的主要人生经历
劳伦斯的写作一直都是在用他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做原材料。对于这一点,评论家们都无异议。劳伦斯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煤矿工人,母亲曾当过教师。常年生活在伊斯威特矿村,劳伦斯一直都憎恨那些黑黑的矿区。因此,首先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人性机械化的场景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此外,他父母的婚姻关系也是影响他作品和个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母亲,利迪娅·比尔兹尔是工程师的女儿,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父亲则是一个矿工兼文盲,身体强健但脾气暴躁。据劳伦斯在《论美国文学名著》中描述,他的父亲“憎恨书籍、憎恨任何人阅读或书写的场面”,而母亲则是“憎恨让她的任何一个儿子注定干体力活的想法。她的儿子必须做高档一点的事”〔2〕。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婚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对于他们,劳伦斯有着复杂的情感。正如他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描述的一样。首先,他深爱他的母亲,依赖她的一切并憎恨他的父亲。然后随着年龄的成熟,他慢慢尝试摆脱母亲对他的影响和控制,开始一步步接受并喜欢上自己的父亲。对于劳伦斯,按照他对女性的分类,他的母亲一直都是一个“公鸡般自负的女人”〔3〕125。因此,他对母亲,既爱又怕,想要依赖她又想逃离她。这也影响到了他对其他女性的态度。一方面,他讨厌“占有欲强的女人”或者“公鸡般自负的女人”;而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她们比起男人要有力量的多〔4〕55。在他的创作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尤其在婚姻中,一直都是他竭力想要去挖掘的主题。通常来讲,他双亲的婚姻是灾难性的,但却“诞生了 D.H.劳伦斯”〔5〕。影响劳伦斯作品的因素,还有他和女性们(像杰西·钱伯斯、露伊·巴罗斯、爱丽丝·达克斯等等)的性经历,尤其是和妻子弗里达。根据与他相关生平的介绍,他年轻时的性意识长期受母亲的权威和基督教教义压制,进入大学后,在阅读了达尔文和尼采的激进书籍后,性对他成为一种崭新的体验〔6-7〕。通过性,年轻的他成功地放下了对母亲情感的迷恋,开始独立地追寻“两性来说,我是谁?”〔1〕33这也是在他的整个写作中为什么如此关注性主题的原因。通过性,他开创性地诠释了男人和女人或性属角色的意义。另劳伦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性之战的年代,他一直“将人类的毁灭归于对征服的欲望——征服自然、征服肉体、征服伴侣、征服下层阶级、征服对手国家以及征服抵触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的一切”〔8〕135。
而他的疾病——肺结核也是一个迫使他发掘该双重主题——死亡和重生的部分原因。对于这一主题,正如桑德指出的,对于劳伦斯来说,上面这些对征服的追求都建立在“分离的错觉”中,都误以为“意识可以和身体分离;自我可以和他人分离;人类可以和自然分离。这种征服的态度前提就假定了有一个统治者,其他都是被统治的对象”〔8〕135。
二、劳伦斯性属哲学在作品中的发展变化
以上这些人生经历都分别被劳伦斯写入了他的小说和作品中,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尽管他从没写过一本哲学书,但他的哲学思想却在他的作品中存在并发展着。他写道:
似乎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哲学和小说的分离。过去,它们常常是一体的,就从神话时代开始……现在小说变得肤浅,哲学变得抽象、枯燥。两者应该再次结合,结合于小说中。〔9〕
劳伦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为此,威廉姆斯赞誉劳伦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思想家,作品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形式中”〔10〕。他建议,要译读劳伦斯的文学作品或者哲学思想,读者们应该把两者结合,因为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上下语境。
不难看出,要理解劳伦斯的作品,他的哲学思想是一根主线,贯穿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关于他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劳伦斯喜欢用矛盾对立的观点陈述问题。在《意大利的暮色》一书中,劳伦斯就写道:“人的圆满有两面性,存在于自我(Self)和非自我(Selflessness)中”。其中“自我”指的是人的黑暗面,意识的底层,“创造性的无限”(Creative Infinite);“非自我”是指对自我的消灭,精神的主体,“不可逾越的无限”(Ultimate Infinite)。在《豪猪之死的反思》中,劳伦斯直接宣称了他的“双重性”原则,“我知道我是由两股流组成的,一股是短暂的,一股是永久的……在这两股对立的流——黑暗和光明的斗争和结合中形成了我”。他相信,“任何一切的本质都存在于两面性,甚至是一个石头”〔11〕。对于劳伦斯来说,宇宙是由对立原则构成的。这些对立既斗争不断,同时又是互补的。而且只要斗争和互补的因素存在,它们之间的对立平衡就一直持续。
可见,劳伦斯的双重性是他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也是他个人的主要特色。对于性属角色的理解,劳伦斯首先在《托马斯·哈代的研究》中就说道:“每一个男人在一开始就由男性和女性因素构成,其中男性因素总是努力占主导地位;而女人也如此,也是由男性和女性因素构成,女性因素占主导地位。”〔11〕他的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同时代女性作家伍尔夫所提的“双性同体”(androgyny)。
对于“双性同体”,女性主义者内部是有争议的。萧瓦尔特认为,它“代表着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相对抗的一种逃避”〔12〕。陶丽·莫伊反对这一说法,认为“双性同体”意味着“女性主义者们的奋斗目标恰恰必须要去解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僵死的二元对立”〔13〕。时间验证了真理。随着性属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认可了性属角色由文化决定而不是由生理性别来决定。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由后天文化环境决定的,与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并无绝对先天绑定的关系。
因此作为20世纪的作家,劳伦斯和伍尔夫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合理、大胆、进步的,但他们受限于时代,似乎无法解释清楚这一现象,只能相信人们可以成为“男子气的女人或女子气的男人”。Moore认为在生活中,劳伦斯本人就非常喜欢做家庭主妇爱做的事,像煮饭、缝补和制衣〔11〕。他还很腼腆,举止优雅、温柔,喜欢和女孩子呆在一起。许多评论家都指出,劳伦斯的小说一直都是在协调他自己体内的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有些甚至认为,劳伦斯就是一个女人,如诺曼·梅勒和开罗·迪克斯就认为他是肉体上的男性,精神上的女性〔1〕266。
关于这一点,女性主义者们和其他男性评论家并不同意。因为纵观劳伦斯的整体作品,他都没有成功地协调好自己身上的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也没有真正在为女性写作,相反,他刻意在作品中一步步地追求和确立男性的绝对意义。他不同阶段的作品和哲学思想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早期和第二阶段——男孩思想到男人思想的转变
劳伦斯第一阶段的作品,《白孔雀》(1911)、《闯入者》(1912)和《儿子与情人》(1913)都是他早期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太成熟,仅仅展示了他年轻时的一些经历以及他和父母关系的一些问题。在这一阶段,劳伦斯只是一个“永远的妈妈男孩”〔14〕。
但从《虹》(1915)的创作开始,劳伦斯就以自己的婚姻实例为蓝本,开始探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并建构出自己对此所持的哲学思想。他的妻子弗里达对他的创作影响至深。在他们相遇之时,她已是一个非常成熟和智性的已婚女子兼母亲。她曾与弗洛伊德信徒奥托·格罗斯交往甚密,相信“要是性是‘自由’的,这个世界将直达天堂”〔4〕Ⅶ。在与劳伦斯私奔旅游时,她脱光所有衣服围着劳伦斯在房间里跳舞。年轻的劳伦斯被她开放的性行为所震惊。而这个场景也反复在他的小说《虹》和《太阳》,以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出现。可以说,成熟、开放的弗里达使劳伦斯在心理上摆脱了对母亲不可自拔的迷恋。但弗里达事实上也和他母亲一样,是一个“公鸡般自负的女人”。矛盾的是,他不但爱上了她,还坚持和她结了婚。根据他的私人信件所说,他正是需要妻子的这种相异品性来引发他们之间的争吵,不然他会变得唯命是从,毁了他的写作天赋。
很明显,劳伦斯的经历不但影响了他的创作,同时也影响到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虹》一书中,尽管劳伦斯提出了“二合一”(two in one)的婚姻观,但同时也感到女性存在的扩张对男性存在是种威胁。他认为,在婚姻中,如果男性在智性或精神上不能征服女性,男性至少在床上要满足她们。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反而女性在性上占了上风,那么男性也将彻底被毁灭。
为追求男性的完整或圆满,劳伦斯继续在《恋爱中的女人》(1920)探讨这一问题。在书中,他放弃了“二合一”的观点,提出“星际平衡”(stellar equi⁃librium)的理论,即“分离中的结合”(unison in separ⁃ateness)。根据这一理论,男人和女人在性上从来不应该追求统治地位或利用对方的性作为意志工具,否则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任何一方必须要打破自我的障碍,放弃所有个性,并超越意识的局限。因为只有这样,双方中的个人才能保持完整的自我,完美地两极化。而当男性感到男子气得到确保,女性感到女子气得到确保,性行为就成为双方满足彼此最美妙的自我实现。
波伏瓦肯定了这一想法,认为“对于劳伦斯来说不是为了定义男女的特殊关系,而是为了使双方恢复生命的活力”〔15〕245。然而,这一想法的实践在伯金和厄休拉的性关系中却无法令读者和有些批评家们信服。书中,劳伦斯对性采取的抽象和象征性描述令人困惑。杰弗里·米耶斯和威尔逊·耐特就一直质疑伯金和厄休拉之间的性行为是“肛交”而不是正常的性交。事实上,正如波伏瓦一语道破的,一方面劳伦斯提出男性的狂妄自大会激起女性的抵抗,只有双方毫无统治欲望的“相互的支配”(the reign of mutuality)才能达到完美的平衡;一方面他却没有构建出这样的支配,女主人公遵从了男主人公的想法,被他统治,被他拯救〔15〕247-248。
(二)第三阶段——男性意义的极端
秉承第二阶段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劳伦斯进入了一个追求男性完整意义的极端。在作品《阿伦的拐杖》(1922),《袋鼠》(1923)和《羽蛇》(1926)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都被创造成主角,都是男性世界的领导者,他们拒绝女性进入世界的权利,在个人关系上,都要求女性对男性绝对的服从。
大多学者都认为这一阶段是劳伦斯写作中最糟的部分,展现的是他在艺术创造上的下滑。事实上,这些作品完整地诠释了他在《无意识幻想》中所叙述的哲学思想——男权至上。对于这一部思想作品,Murry J.Middleton指出,劳伦斯想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亦或我们时代最大的难题——“如何重获性属的纯真”,以及“改变男性世界,使未来没有孩子被培养成具有双重性、制约性,被迫成为他一样的人”〔16〕347。此时的他已经放弃在《托马斯·哈代的研究》中所说的“双性同体”,他认为:
一个孩子在整个心智上要么男性,要么女性;体格上也是要么男性,要么女性。每一个活着的单细胞也是如此,这将持续至生命的终结。所以在男孩身上的每一个单细胞都是男性的,在女孩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女性的。〔17〕96
他相信,“至关重要的性两级”(vital sex polarity)才是“生命的动态魔力”(dynamic magic of life)〔17〕103。达拉斯基指出,这一阶段的思想是“劳伦斯本人一种严重的分裂”〔11〕。
这种分裂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如前面所说,首先是他父母亲对他的影响,其次是他的妻子弗里达。再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见证一系列女权运动的爆发,他的分裂越发严重。原因在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外出工作与男性的恐惧和地位的被动使他坚信,两性角色倒错,这对社会来说既不自然也不健康。这是一种“反常的过程”〔17〕141。
为进一步解释男女性属的不同,他提出男人是积极的“思想家和行动家”,而女人是被动的“情感爆发者”。他认为,当男人发现自己的情感来源于女人时,女人才通过男人学会如何思考,或者至少学会动脑子。他还给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男女角色下定义,提出不管是教育还是婚姻,男女角色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应当在生活的早期阶段设立。他倡议,男孩和女孩应当分开教育、分别教育。女孩应当接受家庭艺术的教育而男孩则要教育成不同的个体。这种隔离教育的目的在于阻止女孩变得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使她们只具备为家庭牺牲的意识;而男孩则能意识到他们的“男性统治”(manly rule)。在婚姻中,女人应当服从,男人则是占支配地位;女性的服从应当是“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服从,发自无意识的忠诚”。除此外,劳伦斯还宣称,男人的世界是对外的,是处理深奥事物的,而“女人对于男人仅存在于黄昏……傍晚和深夜才是她的”〔17〕87-196。在他眼里,女人应该作为男人家里的性伴侣而存在。
达拉斯基从《托马斯·哈代的研究》《无意识》和《凤凰》中整理出了劳伦斯对男性、女性的不同界定(见表1)。他的这些界定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
可以看出,劳伦斯积极地在强调“男子气的绝对程度”,这些对男女性属特点的不同界定明显地以他想当然的男权思想为基础。对于他来说,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是不同的。
但他的这种性属哲学非常不严谨,既形而上还自相矛盾。如在女性原则中的“父亲”(Father)常会误导一些男性批评家,像霍夫先生就曾认为“劳伦斯不是在建构双重性属模式的世界,例如‘父亲’就和女性在同一边”〔11〕。达拉斯基明确指出,“父亲”原则不过是劳伦斯“将女性价值观拟人化的一种上帝宣言”〔11〕。即只要女性接受“父亲”这一原则,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将“无意识地忠实于”男性。

表1 劳伦斯对男性、女性的不同界定
除此外,他的“(通过)肉体(感知)”(knowing by“body”)属于女性原则,却又和男性原则中的“(菲勒斯)意识”(phallic“consciousness”)雷同。而他认为的男性原则,包括“抽象”“精神”“意志”或“思想”(“abstraction”“spirit”“will”“mind”)却又是他一直在致力反对的。事实上,劳伦斯本人也承认他的想法经常是“动态”和“临时”的。正如布鲁斯特伯爵坦言,当他敦促劳伦斯对他自己的哲学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做一番文字表述时,劳伦斯摇摇头说:“我将会在每一页中自相矛盾”〔18〕9。因此,连他自己都喊自己的哲学为“伪哲学”〔17〕14,也不足为奇了。
尽管劳伦斯的思想有其多变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但他却坚持认为男人和女人一直是相互对立,相互争斗却又互补的关系,就像(南北)两极。在回忆录《不是我,是风》中,他的妻子弗里达这样解释道:“(劳伦斯)认为任何一方都应该完整地保持自我的完整和独立,同时又像南北两极一样维持着一种相互依存的联系,由此将整个世界包揽在两者间。”因此在男女双方的争斗关系上,如何“保持(男女关系的)平衡,不僭越、不倒坍”一直是劳伦斯写作探讨的一大主题〔4〕Ⅶ。
这一大主题确实能够粉饰劳伦斯的男权思想,正如辛普森一语道破:“从评论争议之初,对劳伦斯厌女症的攻击以及赞扬他对女性特质感性的描述,就一直并存。”〔19〕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科莫德指出,劳伦斯相信男人统治女人是自然的,如果反过来,女人统治了男人,那就是“身份认同危机”〔20〕。这也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他的哲学和写作中他对女性所具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作为男性作家想要平衡男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却无法纠正自己的男权思想,反而在作品中强调了这一点〔21〕。
(三)第四阶段——男性意义的延生
对男女关系的探讨,进入这一阶段,即劳伦斯创作的晚期,代表作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莫属。这部小说劳伦斯自1926年11月到1928年1月就创作了三个版本,最终以最后一版广为流传。对于这部小说,许多评论家都不承认是劳伦斯的代表作。作为支持者的里维斯就称这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带有劳伦斯创作整体性的许多败笔〔22〕。埃利塞奥·维瓦斯也批评这是一部艺术的失败品,他认为与前面作品相比,不过是“劳伦斯模仿了劳伦斯”〔18〕3。然而,劳伦斯本人却把这部小说“高度视为他对这个世界的信息表达”,因为他“允许自己在性交和爱情游戏的表述上享有高度自由”〔23〕,也正是这样的高度自由使得这部小说既臭名昭著又威名远播。
在小说中,劳伦斯继续发展了他的双重哲学和男权思想。对于他来说,肉体已经被精神和意志牢牢掌控。这种枯燥、抽象、压抑的机械化精神生活已经毁灭了肉体和自我,导致人性和自然的分立。这些不和谐的关系又导致人的自我毁灭。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他赞扬“血性意识”“原始意识”或“菲勒斯意识”,这可以解放真正的自我。因此,他主张要认识世界,肉体比意志更真实,对于保持人的生命力,“肉体接触”“肉体劳动”“肉体意识”比意志更重要。简单地说,他相信“肉体比意志更智慧”〔8〕123。
因此,在小说中,他赤裸裸地描述了查特莱夫人康妮和其丈夫看林人梅勒斯之间的性爱。将性视为大自然原始的生命力,是“大自然整体的灵魂所在”〔8〕101。他自己也说,性就是生命、美和火。性爱的真实魅力在于“性的温暖和火热的交流过程”〔3〕146。性不丑陋,它可以带给人类“一种源源不断的附加能量和乐观”〔3〕148。通过肉体的性,康妮获得了重生,劳伦斯也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英格兰和白人种族的重生”〔16〕353这一伟大社会主题。威尔逊高度赞誉道:“这是我长时间从英格兰看到的最鼓舞人心的书,……最棒的写作之一”,也是“他(劳伦斯)最有生命力和才气的书之一”〔16〕345。应该说劳伦斯仅仅通过康妮的性重生就表达了人类灭亡—重生的崇高主题,不得不说他是个天才。
也正因为这个崇高的主题,使得很多评论家忽视了劳伦斯男权思想的延伸,而一再地“对劳伦斯的用辞累赘的复制和对他的预言仪式般的复述”〔1〕3。像里昂〔24〕和格雷戈尔就坚持劳伦斯对性有特殊的理解,不是菲勒斯崇拜,而是对接触和温柔的表达。是这样吗?
尽管劳伦斯在最后阶段放弃了第三阶段的极端表达,继续发展第二阶段提出的“星际平衡”原则,让部分学者认为劳伦斯回到了研究男女关系平衡的正轨。但劳伦斯最终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如 Daleski〔25〕,Bedient〔16〕370,Rudikoff〔26〕,Tindall〔16〕356-357和 Squaires〔8〕131就指出小说明显体现出了“康妮性爱的被动”“女性意志的被放弃”和“梅勒斯上帝般的权威”。再者说,劳伦斯在这一阶段明确提出了“菲勒斯婚姻”(phallic marriage)已说明了问题。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劳伦斯认为“菲勒斯是服务于两条河流结合的方式;它使这两种不同的韵律结合成一条单独的流”〔15〕248。这种宣称展示了“男人不仅是夫妻双方的一方,而且是他们结合的因素;他提供了双方的超越:‘通向未来的桥梁是阴茎’”〔15〕245。正是这一表述,劳伦斯将“性”等同于“菲勒斯”,证据已足够充分。很明显,他的目的是要巧妙地延续和再创“男性的至高无上”。因此,为了解释宇宙间的性本质,他把对“大地母亲的崇拜”替换成了“菲勒斯崇拜”〔15〕245-248。
波伏瓦继续指出,男主人公梅勒斯,像小说中的其他男主人公一样,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智慧的秘密,这么久以来对宇宙的臣服已经完成,他从中获得了很多内在的肯定,他似乎和任何一个骄傲的个人一样自大。这里有一个上帝在通过他说话——劳伦斯本人。小说中,女主人公“不是坏女人,她很好——却是被征服的”。“这种劳伦斯不得不提供给我们的‘真实’女人的理想类型就是,一个毫无保留接受被定义为他者的女人”〔15〕245-254。
除了这部小说,劳伦斯晚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表述自己对男人女人性属角色的观点。在《女人最好知道》一文中,他指出女性应该照料孩子和整个家庭,男性的兴趣不在此〔3〕83-85。在《他自己屋子的主人》一文中,他认为女性外出所从事的工作是男性不在乎的领域,男人在乎的领域是没有女性的侵扰的,“女人真正接管的不过是一场被(男人)放弃的战争”。他得出结论“男人必须做他自己屋子的主人”〔3〕99-101。在《母系氏族》一文中,他调侃道,男人被家庭牵制就被毁灭了,而女人即使被给予了作为母亲和大家长充分的独立和责任,当孩子冠上了母亲的姓,母亲也要照顾好这个姓〔3〕106。在《女人会变吗》一文中,他认为女人应当如温柔的流,美丽、平静,而现代的“独立女性”不过是一些机器,“爱的机器”“工作的机器”“政治的机器”“追求享受的机器”等等〔3〕153。 在《公鸡般自负的女人和母鸡般温顺的男人》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的女人都表现得如男人一般,再怎么如公鸡般自负,她不过是只母鸡;再怎么追求投票权、福利、运动或事业,到头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母鸡的职责是下蛋〔3〕125-127。
像这些男权思想十足的论调还有很多。这些足以证明,在晚期,劳伦斯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他仍在追求男性意义的确定,并认为女性为追求平等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他倡导女性要温柔和温顺地呆在家里,男人才是一家之主。他并未最终解决男女关系的平衡,也未如他在《查特莱夫人情人的申明》中所说的真正“为女性写作”〔27〕。他最后阶段的作品还是在为男权呐喊,尤其在经历了病魔折磨和男女主权之争后,他更迫切于男性意义的重新确立和延生。
三、结论
劳伦斯是文学研究上最富争议的作家,从其四个阶段的作品可以看出,劳伦斯作为男性作家,在追求性属问题上,受父母失败婚姻的影响,也受自身婚姻和人生经历的影响,一直致力于研究男女关系平衡的主题,并创造性地用性来抽象表述其关系,最终因为将作品和思想深陷自身经历的囹圄,还是没能客观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一步一步彰显了自己不平等的性属主张。从劳伦斯一开始对母亲的依恋和肯定,再到脱离母亲与女性的接触和思考,他对女性充满了好奇、探究,也带着恐慌、压力和保全男权传统意义的危机意识。因此,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性属的平等,在法律之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男权意识的根深蒂固,时刻会威胁和颠覆性属平等取得的成果,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奋斗,为男女的平等坚持和捍卫。
〔1〕FERNIHOUGH A D H.Lawrenc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LAWRENCE D H.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M〕.London:Penguin Books,1985:125.
〔3〕LAWRENCE D H.Late essays and articles〔M〕.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4〕FRIEDA D H.Not I,but the wind〔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34.
〔5〕MURRAY B.D(avid)H(erbert Richards)Lawrence〔M〕∕∕ROGERS J H.British short-fiction writers:1915-1945.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6:315.
〔6〕高万隆.婚恋·女权·小说:哈代与劳伦斯小说的主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9-247.
〔7〕PRIEST A M.Married sex:Ann-Marie Pries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H.Lawrence as a proselytiser for the role of sex in love and marriage〔J〕.Meanjin,2007,66(1):58.
〔8〕MAURO L 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Vol.48〔M〕.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93.
〔9〕LAWRENCE D H.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M〕.London:Penguin Books,1985:520.
〔10〕WILLIAMS L R D H.Lawrence〔M〕.Devon: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1997:4-5.
〔11〕DALESKI H M.The duality of Lawrence〔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59(Spring):3-18.
〔12〕SHOWALTER E A.Literature of their own〔M〕∕∕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41.
〔13〕MOI T.Sexual∕textual politics〔M〕∕∕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37.
〔14〕RUDERMAN J.Lawrence among the women:wavering boundaries in women's literary traditions〔J〕.Studies in the Novel,1993,25(2):249.
〔15〕BEAUVOIR S D.The second sex〔M〕.trans.by PARSH⁃LEY H ,London:Vintage Books,1997.
〔16〕POUPARD 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Vol.2〔M〕.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3.
〔17〕LAWRENCE D H.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an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conscious〔M〕.London:Penguin Books,1971.
〔18〕VIVAS E D H.Lawrence:the failure and the triumph of art〔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0.
〔19〕SIMPSON H D H.Lawrence and feminism〔M〕.London:Croom Helm,1982:13.
〔20〕KERMODE F.Modern essays〔M〕.London:Fontana Press,1990:155.
〔21〕杨文新.《木马赢家》中语言建构的隐含男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8(3):79-83.
〔22〕LEAVIS F R D H.Lawrence:novelist〔M〕.London:Al⁃fred A Knopf,1955:94.
〔23〕CRAIG A.A history of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ry obsceni⁃ty〔M〕.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3:146.
〔24〕LYON J M.Lady Chatterley's lover:overview〔M〕∕∕KIRK⁃PATRICK D L.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Chi⁃cago:St.James Press,1991.
〔25〕DALESKI H M.The forked flame:a study of D.H.Law⁃rence〔M〕∕∕DIMAURO L.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Vol.48.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3:110-117.
〔26〕RUDIKOFF S D H.Lawrence and our life today〔J〕.Com⁃mentary,1959(28):408-413.
〔27〕LAWRENCE D H.A props of‘lady Chatterley’s lover〔M〕∕∕POUPARD 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Vol.9.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3:2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