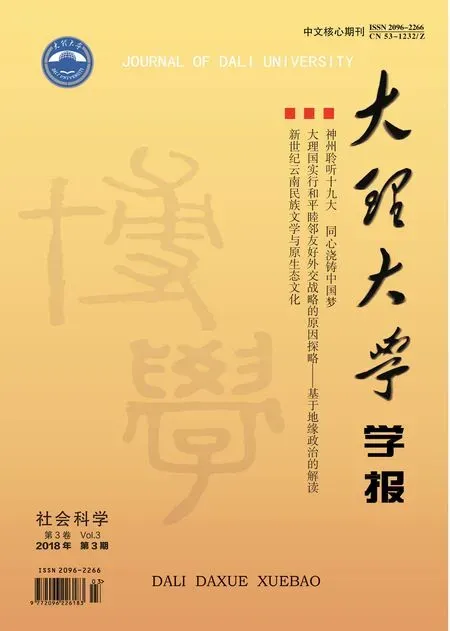自我反映在米勒音乐纪录片的表现
——以《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音交会》为例
2018-04-12颜晓星
颜晓星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克拉考尔认为纪录片特点是偏重表现精神世界,谈到“纪录片导演常常如此热衷于宣扬某些理性或意识形态性的主题”〔1〕。纪录片总是不可避免带着制片人的主观意识对现实进行复制,这种复制也就是记录片的“自我反映”,即“影片中任何涉及自身制作过程的那些方面:影片的立意、获取技术设备的必要程序、拍摄过程本身把零散的图像和声音片段组合起来的剪辑过程、销售影片的期望与要求放映影片的环境条件。这些过程就使得影片具有了人为操纵的性质”〔2〕。米勒本身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主张“摄影机不是用来记录音乐,而是用来表现音乐”〔3〕,这种自我反映的意识对音乐纪录片创作影响深刻,本文试以《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和《音乐的交会:斯特恩重回中国》(以下简称《音交会》)为例,从叙事策略、视觉文化感知、纪录片剪辑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米勒的音乐理念对“自我反映”纪录片拍摄叙事策略的影响
在拍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时,米勒并未与斯特恩一道出访中国,而是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对拍摄素材进行剪辑,他的音乐理念无疑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以往音乐纪录片的叙事模式。
(一)音乐视觉化的理念对纪录片编导的影响
音乐纪录片与一般的纪录片叙事策略有显著不同,它与导演的音乐理念和追求音乐表现的形式密不可分。米勒在拍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记录片时就说:“我当时就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将音乐视觉化,同时又不破坏音乐?我渐渐发现拍摄音乐会的准备情况是一个办法。另外,我对演奏家和作曲家也逐渐发生了兴趣。如果你进入一个音乐家的内心,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排练和演出,就会很精彩。”〔4〕可见米勒不仅关注音乐的曼妙之处,而且主张让音乐视觉化,因此该片中不仅展示了斯特恩的精彩演奏,也拍摄斯特恩为演出做的种种准备:如何与北京演出乐队的磨合、解决上海遇到钢琴调音问题,还充分调动镜头语言记录了斯特恩指导中国学生演奏和中国音乐人的交流情景,这样的编导不仅让单纯的音乐演奏会变得有故事、有悬念,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听觉、知觉的功能,促使观众能够深入理解音乐、欣赏音乐、热爱音乐,实现心理学的“移情”作用。米勒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中无疑创新了音乐纪录片叙事方式,以往的音乐纪录片偏重于音乐演奏会的现场拍摄,或者“直接电影”表现形式,偏重于事件活动过程客观记录,如1968年的《莫回首》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通常被作为音乐研究文献资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自我反映”性质的音乐纪录片。
(二)音乐教化的理念在纪录片的表达
两部纪录片的解说词主要以斯特恩的第一人称来进行解说,除了再现纪录片场景的真实性,也是米勒借斯特恩之口来表达对音乐的认知,二者的音乐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以乐会友”是斯特恩的初衷;寓教于“乐”,传播音乐文化才是斯特恩的最终目的,也是米勒的音乐理念,并且前后20年始终贯穿在两部纪录片创作中。斯特恩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说:“音乐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件工作,也不是偶尔为之,是融入你的生命,是你深信不疑的奉献。”在《音交会》纪录片中斯特恩进一步阐明音乐理念:“音乐的重点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在创造文明社会。”正是基于音乐本质的认知和音乐教化功能的理念,这两部纪录片关注重心实际上都是中国音乐教育,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一片中,米勒选择以上海音乐学校作为样本来考察中国音乐教育现状,时长占纪录片长度的三分之一;《音交会》中的斯特恩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对20年后的中国音乐教育提出疑问:“别的国家播种是长出花朵、香菇、树木,但在这里播种,欲长出30层楼高的建筑物?”此外两部纪录片中都展示了斯特恩不仅重视技能学习,更重视在对中国学生的音乐情感培养和音乐理念的引导,如“音乐不只是黑与白,是各种色彩,有些是连画家都调不出来的颜色”“不是用音乐来演奏小提琴,而是用小提琴来演奏音乐”,实际上是对中国音乐教育进行反思与指导。为了强化音乐教化的理念,米勒在技术剪辑上有意把斯特恩的上海演出场景与北京的指导情景采用时空错序的方式混剪在一起,使之更全面系统地阐释这一理念,如果按时间线索编导该片,则会淡化音乐理念的表达效果,无法在情节编导上达到叙事高潮,因为纪录片也是讲故事。《音交会》结尾中有意安排斯特恩父子与20年后成长为大提琴家的王建、小提琴家徐惟聆、钢琴家潘淳一起同台演奏,暗示中国新一代的音乐人在斯特恩教诲下逐渐成长。
(三)包容的音乐理念在纪录片的反映
音乐在音乐纪录片中不只是表现一种手段,更是表意的象征符号,传达制片人的理念和情感。如《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穿插民乐演奏4次,总计时长达6分钟,还拍摄中国传统京剧、口技、杂技、民歌演唱等,而斯特恩总是神情专注听音乐,表现出对中国民乐的好奇和赞许,展示了世纪音乐大师对不同民族音乐的包容和欣赏,正是这种包容悦纳的音乐理念使该部音乐纪录片也成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汇的窗口。其次是米勒还刻意地展示不同民族音乐的最美情态。米勒说:“我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观众感觉到中国的音乐家能把自己的人文素质完美地体现出来,这是我努力表现的东西。”〔5〕在特定年代,中国音乐家的表情总是较僵硬,米勒在处理中国音乐家演奏的镜头画面时总是煞费苦心,比如弹奏琵琶的演员镜头处理,米勒采用了特写镜头(演员侧面镜头、芊芊细指弹奏镜头)、景深镜头(演员面孔淡化镜头)、摇拍镜头等诸多艺术手段,努力避免让观众看到演员僵硬的面孔,试图表现演奏者音画合一的美感效应。纪录片刻意拍摄了一位唱中国民歌的小女孩镜头,尽管穿红衣服的女孩表情有过多成人化的印迹,但是优美的声音还是较完整地记录下来,时长46秒。在米勒看来,音乐家需要包容不同族群音乐的差异性,尽量避免带主观性的选择样本,因为真实呈现音乐形态也是对音乐制作负责的态度,音乐无国界,更无高低贵贱之分。
二、中国文化的视觉认知在“自我反映”纪录片的表现
(一)透视街头文化,展示中国社会面貌的变迁史
“街道是公众和个人、静止和活动、限制和放松之间进行交流,有活力的载体。”〔6〕在某种程度上看,街头文化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变迁,它往往最敏捷地捕捉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我们可从《清明上河图》都市的街头空间文化了解北宋最大都市的繁华面貌和人情习俗。米勒他们要了解中国,最鲜明、最直接的还是从街头空间的文化镜像去捕捉与感知。北京的街头文化展示的是农村到城市文明的动态画卷,映射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缓慢进程:农村依靠的是脚力,那些挑着各式各样东西的赤脚农民缓慢地从泥土小路走向城市公路,越靠近城市,出现了马车、自行车、货车、吉普车等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镜像,包括象征帝都的天安门广场和宽阔马路等。作为中国最大都市的上海街头文化,则透过江上来往帆船、大型货轮、高楼大厦等影像,形象地说明这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大都市,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如同大海收纳百川最终交汇在一起。上海城市街头的西方广告暗示了这是一座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大都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然在这繁忙紧张的大都市也不忘展示忙里偷闲的人们,如人们悠闲地下象棋、不紧不慢地打太极拳。时过境迁,20年后,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音交会》纪录片还是从北京街头的都市空间来展示大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沧桑巨变:高耸的建筑、川流不息的车辆、繁忙的建筑工地、日常百姓街头购物等揭示了这是一座正在高速崛起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也反映了中国20年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二)透视城市影像人群,感知中国政治的文化生态
街头的空间影像建构的是城市文明外貌,要深入了解一座城市的灵魂,还是城市空间的主人。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中,米勒透过一系列的影像人群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生态特点:中国政治人物对斯特恩一行的热情招待、上海街头受采访青年的话语,勤奋刻苦好学的中国学生等镜头,鲜明感受到中国上下阶层都渴望发展、渴求知识、渴望拥抱世界的情怀。中国人对斯特恩的演出总是报以如潮般的热烈掌声,揭示中国人其实也懂得欣赏西方音乐,不排斥外来文化。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中,李德伦与斯特恩讨论莫扎特的阶级论,这说明中国人受“左”的思潮影响至深,而20年后,再谈老话题时,李德伦承认当时所说的话是违心之话,也侧面展示了中国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专制体制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生态社会。《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纪录片中特意通过谭抒真讲述故事揭示了摧残人性、泯灭生命的文革政治生态;而在《音交会》里,米勒有意采访了当年的几位学生,通过他们的成长来展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沧桑巨变和人性的苏醒与勃发。两部纪录片前后呼应,似乎在告诉人们:尽管人生境遇的改变有运气成分,但大时代环境的变化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最重要原因。纪录片最后安排三位中国音乐家的演奏,与第一部纪录片中的少年演奏形成对比,暗示着中国音乐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融入世界,这正是米勒和斯特恩他们所期待的。
三、高超的剪辑技巧在“自我反映”纪录片中的完美呈现
(一)透过人物细节的特写镜头,展示纪录片的人情美
纪录片人物与电影人物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生活中真实,是本色的记录;后者是接近现实的虚幻,是人工雕琢的表演,具有艺术感染魅力。该部纪录片人物——斯特恩,却与影视中的人物一样具有超级的吸睛魅力,充满个性魅力的斯特恩形象是这部音乐纪录片获得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而这也得益于米勒善于捕捉和剪辑斯特恩的特写镜头,因为特写镜头往往最能波动观众的心灵深处,最能展现人物的形象之美,例如指导小学生演奏时,斯特恩双手搭肩和拥抱学生的特写镜头展现了艺术大师的舔犊情深。斯特恩那些幽默风趣、形象生动、富有启发性话语的一系列的特写镜头诠释了一位可亲可敬优秀音乐教育家的形象。尽管当时的中国百姓,群体的面部表情总是刻板化、僵硬化,但导演米勒总在不遗余力地捕捉街头闹市影像中的人情美: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小女孩的好奇眼神,街边下象棋老人的得意笑脸,剧院里观众的陶醉神情,教室里小女生渴望求知的双眸,这些富有人情美的特写镜头,悄悄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百姓刻板保守的印象。在《音交会》中,阔别20年后的两位中西音乐家重逢情景令人泪眼迷离:斯特恩拉着小提琴与推着轮椅进场的李德伦两人深情对视,不用任何语言肢体动作,千言万语融入音乐声中,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也许纪录片的大部分人物无法像影视人物那样丰富饱满,富有魅力,但是纪录片的导演要善于捕捉人群中的生动影像,运用人物细节的特写镜头来展示人情之美,使纪录片的人物在观众心底扎根,而不是无意识地拍摄剪辑,消弱纪录片的感染力。富有人情之美,无疑会增强纪录片的传播力度和广度。
(二)镜头转换与音乐视觉美感的统一,展示纪录片的节奏美
1.音画合一的视觉转换
斯特恩在中国访问时间达到3周,拍摄的场景镜头众多,而且来往北京、桂林、上海三地,米勒则借助音画合一的镜头来实现空间转换,注意体现音画和谐,产生诗画般的意境,吻合中国人的山水审美感受。例如从农民挑担暗合音乐节拍的步伐,优美中国民乐旋律从田园风光的农村一路挺进热闹的大都市北京,最后通过纪录片的音乐在车马声响中停止,让人们自然地从诗意般的视觉画境走向现实生活的都市;再如从北京到桂林的空间转换,首先在悠扬的琵琶声中慢慢淡化成中国山水画面,音乐悄然转换为《二泉映月》,又通过摇晃的镜头,暗示火车行进在南中国,最后出现火车行进的景深镜头,通过3秒的火车车轨声,音乐戛然而止,显示火车从北京到达桂林,此刻片中音乐旋律与画面镜头彼此间相互呼应,转换节奏自然巧妙。当桂林山水画面转换成北上风光,画面转换过程在“秒杀”中进行:先以“小河中摇船全景镜头”起到自然过渡,也许是桂林小河,也可能是苏杭运河,紧接着出现江上帆船、轮船的镜头,最后从黄浦江全景镜头俯拍到繁忙大都市的街景,实现了桂林到上海的和谐空间转换,产生了视觉美感的效应,镜头画面语言和谐转换使得纪录片的节奏绵密而不拖沓。事实上纪录片中每个场景的转换,米勒都做得十分精致和细腻,绝不拖沓,而且每个镜头转换就像音乐旋律中的每个音符,都传达着情感,也使得纪录片外部节奏产生和谐之美。
2.“可见音乐”的不同呈现
展示“可见音乐”——中国民乐和西方古典乐是《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音乐纪录片的内容主题。这种“可见音乐”的不同呈现如果表现形式始终一致时,就会令音乐纪录片节奏表现为单调甚至缓慢。表现中国民乐时,米勒从不同机位拍摄了中央民乐团的表演,时长1分11秒,共有17个镜头,在画面剪辑中,依次交叉展示中国民乐的不同乐器:唢呐、二胡、琵琶、笙、笛子、柳琴,多采用中景镜头,注意弹奏者的动作与音乐旋律的吻合,特别注意捕捉指挥家的形体语言,试图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民乐之美。对于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会,无论是北京乐团的合奏表演或是上海个人独奏,米勒始终把斯特恩视为音乐盛会上的灵魂人物,采用全景、中景、近景等镜头,全方位展示斯特恩的演奏和神情,总共时长达20多分钟,斯特恩如同舞台的英雄形象让观众如痴如醉,感受艺术音乐的视觉与听觉之美。纪录片中采用不同的剪辑手段以及主次分明的时间分配,使得音乐的内部节奏显得松紧有度,让观众感受“可见音乐”的魅力〔7〕。
(三)大胆创意的音乐时空错序剪辑,展示纪录片的结构美
1.纪录片结构的凝练美
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音乐纪录片的序曲中,通过机场镜头、欢迎宴会的镜头、演奏会镜头交代了斯特恩抵达北京的目的和出访的效果,共1分37秒时长,这是斯特恩为期3周的中国之旅的高度时空浓缩,折叠压缩的时空剪辑使纪录片结构显得更紧凑,不浪费一分一秒。片中以斯特恩观看中国男孩独奏巴赫大提琴组曲作为尾声,米勒这样倒叙的剪辑是有深意的,首先巴赫大提琴组曲的明快节奏中暗含对人生的思考和期待,最后以热烈的掌声作为纪录片的休止符,表达了中国的西洋音乐就像少年一样,令人充满期待和希望。总之这种时空错位跳跃性的剪辑,使得纪录片结构更加紧凑、凝练,更好表达纪录片的主题。
2.纪录片结构的韵律美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米勒的纪录片编排结构富有音乐旋律之美,跌宕起伏,疏密有间。例如欣赏小学生精彩演奏后,从音乐教育话题的讨论到倾听谭抒真讲述沉痛的文革经历,纪录片的气氛达到空前最沉闷和悲愤时刻,此时画面镜头转换到斯特恩演奏《春天奏鸣曲》,西方观众由于长期浸染在古典音乐的语境中,很容易领悟米勒的编导意图,暗示中国正从文革阴霾走出来,迎来了人性复苏的春天,伴随着悠扬琴声,观众心底也透亮起来,演奏的画面镜头起到了暗示蒙太奇作用。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为了全面揭示音乐理念,米勒将在北京指导学生情景与演奏会上的画面混剪在一起,节奏变得舒缓,接着为了展现音乐纪录片的高潮,剪辑了斯特恩在北京表演的莫扎特《C大调变奏曲》,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最后在激情四射演奏的高昂乐曲和观众热烈如潮的掌声中结束了,可以说米勒在音乐奏鸣曲的指挥棒下进行纪录片结构的编导与剪辑,音乐不只是作为背景音乐,也作为纪录片内在的线索进行时空混剪,达到以声传情、以声达意的作用。
总之,米勒在创作音乐纪录片时,在编导、剪辑、音效等方面无不体现“自我反映”意识,创造了音乐纪录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就像拍摄电影那样精细地雕刻每个镜头,每个镜头语言都在诠释米勒内心的思考和愿望,折射出的不仅是音乐的光辉,也包含对社会镜像的诠释〔8〕,使得他的音乐纪录片耐人寻味,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追求艺术美和精神美的统一则是米勒音乐纪录片的自我反映意识的最高追求。
〔1〕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263.
〔2〕珍·艾伦 .纪录片中的自我反映手法〔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82.
〔3〕王凡.镜头间滑动的乐思:美国音乐纪录片导演阿伦·米勒作品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6):34-39.
〔4〕王寅.让眼睛也能感受音乐:艾伦·米勒访谈〔N〕.南方周末,2002-08-30(A10).
〔5〕张爱华,赵斌,单万里.音乐的电影与电影的音乐:阿伦·米勒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6):40-46.
〔6〕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4.
〔7〕马晓晓.音乐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音乐纪录片研究〔J〕.音乐传播,2014(3):86-93.
〔8〕王弘劼.新闻纪录片的讯息载体及传播效果〔J〕.新闻爱好者月刊,2011(9):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