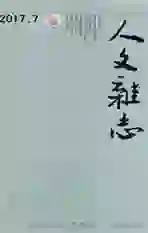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2018-03-09金田林严汉平岳利萍
金田林+严汉平+岳利萍
内容提要 本文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角度研究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基础,发现省际城市规模的空间分布差异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并利用1994-2013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经济赫芬达尔指数为核心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与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表明在长期中城市规模水平的提升越过最优值后,反而不利于人均GDP的提升。这种非线性的关系,不仅能够佐证空间经济学中集聚经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下不断消长的论断,也能为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优化提供科学借鉴意义。
关键词 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首位率 赫芬达尔指数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52-09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充分利用以金融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为代表的溢出效应,引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这一事实已经成为文献的普遍共识。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各种要素资源持续不断地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明显获得提升。事实上,要素空间集聚水平提升对经济发展,是有条件的。②为了实现要素空间集聚的最优效率,在中国推进经济空间优化布局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选择科学正确的路径?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素来有大小城市之争,争论大小城市效率孰优孰劣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③
以上研究为我们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有效洞见。然而,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不同省际内部根据城市实力高低(多以人口和经济为标准),形成了一个城市体系。因此,孤立地研究何种规模的城市更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显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而相对于讨论单个城市的最优规模而言,城市体系的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因此,识别经济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探索省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最优增长区间,对于优化特大城市规模,建立科学的城市体系意义重大。本文利用1994-2013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赫芬达尔指数为核心指标,实证检验了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与省际人均GDP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表明在长期中城市规模水平的提升越过最优值后,反而不利于人均GDP的提升。这种非线性的关系,能够佐证空间经济学中集聚经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下不断消长的论断。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城市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结果,表现为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互相拉扯的动态演进过程,是金融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Fujita M. and Krugman P.R.,“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no.25,1995,pp.505~528; Fujita M., Krugman P.R.and Venables A.J.,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9;梁琦、钱学锋:《外部性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7年第4期。大规模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的高密度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成本等一系列负外部性,必须被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内核的不完全竞争机制所稀薄,才能释放出规模经济效应。然而,要素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的拥挤成本作为决定要素集聚与否的重要力量,其此消彼长的关系往往导致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而这则外化为一个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表征了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规模演变,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不同城市的规模对比关系。经典的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情况下,在规模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下,要素总是倾向于集聚在某些特定区域。要素的空间集聚之所以能够引致区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分享、匹配与学习机制。Gill I. S. and Kharas H.,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7.然而,要素空间集聚引致的規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并非呈现单调线性递增,而是会随着要素集聚的规模不经济等负外部性而逐渐减弱,甚至抵消。当要素集聚引致的分享、匹配与学习效应,逐渐被城市的拥挤成本、通勤成本等负外部性逐渐吞噬,要素将会选择流动到其他收益相对更高的地区实现再次集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实际中,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结构又会导致绩效高低的经济增长表现。Fay M. and Opal C., “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12, 2000; Henderson J.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What Ques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no.8,2003,pp.47~71.不论是沿着新古典城市体系的思路行进,还是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中国城市体系结构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Au C. and Henderson J.V.,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no.3,2006, pp.549~576; Henderson J.V., “Urbanization in China: 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http: / /www.econ.brown.edu/faculty/henderson/finalfinalreport-2007050221.pdf;简新华、黄坤:《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许政等:《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如何评估中国城市体系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学术界大体沿着两条思路进行:其一,从城市规模及其分布的视角出发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城市规模及其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这类文献大多从实证的角度测算并论证了中国城市规模偏离最优状态对经济效率的损失;高鸿鹰、武康平:《我国城市规模分布Pareto指数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李培:《最优城市规模研究述评》,《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美]亨德森:《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政策整体与选择》,《比较》2007年第31期;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谢小平、王贤彬:《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南方经济》2012年第6期;李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差异》,《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其二,从城市化路径及其实现方式的视角出发探讨以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市重点论之争,城市化路径实现方式、城市化路径的制约因素,这类文献一般论证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冯云廷:《小城镇化战略的反思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取向》,《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11期;张景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实证分析》,《财经科学》2007年第5期;柯善咨:《扩散与回流:城市在中部崛起中的主导作用》,《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陈甬华:《中国城市化发展实践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期;钟宁桦:《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章元等:《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不难看出,学术界对城市分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未深入,通常都是从数量角度研究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缺乏从省区内部城市之间规模关系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省级城市规模分布的视角,理解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绩效。而我们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为什么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绩效?这中间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endprint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比观察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市规模分布的演化过程,就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奥秘。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东部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新兴城市,诸如大连、青岛、苏州、宁波、厦门、深圳等等,这些城市不仅没有成为传统中心城市的附庸,反而借力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走上了发展壮大超越传统核心城市的道路,并在省区内部形成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立的城市规模分布结构。这种“双城演绎”的城市规模分布,能够在省区内部形成有效的资源竞争关系,并驱使要素按照边际收益法则进行空间布局,从而取得了经济效率最优的局面。
反观中西部地区,在国家逐渐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支持性政策之后,绝大部分省区将实现“弯道超车”的后发优势希望寄托在省区内部的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省区内部的非省会城市的发展速度则相对缓慢许多。这种“单兵突进”的城市规模分布,一方面集聚了省区内部大量优质高效的要素,却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导致集聚效率被逐步稀释,甚至有可能走向净损失的境地;另一方面省区内部非核心城市要素稀缺性导致的要素成本居高不下,则加重了非核心城市的发展成本。这种要素空间错配的现象势必会影响地区的长远发展,损害地区的增长潜力,最终成为增长拖累。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路径。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一条中小城市蓬勃发展,演化成为大城市的路径;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着一条首位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萎缩的道路(见图1)。而这种城市规模分布演化道路的差异,很有可能就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因。
我们认为,城市规模分布演进引致的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导致的资源配置过度的扭曲。在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背景下,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和财税激励,往往对经济运行进行大规模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是通过在不同城市之间分配政府手中的诸如土地指标、财税转移支付方向和比例,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和范围,新设立工业园区的选址等行政性政治资源,而影响其他资源配置过程实现的。城市规模分布作为表征区域内部城市之间规模大小与力量强弱的因素,代表了不同城市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是一个影响地方政府政治资源配置的重要变量。而地方政府选择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政治资源配置,往往引致了市场性资源配置过程的虹吸效应和竞争效应,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绩效的差异。
所谓虹吸效应,是指在城市规模分布“一股独大”的状况下,首位城市或核心城市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吸引力为基础,以位居城市体系顶端的政治优势为抓手,以超额获取国家与省级政府的支持扶持为推力,通过过度汲取集聚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要素来推动首位城市发展,从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机制。在首位城市规模更大话语权更强的省区,首位城市的发展能够为省级官员和首位城市的主政官员同时带来收益,因此各种政治性资源优先配置在首位城市,其他城市的发展能力相对受到盘剥。首位城市的无限扩张高度集聚了省域内的各项资源,资源的边际收益逐步下降。但受制于大城市的各项政策红利与土地扩张引致的要素边际成本递减速度更快,从而导致了首位城市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强,大量的集聚要素享受來自行政干预带来的“虚高化”边际收益而不愿离开,从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回流效应丧失,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增长。
所谓的竞争效应,指在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均衡的状况下,各个城市之间获取省级政治资源配置偏好的影响力较为均衡,城市之间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原则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规律,而要素流动在自由竞争规律的引领下,选择按照真实边际收益高低在不同城市的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布局,而不同城市之间形成的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的互相竞争关系,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发展的一种机制。在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均衡,存在多个区域经济增长点时,省级政府的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往往是竞争性的过程,而非由某一个城市独享。因此,当首位城市独享的“政策偏爱”被相对均匀配置给多个城市,城市之间互相竞争的基础相对公平,城市之间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比较优势,从而导致了城市之间竭尽所能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合理化的产业分工,吸引要素集聚,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从而不断提升了区域经济增长绩效。
综上,一方面,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省区内部的要素大量集聚在首位城市,首位城市凭借政策红利不断创造“虚高”化的要素边际收益,其城市规模不断膨胀,省际城市规模分布不断朝向“一股独大”的状态演进,从而损害了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另一方面,在竞争效应的作用下,省区内部的要素在真实边际收益的引领下自由布局,城市之间的发展相对均衡,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朝向“多点开花”的状态演进,从而不断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绩效。
三、实证检验
沿着上文的思路,我们将对上文提出的论证逻辑进行经验验证。然而如何准确刻画中国的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是科学研究城市规模分布差异与经济增长绩效高低关系的核心命题。以往考察城市规模分布变化时,学术界通常应用人口指标进行对比研究。顾朝林等:《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地理科学》2005年第6期;杨开忠、陈良文:《中国区域城市体系演化实证研究》,《城市问题》2008年第3期;叶浩等:《中国城市空间分布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2期。然而,中国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数量和方向,难以进行长时期完整的统计,除此之外,人口统计数据之中户籍数据和常住人口数据的差异往往很大。运用GDP数据,则可以填补人口流动频繁导致的数据失真问题,因为不论居住时间长短与否,只要进行了生产与服务供给和消费,就创造了GDP,就能被统计在内,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的真实规模。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取GDP指标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依据。本部分,我们以中国1994-2013年365个地市级区域(包括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或地区,以及级别相当的自治州与盟,简而言之就是所有地级区域)的GDP数据为基础,测算选取赫芬达尔指数(HHI/Herfindahl Index)作为衡量不同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指标,检验省际城市规模分布对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影响。endprint
赫芬达尔指数通常用来衡量产业集中度,主要用于计量某个行业中不同企业之间规模大小引致的市场结构的差别,表征了特定产业中企业规模的集中与离散程度。吴学花、杨蕙馨:《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0期。在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中,Xi表示特定行业中某个厂商的规模,X表示整个行业的规模,Si=Xi/X表示第i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表示某个行业中的厂商数量。本文选取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城市经济集聚指标,表达了某个省域内部所有城市GDP规模之间的离散程度,表现了一个省域内部经济生产的集中程度,反映了不同省域城市之间规模相对变化的演进路径。具体来说,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大多数文献中用于测量城市规模分布的指标有以下三个:(1)首位城市集中度指标;(2)位序-规模法则;(3)赫芬达尔指数。位序-规模是来源于数据之间的拟合值,无法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而相对于首位城市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能够包含整个城市体系中所有城市规模相对大小的信息。Wheaton W.C. and Shishido H.,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0, no.1,1981,pp.17~30; Gabaix S. and Ioannides Y.M., “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 2004,pp.2341~2378.第二,赫芬达尔指数度量的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占整个省域城市总体规模比重的平方和,能够刻画不同省域城市之间相对规模的信息,而前文中已经提及,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赫芬达尔指数能够反映这些信息。第三,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对于大城市的成长和崛起更为敏感,能够捕捉到更多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信息,而在前文中也明显提出了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演进存在着地区差异,因此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路径的差异性信息。如果一個地区存在着中小城市不断崛起成长为大城市的过程,那么原有大城市的比重将会被稀释,城市规模分布将会更为扁平,而赫芬达尔指数则会相对减小;如果一个地区存在着大城市规模不断膨胀的事实,那么大城市的比重将会不断升高,城市规模分布更为集中,而赫芬达尔指数则会更相对变大。
事实上,省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变量设定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之中。本文实证检验所用到的所有变量以及数据的定义都呈现在表1中。
1.数据和变量定义
为了衡量省际经济增长,我们选取“人均GDP”进行测度。根据文献的普遍做法,选取“赫芬达尔指数”(HHI)代表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其中:中国呈现显著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影响巨大,前述文献也进行了相应分析,因此选取“政府作用”(gov)指标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张卫国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王贤彬等:《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刘瑞明、金田林:《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科学》2015年第3期。经济增长伴随着显著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正在日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选取“城市化率”(ubr)指标测度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刘瑞明:《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始终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高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绩效表现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选取“国有职工比重”(soe)来度量地区国有经济水平;刘瑞明:《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刘瑞明:《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对外开放是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契机,在前文中我们对东部地区受益于较早较全面的对外开放,而对城市经济增长以及伴随而生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的作用也进行了阐述,因此选取“对外开放程度”(open)来度量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黄玖立、李坤望:《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毛其淋、盛斌:《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随着教育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因此选取“教育水平”(edu)来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杨建芳等:《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李亚玲、王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差距》,《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经济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东部地区正是受益于对外开放引致的先行工业化,才会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了相互协同分工的的发展格局,引致了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持续向好,因此我们选取“经济结构”(struc)指标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石磊、高帆:《地区经济差距:一个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刘燕妮等:《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越来越高,而投资作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一个手段,其范围与程度自然会影响到对区域经济增长,因此选取“投资增长率”(invest)指标来控制不同地区的投资水平。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郝颖等:《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2014年第3期;范庆泉等:《从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看规模优化》,《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详见表1。endprint
2.实证策略与方法
针对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一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刘学良、陈琳:《横截面与时间序列的相关异质——再论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固定效应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因此,在确定本文采用何种模型之前,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模型设定检验,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准确的结论,因此本文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重点考察解释变量赫芬达尔指数HHI对被解释变量lnpgdp的影响,观测结果是否和预想的一致。
基于此,在参考田超田超:《首位城市过大是否阻碍省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的实证模型: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在回归方程中代表了lnpgdp;X是解释变量,在回归方程中代表了和HHI;下标i和t(t=1994,… ,2013) 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Control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αi表示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 μ是残差项。
3.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利用 stata12.0对上述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赫芬达尔指数及其平方项(HHI、HHI2)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倒U型形态,且不论是否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这一关系始终是稳健有效的,说明存在着一个效率最优的城市规模分布状态,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都明显不利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从模型1到3的计量结果来看,最优的城市规模分布状态应该在0.142~0.168。在模型2与3中,政府作用(gov)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了不同变量以后,这一数值基本没有明显变化,说明回归结果是较稳健的,基本支撑了文献对于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作用的结论;城市化率(urban)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控制了不同的变量之后,这一数值基本上没有显著变化,说明城市化率对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结构(struc)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控制了其他变量,该数值也并未有显著性变化,说明数据考察时期中国进行的工业化历程对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国有经济(soe)对经济发展呈现阻碍作用,但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对外开放(open)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开放程度越高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越有促进作用。在回归中,教育水平(edu)的检验结果出乎意料,竟然呈现了负相关系,这可能与教育因素作为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在短期内不显著有很大关系,同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它也并不显著。投资增长率(Invest)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但回归结果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并不显著。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以人口规模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PHHI),按照模型1-3的方法,重新检验城市规模分布与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观察表2中的4-6列,我们发现以人口为表征的赫芬达尔指数仍然与被解释变量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现稳健的倒U型关系,只不過最优区间相比以经济规模为表征的赫芬达尔指数而言,总体上略小,为0.108~0.142,不过这并不影响模型整体的稳健性。这说明了我们选取的指标,以及采用的实证策略较好地检验了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经济增长效应。
4.进一步讨论
通过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存在着效率最优的结构,即以赫芬达尔指数表征的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在0.142~0.168之间。事实上,回到数据来看,大部分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并没有达到最优效率的结构。我们发现,大部分发展绩效较为良好的省区,都存在着朝向效率最优结构发展的趋势。这也就是说,从时间序列来看,这些发展绩效较好地省区,他们在不断的向着最优区间靠近。而那些发展绩效相对并不理想的省区,则呈现了赫芬达尔指数背离最优结构的趋势。我们将各省区在考察期内的年均人均GDP按照由高到低排列(表2),然后对比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都能佐证我们实证检验的结论。
(1)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排名前半部的省份,赫芬达尔指数呈现了明显的趋优态势。其中佼佼者如内蒙古和陕西,不仅绝对增速方面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5%之上,相对增速方面人均GDP全国排名从中下游跃升前列。江苏省则凭借相对较高的绝对增长率,超越广东、浙江、辽宁三省,一跃成为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一。由于绝对增长率的微弱劣势,福建、广东、浙江、辽宁四省排名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由于增长率的优势,山东省则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人均GDP全国第七的排名。吉林、河南、四川、湖北、山西、湖南和安徽七省凭借相对前列的人均GDP增速,其全国排名都实现了小幅提升。从人均GDP增长率和排名居前的省份的基本情况来看赫芬达尔指数向最优效率区间越靠近,且靠近的速度越快,其经济发展绩效更好。内蒙古、江苏和陕西之所以能够实现增长率和排名的双“逆袭”,江苏和吉林的提升,离不开赫芬达尔指数向着最优结构的快速逼近。内蒙古的赫芬达尔指数从0.112增长到0.127,增长幅度为14%;江苏的赫芬达尔指数从0.111增长到0.131,增长幅度为18%。福建、山东、浙江、广东、辽宁的增长率和排名均出现小幅下滑的原因,也离不开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非趋优化发展态势。河南、四川、湖北、山西、湖南和安徽六省的增长率和排名小幅提升,可以归因于以上六省处于首位城市率和赫芬达尔指数与人均GDP增长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阶段,首位城市发展越迅速,规模越大,赫芬达尔指数越高,人均GDP增长越快。
(2)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排名后半段的省份,赫芬达尔指数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去优化发展态势。探察其中背离优化过程,不难发现:首先,增速后四位和排名大幅度下滑的省区,如黑龙江、云南、海南和新疆,出现了远离效率最优区间的情况。黑龙江的赫芬达尔指数从0.1546增加到0.185,偏离最优区间的上限0.168达到10%,大幅远离最优增长区间;云南的赫芬达尔指数从0.1535的最优区间下滑到0.1326,偏离最优增长区间下限0.142达9.3%;海南的赫芬达尔指数从0.1724快速下降到0.1268,从距离最优区间的2.7%远离到12%。增速靠后但排名相对提升的省区,如青海、宁夏和西藏,出现了赫芬达尔指数远离最优区间,进入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增长负向变动逐步增大的区域。增速相对靠后但名次并未出现变化的省区,如河北、甘肃和贵州,呈现了赫芬达尔指数下降的趋势,也是向着最优的区间逼近,因此相对位次并未变化。
四、结语
当中国新型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经济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核心任务在于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构建有效率的城市体系。但是,何种城市体系是具有效率的?本文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在中国市场分割的背景下,省际经济增长依赖于行政区内部的城市完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分布造就了不同的城市体系,而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发展导致的城市体系的集中或分散趋势,则对省际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经济集聚过度会导致要素边际收益下降,集聚效应降低;而集聚程度不足则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正外部性,导致规模经济效应的损失。因此,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来看,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本文利用中国1994-2013年省际城市规模分布的数据,验证了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发现了城市规模分布促进省级经济增长的最优区间。从赫芬达尔指数来看,最优区间为0.142~10.168。从中国各省区实数据来看,绝大部分省区在考察期内均没有达到最优增长区间,但增长绩效较好的省区则有着明显的趋优化过程。
从当前中国经济“降速换挡”的实际着眼,中国已经走到了必须切实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节点,在人口红利消散和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必须进一步优化新型城镇化战略。本文的工作为优化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针对地方政府通过配置政治性资源而影响其他要素配置的行为,国家必须坚持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重新评估各项行政审批的必要性,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通道,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针对首位城市通过空间扩张和政策红利不断创造要素集聚边际收益的“虚高化”,必须破除首位城市超常发展的政治基础,剪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保障区域经济增长回流效应机制的实现,从而扭转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的制度基础,尽可能提升首位城市的承载能力,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