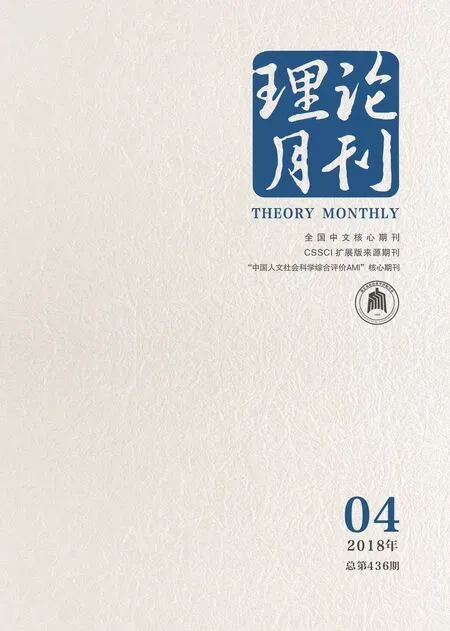荀子为何要言性恶?
——荀子人性论的一种发生学考察
2018-03-08□陈林
□陈 林
(广西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近年来,荀子的人性论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大批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荀子的人性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地探究,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观点。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荀子性恶论内涵的解读上,而且这种解读多是积极为性恶论正名,反对把性恶论理解为人性本恶。但学者们对于荀子为何要言性恶却用笔不多。丁为祥有言:“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1](p35)同样,荀子的性恶论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它也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结晶。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析荀子为何要言性恶,对于我们理解荀子的人性论以至于其整个思想体系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即欲尝试从发生学的角度探析荀子为何要言性恶。
一
孟子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马克思也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p121)一般说来,思想家建构思想学说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会受到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作为个体之人的思想家,其所处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其思想形成的土壤,而其建构的思想学说也是为了回答时代问题、解决时代困惑。二是会受到当世学术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思想学说也会受到当世学术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因革损益的历史链条,并且体现出当世学术思想的特点。因此,我们要了解荀子的性恶论,也必须了解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
从时代背景来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急剧地变化发展着,即使与春秋时期相比,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对于战国时期的新特点,《战国策·叙录》曰:“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顾炎武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日知录》卷十三)。从学术思想来看,战国之世,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各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庄子·天下》)。班固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由此可见,与孔子之世相比,荀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大道沦丧、王道衰微,列国争雄、战争不休,礼乐崩坏、仁义荒怠。面对这样的时代,思想家们纷纷给君王开出了治国理政之方,给世人提出了安身立命之法。由是,儒、道、法、墨、名等学派风起云涌,跌宕起伏。
如果把战国时期的政治和学术对接起来,可以发现贯通两者的桥梁就是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急功近利的风气弥漫于整个社会,各国君王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另一方面,各家建构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实现社会正理平治和个人安身立命提供一套治道①先秦儒、道、法、墨等家虽然思想旨趣不同,但都是以为社会提供治道为其思想的落脚点,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淮南子·氾论训》曰:“百家殊业,皆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一家之学说如能得到统治者认可,便会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不会被统治者所采纳。这点从孟子见梁惠王之事就可窥见一斑。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相问,孟子对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最终,“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如黄俊杰所说:“这绝不是偶发事件,它反映了日益壮大的唯利是求的历史趋势。”[3](p6)面对这一历史趋势,孟子所采取的办法是积极与之斗争,强调“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子为什么要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从某种意义上看,孟子的一生就是同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做斗争的一生。孟子见梁惠王之事鲜明地反映出战国中期功利主义思潮的泛滥。而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的崛起正是此功利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
面对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道、墨、法等学派的崛起,儒家思想面临着极大挑战。赵岐有言:“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齐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孟子题辞》)。这说明,孟子的学说在当时并不受统治者的欢迎,被统治者认为是迂阔之言。孟子自己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其中的原因显然就在于,在统治者眼中孟子的“以仁心行仁政”的思想并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从理论上看,这亦表明,“儒家学说已经与战国后期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脱节。为发展儒家学说,实现儒家理想,儒家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关于道德培养与仁政的学说必须加以修正才能更加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否则,儒家学说在战国时代就不能生存下去,更别提繁盛了”[4](p3)。荀子自觉地承担了发展儒家学说这一历史使命,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发展儒家学说。这从谭嗣同“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5](p337),梁启超“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6](p56)之判断即可窥见一斑。
那么,荀子是怎样发展儒家思想呢?荀子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儒家思想如何有效应对功利主义思潮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荀子采取的方法是自觉与当时的功利主义思潮相对接,把其融入儒家思想当中,发展出儒家式的功利主义思想,以使儒家思想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①荀子是赵国人,而三晋则是以功利主义著称的法家的诞生地。这也是荀子自觉吸纳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因。再放大一点看,战国末年,各家学术思想逐渐走向融合,荀子的思想正是学术融合的具体表现。对此,梁启超言:“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学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庄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韩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4)。王邦雄言:“荀子思想正处在儒法之间转变的关键点,且贴近礼法并重的齐学理路,更贴切地说,他出身于三晋,游学于齐,又终老楚地,兼有法、阴阳与道三家的色彩,也消化了三家的思想特质,成就了迥异孔孟而自成一家的儒学”(王邦雄.由老庄道家析论荀子的思想性格[J].鹅湖学志,2001(12):9)。另外,不少学者注意到荀子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因素。如,冯友兰说:“在荀子的心理学中,只有能虑能知之心,及有求而须满足之情欲。心节情欲,立‘权’‘衡’以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焉。荀子学说在此方面,盖与墨家之功利主义,完全相同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2)。“以功利主义说明社会国家之起源,而与一切礼教制度以理论的根据;与《墨子·尚同篇》所说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5)。但冯友兰又指出:“荀子亦重功利,与墨子有相同处,但荀子对于情感之态度,与墨子大不相同。墨子以其极端的功利主义之观点,以人之许多情感为无用无意义而压抑之,其结果为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虽亦主功利,然不如墨子之极端,故亦重视情感,重用亦重文,此可于荀子论丧祭礼中见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8)。徐复观亦言:“荀子以调节欲望与生产的关系来说明礼的起源,亦即以经济来说明礼的起源,已经深入到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最足以看出其思想上的经验的,功利的性格”(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2:458)。。与孔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不同,当秦昭王认为“儒无益于人之国”时,荀子指出儒家之学说“在上则美政,在下则美俗”(《荀子·儒效》),儒者“在人上为王公之财,在人下则为社稷之臣”(《荀子·儒效》),强调儒家有益于国家社会。事实上,荀子并不讳言“利”,且常常以“利”作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我们从荀子的核心思想“礼义之统”即可窥见其对“利”的重视。荀子之所以隆礼义就在于在荀子眼中礼义具有教化人心、平治社会中的功用。对于礼义的作用,荀子言:“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礼者,养也”(《荀子·礼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荀子·礼论》)。“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荀子·王霸》)。“上不隆礼则兵弱”(《荀子·富国》)。此都是从礼义之功用言礼义之价值。在荀子看来,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义在本质上蕴含着最大“利”,人若能按礼义思考行事自然就能带出“利”来。这也表明,荀子强调礼义对人及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从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而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判定的。另外,荀子在《正论》篇中做出“义荣”与“埶荣”“义辱”“埶辱”之区分②《荀子·正论》曰:“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就是强调人具有追求尊严与荣名的社会情感需求,人最高的价值就是“义利双收”。所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亦是强调,追求个人利益与实现社会正义并不冲突,人的最高价值就体现在把促使社会实现正理平治与个人获取历史荣名统一起来。还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于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各种功利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如,《荀子·富国》专论经济,《荀子·王制》《荀子·王霸》《荀子·君道》《荀子·臣道》专论政治,《荀子·议兵》专论军事,《荀子·致士》专论用人,《荀子·儒效》专论儒学的作用。这些论述有效地回应了那些对儒学功用提出质疑的言论,阐述了儒学在社会治理中的实用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所强调的功利主义与法家和墨家的功利主义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法家和墨家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那么荀子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功利主义①毛朝晖将荀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定性为一种广义的功利主义(参见:毛朝晖.《荀子》中的两种文化:荀子思想的基本性格及其思想史的诠释[D].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2009:16)。。法家和墨家的极端功利主义只注重经济、军事等外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功”和“利”,把人的情感完全看作是物质利益刺激而导致的条件反射。荀子的广义的功利主义则强调“利”和“文”的统一,在突出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注重人的情感需要和礼乐的人文化成作用,是一种儒家式功利主义②荀子注重人情感需要的满足与孟子对“四端之心”的强调是有差异的,其依然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从《荀子·礼论》关于“三年之丧”的论述即可窥见一斑。《荀子·礼论》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将由夫愚陋淫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这是《荀子》文本中少有的关于情感的表述。这里,荀子一方面认为丧礼是人的爱亲之情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强调爱亲之情的表达又要有所节制。而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情感的节制,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社会实现“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可见,荀子即使对最具本真情感的丧礼亦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阐述的。对此,钱穆敏锐地指出:“荀子着眼人类群体生活上来阐述儒家‘礼’之精义。外面注意物质经济条件,内面注意情感需要条件”(钱穆.中国思想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57)。其又言:“皆是人群面对物质生活之所需,而非发源于人与人相处之一片深情厚意而始有,此为荀子与孔孟之相异处”(钱穆.中国思想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62)。。此正如毛朝晖所说:“荀子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礼乐教化,从礼乐教化的角度来讲政治,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军事。他一面回应战国的功利政治文化,积极地丰富儒家的经济、军事等实用元素;另一面又通过对强国政治经验的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功利政治的缺陷,力图拓展功利的内涵,提倡礼乐的政治价值。简言之,荀子的用心其实是试图用战国功利政治的论述来阐扬西周礼乐政治。”[7](p29-30)
二
当荀子以一种儒家式功利主义思想去思考问题时,其必然把自然世界看成一个平面的存在,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经验与历史的存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经验界的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功”和“利”,而不去思考所谓的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意义的或理想的世界。所以,荀子直言:“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这种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功”和“利”的做法使得荀子的思想表现出很强的经验性格。对于荀子的经验性格,陈登元说:“荀子之真精神,以吾观之,即在切实二字上也。”[8](p6)徐复观则说:“欲了解荀子的思想,须先了解其经验的性格。即是他一切的论据,皆立足于感官所能经验得到的范围之内。为感官经验所不及的,便不寄与以信任。”[9](p196)王庆光言:“孟子体系近乎唯理论、转向内在仁心、善性的深化,荀子则是经验派思想家,对‘理’作为‘礼’之本原发现和诠释:‘义,理也’(《荀子·大略》),‘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乐论》),将‘礼’的本原植根在客观而实在的‘理’之上……”[10](p21)吴汝钧则从荀子的认识论与逻辑学上的特点而指出其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他说:“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倘若在认识论和逻辑方面具有成就,但却缺乏纯粹的理论的,形式的思考的兴趣,而强调知识与逻辑的实效,实用方面的性格,则他的现实感通常是很强的,对事物的实然的、现实的面相会很重视。即是说,他会留意事物的经验的性格,或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来观察,以一种平看实然的方式来对待事物,而少注意应然的、理想的,以至于超越方面的问题。即是说,他比较缺乏逆觉的、反省的兴趣,而喜欢以顺取的观察方式来看事物。这便有经验主义的倾向,注意事物的现实的、现前的经验性格,不太留意它们的超越的、理想方面的根源。”[11](p474)正如上述四位学者所言,荀子十分强调现实和经验。荀子言:“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荀子·性恶》)“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具而百陷也”(《荀子·儒效》)。这正是强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参与都必须以现实的经验世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能在经验现象中实践和检验我们的认知和参与。
从学术思想上看,荀子思想中的经验主义也与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毛朝晖指出,战国之时,中国的学术思想兴起了本体论思潮和知识论思潮,而荀子的思想是对这两股思潮的一种反动,而此反动的动力就是荀子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此功利主义思想引申出来的经验主义思维①参见:毛朝晖.《荀子》中的两种文化:荀子思想的基本性格及其思想史的诠释[D].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2009:62-110.。所谓“本体论思想”,是指战国时期一些学派掀起了一股从本体上讨论“道”与“性”的热潮。具体说来,道家的老子和庄子提出了本体论意义的“道”,而儒家的孟子通过把“性”界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建立起本体论意义上的性善论。所谓“知识论思潮”,是指各学派广泛关注“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具体说来,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主张“绝圣去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强调要通过一种“静观玄览”“心斋坐忘”的方式来实现对“道”的体认,并强调对“道”的体认才是最高的知识。孟子则突出“知性”,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后期墨家的《墨经》则从形式逻辑的视角探讨了知识的来源、类型以及检验标准。名家的惠施则认为一切经验认知皆不可靠。而公孙龙则彻底颠覆经验知识,主张完全依靠形式逻辑来确立知识,试图在实体世界背后建立一个所谓的纯粹的概念世界。
不幸的是,此本体论思潮和知识论思潮碰到的是更强大的功利主义思潮。在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此两股思潮走向了衰落。在荀子所处的时代,不论是在政治家眼中还是在思想家眼中,那种对天道、性命之类问题的探讨实无益于实现国家富国强兵和社会正理平治。由是,从形而上的高度来探讨天道、性命的方式不再被思想家们所关注和接受。而名家那种高谈阔论更是与“功”和“利”毫无关系。名家也就很快就后继无人,以至于消亡了。基于发展儒家学说的目的,荀子亦对“本体论思潮”和“知识论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而尝试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来建构思想体系。通读《荀子》文本,我们能很容易地感受到荀子思想的经验性格。荀子主天人之分,乃是为了强调人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荀子·天论》),而在经验世界中积极发挥“人有其治”的“能参”之用以参与天地之生成化育。荀子对人性善恶的判定也是基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而做出经验式的归纳。荀子政治上的思想(如,“法后王”说、“王—霸—危—亡”说)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基础上。荀子作《正名》是对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提出的那种悖离日常经验的知识的批评,而强调知识要回归现实经验。荀子的经验性格正是在这种反思和批评中形成的。对于荀子的这种反动,徐复观曾言:“荀子则将道家思辨性之形而上学,完全打掉。”[9](p198)吴汝钧则言:“荀子的认识论与逻辑……有一个特点,即是,他的知性旨趣并不纯粹,而是带有很浓厚的实效或实用倾向。他论我们的所知,把焦点放在道方面,而他的道,客观真理的意味并不浓,而倾向于伦理的规范义。而他的逻辑,主要只就名实的关系而言,社会功能的意味很重。他并未涉及对概念、命题的纯粹性格的讨论,也未有提到推理的问题。故他虽有认知旨趣,但理论的和形式思考的兴趣却不重。”[11](p474)上述两位学者可谓各从一个点揭示出了荀子对战国时期的本体论思潮和知识论思潮的反动。
三
前文说到,在功利主义的刺激下,荀子关注的是现实的经验世界,并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平面的世界。而在平面的世界里,万事万物之间就是一种“关系”的联系,而不是一种“神秘”或“本质”的联系。所以,荀子不采取宗教或形上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直接就事物在经验现象中的具体存在来言说世界。在这种思维下,荀子认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人是一种“群”的存有,而在这种“群”的生活中,个人通过参与生活而得到了对世界的某种认识,世界也在此生活过程中向人呈现了某种意义①《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在群体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就表为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所蕴含的人类学意义就是其所言的“礼”。所以,一方面,既然荀子把人作为“群”的存有,其就不会给人预设一个先在而超验的本质。对比孟子,我们可以发现荀子几乎不曾就人之作为个体之纯粹面上论人或人性;反之,荀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后天存在决定的,人有什么样的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本质。另一方面,荀子极其重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强调“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礼的实质就是人类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的集合体,是人类的最高“记忆”。
基于荀子对人的这种理解,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为什么会建构起一套与《中庸》、孟子不同的“天人关系”。事实上,荀子仍是从传统的“天人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相对于《中庸》、孟子以天道(天命)作为人之价值本源的宇宙观,荀子的宇宙观乃直接以礼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来统摄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礼者,人道之极也”即是荀子思索“天人关系”而形成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意义也就是强调礼的人文价值——使人类社会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之上成就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生活世界”②从“天人关系”的面向看,荀子的礼论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一种宇宙观。把礼作为道德价值的根源,就是一种与“天命(天道)宇宙观”相对应的宇宙观。伍振勋把荀子的这种宇宙观称之为“礼宇宙观”(参见:伍振勋.语言、社会与历史意识:荀子思想探义[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11-69)。。
正是由于礼是“人道之极”,荀子即以礼为基础来构建思想体系。此正如韦政通所说:“荀子思想系统的中心理念即‘礼义之统’……荀子思想的主要部分,即是以‘礼义之统’为基础,并于礼义效用的思考中,决定了礼义与人,与事,与天的关系;这一关系确定了,性、天的意义也就同时确定。这种由客观礼义的效用问题,导引到天人关系上来的思考方式,即是由荀子思想系统的特质所决定的方式。”[12](p47)荀子正是以韦政通所言的“于礼义效用的思考中”来阐释人的存在。对荀子而言,人之存在表现为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共生共存。一方面,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万物一样具有自然属性,自然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生命不足以凸显人之为人的高贵性,人应该而且能够超脱自然生命之局限,人区别于动物之根本在于人是“礼义化”的文化生命体。用荀子的话来说,人不仅仅是“性”之人,亦不仅仅是“伪”之人,而是“性伪合”之人。
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正是建基于其儒家式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人是“性伪合”之存在的判断,而其对“性”和“善”“恶”内涵的理解以及对“性恶”的论证又体现出儒家式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
对于孟、荀言“性”之差异,劳思光言:“所谓‘性’,在孟子原指自觉心之特性讲,意义略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谓之‘Essence’。”[13](p121)“孟子以为,人与其他存在有一不同之条件,此条件称之为人之‘性’。而此条件非他,即‘有价值自觉’是。”[13](p251)“荀子之论‘性’,即纯取事实义……其所谓‘性’,乃指人生而具有之本能。但此种本能原是人与其他动物所同具之性质,绝非人之‘Essence’,故在开端之处,荀子立论即与孟子之说根本分离。荀子所言之‘性’,并非孟子所言之‘性’也。”[13](p251-252)劳思光此言正是我们通常的观点——孟子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视角言性,而荀子则是从传统的“生之谓性”的视角言性。但笔者认为,笼统地说“荀子所言之‘性’,并非孟子所言之‘性’也”是不够缜密的。事实上,要完整理解孟、荀之“性”必须从性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切入①孟、荀对“性”概念内涵的理解与对人之性是善还是恶的判断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许建良所说:“性的善恶并没有回答本性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回答的仅仅是本性在价值判断天平上所显示的性质”(参见:许建良.荀子性论的二维世界[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4)。。而孟、荀两人对性之形式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对性之内容的理解有差异。
首先看孟子对性之形式与人性之内容的理解。正如梁涛所说:“从孟、告之辩来看,孟子对于‘以生言性’传统并非一概否定,而只是对告子关于‘生之谓性’的具体理解提出批评。”[14](p36-42)所谓“孟子对于‘以生言性’传统并非一概否定”就是指孟子对性之形式的理解依然是基于传统的“以生言性”的方式,认为天生自然之种种就是性。这就是说,告、孟是在“以生言性”这一共同的语境下来谈论人性问题的。如果告、孟之间对“性”的形式内涵的理解没有任何交集,那么,他们之间就是完全不同的语意体系,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毫无意义。事实上,当孟子讲“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时,即是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生而自然本有的。对于这两句话,我们多把注意力放在作为性的内容的仁义礼智上面,而往往忽略了这两句话背后所渗透的对性之形式的理解。所谓“关于‘生之谓性’的具体理解”就是指性之内容了。孟子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其对性之内容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把食色作为性之内容的做法,而把仁义礼智纳入性之内容。具体说来,孟子是通过“性命分立”的做法把仁义礼智纳入性之内容的范围②《孟子·尽心下》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而仁义礼智一类之德性无法在经验现象中直接证实,所以孟子又从人心的真情流露处来提点人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以心善言性善”。而当孟子要把在经验现象中无法把握的仁义礼智纳入人性之内容中时,其必然就会采用《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形上方式来为仁义礼智寻找一个超越的存在根据。在孟子看来,此“非由外铄”的仁义礼智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而人通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方式就可以体悟到天之所赋予人的美好德性。
再看荀子对性之形式与人性之内容的理解。当荀子言“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时,其依然是从传统的“以生言性”的视角来界定性之形式内涵,认为凡天生自然、生就如此、表现为素朴之材质皆属性。但是,在对人之性的内容的界定上,荀子则背离了孟子的理路而回到了以告子为代表的传统的理路上来,以人在经验现象中所具有的种种天生自然的反应、需求和能力为性之内容。具体说来,荀子认为人生而具有的反应与需求(即“情”和“欲”)和人生而具有的能力(即“知”和“能”)符合性的形式定义,因而是人之性的具体内容。对于荀子对人之性的界定,徐复观言:“荀子发挥了‘食色,性也’这一方面的意义,更补充了‘耳明而目聪’的另一方面的意义。”[9](p206)因此,从告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三人对人性之内容的理解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问题是,荀子为什么要回到传统的以食色为人之性的内容的理路呢?前文引《荀子·儒效》“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一句。对于此句话,徐复观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恻隐之心,只能由反省而呈现,不能由见闻而得;荀子说‘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这实际是反驳孟子由反省所把握到的内在经验;而说明他是完全立足于见闻为主的外在经验之上。”[9](p196)如再放大到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一现象表明:受功利主义思潮和经验主义思维的影响,战国后期的思想家不再热衷于讨论人性的依据。
荀子对“善”和“恶”理解更是体现出经验主义的特点。《荀子·性恶》言:“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可见,荀子把“善”定义为正理平治,把“恶”定义为偏险悖乱。《荀子·不苟》言:“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可见,在荀子眼中,符合礼义就是社会安治,违背礼义就是社会混乱。把上述两段话结合起来看,荀子实认为,“善”就是指社会存在状态符合礼义之道,并且表现出一种“正理平治”的良好状态;“恶”就是社会存在状态违背礼义之道,并且表现出一种“偏险悖乱”的混乱状态。由此可知,荀子对“善”和“恶”有着不同于孟子的特殊理解,其不像孟子那样从人之行为的动机来言善恶①《孟子·告子上》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一般认为这是孟子对“性善”的一种定义。“其”是指“性”,“情”乃“实”之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只要顺着本有之性之实而行,则所发动之行为就是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善。,其是从人之行为的结果来言善恶。这就是说,荀子是从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对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影响来言善恶的,换句话说,荀子是基于后天的经验事实来界定人性之善恶的。
正是基于上述对人之“性”以及“善”和“恶”的理解,荀子做出了“性恶”的判断。通读《荀子·性恶》篇,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荀子言性恶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实际生活状态而做出的经验式的把握。《荀子·性恶》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此人之性情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姿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几段话鲜明地反映出荀子论证性恶的思维方式。“今人之性……”“今人……”“今之人……”一类之语句即凸显出荀子做出人性恶的判断是基于人类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一方面,荀子发现,人本有情欲好恶之性,人在自然状态下必然会顺从这些情欲好恶之性,并且事实也证明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顺从人之情欲好恶之性,进而使社会出现“偏险悖乱”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荀子发现,人要做到不顺从人本有的情欲好恶之性则必须借助于礼义教化,并且事实也证明用礼义来教化人可以使人成为君子,进而使社会呈现“正理平治”之良好状态。
基于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荀子直接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批评。《荀子·性恶》言:“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所谓“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正是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不符合现实情况,无法在现实中得以检验和实施。而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也正是认为孟子的思想无经验性。
最后,回到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的现实情境,我们就能同情地理解其为什么要言性恶。战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各国的争霸兼并战争不断。与春秋时期的战争相比,战国时期的战争更为激烈残酷。春秋时期大的战争通常只有一场战役,而且这一场战役几天甚至一天就结束了;而战国时期一些大的战争往往发动了几十万兵马,且持续数年。《战国策·赵三》言:“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可窥见一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学者,不能不考虑社会的安定与天下的统一,思索如何结束战争,天下和平。对战争与和平秩序的思考成为战国时期思想家的重要课题。”[15](p17)事实正是如此,战争问题也是荀子思考的重要课题,荀子专门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并作《议兵》来论述战争。而战国末年那些惨烈的战争对荀子的刺激也是巨大的。面对着长平之战那样惨烈的杀戮,荀子实难以相信人性是善的。正如王先谦所说:“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集解·序》)。
参考文献:
[1]丁为祥.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J].哲学研究,201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黄俊杰.孟子[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4]孙伟.重塑儒家之道:荀子思想再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谭嗣同.仁学[M]//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毛朝晖.《荀子》中的两种文化:荀子思想的基本性格及其思想史的诠释[D].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2009.
[8]陈登元.荀子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0]王庆光.荀子与齐道家的对比[M].台北:大安出版社,2014.
[11]吴汝钧.荀子的知性旨趣与经验主义的人性论[J].能仁学报,1994(3).
[12]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J].哲学研究,2007(7).
[15]陈荣庆.荀子与战国学术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