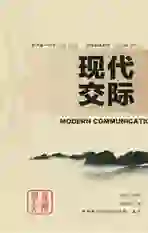论《雨王汉德森》中的非洲风情
2018-03-07陈子豪高艳梅
陈子豪+高艳梅
摘要:《雨王汉德森》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贝娄的名篇,它展现了主人公逃离现代社会,投入原始部落生活的经历。本文以《雨王汉德森》为蓝本,探讨相关的文化问题——非洲部落风情。讨论分为非洲部落原始生存状态、非洲礼仪、非洲人的婚俗习惯,以期增进对非洲的了解及探索全球一体化话题。
关键词:索尔·贝娄 《雨王汉德森》 非洲部落风情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4-0132-02
索尔·贝娄,美国作家,曾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时学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丰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1976年索尔·贝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认为“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这句评语在《雨王汉德森》中得到了体现和验证,贝娄对非洲风俗的研究十分深入,尤其是对非洲整体文化心理有着精妙的分析。《雨王汉德森》对非洲部落的政治、婚姻、礼仪、服饰、建筑、饮食习俗有着具体生动的描写,从而使这部作品丰富而厚重。《雨王汉德森》写了百万富翁汉德森在非洲的一系列离奇经历,书中主要展现了非洲内陆阿内维人和瓦利利部落的生活场景。作者巧妙地将非洲的风土人情和故事情节糅合在一起,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让人了解了非洲的习俗和文化心理。社会习俗、風土人情是了解非洲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学的重要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本文将随着故事的发展解读原始状态的非洲的风土人情。
一、非洲部落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
非洲部落处在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也是世界上部落最多的大陆,大大小小共有2000多个部族,这些部族使用不同的语言,保持着不同的礼仪、宗教信仰和情趣爱好。原始部落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社会处在自然生存状态中,这是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然界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雨王汉德森》所描写的非洲就处于原始、自然的社会场景之中,非洲部落人群有自然崇拜的情节,宗教的偶像崇拜也含有崇尚自然的含义。在《雨王汉德森》中作者描述部落的神像时写道:“在他们眼里这些表情严肃的神祇,是有尊严的——十分神秘;他们都是神,他们掌管着命运。他们驾驭空气、山脉、火、植物、牛群、运气、病痛、云彩、生育、死亡,如山神胡迈特和云彩女神门玛。”非洲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都显现出崇尚自然的文化心理。
非洲的国家、部落、族群的政治体制构成原始而简单,非洲各部族主要由世袭的酋长、国王(国王有男性,也有女性)来统治。《雨王汉德森》中描写的就是这种统治形式,阿内维人由女王来统治,瓦利利部落由男性国王来统治,两国国王性别的不同,体现了非洲内陆政治形式的差异和多样性。阿内维人呈现出原始母系社会的特点,女王威拉塔莉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宗教、政治、生活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被尊为圣者;瓦利利部落却正好与之相反,它是由男性国王充当政治、宗教领袖的,书中描写的瓦利利国国王达孚勇武有力,具有狮子般的体魄和坚强意志,而且他在文明开化地区接受过教育,这让人感受到非洲统治阶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非洲部落的原始性还体现在生产方式上,他们主要从事原始的狩猎、畜牧或种植业。例如,阿内维人就以养牛为主;瓦利利人除了狩猎之外,也种植蔬菜。原始部落的居民们在这些首领的领导下。从事生活、生产、宗教、娱乐等社会生活,在非洲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形成了独特的人文风情。
非洲人对自然的崇拜体现在对动物的爱护中,如书中描写阿内维人对牛的崇拜就十分有趣。《雨王汉德森》中阿内维人对牛非常重视,他们并不把牛视为家畜,而是把它们当作亲人对待,这里禁食牛肉,他们放牛不是一个孩子看一群,而是每头牛都有两三个放牛娃跟着。一旦牛受了惊,放牛娃们就追上去,哄它一番。大人们就更加爱护牲畜了,牛死去了,他们会痛苦不已。哀悼在旱灾中死去的牛时,他们认为旱灾的发生是由于自己的过错——得罪了上天,或者干了坏事。书中描写到,当一头牛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人会拿着笨重的大木梳,梳着厚厚的盖在牛角间隆起部分上的额毛。人会轻轻地拍它,搂它,凄凉地梳着牛毛,人畜双方都笼罩在绝望的气氛中,人们爱家畜就像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亲生子女那样,这里显现出人与动物间的深厚感情。对牛的重视和崇拜,还体现在部落的语言文化中,例如,描述不同形状的牛角的词有五十多个;形容牛的脸部表情的词有好几百;说明牛的动作的还有成套的词汇。作者从饮食上揭示了阿内维人对牛感情如此深厚的原因:牛奶是阿内维人赖以生存的食品,除此以外,他们不喝其他饮料,所以母牛是他们的命根子,平时他们从不吃牛肉,除非母牛自然死亡,在祭祀时才象征性地吃一点。即使如此,他们也认为这是同类相互残杀的行为,所以都是噙着眼泪吃的。死了牛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死了牛的那一家人,每天都为死牛举行临终仪式,而且边哭边吃牛肉,所以他们如此悲恸是一点不奇怪的。
即使是现今非洲的毛里塔尼亚人仍然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重视牲畜,毛里塔尼亚人在互相问候的同时,还常常问候对方“羊怎么样”“牛和骆驼好不好”等话,这些都是非洲人重视自然的传统心态。非洲人亲近自然、尊重生命,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这种淳厚的民风。
二、非洲人的婚俗及日常生活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非洲婚俗一般是一夫多妻制,但也有一妻多夫的情况。一般男子具有无限制娶妻的权力。小说中提到国王的嫔妃数量很多,亲王级的人物——伊特罗和达孚国王的叔叔都是妻妾成群,他们的妻子都是没有定数的,如同私人财产一样,这些是非洲原始而落后的婚俗体现。而小说中的阿内维人带有母系社会的色彩,更为奇特的是女王威拉塔莉不仅多夫,而且多妻。妻子们称她丈夫,孩子们既称她父亲,也称她母亲。她已经超越普通的“人”的局限,她的性别是可以转换的,因为她在很多方面都证明了比别人高超,所以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局限。在这个部族里,女子和男子结婚时,女子要给男子彩礼,例如女王的妹妹爱上汉德森后,就会主动求婚,带来丰厚的彩礼,这不能不说是极有特点的婚俗习惯。endprint
衣食住行方面,处处体现了自然条件对部族民风的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景观。非洲人的衣饰都是根据生存环境就地取材,例如植物、动物等。非洲狮是非洲的特产,所以用狮皮为面料做的服装在《雨王汉德森》中出现了。而且在这里,服装也是任务等级地位的象征,《雨王汉德森》中的女王“身上挂了一张狮皮,狮皮的最宽处,不如一般人所意料的披在她的胸前,而是披在她的背上,尾巴从她的一肩挂下来”,这是标准的非洲酋长的装扮。狮子是非洲的代表,也是非洲人民崇拜的自然的偶像,它勇敢有力,无所不能,因此穿上狮皮做的衣服有如中国皇帝的龙袍,只有王者才能独享此尊荣。
祭祀是非洲部落中的大事,其服饰也很有特点,例如,小说中写道:“在求雨的祭祀上,年轻妇女往佩戴的牛角上涂金粉,还互相涂抹打扮,插上鸵鸟和兀鹰的羽毛等饰物。有的男人在颈上挂一串死人的下颚骨制成的项圈。神像和一切象征神祇的物品统统被打扮一新,刷得雪白,面前摆着供品。”求雨过程中女祭司的装扮为:上身赤裸,发型是羊毛般的卷发,脸上刺满了漂亮的图案,看上去像盲文一样。两条狭长的疤痕直通左右两耳边,第三条指向鼻梁。上身到腰腹处涂了一层赤褐色或暗金色。男祭司则佩戴着一大把朝四面八方展开的鸵鸟羽毛装饰品。非洲人用颜料和黏土制成化妆品,这些天然的材料体现了非洲人在自然界中发现美、创造美的聪明智慧。
非洲人穿衣习惯也和气候有关,非洲地处沙漠地带,气候炎热干燥,所以书中描写瓦利利人时提到国王的妃子全是赤裸的。书中描写道:“一大群女人,初步估计有二三十个——挤在一起,全是赤条条、肉嘟嘟的女人。”而对女武士的描写,也说她们只穿着皮马甲,显得刚柔并济。天然的肌肤让人感受到了非洲崇尚自然的审美观,与崇尚苗条的骨感美不同,非洲女人崇尚以肥胖为美。例如,阿内维人女王的妹妹姆塔尔芭胖极了,尤其是胸部,鼓鼓囊囊,肥得连皮肤都撑成粉红色了。非洲有些地方的妇女都要养得这样胖,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美人。化妆的颜料也是取自天然植物,姆塔尔芭的手指用指甲花染了色,头发涂上靛青染料,硬邦邦地矗立在头上。不要以为非洲人都是这种土著一样的打扮,瓦利利人的国王达孚的穿戴就有文明开化人的特征,书中写道:“他穿着紫色绉绸的裤子,戴着一顶相当大的宽边帽,是紫色的,和他穿的短裤一样,不过这是用天鹅绒做的。帽顶上有人的牙齿,以保护他免受邪恶的眼光的伤害。”
非洲人在饮食上丰富多彩。贝娄对瓦利利宫廷的食品的描写,体现了非洲人食谱的丰富,也很特别。他提到了饮品是掺有鲜牛血的牛奶,牛奶是阿内维人和其他非洲人喜爱的食品之一,可是这里的吃法卻非常有特点。书中居然还提到有用糖浆蘸食的老鼠脚掌这种奇特的食品,不读贝娄的小说恐怕难以知晓。此外,还有枣子、菠萝、彭波酒、冷甜薯和其他食品。
非洲部落人们日常的娱乐生活富有情趣,书中写道:“年轻妇女中有些人往往整整一小时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线在玩翻绞绞。每一对玩游戏的人一般都有好几个观众围着。每当有人翻出一个极其复杂的花样时,观众就喝彩叫好,‘哦哨!旁观的妇女们这时将臂弯交叉起来,双手轻轻拍打着。这是她们鼓励的方式。男人们则将手指插在嘴里,吹起口哨,有时一起合奏。”即使在庄严肃穆的祭祀场合,也有游戏表演,书中提到“非常像美国的杂耍戏”。如,有一个老妇人同一个侏儒摔跤,或是轻松的表演,两个家伙互相用鞭子抽对方的腿,逼得对方腾空跃起。非洲生存环境的恶劣并没有使他们失去快乐的天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学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非洲的原始美、野性美和人情美,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非洲长存的力量源泉。《雨王汉德森》是一部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它将知识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在一起,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索尔·贝娄作为人类学家的严谨和缜密,作为作家书写生活的张力,并为我们展现了非洲特有的风土人情。虽然《雨王汉德森》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距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通过对这部小说多侧面的解读,仍可以增进对非洲的了解,激发我们探索、接近非洲的愿望。
参考文献:
[1]艾周昌.非洲黑人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英)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2.
责任编辑:于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