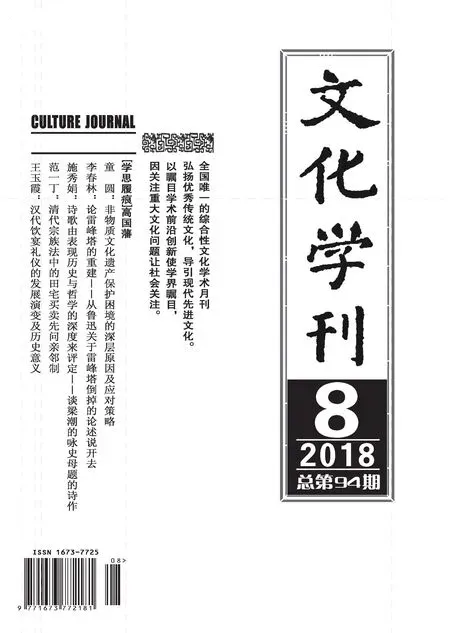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施状”演变探析
2018-03-07王业朝
王业朝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施状”一词,散见于各类典籍中。其作为一种文书,历史亦十分久远,常见于各类记载中。目前,学界对“施状”的研究还很少,也不系统,仅有贾敬颜的《金代的“驱”及其相关的几种人户》[1]、公维章的《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2]、张国庆的《辽代的寺田及相关问题研究》[3]、李静杰的《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4]及杜洪涛的《金代公共资源问题的一个侧面——以中都大兴府栖隐寺与三家村的“山林”之争为例》[5]等五篇文章中有所提及,且对“施状”的格式、用途、演变等问题也缺乏深入探讨,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故本文以宋朝至清朝中期的档案、碑记及地方志等文献中的数份“施状”为史料,对“施状”的基本演变作探究。
一、“施状”的渊源
“施”,有给和给予之意;“状”,文体的一种,是向上级陈述或申诉的文书[6],“施状”,即是一种赠与行为的文书。作为文书,其起源甚早,但历代对其记述甚少,仅在少量碑刻或档案等史料中略见。就现有所见资料来看,“施状”最早或出现于宋代,至元明两代发展,在清代趋于成熟。
辽代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行状碑》中刻记,辽代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归常住,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口器用等物,皆有施状”[7]。而在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所录碑刻中见“及天会九年(1131)有住持普大师将未抚定以前元为主,旧仰山寺道院等四至山林,施每故青州长老和尚为主。其山林系是本寺(栖隐寺)山坡,见有施状碑文”[8]。同时,在陕北一处金代石窟佛坛左前柱正面题记中出现“施状”[9],而在金人刘方《施地碑记》中则详细记述了其将自家地土亩垄布施与山西禅隐山崇胜寺,恐无凭据,故立施状。[10]
可见,宋辽夏金时期的“施状”主要是捐施者与寺院之间订立具有“契约”功能的文书,此时的“施状人”很少将“施状”作为一种捐施凭证来参与诉讼,仅有《宛署杂记》记载因为田土纠纷而使用到了“施状”,而此时的“施状”主要是作为契约来佐证寺院的田土来源是否合乎规范。同时,此时的“施状”,其捐施者大多出于政治考虑将田土捐施,而受施者基本上都是寺院或者寺院僧人。
从笔者所掌握的“施状”材料来看,“施状”在宋金辽时期已经是一种较常见的捐施“契约”,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清代的“施状”虽然还用于捐施,但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施状”的演化
“施状”作为从宋辽夏金时期就出现的文书,随着朝代更替,其主要功能一直是捐施,但其特点及性质则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然而在笔者所见史料中,元明两代的“施状”多为散佚,仅在乾隆《孟县志》中的《元宣慰同知甯德祖舍田碑记》[11]中记载有甯德祖将自家院地尽施,写立施状文字两份,一份烧献神明,一份留存于社。故本文主要比较宋辽夏金时期与清代“施状”的异同,认为“施状”的演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捐施者。宋辽夏金时期,捐施者的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既有辽代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一类的贵族,亦有青州和尚一类的僧侣,同时还有诸如金人刘方等百姓。然在《南部档案》中仅见的两份“施状”记载的李茂林父子[12]与宋长洪[13]皆“耕田栽秧”,可见其身份为农民,故清代的捐施者主体是平民,其身份较为单一,捐施者身份呈现单一化的发展。
其二,受施者。宋辽夏金时期,受施者基本为诸如青州和尚、辽代大昊天寺以及宋代陕北黄陵万佛寺等寺庙僧众。而在清代,李茂林为免侵害,将当价钱三十二串施入赈粜局;宋长洪为了逃避车来友等人的控告,自愿将自家田土所当价钱三百七十串充入习艺所,以为公用。受施者则基本成为了赈粜局、习艺所等官方地方机构。受施者由宋代寺庙转变为清代地方机构,这种变化在表面上更像是一种由“私”转“公”的变化。
其三,捐施物。宋辽夏金时期,捐施物的品种更为多元,前引《妙行大师行状碑》中不仅记载有“宅司诸物”,更有“稻畦百顷,户口百家”,可见此时期的捐施物不仅有田土、住宅,甚至还有人口。清代捐施的物品似乎变得更加单一化,清代“施状”中的捐施物主要为当价钱,即钱款。
清代“施状”相较于宋辽夏金时期已经发生了诸多具体的变化,同时“施状”的性质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施状”不再仅仅是捐施者与受施者之间的“契约”文书,同时还拥有了“诉讼”的内涵。清代的“施状”更多出现在了“细故案件”中,同时也是一份具有效力的捐施凭证,即“契约”,其性质从单一的契约文书转化为了具有双重性的文书类型。“施状”这些变化都是受政治、社会状况、法律制度等影响的结果。
前引金人沈榜《苑署杂记》中记到栖隐寺僧众将寺院山林等施以青州和尚的目的,是期望凭借青州和尚与金朝政府的特殊关系达到保住其占据大量“山林”资源的目的。而在清代,普通平民为脱祸,或将债权等捐给地方机构,意图通过钱财的捐赠及转让达到自己依附于地方政府,使自己同政治相联结的目的。
同时,清代较之宋辽夏金时期,战争动乱较少,僧众平民极少将田土捐施于寺庙获得“常住”,从而以求庇护。宋辽夏金时期,战乱带来的人口伤亡及田土的丧失使得僧众不得不依附于有政治背景的人物,平民亦为躲避战乱依附于寺庙,这也造成了这一时期受施者基本为寺庙僧众。
清代的法律制度较之先前的朝代要完善得多,平民在发生田土纠纷时不再简单地进行“告”及“诉”,而是通过捐施等行为力图将自身依附于法理,在这种由“私”转“公”的变化中,虽然出现了诸多问题,但还是为平民提供了一定的法理支持。
三、结语
由宋及清,“施状”在朝代更替,社会法律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逐渐变化,其功能虽仅限于捐施,但是具体的使用方式及本质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宋辽夏金时期,“施状”更多地依附于政治,是一份契约,而在清代,“施状”则为法律服务,日趋发展为诉讼文书。故施状在社会的变迁中产生了诸多变化,也为后来人研究“施状”一类的文书提供了更多的方向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