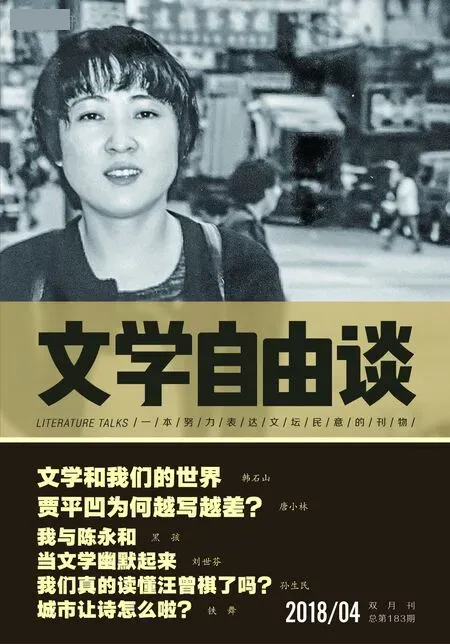作家的“ 俗”命
2018-03-07沈光金
沈光金
最近听说莫言的《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便把《天下太平》找来看看。看罢,沉吟半天,也说不上好在哪里。手头正好有莫言另一篇小说新作《等待摩西》,看了两遍,也说不上好在哪里。反正是莫言的作品,那总是好的吧。
莫言在2008年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被问及中国的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回答是,或许100年之后吧。四年之后,坦言“100年之后”的莫言戏剧性地接到“提早”了将近100年掉下的“馅饼”。
杨光祖先生去山东高密莫言文学馆是2013年,这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看过杨先生刊在《文学自由谈》上的《莫言归来的败象》,方知道“即便是天才如莫言,也走了这么大的弯路,以致贻害终生”。往下看,知道莫言摹学了庞中华的钢笔字,所以,他的字便“其俗在骨,一旦中毒,一生无法清除干净”。芸芸众生,即便俗,倒也无碍此后的一生;可莫言不一样,按杨先生的逻辑,莫言的“那种俗气,依然弥漫,那是骨子里的”,至死终身不得解脱。从字弥散到文,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莫言的“俗”永远是如影随形,那是庞中华害的。我没去过高密,无缘见到莫言早年间那秀丽、规范却是“其俗在骨”的钢笔字。
杨先生算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而庞中华的钢笔书法约莫盛行于80年代,那时杨先生还小,或许有先见之明,没有摹过“庞中华”,得以免俗,大幸也。我曾临过几天“庞中华”,看过杨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我这俗气原来是源于“庞中华”,并导致我至今文武不得。可又没法去找庞中华讲理,你自己上的钩,那只有自认倒霉。有时就想,临摹过庞中华的,和没有临摹过的,他们的俗与不俗,有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但,按杨先生的逻辑,莫言是“俗”到家了。
莫言的打油诗,或者叫顺口溜吧,未见得多好,但凭心而论,也未见的多不好。我也不懂什么叫“心都快成核桃哩”,而“路上走的那小伙哩,你慢点走哩,我把你看上哩”也只能算是大白话,生动在哪里?杨先生没有分析莫言打油诗的酸腐和矫饰,而对《爱情故事》的评价是“如此恶心,如此不堪了”。你可以说,莫言写诗的水平与莫言的声誉不相称,但未必是“要人命,侮辱汉字,又折腾读者”。杨先生说莫言“文言与白话,雅与俗语的混搭,完全超乎于‘恶俗’两个字”,文字无聊恰似“直接给读者的碗里放了一只苍蝇”——批评家的言过其实似乎在表明一种态度:你诺贝尔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以我之见,莫言的打油诗,充其量也就是给读者碗里放了一块咸萝卜,而不会是苍蝇,虽不是佳肴,但可以下饭。杨先生诱导式的比喻,倒真的是像往读他文章的人嘴里塞了一只苍蝇。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这番话是真诚还是矫饰,你可以自己判断。但得奖后成为“众矢之的”的莫言,在文学圈内圈外,都会是万箭追逐的目标。相干的批评家和不相干的挑刺家都在追逐着莫言,但又不是在追逐莫言;万箭追逐的目标是那个戴着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不管是莫言,还是苏童、贾平凹、阎连科——后面这几位还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否则,也会有类似“苏童归来的败象”或者“贾平凹归来的败象”的评价。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譬如,评论家唐小林就将当今文坛上稍有名气的作家数落、挖苦、挑剔个遍,从基本常识到文学修养,从人格品行到治学精神,不一而足。可我奇怪的是,何以这些作家竟没有一个做了回应和反驳?是哑口无言,还是没工夫或不屑理睬?其中的原委至少我不知道。唐先生的“自由谈”成了独白,好比拳击手没了搏击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人的比划,有点无趣。与杨先生“败象”一文同期的唐小林的《苏童老矣,尚能写否?》,汇集了苏童小说中的黄段子”,唯恐读者有遗漏,来个集中展示,而文中属于作者的语言,也就是解释一下这些“黄段子”而已。我很难相信,这就是文学评论?说作家的文学格调不高,那评论家的格调我看比作家也高不了多少,似乎还不如作家。
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被批评家们放大了,放大到了一个以完人的境界去要求莫言的程度;另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又被文学编辑们神话了,只要是莫言的作品,都是中国头牌文学杂志的镇刊之宝”,甚至不用读或者不用读完,就可以照发不误。两个极端的表现,放大了莫言作品可能的不足和可能的平庸,结果是,批评家们左耳光右巴掌地“评”,而编辑们却是前堵截后围追地“约”,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也不碍谁的事。
莫言的《等待摩西》说了一个非常老套的故事,估计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编出来。编辑在卷首语中说:“小说《等待摩西》保持了莫言惯常的叙述语调,第一人称、生动幽默,但更显平静,叙事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传递了人生况味。”这是编辑刊载的理由;如果在杨光祖先生那里,这也许就成了“语言啰嗦、琐碎,真的很难给人以艺术美感”的评语了。
所谓“惯常的叙述语调”,不是莫言一个人具备的。我想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叙事风格或“叙述语调”,所以,这一点不是必刊的理由。如果是另外一位作家,卷首语也可能会这样说:作者以惯用的第三人称,生动、隐喻,更显跌宕起伏,结尾的意外却在意料之中,更显出作家的叙事功力等等,云云。所以,编辑对《等待摩西》的推荐词看起来是针对莫言,实际上没有多少针对性,而刊登的理由——我以为唯一的理由,是它的作者是莫言;舍此无他。
《等待摩西》后面,刊载了莫言的三首诗,汇在“莫言新作小辑”下。我不懂诗,也不知道“叛逆的脚,猛往下踩,红色的法拉利,放出一串激昂的屁,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究竟隐喻了什么?不知道杨光祖先生看过这些诗没有?莫言的“恶俗”有没有改,是不是不那么“恶俗”了,有点雅俗了?按杨先生“一生无法清除干净”的道理来推,应该还是“俗”的;或者可以断言,在杨先生的眼中,莫言的诗可以休矣。不过,杂志的编辑将它们照登不误,一点也没顾及杨先生的情绪。
一个作家,成名的也罢,未成名的也罢,都在写。成名的作家也许更加无奈,或许储备耗竭,或许精力下降,不是每部作品都能不同凡响,犹如一只母鸡,偶尔也会下一只软壳蛋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其一些作品的不凡,但并不代表他的所有作品都在这个高度——也许达到这个高度的就那么几篇。譬如刘翔吧,2006年,以12秒88打破了保持13年的110米栏世界纪录夺冠,却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赛中,因伤退出比赛,直到2015年正式宣布退役,再也不能超越2006年的好成绩了。英雄也有末路,江郎也会才尽,说到底,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凡人、常人。在当下,与莫言平起平坐的作家多了去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必然,却是莫言的偶然。既然是偶然,比较就没了意义,诸如为什么不是贾平凹,不是余华,不是阿来,不是王安忆……都可以是,也都可以不是。村上春树获其他奖项无数,却连续将近十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很少有人说他的作品平庸,但像《挪威的森林》那样杰出之作也不多。村上春树也会偶尔下个软壳蛋的,这不足为怪。
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的得主莫言、赵本夫、王安忆,都和汪曾祺本人有过密切的交往。莫言自谓,在三十多年前,在军艺文学系的课堂上亲耳聆听过汪曾祺的讲课,汪先生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王安忆问汪曾祺“短篇小说是什么”,汪先生回答说,就是“将必要说的话说出来”;又问“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就是“把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汪先生确为高人,连创作经验都是这样高妙,玄奥,犹如参禅一般,也许只有莫言、王安忆、赵本夫能懂。汪先生犹如高僧传道,芸芸弟子不是都能理会的。能悟得的便得道,也许莫言、王安忆、赵本夫悟性高,才得汪先生之真传,得汪曾祺奖那是衣钵所传,理应如此。
再回到杨光祖先生的文章。莫言不止是“归来的败象”,还因为“庞中华”,便“其俗在骨”,“一生无法清除干净”了。但是,莫言鬼使神差”地获得诺奖,这玩笑可开大了,也许真的应了那句大俗即大雅”——莫言俗到家了,也就雅到家了。其实,他的俗与不俗,我以为和“庞中华”无关;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母鸡也有下软壳蛋的时候。
有人劝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其实何止是作家,读者、编辑,尤其是编辑,也要有平常心。发现好作家,发现新的好作家,也许是文学刊物编辑更重大的责任,不要年年的 “鲁奖”、“茅奖”都是那几张老面孔,也不要等到一地软壳蛋,才心急火燎地去踅摸品优质良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