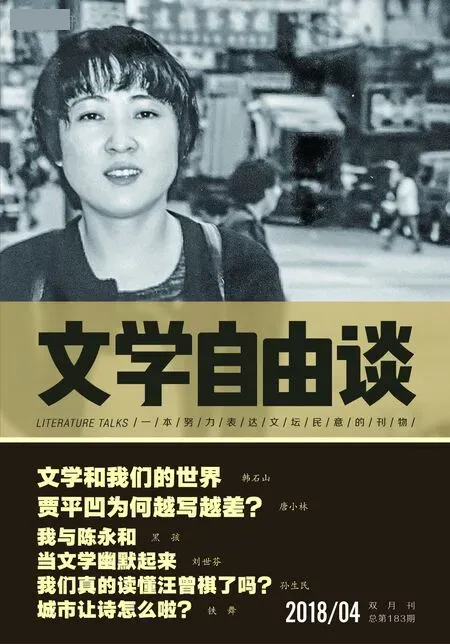怀念陈冲老师
2018-03-07唐慧琴
唐慧琴
时光荏苒,陈冲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
陈老师去世后,我和梅驿、夜子经常打电话念起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陈老师在的时候,也没觉得他有多么重要;他走了,却总感觉背后空荡荡的,尤其是在创作中遇到困惑时,总会下意识拿起手机;等想起他已经不在了,就会揪心地疼一下。
明天就是陈老师的一周年忌日了,打开邮箱,翻看着陈老师与我的来往邮件,思念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与陈老师相识于2008年。省作协为我的长篇小说《日头日头照着我》召开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陈老师问我:“会上的发言,听明白了吗?”
我回答说:“有些听不懂。”
他笑着说:“就知道你听不懂,抽时间跟你聊聊。”
我惊喜万分。在我的心目中,陈冲老师可是重量级的大作家,能得到他的指点,对于初入文坛的我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回去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并把新写的中篇小说《千里迢迢》发到了他的邮箱。
没过几天,陈老师回电话说:“我在作协见到王力平主席了,我跟他说,唐慧琴又写了一篇不错的稿子,悟性不错,就是欠调教。王力平说,这不正是你这个小说艺委会主任该干的事儿吗?我想想也对,的确是我该干的事。”
他问我:“你愿意听一个老头儿跟你唠叨吗?”
这还用说吗?求之不得啊。
他说:“那好,咱们就从你这个中篇开始。”
当晚,我就收到了陈老师的邮件,是对《千里迢迢》的总体分析:小说通篇弥漫着一种温暖,人物关系富有变化,最好最闪亮的细节是结尾女主人公躺在床上憧憬大学生活……他把这封邮件命名为:课程1。他说,以后还会有课程2,课程3……
我没有想到,陈老师会以这样的方式给我讲课。我既激动又感动,在邮件里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并说想拜他为师。
陈老师回邮件说,文学上没有谁能真正教谁,作家不是教出来的,但是,可以点拨,能不能领悟,全靠自己的造化。你悟性不错,我愿意试试,你也不必客气,你愿意听,我愿意说,这是两厢情愿的事。
接下来,课程2,课程3……一封一封的邮件来了,陈老师把千里迢迢》通篇解剖了一遍,从整体结构,到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可能,都一一讲到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么系统这么专业的文学讲解,我学得认真却还是一知半解。有些地方有触动了,就马上改,然后发给他看。他在肯定我的同时一直告诫我,你这么快就有想法了,说明你悟性还行,但是,你要养,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好小说是养出来的。
我一时理解不了他说的“养”,再也不敢轻易动笔了。
他发邮件说,咱们该当面聊聊了。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把邮件里的课程又系统地分析了一遍。
他问我:“有收获吗?”
我惭愧地回答:“好像听懂了,又好像听不懂。”
他看起来有点着急:“你的知识储备太少了,你现在的年龄,大量读书也不现实。我给你一个超近的方法,你回去看电影吧。”
我赶紧说:“到哪儿看电影?看什么?”
他说:“我家里有很多影碟,我帮你挑一下。太复杂的,你目前也看不懂,先从简单的看起,慢慢再看复杂的。”
过了几天,他让我过去拿影碟。一包一包已经分好了,先看哪个,后看哪个,都做了标记。
我心里的感激无法言说。如果再写不好,真是辜负了陈老师的一片苦心。
我开始看影碟。有的看懂了,有的看不懂,看不懂就打电话问,陈老师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认真解答。有一次,看完一张碟已经夜里十点多了,心里实在迷惑,就给陈老师打电话。很快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看看表,十一点多了,我赶紧表达歉意。
他说:“没事,我喜欢晚睡。”
影碟一张一张看下去,话题也慢慢广泛起来,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生活和工作上有了迷惑,也跟他说说,他总能一句就点中要害。
有段时间,我遇到一件烦心事,有人莫名其妙地在网上骂我,还到纪委告我。我异常愤怒,忍不住就跟陈老师诉说。
陈老师了解情况后,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理他。你理他,我就不理你了。”
那个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小说《牵牛花》。陈老师怕这件事干扰我,就鼓励我:“好好写,等你长成一棵大树,他就摇晃不动你了。”
《牵牛花》完稿后,我把稿子发给陈老师看。
陈老师说,《牵牛花》题材、人物关系都很好,就是结构还有问题。他说,你不要急于出版,养上一两年,好好磨一磨,会是一篇不错的作品。
见我一直沉不住气,他又跟我说:“一个作家的创作资源是有限的。”
可惜,我最终没有跳出狭隘的小圈子,就因为那个人的挑衅,赌气把《牵牛花》交给出版社,仓促地出版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陈老师当时的意见非常正确,《牵牛花》因为没有养熟,成了我创作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此以后,每写完一篇稿子,我就发给陈老师看,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稿子的问题,我按着他的意见去改。可改来改去,总也达不到他的要求,就十分苦恼沮丧。越这样,就越写不成。慢慢的,我下笔时再也不像原来那么随意了,变得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总是想陈老师说应该怎么写。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迷茫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写作状态。
陈老师见我着急,就安慰我说:“别着急,慢慢就会好的。”
后来,省作协实行导师制,要给青年作家分导师。陈老师就问我:“梅驿跟我,你跟何玉茹怎么样?”
何玉茹老师也是我仰慕的作家,就不假思索地说:“可以啊,我跟谁都行。”
陈老师说:“梅驿是写工厂题材的,跟我比较合适;何老师主要写农村,你跟她更合适。还有,她比我温和。”
果然如陈老师所说,何玉茹老师在创作上给我充分的自由。她说,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顾忌太多了,反而成了束缚。在何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调整好了心态,写作开始了新的阶段。
由于梅驿和我是很好的朋友,陈老师和何老师也就成了我们两个共同的导师。我们写了稿子,就发给两位导师看,看完后,我们四人聚在一起交流,意见不同就互相辩论。在这样不断地讨论碰撞中,我欣喜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两位老师对小说的分析我能听懂了,影碟也能看懂了,对自己小说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
我把这个变化告诉陈老师,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然后他又笑着说:“我的几个学生跟你以前的状态差不多,都被我教‘休克’了。 ”
我就斗胆开玩笑说:“陈老师,你这是’毁人’不倦啊。”
他一点也不恼,笑眯眯地说:“一旦醒过来,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当时,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现在慢慢有些理解了。也许陈老师的指导方法对有些年轻作家来说,有点太过严厉苛刻,但是,他对年轻作家的这种耐心和认真,却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小说的一些深刻认识和见解,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清醒,与陈老师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不经意间我对小说已经明白了不少,写起来也顺畅了许多。
就在这个时候,陈老师却突然很少露面了,几次跟他通话,他都说脊椎不舒服,不方便见人。
他去世的前几天,我还跟他打电话,说想去看望他。
他说:“再等等,我快好了。”
谁知,等来的却是他去世的讣告。
陈老师去世后,没有举行任何丧葬仪式,一如他行事的风格:活得明白,走得洒脱!
陈老师走后,他的女儿跟我联系:“爸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你,如果你愿意,我带你去他的墓地看看。”
站在陈老师的墓前,我除了默默掉泪,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我内心深处的感激和怀念,不用说,陈老师也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