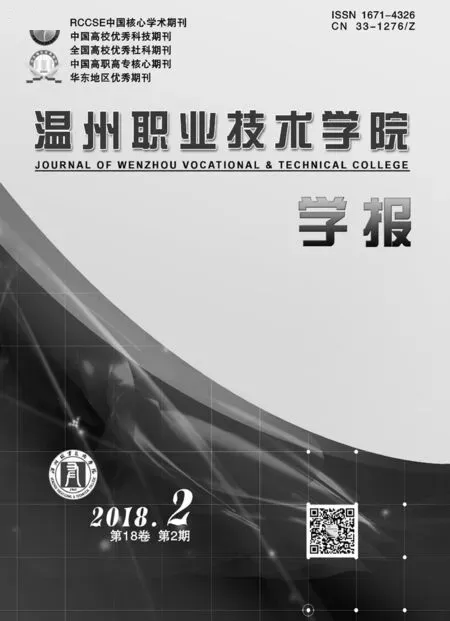传记中的时空之舞
——电影《少年闵子骞》的叙事分析
2018-03-07邵吟筠
邵吟筠
(温州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人物传记电影是展现人物独特人生经历及人物与时代关系的影片。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影片,要有鲜明的立场,要有在浩繁资料中选取和加工整理的认真精神,还要有娴熟的剪辑功夫和高超的镜头表达技巧。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少年闵子骞》在弘扬主旋律、净化观众心灵等方面发挥了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的作用与功能。这不仅与其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立场相关,也与其紧凑的叙事结构、恰到好处的叙事手法及细节处蕴含的传统美学追求有关。孔子称赞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其感慨源于闵子骞的少年经历:“闵子骞,名捐(损),鲁人也。父取后妻,生二子。骞供养父母,孝敬无怠。后母嫉之,所生亲子,衣加棉絮,子骞与芦花絮衣。其父不知,冬月,遣子御车,骞不堪甚,骞手冻,数失韁靷,父乃责之,骞终不自理。父密察之,知骞有寒色,父以手扶之,见衣甚薄,毁而观之,始知非絮。后妻二子,纯衣以绵。父乃悲叹,遂遣其妻。子骞雨泪前白父言:‘母在子寒,母去三子单,愿大人思之。’父惭而止,后母改过,遂以三子均平,衣食如一,得成慈母。孝子闻于天下。”[1]广招门徒的孔子为其“单衣顺母”的孝行感动,招为门徒,之后与颜回、冉伯牛、仲弓成为孔子门下任用德行(在弟子中可仕之人)的贤士。
2013年上映的电影《少年闵子骞》正是以这一故事为蓝本拍摄而成,讲述这一历史人物求学及感人的孝顺故事,使传统的孝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就当前商业电影景观化叙事愈演愈烈,充斥着断点式、碎片化的表述,以及为了商业利润而不惜放弃好故事的主流银幕而言,《少年闵子骞》不失为一部弘扬主旋律、净化观众心灵的好影片。
一、可然之下的经典叙事结构
叙事是存在于叙述文本中的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叙事就是在一段时间之中发生的故事。”[2]呈现的是置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连串相关的事件,表示一种选择和一种安排。叙事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于影像话语中。较为特殊的是,影片叙事是一种将时空性的材料组织进事件因果链条之中的方式,这一因果链条具有开端、高潮与结尾,表现出对于时间本质的判断,也证明它如何知道并因此讲述这些事情[3]。这不仅是不同形式的文化表达的基础,也是经验模式的基础,是一种将素材组织进特殊模式以表现和解释经验的感性活动。
电影《少年闵子骞》以闵子骞为主线展开叙事,分为幼年失母、少年遭后母嫌弃、真情感化后母三个阶段。影片开篇,鲁定公驱逐孔子及门客,将观众带入兵荒马乱的战国时期。闵子骞之父闵马夫为鲁国闵公君之八世孙,因三桓专权铲除异己而携妻子流落宋国,不料身患重病的妻子不堪路途劳累,命丧途中。闵子骞之母临终交一玉环于幼年闵子骞,并嘱咐其“懂事、听从父命、好好读书(拜师孔夫子)”,之后便撒手人寰,留下马车外幼年闵子骞娇小可怜的身影。短短5分钟内,在交代故事背景的同时为之后的叙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影片这样的叙事安排,符合亚里士多德对于故事开端应按照“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提供破题信息创造人物和一个实在世界的叙事要求[3]。影片的第二阶段是正片阶段,延续了开篇结束部分的凄凉感,从朗朗读书声环绕的私塾开始,同样凸显了一个可怜的身影。八年之后,私塾内的满座孩童与窗外蜷缩着身子偷偷旁听的少年闵子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镜头推至比这些孩童略显成熟的闵子骞的脸部时,其窘困的生活境遇不言而喻。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冲突逐步加剧,在“鞭打芦花”之后“闵父休妻”时达到戏剧冲突的至高点,最终在闵子骞替后母求情、感化后母时“结和解”[3]完成叙事,并为影片提供了一种结束感。这个结局虽然未能达到亚里士多德的“不可避免而又出乎意料”的效果,但影片完整的叙事线索和叙事价值使整体结构凸显了经典叙事的一贯特色。
二、基于时空整合的叙事手法
一部电影的完成除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外,叙事技巧亦是其展现自身特点与个性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叙事走向相对封闭的历史人物传记电影。正如苏珊·朗格所言,任何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表现的对象是什么,而取决于怎样表现[4]。影片在90分钟内将少年闵子骞的某段经历完全呈现出来,依靠的正是影片制作者对于时空的整合与安排。
1.运用字幕转换时空
运用字幕是历史人物传记电影叙事最常见的时空转换方式,一般会在时间跨越较大时使用,以字幕标识之后影像呈现的时间与地点。影片共出现两次时间字幕,分别于影片一、二阶段和二、三阶段的转换时刻。影片开篇,交代了春秋时期鲁国三桓排除异己,闵子骞父母也被迫逃亡宋国,沉疴已久的闵子骞之母在辗转逃亡中客死他乡。第一次转换出现在闵子骞随父到达宋国,其生母去世之后,通过字幕将空间转换到了八年后的“私塾窗前偷偷学习”的镜头。第二次转换是在父亲打算休妻,闵子骞单衣为刻薄后母求情,长跪雪地晕倒之后。这两个时间节点正是闵子骞成长境遇的两次转变:一次丧母,自此孤苦;一次孝心感动后母,自此诚心相待。两次时间字幕,一方面作为时空转换的说明;另一方面作为叙事结构的转折点,推动叙事发展。
2.多重时空交汇
一般而言,电影共有现实时空、过去时空、虚拟时空三重时空结构,现实时空作为故事的叙事主线,其间按剧情设置需要穿插过去时空和虚拟时空。影片以闵子骞少年时期的日常生活为现实空间,以线性顺序相互连贯,描述一个个生活事件。时间的进程比较缓慢,但情节点编织顺畅。在闵子骞生活的宋国相邑,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芦苇,其父闵马夫流落宋国之后也以卖芦花为生,在营造战国时期城邦景象的同时,为“鞭打芦花”这个高潮对抗点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使之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有些情节光靠现实时空实难诠释,如何让少年闵子骞的善良、懂事在后母的百般刁难之后依旧合乎情理,是影片叙事进程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3.利用承接因素转换时空
利用上下镜头之间在造型或者内容上的某种呼应、动作连续或者情节连贯的关系,使时空过渡顺理成章。相对于文学叙事,电影叙事是一种既重视叙述人的功能也注重叙述接受者对故事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叙事体系,是一种比文学叙事更强调接受主体作用的叙事体系。观众首先看到这只是一个孩子,他如何能平复自己的委屈与不满而坦然面对不公。于是闵子骞生母生前遗言、教育场景的过去时空,以及闵子骞在梦中生母叮嘱他“对待后母要像对待我一样孝顺”的虚拟时空,因具有内在关联性便对现实时空起着补充的作用。当闵子骞受委屈时,影片总是用生母在世时说的话语来开导和宽慰他。它们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角色情感出发,当过去时空中的情感与现实时空中的行为相互作用时,角色在现实时空的转变便显得合理了。
另外,影片还采用闪回单个画面来加强叙事的张力。当闵子骞将一天寻得的柴草赠予因年老而被儿子儿媳嫌弃的二奶奶而空手回家,与其父财物被盗两个事件重合时,为了延续故事的连贯性,突出叙事重点,影片只是采用了一个后母责备的闪回镜头交代了闵子骞受罚面壁的原因,实现了此时两个事件的并行。之后闵子骞被后母冤枉偷了钱,遭父亲责骂时,看见远处桌台上生母的遗物镜子时,镜头快速闪回生母面容出现在他眼前,看得出神的他因此而遭到了后母的打骂。这一镜头的闪回,一方面表现了一个孩子委屈时想念生母的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凸显了后母的刁钻跋扈,同时开启了下一摔镜事件的引子。
三、追寻传统美与善的美学意蕴
1.因果关系的设计与安排
电影的最终目标是讲故事。换言之,电影其实就是导演及演职人员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所看到的,并以电影特有的镜头语言进行解释,结果就是一个故事的诞生。电影是使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的重构,建立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的因果链条。通常一部电影最终留给我们的,总是一组事件序列,而不是摄影机镜头序列。这个序列是按照事件之间一定的因果关系得以延续的。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与听到的所有偶然性事件的结构性呈现称之为情节,它是影片中事件呈现的顺序。影片中事件、因果链条、情节,一步步将叙事推向终点。正如吉恩·盖里斯所指出:“对于以主角为驱动力的故事片,主要通过它如何漂亮地解决影片所产生出的各种难题,以实现剧情缝合的方式以及它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美学机制对故事情节作出价值评判。”[5]1
影片中故事的情节环环相扣,以闵子骞为核心的因果关系承前启后,实现了多处跳跃性情节的连贯及剧情的缝合。以闵子骞的“孝”为中心的两条叙事线索(感化后母与教化邻舍)交相呼应。邻居苟剩偷盗闵子骞之父钱财,引发后母对闵子骞动手打骂,被其父阻止之后,后母又转而问询江湖术士,听信谣言,认为闵子骞“命犯狐仙,八字相克”,引发了后母对闵子骞更深层次的厌恶和嫌弃。同时,闵子骞因不忍二奶奶年老遭儿子儿媳嫌弃,多次劝阻他们要善待老人无果,最终受到他们挑唆、摔镜的报复。自此,两条叙事线交错前行,将故事逐渐推进,在闵子骞竹简被烧、后母做芦花袄时达到高潮。最终,闵子骞陈述“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替后母求情感化后母,将叙事推至高潮对抗点,“结和解”[3]完成叙事,为故事提供了一种结束感。
影片遵循着这样一种因果律,通过对角色完成某个目标的行为描述呈现出来,推动了影片情节的发展。心理学意义上的因果律通过精巧构思的编剧传统,包括诸如激烈的开场、对抗与反对抗、极端的命运反转及骤然的结局等,它们都在因果关系中得到解释。这样的电影进程就如同一个楼梯,“每一个镜头段落都表达了一定的东西,实现了某个目的,并在叙事中一步一步接近高潮”;行动引发反应,每一步所产生的结果都反过来成为下一步新的原因[6]。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影片的诸多元素之间建立起这样的因果联系,能保证观众对故事的清晰体验,让观众得以畅通无阻地理解影片情节中的事件及它们在故事中的意义。
2.抒情意境的营造
正如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言:“一件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与其产生的传统基本因素密不可分”[7]。每一件文化艺术作品的诞生、每一种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的选择都浸润着其所在的文化艺术传统的影响。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整体风格和所传达出来的意韵亦体现了一种传统特色。影片中运用大量的背景音乐、古诗词和物件营造了一种抒情意境。
影片多处使用背景音乐,以烘托场景、渲染气氛。叙事的开篇,三桓排除异己、孔夫子被迫离开鲁国、孔子门生通报闵马夫携妻儿逃跑,三个不同事件在同一悲壮背景音乐的贯穿中平稳过渡;转而紧迫的音乐,用以衬托闵马夫携妻儿逃离鲁国沿途的危险和紧张气氛,此刻通过音乐自身的紧张之弧强调了叙事中的紧张;在闵马夫妻子撒手人寰,幼儿闵子骞只身立于马车外哭泣的场景中,影片使用了悲凉的背景音乐,用以烘托幼儿闵子骞此刻的悲恸和凄凉。影片前五分钟,三个音乐,五个情节,故事背景、人物、事件起因都得到了清晰交代。叙事的第二阶段,闵子骞旁听被发现,被迫熟练背诵《硕鼠》之后,影像停留在莲儿闪着同情眼神的善良面庞时响起了单薄、清冷的背景音乐,一直延续到后母背地里做肉饼给两个亲生儿子吃的场景,并在少年闵子骞因将柴草赠予二奶奶而空手回家受罚时相同音乐再次响起。这一音乐在缝合叙事的同时,亦是凸显了少年闵子骞的处境——孤独、凄凉。之后,后母听信谣言之后的镜前独处、两个弟弟被马蜂蛰及后母梦见亲生儿子遇害的场景中,为配合场景气氛,背景音乐选用了悬疑乐旨的音乐,在烘托气氛的同时突出了后母日渐厌恶、嫌弃、怀疑闵子骞的扭曲心态。此刻,音乐用于对单个关键叙事事件进行强调、预期和“诠释”[5]31。而在闵子骞与莲儿在稻田中相见时,背景响起了主调清灵的音乐,如清风扑面而来,犹如四周随风摇曳的芦苇清新动人,音乐仿佛让叙事慢了下来。这一清新的气氛一直延续到闵子骞与其父在田埂长聊之后。
影片大量的音乐为传统音乐,作为背景支持、构造叙事,用以强调、衬托故事情节中的气氛。另外,还有一些背景音乐用于塑造、强调人物特征。如闵子骞带着两个弟弟玩打瓦游戏及赶跑苟世义的情节中,影片中使用了节奏跳跃、轻快的乐曲来衬托孩童嬉戏的场景,突出了闵子骞沉着、懂事之外开朗、俏皮的一面。又如苟剩到闵家,欲看后母打骂闵子骞的“好戏”时,恰遇家中没人,爱贪小便宜的苟剩假扮后母的情节中运用了旋律诙谐、滑稽的乐曲来凸显苟剩丑陋的市井小民形象,等等。背景音乐特有的叙事、情感、辅助、评判功能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与正统音乐不同,影片的背景音乐是一种功能性的音乐,它在叙事的背景中所起的作用,既可支持屏幕上的情节,又可匹配场景的气氛。其结构由存在于音乐本身之外的因素决定,进而去强化故事中的角色与主题,以增加对观众的情绪感染力。相对于正统音乐,影片的背景音乐常常由碎片化的、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音乐片段组成,它最重要的任务是作为对影片的一种“平行”的评论而起作用,作为音乐之外的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音乐以它自己的语言复述它所伴随的画面的某种趋势或含义。”[8]
此外,影片引用《诗经》中的《硕鼠》 《关雎》两篇诗文,以全知叙事者的角度对故事进行评判。前者,借魏国民歌表达了战国时期民众对于当政者的不满及对于理想国度的向往;后者则以整体描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男女之情,体现了影片人物对于生活的积极、热爱之情。以传统民歌表达叙事者的价值评判,既立场鲜明又独具传统特色,借诗歌的意境营造了抒情的意蕴。
3.细节传达的意象
影片中意象性最强的就是闵子骞生母生前留给幼年闵子骞作念想的玉环。影片先后三次出现这个玉环。第一次是生母临终的留赠;第二次是闵子骞在弟弟被马蜂蛰后受到后母责备,夜深人静时取出,将其视为生母,与其对话;第三次是闵子骞随孔夫子游学,临行与后母告别时,后母将祖传玉觽赠予闵子骞留作念想,而闵子骞取下随身携带的玉环作为回应之物赠予后母。玉环在影片的三个阶段分别出现,寓意各不相同。
叙事的第一阶段,生母的玉环作为遗留之物除了留给闵子骞一个念想之外,为故事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推动力与预见。玉作为中国传统的佩饰,其寓意尤为深刻。传统文化视玉之品性为君子之德的典范。在影片开篇出现玉环,一方面使影片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作为生母遗愿,为叙事进程埋下伏笔。另外,玉环之“环”与“还”字同音,寓意重归于好、认可之意,与影片的结尾形成呼应。叙事的第二阶段,玉环作为生母的象征,为《史记》中少年闵子骞过人的仁慈、懂事寻得了现代诠释。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遇到挫折、苦难之时,因为有生母遗物作为精神依托才保持着宅心仁厚的本性,使《史记》中历史人物的诸多看似不合现代孝行理念的行为显得真实了一些。在影片结尾部分,玉环作为少年闵子骞临行赠予后母的信物,将故事推至高潮结束点。在遵循叙事构建的同时,也将情绪推到了至高点,通过两块玉的交换,“仁”字在影像呈现中得到了最终的诠释。通过影片细节的设计与意境的营造,中国传统由善到美的美学追求得以体现。
影片中战火纷飞、道德沦亡的时代背景对应的正是当下消费主导、“新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传统价值观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少年闵子骞的善良、仁义、勤奋等优秀品质正是当代青少年缺乏但必须具备的德行。“试图概括人物是徒劳无益的,必须听从暗示,而不是分毫不差地听从说过的什么,也不是完全依赖做过的什么。”[9]影片创作与欣赏是自我与影片中的他者的辩证对立过程,对影片中人物的体会是一种辩证生成的自然产物。只有把握住影片人物与历史纪事之间的生长性,才能让观众在心领神会中真正感悟影片的历史价值和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