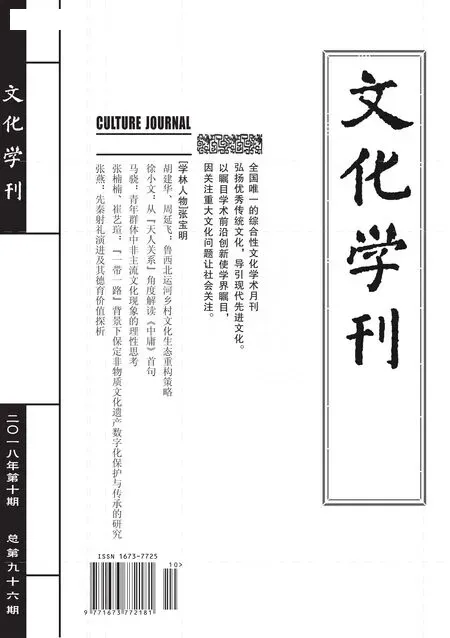以《宠儿》看孤独困境下的女性写作
2018-03-06智丽
智 丽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一、孤独困境下的男性身份
莫里森将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现实主义关怀投射到作品中,使得《宠儿》呈现出诸多新颖之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本中男性的“缺失”,即不在场。
作品以塞丝在蓝石路124号以自由人身份生活的一天开始,婆婆贝比·萨格斯认为那个被塞丝杀死的孩子的鬼魂逼走了两个男孩子,随即到来的男人保罗·D,给了塞丝新的希望。保罗希望以他的“男性气概”镇压“鬼魂”,在地震中试图通过“四处乱砸一气,毁坏每一样东西”来驱赶“鬼魂”,但最终证明他并不能使“鬼魂”安生。黑人女性宠儿是一个流浪者,这个从不说自己来历和身份的年轻女性正是“鬼魂”的肉身代表,她的到来使塞丝走到记忆的更深处,历史也因塞丝视角的介入变得清晰完整,而塞丝也在正视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灵魂的救赎。可见,保罗的到来并没有使塞丝的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得到改善,却使她沉浸在过去被欺压的回忆中,使她被奴役的痛苦如同其背部形状像树似的伤疤一样,不断蔓延滋长,可以说他的存在难以帮助塞丝及丹芙成长。黑尔虽扮演着丈夫、父亲、儿子等三重角色,但他没有在妻子即将临盆时陪伴在她身边,更没有在她逃离“甜蜜之家”时伸出援手,同时他也缺席了丹芙的整个成长过程。莫里森在创作时有意改写男权主义下被定义的女性历史,打破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观念,颠覆男性作为未来代表的终极真理,通过展现第三世界妇女的精神力量来重构第三世界妇女的自我身份。
二、殖民语境下的孤独困境
在种族隔离政策下,人际关系被肤色定义,不同肤色人群间的关系因种族主义色彩变得畸形,而同一肤色人群间也因阶级差异变得充满隔膜。“他人即地狱”的痛苦境遇存在于被主客二分的传统西方理性哲学笼罩的世界中,黑人、女性被视为处于“边缘的兽类”,是没有灵魂和自我的肉体。在作品中,莫里森正是通过女性视角对导致人际交流困境的西方理性哲学进行了批判。
塞丝是《宠儿》的主人公,她既是一个有着特殊遭遇和命运的母亲,也属于万千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群体。莫里森在奴隶制废除一百多年后再现了奴隶生活场景,写道:“我们离开了奴隶制,也告别了奴隶,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因此我们要重新塑造那些人。”她的目的是要进入心灵深处,“种族歧视的创伤在于自我的严重割裂,而我始终认为这是精神病的一个诱因而不是一种症状”。[1]交流障碍是造成人物孤独的主要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我封闭。因此,孤独这种深层的情感体验是对外部环境的本能反应。塞丝独自带着孩子们逃离“甜蜜之家”,她明白如果被捕,那么“在她的丈夫失踪不久,在她的奶水被抢走,后背被捣了个稀烂,孩子们变成孤儿之后,在俄亥俄河附近的一座松岭上,她将不得好死”,但她最终以顽强的生命力顺利来到了蓝石路124号。在面对“学校老师”等追捕者时,塞丝通过杀死孩子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阻止他们被奴役。而保罗·D和邻居们一样,选择了“抛弃”贝比一家,将塞丝看作是恶魔一样的存在。在奴隶主长期的愚民“教育”下,大部分黑奴已经丧失了反抗意识,他们知道自由可贵,也明白为追求自由要付出的惨痛代价,所以他们选择忍受,而塞丝在成功逃离殖民地后,“不能让一切回到从前,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手底下活着”,这是一位母亲深沉的爱,她要为孩子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指出女性不要继续做“沉默的他者”,她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及“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发言’”,女性要重写被“解读”的历史,还原真实面貌和生存状况。[2]莫里森有来自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血脉,在作品中不但回顾了美国奴隶制的历史,而且对黑人女性做了全面解读,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女性历史。莫里森通过展现塞丝的自我意识由觉醒到极端的演变过程,表现其对种族压迫及性别压迫进行的反抗,也揭示了这种反抗必然会困难重重,也会延续在几代人身上。塞丝由被人定义为异类到本能地拒绝同人沟通,孤独一直伴随着她。没有人愿意走进她的内心理解她对孩子们的爱,也没有人反思塞丝这种极端行为背后的原因,更没有人关心她承受的痛苦,塞丝只能选择沉默,不让记忆浮现出来。
最小的女儿丹芙的孤独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同伴因为她母亲的缘故有意疏远她;母亲只知道终日劳动,从不提起关于身世或家族的故事;外婆贝比在病榻上玩味色彩。她作为年轻一代的美国黑人女性,对殖民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但那段她没有参与的历史始终以无形的力量出现在生活中,她渴望了解那段不愿被人提起的历史。宠儿的到来使丹芙的存在价值得到肯定,她细心照顾宠儿,同宠儿玩耍,宠儿既扮演她的玩伴,又是她解开过去秘密的钥匙。在丹芙发现宠儿就是“起居室里和她妈妈跪在一起的白裙子,是伴她度过大半生的那个婴儿以真身出场了”后,她更加渴望得到宠儿的注视,“即使在其余时间里只当个注视者,也让丹芙感激涕零”。丹芙渴望来自宠儿这个“他者”的注视,希望通过宠儿的讲述了解过去,同时她也显示出超越其母亲塞丝的坚强、勇敢和智慧:当宠儿占有了塞丝的一切仍不罢休,以近乎疯狂的方式向塞丝“索爱”时,沉默寡言的丹芙勇敢地走出蓝石路124号,与外界融合,帮助母亲重新融入社会,同更多的黑人女性结为伙伴,最终使宠儿的灵魂得以安宁,并拯救了塞丝的生命,也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崭新而又坚强的女性,她代表着千千万万黑人女性的未来。
三、种族隔离制度下跨种族的“姐妹情谊”
莫里森借废奴主义者斯坦普·沛德之口,道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眼中的黑人形象:“不管有没有教养,每一张黑皮肤下都是热带丛林。不能行船的急流,荡来荡去的尖叫的狒狒,沉睡的蛇,觊觎着他们甜蜜的白人血液的红牙床。”黑人奴隶在白种人的歧视或奴隶主长期的驯化中丧失了身份认同的能力,不论是作为被殖民者个体还是民族身份,长期处于被定义的语境下使他们逐渐接受了低人一等的身份,形成了自轻自贱的自卑情结,而这种被建构的身份正是后殖民主义家所批判的。白人女性对自身的处境有着清醒认识,她们同有色人种的女性一样,是男性世界的附庸,在家庭中处于下等地位,而受到“白人惟我论”思想影响的她们又向有色人种施加着权威,因此,塞丝看到丹芙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被揭发。丹芙对塞丝施以援手,使塞丝感受到了白人姑娘的善良和坚毅,为报答她的恩德,为小女儿取名丹芙。文中写道:“两个无法无天的亡命徒——一个奴隶和一个散发跣足的白女人——用她们穿的破衣裳包着一个刚刚出生十分钟的婴儿。”但正如法农所说“黑人的灵魂乃是白人的人为制造”,黑人的“奴隶”身份已经内化为文化和心理运作模式。在与塞丝相处中,丹芙也流露出了白人种族优越感,在与塞丝分别时,她扬起下巴,说“你最好告诉她。你听见了吗?就说是爱弥·丹芙小姐。波士顿人”。
西方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曾有将性别作为惟一分析因素建构“妇女共同体”神话的设想。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妇女共同体”理论虽以研究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压迫为主要目的,但却忽视了女性团体内部赫然存在的阶级压迫。墨罕清醒地提出:“在姐妹情之外,仍然存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论建立两个种族间的“姐妹情谊”的合理性,莫里森设计丹芙帮助塞丝,塞丝给孩子取名丹芙的情节可看作是她对于第一世界女性同第三世界女性平等相处的美好期望,正如她本人所说,“我的作品源自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3]。她在作品中既展现了被边缘化的黑奴历史,也自觉地书写了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和身份的构建,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第三世界的生存境遇,尤其是关注第三世界女性的成长,承担起了赛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