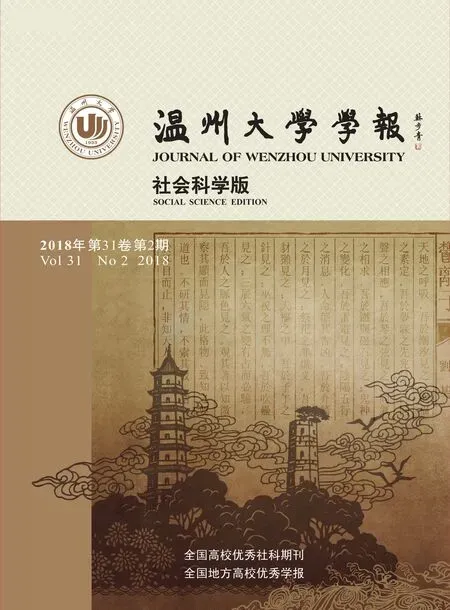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8-03-03张再林张慧敏
张再林,张慧敏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有关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并不多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时代性重大课题。以感性作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一个非常恰切的视角,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中国哲学如果要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必须立足于感性平台。
一、中国哲学的身体性
中国哲学的身体性,主要可以从哲学方法、哲学任务、从哲学历史这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哲学方法来看,什么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以事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则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主要方法。”[1]序4在古汉语中,“生”字与“身”字相通,“生”被视为是“身”的代称,生命之生成演变的最基本的载体和体现即是“身体”显现自身和世界的生生不已的活动。因此,这种系谱学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涉身性的方法。具体而言,这种方法就是论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所谓“下学而上达”,即《论语》所言“切问近思”,中庸所言:“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也是就是说,人们把握世界应该从最贴近我们自己的东西开始,而最贴近自己的东西是我们的身体,古人云“亲己切己,无重于身。”身体是人可以把握的最直接的存在。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身体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此在”的深刻意义,世界通过身体而向我们显现。以身体之,从本质上来说一种从感性出发的带有直觉性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使得中国哲学的方法与作为西方传统哲学方法代表的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义方法判若云泥。就如海德格尔把亲在、此在看作是世界的根本,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身体是世界的根本。“几千年来华夏民族尊重身体,他们注重身体的宗教和哲学价值,以自己的体验来认识世界,身体也超越肉身而具有一切活动的根本地位。”[2]从王夫之主张“即身而道在”到李贽所言“万化根于身”,身体在中国思想史中回响连绵不绝,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哲学方法的隐秘之道。
从哲学的内容上来看,中国哲学最关注的东西不是类似于康德哲学所说的意识和感性、知性和理性等,而是生命、阴阳男女,家族宗法,血缘亲情等东西。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是礼法日用还是终极思考都与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和身体有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亲情的“情”字。蒙培元曾指出,儒家哲学一种十分重视情感体验的“情感哲学”。郭店竹简所载“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尽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为人们揭明了中国古代哲学久被尘封的真正面目。性与生、身相通,情之根源乃在于身,如荀子所言:“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之天情。”(《荀子·天论》)情之生发则是身心一体的内生外成的过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按照海德格尔、黑格尔和梅洛·庞蒂的观点,情是身心一体的东西,情既不能看作是纯心理,也不是纯生理,而是心理和生理的同一,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现代人单纯从生理或者单纯从心里出发来解释情,最终无疾而终。但是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却对阴阳男女,家庭宗法、血缘亲情等东西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甚至包括被人为中国哲学研究最权威的学者牟宗三先生也不例外。
从哲学历史上来看,中国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身体的崛起。第二个阶段是宋明时期身的退隐。这个时期人们大谈特谈心性之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和佛学的影响有关。与先秦儒家学说的身体性不同,佛学最为强调的不是身而是心,佛学把身体称为臭皮囊,对心倍加推崇,佛学讲一念三千,一心开二门,比如佛学唯识论把人的心得意识分为八识,对心得研究做到了淋漓尽致,细致入微。我们不能小觑佛学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在佛学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可以说是没有心的人,或者说是心没有独立出来的人,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心身一体的人。在佛学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有自己的心,开始独立于身,才开始有超越世俗性的纯精神的追求,也才开始有了形而上的所谓心性之学。面对佛学的风靡,“宋儒力阐心性形而上学以应对佛老挑战,大有功与圣学,但不仅有断裂只是失,而且极大遮蔽了‘气-身体’蕴含。”[3]424陆王同样也“放弃了社会实践论而代之以心性修养论”[3]424。第三个阶段是明清之际的身的回归。在这个时期,哲学家通过对宋明理学的反思,认为宋明理学是一种袖手谈心性的学说,通过这种反思,身又一次破暗而出,成为中国哲学的主题。宋明理学虽然被认为是心识之学发展的高峰,但是其中却也内涵了身与心的张力,尤其是阳明心学既强调“心知”又强调“身行”,既反对“不能精察明觉”的“冥行”又反对“不能真切笃实”的“妄想”[1]80,为后继哲学重归身体埋下了伏笔。之后泰州学派对心性理论进行了批判,重新彰显了身体的地位。王艮提出“明哲保身”,罗近溪提出“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李贽提出“万化根于身”,王夫之提出“即身而道在”,戴震提出“出于身者,无非道也”将身重新置于了哲学史的显处。而刘嶯山所提出的那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身子”的概念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对身体的最高的理论概括、理论总结。总而言之,这三个阶段体现了中国哲学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式再次表明了中国哲学的身体性。
二、身体性是对一切重要的中国哲学问题的真正解答
“传统哲学以及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都把事实性的‘事质领域’作为它们的专题领域,忽略了对作为‘事质领域’何以能够成为现实状态领域的这种可能性的追问。”[4]在这种深层追问的意义上,身体性是对一切中国哲学问题的真正解答。以中国哲学中的天人观为例,李泽厚曾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哲学之所以大讲特讲天人合一,和中国哲学的身体性有关。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人和自然的交织,身体既可以看作是属于人的,也可以看作是属于自然的,以其心理看作是属于人的,以其物理看作是属于自然的。同样的,在中国哲学中,天与人不是西方主客二分式的对立关系,宇宙的发生也并非神秘莫测之事,而是“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之过程状态,其“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人自身身体发生的事件里。”[1]8因此每个人的身体就是天人合一的最好作品。中国哲学另一个非常主要的精神就是依自不依他,这个是为梁漱溟和章太炎先生极为推崇的精神。依自不依他实际上是讲人可以自信圆满,人可以自作主宰,人可以不假他求。中国古人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古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身体,而身体作为宇宙依据,作为宇宙根本,就是李贽所说的万化根于身,他是本自具足的,这就是身体的自足性。一方面,这种自足性来自于生生之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所造就的生命实践勉力进取的积极维度,即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主体亦可致虚守静,顺世而为,切己自反,从消极维度上使生命实践以圆融的方式与世界交织在一起。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感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了解什么是感应,就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哲学,正是有了感应,才有了儒家的恻隐之心,才有了儒家的仁爱,中国哲学所讲的情是感情之情,通过感应产生的情。正是由于感应,才使中医提出天有五星,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的不和谐必然导致人生命的不和谐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人为何讲感应,实际上也和身体有关,更具体地说,是和身体的感觉有关,即身体觉有关。我们知道佛教有六根之说,六根里有身根,身根就是触根,所以身体觉就是触觉,因为触觉有别于其他感觉的一个最主要的性质,就是触觉具有双重性。所谓双重性,就是说,触就是被触,触与被触是亦此意彼的,存在触觉中,我们很难区分什么事能动,什么事手动,什么事主体,什么是客体。梅洛庞蒂以左右手相互触碰为例,在触碰过程中,无法感觉哪只手主动,哪只手被动。相反,视觉没有这种特性,胡塞尔曾提出,我们用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眼睛自身。如果西方把这种情况成为触觉的双重性的话,中国人则把他称作是此感彼应,感而遂通的感应。周易的咸卦阐释的就是这种感应。咸卦亦被称为感卦,是通过男女之间身体的相触来谈男女之间如何心灵相通,如何成为有情之人的。现在大家都开始认识到情对中国哲学,乃至人类哲学的重要性,把情谈透,是离不开对触觉的分析的。
三、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相径庭,旨趣各异,但我们对中国古代身体哲学进行一番考察之后,再来反观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甚为契合之处。
首先,两者都是对唯心主义的身体原罪说的颠覆,都把头脚倒立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都从思想的理性走向了现实的感性。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马克思摒弃了西方传统哲学意识性和抽象性的特质,从社会关系中的人和具体的生产活动出发,将理论建立在了现实的、感性的日常生活之上,并把感性的人的回归作为批判资本逻辑下人的异化的武器之一。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则从肇端之际便奠定在身体的基础之上,这个身体不是柏拉图式作为灵魂居所的代表了“恶”的肉身,而是一种即心即身、身心一体的经验主义的身体。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皆自身体而生发,从一开始所面向的就是一个生活世界。从“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无论是玄妙的终极思考还是人的现实存在和具体活动都与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即“我‘在我身上’又重新发现了作为我的全部我思活动的永久界域,作为我不停地置身于其中的一个维度的世界。”[6]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都强调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我们所说的中国身体哲学人与自然交织的天人合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多次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95在明确把人视为自然界一部分的基础上,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122经由社会实践,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实现了统一,社会的存在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相统一最集中的体现。在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命题。中医观点认为“人身虽小,暗合宇宙”,例如人的脏腑状态与四季更替、方位变化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从经验出发说明了身体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之义。从哲学层面上看,天人合一之“人”即指向人自身,同时又从“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的人与自然生成和共在的意义出发,指向一种“体万物而不遗”之人。以至于程颢直接提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人与自然以一种共生共在的方式浑然无隙地融合统一在一起。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都主张实践至上。在古汉语中,身字也被写作躬字,后者同时具有“亲身”和“躬行”之义,简言之,躬就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身体”一词本身包含着行动、践履的涵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把认识转化为现实那样,中国古人也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尔”,在重视实践这一点上,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也最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46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实践是人和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是解释和理解人的存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在《尚书》中便已提到“天之历数在汝躬”,古人把躬行实践视为天命所寄的应然之道。《周易》在“生生之之谓易”的生命发生学基础上,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推崇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积极进取的实践行动。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传统为后世哲学家继承。先秦儒家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并将“行”具体化至以仁与礼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去。正如后世儒家所指出:“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朱子语录》)当然,中国儒家的实践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区别之处,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前者侧重于道德践履,后者含义更加广泛,涵盖了人类实践的各个方面,但两者内涵的实践精神是极为相近的。
最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走向了生命力学说,即生命能力学说,在古汉语中,“身”字也就是伸展的“伸”,伸着,身也。“伸”原本是“申”,在甲骨文中,“申”字是一个象形字,象征男女两性的结合,引申为生产、繁殖。因此中国哲学的身体是通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是生产力,如果对生产力这一概念进行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能力。“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8]生产力概念蕴含了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能动的创造和发展的能力,类似牟宗三先生曾指出的“创生不已之真几”。
但我们在看到两者一致之处同时,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恩格斯曾提到“两种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活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9]虽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了人自身生命的生产,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但是其更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更强调人自身生命的生产。两种生产哪种更为根本?在笔者看来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容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偏颇,过于聚焦人自身的生产则可能流于“见人不见物”的弊端。这种两难境况正说明了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实现互补的必要性。
[1]张再林.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张晓虎. 实践哲学的身体维度[J]. 理论月刊,2012(12):32-34.
[3]周与沉. 身体:思想与修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燕燕. 梅洛·庞蒂具身性现象学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
[5]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6]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
[7]马克思. 1844年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
[9]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10]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