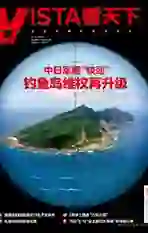北大教授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2018-02-28沈佳音
沈佳音
罗新继续上路,但他不认为重新发现中国的任务能够完成
2016年夏天,53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是元代皇帝如候鸟一般春去秋回的线路。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连接两都之间的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辟的道路为辇路。
一年来常有人问他,走了这么一趟有什么收获?你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发现?他很诚实地回答——没有获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但他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说到底,他本来就是“为走而走”,走出象牙塔,走出论文体。他想用行走来感受中国的现实,并探究一种新的写作形式。
“我了解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他一再地问自己。回来之后,他用九个月的时间写了新书,《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山川都带字幕
十五年前,罗新看书时,读到有关辇路的诗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史料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所以史学界对辇路的认识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罗新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
这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2016年4月间的一天夜里,北京五道口的寓所中,耳畔轰响着前往八达岭方向的列车,他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计划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今年 呢?
2016年6月24日,他从大都的健德门出发,走向上都的明德门。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來从华北平原进入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是连接农耕文化与草原文明的历史走廊。
八百年前,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万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风云变幻隐没在平凡的村庄与深山荒草间,还有那些似是而非的地名上。比如皇后店村,有一种解释说是“皇后田”的讹写,而皇后田是金代皇后的奁妆田。
“皇后店、皂角屯、龙虎台等地名都保留至今,显示了历史与社会强韧的连续性。”作为历史学家,这一路上的典故与争议,罗新信手拈来,“地名连续性是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方面,但这种连续性有时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就如同今人在西直门见不到门,在双井看不到井一样。”如今,连皇后店村也不复存在了,已经被拆迁,建成了城市学院的新校 区。
过去是已经发生的,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要重建过去的真相时,其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与未来一样,过去也是开放的、流动的。站在静默的遗迹前,罗新讲述了许多罗生门的故事。
河北沽源县的梳妆楼是一座全砖横券无梁结构的建筑,形似一个方块,上端一个穹窿顶。可以推定这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的墓地,墓主人的名字是阔里吉思。这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他到底是谁呢?至今没有定论。一说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他曾在平定叛乱时身中三箭仍英勇作战,后来远征时作战被俘、不屈而死。又说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曾有资格问鼎可汗大位,最后死于与武宗海山争位。还有说是武宗的亲信大臣怯薛,历经元朝三代皇帝。
不同的人物,却都拥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家李旻评论说:“跟着罗老师去旅行,山川都带字幕。”
这次行走其中有三百公里左右都是在长城内外,罗新就把有关的书都读了一遍,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他看到当代著名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曾和前男友乌雷做过一个关于长城的行为艺术。设计这个以长城为舞台的表演时,他们还在热恋之中,按照设想,他们两人分别从长城的两端嘉峪关和山海关走向对方,走到中间相遇后,立即举行婚礼,作品名为“情人”。
由于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的过程极端复杂,这个项目拖了很多年。在等待的那些年里,两人关系恶化,终于耗尽了温情与爱意,不再相爱。因此,1988年,项目实施时,最后相会结婚的情节改成了分手。作品的最终版是两人经过三个月的跋涉后相遇,两人同志式地拥抱。在行走长城的途中,乌雷让他的翻译怀孕了,两人很快结了婚,而阿布拉莫维奇独自一人飞回阿姆斯特丹。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取消这个表演,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终结……某种意义上还挺符合人性的。这比仅仅一个浪漫的情人故事更有戏剧性,因为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说到底你真的是孤独的。”阿布拉莫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穿墙而行》中写道。
日复一复地行走,让人专注于自身,记忆里一朵牵牛花的摇曳,都因某一地点某一场景,在路上被恍然忆起。关于这次旅行,罗新决意不把它写成历史学著作,而是一次关于行走的非虚构写作。“我希望整个旅行写作是有一个主线,主线是这个路线,就是行走本身。所以在写作中,走到哪儿了,就写写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事。”
过去五十年的人生片段在罗新脑海零星闪烁:年少时不为人知的暗恋,大学时半途而废的远足,年轻时对打牌的迷恋,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人生的五味杂陈,罗新都一一忠实记录。“哪怕当天的行走笔记里只记到一句,也要把它仔细地叙述一下。既然笔记写到了,说明那天我真的在想这个事。”
夹缝中的人
罗新不想写的是那些别人已经写过的,或者说经常写的东西,他想写一个特别的长城。他想看看明代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长城,找来找去只有徐渭。
徐渭56岁那一年,即万历五年,在明朝的北部边疆生活了大半年。他写下了一些与文学传统不太一致的、温情脉脉的边塞诗。比如有一首诗写他到蒙古人家里做客:“胡儿驻牧龙门湾,胡妇烹羊劝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过河难。”他大概不止一次去观摩边境互市的所谓“胡市”,写有好几首诗。作为江南人士,他无法忍受市场里的羊膻味,更糟的是这种味道还要保留好几天,“胡馆不一刻,膻触数日”。endprint
这不是一个对抗的长城,战争的长城,而是一个共生的长城。长城不是一条分割线,而是把两种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走廊。“历史真实的一面就是两边都是混合的,可是在历史记录里面只看到两边的对抗或者领导人之间在博弈。其实没有这样一个清楚的分界线,我们看到的是彼此混合的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说分界线,也是这样一个很宽的、很模糊的灰色地带。”
罗新发现在明蒙互市中,蒙古的马尾很受明人欢迎,这是因为当时北京流行一种来自朝鲜的服装样式,叫做“马尾裙”。这种裙用马尾织成,系于腰间,衬在外衣之内,使腰腹以下的外衣向外鼓胀,看着像撑开的一把伞。
在明蒙“隆庆和议”之前,内地市场对马尾的需求大,而供应渠道狭窄,价格高企。因此,在长城地带的越境走私贸易中,马尾是主要货品之一。有些走私马尾生意的边民,如果受到明朝政府打击,其中一些人会逃到蒙古 去。
这些在明蒙两个政权之间生存的老百姓,也是罗新特别关注的。他们在两个政权之间游走,“用脚投票”。既有大批蒙古人以属夷或俘虏等身份进入长城以南,也有大量明人出边叛降或被入边的蒙人掳掠进入蒙古。比如明代的降蒙汉人赵全,他原本是山西的一个农民,因害怕被举报信奉白莲教而举家投奔蒙方,并在蒙古混得风生水起。但当明蒙议和后,他被蒙方交给了明朝,草草审讯一番,十八天之后被杀。
“我不想写两边的领导人,不想写那些英雄事迹。”罗新在书里多次寫到这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边缘人,无论是在历史记录还是在真实的权力结构里面都不提他们。但我希望能够把他们多多少少找出来一点点,即使他们的命运仍然有很多不清晰的、模模糊糊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老盯着那些被宣称出来的、被推出来的典型人物、重大英雄,围着他们转,而要看到他们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有意塑造的结果,而这个塑造的过程才是历史本身。”
破墙而出
450公里的路程,开车三四个小时即可到达,换作高铁或者飞机更快。罗新走了十五天,元人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罗新一直在警惕自己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隔膜。“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
有一天傍晚,罗新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站在一起,打工者身上酸臭的强烈味道让他难以呼吸。“我和他贴得那么近,我却分明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沟,我甚至期待这界沟变成一堵物理的高墙,好隔住他的味道,好让我看不见他。”罗新诚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
这一次,罗新从书斋里走出来,用脚步丈量中国。他的专业是北方民族史,主要研究游牧跟农耕两个大的社会之间的长期共生、共存、对抗、竞争。他们之间有战争与和平,有征服与统治,有正常的经贸往来,也有可怕的相互攻击。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理解长 城。
长城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在中亚,在伊朗,在高加索地区,以及历史上跟中国长城一样有名的罗马长城。企图用墙隔开的方式,把同一个人群,把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分割开来,无论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墙,还是特朗普想修的墨西哥的墙,抑或是在中国境内看到的各种围墙、铁丝网,我们都称之为修 墙。”
他还留意到几乎经过的每个村口,都有横向的金属卷闸门,只是都卷起来堆在一边,似乎并未打算使用。不过可以设想,如果需要,这些卷起的门可以立即展开,封堵住通向村内,以及村子与村子之间的交通,经过或进入这些村庄的路就被切断了。
今年暑假,罗新计划徒步穿越英国的哈德良长城。这是罗马帝国在占领不列颠时修建的,把整个英国大岛一分为二。“罗马人认为长城北边的就是蛮族,这条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堵住北方人。这也是一种南北对抗,一种所谓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隔。”回来之后,他要以这次徒步为线索写一本关于墙的书,看得见的墙和看不见的墙。
罗新继续上路,但他不认为重新发现中国的任务能够完成。“对中国的了解永远不够,就像我们对历史也永远了解不够。但你不满足于被困在某一个具体的空间里或者是状态里,你希望能打破它,就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墙的问题。我希望能跨出去,把这个墙推倒。所以我觉得所谓发现也是这个意义,就是你总是想知道得多一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