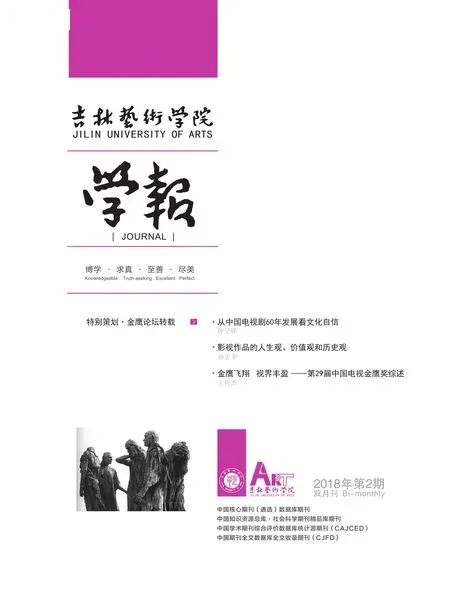“文化”与“艺术”的双重表演
——客家“哭嫁”仪式音乐的文化阐释
2018-02-25罗钢芹
罗钢芹
(嘉应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自东晋开始,由于常年的战乱和饥荒,中原汉民经过数次南迁分批到达闽、粤、赣三地交汇处。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不断融合、同化,形成了我国的一大民系——“客家民系”。客家学者房学嘉认为:“客家文化可以视为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以汉文化为总体背景,而且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以及土著文化。”[1]
千百年来,客家人在汉文化的背景下吸收了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俗仪式,“哭嫁”就是传统客家婚俗仪式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民俗学者张嗣介指出:“客家过去闺女出嫁,流行哭嫁。……哭嫁是新娘才艺智慧和家传礼仪的一种传统形式,否则将被族人视为没出息,没良心不懂规矩的村姑。”[2]
一、关于客家“哭嫁”
客家哭嫁一般分为三次。第一次哭嫁发生在迎亲前一天的晚上,男方迎亲队伍敲锣打鼓来到女方家中,当迎亲花轿到达女方厅堂时,那声声唢呐和阵阵锣鼓,迅速催哭了母女俩。第二次哭嫁发生在第二天拂晓,女儿在梳妆打扮时,面对姑、嫂、姐妹,催发了第二次哭嫁。第三次哭嫁发生在早宴后,当女儿蒙上红头巾时,母女、亲人之间对哭。但有些客家哭嫁在出嫁的数天前就已经开始,这些姑娘出嫁前见人就哭,表达自己内心的不舍,因此所发生的哭嫁次数也无法统计。
客家哭嫁不仅要高声痛哭,还要边哭边唱,因此哭嫁歌就成为客家婚俗里的一种独特文化。据定南县陈招娣老人介绍,“哭嫁,不仅仅是哭,还包括有板有眼地边唱边哭。而且在婚礼前就开始了,女方的所有女眷都要参与进来,哭诉命运的不公,对父母、亲人的不舍和对媒婆的谩骂”。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哭嫁,她们边哭边诉,有板有眼,往往即兴地将当地山歌曲调套上诉词即成为哭嫁歌。

歌词2、3段:喇叭(即唢呐)吹的嘀嗒响,只怪出世乱忙忙,唔(客家话“不”)该变成黄花女,一上花轿到别乡。喇叭吹的嘀嗒响,舅公牵捱(客家话“我”)到厅堂,娭爷厅下拜三拜,屋中姐妹痛心肠。
这首哭嫁歌为客家民间典型的叹息似音调组成。徵调式旋律框架,每一句的落音均在徵音上。旋律以级进的形式先上行后下行,配合五拍子的节拍律动和较高的音区,很有哭诉的意味。
二、“文化”与“艺术”的双重表演
“表演”和“艺术”是密切相关的词汇。一般来讲,艺术是通过声音、动作、图像等表演来获得某种审美的体验。民族音乐学家张伯瑜指出:“当民族音乐学把研究视角转向了“文化”之时,其研究便不仅仅思考艺术问题,而且还关注声音和生活的关系问题。”[3]客家哭嫁歌就属于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其歌声属于客家人民生活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客家哭嫁歌的研究必然要融入到婚俗仪式当中去。这时,哭嫁就不仅仅是一场艺术表演,更是一种客家文化生活的体验,也是客家人族性内涵的体现。
客家人聚居区范围较广,不同区域的成婚仪式略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客家婚礼还是继承了传统汉族婚礼中的“六礼”。第一礼“问名”,即通过媒人了解对方姓名、年龄、家庭情况等。第二礼 “纳彩”,即男、女方如果满意,男方给女方下彩礼。第三礼“纳吉”,即男方将订婚礼物送予女方。第四礼“纳聘”,即男方将鞋子尺寸告知女方,女方根据尺寸做郎鞋。第五礼“请期”,男方根据黄历选好迎亲日期,并告知女方。第六礼“迎亲”,男方赴女方家迎亲,行成婚大礼。
过去的客家婚宴,男方必须宴请三天,女方须宴请两天。迎亲时,男方须请花轿、八音乐班等队伍浩浩荡荡前去迎亲。回来时,请挑夫把女方嫁妆一同挑回男方家。现在的婚宴,一般就举办两场,即男方一场,女方一场。在仪式用乐上,除了常见的唢呐、锣鼓之外,有些富裕家庭还会邀请西方铜管乐队加入其中。在演奏安排上,八音乐班常常演奏仪式核心环节,铜管乐队则在闲暇时穿插演奏。可见,客家的婚礼已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然而,传统的客家婚礼,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经历数天的哭嫁。以前的姑娘在出嫁前,都要跟母亲学唱“哭嫁歌”,这是客家先人留下的“规矩”,也是婚俗仪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演唱哭嫁歌是客家已婚女性的必备能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客家婚礼已经很少有人会唱哭嫁歌了,大部分的婚礼不唱哭嫁歌,会唱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现在能够完整演唱哭嫁歌的村民大多成为了哭嫁歌的传承人,她们偶尔会被邀请到一些村民家中为婚礼演唱。通过整个仪式过程我们发现,哭嫁者是在“表演”,而且是非常艺术化的表演。此时,哭嫁歌又由“文化表演”演变成了“艺术表演”。
三、“哭嫁”仪式的文化功能阐释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 al ino ws ki)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为满足需要而生的,是有特点功能的。正是因为社会有需要,文化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延续。”[4]传统客家婚礼常常以欢腾喜悦的唢呐锣鼓表演和悲切控诉的哭嫁场面,吸引了大量客家人前来观看。从表面上看,婚礼场面悲喜交加,婚礼仪式的娱乐性极强。但从哭嫁的运用场合来看,其仪式的文化功能性色彩远远大于娱乐性。
1. 情感宣泄功能
在传统客家社会中,婚姻的缔结主要是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未婚女性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是未知的,她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在没有话语权的历史情境中,客家女性只有在结婚之日才受到最大的关注,这一天她可以在众人面前尽情的倾诉着自己的情感。此外,客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民系,重男轻女是客家人的一贯传统,客家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因此,哭嫁就成为一种情感宣泄的最好手段,女性通过哭嫁来哭诉对命运的不公、对未知生活的忧虑、对亲人的不舍、对媒人“多事”的怨恨等等。
2. 社会教化功能
在客家哭嫁仪式中,哭嫁的另一个主角是母亲。母亲一方面表达对女儿的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对即将踏入社会,为人妻母的女儿进行教导。因此,哭嫁就成为女儿出嫁前母亲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在兴国县的实地调查中,母亲黄云英唱到:
乖呀!妹呀!尺子带大在身旁,唔知唔觉20年,今普结良缘;
乖呀!妹呀!早去早成家,勤打扫、动烧茶,是非场合切莫惹;
乖呀!妹呀!丈夫面前细思量,粗言细语肚中藏;
乖呀!妹呀!家官家娘大声叫,你要细声应,刺耳之语莫发言,酸甜苦辣把话吞;
乖呀!妹呀!锄园种菜要向前,做好家务把田耕……
在这里可以看出,客家女性出嫁前母亲对女儿未来婚姻生活的诸多教诲,所述内容多为教导女儿婚后要勤劳、隐忍、孝顺等等。
3. 文化认同功能
英国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st Geller)指出:“人们热爱自己的文化,他们知道自己离开了文化就不能呼吸,不能保持自己身份的完整性。”[5]在传统客家社会中,新人只有通过举办婚礼,才能得到宗族和社会的认同。而对于女方家庭,女方只有通过哭嫁才能得到父母、亲人的认可。同时,女方通过哭嫁仪式来表达女性的“孝”,男方也在这一过程中对女方进行了品格的认可。在女性哭嫁过程中,哭父母、哭姐妹、哭兄弟、哭叔伯等,女方在这些哭诉中强化了这种社会关系,同时在这些哭诉中也增强了社会对客家女性的品格认同。
4. 驱邪降福功能
在客家地区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结婚乃大喜之事,必招恶鬼嫉妒”,于是大婚之日,新娘不乐反哭,以悲伤之感来蒙骗恶鬼,从而确保新娘的安全。这种做法在客家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体现,如某家小孩实际长的很好看,却愿意叫他丑小孩,还给他取一个难听的名字。这些都是害怕鬼怪惦记,故意丑化子女的做法,而其中又和哭嫁一样,饱含着祥瑞之意。另一方面,在客家话中“哭”和“福”是谐音,客家人认为哭的越多则福气越多,不哭反而带来晦气,因此哭嫁便成为了一种客家风俗。
民俗专家曲彦斌指出:“物理意义上的声响,即便是万钧雷霆,也不强大,也并不让人畏惧;而民俗、神话意义上的语词却有着强大的魔力,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6]客家哭嫁仪式正是如此,它以哭嫁传递了客家女性对不平等社会的控诉,对未知生活的忧虑和对亲人的不舍,同时哭嫁的背后又传递了父母、亲人对出嫁女性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在哭嫁仪式中,一句句娓娓道来的诉词,一首首哀怨悠长的曲调,使哭嫁成为沟通祖先、神明的重要媒介。女方家庭通过哭嫁的行为展演,在祖先和神明下祈求祝福。因此,传统客家婚俗仪式中,哭嫁自然而然就成为仪式的中心,也被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四、“哭嫁”的生存困境与文化人类学阐释
民俗活动和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它的生成、演变与群众的信仰需求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群众的信仰也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民俗活动就会随着群众信仰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7]
1. 生存困境
(1)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般而言,当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方式已经与传统观念相背离,或与传统日常生活脱钩的时候,传统的东西要么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得以流传,要么就被新的文化形态所替代。这是文化变迁的规律。”[8]
改革开放以来,客家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客家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明显提升,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另外,随着交通和信息的快捷便利,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特别是一些新思潮正逐渐冲击着那些古老的客家习俗。随着文化土壤的瓦解,客家哭嫁仪式变得越来越少。据笔者对广东的五华县、兴宁市,江西的上犹县、定南县调查情况来看,四十岁以上的人对哭嫁仪式有较深的记忆,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哭嫁习俗。据定南县哭嫁仪式传承人廖云白介绍,现在很少有人家会请她去“表演”哭嫁,一年能接两三场婚礼哭嫁就不错了。可见,随着文化的变迁,哭嫁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
(2)传承的困境
哭嫁民俗具有“以人为载体”的鲜明特征。非遗专家冯骥才先生曾经指出:“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①哭嫁仪式生存土壤的急剧萎缩,造成了该项民俗活动传承上的困境。现在客家地区的哭嫁传承人屈指可数,四十岁以下的传承人已经绝迹。可以说,客家哭嫁民俗活动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2. 文化人类学阐释
哭嫁民俗反映了客家人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观,表达了客家女性对不平等社会的控诉,对父母的感恩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哭嫁歌的各个仪式文本都作为一种客家族群记忆的“符码”,充当起了客家文化记忆的职责。如高亢哀怨的哭嫁音调,如泣如诉的哭嫁言词,都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客家哭嫁仪式通过各类表演文本的构建和音声符码的系列构建,重构了客家族群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客家文化认同的重复性和持续性。这种认同的重复和持续,将作为一种纽带,将“客家”与“客家”,“客家”与“中原”牢牢联结在一起。从这一层面来看,客家哭嫁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华文化的认同”?
五、结 语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将民间表演艺术的研究上升到对其文化表演的研究。但随着文化变迁和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本属文化表演的民俗正在逐渐演变成艺术的表演,客家哭嫁民俗就是其中的典型。直到今日,哭嫁仪式仍然是客家社会维系宗族情感、凝聚宗族人心的重要纽带,也是彰显宗族尊卑,促进客家文化认同的有效方式。正是这种强烈的区域文化认同,才不断促发闽粤赣一带客家民系在传承客家文化方面呈现出的“认同力量”。今天,虽然哭嫁仪式生存空间急剧萎缩,但我们相信,只要客家人的信仰观念不变,宗族文化不灭,哭嫁仪式就仍然会在客家婚俗中扮演重要角色。
注释
①2005年3月22日非遗专家冯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发言”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