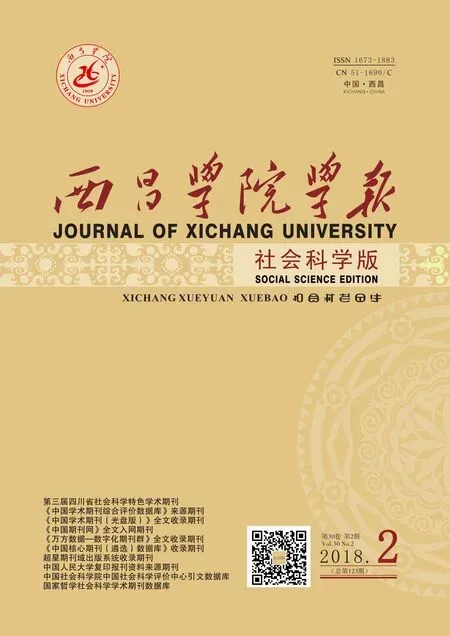《七宗罪》的超我化暴力:拉康精神分析的诠释
2018-02-24张维元
张维元
(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作为当代经典电影的《七宗罪》(Seven)与《电锯惊魂》(Saw)已经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目光,过去论者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两部电影的悬疑设置策略、运镜与剪辑技巧、黑色美学建构与叙事策略等方面,对于剧中的谋杀快感较少触及。本文主要以《七宗罪》,并辅以《电锯惊魂》为考察对象,试图借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倒错快感”(perverse enjoyment)与“超我”(superego)概念,解析当代惊悚电影连续杀人狂的谋杀快感逻辑。通过突显《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展现的“超我化暴力”,与传统连续杀人狂电影,如《惊魂记》(Psycho)中的“病理化暴力”及日常生活中之“逾越性(transgressive)暴力”的差异,继而对电影文本的核心意涵进行再诠释。
一、从《惊魂记》到《七宗罪》:当代惊悚电影暴力形态的转换
“杀手形象”一直是以连续杀人狂为主题的惊悚片的核心元素。此类型电影中,杀手不只是核心角色,更是故事展开的决定性中心转轴,影片基本上沿着杀手的虐杀计划逐步展开,而观众对故事的理解则由虐杀计划的揭露程度来决定。当然,电影的高潮总在于杀手神秘意图的最终揭露,某种程度上,这一最后意图揭露的巧妙程度经常决定着这一类型电影的成败。
1960年上映,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导演的《惊魂记》已在影史上奠立了经典地位,该片中诞生的连续杀人狂诺曼·贝斯(Norman Bates)也已被视为上世纪60年代连续杀人狂的经典形象。影片中我们连续目击那无法看清形象,却能清楚听见其声音的“母亲”挥刀杀人,影片的最后高潮也正在于揭露贝思即是杀人母亲形象的真正扮演者。如研究者指出的,《惊魂记》所环绕的悬疑母题即是“将声音附着回身体的不可能性”[1],影片中高分贝、充满咒骂的母亲声音如同鬼魅般飘荡于所有空间,持续地进行谋杀,我们却一直看不清其形象,而当声音找回其身体时,它却黏附回了错误的身体,也就是回到了贝斯身上,母亲真正的身体则早已被贝斯制成木乃伊般保存着,这一以声音找回身体,但却是错误的身体的悬疑解决,更让电影结尾显得离奇与不可思议。而影片最后一个镜头,贝斯对着镜头诡笑,背景音却充斥着母亲的声音,更是一镜式地再现了整部电影的母题。整体来说,《惊魂记》中贝斯的连环谋杀是一种病理化暴力,这一暴力源于对内在精神冲突的解决,贝思的母亲生前阻挡贝斯与异性交往,母亲死后,贝斯因将母亲的命令“内化”而产生精神分裂,一旦遇到对自己具吸引力的异性,贝斯内化的母亲意识就会驱使贝思变装为已死的母亲,并将该女性杀害。
相对于《惊魂记》中的贝斯在精神疾病的驱使下谋杀,《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的连续杀人狂无名氏(John Doe)与拼图杀人狂(Jigsaw Killer)则主动搜寻犯下罪行的对象,并透过缜密的杀人计划让其直接死于其所犯的罪恶之中。《七宗罪》的杀手让犯下基督教传统中七项罪恶(骄傲、忌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与色欲)的人死于其所犯的罪恶中,如将犯下暴食罪的人喂食至死;将犯下懒惰罪的人注入大量迷幻药物,但通过照护让其长期卧床,使其身体僵尸化而懒死;将名模毁容,然后让其选择放弃通报救援,自己举枪自尽,因不愿放弃美貌的骄傲而死等等。《电锯惊魂》中的杀人狂则搜寻任何不尊重“生命”之人,让其死于当初不尊重生命的行为(如杀手于片中持续复诵的“不珍惜生命之人,不值得拥有生命”或“我要看你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能走的多远”)。譬如,诱使一个曾经割腕自杀获救的受害者爬过利刃构成的铁笼,以避免被封死在地下室内孤独死去。杀手让被害者死于为求生而挣扎爬过之刀刃铁笼的谋杀策略,一方面让被害者自己向自己证明当初选择割腕自杀,不珍惜生命的愚蠢,另一方面更证明了一个大写化“生命”的价值。
和《惊魂记》相比,《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的连续杀人狂没有清楚的精神病病理表现,而和贝斯无针对性、无计划性的谋杀相比,无名氏与拼图杀人狂的连环谋杀是计划缜密的、具有清楚策略原则的。此外,《惊魂记》的谋杀真的意在杀人,而《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的杀手则是个极端讲究的“方法论者”,强调以“对的”方法杀人。再次,《惊魂记》的杀手倾向掩埋犯罪事实(贝斯总是在谋杀后将车连尸体沉入湖底)并躲避追查,《七宗罪》与《电锯惊魂》的杀手不但不掩盖其罪行,反而喜欢展示谋杀奇观,如《七宗罪》中的杀手称其一系列谋杀为“作品”,而前述《电锯惊魂》谋杀场景中的刀刃铁笼则如同一个装置艺术展品。总体来说,《惊魂记》的谋杀是防卫式的减低心理痛苦,谋杀本身是一种解决方案,相对于此,《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的连环谋杀则是积极式的追求快感,谋杀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受害者的死亡不仅有着解脱之意,在整个计划中,受害者的死亡本身甚至是反高潮的,真正的高潮乃受害者迈向死亡过程中痛苦的、奇观化的历程。
在这一论述脉络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连续杀人狂,尽管受精神分裂之苦,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贝斯相对容易理解,而分别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与21世纪初期出生的无名氏与拼图杀人狂则更难理解。在没有清楚病理状态下,我们如何诠释这种“作品化”的连环谋杀?如何诠释这种淫邪的施虐快感?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倒错快感与超我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风靡当代电影界的连续杀人逻辑。
二、超我化暴力:《七宗罪》的暴力模式解析
当代知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理察·戴尔(Richard Dyer)指出,《七宗罪》对连环杀手形象的建构颠覆了一般的常识性看法。在一般性认知中,连续杀人狂是反社会、反道德的激进他者。与此正好相反,《七宗罪》中的连环杀手却对社会律法与社会规约产生了“过度认同”(over-identification)[2]。如戴尔所言,影片中杀手“对上帝律法的认同过剩可被视为他对一般性律法过度认同的一个面向”[2]。
戴尔的诠释点出了《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当代连续杀人狂的深刻之处,亦即一般状况下被视为对立两面的“律法规约”与“暴力快感”在影片中相互混生的离奇景象,但这一诠释却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一诠释忽略了影片中连环杀人的快感因素,而这一因素却是影片中最为难解,与最具吸引力的核心面向。第二,这种诠释基本上预设了一种阿图赛式(Althusserian)或福柯式(Foucaultian)的主体观,也就是认为个人可以被社会规约“召唤”(interpellated)或“接合”(articulated)进入既存社会体系中,被转换为一“从属化”(subordinated)的主体,这种从属化主体的预设不合于影片中连续杀人狂接近全能且能控制整个故事世界的形象。最后,这一诠释只强调“量”的差异(所谓的“过度”认同),这种解释无法清楚分辨成功社会化的一般人与连续杀人狂间的区别,也就是“到底多少认同算是正常的,又多少认同可说是过度的?”这一难以回答的问题。通过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快感逻辑的讨论,我们一方面可以诠释影片文本中律法与暴力快感的奇异融合,另一方面可以从“质”的角度,辨析其与一般社会化主体对律法认同状态之差异。
拉康理论一方面强调律法规约对主体的深刻影响,但又同时认识到快感主体不可能完全同化于律法,而可以针对律法采取不同位置这一观念起点[4]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影片中奇异的连续杀人逻辑。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拉康作品中所谈论的「律法」并非指涉特定的法条,而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基础性与总体性原则[5],而在拉康理论中,一般性快感主体对律法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的。因为对一般性快感主体来说,作为调节总体社会关系的律法一方面是终极幸福的指引,但另一方面,律法也持续地被快感主体视为一种阻碍实时快感追求的阉割(castration)。快感主体的这种暧昧态度使律法从其根本就无法脱离欲望与逾越(transgression)的纠缠。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言,根本没有“中立地”遵守律法这种事,我们遵守律法时,总是先投射出一个被律法禁止的诱惑世界,然后通过抵抗那个诱惑世界来“倒回来”遵守律法,亦即“对律法的遵守总是已经由对逾越的欲望进行压抑所中介”[3]。简言之,在拉康理论中,一般性的快感主体乃是一个持续徘徊于律法周围不知如何是好的主体,对这一主体来说,律法是个既难以完全认同又难以完全摆脱的麻烦对象。律法对我们做出“禁止暴力”的指示,这不但不能阻止“逾越性暴力”的发生,有时反而助长这种暴力,因为被禁止的暴力反倒成了一种诱惑,但一般的快感主体在真的做出逾越性暴力行为后,懊悔与罪恶感随之而来,这一“逾越性暴力—罪疚懊悔”的循环乃是一般性快感主体暴力行为的宿命循环。
《七宗罪》与《电锯惊魂》的连环杀手则透过倒错快感的策略摆脱了上述的“逾越性暴力—罪疚懊悔”循环,并进一步强化其谋杀暴力的快感。“倒错化暴力”与一般性暴力最大的差别在于,一般性暴力是一种对律法的逾越,而倒错化暴力则透过故意设下不可能被遵守的律法规约来猎捕受害者,然后以律法之名行使暴力,由此一方面升高暴力快感,又于另一方面否认暴力快感的存在(“不是我要…是他先……我才……”)。戴尔在分析《七宗罪》的著作中曾提醒我们注意,影片中连续杀人狂所选择要惩罚的“罪恶”十分奇特,杀手所选择的并非当代社会认为罪大恶极之事,如强暴、性侵儿童或甚至谋杀,而是选择了只被当代社会认为是瑕疵的行为,如“暴食”,或甚至是被隐晦赞许的特质,如“贪婪”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经常被认为是具抱负心的表现之一[2]。最明显符合戴尔所言的,应该是影片中“懒惰”罪名的受害者,从影片中我们知道,受害者是个毒贩,有多重暴力前科纪录且曾性侵儿童,但他却是因为“懒惰”这项我们都犯过的罪而被惩罚。戴尔所提示的罪恶选择之奇特性正与倒错快感策略相关,《七宗罪》中的杀手选择了那些在当代几乎不可能被遵守的律法来猎捕受害者,而《电锯惊魂》的杀手所选择的“珍惜生命”律令更是因为可诠释范围过大,以至于不可能被遵守,从曾经有过自杀企图到当狗仔队记者虚掷生命都可以掉在违反“珍惜生命”律法的范围中。
当代拉康派学者曾将被倒错快感激活的律法为“想象性律法”(imaginary law),它和一般性社会律法不同的地方在于,一般社会性的象征律法因为必须调节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所以无法构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完型体系。但在拉康理论中,律法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一个无法完全自我封闭的律法场域和主体积极的自由维度相关,唯有律法场域内涵空缺与裂隙,主体才能有自由选择与行动的空间。拉康的“主体自由”并不直接来自主体本身,而来自律法场域内部的裂隙、不一致与无法完全自我封闭的特质,这一非封闭性给予主体面对社会规约时的回旋空间,使主体不至于直接服从地贴合于社会系统,成为无自主意识的纯粹社会人。想象性律法则完全不同,它是从不一致的律法场域中挑出的特定规约,然后被幻想式地想象为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完全调节,覆盖所有社会关系场域,并进而分配“良善”(‘goods’)的律法碎片[5]。这种透过倒错快感操作而贯注了快感的律法碎片生来就为了透过掠捕与惩罚证明自身,而非进行总体社会调节。
在拉康自己的理论词汇中,“超我”这一概念则用来描绘被注入快感的律法。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超我不同,弗洛伊德的超我为禁止(prohibition)的发布者,它的主要话语是“你不可以……”,拉康的超我所发出的命令则是正好相反的“享乐吧!(enjoy!)”[6]。拉康的超我概念特别地具有当代性,我们现处于一个后现代的快感社会中,“享乐吧!”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强制性律令,当这一“享乐吧!”被贯注入律法,超我化的想象性律法随之而生,拉康曾评论道,超我化的律法“同时是律法及其自身的毁灭”[7]。
《七宗罪》与《电锯惊魂》中连环杀手施展的超我化倒错暴力的吊诡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不可思议之任务,这一不可思议性表现在一连串的矛盾融合与时序倒转上。首先,倒错快感策略完成了快感与律法的融合,在此,快感既非律法的反面也非纠缠律法之物,律法直接成为快感的泉源,影片中的连环杀手的暴力谋杀乃以律法之名而行。第二,倒错快感的策略同时增强又否认了快感,它透过想象性律法增强暴力快感的同时,又允许快感主体躲在律法的面具之后,宣称它不过是在执行任务而已,如《七宗罪》杀手所说的,他是“被选中”的人,他自己并不想从事这些谋杀。第三,倒错快感的操作将律法与惩罚的时序倒转了过来,在一般状况下,律法在先,其次违反,最后惩罚,但倒错快感策略则以惩罚来回溯性地建构一个全能(想象性)律法的存在,此为影片中连续杀人狂将其谋杀美学化与“作品化”的来源。因为唯一能证成想象性律法不可置疑的存在的只有惩罚,惩罚的细节便必须被展示,折磨的历程必须延长、定格与奇观化。整体而言,倒错快感主体将自身的暴力快感注入律法中而建构了一个具有掠捕性的、“活”的想象性律法,从而将律法转换为汲取快感的工具,由此展演出诡谲离奇的暴力形态——超我化暴力。
尽管《七宗罪》和《电锯惊魂》都具有宗教色彩,如研究者指出的,《七宗罪》的连续杀人母题为“强制赎罪”[9],而《电锯惊魂》则将“珍惜生命”转换为“宗教训诫”式的“强力规则”[9],但从拉康快感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连环杀手绝非简单的“信仰型杀手”[10]。根据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不管是《七宗罪》中的七项罪恶,或《电锯惊魂》中的“珍惜生命”这种“类宗教式的”(quasi-religious)的律法规则,都只是影片中连续杀人狂施行超我化暴力的策略性工具,是杀手从当代律法的不一致场域中挑出来作为想象性律法的律法碎片。
我们不应过度注重这里的宗教因素是因为倒错快感逻辑与超我化暴力的规划与执行不一定需要宗教性元素,在当代流行文化的场域中,媒介文化研究学派学者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所称的“掠捕式新闻学”(predatory journalism)同时也展演了倒错快感与超我化暴力的策略。特纳给了我们两个来自澳大利亚电视节目《时事》(Current Affair)的掠捕式新闻例子。在第一个例子中,《时事》以类似调查性报道的方式试图探索长期失业对年轻人的影响,节目首先找到三个长期失业,居住在墨尔本的年轻人,简单地说明他们的失业状况对所属家庭的伤害后,节目帮他们在离家三千公里外的昆士兰北部度假胜地找到了工作。但三位年轻人后来都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两位兄弟不想为新工作理发,而妹妹则不喜欢新工作的制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澳大利亚的观众在屏幕上看着他们三兄妹飞到邻近小岛上玩帆船,享受日光浴。根据特纳的说法,节目的播出如同打开了地狱之门,电视台被愤怒的电话灌爆,邻居在电视上对他们做出恶评,各级政治领导人(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都指责这种行为,三兄妹及他们家人在街上被人吐口水,甚至接到死亡威胁。后续追踪显示,这一关于青年失业之调查性报道的“剧情发展”其实一直由节目制作单位所主导。在第二个例子中,《时事》的工作人员给予一位移民电器修理员一组损坏的录像机,并秘密地拍摄这位移民工人的工作过程,事后再将收据与拍摄内容进行对比,暗示这位移民工人对客户进行敲诈,这位移民工人无法以其生涩的英文面对后续排山倒海的质疑,最终选择以自杀收场。特纳指出,这种掠捕式新闻学的操作以一连串技巧布置(隐藏摄影机、狗仔队、脱口秀中“意外”的特别来宾等等)来围困被报道对象,通过暴露并放大被报道对象的瑕疵行为以在市民社会中生产(针对被报道对象的)大量义愤,上述一切策略都是在“公共利益”之名下进行。特纳指出,整体而言,掠捕式新闻学常奇异地透露出一种能高度控制媒体再现技巧的把握,及随时准备动用这些技巧的信心[11]。这种以“勤奋”与“诚实”的美德为想象性律法的掠捕式新闻学,难道不是当代新闻场域中的无名氏与拼图杀人狂?
三、《七宗罪》对“邪恶”的再思考
从故事情节、人物设定、打光与场景设计等面向来看,“罪恶”毫无疑问是《七宗罪》的主题。影片的主要人物由一个老警探、一个年轻警探与一个连续杀人狂构成,从片头设计开始,整部电影的黑色风格便极为鲜明[12],故事发生在暴力与罪恶聚集且最能代表人类现代性的地理空间——城市。这个城市没有名字,我们只知道它充满着肮脏的街道与没完没了的下雨天,导演极少使用自然光而采用大量人造打光,以营造影片的黑色基调与光影效果[13]。影片中更运用大量微型故事、画面细节及画外音营造一个罪恶城市的形象,譬如,老警探诉说着他越来越不能接受现代的犯罪,一个劫犯在抢到东西后,还刺瞎倒在地上受抢者的双眼;他更不能接受现代人的自私心态,如他所说,现在“在任何大城市,人们都习惯于少管闲事,在女性防身课程中,第一条就是教遇到暴徒时,不要喊救命,而要喊着火了,喊救命没人会理你的,大吼着火了,他们才会过来”;他搭出租车时,看见下雨的窗外街道上有人倒在路中央,周围则有围观人群相互拉扯。这些城市的罪恶甚至渗透到最温暖的私人家庭空间,老警探所居住的公寓房间随时充斥着隔壁邻居叫骂与相互殴打的声响,年轻警探则因为被地产中介商欺骗,而居住在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地铁通过吵得不得安宁,家具器物震动摇摆的居家空间中。《七宗罪》中的人类空间是一个“罪孽绝对蔓延与世界对这些罪孽漠不关心”[12]的世界。
故事中的罪恶顶点表现在年轻警探的妻子被杀害的情节发展上。尽管出场时间不多,年轻警探的妻子无疑是影片中唯一的善良慈祥象征,她总是穿着白色衣物并被柔和灯光笼罩着出场,年轻警探出门打击犯罪时,她总是睡得像个婴儿,象征着警探每天面对邪恶“为何而战?”的一切理由答案。她弥合了老警探与年轻警探交往关系的鸿沟,她怀有身孕,是影片中唯一的“新生”象征,但这唯一的天使却遭到“斩首”这种最具象征性的暴力处决。她的首级甚至被连续杀人狂以开玩笑的方式装在纸箱中寄给警探,由此触发最后的终极谋杀,让年轻警探犯下“暴怒”之罪,盛怒下杀死“忌妒”警探拥有天使般妻子的凶手。这唯一善的死亡成为罪恶达到极致的最后媒介,并让“作者”般的杀手被直接镶嵌进他的“作品”中,由此正式完成七宗罪谋杀的“作品化”工程。《七宗罪》给了我们比抓不到凶手更绝望的结局。
影片中“罪恶城市”的场景设计与“超我化暴力谋杀”的故事主线两者构成了一个相当明显的关系,即“罪恶城市”建构了超我化暴力谋杀的“背景”。但若我们进一步追问罪恶城市“究竟如何”作用为超我化连续谋杀的背景这一问题时,就可能出现不同的诠释。一种诠释方式是认为罪恶城市之设定和超我化连续谋杀两者间乃故事设计之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前者预示着后者的到来。奠基于前一部分对于倒错快感与超我化暴力的诠释性文字,另一种诠释方式可能更具说服性,这一诠释认为罪恶城市的设计与一连串超我化谋杀间的关系并非有机整体,前者并无法预示后者的到来,相反地,两者间的关系是差异化或甚至断层化的,而这一对邪恶内部的断层式差异之描绘可能是《七宗罪》的核心启示。
不管影片中所描绘的罪恶如何蔓延在城市的所有角落,或甚至侵入到私人的居家空间,但这些暴力都属于逾越性暴力的范畴。相对于此,影片中连续杀人狂所展演的暴力却是倒错的超我化暴力,这是连环杀手的暴力比罪恶城市更邪恶之处。首先,影片中老警探无奈地认为警察的工作常只是哀伤地纪录犯罪事实,把它们“存放好,以备万一法庭上用得着它们”,相反地,年轻警探则深信自己的工作并疾恶如仇,尽管他们在面对充满逾越性暴力的罪恶城市时,表现出清楚的二元对立看法,无名氏的凶行却一次性地以其作品化的连续谋杀直接爆破了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将罪恶断层式地上升到突破两位警探所习惯的逾越性暴力的罪恶层次。其次,年轻警探的天使妻子尽管无奈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但仍以优美慈祥的姿态生活在罪恶城市中,成为片中唯一的城市之光,逾越性暴力无法捏熄这一城市之光,但她却遭到超我化暴力的斩首,并触发了完成整个谋杀作品的终极谋杀。最后,影片中超我化暴力断层地超越逾越性暴力还表现在“无力执法者”这一面向上,《七宗罪》和《电锯惊魂》中的警探不但无法抓到凶手,《电锯惊魂》中与连环杀手失之交臂的警探后来进入走火入魔的执迷疯狂状态,而《七宗罪》中疾恶如仇的年轻警探最后则受到毁灭性打击,呆若木鸡地坐在警车后座被载离终极谋杀的现场,他的意识推缩到与现实世界断绝联系的状态,在这里,倒错快感与超我化暴力对执法者产生了毁灭性的效应。这是因为执法者权力的基础乃是针对逾越性暴力行为的一般性律法,这让执法者在根本上无法面对同时是“律法及其自身之毁灭”的超我化暴力。这一“邪恶的断层”或许才是《七宗罪》和《电锯惊魂》两部当代惊悚电影经典的核心启示,也就是,相对于充满逾越性暴力的罪恶城市,以(想象性)律法为武器的超我化暴力才是真正的终极邪恶。
注释:
①正因为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快感主体不可能与其所认同的律法、规约与既存秩序完全合一,所以拉康学派的学者持续地反对阿图赛式或福柯式的主体观,Slavoj Zizek反复地强调意识形态召唤总是“失败的”,而精神分析的快感主体总是“超越召唤的”,参见Zizek,Slavoj.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New York and London:Verso,1989:126,139。另一方面,更有知名的拉康学派学者以整本书的篇幅反对福柯式的主体观,参见Copjec,Joan.Read My Desire: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M].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MIT press,1996.
[1]MICHEL C.The Impossible Embodiment[A]//Zizek,Slavoj,ed.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C].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2:195.
[2]DYER,RICHARD.Seven[M].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9:46-47,70,12-13,10.
[3]EVANS,DLYAN.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M].London:Routledge,1996:98.
[4]ZIZEK,SIAVOJ.Fragile Absolute:Or,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100.
[5]ROTHENBERG,Anne Molly and Foster,DENNIS.Beneath the Skin:Perversion and Social Analysis[A].Rothenberg,Anne Molly,et al.eds.Perversion and Social Relation[C].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5.
[6]ZIZEK,SLAVOJ.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M].New York and London:Verso,1994:20,67.
[7]LACAN,JACQUES.TheSeminarofJacquesLacan,BookI:Freud'sPapersonTechnique(1953-1954),NewYork:Norton,1991:102.
[8]刘永清.电影《七宗罪》的后现代主义意识[J].电影评介,2012(16):57-58.
[9]施畅.惊悚片《电锯惊魂》中的宗教隐喻与强力规则[J].电影评介,2010(6):69.
[10]刘裕利.信仰型杀手的人格研究─以电影《七宗罪》中的角色John为例[J].历史与文化,2013(394):178-181.
[11]TURNER,GRAEME.Tabloidization,Journalism,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qu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999,2(1):59-76.
[12]李彬.把世界涂黑──谈影片《七宗罪》中的幽暗意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2):85-88.
[13]郭斐.从《七宗罪》解读戴维·芬奇的黑色暴力美学[J].电影评介,2015(21):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