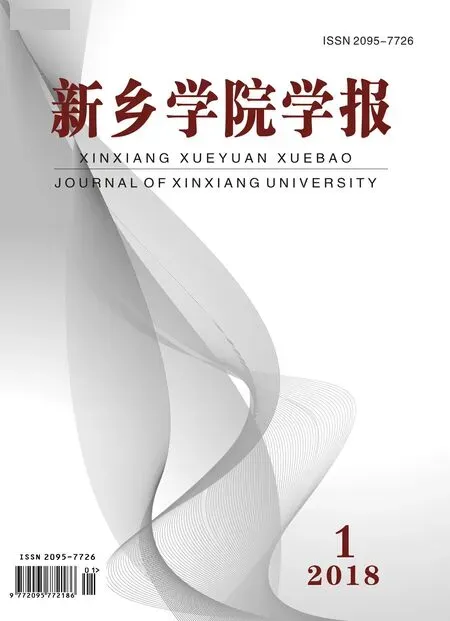论《我不是潘金莲》的反讽修辞
2018-02-23高芳艳
高芳艳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修辞就是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换言之,是指为造成特定语境中表达效果而组织并调整语言”[1]。而反讽修辞就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2]。反讽修辞是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耀斯说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3]反讽修辞有助于作者含蓄有力地体现自己的修辞目的,避免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以武断、直接的方式强加给读者,而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将自己的态度或事实的真相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通过表象领会其深层含义。善于讲故事的刘震云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喜欢用反讽手法叙事。《我不是潘金莲》是他在2012年推出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刘震云更是将反讽修辞运用得淋漓尽致,全面体现了反讽修辞所具有的滑稽、荒唐、调侃、戏谑等喜剧性的美学表征。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民妇上访的故事。一个叫李雪莲的农村妇女为偷生二胎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结果弄假成真,丈夫抛弃了她。倔强的李雪莲由开始的状告丈夫秦玉河,到最后状告各级政府官员,这个过程坚持了20多年。这是一个“蚂蚁滚成大象”“芝麻变成西瓜”的近乎荒诞的故事。本文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意象反讽和结构反讽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展示的反讽修辞魅力,并思考多种反讽修辞构建的荒诞故事背后,作家对官场生态现状的反思和对底层女性在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双重弱势地位的审视。
一、多样化的反讽修辞打造的荒诞效果
(一)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从字面意思来看即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说者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其内心真正的想法,而是相反的意思。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式,比直接陈述更加深刻、尖锐,也使叙事假象和真实内涵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对比反差中达到反讽的效果。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的言语反讽修辞是通过反语和语境误置来体现的。
反语即说反话,就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故意表述相反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里,反语达到的修辞效果也不一样,具有嘲弄、挖苦、谴责、批判、否定、幽默、暗示和亲昵等不同的情感意味。刘震云就是通过语言表层本身的悖谬性造成的陌生感,召唤读者体悟其真实意指。如小说写李雪莲去找王公道告状时,在王公道家门口,“李雪莲手拍酸了,老母鸡被拎得翅膀也酸了,在尖声嘶叫,最终是鸡把门叫开的”。最后“为了安置半布袋芝麻,主要是为了安置还在尖叫的老母鸡,也不是为了安置芝麻和老母鸡,是为了早点打发走李雪莲,李雪莲坐到了王公道新婚房子的客厅里”[4]7。在这里,把门叫开的其实不是“鸡”,而是李雪莲的“执拗”和“一根筋”,王公道最终让李雪莲进屋,也不是要听她的故事,而是为早点撵走她。
小说写李雪莲去北京告状:“李雪莲去北京没去对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北京不准闲杂人等进入。何谓闲杂人等,没有明确规定,凡是不利于大会召开的,皆属于闲杂人等。”[4]72可事实是李雪莲“很重要”,不是“闲杂人等”,她有冤情在身,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是体现人民权益的大会,李雪莲去北京的时间恰到好处,歪打正着。再如小说中市长马文彬对李雪莲的评价:“她是当代的‘小白菜’呀……她是一个名人呀。出了这个县这个市,没人知道马文彬和郑重是谁,但大家都知道这里出了个‘小白菜’……她不是‘潘金莲’,也不是‘窦娥’,她的确是哪吒,是孙悟空。”[4]157这段话体现了马文彬对李雪莲的复杂情感,既有挖苦、否定,也有嘲弄和谴责,甚至还有些许的无奈。其实李雪莲只是马文彬这些政府官员眼里没事找事、胡搅蛮缠的刁民,和真正的“名人”毫无关联。
除了反语外,小说还运用语境误置来表现言语反讽。语境误置即把某些特定话语,如某一时期的流行语,或某一领域的专门术语,抑或某些特定场合的话语,放在明显不符合情境的另一时期、另一领域和场合,造成语言与语境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导致的言外之意对字面之义形成了深刻的反讽。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是郑重在给马文彬汇报工作时马文彬的回答。
李雪莲的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领导能力,也没有提高;我们驾驭和引导事情的水平,还是那样一个水平。老郑啊,还是那三个成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刚才不还说到蚂蚁吗?还有‘防微杜渐’和‘因小失大’。李雪莲的事,今年折腾了几个来回;也不是光今年折腾了,整整折腾了二十年;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出在大的方面,我就不说了,还是像其它任何事情一样,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老话,往往出在‘小’的方面,出现在细节。老郑啊,我劝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李雪莲的事情结束了,事情就真的结束了;还是要从李雪莲这件事情上,汲取深刻的教训。不然走了一个李雪莲,还会出现一个王雪莲![4]258-259
防微杜渐原本指坏思想、坏事或错误刚刚冒头时就加以防止、杜绝,不让其发展下去。而用在这个情境里,意在揭示马文彬和郑重之流身为官员,不认真为百姓做实事,忽略民众的心声,对李雪莲的冤情视而不见,还要阻止她上访告状,还道貌岸然地“防微杜渐”,冠冕堂皇地说不要“因小失大”,是怕因为一个“小”李雪莲丢了自己的“大”乌纱帽,这样张冠李戴营造出的特殊氛围,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二)情境反讽
在通常情况下,人一旦有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就会朝着目标努力。但是世事的无常,人事的多变,往往使得人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变成了阻碍自己成功的绊脚石,为防范某事发生而采取的措施又恰恰导致不愿意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事与愿违、目标与现实的南辕北辙就构成了情境反讽。情境反讽追求一种整体化效果、南辕北辙的巨大反差,在揶揄的同时,达到了曲尽其妙的反讽效果。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情境反讽几乎贯穿作品始末,主要体现为手段与目的、行为与结果的错位。
如李雪莲为了逃避计生政策,主动提出和秦玉河假离婚来避免遭处罚,离婚只是李雪莲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或手段,但让她没想到的是,目的达到后,即生完孩子后,作为策略或手段的离婚却不受控制,丈夫秦玉河的背叛使离婚弄假成真了,手段就这样荒诞地颠覆了最初的目的。再如李雪莲坚持20多年的上访告状,最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自己更不是“潘金莲”。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在各级官员的层层推诿下,最后“由芝麻滚成了大象”,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但凡接触过李雪莲案件的相关人员无一幸免被罢官,李雪莲的离婚真假依然无人证明,“潘金莲”的帽子依然没有脱掉。这是包括李雪莲在内的所有人没想到的一个结果,行为和结果的错位强化了故事的荒诞性。
除了李雪莲之外,各级官员们的行为动机与后果之间的反差也构成了情境反讽。如李雪莲第一次去北京告状误打误撞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她的事被一位大领导知晓纯属偶然,而这位大领导向她所在省的省长提到李雪莲也是讨论时举了个例子,并无什么深刻用心。然而,省长认定大领导是别有用意,在自己面临升迁的关键时刻,为避免节外生枝,省长毅然把涉及此事的各级官员全部撤职,引发当地政坛的大地震。省长惩处涉案官员是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升迁,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大领导听说此事后,反倒认为省长心机太重,从此对他有了看法,升迁之事也没了下文。再如阻止李雪莲告状一直是各级官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首要的任务,为此他们倾巢出动,围追堵截,无所不用,但最后的结果是李雪莲绕过一个个坎去了北京告状,而且告到了人民大会堂。20多年后,当身心疲惫的李雪莲被“牛”劝说,决定放弃告状时,心惊胆战的各级官员却不相信她的放弃,于是巴结、贿赂,多方试探,软硬兼施,派人看守,甚至设计爱情阴谋,让李雪莲写保证书,步步紧逼,最后把本不想再告状的李雪莲又生生逼上了上告之路。
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南辕北辙,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性。类似这样的情境反讽在小说结尾也有所体现。小说最后李雪莲告状的落幕,并不是她的案子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完美解决了,而是被告人秦玉河的意外死亡,导致她的告状没有了被告而自然落幕。就像作品中马文彬说的:“事情的解决不是我们主动努力的结果,而是靠一场意外事故划上了句号,事情是以不解决而解决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个意外。”[4]258还有被李雪莲事件牵连丢官的史为民,年关为了陪得了癌症的老友打一次麻将,在春运期间的北京买不到火车票时想起李雪莲的上访告状,于是在北京火车站高举起申冤的牌子,旋即被警察遣送回家,如愿上了麻将桌。在这里,史为民为回家赶牌场而故意使出的上访伎俩,让两个警察千里迢迢的紧张押送变成了一个笑话。而更可笑的是两个警察后来明知被骗,竟还向上级邀功请赏,谎报阻止了一场严重的上访。这些制度的守护者最后都变成了制度漏洞的玩弄者,行动与结果的背道而驰,使得小说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
(三)意象反讽
意象反讽是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不是应合关系 ,而恰似悖逆乖离,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两者之间的悖反在矛盾统一体中体现了浓郁的反讽意味,生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并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更好地传达意旨[5]。刘震云以往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没有具体的名字,仅仅使用一个代号来命名,例如小林、女小彭、男老何、老郭、女老乔等,但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他并没有延续一贯的作风,而是在人物名字的安排上别有用意,采用谐音命名。例如法制系统一般代表公道、懂法和正义,所以法院法官叫王公道,法院专委叫董宪法,法院院长叫荀正义,法院专委叫贾聪明。而代表民意的县长、市长、省长,他们的姓名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本色,所以县长叫史为民,市长叫蔡富邦,副市长叫刁成信,省长叫储清廉。这些官员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及从事的行业都有关系,听上去都是很正义、很公道、很为民、很清廉,但这些官员往往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刘震云通过大量充满讽刺意味的名字给读者传达了一种带有强烈戏谑味道的言外之意,达到了一种幽默荒诞的效果。
如法官王公道在面对老晁哥俩的官司时明显偏向他同学,面对李雪莲的案子时,觉得李雪莲来回折腾太麻烦,直接判她败诉;法院专委董宪法有职无权,是个整天蹭饭的大闲人,碰到来申诉且跟他纠缠不休的李雪莲,不仅骂她“刁民”,还轰走了她;法院院长荀正义,酒醉时碰到来告状的李雪莲,也骂她是“刁民”,并赶走了她;县长史为民路遇李雪莲拦车喊冤,他不问详情就把她推给县信访局长,县信访局长把李雪莲当闹事的“泼妇”轰走了;市长蔡富邦在创建“精神文明城市”的关键时刻,下令轰走李雪莲这只“大苍蝇”,使得李雪莲被关进拘留所7天。20年后,新上台的法院专委贾聪明急于立功升职,派赵大头“色诱”李雪莲,想终止李雪莲的上访,最后弄巧成拙,反使事情变得更难处理,升职不成还挨批。人名本身相关联的身份象征与行为举止之间的悖反所体现的反讽意味,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呈现出一种荒诞的效果。尽管刘震云在谈及文中的名字时这样说:“名字跟行业有关系,从事手工业的人,如果正处在民国时代,他肯定会叫王麻子。人物命名上我并没有有意怎么做,但是这些名字都汇聚到一块儿就出来另外一种荒诞的效果。我起名字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但出来的效果是荒诞的。”[6]但“枉公道”(王公道)、“似为民”(史为民)、“踩富邦”(蔡富邦)、“(不)懂宪法”(董宪法)、“除清廉”(储清廉)、“寻正义”(荀正义)和“假聪明”(贾聪明)等读来蕴含着文化批判的名字,暗示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寓有鲜明的讽刺意义,达到了独特的荒谬效果,亦承载了作者对官场文化的揶揄和嘲讽。
(四)结构反讽
“作为一种文体的序,其性质或功能是对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说明,或以议论为主,或以叙述为主,或二者兼备;其名称尚有‘引’‘题词’等”[7]。一般来说,序言部分是少于正文部分的。但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却打破了传统的序言与正文的结构模式,内容总共三部分的小说文本,其中序言部分占了两章,占小说的绝大部分,即全书287页,序言268页,正文不到20页。小说采用这样的序言长于正文的结构,别致、新颖,又引人深思。
序言部分写了63件事,件件都是围绕着李雪莲,围绕她的上访展开,写她上访的原因、曲折的过程和意外的结果,洋洋洒洒写了17万字;而在小说第三章正文部分,却撇开李雪莲去写被贬的官员史为民的经商和交往。序言部分看似主要在叙说故事,正文却像是尾声。但其实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史为民,而不是序言中的李雪莲。史为民之前在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李雪莲的案子意外被免职,后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名叫“又一村”的小饭馆,每天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又一村”似乎也在暗示史为民人生的柳暗花明,他摘掉官帽后的洒脱未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小说看似是李雪莲在追寻正义,其实还有像史为民这样的官员也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洋洋洒洒的序言和惜墨如金的正文似乎给读者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但作家恰恰是以“本末倒置”的叙事策略,以严重失衡的小说结构,来暗讽官场之弊对人性的扭曲与戕害。
序言里李雪莲的上访故事,作者写得极其琐碎,场景也非常开阔,一件家务事最后变成了国家大事,这本身是一件逻辑很荒谬的事,但李雪莲执着地以严肃对待荒谬,结果导致她的告状不仅失败,还随着秦玉河的死变成了一个笑话。小说的正文和序言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唯一的关联点在于“上访”。 正文中史为民在年关回北京买不到火车票,但又必须回家陪即将住院的老牌友打一次麻将,情急之下借用了李雪莲的模式,顺利回到了家还打了牌。史为民以荒诞应对荒诞,所以他成功了。序言和正文不仅是字数的对比,也是李雪莲和史为民上访结果的对比,就像正文标题“玩呢”,刘震云探寻的恰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
二、反讽修辞背后作家的思考
反讽修辞的多样化灵活运用,使刘震云在构建一个荒诞的艺术世界的同时,又把一个农妇耗费20多年上访的故事讲述得不紧不慢,轻松、诙谐的话语和荒诞的笔调背后传达的是作家冷静的思考。
(—)官场生态现状的反思
刘震云在他早期的作品《新兵连》《官人》《官场》《单位》以及后来的“故乡”系列小说中,多次或点或面地描写过官场百态,对权力崇拜的批判也一直是刘震云小说主题之一。《我不是潘金莲》几乎是一部别样的《官场现形记》,一个民妇上访的荒唐案子,不经意间再次“折腾”出了官场百态,反映了官场生态现状的恶化。
从法院法官王公道、法院专委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到省长储清廉,他们要么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么混日子、不管世事,要么惧怕有事、事来推事,没有一个是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如法院民事一庭的庭长老贾,知道李雪莲的案子难缠,李雪莲这个告状的妇女也难缠,他“害怕事情越说越多,说来说去,反倒把自己缠在里面了”[4]36,于是把麻烦推给了法院有职无权的专委董宪法;董宪法在明白有人背后给他挖坑后,没蹭到酒席的他,恼羞成怒,大骂李雪莲是“刁民”;已退休的老曹在喝完酒后碰上李雪莲来找法院院长荀正义告状,醉酒之际不忘摆出老领导的架势,叮嘱荀正义好好问一问李雪莲的案子,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荀正义嘴上答应老领导,内心却在担心如果自己现在不搭理李雪莲,老曹第二天酒醒后知道他阳奉阴违,自己就会因小失大,“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帮你忙是不可能了,但想坏你的事,他还是有能量的;他在台上那么多年,上上下下,也积累下丰厚的人脉,料不定哪块云彩下雨,就砸在了你头上”[4]45。市长蔡富邦在创办精神文明城市过程中,只顾忙着做一些表面文章,大搞形式主义,让人把来喊冤的李雪莲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关进了拘留所。副市长刁成信无视市政府门口静坐的李雪莲,把全部心思放在给市长蔡富邦使绊子上;正处在升迁关键时刻的省长储清廉由于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顺便提到李雪莲的案子,紧张之余把涉事官员全部罢免。20年后新上任的县长郑重软硬兼施,让李雪莲写保证书,硬把不想再告状的李雪莲又逼上了上告之路。新上任的市长马文彬为阻止李雪莲上告,甚至屈驾去镇上羊汤馆请李雪莲吃饭。可以看出,每个官员担忧的都是自己头上“政治云彩”的变化,为此他们勾心斗角,寝食难安。就像刘震云在《官人》中写的那样:“有劲不往工作上使,相互拆台,相互想看笑话,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8]无人去真正倾听一个农村妇女的诉求,民众上访制度成了现行官场规则中的摆设。
(二)底层女性现实处境的审视
刘震云坦承《我不是潘金莲》是他试图接近女性、以女性视角来表达对世界看法的一部作品。作品中李雪莲在维护自身生存价值时的诸多困惑以及最终“求生难安,求死无处”的尴尬窘况,也体现了作家对当代底层女性在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双重弱势地位的审视。李雪莲尴尬无助的境况是所有底层女性现实处境的一个缩影。
从表面上看,李雪莲是在求证一纸证书的真假,“其实是在维护其婚姻的合法性和伦理性,是在维护她在这片天地的合法地位”[9]。她作为一个底层女性,已经不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罗淑笔下的生人妻、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张弦笔下的菱花、孙犁笔下的水生嫂,她不再隐忍和软弱,而是胆大、泼辣、坚强、倔强和叛逆,她是一个具有鲜明女性独立意识的女性,她有着明确的对个体价值的追求。离婚由假变真,当这中间的诚信逻辑被扭曲时,李雪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漫长告状是在维护人的诚信和基本的道义。但她和秦玉河离婚手续的办理在制度层面都是合乎规范的,秦玉河的再婚也是合法的。她执拗地要求与秦玉河复婚再离婚,使她成了既有规范的破坏者,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泼妇”,她的种种申诉不仅荒诞可笑,而且在一个正义和话语权都被掌控在男性手中的社会,必然得不到任何制度层面的回应。从古到今,女性一直被视作沉默的“第二性”,她们无权在男权社会表达自我。而当以秦玉河为代表的男性竭尽所能企图使李雪莲失语时,李雪莲的反叛就是造反,是大逆不道,所以在他们眼里,李雪莲不是“小白菜”,不是“窦娥”,而是哪吒、孙悟空,是既有秩序的破坏者。
历史上,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处处留情,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恪守妇道。女性的婚前失贞被视作道德被坏,女性婚内的突围更是淫荡的行为,所以“潘金莲”才被视为荡妇的代言人,一直作为“好女人”的对立面而存在。如果顶着“潘金莲”的帽子,她是无法开辟自己未来的。因为“世上还有谁,愿意娶一个潘金莲呢”[4]70?秦玉河深谙此理,他用一顶“潘金莲”的帽子,轻而易举为自己甩掉李雪莲找到了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借口,同时也让李雪莲陷入“不贞”的泥淖中备受煎熬。李雪莲为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告状,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因为“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理论包含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都反映在与环境相关的父权制的实践和话语中”[10]。李雪莲急切地想对自我身份进行认证,可是又有谁会关注她的诉求呢?她试图用告状去冲破一个由男性构筑起来的写满他们自己话语的伦理道德的牢笼,她的失败暗示了这个牢笼坚不可摧。刘震云正是通过李雪莲一系列堂吉诃德式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底层女性在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双重弱势地位的忧思。
三、结语
刘震云是当代具有大智慧的小说家,他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当社会价值标准脱离正轨时,他便用反讽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引导读者在他构建的真真假假的故事中去联想、去思考、去反思。就像叶圣陶所说:“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所以我的期望常常包含在没有说出来的部分里。”[11]《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荒诞不经故事,涉及上访、生二胎这些当下社会的敏感话题。刘震云借助反讽,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阐述了当今社会的生活逻辑和社会思维。在叙述时,刘震云极力隐退自己的声音,用多样化的反讽修辞揭露了官场丑陋的众生相,表达了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寻找正义之艰难的同情,以及对官员们忽视民间疾苦、漠视民众、与民对立的愤慨。同时,反讽手法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运用,使小说具有幽默、戏谑、调侃的成分,少了些尖锐的批判,多了些隐蔽与含蓄,作品的艺术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也有了多层次的审美意蕴。
[1]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26.
[2]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5):105-111.
[3]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82.
[4]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5]黄擎.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13-116.
[6]刘颋.一个作家身后的“蓄水池”:刘震云访谈[J].朔方,2013(2):99-104.
[7]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78.
[8]刘震云.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4.
[9]王萍.个体价值的追寻与审思:以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为例[J].文艺争鸣,2015(3):163-168.
[10]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11]刘增人,冯光廉.叶圣陶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