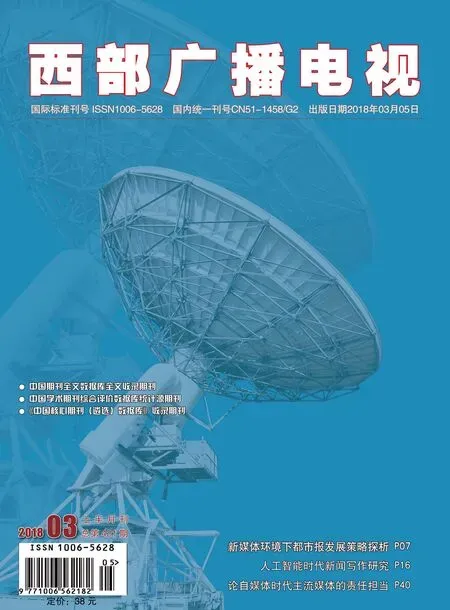张力叙事视角下谍战剧的效果增值
2018-02-22王博林
王博林
谍战剧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学者郝建认为,谍战剧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电视剧类型,它将侦探剧的逻辑﹑悬念等观赏元素和惊险片中主人公身处危险中的兴趣点,与主旋律电视剧需要的思想内涵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观赏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将谍战剧定义为以间谍活动为主题,包含卧底﹑特务﹑情报交换﹑悬疑﹑爱情﹑暴力刑讯等元素的影视剧。近几年,消费奇观驱动下谍战剧的“鲜肉”化﹑暴恐化以及世俗化让观剧行为退化为“一次性消费”。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从谍战剧艺术魅力的根源“张力”着手。
1 实现叙述效果陌生化
艺术并不是对现实的复制。张力叙事下的谍战剧文本,在故事构建与讲述方式上都超越了常事﹑常情﹑常理,让受众收获感官刺激与情感震动,进而达到叙述效果陌生化。因此,对审美距离的恰当把握成为谍战剧创作者需要观照的方面。在《伪装者》中:明楼既是共产党阵营的“眼镜蛇”,也是国民党军统高管“毒蛇”,同时还在汪伪政府中担任经济司要职,三重标签下的明楼复杂得几乎难以辨认,让观众追问到底哪个才最真实。另外,对专业谍战工作的影像化再现同样能为受众带来独特体验:如收发电台信息﹑“花式”密报传递﹑出家门前要往地垫上洒炉灰﹑随时注意并拆解监听设备﹑常用拷问与刑讯手段﹑伪造身份的技巧。
悖论的运用同样能产生这种效果。在《潜伏》女主人公左蓝的心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信仰和工作。而余则成的信仰就是左蓝,他只想和恋人在一起过上平凡生活,其加入共产党更是为了左蓝。可事与愿违,左蓝为掩护余则成和翠平悲壮牺牲,余则成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当信仰消逝,他何去何从?剧中给出了这样的悖论式答案:为自己深爱的女人所坚信的信仰,余则成选择继续潜伏下去。相似地,《伪装者》中九死一生,被生活蹂躏得冰冷﹑麻木的于曼丽,在明台的引领下结束西绪弗斯式悲剧命运,经历凤凰涅磐,重燃对生活的渴望。《悬崖》中性格冷静缜密的周乙为防止身份暴露果断枪杀年轻有为﹑对其信任有加的任警官,都是悖论的显现。
2 促进文本意义衍生
谍战剧中的对白﹑人物﹑声音﹑画面都是能指。所指则是一个心理概念,是被表示者。谍战文本中传递和演绎的任何意义都是所指。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在约定俗成中被规定,但并不是必然的。一个能指可以对应多个所指,张力叙事让这种意义衍生成为可能。
在《潜伏》中,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李涯被塑造为与余则成一样具有坚定信仰与卓越才能的人物。尽管他是军统特务,可有评论说李涯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角色”,同样是“智勇双全的爱国志士”。这种情况在传统反特片及谍战剧中是难以想象的。以《潜伏》举例,有人从中读出了“办公室哲学”,有人读出了“爱情圣经”,也有人读出了“幽默段子”……对职场桥段﹑爱情故事与幽默话语的客观呈现平行于宏大国族叙事,为受众提供了想象空间。
3 激发个性化力感体验
张力美感是一种“虚化的心理力感形式”,于各种张力结构中孕生。张力机构中对立的两极之间相互抵牾﹑摩擦,却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和谐统一之态。《伪装者》中,明楼为了不使自己暴露身份痛扇大姐耳光;《潜伏》中,余则成与革命恋人翠平相濡以沫却相忘江湖;《黎明之前》中,刘新杰为营救“水手”将弟弟阿九亲手送上绝路;《悬崖》中,已经脱险的周乙,为了战友顾秋妍及其女儿的安危重返险境献出生命……这些情节都强烈激发了受众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剧体验。
除此之外,对刻板人物形象的新式呈现也能激发受众的思考与回味。《潜伏》中的李涯被塑造成与余则成等共产党员同样智勇双全的谍报人才及爱国志士,虽然存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诉求的可能,却为受众提供了窥视真实历史镜像的窗口;《伪装者》等剧中对我党转变者形象的塑造,不仅为受众展现了战争年代的人性真实选择,更提出了义利生死等更深层次的悖论命题,即反面人物虽抱得金钱权利,却在道义精神上缺位。正面人物为民族大义压抑个体真实欲望﹑在“圆梦”的同时,个体诉求似乎却从未得到观照。
参考文献:
[1]白小易.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2]陈杨.新世纪谍战题材电视剧研究[D].徐州:江苏师范大学,2014.
[3]桂璐璐.论毕飞宇小说《推拿》的张力叙事[J].吕梁学院学报,201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