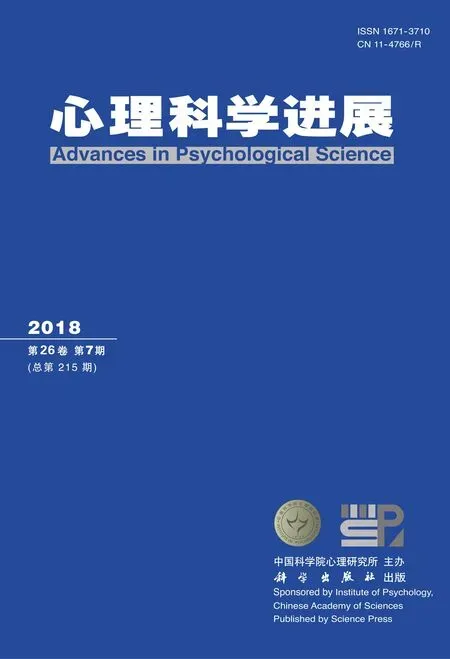手写体文字识别的特点及神经机制*
2018-02-22任晓倩
任晓倩 方 娴 隋 雪 吴 岩
(1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评定与培养协同创新中心, 大连 116029)(2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长春 130024)
1 问题提出
文字材料可以呈现为手写体文字和打印体文字, 而手写体文字作为早期文化流传的重要载体,曾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打印体文字的出现, 手写体文字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打印体文字相对规范, 相同词汇经过多次打印, 可以做到其形状基本不变, 其中的细微差别很难用肉眼发现。手写体文字有区别于打印体文字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 手写体文字大小不一, 结构多变, 而且与书写者的书写风格及书写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手写体文字不可能完全被打印体文字取代, 在小学生识字过程中, 学习文字书写是他们的必经阶段, 也是个体内化汉字及其文化的过程。此外, 手写体文字的书写及其阅读需要通过大脑的监控, 并且还涉及到语言和视觉处理的复杂过程(Dehaene, Cohen, Sigman, & Vinckier,2005), 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方块文字还是拼音文字, 其手写体形式和打印体形式都有明显差异, 具体表现在文字物理结构、文字相似性、书写风格等方面。文字复杂的物理结构使得手写体文字相较于打印体文字有更多噪声, 例如笔画模糊不清、连笔、畸变、倾斜等。文字间的相似性也使手写体文字识别区别于打印体文字, 例如“人、入”、“辩、辫、辨”、“未、末”等相似的汉字, 当个体不能规范书写时,手写体文字的识别过程将会变得困难。另外, 手写体文字相较于打印体文字, 其书写风格多变,无规律可循, 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现今, 大多数词汇加工理论和模型都是围绕打印体文字的研究结果构建的。比如E-Z读者模型(E-Z Reader Model), 该模型认为, 词汇识别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早期的熟悉度筛查阶段(L1)和晚期的词汇通达阶段(L2) (Reichle, Pollatsek,Fisher, & Rayner, 1998)。在早期熟悉度筛查阶段,词汇的注视时间受词汇熟悉度影响, 熟悉度高的词注视时间短, 熟悉度低的词注视时间长; 在晚期的词汇通达阶段, 注视词加工完成后, 注意将转移到下一个单词, 并触发眼跳, 开始新的注视(Reichle, Pollatsek, & Rayner, 2006)。再比如SWIFT模型(自发眼跳−中央凹抑制模型, Saccadegeneration With Inhibition by Foveal Targets, 简称SWIFT模型), 该模型认为:(1)加工时提取的词汇信息分布在注意窗口上; (2)扫视时间与扫视目标的选择是分离的; (3)扫视生成过程是一个自主(随机)过程, 该过程受中央凹目标词的抑制。这一模型认为注意在注视广度中呈不同梯度分布, 其中加工程度最深的是位于中央凹的词汇, 而两侧词汇随着与中央凹的距离增加其加工梯度随之下降,但新的注视往往取决于中央凹词汇加工的结果(Engbert, Longtin, & Kliegl, 2002)。
研究者们也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对手写体文字的阅读进行了研究。Bub, Arguin和Lecours (1993)探究了阅读的神经基础是否与视觉皮层有关, 阅读是否依赖视觉信息并将其嵌入到语言系统等问题。他们发现, 当给失读症患者(左侧枕叶损伤)呈现一段句子材料时, 患者能够正确书写并理解其具体含义, 但是不能进行阅读。他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文字识别加工过程由视觉中枢与双侧枕叶通过协同作用完成, 而枕叶损伤将会破坏视觉信息与语言系统间的联系。另外,Wandell, Rauschecker和Yeatman (2012)研究了快速识别书面文字的过程。当被试加工熟悉度高的单词时, 主要依赖大脑皮层一系列的正确处理,所涉及的脑回路主要包括:局部大脑皮层(涉及视觉和语言加工的腹侧枕叶区域)及其连接的白质束, 并且在该处理阶段以时间顺序进行加工。另一方面, 视觉词汇识别过程要经过通达字词正字法表征和通达意义两个阶段。由于该过程与书写系统有共同的正字法表征, 所以被称为共同表征假设。研究表明, 书写过程中不正确的正字法表征在阅读时不能被准确理解(王成, 尤文平, 张清芳, 2012)。但是, Guan, Liu, Chan, Ye和Perfetti(2011)则认为阅读和书写两者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通过某些第三变量互相联系的,例如正字法知识、语音记忆能力等, 这表明额外变量可以显著地影响阅读和书写技能。Magrassi,Bongetta, Bianchini, Berardesca和Arienta (2010)等人发现, 刺激混合性失语症(拼写错误, 键盘录入困难)患者上顶叶的有限区域时, 会引起患者在拼写任务中的书写错误, 这种电刺激引起的书写错误与其接受刺激前的自发性书写错误相比较,其阅读理解能力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书写与阅读相互独立。
综上所述, 手写体文字与打印体文字在形态大小、字体结构等物理特性方面确实存在明显差异。那么, 手写体文字加工有什么特点呢?手写体文字加工的神经机制与打印体文字有哪些不同呢?已有的理论模型能不能很好地解释手写体文字的阅读呢?
研究发现, 识别难度大的字体会使阅读策略发生改变(Rayner, Reichle, Stroud, Williams, &Pollatsek, 2006)。宫殿坤、郝春东和王殿春(2009)研究了不同汉字字体对视觉搜索的影响。实验发现, 阅读宋体字的反应时明显比楷体字的反应时短。他们将该实验结果解释为, 相同字号的宋体字与楷体字相比, 在印刷时或屏幕上呈现时, 宋体字笔画更粗、字体更大, 更便于视觉搜索。另外, 他们还提出, 不同难度的刺激材料和不同难度的实验任务所对应的视觉搜索方式和信息加工模式(包括编码, 存储, 受控搜索/自由搜索, 和匹配过程)也不同, 即识别简单材料和完成简单任务只依靠本能, 其信息加工模式只涉及自由搜索阶段; 而识别困难材料和完成困难任务则需要依靠本能和意识, 信息加工模式涉及受控搜索阶段。陈琳、钟罗金、冷英和莫雷(2014)等人考察了汉语拼音的自动加工与语义加工对汉字字形激活的影响, 实验发现, 当进行拼音自动加工时, 汉字的字形信息未被激活; 而进行拼音语义加工时, 汉字字形信息被激活。这一结果与宫殿坤等人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 由于拼音基本不会出现在汉语母语者的阅读材料中, 所以其自动化加工程度较低, 因此, 加工拼音会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在手写体文字研究水平上, 沈模卫和朱祖祥(1995)发现, 打印体文字和手写体文字加工时的视觉特征提取存在差异。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 在字形识别系统中存在文字和文字特征相对应的觉察器网络。识别打印体文字时, 打印体文字的特征觉察器与相对应的字觉察器之间传递兴奋, 促进整字识别; 手写体文字识别时, 在字水平上不存在与打印体文字相对应的字觉察器, 所以对应的特征觉察器不能受到来自字的激活。可见, 随着文字识别难度增加, 文字加工系统会由自动加工转变为有意识参与的加工, 这种加工方式的转变使打印体文字与手写体文字在识别上存在很大差异。
研究者还对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手写体文字进行了研究。Perea, Gil-López, Beléndez和Carreiras (2016)等人以西班牙文字为实验材料研究了手写体文字的加工特点, 他们发现, 与打印体文字和简单手写体文字相比, 困难手写体文字的阅读成本更高(即更多的注视, 更长的注视持续时间和更短的眼跳距离)。Dinges, Al-Hamadi,Elzobi和 El-etriby (2016)等人通过研究阿拉伯手写体文字发现, 在书写过程中, 有些单词的字母会被省略。那么, 与阅读打印体材料相比, 如果阅读包含省略字母的单词的手写体材料时, 读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上下文信息, 来识别阅读材料。
这些研究表明, 手写体文字的加工机制与打印体文字的加工机制可能存在差异。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手写体文字识别的研究, 可以发现, 识别手写体文字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影响因素。另外,神经机制的研究可以揭示加工手写体文字与打印体文字时, 其大脑机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种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加工过程, 也有助于判断各种理论模型对手写体文字的解释能力。
2 文字物理特性对手写体文字识别的影响
2.1 文字的结构特征
文字结构是由文字的符号形式、语音、语义三者联系起来组成的, 是具有一定社会文化意义的结构范畴。其中, 汉字主要是由点和直线组成的方块字。汉字以平面布局的形式表达语音和语义信息。打印体汉字的笔画部件之间是相互协调的, 而手写体汉字的笔画结构灵活, 当其横竖笔画的组合方式、长短和分布位置不同时, 字形就会有不同表现形式。手写体汉字有较大的随意性,一定程度上使其结构更加多变, 字形更加复杂。拼音文字的字母主要是由直线和圆弧组成的几何结构, 不同字母的外形不同, 有些字母有超出或低于其主体的部位, 增加了识别难度; 字母间的间隔随着字母形状不同而发生变化; 字母之间存在大小写的转换等特点。这些文字结构特征在以手写体文字形式呈现时可能会被放大或缩小, 进而影响文字的加工识别过程。
在识别加工过程中, 无论打印体文字还是手写体文字, 笔画数及笔画类型都会影响汉字的整体识别。与打印体汉字相比, 手写体汉字受书写者的书写习惯影响, 其笔画存在较大变异, 所以笔画对手写体汉字识别的影响更大。尤其当书写中出现连笔现象时, 会导致字体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 增加识别难度。不过, 即便字体结构存在如此大的变异, 熟练的读者依然可以顺利地对其进行识别。
对此, 金连文(2016)等人指出, 在汉字识别时, 存在“整体优先”的原则(视觉检测是一个由整体到局部的过程), 因此, 读者也能识别局部缺失的汉字。王静、薛成波和刘强(2018)也认为处理视觉信息时, 首先对物体的整体特征进行记忆提取,然后再分别完成物体各部分特征的再现, 这样有利于提高加工效率。手写体文字虽然在物理特性等方面与打印体文字有明显差异, 但是作为汉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依然具有汉字的基本属性。汉字依靠形体结构表义, 这里的结构通常指感知的整体, 对结构的解析过程意味着文字识别进入高级认知阶段。基于汉字整体结构的规定,各结构成分间相互依存, 离开了结构的整体框架,成分的功能无法实现(臧克和, 2006)。常玉林、王丹烁和周蔚(2016)研究中将汉字部件位置和内容错误作为实验变量, 观察被试对整体或局部属性遭到破坏的文字的敏感性。他们发现从眼动指标来看, 在文字加工的早期阶段以特征加工为主,晚期阶段则呈现整体加工的趋势; 从反应时指标上看, 整体加工是文字加工过程的主要方式。由此可以推测, 整体加工和特征加工都参与手写体文字的识别。
除了笔画数, 汉字的偏旁部首对词汇识别过程的影响也很大。汉字部首位置不同, 所提供的信息和其重要性也不同。多层次激活模型(multileve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MIA)认为, 汉字结构中的笔画层次、偏旁部首(部件)层次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 笔画层次信息中包含了笔画间的相对位置信息; 部件层次信息中包含了部件间的相对位置信息。MIA本质上是从特征加工角度揭示汉字识别中的笔画、偏旁部首和字体间的关系(管益杰, 李燕芳, 宋艳, 2006),这与“整体优先”加工策略观点不同。Corcoran和Rouse (1970) 的研究结果再次证明了打印体文字和手写体文字的识别过程存在差异。与打印体文字相比, 手写体文字的变异性更高, 识别过程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Barnhart和Goldinger(2010)则认为, 在感知手写体文字时, 读者会自然地适应这种书写方式, 并且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反馈使手写体文字字体结构模糊性缺陷所带来的影响减弱。曾捷英、周新林和喻柏林(2001)研究了经过劣化处理(对汉字进行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压缩)的汉字, 改变汉字的通透性, 提出了通透性中介假设, 即字形属性不直接影响文字识别, 而是以文字通透性作为中介间接影响文字识别。通透性中介假设可以用来解释笔画类型效应和部件位置效应。该假设可以解释各种字形属性效应产生的原因。那么,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是否可以用通透性中介假设来解释呢?尽管, 手写体文字与经过劣化处理的文字在字形属性上存在相似特征, 但是, 劣化处理的文字是经过水平或垂直压缩的, 其变化方式遵循一定规则, 与手写体汉字的变异性是不同的, 因此, 通透性中介假设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手写体文字识别。
除了文字的笔画数及其结构的影响外, 正字法深度也会影响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正字法深度(Orthographic Depth), 是指字体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深的正字法容易使读者使用视觉码(如字母特征、序列和字符空格等)来加工词汇, 而浅的正字法容易使读者采用表面音位策略(能够借助文字的声符实现语义通达)。由于汉字的正字法深度比拼音文字深, 读者就容易使用视觉码加工词汇, 识别词汇所消耗的时间比拼音文字短(印丛, 王娟, 张积家, 2011)。Chen和Cherng (2013)以中文手写体词汇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影响汉字识别过程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语素(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 是词语的组成部分)对汉字识别有预测效应, 笔画则对其没有预测效应。在他们提出的关于中文手写体文字的加工模型中, 只有部件和语素被看作是功能单元(手写体文字的处理单元), 而笔画在文字加工中只发挥微弱作用, 因此笔画对汉字识别的预测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在阅读汉字时, 颞叶和前侧顶叶会被激活, 并将文字以图形的方式映射到词素和音节水平上(Perfetti & Tan, 2013), 这说明, 汉字以类似图形的方式进行加工。上述结果表明, 手写体文字的加工具有书写系统变异的普遍性。Zhang和Feng (2017)通过实验检验了偏旁部首和词法对汉字手写体文字的影响。他们认为, 在书写过程中若排除其他因素, 只考虑文字的笔画因素, 多笔画条件下的书写速度比少笔画条件下慢。汉字部件复杂性也会影响书写过程中的书写速度和非笔画的移动速度(非笔画长度与时间间隔之比), 尤其在书写分布在部首边界的笔画时, 书写速度明显减慢。由此可见, 手写体文字加工的中央处理和外围处理过程受词法和部件复杂性影响。
手写体文字物理结构的特殊性区别于打印体文字, 导致了加工上的差异, 接下来将探讨手写体文字的文字结构与非文字图形识别相比有何差异。Tan, Spinks, Eden, Perfetti和Siok (2005)发现在书写运动系统(受书写运动与言语刺激共同作用的促进文字表征的认知系统)中, 假字识别和其他涉及精确协调的运动(绘画)也与阅读有关, 但在一定程度上, 绘画要求更高的阅读表现能力。在识别简单图形(圆形或者三角形)时, 其物理特征能够被无意识加工, 甚至还能达到语义加工水平(柯学, 白学军, 隋南, 2004)。这与手写体文字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有所不同。关于视觉图形加工, 柯学、白学军和隋南(2008)认为图形的局部形状特征加工与整体形状加工会相互影响。一方面,当注意落到局部形状特征时, 语义图形的意义将被激活, 但是该过程将会抑制整体形状信息的加工, 另一方面, 对图形整体形状信息的优先加工会干扰对局部形状信息的加工。在手写体文字中,笔画、部首、字母等作为文字组成的一部分, 对文字识别加工过程的影响是单向的, 即文字的局部特征对整字识别有影响。周爱保、张学民、舒华和何立国(2005)认为文字识别时, 会经历字体形状与经验中熟悉的心理模型相匹配的过程。而在识别简笔画类型的图片时, 个体也要先搜索已有的经验图式, 才能进行有效识别(胡学平, 孙继民, 曹蕊, 姚温青, 王美珠, 2014)。因此, 手写体文字的加工过程既有特异性, 又有与非文字图形加工过程的共性。
总之, 文字物理结构的复杂性使个体在识别加工手写体文字时表现出区别于识别打印体文字的过程。手写体汉字的偏旁部首和其位置信息变化导致的字体总变异需要更多自上而下的加工参与, 增加了识别难度, 延长了识别时间。
2.2 文字的书写风格
每个人的书写习惯和书写方式不同, 所以写出的字体风格也不尽相同。因此, 在研究手写体文字识别时, 要考虑到手写体文字的书写风格对手写体文字加工的影响。金连文等(2016)提出在汉字识别过程中, 汉字的识别程度与个体的阅读水平和对字体的熟悉程度有关。由于书写风格不同,有的手写体汉字连笔较多, 有的连笔较少。对连笔汉字不熟悉的个体, 较难识别这类手写体汉字。另外, 手写体汉字的倾斜度也会影响汉字识别。Vajda, Ranqoni和Cecotti (2015)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旋转简单字符的形状不会改变该字符所代表的含义。但是, Dinges, Al-Hamadi, Elzobi,El-etriby和 Ghoneim (2015)等人发现, 在加工单个字母或由字母组成的单词时, 旋转会扰乱单词和文本行的识别过程。Qiao等 (2010)等人在大脑激活水平上进行研究也发现, 无论是阅读简单手写体文字还是困难手写体汉字, 旋转都对文字的语义识别具有显著影响。对此, Barnhart和Goldinger (2013)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研究, 探究了手写体词汇向任意方向旋转90°时的加工特点。他们发现, 手写体文字旋转会造成感知不对称, 在对比了打印体文字与手写体文字沿不同方向旋转后发现, 沿顺时针方向旋转比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对词汇识别的影响更大。另外, 他们还指出, 当手写体文字的旋转方向与其内部特征相反时, 被试往往不能对词汇信息进行感知。
文字的书写风格也受文化的影响, 进而影响手写体文字的识别。Diaz-Cabrera, Ferrer和Morales (2015)在研究西方人签名的具体特征时发现, 大部分人的签名呈现整体椭圆轮廓, 且右侧部分略小于左侧部分。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书写是从左向右的顺序引起的。另外, 他们还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个体展示其签名的形式不同。例如, 有些地理区域的人, 倾向于写下全名和姓氏, 有些则偏向于用字母缩写代替。Rosso,Ospina和Frery (2016)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签名的形成涉及到大脑从长期记忆中恢复信息这一过程,但是该过程不涉及提取字体细节特征(例如:大小,形状等)。所以, 个体的签名风格一旦确定之后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不同个体书写的字符形状和大小存在不均匀性, 倾斜存在不同程度, 导致识别难易不同(Mukhopadhyay, Singh, Sarkar, & Nasipuri, 2018)。因此, Qiao等 (2010)基于行为实验将实验材料进行了区分, 即简单手写体和困难手写体(书写规范和书写不规范)。他们发现在识别困难手写体时,需要额外的注意参与自上而下的加工, 并且在手写体文字加工的早期阶段, 词汇信息对处理模糊视觉刺激起着很大作用, 而困难手写体文字的词汇信息提取较难, 导致该阶段阅读成本增加。Qiao等人的实验表明, 困难手写体文字识别所需的连续注意只有在有意识地识别目标词时才能被触发。另外, 他们认为不管是识别困难手写体文字还是简单手写体文字都不存在行为启动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困难手写体文字的识别缺乏自动性,而且不参与注意驱动的串行解码; 另一方面, 是由于简单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对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 所以视觉系统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处理。但是, 关于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时间比打印体文字的识别时间长这一问题, Perea和 Gil-López等(2016)认为, 这是因为在识别困难手写体文字时,呈现出的词频效应比简单手写体文字和打印体文字的更加显著; 并且识别手写体文字时, 会出现阅读成本, 再加上文本和词频效应的相加性, 所以,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时间比打印体文字的识别时间长。
关于书写风格对字迹(文字书写时的笔画形体)识别影响的研究发现, 手写体文字的整体书写风格对文字的识别过程有显著影响, 其影响具体表现在反应时和准确性上, 当书写风格不一致时,识别时间更短, 准确性更高。大多数研究者将此解释为, 被试利用书写风格间的显著差异快速判断前后字迹是否具有一致性, 也就是说, 书写风格一致性越高, 要获取的字体特征信息越多, 反应时就越长(黄志平, 2012)。关于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模式, 结合阅读实验中的各种眼动指标的分析后发现, 在手写体文字识别过程中优先使用整体识别策略, 当使用这种策略识别失败时, 会采用图像识别策略, 即识别单个字迹的具体特征, 再次印证了手写体文字识别加工受整体加工和特征加工的共同作用。
综上所述, 手写体文字模糊的物理结构, 多变的书写角度, 书写不规范性等因素使其加工识别方式与打印体文字存在差异。手写体文字模糊的物理结构主要影响语义加工过程, 结构改变越大, 识别难度越大, 语义加工花费时间越长; 书写角度则主要影响视觉信息的提取过程, 当手写体文字书写角度与文字的内部表征相反时, 对视觉信息提取越困难; 书写风格影响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加工过程, 具体表现为困难手写体比简单手写体和打印体有更大的阅读成本。
3 文字语言特性对手写体文字识别的影响
3.1 文字的词汇特性
文字在语言中的应用以词汇为主, 文字通过词汇特性展现其作用, 即词汇效应。词汇效应按照词汇的具体特性可以分为:笔画数效应、正字法相邻效应等; 按照语言因素分类包括:词频效应、预测性效应、熟悉度效应、语义透明度效应等。De Zuniga, Humphreys和Evett (1991)认为在词汇水平上, 打印体词汇和手写体词汇的识别存在词频效应(低频词加工比高频词加工更困难, 更费时间)。Perea 和 Gil-López 等(2016)认为, 手写体文字词频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手写体文字固有的物理变异性或者难以加工的模糊字形。他们发现实验材料的质量(一种感知因素)对词频效应有影响。同一文本内容下, 实验材料质量越差,阅读中的词频效应越显著, 即手写体文字会放大阅读中的词频效应, 低频手写体文字相对于高频手写体文字和打印体文字有更大的词频效应, 这是因为实验材料质量和词频作用于文字识别加工的不同阶段, 实验材料质量影响文字识别加工的早期阶段, 而词频影响文字识别加工的晚期阶段(Balota, Aschenbrenner, & Yap, 2013)。也就是说手写体文字的物理变异性和模糊字形对词汇效应都有影响。不过, Coltheart, Curtis, Atkins和Haller(1993)等人通过词汇命名实验发现, 只有在命名低频词时才出现词频效应。Perea, Marcet, Uixera和Vergara-Martínez (2016)通过分析被试阅读手写体句子和打印体句子时的眼动指标(包括凝视时间, 首次注视持续时间, 总注视时间等)后发现,困难手写体的词频放大效应主要表现在晚期眼动指标(总阅读时间)上; 困难手写体句子中的目标词有更高的回视概率, 但与总阅读时间没有显著交互作用, 仅通过时间与总阅读时间有显著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 困难手写体的词频效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重读的累积效应。
Barnhart和 Goldinger (2010)以 De Zuniga 等(1991)的实验为基础, 在实验中, 增加了相应的实验条件, 发现(1)在手写体文字条件下, 模糊的视觉特征使词频效应增加; (2)当词汇以手写体形式呈现时, 低频手写体词汇产生的词频效应明显大于高频手写体词汇和打印体词汇, 高频手写体词汇与打印体词汇的词频效应相比无明显差异。总之, 词汇的词频对手写体词汇识别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是由字体的分布偏移和倾斜造成的。阅读时, 高频词常以打印体文字形式呈现, 因此, 当相同的高频词以手写体文字形式出现时,往往不能直接实现词汇通达, 读者会固着于打印体文字的识别模式, 对手写体文字的字形特征进行再判断。
另外, Perea和Gil-López等(2016)在仔细分析了反应时和反应时分布认为, 手写体文字的物理特性更多地依赖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当手写体文字的物理模糊性较高时, 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词汇效应会被放大(Barnhart & Goldinger, 2010)。另外, 由于手写体文字形状多变, 没有典型特征,与打印体文字自下而上的加工相比, 完成词汇通达需要更长时间(Qiao, et al., 2010)。
Perea和Marcet等(2016)在分析眼动指标时发现, 不同文本类型目标词词频效应的差异主要反映在晚期眼动指标上, 即在总注视时间上有显著差异, 手写体文字的总注视时间明显比打印体文字的总注视时间长。De Zuniga等(1991)将手写体与打印体间的整体差异归因于发生在字母水平上的“规范化加工”, 即当整体与特征在加工过程的视觉环境中相互作用时, 会随着视觉环境的改变变换其加工方式的过程。他们认为, 当阅读难处理的手写体文字时, “规范化加工”将发挥作用, 所以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额外加工成本会使阅读手写体文字的总注视时间变长。Barnhart和Goldinger(2015)通过词汇命名实验范式检验了四种不同条件下的字体(包含打印体和手写体), 实验结果表明, 打印体条件和手写体条件正字法相邻效应(The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effect, 即相邻的词汇越多, 目标词的识别速度越快)都稳定存在,但是, 手写体文字的正字法相邻效应则比打印体文字的更加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手写体文字字形结构的不稳定性和相邻手写体文字字形的熟悉度会影响正字法相邻效应。
3.2 文字的语境特性
手写体词汇的识别加工研究之后, 逐渐将研究方向扩展到了手写体句子的研究上, 并且, 发现阅读语境对手写体文字加工也会产生影响。Perea和Marcet等(2016)将嵌入高频词和低频词的手写体句子作为实验材料, 详细记录并分析了被试的眼动数据, 揭示了手写体句子与打印体句子在阅读时的差异。他们认为在句子阅读的总体水平上, 手写体句子的阅读成本比打印体句子的阅读成本更大, 需要的注视时间更长。在局部水平上, 句子中的手写低频目标词的注视次数比手写高频目标词和打印体的高/低频目标词的注视次数多, 但手写高频目标词与打印体的高/低频目标词的注视次数无明显差异。
Dinges等(2016)考察了不同文本条件下, 文字识别的策略。他们发现, 识别手写体文字时读者主要采用分割决策策略, 这种策略指, 文本中相邻文字合并识别的方法, 若其中一种合并方式识别失败, 则会尝试其它合并方式, 直到识别成功为止。Dinges等(2015)认为在涉及手写体文本识别任务的上下文中, 被试会选择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由于特定的语境能够消除文字识别过程中的歧义干扰, 所以, 当识别手写体文字时, 阅读语境作用于手写体文字识别的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 缩短了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时间(Barnhart &Goldinger, 2015)。总之, 他们认为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受到前后语境的影响。
文字的语境特性的习得受视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共同影响。Gordon, Spivey和Balasubramaniam(201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运动系统与文字的习得相关, 说明运动系统影响包括手写体文字在内的书面语言的学习过程。文字识别中, 视觉系统对文字进行提取和加工, 同时运动系统也影响文字识别。个体在学习文字过程中, 要经历一个手写文字的过程。手写的动作产生了对所写文字的视觉空间记忆和书写运动记忆。这种运动记忆在不断的书写练习强化下转变为长时记忆, 由于该记忆是与视觉表征相联系储存的, 所以, 在知觉文字和字符识别的过程中会激活手写的运动记忆(Cao et al., 2013)。Li和 James (2016)通过儿童书写训练的实验研究揭示了, 在书写过程中, 由于运动与感知系统存在直接联系, 书写动作实际上会增强被试对书写内容的理解。也就是说, 手写与文本内容间的联系是由脑−躯体−环境相互作用引起的, 环境信息输入系统造成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发生改变, 表现为运动系统对手写体文字的作用比打印体文字的作用更大。
综上所述, 手写体文字的视觉模糊性特征放大了词频效应, 具体表现为, 低频手写体词汇比高频手写体词汇更难识别; 手写体文字的字形结构和字形熟悉度使其正字法相邻效应比打印体文字更显著; 文字的语境通过消除阅读中的歧义来影响手写体文字的加工过程。与打印体文字识别相比,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受到语言特性更大的影响。
4 手写体文字识别加工的神经机制
关于文字识别的神经机制, 有关打印体文字的研究表明, 语言加工(包括文字和口语的识别)和语义记忆检索(包括分类和生成)主要集中在左前额叶和颞叶区域。这些区域的大脑活动也与文字理解和语义通达有关。其中, 文字理解将激活左颞叶区域, 语义通达激活前额叶皮层(Cabeza &Nyberg, 2000)。研究认为视觉“词形”的具体身份识别区域位于左内侧纹外皮层, 中间颞叶皮层,或左颞叶和梭形脑回。王磊、杨丽川、孟千力和马原野(2018)认为由视网膜、上丘脑、丘脑结节和杏仁核构成的视觉皮层下通路负责对视觉信息的整体性质进行快速加工处理。但是, 不同形式的书面文字, 大脑的激活区域和激活模式存在差异。在汉字书写中, 笔画和部件作为文字的内部结构会形成一种高阶组织, 该过程将手写的运动模式与语言相联系, 有利于形成关于汉字书写动作的长期记忆, 这种运动记忆将促进认知系统对文字表征的巩固过程, 并且不会干扰手写体汉字内部结构的识别(Tan et al., 2005)。当被试阅读文字时, 手写体文字也会激活手写过程的动作加工(李辉, 王晶颖, 2016)。一方面, E-Z读者模型认为,在L1 (文字的熟悉度检验阶段)阶段, 注意参与将视觉信息由视网膜传送到大脑皮层的过程, 继而调动手写体文字书写笔画、部件的运动记忆, 使其参与手写体文字的熟悉性程度的判断过程。另一方面, E-Z读者模型认为早期的视觉信息被平行加工, 通过注意所获取的视觉信息对之后的加工都有效(胡笑羽, 刘海建, 刘丽萍, 臧传丽, 白学军, 2007)。而手写体文字的物理特性会影响整体的感知, 所以相对于加工相同数量的打印体文字, 其加工时间更长。Bolger, Perfetti和Schneider(2005)通过元分析技术研究发现, 书写系统会激活一个强大的脑皮层区域网络, 这个网络主要是由大脑皮层中的三个区域构建而成:(1)左上颞叶后回(中/前部; BA22); (2)左下额叶回(上后区BA6); (3)左枕叶后回(两部分:后梭形/下枕骨区域[BA19]和中间梭状回)。另外, 由于不同种类的视觉刺激在高阶视觉水平上共享潜在的神经回路,所以尽管单个的书写系统对应某一类视觉刺激,也不能否认视觉信息与书写系统存在紧密联系。Longcamp, Anton, Roth和Velay (2003)等人发现,当个体看到字母时, 手写过程中的动作加工被激活。Tan等(2005)通过研究儿童学习过程后发现,在书写过程中, 儿童会将文字分解成特定的笔画和部件, 然后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成新的语言单位。他们假设书写会促进正字法意识的发展, 进而对阅读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MIA认为, 汉字加工有处理正字法信息和处理语音信息的两条通路, 其中正字法通路负责加工笔画、偏旁部首等部件层信息, 各层之间包含大量由不同单元构成的联结。当汉字以视觉方式呈现时, 将从笔画、部件到整字依次被激活, 直到整字激活到达阈值,汉字即被识别(严建雯, 孙善麟, 2005)。这就解释了在学习汉字过程中, 儿童通过文字笔画、部件的分解和重新组合过程逐渐形成正字法意识, 并在视觉系统和运动记忆系统形成记忆的原因。但是MIA的本质是特征加工, 没有详细解释文字识别的整体过程, 并且它遵循自上而下每次加工一个输入项目的原则, 而手写体文字既包含自上而下加工, 又包含自下而上加工, 因此, MIA不能完全解释手写体文字识别加工过程。Magrassi等(2010)研究了失写症患者关于文字加工的神经机制。失写症一方面指在书写中字母形状良好但拼写不准确; 另一方面指书写时字母形状不规范并且无法通过练习改善。他们在手术中, 只对患者的上部顶叶进行电刺激, 而没有影响大脑皮层其他区域的正常活动。手术后发现这种刺激会造成中央和外围的书写错误, 这表明书写所涉及的运动和言语加工与上顶叶皮层的有限区域相关。
Hellige和 Adamson (2007)发现, 在文字识别过程中, 大脑的两个半球均参与文字加工过程,但由于视觉的复杂性, 使得大脑右半球对识别手写体文字的作用更大。Nakamura等(2012)研究了个体阅读手写体文字的过程后指出, 熟练阅读普遍依赖于后左半球网络, 该网络中的下顶叶和上级皮质层主要与打印体文字的识别相关, 枕叶视觉字形分析区域(VWFA)主要负责对手写体文字进行感知分析, 并且对手写体文字中字形清晰的字符串反应更敏感。SWIFT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在文字识别过程中, 对激活区域进行空间分配加工, 即以文字的激活程度竞争为基础(隋雪, 沈彤,吴琼, 李莹, 2013), 清晰的字符串的激活竞争更强, 所以, 对此反应更敏感。Nakamura等(2012)假设成熟的阅读网络包括VWFA和运动手势解码系统, 而阅读网络又可以根据书写系统的可变性需求进行调节。他们在实验中运用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记录了被试阅读正常手写体文字和经过空间扭曲的草书手写体文字时的脑区激活情况, 结果表明, 相较于未经加工处理的手写体文字, 空间扭曲的文字激活了双侧枕叶后区, 后侧顶叶皮层(PPC)和外侧前额叶(PMd)区域, 说明大脑对文字的加工是随着字体的变化而变化的。最后, 他们认为手写体文字能够无意识地快速驱动VWFA来识别格式正确的字符串, 但是当目标词是经过空间扭曲的文字时, 这种快速的视觉编码系统将不再被启动, 并且其阅读速度与正常字形相比明显减慢。E-Z读者模型的假定是, 词汇后整合阶段的失败导致了对之前信息的回视(Reichle,Warren, & McConnell, 2009), 这说明空间扭曲文字相较于手写体文字来说, 其信息在运动系统和VWFA中没有相应的匹配, 从而导致信息整合失败, 产生回视, 使阅读速度减慢。手写体文字的书写过程能帮助建立关于文字识别加工的“视觉空间结构”和“字形表征”, 从而引起更多感觉运动信息与文字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 促进语义通达(李辉, 王晶颖, 2016)。Cao等 (2013)实验研究发现,被试文字识别任务中的表现在手写体文字条件下更优秀, 他们认为在手写体文字条件下, 文字表征的质量更高, 这种高质量的文字表征有利于后期文字的识别。由于手写笔迹会对陌生字形产生提示线索, 因此, 可以说手写体文字的识别相较于打印体文字, 更多地涉及到视觉空间记忆与运动记忆的共同作用, 从而使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更容易。
图形识别的脑成像研究显示, 形状知觉引起与物体识别相关的腹侧通路(初级视觉皮层−次级视觉皮层−高级视觉皮层−颞下回−额叶)兴奋, 空间位置知觉则会引起与运动和空间位置相关的背侧通路(中颞区−顶叶−额叶)兴奋, 形状空间位置知觉引起腹侧通路和背侧通路并行协作(周群等,2005)。手写体文字识别加工涉及的脑区与图形识别相关联的空间位置知觉涉及的脑区大致相同,因此, 手写体文字识别与图形识别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同的模式。
相对于打印体文字,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更多地涉及到大脑右半球脑区; 在识别过程中, VWFA首先对手写体文字的字形进行感知分析, 并在广泛的双侧皮质层网络中引起重复抑制, 这些网络不仅涉及枕叶、外侧额叶等一般阅读脑区, 还涉及到具有文化特异性的阅读脑区, 即左侧前额叶皮质(BA9)周围, 左侧 PMd, 双侧PPC,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高度互联的网络, 与行为结果紧密并行,完成对手写体文字的加工。另一方面, 对阅读的习得开始于对文字图形严格的视觉空间分析, 然后将组合后的笔画和部件映射到正字法意义和语言学意义, 该映射过程的发展是通过重复书写单个字符的形式来促进对文字的视觉分析, 并建立长期记忆表征实现的(Tan, Xu, Chang, & Siok,2013)。因此, 手写体文字对促进学习字形形成与文字理解有重要意义。
5 研究展望
大多数情况下, 成年人通过计算机输入文字并使用文字处理程序及其他便捷工具进行文字加工, 但是这种由键盘输入的文字与原始手写体文字之间存在较大的物理特性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影响文字识别加工过程。研究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加工过程将丰富文字识别加工领域的研究。本文着重从词汇、句子和书写风格等方面分析了手写体文字识别的特点, 并且比较了手写体文字与打印体文字识别过程中的具体差异, 发现手写体文字识别既涉及整体加工策略, 也涉及特征加工策略。关于加工的脑机制, 除了涉及到加工打印体文字的脑区, 手写体文字加工还涉及到了双侧枕叶后区、后侧PPC、外侧PMd。由于现在对手写体文字的研究还很有限, 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 对手写体文字识别机制缺乏具体的理论解释。MIA认为识别文字时是通过分解文字的笔画、偏旁部首, 并利用其位置信息进行特征加工, 但手写体文字的笔画和部件位置会随着书写者的书写习惯发生变化, 并不固定, 所以 MIA不能完全的解释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双通道理论认为实现词汇通达有两条途径, 即词形−词义和词形−语音−词义(Xu, Pollatsek, & Potter, 1999), 两条途径中所包含的词形加工是针对打印体文字的字形, 没有单独考察手写体文字的字形特征是否适用于该过程。对此, Planton, Jucla, Roux和Demonet (2013)等人认为同其他语言技能相比,对健康被试书写时的功能性脑成像技术的研究还不充分, 因此, 难以建立可以解释手写体文字阅读的神经功能模型。现有大多数理论都是以打印体文字识别为基础提出来的, 而手写体文字与打印体文字具有显著的特征差异, 现有的理论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手写体文字的识别过程, 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 要考虑建立解释手写体文字识别的理论。
其次, 关于大脑怎样处理手写体文字中嘈杂的视觉信息(即妨碍视觉器官对信息加工的因素)这个问题, 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由于手写体文字的识别加工涉及到许多过程, 通过分析输入的感官信息, 其视觉分析系统和视觉输入系统对这些信息进行集中加工, 并输入到与目标词有关的知识语义系统中(Planton, Jucla, Roux, &Demonet, 2013)。李宁和梁宁建(2014)认为汉字的通透性(即, 笔画之间的水平距离, 垂直距离以及对称关系)主导汉字字形加工。他们研究发现, 笔画之间离散程度越大, 对称性越高, 则笔画越清晰, 形码的知觉速度越快, 越符合局部格式塔假设; 另一方面, 整字字形越对称, 整体格式塔越明显, 所以, 对称字字形加工明显优于非对称字字形加工。因此, 需要深入探究当手写体文字的字形通透性在各水平上出现差异时, 大脑是怎样区分其字形特征并对其进行识别的。为解决手写体文字识别过程中视觉信息与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 未来应该尝试结合使用脑电设备和眼动设备,探究出手写体文字加工的神经生理机制和识别加工模型。
最后, 实验室实验不能满足研究手写体文字识别所需要的环境条件。非实验室条件下通过书面形式传达信息, 而实验室实验中被试识别的手写体文字往往是通过电脑屏幕以呈现图片的方式传递文字信息, 这种方式是被试所陌生的, 因此,会对实验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 手写体文字的识别会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 而这些变量很难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出来, 所以会对实验效度造成影响。
字符识别的研究不管是在认知心理学还是语言学领域都有很多成熟的理论模型作支撑, 但这些理论的建立大多数以打印体文字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手写体文字识别将会拓展字符识别的研究范围, 丰富文字识别的研究内容。而且, 手写体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 对其识别加工过程的研究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研发计算机识别技术等, 所以研究手写体文字的识别是非常必要的。
陈琳, 钟罗金, 冷英, 莫雷. (2014). 拼音自动加工和语义加工中汉字字形的激活.心理学报, 46(11), 1661–1670.
常玉林, 王丹烁, 周蔚. (2016). 字形判断过程中的整体与局部优先效应: 来自反应时和眼动指标的证据.心理科学, 39(5), 1040−1044.
管益杰, 李燕芳, 宋艳. (2006). 汉字字形加工的关键特征模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 1(2),126–129.
宫殿坤, 郝春东, 王殿春. (2009). 字体特征与搜索方式对视觉搜索反应时的影响.心理科学, 32(5), 1142–1145.
胡学平, 孙继民, 曹蕊, 姚温青, 王美珠. (2014). 实物形状的知觉相似性对视觉隐喻加工的影响.心理学报,46(5), 607–620.
胡笑羽, 刘海健, 刘丽萍, 臧传丽, 白学军. (2007). E-Z阅读者模型的新进展.心理学探新, 27(1), 24–29, 40.
黄志平. (2012).字迹风格对字迹识别影响的眼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
金连文, 钟卓耀, 杨钊, 杨维信, 谢泽澄, 孙俊. (2016).深度学习在手写汉字识别中的应用综述.自动化学报,42(8), 1125–1141.
柯学, 白学军, 隋南. (2004). 视知觉无意识加工中的形状优势效应.心理科学, 27(2), 321–324.
柯学, 白学军, 隋南. (2008). 视知觉无意识对局部形状和颜色特征加工的注意调节.心理科学, 31(2), 336–339.
李宁, 梁宁建. (2014). 多层次格式塔双向加工模型: 汉字输入中形码的认知加工机制.心理与行为研究, 12(4),441–446.
李辉, 王晶颖. (2016). 汉字加工神经机制的特异性与一般性问题.当代语言学, 18(4), 568–580.
沈模卫, 朱祖祥. (1995). 整体汉字字形识别过程探索.应用心理学,(2), 43–48.
隋雪, 沈彤, 吴琼, 李莹. (2013). 阅读眼动控制模型的中文研究——串行和并行.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672–679.
印丛, 王娟, 张积家. (2011). 汉语言语产生中语音、字形启动的位置效应.心理学报, 43(9), 1002–1012.
王成, 尤文平, 张清芳. (2012). 书写产生过程的认知机制.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560–1572.
王磊, 杨丽川, 孟千力, 马原野. (2018). 上丘-丘脑枕结节-杏仁核视觉皮层下通路及其生物学意义.生理学报,70(1), 79–84.
王静, 薛成波, 刘强. (2018). 客体同维度特征的视觉工作记忆存储机制.心理学报, 50(2), 176–185.
严建雯, 孙善麟. (2005). 汉字识别的加工模型.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18(3), 329–332.
周群, 尧德中, 尹愚, 饶恒毅, 卓彦, 陈霖. (2005). 图形形状与空间位置知觉诱发脑电的相干性分析.生物物理学报, 21(5), 391–395.
周爱保, 张学民, 舒华, 何立国. (2005). 字体、字号和词性对汉字认知加工的影响.应用心理学, 11(2), 128–132.
曾捷英, 周新林, 喻柏林. (2001). 变形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笔画数效应.心理学报, 33(3), 204–208.
臧克和. (2006). 结构的整体性——汉字与视知觉.语言文字应用,(3), 42–48.
Barnhart, A. S., & Goldinger, S. D. (2010). Interpreting chicken-scratch: Lexical access for handwritten word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 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6(4), 906–923.
Barnhart, A. S., & Goldinger, S. D. (2013). Rotation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configural cues in handwritten word perception.Psychonomic B ulletin & Review, 20(6),1319–1326.
Barnhart, A. S., & Goldinger, S. D. (2015).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neighborhood effects in handwritten word perception.Psychonomic B ulletin & Review, 22(6),1739–1745.
Balota, D. A., Aschenbrenner, A. J., & Yap, M. J. (2013).Additive effects of word frequency and stimulus quality:the influence of trial history and data transformat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Cognition, 39(5), 1563–1571.
Bolger, D. J., Perfetti, C. A., & Schneider, W. (2005).Cross-cultural effect on the brain revisited: universal structures plus writing system variation.Human Br ain Mapping, 25(1), 92–104.
Bub, D. N., Arguin, M., & Lecours, A. R. (1993). Jules Dejerin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pure alexia.Brain and Language, 45(4), 531–559.
Cabeza, R., & Nyberg, L. (2000). Imaging cognition II: An empirical review of 275 PET and fMRI studie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1), 1–47.
Cao, F., Vu, M., Chan, D. H., Lawrence, J. M., Harris, L. N.,Guan, Q., … Perfetti, C. A. (2013). Writing affects the brain network of reading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Human Brain Mapping,34(7), 1670–1684.
Chen, J. Y., & Cherng, R. C. (2013). The proximate unit in Chinese handwritten character production.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517.
Corcoran, D. W. J., & Rouse, R. O. (1970). An aspect of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involved in reading typed and handwritten words.Quarterly Journal of E xperimental Psychology, 22(3), 526–530.
Coltheart, M., Curtis, B., Atkins, P., & Haller, M. (1993).Models of reading aloud: Dual-route and 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 approaches.Psychological Review,100(4), 589–608.
De Zuniga, C. M., Humphreys, G. W., & Evett, L. J. (1991).Additiv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repetition, degradation,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reading of handwriting. In Besner, D. & Humphreys, G. (Eds.),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pp. 10−33). Hillsdale, NJ: Erlbaum.
Dehaene, S., Cohen, L., Sigman, M., & Vinckier, F. (2005).The neural code for written words: A proposal.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9(7), 335–341.
Diaz-Cabrera, M., Ferrer, M. A., & Morales, A. (2015).Modeling the lexical morphology of western handwritten signatures.PLoS One, 10(4), e0123254.
Dinges, L., Al-Hamadi, A., Elzobi, M., El-etriby, S., &Ghoneim, A. (2015). ASM based synthesis of handwritten Arabic text pages.The Scien tific World Journal, 2015,323575.
Dinges, L., Al-Hamadi, A., Elzobi, M., & El-etriby, S. (2016).Synthesis of common Arabic handwritings to aid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research.Sensors, 16(3), 346.
Gordon, C. J., Spivev, M. J., & Balasubramaniam, R. (2017).Corticospinal excitability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handwritten and typed words and non-words.Neuroscience Letters, 651, 232–236.
Engbert, R., Longtin, A., & Kliegl, R. (2002). A dynamical model of saccade generation in reading based on spatially distributed lexical processing.Vision R esearch, 42(5),621–636.
Guan, C. Q., Liu, Y., Chan, D. H. L., Ye, F., & Perfetti, C. A.(2011). Writing strengthens orthography and alphabeticcoding strengthens phonology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3(3), 509–522.
Hellige, J. B., & Adamson, M. M. (2007). Hemispheric differences in processing handwritten cursive.Brain andLanguage, 102(3), 215–227.
Li, J. X., & James, K. H. (2016). Handwriting generates variable visual output to facilitate symbol learn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 eneral, 145(3),298–313.
Longcamp, M., Anton, J. L., Roth, M., & Velay, J. L. (2003).Visual presentation of single letters activates a premotor area involved in writing.NeuroImage, 19(4), 1492–1500.
Magrassi, L., Bongetta, D., Bianchini, S., Berardesca, M., &Arienta, C. (2010). Central and peripheral components of writing critically depend on a defined area of the dominan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Brain Research, 1346, 145–154.
Mukhopadhyay, M., Singh, P. K., Sarkar, R., & Nasipuri, M.(2018). A study of different classifier combination approaches for handwrittenIndicScript Recognition.Journal of Imaging, 4(2), 39.
Nakamura, K., Kuo, W. J., Pegado, F., Cohen, L., Tzeng, O. J.L., & Dehaene, S. (2012). Universal brain systems for recognizing word shapes and handwriting gestures during reading.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50), 20762–20767.
Perea, M., Gil-López, C., Beléndez, V., & Carreiras, M.(2016). Do handwritten words magnify lexical effects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9(8), 1631–1647.
Perea, M., Marcet, A., Uixera, B., & Vergara-Martínez, M.(2016). Eye movements when reading sentences with handwritten word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doi: 10.1080/17470218.2016.1237531.
Perfetti, C. A., & Tan, L. (2013). Write to read: the brain’s universal reading and writing network.Trends in Cog nitive Sciences, 17(2), 56–57.
Planton, S., Jucla, M., Roux, F. E., & Demonet, J. F. (2013).The "handwriting brain": A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motor versus orthographic processes.Cortex,49(10), 2772–2787.
Qiao, E., Vinckier, F., Szwed, M., Naccache, L., Valabrègue,R., Dehaene, S., & Cohen, L. (2010). Unconsciously deciphering handwriting: Subliminal invariance for handwritten words in the visual word form area.NeuroImage, 49(2), 1786–1799.
Reichle, E. D., Pollatsek, A., Fisher, D. L., & Rayner, K.(1998). Toward a model of eye movement control in reading.Psychological Review, 105(1), 125–157.
Reichle, E. D., Pollatsek, A., Rayner, K. (2006). E-Z Reader:A cognitive-control, serial-attention model of eyemovement behavior during reading.Cognitive Syste ms Research,7(1), 4–22.
Reichle, E. D., Warren, T., & McConnell, K. (2009). Using E-Z reader to model the effects of higher level language processing on eye movements during reading.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6(1), 1–21.
Rayner, K., Reichle, E. D., Stroud, M. J., Williams, C. C., &Pollatsek, A. (2006). The effect of word frequency, word predictability, and font difficulty on the eye movements of young and older readers.Psychology and A ging, 21(3),448–465.
Rosso, O. A., Ospina, R., & Frery, A. C. (2016).Class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handwritten signatures with time causal information theory quantifiers.PLoS One,11(12), e0166868.
Tan, L. H., Spinks, J. A., Eden, G. F., Perfetti, C. A., & Siok,W. T. (2005). Reading depends on writing, in Chines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24), 8781−8785.
Tan, L. H., Xu, M., Chang, C. Q., & Siok, W. T. (2013).China's language input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affects children's reading development.Proceedings oftheNational Academ y of S 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3), 1119–1123.
Vajda, S., Ranqoni, Y., & Cecotti, H. (2015). Semi-automatic ground truth generation using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and limited manual labeling: Application to handwritten character recognition.Pattern R ecognition Letters, 58,23–28.
Wandell, B. A., Rauschecker, A. M., & Yeatman, J. D. (2012).Learning to see words.Annual R eview of P sychology,63(1), 31–53.
Xu, Y., Pollatsek, A., & Potter, M. C. (1999). The activation of Phonology during silent Chinese word reading.Journal of E xperimental Psycho logy: L earning, M emory, and Cognition, 25(4), 835–858.
Zhang, Q., & Feng, C. (201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processing in Chinese handwritten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 of lexicality and radical complex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