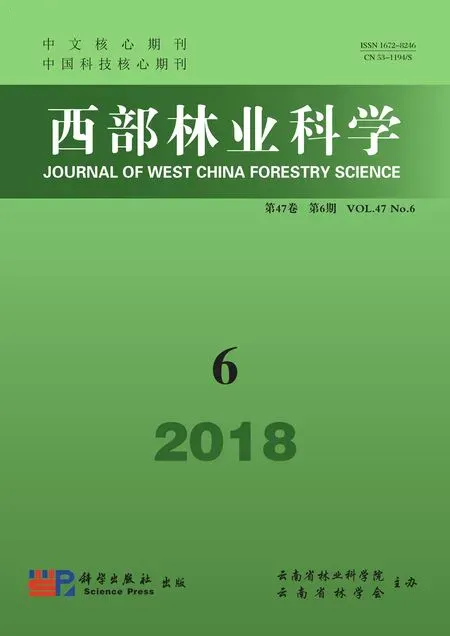云南松及其林分退化现状与生态系统功能研究进展
2018-02-16王磊张劲峰马建忠魏巍胡青
王磊,张劲峰,马建忠,魏巍,胡青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云南松(Pinusyunnanensis)又名青松、飞松、长毛松等,在分类上属于裸子植物门(Gymnospermae)、松杉纲(Coniferopsida)、松杉目(Pinales)、松科(Pinaceae)、松属(Pinus)中的双维管束——松亚属、油松组里的一员[1-2]。在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上,云南松的属级区系为北温带成分,云南松的种级区系为我国西南特有种成分,也是组成滇黔桂亚热带山地针叶林植被的主要成分之一[2]。云南松以云贵高原为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是云贵高原上成林面积最广的树种[2-3]。云南松林是云南省分布面积最大的森林植被类型,占全省林地面积的52%,占有林地蓄积的32%,是在地带性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破坏后天然或人工更新起来的次生林,也是比较稳定的森林群落,在林材产品生产和国土安保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4-6]。然而,云南省内的云南松80%为纯林,生物多样性低[7],而且,近段时期以来,由于砍优留劣、毁林开荒、极端天气、生物入侵、火灾及病虫害的频繁干扰,使云南松种源质量下降,出现了云南松单株或成片死亡的现象,绝大部分云南松林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扭曲林分、疏林、低产林日益增多,这使得人们对云南松林的经营前景产生疑虑和担忧[6,8]。另一方面,人们长久以来所看重的是可直接货币化的森林经济价值(如木材、林副产品、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却忽略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这正是森林屡遭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9]。而很多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是难以被货币化和商品化的,其中诸如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等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且长远的贡献[10]。
因此,基于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理念和评价方法,开展云南松林分的恢复生态学研究,这将对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对云南松的形态特征和林学特性进行了简要介绍,综述了近年来关于退化云南松林及其生态功能的研究情况,针对退化云南松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今后的研究设想,以期正确评价云南松林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全面认知云南松林、完善其林分的经营管理、精准提升林分质量等提供科学依据。
1 云南松的形态特征
云南松为常绿乔木,高可达30m,胸径可达1m。一般一年生长1台枝。树皮褐灰色,深纵裂,裂片厚或裂成不规则的鳞状块片脱落。一年生枝粗壮,淡红褐色;二年生枝上的针叶宿存。针叶通常3针1束,偶见2针1束,长10-30cm,径略大于1mm,先端尖叶质柔软,背腹面均具气孔线,边缘及中肋具有细锯齿;树脂管4个,边生,有时腹面的1个中生;叶鞘宿存,呈管状。雌雄同株,雄球花呈黄色,圆柱形长2-3cm,生于新枝下部的苞腋内,聚集成穗状;雌球花常数个生于枝顶;球果圆锥状卵形,长5-9cm,具短柄或近无柄,未成熟时为绿色,熟时呈褐色或深褐色,具果鳞,鳞盾肥厚,平或隆起,偶见反曲,鳞脐微凹或微隆起常具短刺,球果成熟时种鳞张开。种子呈褐色卵形,一端有翅,连翅长约2cm,薄膜状易脱落。花期4-5月,球果翌年10月成熟,成熟后可多年宿存于枝上[1-2,11],形成植冠种子库。
有研究[12-15]发现,滇东南地区云南松针叶的内皮层细胞出现了凯氏带加厚的现象,而按“滇东南-滇中-滇西北”的地理顺序,云南松的各构件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随海拔升高,其针叶长度逐渐减少,针叶的发育为不对称叶原基分化,形成不同针叶数的针束,3针1束的比例、短枝上的针叶数目、针叶断面积均表现出“小型化”趋势,而叶鞘长度、芽鳞长度和芽鳞排列的紧密程度等则有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纬度的增加,云南松茎干材的年均生长轮宽度亦有“小型化”的趋势,其树脂道的数量随之增加,树皮的类型和韧皮部的颜色也呈现出多样性。
2 云南松的林学特性
云南松为喜光性强的深根性树种,适应性强,耐冬春干旱气候和瘠薄土壤,能生长于酸性红壤、红黄壤及棕色森林土或微石灰性土壤上,但以气候温和、土层深厚、肥润、酸性砂质壤、排水良好的北坡或半阴坡地带生长最好[1]。云南松天然更新容易,能飞子成林,是荒山造林和迹地更新的主要树种[11]。云南松的木材呈淡红黄色,材质较为轻软、细密、纹理不直、力学性质不均,可用于建筑、枕木、板材、家具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云南松树干连树皮多扭转生长,树干可割取树脂;树根可培育茯苓;树皮可提栲胶;松针可提炼松针油;木材干馏可得多种化工产品,因此,云南松也是森工和林化企业的主要采伐对象[1,11]。
邓喜庆等研究发现[16],在云南省境内,云南松林水平分布范围是23°01′20″-28°23′33″N,97°46′39″-105°54′05″E,垂直分布范围在海拔710-3 320m之间;云南松林下土壤包括8个土类,按分布面积排序为:红壤>紫色土>黄棕壤>黄壤>棕壤>赤红壤>暗棕壤>石灰土;云南松林在阳坡的分布多于阴坡,但分布于阴坡的云南松林质量总体上优于阳坡;就其坡位分布来看,中坡位>上坡位>下坡位>山脊;从林分质量上看,山脊>上坡位>下坡位,并由此提出,在现有云南松林中,人为干扰因素已经取代了立地条件等自然因素而成为影响云南松林分质量的主要因素。
3 云南松林分退化现状
3.1 云南松林分退化的成因
退化云南松林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致使云南松种群质量下降,群落出现逆演替现象。云南松林分衰退的主要表征,即生长速度明显减慢、枝叶稀疏、枝干扭曲、球果发育不全、结实量减少,以及出现顶尖分叉、断头等现象,其树势明显衰弱[17]。此外,在退化云南松林分中,树种组成较为单一、生物多样性较低。邓喜庆等[18]研究了云南松林资源的动态变化,发现在1987-2007年的20年间,云南松林资源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是,过熟林资源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优质可用云南松林资源的数量持续减少,濒临枯竭,大径组和特大径组林木蓄积所占比例则呈下降趋势;认为云南松林可用资源数量在快速减少,材种结构低质化倾向加剧,而且云南松林分林龄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低龄化特征。
李莲芳等[19]将云南松林退化的自然成因归纳为:①树种特性(包括云南松的遗传学特性、生态学特性、生物学特性),认为云南松存在遗传多态现象,其种群、家系和个体间严重分化,营养生长与繁殖生长间呈现反比现象,在苗期和幼林期,其个体在林分中的竞争力较弱;②异质地理环境(包括经纬度、海拔、地形、坡向、坡位、土壤等),认为不同的云南松地理种源和种群存在差异,若用非适宜区种源造林,将导致云南松林分的衰退;③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云南松林早已适应的生长环境;④生物入侵,影响了森林群落中乔灌层植被的更新;⑤其他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病虫害及火灾),降低了云南松林分质量,破坏其林分结构。在云南松林退化的人为成因方面,李莲芳等[19]将其归纳为:①种源干扰,即从非适宜区调拨种子造林;②改变林地环境,如开垦农地导致灌草繁茂,林地放牧导致土壤板结;③缺乏适当的抚育措施及初植密度过高,引起林木强烈分化,单位面积蓄积量低于其立地和林龄的标准蓄积量,或林木单株胸径和材积低于标准蓄积量;④不当采伐和清林。
杨超本等[17]认为云南松林分的衰退主要是由人为经营措施不当、地力退化和有害生物等三方面原因诱发的,并将其归纳为生物和非生物两大类影响因素,其中,生物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云南松林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较低,尤其是人工纯林的林分结构单一,对有害生物的自控能力极为脆弱,当外界环境改变时,极易导致林分衰退;而非生物因素的影响则是由于过度采伐、缺乏科学的抚育措施,以及长期不适地适树而大规模营建人工纯林,造成云南松林分水分流失、营养减少、土壤酸化、稳定性下降,最终导致其林分发生衰退。
3.2 退化云南松林的判定
对退化林分进行判定,需要综合考虑林分所处的生物地理环境(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林木树种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以及受(自然/人为)干预程度等影响因素。当前,有关退化云南松林恢复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云南松低效林的分类、分级与改造等方面。云南松低效林是一类受不良环境(气候紊乱、土壤退化、水源枯竭、人为扰动等)影响,林分结构发生逆向演替且活力衰退的、未充分发挥林地立地条件下主导生态服务功能的林分的统称。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判别云南松林分是否退化和退化的程度主要是看该林分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低效林。
此前已有研究[20-22]通过对立地条件的分析,将退化林分划分为极低质低效型、生长潜力型、低质型和综合低质低效型;也有针对特定区域,采用树种组成的特征划分低质低效林的类型[23];或采用起源、树种组成、更新方式、林分生长状况等对低质低效林进行分类[24]。
李贤伟等[25]指出云南松低效林有明显的渐蚀、片蚀、沟蚀等现象,侵蚀深度>5mm,有的可达1m,林下植被覆盖度低于30%,林内乔木林稀少,树冠窄小,林分结构残缺不全,缺乏正常的复层结构;并认为乔木层稀疏,郁闭度低,林分结构单一,林下植被少,树冠圆满度低等是云南松低效林的主要特征,并认为云南松低效林是一个生态经济系统,可将云南松低效林划分为一般低效林、低产低效林、高产低效林。
李莲芳等[19]则提出了判定低效林的两个关键条件,即所处林地立地条件和林分的效能目标,并将云南松低质低效林划分为劣质低产用材林和低效生态公益林两大类,其中在低效生态公益林中又分列出低效天然次生林和低效人工生态林两个类别,在劣质低产用材林类型中划分出低产用材林、劣质用材林,再进一步将低产用材林细分为低产天然次生林和低产人工林,将劣质用材林细分为低质天然次生林和低质人工林。
3.3 退化云南松林的恢复与改造
近年来,在云南松退化林分改造与恢复的实践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云南省峨山县通过营造云南松与旱冬瓜(Alnusnepalensis)、直干桉(Eucalyptusmaideni)等树种的混交林,对原有种源退化、生长缓慢、出材率低下的扭曲云南松低效林分进行了改造,已取得良好的成效[26]。钟华等[6]开展了退化云南松林恢复技术试验,总结出了混交阔叶树种控制紫茎泽兰(Eupatoriumadenophora)的恢复技术模式,通过林分的抚育间伐、封山育林,以及对恢复过程中侵入林分的紫茎泽兰实施人工防除等,最终把退化云南松林逐步引向针阔混交复层异龄林。也有研究[27]指出,抚育间伐是云南松劣质低产用材林分改造的主要措施。此外,疏伐作为林分结构调整和改善林木生长的森林培育重要措施,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中。李莲芳等[28]研究了滇中云南松低质低效人工林疏伐的密度及生长动态,揭示了云南松林分于幼林时期疏伐的必要性,即疏伐越推迟,其效果将越差,对于亚热带分布的云南松林分应开展适时疏伐。
国内有研究[29]指出,由于低效林固有的复杂性,在进行改造时,不能采用单一的措施,而应当对各种营林措施综合运用。该研究还提出对天然次生林区低效林分进行技术改造的措施,包括全部伐除,全面造林;清理活地植被,林冠下造林;抚育采伐,伐孔造林;带状采伐,引入珍贵树种;局部造林,提高密度;封山育林,育改结合。罗晓华等[30]提出的低效林改造措施则包括树种选择、改善层次结构、培育措施和封山育林,其中培育措施涉及到补植补播、调整群落密度和结构、营造混交林等方面的内容。吕勇等[31]总结出5种低质低效次生林的改造模式,即全面改造模式、局部改造模式、抚育改造模式、择伐改造模式及封禁管护模式。
4 云南松林分的生态系统功能研究
4.1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极大的重视,其中,生态系统服务,是由自然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并维系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9,32-33],它支撑和维护了地球的生物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命物质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大气化学成分平衡与稳定等[34-35]。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生态学中的新兴研究领域,但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提出也已经历了一段历史时期。美国学者Marsh[36]描述了在地中海地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认为动植物、水、空气和土壤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Leopold[37]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可替代性;King[38]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探讨;Gordon[39]论述了自然对人类的一些服务;Daily[40]和Costanza等[34]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形成的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条件和过程。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是Daily等[33]人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
与国外相比,我国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较晚,功能分类上也还不完善[10]。欧阳志云等[32]曾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别做了具体阐述。而蔡晓明[41]则分别论述了生态系统功能(包括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流动、物种流动等)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土壤形成及其改良、减缓干旱和洪涝灾害、净化空气和调节气候、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传粉、传播种子、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生物防治、休闲、娱乐等)。高广磊等[9]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包括自然-社会复合性、继发性、多维性、动态性和公益性等方面。
2001-2005年期间,联合国开展了名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MA)的国际合作项目,其核心是审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联,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尤为重视[42]。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这些服务功能及效益进行科学的评估,业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43]。一些林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将其列进森林经营的投入产出项目中[44]。国内外评价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非物化商品价值的经济学指标涉及影子价格、支付意愿和消费者剩余[44]。然而,由于世界各国关于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都有明显的区域性和目的性[45],以及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多维属性和研究者对其认知差异的影响[9],迄今全世界还没有统一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10,33,43-44]。因此,在实际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相应的评估方法。
4.2 云南松林分的生物多样特征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并非仅提供单一的生态系统功能,而是能同时提供多种功能,但直到2007年,研究人员才开始定量描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之间的关联[46]。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研究[47-53]表明,维持生态系统多功能性所需的生物多样性比预期的更高。
虽然可以对不同尺度和等级的生物多样性开展独立研究,但究其核心应居于种级水平,物种才是生物多样性最根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54]。云南松林的林木组成单纯,基本上是以云南松单优势树种组成的单层同龄林,林相较整齐,自然稀疏强烈,在现实林分中,常见到云南松与其他树种组成的针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林[2]。李贵祥等[55]调查研究了滇中地区永仁县白马河林场云南松原始林群落特征及物种多样性,基于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和Shannon-Wiener指数分析,发现云南松原始林以云南松纯林为主,林下层次结构复杂,较之云南松次生林,具有更丰富的物种多样性。蔡年辉等[56]针对滇中地区禄丰县一平浪林场樟木箐林区云南松人工林和天然林的群落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云南松天然林的物种丰富度明显高于人工林。韩明跃等[57]曾对滇中宜良县云南松天然次生林的物种组成及生长状况开展过调查研究,认为当地的云南松天然次生林中物种较少,群落结构简单,但较为稳定。王健敏等[58]通过调查研究云南省滇中地区云南松天然林和人工林的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发现在森林起源过程中,随着干扰程度的增加,云南松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稳定性、自然修复能力与协调平衡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并认为可将入侵种紫茎泽兰作为森林群落生物多样性、干扰程度和森林健康评价的指示物种。
此外,在遗传特性方面,云南松种群内部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变异,而且种群中许多形态性状表现出较明显的生态地理变异式样,具有丰富的多态性,种群间则表现出多型性,从而为云南松种群进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Wang等[59]运用遗传学和生态学方法对分布区中的云南松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生态位分异的研究。许玉兰[60]采用形态性状和SSR分子标记分析方法,对云南松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群体间和群体内的遗传变异特点、遗传多样性分布格局等开展了相关研究。
4.3 云南松林分的水土保持功能研究
云南松林分的水土保持功能包括了涵养水源与保育土壤两个方面。水源涵养功能是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森林植被层、枯落物层和土壤层对降雨拦蓄及再分配的复杂过程[61]。森林的保育土壤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固土功能和保肥功能。森林植被通过截留降水,降低雨滴的冲击和地表径流的冲刷侵蚀,减少径流的形成,起到保护土壤的作用;同时植物根系固持土壤,改良土壤的物理性状,保持土壤肥力,具有改善土壤化学性质的功能[62]。云南松林区地处横断山脉,是长江、珠江及多条国际河流的上游[63],因此,水源涵养功能和土壤保育功能已成为云南松林分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重要指标。
刘文耀等[64]曾研究了滇中地区山地常绿阔叶林及云南松林的林冠截留量、冠流和径流量、地表水土流失量、林地枯枝落叶层持水量、土壤含水量等,提出云南松林下的枯枝落叶层与林内良好的水文效益有密切的关系。孟广涛等[65]通过对金沙江流域不同植被类型的林分截流、渗透性能、持水能力及径流进行测定分析,发现乔木层云南松林的持水能力较好,而土壤渗透性能较差,侵蚀较严重。毛慧玲[66]以滇中地区云南松纯林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林龄云南松林的生态水文功能,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云南松林生态水文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对云南松林生态水文功能进行了评价。有资料[2]介绍,在云南,云南松林有1 181.28×104hm2,相当于建了3 544座100×104m3的水库。
吴晋霞[62]采用野外调查、取样与室内实验测定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选取云南省玉溪市尖山河小流域的云南松林和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云南松林为研究对象,从固土功能和保肥功能两个方面对云南松林的保育土壤功能进行了量化研究。另有研究资料[2]表明,金沙江虎跳峡地区的云南松林的截留率相对较高,松林的叶滴溅蚀作用及其功能效应随降雨的强度而改变,云南松林分布地段具有保护地表和土壤的作用;另一方面,云南松根系对土壤具牵引效应,这对高山峡谷陡坡侵蚀的控制和坡面保护有重要意义。在云南,云南松林每年可固土7 088×104t,可保肥99×104kg[2]。
4.4 云南松林分的生长量特征研究
森林生长量的调查和研究,可揭示林分生长发育规律,提高林分生产力,更好地发挥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根据1997年云南全省森林资源清查统计,云南松林在1992-1997年5年间,幼龄林、中龄林的生长量大于消耗量;相反,近熟林、成熟林及过熟林的消耗量则大于生长量。这说明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的可采资源少,中、幼林蓄积比重加大。云南松林总生长量为1 389.20×104m3,总消耗量为1 232.11×104m3,其生长率为6.95%,消耗率为6.16%。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云南松林被列入天然林保护区域,进而有利于林分的良性发展[2]。
廖声熙等[67]曾对滇中高原云南松林分进行调查以及树干解析,将云南松生长发育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即苗木生长初期、树高速生期、直径速生期、速生后期、成熟期;发现林分中云南松优势木材积生长量是平均木的3-4倍;云南松材积生长的重要年龄阶段为15-45年;50年生云南松开始进入数量成熟阶段,可以采伐利用。陈建珍等[68]通过研究滇中-平浪林场的云南松天然次生林的生长状况,发现50年生的优势木材积总生长量和连年生长量分别约为平均木的4倍和5倍;还发现平均木和优势木存在2个速生时期,分别为5-10年和35-40年。
此外,邓喜庆等[18]深入研究了1987-2007年云南松林资源的结构、数量、质量、主导利用方向等变化情况,认为在监测期间,云南松林可用资源质量呈快速下降趋势,林龄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低龄化特征,材种结构已显著低质化,大径组与特大径组木材资源消耗过快,尤其是特大径组优质木材资源数量快速减少。
4.5 云南松林分的生物量特征研究
云南松林分的生物量与其木材蓄积量密切相关,可以反映出云南松林分的生产与供给能力,也是云南松林生态系统功能一个重要方面。据调查[2],现实的针叶林分平均蓄积量为100m3/hm2以上,而云南松林木材蓄积量仅为60m3/hm2左右,可见,云南松林的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
党承林和吴兆录[3]曾分析了云南省易门县海拔1 600-1 700m云南松中幼龄天然次生林生物量的变化情况,观测到4年生林分的总生物量为9.985t/hm2,11年生林分为27.874t/hm2,23年生林分为69.852t/hm2;发现林分中乔木层针叶和树皮的生物量分配比例随林龄的增加而下降,干材和根的比例则不断上升,其中以干材增加最快。蔡年辉等[69]对云南松天然林分单木和种群生物量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其单木生物量在26龄前增长缓慢,26龄后增长速度较快;种群生物量在4龄前增加较快,5-7龄增长缓慢,8-9龄直线增长,10-20龄缓慢增加,21龄以后增长较快;在4龄前,地下生物量所占比例较大,并随着林分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最后趋于稳定;4龄后,地上生物量占个体生物量的比例较大,占主导地位。
在云南松人工林分生物量的研究方面,孙宝刚等[70]利用标准木法测定了不同径级云南松人工林生物量及生物量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随着径级的增大,主干和根部生物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枝和叶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比例为先升高后降低,而树皮的比例则一直下降。张志华等[71]通过在滇西北设置云南松人工林样地,分析了林分乔木层各器官生物量分配及乔木层、草本层及灌木层的生物量,发现乔木层各器官的生物量分配为树干>树枝>树根>树叶,各器官生物量中,树叶生物量所占比例最小,并指出云南松生产力在平均胸径为15.3cm时达到峰值。刘林森[72]也对滇西北云南松人工林生物量进行了研究,计算分析了滇西北云南松单木及林分生物量模型、林分生产力的差异,得出滇西北云南松种群生物量为8 228.3t/hm2。
另有研究[18]显示,1987-2007年20年间,虽然云南松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提高了27.05%,提升幅度较大,但大径组和特大径组林木蓄积所占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特大径组所占比例仅为原来的1/3,而云南松近成过熟林的单株材积降幅则高达241.5%。该研究认为云南松林分质量总体上虽有所提高,但可用的资源数量在迅速减少,而且材种结构低质化倾向严重。
4.6 云南松林分的人居保障功能研究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2015年修编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的相关内容,我国生态系统功能分为生态调节功能、产品提供功能、人居保障功能3个类型,其中人居保障功能主要是指满足人类居住需要和城镇建设的功能,主要区域包括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大都市群和重点城镇群2个类型。云南省的滇中城镇群已划入重点城镇群人居保障功能区。而滇中地区正是云南松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但目前鲜见关于云南松林分人居保障功能研究的报道。
4.7 云南松林分的固碳释氧功能研究
森林是陆地碳库主要的源和汇,其碳储量占整个陆地植被碳储量的76%-98%[73]。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储存碳,同时释放出氧气,因此,研究森林植被的固碳释氧功能将对量化森林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积极的作用[74-75]。
陆洪灿[76]初步测算过云南省云南松林的碳储量,结果显示全省云南松林储碳总量为4.649×108t,按其森林生长量估算,在2008年的基础上,储存量能逐年增加0.2×108t,以国际碳汇交易市场价10美元/t计算,每年可产生2×108美元的经济效益。
关于云南松林分释氧价值的评估尚未见报道。
4.8 云南松林分营养物质积累功能的研究
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的相关内容,森林植被的营养物质积累功能,是指森林植物通过生化反应,具有在大气、降水和土壤中吸收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并贮存在体内各器官的功能。
佟志龙等[77]对云南省玉溪市磨盘山云南松天然次生林5种营养元素N、P、K、Ca、Mg的含量、积累、分配及其随林龄变化的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云南松不同器官营养元素含量大小次序为树叶>树枝>树根>树干;各器官营养元素含量均以N最高,其次是K和Ca,Mg、P较低;乔木层、林下植被层和凋落物层均以N积累量最多,P最少;云南松N与P含量比随着林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15年、30年和45年生云南松天然次生林每积累1t干物质需要5种营养元素的总量分别为8.38kg、8.52kg和7.68kg,其中对N的利用效率最低,P最高。
苗娟等[78]以贵州省盘县19年、28年和45年生的云南松林为对象,研究了林地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垂直分布、积累特征及其与土壤容重的关系,发现不同林龄云南松林土壤剖面的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变化规律一致,表层呈富集现象,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逐渐减少;19-28年生林地的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积累速率高于28-45年生的林地。
4.9 云南松林分对大气环境净化功能的研究
森林生态系统通过吸收、过滤、阻隔、分解等过程,净化和降解大气中的氮氧化物、氟化物、二氧化硫、粉尘等有害物质,并释放出负离子、萜烯类等物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噪声污染[79]。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该项功能的评估指标包括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降低噪音、滞尘4个方面。
聂蕾等[80]以昆明东三环周边分布的云南松林、华山松(Pinusarmandii)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为研究对象,对森林净化大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效果开展了研究,测得云南松林吸收SO2的量为0.007 3mg/m3,吸收NOX的量为0.003 7mg/m3,最终分析认为昆明不同类型林分对大气环境的净化效果为常绿阔叶林>灌木林>针叶林。
4.10 云南松林分的负离子供给功能研究
集中分布的纯林环境可以产生相当于城市平均含量5-l5倍的空气负离子,而空气负离子具有降尘、杀菌、清洁空气的功效[81]。《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中指出:森林的树冠、枝叶的尖端放电以及光合作用过程的光电效应均会促使空气电解,产生大量的空气负离子,而且植物释放的挥发性物质如植物精气(芬多精)等也能促进空气电离,从而增加空气负离子浓度。据吴楚材等[82]研究,针叶林的负离子浓度平均为1 507个/cm3,阔叶林为1 161个/cm3。
目前,尚未见到关于云南松林区空气负离子研究的报道。
4.11 云南松林分的森林游憩功能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倡导回归自然、欣赏自然、参与森林旅游己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森林生物资源及其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森林游憩资源,既是森林旅游的物质基础,又是森林资源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3]。人们通过知识获取、主观映像、精神感受、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从森林生态系统中获得非物质利益,其中就包括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基础形成的森林游憩价值[84]。因此,认识和评价森林游憩功能已逐渐成为当今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也未见到与云南松林分有关的森林游憩功能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
5 讨论
究其根本,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是由于在干扰压力下,森林生态系统结构遭受破坏失去原有的平衡[85],其林木产品和生态服务功能发生逆向改变[86],最终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弱化。而森林生态系统在维持与改善陆地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对森林退化含义的深刻理解是判别森林退化状况和构建森林恢复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的前提[87]。
在云南的森林资源中,云南松是用材树种的主体[2],但如前所述,由于受到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林地上所形成的云南松林分多为疏林、扭曲林、低矮林、地盘松灌草丛等,其群落及生境向日益退化的方向发展,且面积也不断扩大,林分林龄结构已呈现出显著的低龄化特征。云南松林可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均呈快速下降趋势,材种结构已显著低质化。在人们过于关注云南松林的木材产品供给能力的背景下,这确实是林业生产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是,提供木材产品只是云南松林众多生态系统功能中的一部分,只有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云南松林生态系统功能,才能让云南松林的经营管理及生产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往对云南松林进行改造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升其林产品产量、木材蓄积量等生长量与生物量指标,而对于云南松林分的水源涵养、土壤保育、固碳释氧、营养物质积累、大气环境净化、物种多样性保护、森林游憩等生态系统功能则考虑较少,尤其对云南松林分的归类及其生态功能评价,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这就容易造成对云南松林划分不明、错位改造等问题,会给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云南松林的涵养水源、保育土壤、营养物质积累等生态系统功能对流域水量调节和降低下游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云南松林在云南省的水平分布范围十分广阔,滇西分布至保山、腾冲、陇川等地,并延伸到缅甸[16],云南松林是该区域的重要植被类型。滇西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88],是我国主要的天然林保护区,也是世界松柏类植物的分化中心之一[89],对怒江、澜沧江、大盈江、瑞丽江等重要流域具有显著的水源涵养功能。因此,建议选择滇西地区重点开展云南松林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云南松林分类型进行划分,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为实现云南省云南松林分质量精准提升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