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公共健康,请珍惜疫苗
2018-02-15周叶斌
■文/周叶斌
再有效的疫苗,也离不开人们对它的信任与接纳。
从最早的牛痘疫苗开始,安全、有效一直是疫苗研发中同等重要的两个标准。
无论中外,只要是有关保健品的广告宣传,几乎都会把“增强免疫力”列在主要功效里,似乎也没人担心它们的不良效应。然而,接种疫苗这种真正“增强免疫力”的方式却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些质疑有各种原因,国内更多是受近几年多起疫苗生产质量事故的影响,欧美主要是源于已被证伪的疫苗接种导致自闭症的谣言。无论是何原因,我们都有必要让公众更多地了解疫苗的作用与意义。作为公共卫生与健康的重要支柱,疫苗离不开大众的信任。
与免疫学同龄的疫苗
如果把时间退回到18世纪,免疫这个词根本不存在,也没有疫苗,有的却是肆虐欧亚的传染病——天花。18世纪末的欧洲,每年死于天花的人估计有40万。1796年,一位非常细心的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注意到,因工作缘故感染牛痘的挤奶工中没人得天花。詹纳大胆地把一位女挤奶工的牛痘接种到一个小孩身上,并用后续的天花病毒接种试验证明了接种牛痘可以防止天花感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疫苗就此出现!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疫苗的原理有了更深的认识,研发疫苗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比如,我们可以用弱化的活体微生物做疫苗,也就是弱化疫苗,牛痘就是这类。我们还可以用已经被杀死的病原体做疫苗,就是所谓的灭活疫苗。这些已经死了的细菌或病毒,即便接种到人体内也不能再繁殖扩张,但它们那些能被我们免疫系统识别的部分依然完好而且与活菌无异。随着对疾病机理的了解,我们认识到很多疾病的病原体是通过释放毒素来危害人体的。对于这些病原体,我们可以利用消除毒性的类毒素来开发相关疫苗。我国一类疫苗里的百白破疫苗中的两个成分就是灭活后的白喉类毒素和破伤风类毒素。
如何选择疫苗
这么多种利用不同方法、原理制备的疫苗,很多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有一种或几种比其他的好?是不是有些会更“安全”?其实从最早的牛痘疫苗开始,安全、有效一直是疫苗研发中同等重要的两个标准。现在,大部分疫苗都属于弱化疫苗或灭活疫苗。那么,弱化的疫苗可不可以由灭活的来代替,毕竟弱化的细菌、病毒依旧有致病性。有一些病原体的疫苗,非常幸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制作方式。在这种少数的有选择的幸福时刻,我们仍然要客观、理性地来分析。一般来说,“活”的疫苗比灭活疫苗的效果更好。因为前者接种后仍然能在体内有限增殖,在不致病的前提下激发更强的免疫反应,保护时间也更持久。在实际应用中,“活”的疫苗可能只要接种一次就能引起足够的免疫反应,灭活疫苗往往要追加多次接种。因此,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免疫功能有缺陷的健康人群,应该优先考虑弱化疫苗来获得更好的免疫保护。
不同类型疫苗的选择有时候还要考虑所在区域的具体情况。例如,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是通过注射来接种的,简称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IPV);另一种是弱化疫苗,就是大家熟悉的口服糖丸疫苗(OPV),这恐怕是世界上接种最不痛苦的疫苗了。
目前认为,注射用的IPV免疫保护功效能够持续多年(具体多久没有定论),口服的OPV由于是活疫苗,目前普遍认为是终身保护。此外,由于OPV是口服,它还能在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入侵处——肠道引发免疫反应,起到保护作用,这是IPV不能做到的。然而,由于OPV是活病毒,有很小的概率发生突变,重新获得致病性,IPV没有这种风险。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概率极小(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1/270万),而且由于与感染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无法区别,报道发生的地方也一般在疫苗覆盖率低的地区,有时候很难确定是否真是由疫苗突变造成的。
这些区别会怎样影响接种选择呢?2000年以后,美国只选用IPV而不再使用OPV,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最早使用脊髓灰质炎疫苗,起步早,推广程度高,在1994年就已经成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OPV的肠道免疫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意义就不大了,新生儿只要按时注射IPV就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作用,倒不如干脆避免哪怕极小概率的OPV突变风险。但是,针对大部分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Rotary基金会在1988年开始的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中选择了OPV。在脊髓灰质炎疫情严重的地区,OPV由于有肠道免疫功能,即使摄入了病毒,也能在病毒侵入处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对于不少医疗水平落后的地区,口服的便利性也是IPV不能比拟的(OPV更便宜)。在疫苗覆盖率低的地区,OPV还有另一个加成效果,由于是口服,活病毒在肠道增殖后有一部分会随粪便排出体外,这在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传播疫苗的途径。OPV在全世界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努力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因此,疫苗的安全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完善与质量监控。如果做不到这些,无论哪种方式制备的疫苗都可能会出问题。另外,如果我们能通过推广包括良好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在内的各种公共卫生措施,大幅降低一些传染病的感染率、发病率,我们会在疫苗接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就像美国,在几十年成功的疫苗接种运动后,他们可以选择保护范围稍有欠缺的IPV而不用担心疾病暴发。另一个例子是卡介苗,卡介苗的有效性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特别是在成人中,不同地区显示的保护率差异巨大),还有万分之三的不良反应率(大部分是轻微反应,但在普遍推广的疫苗里仍然是比较高的)。英国和法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学龄儿童全部接种,到了21世纪初,他们的结核病感染率、发病率都已经很低,就停止了全民接种计划,转而只接种医务人员等高风险人群。随着全世界成功消灭天花,我国也在1984年停止了天花疫苗的全民接种计划。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停止某些疫苗的全民接种,很多情况下不是为了避免小概率的不良反应,而是由于在这个地区感染可能性变得极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全民接种的回报很低,不如把这些投入转到其他尚未得到良好控制的公共健康问题中。
公共健康的支柱
由于疫苗在对抗传染病上的特殊作用,很多疫苗一问世就迅速成为公共健康的支柱。詹纳发明牛痘疫苗后,我们用了170年左右时间,完全消灭了天花。实际上,很多曾经肆虐的恶性传染病,我们如今不再听闻,最大的功臣就是疫苗的推广。
在疫苗出现前,美国麻疹的发病率基本在每10万人中200~600例,但从1963年第一个麻疹疫苗推广开始,10年不到,就基本不再有病例发生。脊髓灰质炎也是一样,疫苗一出现就在几年内迅速降低了发病率。这两类疾病疫苗在我国通过一类疫苗计划大规模推广,如今发病率也很低。
疫苗与其他药物不同,是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意味着通过疫苗来预防、消灭疾病的经济、健康以及社会代价往往远低于其他医疗手段。接种疫苗的经济成本也远低于染上恶性传染病后住院治疗的花费。此外,推广大规模接种疫苗往往可以让整个社区、社会获得群体免疫,所有人都可以安心生活工作。相反,若仅依靠得病后再就医,所有与病患接触过的人都得提心吊胆,时刻担心自己是否也会染病,这其中的社会、经济代价恐怕难以估量。大家可以回想21世纪初“非典”暴发时的情形,每确诊一个患者往往意味着上百个人需要隔离,而交通集散处、学校、企业等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检测可能的感染者,这就是一个恶性传染病在没有疫苗可以预防、阻断传播情况下的破坏力。可以说,很多疫苗在无声无息中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安心地生活。
新世纪的质疑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疫苗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抗疾病的方法,对我们的公共健康做出的贡献恐怕比抗生素还要巨大。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疫苗,特别是一些被推荐全民接种的疫苗越来越受到各种质疑。
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公共疫苗接种计划,麻疹、脊髓灰质炎等恶性传染病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在这种安逸的氛围里,近20年里出现了对疫苗不良效应的各种谣言,甚至对一些疫苗的接种率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已经开始威胁公共健康。始作俑者是英国医生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声称MMR疫苗(麻疹、腮腺炎与风疹三联疫苗)与自闭症、克罗氏病(一种肠道炎症)有关的论文。一开始他的文章并未引起社会关注,但当时正值英国进行全国MMR儿童再接种,而欧美自闭症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诊断数量又大幅上升,韦克菲尔德的工作几年后被广泛报道,而一些不幸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也开始公开质疑疫苗是否安全。
疫苗的安全更多的是依靠技术的完善与质量监控。
实际上,由于MMR的广泛使用,几乎每个英国儿童,无论是否患有自闭症,都有接种,韦克菲尔德的结论近乎于说中国的癌症患者都吃过米饭所以米饭致癌。面对突如其来的公众关注,很多科学家开始尝试分析疫苗接种与自闭症是否有关联,可后续的研究,没有一项重复出韦克菲尔德的结论。眼看着这要成为一桩科学悬案的时候,一位英国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韦克菲尔德隐藏了自己关于疫苗研究的诸多利益冲突。概括来说,韦克菲尔德获得了一些在起诉疫苗厂商的律师的经济支持,还在投资建立单独的麻疹疫苗(MMR是三种疫苗的混合体,韦克菲尔德声称独立的三种疫苗更安全)。后续的调查进一步发现韦克菲尔德篡改甚至捏造数据来得出MMR有安全隐患的结论。经过漫长的争论,《柳叶刀》在2010年终于撤回了韦克菲尔德的论文。遗憾的是,这起事件对公众信心造成的打击至今无法挽回。防范恶性传染病的疫苗,陷入了各种谣言、谎言的浑水之中。更不幸的是,尽管科学家提供各种研究数据,反疫苗运动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同样的问题,中国恐怕也难以避免。近几年,几次大批量的疫苗生产安全事故对公众信心造成巨大打击。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向公众普及好不同的生产事故对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可能影响。比如说,几年前未执行冷链运输或最近的稀释疫苗有效成分的行为,对疫苗的影响更多的在于有效性而不是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这些不合格产品不能起到对疾病的预防保护作用,但还不至于直接造成身体伤害。更值得担心的是,伴随多次安全事故的,是对疫苗不良反应的各种传闻。几年前未执行冷链运输的疫苗流入市场的新闻曝光后,出现了很多疫苗不良反应的消息,描述幼儿接种疫苗后出现各种不适甚至致残致死。这些描述大部分情况下难以核实,很多也无法确定是否真与疫苗有关,但各种图文并茂的文章严重打击了公众信心,有统计显示,一些疫苗接种量在此后出现了大幅下滑。
如今曝光的疫苗龙头企业长春长生公司多年屡次违规,篡改生产记录,自然也不会对公众信心的恢复有任何帮助。可悲的是,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些行为不仅没有帮助公众了解真相、恢复信心,反而在消费自己并不富余的威信。我们依然没有公开、透明、完整的疫苗不良反应数据库。当公众对疫苗的安全有疑虑时,我们不能列出实际数据,解释实际发生的不良反应到底是多少,有多少是严重的,有多少可能只是偶然,与疫苗其实无关。职能部门甚至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那么多年生产不合格疫苗却不被发觉。
疫苗的监管过程有许多需要做到更透明。我们需要有切实的数据来告诉疫苗的使用者——普通大众,我们的疫苗推广计划如何制定,生产厂家的招标标准、监管抽查有多少步骤,发现了多少违规行为以及处理结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调研报告来公布可信的疫苗实际效果,每个地区的普及率,对发病率产生了多大影响,不良反应率是多少。虽然大规模推广的疫苗安全性很高,但由于接种人数众多,依然会出现不少不良反应案例,部分甚至会很严重。我们应该正视这些案例,及时提供医疗补救措施,也应参考不同国家的疫苗不良反应处理方法,尽早建立一个良好合理的补偿机制。
很多恐惧源于无知,我们不能仅仅让公众被动地接受疫苗接种,而是要让大家都看到一个公开、透明的疫苗推广监管过程,能了解疫苗对疾病预防的积极作用,这样才能维持疫苗的公众信心,维护我们的公共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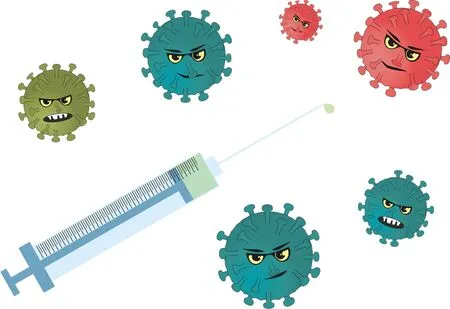
前景堪忧的疫苗
实际上,即便没有各种谣言打击,疫苗的发展也已经遇到了瓶颈。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力、物力是投入在疫苗研发的?2016年,全球疫苗销售总额是275亿美元,看上去是个巨大的市场,但如果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个275亿的大市场,90%是在默沙东、辉瑞、赛诺飞与葛兰素史克4家医药巨头。再看一下具体的疫苗营收,辉瑞的13价肺炎疫苗贡献了60亿美元,默沙东的疫苗贡献了24亿美元,赛诺飞的流感疫苗贡献了17亿美元,可以说能成为重磅产品(一般指年销售过10亿美元的药物)的疫苗也就是有限的几个。
一个成功的疫苗确实有可能成为重磅产品并且保持与其他药物类似的利润率,这也是如今还有少数医药巨头依然愿意开发新疫苗的原因。但不能忽视的是,能成为重磅药的疫苗大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性传染病了,疫苗也开始变“潮”了。这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恶性传染病已经消失了呢?当然不是,只不过是如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差异”越来越大,那些过去让人闻之色变的恶性传染病越来越局限在落后地区,针对这些疾病的药物包括改进现有疫苗或研发新疫苗,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低,自然少有企业涉足,甚至连基础科研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影响。结核病就是一个例子。卡介苗依然是目前唯一有效的结核疫苗,但如之前所提,卡介苗的效果非常不稳定,有的地区保护效果统计研究出来可以到80%,另一些地区却只有20%。而且卡介苗的菌株依然是将近100年前那两位法国科学家培养出来的,新的耐药结核菌不断出现,卡介苗能不能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变异菌一直保持有效也不好说。可以说,改进卡介苗甚至是开发全新的结核疫苗是有社会需求的。
疫苗与其他药物不同,是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意味着通过疫苗来预防、消灭疾病的经济、健康以及社会代价往往远低于其他医疗手段。
那么,现在的结核病主要发生在哪里?欧美国家基本没有。之前说过,英国、法国已经停止卡介苗广泛接种计划。美国甚至从来没有推广过卡介苗,靠自己相对普及和完善的医疗系统,直接筛查高危人群里的潜伏期患者进行治疗,2016年全美结核病例是9 272例,每10万人发病仅2.9例,还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下,还有哪家欧美企业愿意出大钱开发结核疫苗?然而,中国每年依然有90万的新增结核病,仅次于印度。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也是相对落后的新疆、西藏、贵州(新疆的发病率超过每10万人100例)。
谁愿意为穷人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开发疫苗?这个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困扰我们。很幸运,我们还有盖茨基金会等一系列慈善组织愿意支持一些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疫病疫苗研制。但是,仅依靠这些组织的努力也只能缓解部分问题。一些在欠发达地区肆虐的疾病离我们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埃博拉(Ebola)病毒在非洲时有暴发,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处于看热闹的境地,但在2014年,美国终于无法幸免地发生了4例本土病例。在慌乱中,更改预防治疗措施、增加监测、加快治疗方法与疫苗研发以及向非洲提供援助都提上了议程。2016年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寨卡(Zika)病毒也是如此,在东南亚偏远的雨林地区一直存在感染人群,只不过我们一直“看不见”或者选择“不看见”这样的病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日益发达的国际交通、贸易,这种不知躲在哪个山沟里的疾病突然威胁到“养尊处优”的“城里人”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
遗憾的是,现代制药业与医学研究日渐专注于发达地区的健康挑战,对所谓的“热带疾病”的防备远远不足。发达国家有一些针对“热带疾病”药物研发的激励措施,最出名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售”快速审批权的做法。成功开发“热带疾病”药物的公司可以获得一个“快速审批”权(适用于任何新药申请,不保证批准但保证快速获得结果),这个“加速卡”可以出售给其他公司。这样,一些小型制药企业,通过转卖“加速卡”也找到了新的经营模式,在本不赚钱的疾病里获得了商机。作为全球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员,同时自身又存在巨大地区经济差异的中国,我们也应该考虑参考一些类似方法,参与到一些不受关注的传染病的疫苗或药物研发中来。
再有效的疫苗,也离不开人们对它的信任与接纳。詹纳发明天花疫苗后,拿破仑让自己的军队全部接受疫苗接种。在英法战争时期,詹纳写信为被俘的英国士兵求情,拿破仑收到信后立刻释放了所有战俘,说自己不能不接受对人类社会助益最大的人的请求。在享受疫苗为我们带来的保护时,请不要忘记这背后几百年的曲折艰难,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公共健康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