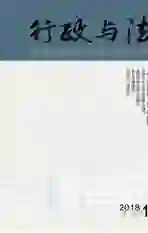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的原告举证责任分析
2018-02-14杨杰
摘 要:在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仍需原告对该损害事实承担证据提出责任。原告证明的损害事实可以分为普通财物和特殊财物两大类,原告对普通财物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几乎不需加以证明,举证责任即可发生倒置;原告对特殊财物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必须加以证明,举证责任才能发生倒置。原告对特殊财物证明难度较大,并且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不能仅根据证据形式来判断证据的效力。因此,即使在特定情形下由被告承担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免除原告对损害事实的证据提出责任。行政诉讼中应划分“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并适当运用价值衡量,以促进举证责任合理分配。
关 键 词:行政强拆;举证责任;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12-0107-14
收稿日期:2018-09-24
作者简介:杨杰(1993—),四川宜宾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度校级研究生科研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ZD014。
《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①据此,被告不仅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以及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还应对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②表面而言,该类型案件中几乎所有举证责任都由被告承担,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否掩盖了原告理应扮演的角色。毕竟在举证责任倒置条件下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性已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民事诉讼领域已有“举证责任分割论”的观点出现,但行政赔偿诉讼领域却鲜有相关讨论。[1]本文通过梳理学理争点并考察典型行政强拆赔偿案例,以探究我国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在被告承担损害事实举证责任情形下,原告对损害事实提出证据行为的性质、证据构成和证明范围等。希冀抽象出基本规范内涵,用于指导以后的相似案件,[2]为行政强拆赔偿案件更公正合理的举证提供些许更易操作的具体方法。
一、学理分野与现行规范
(一)学理分野
《行诉法》第34条第1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①据此,我国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一般原则。[3]該款确立起被告提供证据的行为被学界普遍定性为被告的举证责任,但对于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的性质学界却存在不同的观点。[4]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原告对损害事实提出证据,属于司法实践中原告提供证据的具体类型之一,故有必要对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的性质进行回应,进而厘清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的性质。
⒈权利说。自由心证模式下,当事人提供证据是其基本的诉讼权利。[5]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权基于职业道德和裁量权对双方证据作出认定并进行裁判。当事人为了己方诉讼请求被法庭支持便尽可能充分地向法庭提供证据,故此种模式中,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行为是非常积极主动的,类似于对权利的主动行使。我国行政诉讼中虽然不适用自由心证,但有学者认为《行诉法》第37条规定的“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是原告的一种举证权利,并非举证责任或义务。[6]故该条款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利说的特点,原告可以基于该条款规定积极主动提供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使法官更清晰准确地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对比,最大程度还原案件真相,达到法律真实,从而更倾向于支持己方的诉讼请求。但笔者认为,第37条规定的原告提供证据与行政强制拆迁赔偿案中的原告提供初步证据其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可以”提供证据,原告具有选择性,可以积极提供被告违法证据,也可以不提供被告违法证据。原告提供证据指向证明“合法性”的实体问题,不会直接阻碍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即使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也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所以,原告是否提供证据对案件结果没有直接关系,原告在诉讼中是选择性的“协助”,可有可无;而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都需要原告提供证据,其赔偿诉求才能获得支持,目的是证明“程序性”问题。换句话说,在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损害事实的证据,如果原告提不出证据就无法证明行政争议的存在,这将导致原告立案困难或被驳回起诉,此种程序性阻碍使得原告赔偿诉求极有可能不被支持,原告在诉讼中是责任性的“参加”,必不可少。因此,虽然强拆赔偿案件中的原告提供证据行为与《行诉法》第37条为代表的原告提供证据行为都是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的具体表现,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强拆赔偿案件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明显不是一种权利,虽然其具备权利的构成要件和表征,但原告不能凭借个人意志去自由决定是否在诉讼中提出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提出证据行为受到法庭的干预。
⒉义务说。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中提供证据是当事人所负有的法定义务。当事人双方特别是原告应对其所诉求标的承担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该责任的基石便是有义务举证证明己方诉讼请求的合理性,是故原被告均有义务在案件诉讼中向法庭提供尽可能充分的证据。[7]基于上述观点,有学者主张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是原告对人民法院的相对义务,其理由在于:根据《行诉法》第34条确立的证据制度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原理,行政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故举证责任只能由被告负责,应为被告专属,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的只能是行政机关,如果原告提供证据的行为定性为举证责任,便意味着原告承担了本应由被告承担的证明任务。同时该观点还认为,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证据证明符合起诉条件,那么原告将承担败诉风险,为了将原告和被告承担败诉风险的原因相区别,创设出了原告承担的是一种义务的学说。[8]笔者认为,该观点实际上把举证责任等同于说服责任,没有进一步厘清举证责任的内涵。因为举证责任不仅包括实体上的说服责任,还应当包括程序性的证据提出责任。司法实践中若没有原告承担证据提出责任,则很难证明行政争议的存在,整个诉讼程序都将无法开启。正如上述观点所主张的,原被告在不能提出证据时,均将面临败诉风险。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原被告提供证据所证明的对象不同而作出“责任”或“义务”的划分。有学者已经对《行诉法》第34条的理解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该条款规定的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并没有规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事项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在具体案件中,要求被告对所有事项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切合实际的。[9]该观点实质上把原被告提供证据的行为同等对待,均认定为举证责任。更有观点认为,《行诉法》第34条的规定仅仅是被告举证责任的规定,既不能推断出行政诉讼仅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也不能推断出行政行为合法性仅由被告负举证责任。[10]而且“确定举证责任时需考量公平价值观,‘谁主张,谁举证便是公平价值观具体表现,对行政诉讼来说应同样遵循。”[11]即使不论立法或者司法实践,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这也只是司法个案的价值权衡,而不具有普遍性的建构意义,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是不妥当和不公平的。因此,原告提供证据是一种相对义务的观点是不足以采信的,更倾向于是一种责任。此外,义务说的大前提是在当事人进行主义国家,而我国行政审判是典型的法官主审制,且现行行政法律条文中也很难解释出原告提供证据是一种义务。由此可知,原告在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提出证据并不是一种义务。
⒊举证责任说。法官主审制模式下,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是一种法律责任,学界也叫做举证责任。随着诉讼的开启,双方当事人都和法庭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法官居中裁判,处于主导地位,当事人都有对法庭负责的行为取向,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由此产生。[12]首先,从举证责任的概念可以得出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需对法庭负责,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所以举证责任并不专属于被告;其次,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告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需通过举证责任予以体现;再次,行政诉讼法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原告的实体权利主体和诉讼地位需通过举证责任体现,而且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将会降低其败诉风险;最后,有些案件中原告比被告更靠近证据,所以原告取证难度较小,如果一味让被告举证,则可能陷入证明受阻的困境,也有违诉讼中当事人地位平等和公平原则。因此,把原告提供证据的行为定性为举证责任并无不妥。
学者们也认可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就损害事实提供证据行为是承担一种举证责任。刘飞认为行政诉讼中原告也负有举证责任,“被告负有举证责任”的观点实际上混淆了“被告对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和“被告在行政诉讼中负举证责任”的区别。”[13]王天华认为:“《行诉法》第34条没有排除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的存在。”[14]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不仅需要负举证责任,甚至不排除特殊条件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举证。通过上述两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行政诉讼中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命题在学界具有一定共识。而具体到行政赔偿诉讼中,马怀德认为:“行政赔偿诉讼在程序上区别于普通行政诉讼,原告对造成的损害事实应承担初步举证责任。”[15]可见,此观点将原告就损害事实提供证据的行为界定为举证责任,并不是一种权利或者义务。此外,邓刚宏也从主观行政诉讼角度主张在行政赔偿之诉中,原告就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16]原告为自身利益而提供证据的行为是履行举证责任。
从司法解释角度审视,最早将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损害事实的行为界定为举证责任的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从中可以推导出原告需对自己主张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行诉法>的解释》)第27条第3项:“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条首次明确提出原告对损害事实承当举证责任;最新的规定是2018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行诉法〉的解释》)第47条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也就是说,当原被告双方对行政赔偿数额产生分歧时,若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则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从上诉三个司法解释可以窥见,司法实践中原被告提供证据的行为均被视为举证责任,保障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也体现了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在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原告就损害事实提供证据的行为宜定性为一种举证责任。
(二)现行规范分析
⒈规范梳理。我国在行政赔偿诉讼中确立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主要依靠三个规范性文件:一是2013年《质证程序规定》第6条第3款规定:“下列事实需要证明的,由赔偿义务机关负举证责任:因赔偿义务机关过错致使赔偿请求人不能证明的待证事实。”二是2015年《行诉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三是2018年《适用〈行诉法〉的解释》第47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⒉规范分析。首先,在三个规范性文件颁布之前,行政赔偿案件中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突破,而是对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完善。不能简单地以《行诉法》第34条所规定的“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为依据将行政诉讼举证规则解释为“被告负举证责任”。该法条可以确定的是被告负举证责任的主要范围是被诉行政行为合法。①换句话说,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待证事实,确定性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专属于被告,但未清楚地说明除此之外的待证事实由谁承担举证责任。[17]故在以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为前置条件的行政赔偿领域,仍然遵循公平价值,体现原被告双方平等地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事实上,随着行政事务日益繁多和立案登记制的实施,也使得行政诉讼案件迅速增多,行政强拆赔偿诉讼中完全由被告举证既不符合诉讼规律,也无法保障案件得以及时公正的审判。若举证责任全部归被告一方,原告对己方诉讼请求不负任何举证责任,那么某些原告势必会恣意提起行政诉讼而导致滥诉频现。而公正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减少和抑制行政纠纷,具备息诉止争的功能。”[18]并且行政诉讼原告承担与其诉讼请求和举证能力相匹配的举证责任,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②是故原告负举证责任不仅仅是基于学理上的考量,也是司法审判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次,上述三个规范性文件确立了被告对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这是我国行政赔偿领域举证责任的一次巨大变革,成为原告承担损害事实举证责任的例外,改变了传统行政赔偿损害事实“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该例外为行政赔偿案件损害事实举证责任的倒置。但“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主体在诉讼中对全部事由担负完全的举证责任,而是原告方也应对发动诉讼的特定事由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19]并且“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原告应对有些事项提出证据,这是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新趋向,并被相关的法律解釋所确认。”[20]所以,即使在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原告也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因为从实体法层面而言, 权利主张的正当性根源于证据的支撑,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权利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从证据法的层面而言,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从行政法限制公权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特定目的出发,考虑到行政强制拆迁赔偿案件中由于房屋或者违法建筑物已被拆除,相关证据难以固定,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陷入举证不能困境所进行保护,进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损害事实)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说服责任,但并不是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都交给被告独自承担。
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原告此种举证责任究竟是证据提出责任还是说服责任抑或二者兼有之,原告举证需到达怎样的证明标准以满足诉讼需求,初步举证时对证据形式有无特殊要求,原告举证责任的范围、时限等等均值得深入研究。然而,学理和现行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判断方式与裁判基准,故笔者试图通过司法案例的研习解决这些问题。
二、典型案例的司法考察
学理上的考量和考察行政法律规范中涉及行政赔偿损害事实举证责任的规定只是宏观维度的分析,为解决上述疑问和考察实践中法院是如何確立原告的举证责任的,笔者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予以完成。以指导案例91号: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为点,通过北大法宝推介的同案由重要案例和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经过阅读与筛选,选取部分比较典型的案件进行群案研究。①此类案件均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法院在诉讼中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对于损害事实或多或少承担了举证责任。②
表一:新《行诉法》颁布之前的典型案例
■
表二:新《行诉法》颁布之后的典型案例:原告对损害事实的初步举证责任履行后,其赔偿请求获得支持或部分支持
■
表三:新《行诉法》颁布之后的典型案例:原告未对损害事实履行初步举证责任,其赔偿请求未获得支持
■
由表一至表三可以看到,近年来涉及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争议纠纷大量涌现,其中由于行政程序违法而导致的行政赔偿问题日益凸显。此类型案件中涉及的建筑物已被拆除,导致相关证据缺失,因此如何确定原告的损害事实成为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由表一可知,在《行诉法》第38条第2款确立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之前,司法实践基于公平原则已开启了被告承当举证责任的先河,对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是在典型案例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肯定和推广。这种把典型案例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是我国目前立法模式之一。有学者就曾提出“在法治实践中以司法续造为基础的渐进式入法路径正在逐渐成形。”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也注意到了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创新,[21]以典型案例为基础,经过司法解释的提炼,最终形成规范的普遍化建构,这一特色路径在行政赔偿领域同样适用。由表二、表三可知,即使在适用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下,原告仍需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履行举证责任,则其诉求可能不被支持。
三、案例规范的内涵及“射程”
(一)案例规范的内涵
⒈原告需承担证据提出责任。姜明安认为,完整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由证据提出责任(程序责任)和说服责任(实体责任)两部分构成。证据提出责任的法律效果在于证明构成法律争端,说服责任的法律效果是使法官确信其实体主张,是一种决定败诉后果由谁承担的实体责任。[22]该观点厘清了举证责任的内涵,其中证据提出责任指当事人应该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构成行政争议,以推进诉讼的进行。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官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在不能证明特定事实或者特定的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上述定义笔者认为,《质证程序规定》和《适用〈行诉法〉的解释》中的“举证责任”应界定为说服责任,《行诉法》第38条第2款中既包括证据提出责任也包括说服责任。而行政赔偿诉讼中最典型的证据提出责任应是《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1款:“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内涵不甚统一,也正好印证了湛中乐等学者的观点:我国目前在诉讼法领域使用的“举证责任”概念,即包括了证据提出责任也包括说服责任。[23]所以,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大体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证据提出责任。原告对损害事实的诉讼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推进诉讼的进程。二是说服责任。提出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当行政赔偿损害事实然真伪不明时,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结合本文案例,在原告因被告原因无法就损害事实举证的案件中,可以把整个案件的待证事实简单的分为:a被告实施了强制拆迁行为,b被强制拆迁建筑物内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财物,c原告财物是否受到损失,d原告损害事实与被告强制拆迁行为有无因果关系。根据具体判决要旨的梳理,如禄久顺案中“上述人出具证人证言、发票及现存邮票等证据”、于保志案中“根据生活常理,结合其提供的受损物品清单”、孙美玉案中“原告提供了现场照片,被告虽不予认可,亦不能举出反证”等等可以发现,这些证据的作用主要指向的是b——证明被强制拆迁的房屋内存在相对人一方主张行政赔偿的物品,原告并未承担举证证明该物品是否遭受损失、损失程度以及损失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未进一步承担使法官确信财物受到损失的说服责任,仅仅是一种程序性推进责任,目的在于证明原告赔偿主张的物品属实,进而构成行政争议,至此由举证责任倒置引发的原告举证责任履行完毕。所以基于《行诉法》第38条第2款确立的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在司法实践中提供证据的行为是承担证据提出责任,是原告对损害的事实提出初步证据,合理说明和证明争议财物的存在,证明构成行政争议,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此时法官审查证据的标准是合理性而不是证据优势,更不是严格的说服责任。
笔者在这里主张直接采用姜明安的举证责任二分法,把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定性为证据提出责任,不建议借鉴本文引言所提及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割论”,①虽然都是因举证责任倒置后遗留给原告的举证责任,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本文案例所涉及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的行为在于推进诉讼程序的进行,没有提升到“说服”层次。退一步说,即使存在“说服”,也是说服行政争议的存在,而不是说服法官支持其诉讼请求。而且“我国行政诉讼有其自身特点,它存在着说服责任与证据提出责任的区别,”[24]故笔者的讨论也是符合现有举证责任划分理论的。经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仅限于证明被强制拆迁建筑物内存在其所主张的财物。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时间仅限于诉讼开始阶段,由原告先承担证据提出责任证明行政争议的存在,使案件顺利进入诉讼程序,被告暂时不承担举证责任;当原告按照要求履行完证据提出责任后, 被告再承担法定的举证责任, 这时原告不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
原告之所以承担证据提出责任,一方面利于诉讼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具体而言,在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建筑物、屋内财产等不可避免地被损害,行政机关基本不可能对其财产登记毫无遗漏,而被拆迁人通常对其屋内财产比较清楚,如果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让行政机关进行举证,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无所适从,不知从何举证;而且由作出否定性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不符合人类理性的认知。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如果当事人作出肯定性主张则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主张,如果当事人作出否定性主张则不负举证责任。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让本会作出不存在损害事实(否定性主张)的被告提出证据证明其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肯定性主张),相当于“自证其罪”,难度可想而知。相反,让原告提出证据证明其损害事实是相对容易的,而且更加节省时间和精力,符合诉讼效率原则。不过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相对人因为房屋灭失,举证难度较大,所以让其承担损害事实的证据提出责任是比较合理的,同时符合现有法律框架。至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不难理解,诉讼中不排除一些相对人利用证据已经灭失的漏洞而漫天要价,虚构财产损失,在相对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而行政机关又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下,极有可能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裁判,导致国家财产损失。如果原告对损害事实承担证据提出责任,则可以大大降低此种风险。
⒉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程度。证明程度即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认定待证事实存在时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笔者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梳理已经呈现出了原告举证的差异将会直接决定其赔偿请求是否被法院支持,同时发现,在相对人主张的财物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财物如日常生活用品、装修损失等,一类是特殊财物如珠宝、首饰、邮票、大件物品等。针对第一类财物,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几乎不需加以证明,举证责任(主要是说服责任)即可发生转移。如沙明保案中法官认为“物品均系日常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物品不存在,故对该物品应予认定”;庾家乐案中“根据原告原先开办企业的情况,有相应的办公用具及生活用品予以出租,合乎情理”;高新会案“结合申请人提供的财产损失清单,根据日常生活经验,适当赔偿。” 由上可知,对于普通财物相对人往往易于举证,在讼诉中可以通过相对人陈述、自制财物清单等主张赔偿损失,甚至法院亦可根据常识进行酌情判决而不需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即使是“单一证据”也可能获得支持。对这一部分普通财物之所以采取极低举证责任是不难理解的,根据常识性判断,被强制拆迁的房屋内基本均存在日常生活用品,这也是保障相对人基础性财产损失、规制行政机关强制拆迁行为的有效手段。但此部分赔偿数额一般较小,有时还会考虑折旧因素。针对第二类财物,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所负担的证据提出责任必须加以证明,举证责任(主要是说服责任)才能发生转移。如禄久顺案中“禄久顺出具了证人证言、发票及现存邮票等证据”、姿博汽车案中“原告提供烧毁财物清单与残骸照片”、大恒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公证材料和物品清单予以证明”,这些案例中法官均支持其赔偿诉求。故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据优势,那么法官一般会支持其诉讼请求。相反,如果原告不能进行证明,那么其赔偿诉求往往不被支持,如赵伯涵案中“上诉人主张阁楼中的物品,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部分损失的存在,不予支持”、李桂兰案中“上述人提出储藏间价值67000元,未提交购买依据,对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吕新蕾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图纸及其它物品并非生活必需品,必须有证明该物品存在、数量多少、价值大小的证据。但原告一直未能提供初步证据,因此未尽到初步的举证责任,故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马旭池案中“原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等等。所以在诉讼中,原告若对特殊财物提出赔偿诉求,至少需要举出两种以上证据且能相互印证,不然将面临败诉风险。在賠偿数额方面法官会比较谨慎,不像普通财物一样进行笼统计算,而是单独计算,根据市场价格就高不就低,如沙明保案中“上诉人主张实木床价值为5万元,法院结合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赔偿3万元。”
⒊原告提供证据的形式要求。通过对判决书的研习,案件中证据形式主要呈现为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涉及普通财物的赔偿案件主要依靠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进行取证,涉及特殊财物赔偿案件主要依靠书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证据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证据的证明力,一般说来,此类行政赔偿案件中应当遵循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证据证明力的规定,但在一些强制拆迁案件中,若行政机关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则不能仅根据证据形式来判断证据的效力。如在大恒案中,①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支持各自的主张,其中原告方最主要的证据是公证处在房屋被拆除一个月以后对现场拍摄照片的公证证明,而被告方最主要的证据是当地法律服务所在拆除当日制作的《用品清单》,其上有规划局、村委会、镇政府及大恒公司员工的签名。如果仅从双方的证据本身来看,原告提供的是公证文书,被告提供的是国家职能部门制作的公证文书,而且属于现场笔录的性质,因此,根据《证据规定》第63条第(1)项和第(2)项“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现场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和证人证言”的规定,被告方的证据效力似乎比原告方更高,更值得采信。而从时间上看,原告的证据是在拆除一个月后作出,期间不排除原告改变现场、变更证据的可能性,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则是在拆除当日作出,时间上似乎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然而,两级法院均未采纳被告方所提供证据,而是直接根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确定了被告应当赔偿的数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未能遵循程序规定,强拆时未对现场进行证据保全并对相关财物进行登记及公证保全代管,致使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损失的大小,故只能以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作为强拆现场的依据。
(二)案例的“射程”
⒈行政诉讼中应划分“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被告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负举证责任”规则和其他待证事实“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但仅有这两个规则是不够的,对于这里的“举证”性质还应当予以明确,故应明确划分“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这样可使“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更精细化的维度展开,有助于在一定的规则基础上使举证责任能在当事人之间条分缕析,避免责任的片面单一化倾向。”[25]这对于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更清楚具体地实现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合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实际上,我国《行诉法》虽然没有明确划分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但法条内涵当中已经体现出划分的趋势。比如《行诉法》第34条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这里的举证责任便是说服责任,而《行诉法》第49条原告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举证责任属于证据提出责任。[26]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部法律中出现相同的“举证责任”,但其表达的内涵却不相同,反映出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性。因此,如何建构一个清晰明确的举证责任概念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当前举证责任概念其实是建立在法律要件分类理论基础之上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論不周延。故建议摒弃法律要件分类理论,把举证责任进一步明确规定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这样才能使行政诉讼中证明更加合理可操作,规避审判实践中由于举证责任概念模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⒉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可适用价值衡量规则。价值衡量规则是指法官通过对相关社会价值的关注,运用法的衡平原则追求一种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因此审判实践中,在适用成文规则明显与社会价值相悖的情形下,法官可以运用价值衡量规则为补充,重新分配举证责任。法官需区分不同情况将举证责任分配的双重规则有机结合,以作出符合法的正当性的裁判。在运用价值衡量规则时法官应当结合当事人诉讼请求和具体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等,酌情确定由具备举证能力或举证能力明显强于另一方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如禄久顺案、姿博汽车案、大恒科技案等均是法官运用价值衡量规则的典型案例。行政赔偿案件中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肇始于2013年的《质证程序规定》,但上述三个案件均判决于《质证程序规定》颁布之前,禄久顺案中法官基于公平原则要求赔偿数额的确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姿博汽车案中法官运用价值衡量的方法重新分配举证责任,要求被告承担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如无法举证的,则由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大恒科技案中法官认为应当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责任,以体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些运用价值衡量的司法案例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也间接推动了行政赔偿诉讼中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出台。因此,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坚持价值衡量的方法,发挥司法能动的作用。法官可根据具体案情,运用价值衡量的方法对原被告举证责任作出适当调整。
⒊《行诉法》第38条第2款的完善思路。总的来说,基于诉讼规律,立法首先应当给予原告和被告同等对待,将“谁主张, 谁举证”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27]这样,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不再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意义,不会再引起“被告举证责任”理解的误区,从而恢复原告的举证责任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发挥司法解释的功能,将举证责任划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明确若适用《行诉法》第38条第2款,即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因果关系以及损害事实负举证责任,同时补充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承担证据提出责任,且原告提供旨在证明损害事实的证据应当与行政行为在时间、方式上具有合理的相关性。
⒋《行诉法》第38条第2款中“被告的原因”解读。《行诉法》第38条第2款后半句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其中“被告的原因”在具体案件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有的是未进行财产保全:如在大恒案中,“上诉人并未将涉案物品进行公证保全代管”;在沙明保案中,“行政机关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资博汽车案中,“被告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之前没有履行证据登记与保全的法定义务”。有的则有违妥善保管义务:如禄久顺案中,“被告在保全财产后,没有尽到注意及妥善保管的义务”;在赵伯涵案中,“因政府保管不善,物品现已灭失”;庾家乐案中,“财物由被告保管但至今未归还,推定已灭失”。所以,基于前述具体案件的剖析,根据现行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①第17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拆迁时,应当由公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及其房屋内物品进行证据保全。笔者大致把“被告的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违反实体性规范,一开始就未履行义务保全;一类是违反程序性规范,保全以后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此外,从保全以后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也可能承担赔偿义务可以推导出:即使是强制拆迁行为本身合法,也有可能造成因被告的原因致使原告无法初步举证,这与当前绝大多数因违法拆迁导致原告无法初步举证是有所区别的。“被告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限于行政机关的违法拆迁行为导致相对人财产损失,其外延更为广阔,如行政机关财产保全中尚不构成违法的轻微程序瑕疵亦可归类于其中。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涉及强制拆迁引起的行政争议大量涌现,妥善解决相关赔偿问题不仅涉及被拆迁人权益的保障,更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基于被告原因造成原告难以就强制拆迁导致的损害事实提供充分证据的行政赔偿问题日益凸显,由被告承担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但因我国举证责任概念模糊,往往造成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分配不清。对此,笔者认为,即使由被告承担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免除原告承担对损害事实的证据提出责任。据此,为了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被拆迁人正当权益,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中承担证据提出责任,促进行政赔偿诉讼的顺利进行。笔者坚信通过厘清举证责任倒置下原被告承担的具体举证责任,必将有利于现有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叶自强.我国举证责任概念的模糊性问题[J].证据科学,2010,(06):657;叶自强.举证责任的倒置与分割[J].中国法学,2004,(05):138.
[2]杨杰.工傷认定案件中的优势证据标准研究[J].证据科学,2018,(02):197.
[3]沈福俊.论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优化[J].法商研究,2006,(05):108-114.
[4]关保英.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研究[J].法律适用,2011,(07):50-55.
[5](美)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235.
[6]郑元健等.《行政诉讼法》新修评议[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5,(02):67;刘善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论纲[J].中国法学,2003,(03):69-75.
[7](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97.
[8]关保英.行政诉讼中原告提供证据行为研究[J].法律适用,2011,(07):51.
[9]甘文.规范和理论的缺失与发展关于行政诉讼原告举证责任的几个问题[J].法律适用,2005,(08):7.
[10]刘善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新论[J].行政法学研究,2000,(02):16-19.
[11]杨寅.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梳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 ,(03):14-21.
[12](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486.
[13]刘飞.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1998,(02):50-53.
[14]王天华.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公法研究,2009,(01):89.
[15]马怀德.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J].证据学论坛,2002,(01):210-224.
[16]邓刚宏.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逻辑及其制度构建[J].政治与法律,2017,(03):141.
[17]张步洪.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体系解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04):45.
[18]江必新.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J].中国法学,2013,(01):5-20.
[19]王利明.论举证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3,(01):150.
[20]刘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学理分析[J].政治与法律,2008,(05):17.
[21]江必新.论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创新[J].法律适用,2018,(07):5.
[22][24][26]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63,464,466.
[23]湛中乐.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J].行政法学研究,2000,(04):21-27;李年清.行政强拆赔偿案件中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J].时代法学,2015,(01):89.
[25]沈岿.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个性化研究之初步[J].中外法学,2000,(04)456-465.
[27]王彦.行政诉讼原告举证责任的立法完善[J].法律适用,2006,(08):26.
(责任编辑:王秀艳)
Analysis of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in Administrative Forcible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Cases
——Reflections on the Invers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Article 38,
Paragraph 2,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Yang Jie
Absrtact:In the case of administrative forcible demolition compensation,if the plaintiff is unable to prove the damage due to the reasons of the defendant,the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damage,but in judicial practice,the Plaintiff still needs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damage fact.The damage facts proved by the plaintiff can be divided into ordinary property and special property.Th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on the damage facts of ordinary property can be inverted without proof.Th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on the damage facts of special property can only be inverted if th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on the damage facts of special property is proved.It is difficult for plaintiffs to prove special property,and under some special conditions,the validity of evidence can not be judged only by the form of evidence.Therefore,even if the defenda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of damaged facts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the plaintiff can not be exempted from the burden of proof of damaged facts in judicial practice,and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divided into “burden of proof” and “burden of persuas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and the value measurement can be used appropriately to promote the clear and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emolition;burden of proof;damage facts;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