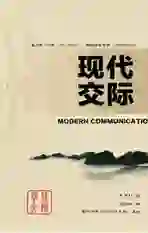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解释与适用
2018-02-13郑燕秋
郑燕秋
摘要:扰乱法庭秩序罪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几种行为方式,引发了律师界的质疑,被认为是针对部分群体的修正。然而,本罪的关键是在于如何理解适用修订后的罪名。本文以限制解释为视角,对主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等进行了解释学上的分析,以求平衡司法权威与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间的冲突。
关键词:扰乱法庭秩序罪 适用 限制解释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1-0255-02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原来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较大的修订,该罪名的最终条文在原309条之上,增加了两种行为方式,作为补充项,一是针对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有侮辱、诽谤、威胁的行为,且不听法庭制止,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程度;二是针对诉讼文书、证据等法庭材料和法庭设施,有毁坏,抢夺、损毁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时,殴打的对象也进行了扩大,将诉讼参与人纳入本罪的犯罪对象。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死磕派”律师在庭审中的“闹庭”现象已为法庭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因此有人认为此次的修订,是针对这个特殊的律师群体。虽然该罪的修订在律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声讨,并最终将一审稿和二审稿中的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予以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行为方式,避免罪名落入“口袋罪”的口实之中。笔者认为,扰乱法庭秩序罪确实不宜采用例示与概括的方式规定罪状,“口袋罪”的担忧不无道理,毕竟司法权及司法机关的力量远大于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若是不加以具体规定的限制则可能滥用甚至异化扰乱法庭秩序罪。因此,为了平衡司法权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也为了维护法庭秩序与司法权威,应肯定此次扰乱法庭秩序罪修订中的具体规定。
然而,由于对该罪名尚未存在有效的法律解释,有人担忧公权力可能利用该规定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司法人员利用职权扩张解释条文,使得条文被滥用。虽然笔者以为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对于该罪的解释与适用确实是值得探究与明确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解释学上作出努力,为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阐释和适用提出建议,也希望使得司法权和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威能够达成新的平衡。
二、以限制入罪为方向的解释
经历三审稿,修正案(九)的最终修订版中删除了备受诟病的“其他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的草案,去除了兜底性质的条款,此行为符合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明确性原则,是指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应当清楚明确,使公众能够确切地了解犯罪行为的内容,准确地圈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刑罚的触须不会触及刑法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立法要求明确,然而由于法律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无穷性,二者之间的衔接始终离不开对法律进行解释,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罪状解释实属必然,同时这也是在司法层面对该罪进行限制,以降低其负面效应。
(一)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修订前的《刑法》309条中关于本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只是将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归纳为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方式,并进行刑事规制,而其他轻微的扰乱行为便由行政处罚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进行规范或者不看作犯罪行为。然而无论是修订前后,本罪处罚的都是严重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且都是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因此,对扰乱法庭秩序具有程度上的要求是本罪的固有内涵。
(二)言论犯的限制解释
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审判中,“闹庭”现象愈演愈烈,从刑事审判蔓延至行政审判、民事审判,而扰乱法庭秩序罪对于罪状的扩大,显然已经将行为犯发展为言论犯,不再是单纯的哄闹、冲击法庭的肢体冲突行为,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应该是能够即时、了当地使庭审无法进行下去的行为,但是侮辱、诽谤和威胁这种非暴力性质甚至非实际上的肢体行动的方式,与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以及殴打等具有暴力性肢体冲突的行为相比而言,对法庭秩序的扰乱是否具有同质性尚值得商榷,即言语暴力和严重的肢体冲突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但一些言语暴力对法庭秩序的扰乱也具有相当的严重性,比如在法庭上对法官人格的公然贬损和辱骂言行,毋庸置疑是对法庭秩序的肆意破坏,“言论犯”入刑的正当基础也正是有基于此。
至于如何認定扰乱法庭秩序罪中的“侮辱”和“诽谤”行为,笔者认为,应当依据《刑法》现有的条文进行解释,即采取第246条的标准。侮辱、诽谤罪必须是在主观上具有侵害他人名誉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客观的侮辱、诽谤的行为,满足情节严重的要求,即指侮辱、诽谤的内容,足以使他人的人格和名誉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损害,也指对被害人引起的心灵创伤和恶劣的影响;还应该同时满足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条件,才能构成此罪。基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中本身有对侮辱、诽谤行为的解释,该标准的确定应当是明确的。另外,关于“威胁”的理解,笔者认为也应当做限定解释,确定为具有“暴力”性质的强制而非一般广泛层面上的强制,如恐吓、精神强制等;由于本罪的发生空间必须是在庭审期间的法庭上,因此只有具有暴力性质的威胁才具备扰乱法庭秩序的严重性,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物、毁坏名誉等相威胁。
(三)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解释
所谓聚众哄闹法庭,是指纠集三人以上,公然违反法庭纪律,在法庭上大声喧哗、吵闹、吹口哨等起哄捣乱、制造事端的行为。所谓聚众冲击法庭,是指纠集三人以上,强行闯入法庭,强占庭审席位等,导致法庭秩序混乱的行为。有人认为:“纠集三人以上在法庭内进行录音、录像和摄影的行为也是聚众哄闹。”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哄闹行为的特点在于通过身体的口、手等器官或其他工具发出噪音来实施干扰,由于法庭是通过听取诉辩双方的发言及辩论来审理案件,需要一个肃静的环境方能顺利进行,而一定程度的噪音恰恰破坏了这样一种特别的环境,导致法庭庭审活动的中断或者是无法进行下去。而该行为显然并不符合上述特点,未经法庭批准的录音、录像、摄影行为虽然也是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但录音、录像、摄影行为本身并不会产生噪音,不可能以上述方式来干扰法庭秩序。当然,如果在非法录音、录像、摄影行为被制止的过程中,行为人以大叫大嚷等方式进行抗拒的,其后面的行为还是可以认定为哄闹行为的。endprint
所谓殴打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进行限制,指那些正在庭审中或者法庭外履行司法职责的工作人员,且根据法定刑来判断,殴打应当是轻微的肢体暴力而不能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否则直接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关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笔者认为,对这里所讲的司法工作人员范围不能随意解释,应当以刑法的规定为界,包括正在履行审判工作职责的审判人员,包括陪审员、书记员、正在履行检察工作职责的公诉人、正在履行监管工作职责的司法警察。根据法条的表述可知,“聚众哄闹、冲击法庭”和“殴打”是属于两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性要件,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行为之一即可构成此罪。
(四)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毁损诉讼文书、证据“等”的解释
这里的“毁坏”具有明确的指向范围,是针对法庭的设施和设备,应当是隶属于庭审中固有财物的部分,而“抢夺、毁损”的则是针对法庭中的诉讼文书、证据材料的抢夺和破坏。另外,“等”的解释必须是指其他具有和上述行为相同性质的物理上的破坏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中采取了同类解释的要求,例如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这里的其他方式应当具有和放火、爆炸、决水相当的危险性。
(五)特定时空的解释
虽然第309条并没有明文把时间和地点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但分析本罪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特定的时空条件应当是本罪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犯罪客体方面而言,本罪侵犯的是法庭的正常秩序,因此时间上只能是发生于庭审期间,地点上也必须符合法庭内外。所谓“庭审活动期间”,应当始于宣布开庭,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合议庭评议、法庭宣判等各个中间环节,止于宣布休庭或闭庭时;这里的“庭审”,应当做广义理解,包括横向上的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类诉讼案件的开庭审理活动以及纵向上的一审、二庭、再审等各个审级别。所谓“法庭内外”,自然不包括法院内设的厅室,而必须是具有审理和裁判案件职能的场所,应当通过法庭的功能属性进行判断,例如有时法院将庭审活动安排在田间、村头、病房甚至露天会场等处,由于此时该类设施是作为法庭审理案件的功能场所,理应视为法庭。而若是在法庭之外的殴打、辱骂司法接待人员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法中规定扰乱法庭秩序罪保护的是法庭开庭审理案件的正常活动和秩序,因而该罪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若是不符合该罪的时空条件,可以妨害公务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或故意伤害罪等论处。
三、扰乱法庭秩序罪的适用
(一)严格遵守程序
国外的立法中有藐视法庭罪,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无需起诉,可由法官直接进行裁断,这是基于“法官所见,无需证明”的原理。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可借鉴国外模式但不可照搬,法庭中,控辩审三方的地位是不一致的,在目前纠问制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在庭审中的主导作用是强大的,若是法官在庭审冲突发生的过程中自审自判,很可能导致法庭冲突的升级,不利于维护法官中立的形象和司法的公平公正的權威,控方和辩方的平等是程序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若是发生在庭审中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仍应移送公安机关,严格执行公诉案件的侦查起诉程序,再交由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当然,由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必然事牵发生地法院的利益和冲突,因此事发地的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不宜参与审判,而是应当坚持异地原则,由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二)审慎适用法律
总体上来说,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是法律完善的一大步,对于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解释与适用也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着限制解释的理念,应当能够兼顾司法权利和辩护权利等的平衡。法律的正确适用是理解法律的前提,而法律的审慎适用是一部善良之法的外化表现。在律师群体的担忧面前,法律应当作出合理的回应,在扰乱法庭秩序的认定中,坚守住“情节严重”的底线与要求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司法工作人员要注意区分案件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只有严重扰乱了法庭秩序,致使庭审活动难以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否则可以通过《刑法》13条的但书规定予以出罪,采取行政或是其他性质的替代性处罚措施;而立法者也应当采取限制解释的态度,坚持平衡控辩双方权利的立场,从而防止由于法律的制定导致庭审冲突的升级或是激化法庭矛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