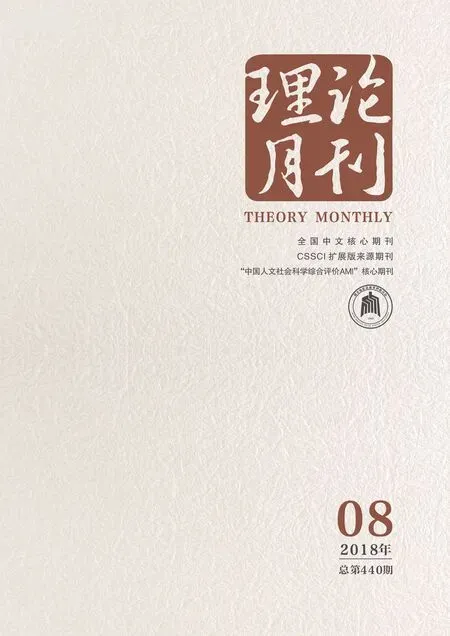从批判到同情: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演变
2018-02-11□黄伟
□黄 伟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最初反映在一系列宗教著作中,这其中就涉及犹太教。从1792到1797年,黑格尔在伯尔尼相继完成了《民众宗教和基督教》《耶稣传》《基督教的权威性》等三篇著作。虽然基督教才是其真正关注的对象,但鉴于基督教与犹太教、新约与旧约、耶稣与犹太人的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批判基督教黑格尔就必须研究犹太教。
伯尔尼时期的黑格尔还陶醉在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的理想中。启蒙运动宣扬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其主旨必然包含有对犹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的积极肯定和承认。也正是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影响,犹太人才发起了哈斯卡拉(Haskalah)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战欧洲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的解放事业,使法国犹太人和受拿破仑控制的部分中欧犹太人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权和平等权。但由于欧洲社会的反犹偏见根深蒂固,再加上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基督教会传统权威方面太过极端,犹太教、基督教被一起打入“蒙昧主义”的冷宫,故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摆脱不了传统的反犹偏见,其中以伏尔泰、狄德罗为典型[1](p146-147)。康德也对犹太人颇有微词,他认为:犹太民族受烦琐仪式的外在强制而无真正自由的道德,他们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缺乏天国和来世观念,故犹太教完全是一种政治组织而绝非宗教[2](p77,128,129)。启蒙思想家和康德有关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些消极认识自然影响了黑格尔,使其早期宗教著作沾染上了欧洲文化的反犹情绪。
一、早期的激进批判:从《民众宗教和基督教》到《基督教的权威性》
在《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一书中,通过犹太文化与希腊精神的对比,黑格尔认为,犹太人缺乏希腊人自由交谈的优美精神,只习惯于直接听从外在权威的教导和训斥,在反驳对手时也采用外在的粗暴方式,对话中毫无自由平等的优雅感。“自他们的先人以来,他们就已习惯于由他们的民族诗人以极粗糙的方式来指引自己,从他们有宗教集会以来,他们的耳朵就已习惯于道德说教,习惯于直接教训的口吻,听从他们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争吵,又习惯于一种粗暴的驳斥对手的方式。”[3](p34)这种对话方式反映了犹太人的民族性格,而这一民族性格又源自摩西时代。当摩西在西奈山颁布上帝律法时,他用的是权威性的命令语气,仿佛主人教训家仆一般。黑格尔还模糊意识到,犹太人的这一民族性格与其上帝观念有重要关联:“宗教中的这种幼稚智能把神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主人,这位主人和人间的统治者一样……因此人们可以献媚;在他面前,与(向他)献出的爱相比较,人们更多(感到的是)恐惧,最高的是敬畏。”[3](p39)这句话暗指犹太教,其上帝雅赫维(Jahweh,旧译为亚卫或耶和华)是绝对的威力、强有力的主人和统治者,有限者在他面前是卑微渺小和被否定的,故其主要的情感是敬畏和恐惧,爱则是次要的。上帝是威严的主,而主仆关系与“爱”中的自由平等关系是相对立的。因此,犹太人宗教意识中这种非自由的主仆关系,是与其缺乏自由交谈且习惯于权威教训的民族性格相适应的。
如果说《民众宗教和基督教》主要批判了犹太教的非自由性,那么,《耶稣传》所批判的则是犹太人的骄傲、狭隘和顽固不化。与《民众宗教和基督教》所表现出来的希腊主义理想不同,《耶稣传》展示了“康德情结”和道德理想主义。黑格尔用康德实践理性概念来重新阐释福音书中的耶稣生平,将耶稣改造为纯粹理性的道成肉身和道德理想的完美楷模。耶稣向犹太人播撒自由道德的种子,并用纯粹理性之光照亮他们蒙昧固执的心灵。黑格尔说道:“他通过以身作则和他的教训要把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和民族骄傲的狭隘精神从他们之中扫除,使他们充满他自己的精神,这个精神只着重把价值放在与一个特殊民族或权威的制度没有直接联系的道德上面。”[3](p82-83)但犹太人却“固执于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和缺乏对高尚事物的感受力”[3](p83),“骄傲于他们的姓氏、骄傲于他们的血统,把姓氏、血统看成一大优点”[3](p102)。他们以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的后裔这一血统而骄傲,以领受并遵行割礼、摩西律法而自豪,而这种骄傲和自豪正好就是他们心灵深处的民族偏见,这一偏见必然阻碍他们对纯粹理性之道德真理的认知,并使其丧失对纯粹道德这一高尚事物的感受力。在黑格尔看来,纯粹理性的感召并未使犹太民族觉醒,并未使他们意识到:只有普遍理性的纯粹道德才是绝对真理,“那打破一切限制的纯粹理性就是上帝本身”[3](p79)。所以,黑格尔经常批评犹太人太过“顽固执拗”,甚至耶稣的十二门徒都没能彻底摆脱这种犹太性格,他们依然从犹太眼光来看待耶稣所说的天国,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天国就是纯粹理性的道德王国,这特别反映在以下事件中:门徒争论“天国里谁为大”、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儿子求权柄和高位[3](p109,126,127)。
1796年,黑格尔写出了《基督教的权威性》,他专门却简短地探讨了犹太教和犹太人问题,并批判了犹太教权威性的非精神性和犹太人的奴性意识。前文已提到过康德对犹太教的批判,现在康德的这种批判性认识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黑格尔以康德的语气批评道:“他们的法令是直接从一个排外性的上帝那里派生出来的。他们的宗教主要地充满了无数的毫无意义的、一套一套的礼节仪文,这种学究式的带奴性的民族精神还为日常生活无关轻重的行为制定一套规则,使得整个民族看起来好像都在遵守僧侣式的清规戒律。注重道德、崇拜上帝是受一套死板公式支配的强迫性的生活。除了对这种奴隶式地服从非自己建立的法规之顽固的骄傲外,已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之可言。”[3](p166)犹太教充斥着大量外在性异己性的强制力量,这种力量的抽象否定性便导致犹太人无自由无真正道德的非精神性,以精神和自由为本质的人现在却丧失了他的本质性,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多么可悲的惨况啊!他几乎是带着愤怒之情来批评这种非精神性:犹太人“从事于繁琐习俗仪文之无灵魂、无本质的僧侣式的机械事物,过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生活”,他们的崇拜是“没有爱、没有灵魂的机械崇拜”,最终“陷入了精神奴役状态和不可救药地缺乏道德”[3](p166-167)。其实,就黑格尔的逻辑思路来看,他所强调的是:正是由于犹太人的这种非精神性、无自由、无主观内在性,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纯然外在性的、被外在强力所支配的奴性存在,以至于只剩下机械性的躯壳,外在强制性的权威宗教便由此而生。因此,犹太人的理性还不成熟,还不知道自身的自由,他们要想达到自由的道德是极为困难的。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黑格尔对犹太教的批评基本与康德一致,但两者仍有一重大差别:康德视犹太教为政治组织而绝非宗教;但黑格尔并未明确或隐晦地表达过“犹太教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之类的观点,也没有将其排除在基督教会的考察范围之外,反而在考察基督教的权威性之前首先专门考察犹太教,这种处理方式也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之中得到延续。
二、缓和了的总体批判:《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
1798—1799年黑格尔完成了《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一文,其中有关犹太教的篇幅已远远超过之前论述的总和,他对犹太教的精神与命运进行了相当具体和全面的考察。此时,历史的考察方法开始萌芽,“进入到事情本身”的科学风范也初现端倪,“历史—科学性”的具体批判或内在批判已初步形成。
其实,这种“历史—科学性”的考察方法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就已有了萌芽,不过它是只用来考察基督教的权威性。1800年黑格尔专为《基督教的权威性》撰写了部分修改稿,并对启蒙理性的人性概念有了相当深刻的反思[4](p48-56):“人性的一般概念已不复够用了;意志的自由也成了片面性的标准,因为人的礼俗和性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教是不取决于通过概念作出的规定的。在每一种文化形式里,必定有一种较高力量的意识,以及随之出现的一些超出知性和理性的观念。”[3](p157)而这种“较高力量的意识”和“超出知性和理性的观念”便是黑格尔后来所讲的民族精神,它既是主体也是实体,并从本质上规定了一个民族的宗教、哲学、艺术、政治、法制、历史、家庭伦理和民族性格之具体状况,故它远远高于启蒙理性的抽象人性概念。正是由于对民族精神概念有某种不自觉的洞见或直观,黑格尔才写了《基督教的权威性》的修改稿。
同样,也正是因为对民族精神概念有某种不自觉的洞察,黑格尔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才对犹太教进行了相当具体的总体性考察,并开始有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感。他从大洪水、挪亚献祭和“彩虹之约”、尼姆罗德①中译本《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将其音译为“尼姆罗德”(Nimrod),而圣经和合本对应的则是宁录,可参见英文圣经新国际版(NIV)第10章8—12节,中文圣经和合本《创世纪》第10章8—12节。建巴别塔等事件来阐明犹太精神征服敌对力量的最高统一性之两种形式(挪亚将最高统一设定在思想中,而尼姆罗德则将其设定在现实里),从亚拉伯罕的个性来探究犹太人精神及其命运的最初起源,从出埃及和西奈山立法来分析犹太人无道德无自由无财产所有权的精神奴性状况,从占领迦南、古以色列王国的兴衰成败、先知时代的呐喊和犹太教派的分裂来审视犹太民族的悲剧命运,黑格尔的考察几乎跨越了整个犹太古史。由于“历史—科学性”的考察必定具有某种超主观、超个体的客观普遍性,故它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消磨人的主观情绪。同理,上述“历史—科学性”的考察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黑格尔的主观情绪,使其对犹太教的激烈批判之情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黑格尔首次肯定犹太教还有某种人性的光辉。在讨论犹太节日时,他称赞了“三大快乐节”(逾越节、住棚节、七七节):“每年的三大节庆,大部分以举行宴会和舞蹈来表示庆祝,是摩西的宗教制度中最合乎人性的因素。”[3](p292)另外,在占领迦南时,绝大部分原住居民被杀,可仍有少部分的迦南人得以存活下来②这些存活下来的迦南人有基遍人、基述人和玛迦人等,可详见《旧约》书第9章26—27节、第13章13节。,黑格尔对此肯定道:“如下的情况在这里还是部分地补救了人性的光荣……它的原始的本质却还没有完全丧失,而它的被歪曲也还不是一贯的,不是完全贯彻到底的。以色列人毕竟让很多原来的居民依然活着。”[3](p293)在先前著作中,黑格尔完全不提犹太教的积极价值,也不对其做正面的肯定,仿佛犹太教只有缺点,但现在终于有所改变了,他开始正面评价犹太教,并对其中的人性光辉直接予以肯定。
其二,黑格尔初步意识到犹太上帝的统一性和无限性,并尝试用哲学概念来理解。比如,他称亚伯拉罕的神为“精神”,它是“无限的客体,是全部真理和一切关系的总和,严格讲来,也就是唯一的无限主体;这一无限客体只能叫做客体,只是就如下情况而言,即被赋予生命的人被假定且被称作有生命的绝对主体”[5](p191)。倘若唯独人才是主体或绝对主体,那犹太上帝这一无限客体便只能是客体而不能成为主体;但黑格尔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上帝也是精神(人格神),故无限客体又是无限主体。后面他还再次肯定犹太上帝就是无限主体:“这无限的主体必须是不可见的,因为一切可见之物都是受限制的。在设立圣幕以前,摩西仅向以色列人展示出火和云,这就使他们的眼目只忙于观看那不断改变形象的不定的戏剧,而不会固定在一个特定形象上。”[5](p191-192)故可知,在黑格尔看来,犹太上帝是一切的总和或统一,他既是无限客体又是无限主体,这就意味着,他便是超越一切有限性的绝对者。这种认识是对犹太教的某种正面肯定,已比较接近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主观统一、无限主体性等概念。而在1821、1824和1827年《宗教哲学讲演录》(以下皆依次简称为1821年讲演、1824年讲演和1827年讲演)中,正是凭借这一无限主体性及其统一性,精神才克服并超越了直接性、自然性、感性和有限性,东方各自然宗教才过渡到崇高的宗教(犹太教)。
当然,从总体上看,《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仍对犹太人、犹太教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而且这种批判比以前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批判的具体性以对亚伯拉罕和犹太命运的精神分析为代表①有关黑格尔对亚伯拉罕和犹太命运的精神分析,可详见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依次为第281—286、298—302页。,而批判的全面性则表现在,它涉及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亚伯拉罕的个性、出埃及时的道德败坏、西奈山立法的非自由性、国家政治和法制的非自由性、无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民族历史的悲剧命运等诸多方面。黑格尔批判的语调还夹杂有明显的欧洲反犹情绪,比如:亚伯拉罕“简直把整个世界看成他的对立物”,其后代在力量强大时便会“毫无顾忌地以最暴虐、最强烈、最灭绝人性的暴政统治一切”[3](p285,286);出埃及事件中,以色列人“只有懦夫式的幸灾乐祸心理……用欺骗去借贷,并且用盗窃去回答信赖。这是无足怪的,这个在它的解放里最具有奴性的民族……在这个民族的解放里是怎样没有灵魂和要求自由的内在需要的”[3](p288-289);犹太人“没有生命、没有权利、没有爱……这样的普遍敌对性所剩下的只能是对物质的依赖和一种动物的存在”,他们所崇拜的东西就是“对于具有丰富的蜂蜜和牛奶的土地的占有、以及充分有保证的事物、饮料和两性生活”,这种崇拜就是“奴性的表现”“动物式的生存”[3](p289-290);犹太人的独立状态是一种“极其丑恶的状态”[3](p299),分裂后的犹太民族则“以前此用来反对异族的同样暴烈的无爱和无神的精神来反对他们自己的脏腑”[3](p300),他们的悲惨命运“并不是希腊的悲剧……不能唤起人的恐惧和怜悯……犹太民族的悲剧只能唤起憎恶”[3](p302)。
因此,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对犹太教主要持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是总体性的,且带有欧洲反犹情绪的消极影响。不过其批判的激进情绪毕竟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缓和。
三、重大转变的开始:1821讲演
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重大转变出现在1821年讲演,这时他的哲学体系已经成熟,宗教哲学思想也基本成型,宗教考察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展。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第七章“宗教”部分,犹太教没得到任何考察,与这种漠视态度相反,他在1821年讲演中首次将犹太教正式纳入宗教哲学体系,并将其规定为壮美的宗教或崇高的宗教。整个1821年讲演由三大部分组成:宗教概念、特定的宗教(有限的宗教)、完善的或天启的宗教(基督教)。特定宗教又被划分为A.直接的宗教(东方各自然宗教)、B.壮美与优美的宗教(犹太教、希腊宗教)、C.合目的性的宗教(罗马宗教)等三大环节。与东方各自然宗教相比,犹太教、希腊宗教共同凸显了精神的极大进展。黑格尔讲道:“各个已能了解和尊重客观实体的民族,因而进入了观念性范围,进入了灵魂王国,踏上了神灵世界的领地;(这些民族已经)把感性直观的桎梏,把漫不经心的谬误的桎梏从额头上扯下来,把握和创造了思想和理智领域,并在内心获得了牢固的基础。”[6](p128)
东方宗教之所以是自然宗教,主要是因为其精神仍沉浸在感性、自然性和直接性的束缚中,没能在自身内克服或超越这些直接性、自然性,从而将直接的自然物或有限物视为神,这就是偶像崇拜。黑格尔对此极为不满:“而这种规定性在这里是存在于直接的直观中;埃及的阿匹斯,印度的大象,尤其是猴子和母牛——这头公牛、这只猫、猴子,不是作为象征,而是具有其现实性。人、达赖喇嘛、印度国王、婆罗门总归都被扩大为神。”[6](p116)这类宗教“是最愚昧、最野蛮、最低级的宗教;膜拜一种动物对我们来说必定是可鄙的,同样,崇拜这样一位当下存在的人也是最可耻的”[6](p116)。其反感厌恶之情几乎达到极致,甚至直接称其为“卑鄙无耻”“最堕落的宗教”[6](p117)。
与上述态度截然不同,黑格尔现在明确认识到犹太教的重要性及其精神意义,其批判也变得相当温和或隐晦。精神在经历了东方自然宗教的各种“堕落形态”之后,终于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桎梏”并由此进入“思想和理智”的自由领域,在宗教史上,是犹太一神教首先达到这一自由领域。而精神的这种进展便催生了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肯定认识和同情态度。
黑格尔称犹太上帝为“本质……与自身的主观统一,独一无二者”[6](p131),这就是“唯一者”、无限的主观统一。他还强调,“认识上帝的统一具有无限的重要性”,“意识进入了理智世界的领域和地盘”[6](p131),犹太上帝是“思想的上帝”,其宗教是“思想的宗教”[6](p142,136)。他虽未有进一步的说明,但后面三次宗教哲学讲座却是以此为基础并进一步做出阐释。例如在1827年讲演中,正是由于上帝的统一性有了具体规定,其重要性也得到强调,希腊宗教的缺陷和有限性才被凸显,犹太教的逻辑次序便被提升到希腊宗教之上[7](p357-359)。
犹太上帝的这种主观统一不是抽象普遍的“太一”,不是“无尺度的东西、软弱无力的东西”,而是“在自身内经过映现的无限东西”[6](p131-132),亦即是“己内反思”的无限主体和绝对力量,这绝对的力量也就是“神圣威力”,它包含有创造、保存和消灭三个环节。创造、保存反映了万物与神圣威力之间的肯定关系,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宇宙万物并赋予其实存,这就是上帝的良善;而消灭则反映了两者间的否定关系,作为有限物、特殊物,万物都没有独立自存的本质性和永恒性,它们通过自身的消逝、灭亡从反面凸显了上帝的无限超越性和崇高性,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在黑格尔看来,由于犹太教还缺乏自由精神,故神圣威力也有一些缺陷,如它“不是向自身的回归运动;不是精神”,“在根本上是与整个自然对立的”,“抽象的神圣威力”是“纯粹的威力”,约伯的信心只是“建立在威力之上的”,他“对主的敬畏只是起到绝对服从的作用”[6](p140-141)等。但这些批判主要是理解式的内在批判,其语调也相当温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肯定和强调犹太上帝的无限超越性,而不是为了否定而批判。况且,其言辞基本摆脱了欧洲反犹情绪的不良影响,早期那些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辞也不再出现。比如,黑格尔现在用“主仆关系”“敬奉”“畏惧”“仆人意识”等术语来批评犹太教精神的非自由,而根本不采用“奴性”“奴隶”(the slavelike orslavish)、“动物式的生存”(animal existence)等早期宗教著作中极具蔑视性的词汇①详见:黑格尔著《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290、294、299、300页。Hegel,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trans.by T.M.Knox and Richard Krone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5,pp.190,191,195,200。。
在崇拜方面,有限自我意识虽与神圣威力有某种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只是自我意识以神圣威力这一绝对者作为自己的来源、本质和信靠,是主仆关系的抽象同一。有限意识在神圣威力中还反思不到自身的自由和独立性,还缺乏神圣化的精神提升或中介,故神圣威力的抽象否定性就对自我意识保留着某种陌生性、异己性和彼岸性。于是,犹太人“对主的畏惧”便由此而生。黑格尔对这种畏惧意识有相当具体的演绎和描述,还分析了与此相关的其他规定,如犹太教严格排他的民族性、缺乏灵魂不朽和永恒天国的观念、无土地的真正所有权、惩罚的外在性等。但这种略带批判性的认识并不是为了纯粹否定,而是从更高真理的立场来分析此畏惧意识的某种缺陷,且占据主导的是内在的同情式的理解。这种理解表现在,黑格尔积极肯定了这种畏惧意识的合理地位:“对于主的畏惧是这样一种绝对的宗教义务:把我视为子虚乌有,认识到我只是完全依附的——对主的仆人意识;正是这种畏惧在我的重建中赋予我绝对正当的理由。”[6](p153-154)黑格尔还意识到,这种畏惧意识乃是真理和智慧的开端,是精神一神教的根本基础:“对主的畏惧是这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上帝仅仅以唯一者的抽象规定加以领会,人的这种真实的不自由是基础”[6](p154)。不过,他并未对这一“绝对的宗教义务”或“基础”做出具体说明,直到1824、1827年讲演才正面阐释了它们的精神内涵及合理地位,这就是:对主的畏惧,不是对任何感性物、自然物和有限物的恐惧,而是对超越性的绝对者之恐惧,故反而使自我意识有某种抽象的自由,即从对各种感性物、自然物和有限物的恐惧中抽象出来、解放出来。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真实的不自由”之隐义。
由此可知,在1821年讲演中,黑格尔已明确意识到犹太教的精神内涵和合理地位以及与东方自然宗教的重大差异,他虽对犹太教有一些批判,但却是理解式的内在批判,绝非早期的激进批判态度,也基本摆脱了欧洲反犹情绪的消极影响,其批判的语调也变得相当温和与隐晦。于是,黑格尔犹太教观念便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早期激进的批判态度转变为成熟期理解式的同情态度。
四、走向同情的高峰:1824、1827年讲演
虽然黑格尔1821年讲演对犹太教的态度是以同情为主,但主观统一性还未得到具体规定,神圣威力和畏惧意识才是核心概念,而这两个概念都隐含着某种消极的指向:即上帝的抽象否定性、自我意识的非自由,故其理解模式仍有早期著作的某种印记。正如彼得·霍奇森所言:在1821年讲演中,“即使新的范畴和主题已经出现,但黑格尔对犹太教的描述仍与《早期神学著作》和《精神现象学》的解释方式相一致”[8](p44-45)。在1824年讲演中,黑格尔首次引入了“精神个体性”“自由主体性”等概念,并将犹太教、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依次设定为其中的三个环节,自由主体性则成为统摄这三个环节的核心概念,主体性及其主观统一性也得到强调和具体阐释[9](p382-383)。而犹太教上帝概念的主体性形式就是智慧和目的,上帝既是智慧也是目的[9](p423-425)。
上帝是智慧,这首先体现在创造中。黑格尔首次将创造概念与宇宙起源、产生或人类生产等概念做出明确区分,认为真正的创造概念是犹太教最先达到的。它是无限主体在自身内的永恒直观活动,是无中生有的绝对创造,上帝是最初的起点和唯一者,没有任何他者能独立自存或与其并列[9](p426-428)。因此,一切事物都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本质性,而只是被上帝所设定的有限者,是被规定的否定者。于是,有限物自身就被剥夺掉了神圣性或独立自存性,对有限的自然者精神者的崇拜或神化便丧失了合法性,这就是无诗意的理智或散文化[9](p430)。进而,有限物或自然物虽然为上帝所创造且成为上帝自身的显现形式,但这种显现还是抽象的,即“上帝是作为在它们之上的力量而显示自身在它们中”,这力量是有某种抽象否定性的绝对力量,它使这些有限物或自然物同时成为与独一上帝既不相配也不相称的被否定者,这就是崇高的宗教。由此,黑格尔便第一次正面阐释了崇高的概念:“崇高就是这种理念,它表现或显示自身,但却是以这种方式,即在显现于现实形态之时它同时也展示自身为崇高,并提升到现象和现实形态之上,以至于现实形态就被设定为否定,这显现的理念便被提升到它所显现的形态之上,故它的显现就是一种不合适的表达。”[9](p432)
作为自由主体性的上帝,他还是目的:一方面,这目的是理论的或普遍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需要得到所有人的承认、称赞和崇敬;另一方面,这目的又是实践的或特殊的,它被限制在一个家族(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一个民族,上帝主要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只与以色列立约并率领他们出埃及、占领迦南地、建立大卫国等。黑格尔认为,这就是犹太教上帝理念所面临的“惊人的反差”和“无限的困境”[9](p436)。
主体性、智慧和目的是1824年讲演的新范畴和新的认知模式,它们明显比1821年讲演的核心概念“神圣威力”要更具正面性、积极性和肯定性,这表明1824年讲演对犹太教有了更多肯定性的理解。
此外,在崇拜方面,1824年讲演仍以1821年“对主的畏惧”为基础,却弥补了1821年讲演对畏惧意识的肯定性合理性认识不足的重大缺陷。黑格尔现在已明确意识到:对主的畏惧,是对“不可见的绝对力量”之畏惧,而不是畏惧任何属世的有限物、特殊物或感性物,故人的力量和特殊兴趣、所有短暂易逝的和偶然性的东西现都被放弃了,意识在这种“绝对否定性”中便提升至“纯粹思想的高度”。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得释放的自由感,即从所有特殊兴趣、特殊事物及其有限性中抽身而出,并摆脱了对它们的依赖性,这就是“智慧的开端”,是“自由的一个本质方面”[9](p442-444)。正是以这种畏惧意识为真理或智慧的基础,犹太人才产生出“绝对的相信”和“无限的信仰”[9](p444)。而这种信仰“是通过许多伟大的胜利才得以保存,这也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它就是相信、亚伯拉罕的信仰,那使这一族群的历史得以延续的信心”[9](p446)。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亚伯拉罕被批判为异化精神的代表,是“与自然世界相敌对”的消极例子,但现在却成为犹太教、基督教的“信心榜样”。这一翻转性的认识表明,黑格尔对犹太教的同情感已急剧增强,逼近高峰。
而在1827年讲演中,黑格尔的这种同情感才真正达到高峰。其首要标志是:他改变了犹太教、希腊宗教之间的逻辑次序,将犹太教置于希腊宗教之后,使其逻辑次序略高于后者。
黑格尔这时将犹太教和希腊宗教统归为“特定宗教”的第二大环节,并称其为“精神提升到自然之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宗教”。此标题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黑格尔强调的重点在于:精神与自然之间的思辨关系。在东方自然宗教中,精神性的东西与自然性的东西还混杂在一起,精神没有能力将自然性的东西吸收并克服在自身内,而是沉浸在自然的直接性、感性和有限性中并受其限制,故精神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主体性。但精神的概念和本质正是自由,这一自由本质内在地支配并推动着宗教哲学的进展,精神必定要自我提升到自然之上,并在自身的主观性中克服或超越自然性。精神自我提升的两种方式便是希腊宗教和犹太教。在这两大宗教中,直接自然性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都“在主观统一的理想性中被理解……并返回到主观统一之中”[7](p328-329)。这种主观的统一也即是自由的主体性或纯粹的主体性。
就希腊宗教而言,自由的主体性就是希腊诸神,他们显现在有限的感性者和自然者中,而这些感性者自然者是非本质的和不能独存的,它们仅仅是精神的外观或标志,是被设定者;虽然被自由主体性所吸收并改变形态,但它们仍保持着感性、自然性的外观,其外在性和感性虽被精神所中介但并未得到纯化[7](p330)。所以,希腊宗教的自由主体性还是有限的主体性。就犹太教而言,其自由的主体性就是独一上帝耶和华,他是无限的主体和绝对的力量,并显现在有限的感性者和自然者中,但这些有限形态同时也与他既不相配也不相称,它们没有被无限主体所吸收并改变形态,而只是抽象的被否定者[7](p365-366);这一无限主体“被提升至思想的纯粹性中”,他便超越了一切感性、自然性、外在性和有限性[7](p330,357-359)。因此,若从无限高于有限、精神高于自然的视野来看,犹太教确实比希腊宗教更高,1827讲演所强调和突出的正是这个;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黑格尔宗教哲学中,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关于上帝理念的统一性、无限性和超越性之认识就是最高的了。故黑格尔常以欣赏和称赞的口吻来描述犹太教,并认为:只是在无限主体性中,真正具体的同一性才被发现[7](p364);只是在崇高宗教中,“有限者第一次被精神所统治,精神自我提升以至于它被提升到自然性和有限性之上,而不再被外在性所折磨和玷污”[7](p330);犹太教无限的主体性,就是纯粹主体性,“它是精神性的主观统一,对我们而言,这便是第一次与上帝之名相配的规定”[7](p357);犹太上帝的良善就是无中生有的自由创造,“只有在这里,上帝才在无限主体性的真实意义上成为造物主”[7](p363)。
此外,1827年讲演对犹太教的同情态度达到高峰的另一大表现就是:犹太教伦理规定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了充分认识和正面强调,而这既是早期宗教著作所完全没有的,也是1821、1824年讲演所忽视的。在1827年讲演中,上帝智慧的第四个规定是“上帝的目的”,此目的既包括理论上的普遍目的,也包括实践上的伦理目的,而伦理目的才是黑格尔分析和强调的重点。在他看来,上帝所颁布的伦理规定是普遍意志,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当遵循上帝意志、与上帝同行并荣耀上帝之名时,人是自由的并摆脱了自私自利,其内在意志的价值也得以实现[7](p367-368)。这时,黑格尔对犹太教伦理规定基本持正面的理解和肯定的评价。此外,“内在的”一词还被多次使用,以此来强调伦理意志的内在性,他后面甚至还将这一内在性推向高峰,并以最大的同情心来称赞犹太教伦理规定的这种内在性和精神性:“我们在这里仍需注意精神的这种内在化,它在自身的运动。一个人应该行事正当;那是绝对的命令,这正当行为在人自身的意志中有其地位。结果,人被指向他内在的存在,被他自己内在性的考虑所占据,它是否正当,其意志是否良善。对这正当性的内在反省,当其非正当时的忧伤,灵魂对上帝的呼求,沉浸到精神的深处,渴望精神趋向正当、趋向与上帝意志相一致,这都是特别的特征,此特征在诗篇和先知书中占主导地位。”[7](p370)这种对内在性、精神性和某种自由性的认识与强调,与早期宗教著作的态度截然相反,那时黑格尔只知道猛烈批判犹太伦理、律法的外在性、非自由性和非精神性。
黑格尔还意识到,犹太伦理规定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个人的自然实存状况(幸福)与正当意志之间的客观联系,而客观联系便是:顺服上帝的律法,便得到祝福;悖逆上帝的律法,便遭受咒诅。不过,这种必然性不同于希腊人的必然性。希腊必然性是“盲目的、空洞的、未规定的和无概念的必然性”[7](p368),它对希腊人是神秘的、抽象的;但犹太教伦理规定的这种必然性却是具体规定了的,它为无限主体性的上帝所设定,并呈现在有限自我意识中。故犹太教的必然性概念要比希腊宗教的盲目必然性更具体、更确切、更有积极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对这种具体必然性的明确意识是犹太教的重要特征,它最典型地体现在约伯身上。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义人,但却遭受了巨大的灾祸和痛苦,故其自然实存状况与正当意志不相符,也与上帝的必然性规则不一致。约伯对此极为不解,满是抱怨和质疑,但这正好从反面体现出:那一具体必然性的客观联系对他而言是清楚明确的,他对此充满确信。最后,上帝在旋风中向他显现,其不满和沮丧才得以消除并臣服于那绝对的、纯粹的信心。黑格尔对约伯故事的分析与处理,不再像1821年讲演那样去突出上帝神圣威力的抽象性,而是转而强调他对具体必然性的确信和对上帝的绝对信靠,他最后的顺服也被肯定为:“对上帝的力量和上帝的真理正义相和谐统一的意识”,“这种对上帝的信靠不是别的,而只是对力量与智慧的和谐统一之意识”[7](p370)。
由此可知,在1827年讲演中,犹太教的逻辑次序被提升到希腊宗教之上,犹太教伦理规定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了充分认识和正面强调,伦理规定的内在性、精神性和具体必然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积极肯定,对约伯的分析完全改变了1821年讲演的消极模式而只有正面的评价,这表明黑格尔对犹太教的同情态度此时已达到了最高峰。
五、结论
综上所述,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从批判到同情的复杂演变过程。在早期《民众宗教和基督教》《耶稣传》《基督教的权威性》和《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等著作中,他对犹太教的非自由性、非精神性和权威性,对犹太人骄傲、狭隘、顽固不化及其奴性意识,都进行了猛烈的激进批判;而《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却展现了某些新特征,其批判是有了某种“历史—科学性”的内在批判和总体性批判,批判时的激进情绪也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缓和;只是在1821年讲演中,他才对犹太教有了更多肯定性的认识,并基本摆脱了欧洲反犹情绪的消极影响,其批判的语调也变得相当温和与隐晦,其态度主要是理解式的同情。于是,黑格尔犹太教观念便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早期激进的批判态度转变为成熟期理解式的同情态度;而1824年讲演首次运用了主体性、智慧和目的等概念的理解模式,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对犹太教的同情感,并在对亚伯拉罕的翻转性认识中逼近同情的高峰;最终,1827年讲演才真正达到了这一同情态度的最高峰。
当然,即使在1827年讲演,黑格尔仍明确提到了犹太教的诸多缺陷,比如:上帝概念与上帝智慧无内在发展的抽象性、上帝目的受犹太民族性的限制、神圣命令或律法的外在被给予性及其抽象性、政治领域上的外在性抽象性、无个体的真正所有权等,只是讨论不多、不具体罢了。事实上,在黑格尔心中,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符合宗教概念及其理想的宗教形态,才是宗教哲学的最高真理。这可能是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最大前设或“偏见”。除此之外,在1827年讲演中,黑格尔对犹太教的同情态度确实达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高峰。
而之后的1831年讲演,由于黑格尔对自由原则、埃及学和灵魂不死观念的更多重视,以及对精神辩证进展的中介原则和对立环节之强调,他便突出了犹太教在自我意识方面不自由的这一缺陷,并将其逻辑环节降低到波斯宗教和叙利亚宗教之间,成为“善的宗教”之第二环节。于是,黑格尔对犹太教的批判态度仿佛又回升了①有关黑格尔1831年讲演犹太教观念的一些变化及其原因,可详见Peter C.Hodgson,“The Metamorphosis of Judaism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Religion”,The Owl of Minerva,Vol.19,No.1(Fall,1987):pp.49-51.Amy Newman,“The Death of Judaism in German Protestant Thought from Luther to Hegel”,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Vol.61,No.3(Autumn,1993):pp.476-479.。但因为1831年讲演的完整内容已不可能再次重建,现有的唯一资源(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49页摘录)又太过单薄且记录极不完整②关于黑格尔1831年讲演的原始资料情况,可详见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One Volume Edition:The Lectures of 1827,ed.by Peter C.Hodgson,trans.by R.F.Brown,P.C.Hodgson,and J.M.Stewa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S.Harri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Editorial introduction,pp.5,8。,故黑格尔1831年对犹太教的具体态度还较为模糊,恕笔者在此不能详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