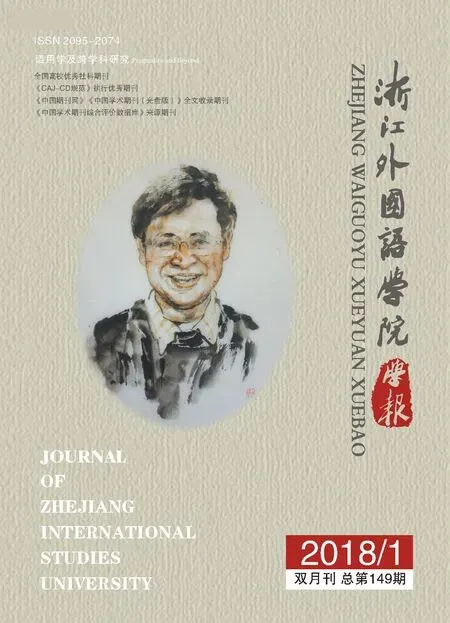论《驱魔》对奥尼尔晚期戏剧的影响
2018-02-11张烨颖康建兵
张烨颖,康建兵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重庆 400031;2.重庆工商大学 艺术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驱魔》(Exorcism)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在 1919 年创作的一部短剧。奥尼尔写完这部剧后,没有将其发表,而是把它交给普罗文斯顿剧社排演,于1920年3月26日晚在格林威治村剧作家剧院首演。两周后,奥尼尔突然宣布取消演出,并召回剧本的复印本等资料,将它们全部销毁。自此,《驱魔》成为失传剧作。2011年这部剧的一个复印本被偶然发现,在美国引起轰动。大家普遍认为此剧具有高度的自传性,对于补全奥尼尔的传记书写具有重要价值,但戏剧界对于它在艺术方面的表现评价不高,毕竟这是奥尼尔早期的青涩之作。然而,若我们把《驱魔》置于奥尼尔一生的戏剧创作中予以审视,可以发现这部早期短剧跟他的晚期剧作如《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送冰的人来了》①《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送冰的人来了》后文分别简写为《进入》《送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换句话说,奥尼尔早期销毁的《驱魔》与曾被他要封禁25年的《进入》之间,以及《驱魔》与他最重要的、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送冰》之间,在题材、主题、人物乃至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奇妙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谈《驱魔》,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这部失而复得的早期作品,也可以为重读奥尼尔晚期戏剧提供新的角度。
《驱魔》的发现颇具偶然性。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和原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一直致力于奥尼尔文献的收藏,该馆在2011年新购入的美国电影编剧Philip Yordan的一批文稿中,意外发现了一份《驱魔》剧本的复印件。要知道,当年接触过这个复印本的人,包括奥尼尔和Philip Yordan等人,早已去世多年。作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尼尔的失传剧作失而复得,必然成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先是《纽约客》抢先在2011年10月17日发表此剧,然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2月将其出版。随之,此剧成为美国戏剧界关注的焦点。2012年5月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文学会年会和奥尼尔学会年度理事会上,专门举行了《驱魔》专场讨论会。不少剧团纷纷举办剧本朗读会,纽约外百老汇的马维尔剧院、新泽西州的南卡姆登剧院等陆续把《驱魔》搬上舞台,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还在2012年春拍摄了同名电影。围绕《驱魔》的活动不断涌现。
迄今为止,美国对《驱魔》的研究主要有:一是对这部剧的创作、失传和重现等进行详细考证和梳理。在奥尼尔的全部剧作中,《驱魔》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它得以被创作完成,却未被发表或出版,但又被搬上过舞台,旋即又被销毁,充满曲折性和戏剧性。即便《驱魔》被演出过,但当时普罗文斯顿剧社也只是在小剧场短暂演出。据此可推测看过此剧的人并不多,接触过剧本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当时评论界几乎未关注此剧,再加之它从失传到重现达92年之久,要勾勒出《驱魔》的创作情形,难度不小。尽管如此,相关学者也作了努力。比如,奥尼尔学会副主席Jeff Kennedy在2012年奥尼尔学会年度理事会议上便作了题为Exorcism:The Context,the Critics,the Creation,and Rediscovery的发言,他回顾了此剧在当年的排演情形、当年奥尼尔与普罗文斯顿剧社的关系,以及当时评论界的反应(Kennedy 2013)。二是分析其传记价值。众所周知,奥尼尔戏剧从早期的大海主题剧到晚期的《送冰》《进入》和《月照不幸人》等名剧,均带有强烈的自传性。《驱魔》作为奥尼尔描写自己早年自杀事件及其当时个人感情和家庭生活等隐秘事迹的剧作,其在自传性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驱魔》的重现,不仅能够为传记学家直接补全奥尼尔1912年自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有助于理清奥尼尔的第一段婚姻纠葛,有利于廓清奥尼尔青年时期与家庭的关系、与底层的友谊等,而这些又都是奥尼尔毕生创作的重要题材和主题,并深刻地体现在他的经典作品如《进入》和《送冰》等剧中。因此,仅就传记价值层面而言,《驱魔》失而复得,弥补了奥尼尔传记方面的一个空白,也在汗牛充栋的奥尼尔研究中开辟了重读奥尼尔戏剧的新视角。作为奥尼尔传记写作者的重要代表,Arthur Gelb&Barbara夫妇在他们合著出版的第三本奥尼尔传记中,从《驱魔》的自传性及其史料辨析切入,补入了奥尼尔早年自杀一事及其前后的生活经历。三是对此剧作文本细读,对主题和人物等进行分析。尽管我们认为《驱魔》只是奥尼尔青年时期的一部青涩之作,自传性胜过艺术性,艺术成就不高,但它毕竟源于奥尼尔对死亡经历的真实体验,而且其涉及的婚姻纠葛、父子冲突等,又是奥尼尔后来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再加之奥尼尔在剧中对人物塑造和内心活动着墨较多,对反讽、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这些手法同样为奥尼尔后来的创作所青睐。就此而言,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艺术层面而言,《驱魔》这部青涩之作都可谓奥尼尔中后期创作的雏形。因此,尽管我们大体认为此剧艺术成就不高,但仍值得认真探讨。一些学者也在此方面作了探索。例如,奥尼尔学会主席Kurt Eisen(2013)指出,奥尼尔把妻子和母亲糅合为内德的妻子这一形象,表明他的某种愿望满足或是逃避,这也是他的某种妥协,是当时他对婚姻的真实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家为《驱魔》的重现兴奋不已,但也有人认为过度的热情和溢美之词会导致对其价值作无限拔高。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认为,此剧“在他作为戏剧家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一部很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剧作”(O’Neill 2012:IX)。
我们认为,对《驱魔》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传记价值方面的探讨,也不能脱离此剧的时代背景及在当下的重现意义,而仅就剧作本身作文本解读,而是应将其置于奥尼尔的整体创作关系中进行分析。这也是此剧的独特性使然,因为《驱魔》不像奥尼尔早期独幕剧如《渴》(1913)和《雾》(1914)等剧,这些短剧可以被单独作文本解读。《驱魔》与青年奥尼尔的人生经历、当时的情感生活以及精神状态等密切相关,更在很多方面开创了他后来颇为重视的一些主题和意象,因而有必要打通此剧与其他剧作特别是晚期戏剧的互文性关联。
二、题材续写:从场景、情节到人物
较之当下美国戏剧界对《驱魔》的关注热度,奥尼尔本人无论在1919年写作此剧时,还是在后来终其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中,都对这部剧所讲述的自杀事件几乎只字不提。他唯一在创作中涉及此剧的只言片语是在《进入》一剧中,而此时距《驱魔》写作已有20余年。我们知道,《进入》同样是一部具有高度自传性的作品,剧中的埃德蒙是奥尼尔的化身。在此剧第四幕,埃德蒙对父亲蒂龙提起他年轻时自杀一事——“几乎真的自杀的那一次”,立刻被蒂龙打断。蒂龙训斥道:“只要是我的儿子就永远不会——”,“我们家里人永远没有人——”(尤金·奥尼尔2006a:432)。蒂龙恪守天主教教规,反感任何有关死亡的话题。虽然蒂龙对埃德蒙自杀一事刻意回避,但这个话题对于奥尼尔研究来说却很重要。多年来,奥尼尔传记家努力寻觅埃德蒙即奥尼尔自杀一事的蛛丝马迹,希望以此更深入地解读其剧中广泛存在的死亡主题。但奥尼尔在《进入》中一笔带过,使得奥尼尔研究者对此事无从可知,由此也造成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如今,失传的《驱魔》失而复得,为解开奥尼尔当年的自杀之谜提供了唯一而直接的线索。
《驱魔》的故事发生在1912年3月中旬的某天。24岁的主人公内德·马洛伊是奥尼尔的化身,他住在纽约市中心滨海附近的一家普通的小酒店。此时内德正在跟妻子闹离婚,跟父亲的关系也不愉快,事业方面也是一事无成。总之,他感到一败涂地,焦头烂额。在迷惘和冲动中,内德吞食安眠药自杀,所幸被室友吉米发现,经抢救捡回一命。他的父亲爱德华·马洛伊前来看望内德,并承诺要送他去疗养院治病,父子关系得到和解,内德的妻子也答应离婚,这一切令内德感到获得新生。全剧在内德的朋友们欢庆他“重生”的歌声中落幕。
与其说《驱魔》是一部艺术之作,不如说它是青年奥尼尔的戏剧体自传,它详细记述了奥尼尔当年与妻子Kathleen Jenkins的婚姻纠葛,以及他跟父亲James O’Neill的矛盾。奥尼尔写完这部剧后,没有将它发表,而是把它交给普罗文斯顿剧社排演,首演后随即宣布取消演出,并销毁了此剧。有关这部短剧的研究,仅见《纽约时报》剧评家Alexander Woollcott的一篇短评(1961:142-143)。1922年,奥尼尔在一封信中提到:“《驱魔》已经被毁掉了……,越早忘记这部剧的所有记忆越好。”(qtd.in Sheaffer 1973:12)从此,大家都相信《驱魔》已被奥尼尔彻底销毁,谁也不会料到多年后它会被人从故纸堆中翻出来。
阿尔比虽然直言《驱魔》在奥尼尔作为戏剧家的历程中并不是一部重要的里程碑式剧作,但也承认,鉴于奥尼尔在《送冰》和《进入》中最敏锐地剖析过“他的心魔”,使得《驱魔》“作为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值得被认真审视(O’Neill 2012:VIII)。的确,《驱魔》在很多方面对奥尼尔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剧中的场景、人物、主题等在后来的剧中不断被重现和续写。拜内克珍本和原稿图书馆馆长Louise Bernard特别强调《进入》中的《驱魔》印迹,认为《进入》是对《驱魔》的续写。阿尔比则把《驱魔》看作《送冰》的一幕,认为《送冰》对《驱魔》作了容量扩充和主题深化(O’Neill 2012:X)。
《驱魔》《送冰》和《进入》都是写1912年的故事。奥尼尔晚年意识到每况愈下的身体难以支撑他完成大型组剧《一个自我放弃占有的占有者们的故事》,便果断放弃这个浩大工程,转而写三部自传体戏剧:《送冰》《进入》和《月照不幸人》。他在1946年10月6日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道:“我认为写现在是写不出什么有价值和有理解深度的作品的。只有当现在的生活成了较远的过去,你才有可能描写它。”(2006b:308)其中,《驱魔》的剧情时间是1912年3月中旬的某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地点是内德和吉米合住的酒店小房间;《送冰》发生在1912年夏天的两天时间,地点是哈里·霍普酒店的里屋和酒吧间的一部分;《进入》发生在1912年8月某天上午八点到当天午夜,地点是蒂龙一家避暑别墅的起居室。奥尼尔在三部剧的有限时空中展现了难以忘却的往事。
《驱魔》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市中心滨海附近小街的一个小酒店内,这个小酒店是后来不断出现在奥尼尔戏剧中的吉米牧师酒店(Jimmy the Priest’s)的雏形,该酒店也是《送冰》的故事发生地。1911到1912年间,奥尼尔住在这个被内德称作“垃圾堆”和“老鼠洞”的地方。《送冰》中的哈里·霍普酒店则是吉米牧师酒店、格林威治村地狱洞酒吧和麦迪逊广场花园对面的花园旅馆酒吧的综合。《驱魔》中,内德的室友有吉米和马乔·安德鲁斯,两人的原型分别是吉米牧师酒店的常客詹姆斯·拜斯和亚当斯少校。《送冰》中,詹姆斯·拜斯由《驱魔》中的吉米变为詹姆斯·卡梅伦,绰号是吉米·托莫罗。《驱魔》中,吉米喝醉后喜欢向人们讲述他那些子虚乌有的悲伤往事,他说他之所以染上酗酒恶习,原因是他要以此报复他通奸的妻子。《送冰》中,希基揭穿了吉米这个老掉牙的借口,即吉米在年轻时就觉得头脑清醒的生活叫人害怕,他在编造妻子通奸这个谎言之前就是个酒鬼。《驱魔》中,吉米救了内德一命,现实中拜斯确实是奥尼尔的救命恩人,但他后来也像《送冰》中的帕里特一样跳楼自杀。为此,奥尼尔在1917写了短篇小说《明天》(Tomorrow)来怀念他。值得一提的是,奥尼尔最初给《送冰》取的一个剧名便是《明天》。再看《驱魔》中的马乔·安德鲁斯,每当他醉酒后,便会挽起裤腿向人展示他腿上的伤疤,那是在祖鲁战争中被敌人用刺刀挑的。《送冰》中,马乔变为绰号“上尉”的塞西尔·刘易斯,每当刘易斯酩酊大醉时,他也会掀起衣服炫耀背上的伤疤,那是他在布尔战争中被布尔人用长矛刺伤的。《驱魔》中还有一些没有直接出场的人物,如被内德找来和他假装通奸的妓女,而《送冰》中也有珀尔、玛吉和科拉三个妓女出场。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内德的父亲,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奥尼尔父亲James O’Neill的浓厚影子,他在《进入》中得到了最集中和最形象的刻画。
《驱魔》中,内德对吉米说他想要去作一次“长途旅行”(long trip),这个长途旅行暗指寻死,《进入》的剧名Long Day’s Journey是对long trip的化用。《驱魔》是“捉鬼”,是驱除心魔,《进入》则是慰藉游魂。《驱魔》中,内德自杀未遂,父亲前来探望,表示愿意跟儿子和解,要把他送到疗养院去,一个精心挑选的隐密之地——“仅有很少的病人获准入住”,内德假装接受父亲的好意。真实情况是,据一些奥尼尔传记记载,当年奥尼尔确实回到新伦敦海滨佩夸特街325号的家里短住,但同家人一起生活让他感到别扭甚至痛苦,每个家庭成员身上都有着某种缺陷,都对现状不满,都在交织着怨恨和宽恕的复杂感情中郁郁寡欢。《进入》在蒂龙家的起居室接着《驱魔》讲诉家庭恩怨。《驱魔》中,内德对人生的思考在《进入》中被转化为埃德蒙的有关死亡和人生的大段独白。内德一开始表示绝不回到“老家伙”父亲的身边。《进入》中,“败家子”“老东西”“他妈的”等,成为父子对骂的口头禅。《驱魔》中,内德这一奥尼尔的自传式人物从死神的魔掌逃脱后,父亲要送他到疗养院。与此对应,现实中奥尼尔恰好在这个时候被查出患上肺结核,随后果真被父亲送到一所治疗结核病的疗养院。只是这家疗养院价格低廉,医疗条件落后,引起了奥尼尔的不满。《进入》中,蒂龙一家的很多谈话正是围绕此事展开。
《驱魔》中有不少虚写,奥尼尔写到内德的母亲已去世,但1912年奥尼尔的母亲Mary Ellen Quinlan还在世。通过内德父亲之口我们得知内德有姐姐,现实中奥尼尔只有哥哥Jamie O’Neill,并在晚年为他写了《月照不幸人》,它是奥尼尔对他哥哥的“忠实得达到残酷的程度的但是亲切的回忆”(弗吉尼亚·弗洛伊德1993:560)。奥尼尔在《驱魔》中没有提及他和Kathleen Jenkins的儿子Eugene O’Neill Jr.。Eugene O’Neill Jr.生于1910年,到1919年时9岁,他后来回忆说直到12岁时他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些虚写多少表明奥尼尔在写《驱魔》时的一些避讳,但他在《进入》中却“带着血和泪”讲述了这些家庭往事。
三、主题共享:父子冲突、婚姻纠葛和底层友谊
奥尼尔在《驱魔》中并没有详细交代父子矛盾的缘由,却又首次鲜明地展现了父子冲突的主题。尤其是父亲的强势和吝啬让内德反感,内德的一事无成也让父亲气恼,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具有张力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也是内德充满挫败感的部分原因。
谈到这个话题,我们有必要说一说内德父亲的原型,即奥尼尔的父亲James O’Neill。James O’Neill 1846年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的一个小村庄,全家为了逃避爱尔兰大饥荒,1854年到了美国,生活赤贫。James O’Neill的父亲托马斯得了肺结核,念念不忘故乡,丢下妻子和八个孩子独自跑回爱尔兰,死在故乡。从此,长子James O’Neill担起了养家重担,他在码头干体力活,在剧团做杂工,跑龙套,后来获得表演机会,靠演基督山伯爵名声大震。基督山伯爵这个角色给他带来财富,但他也被这个角色所困,毁掉了本来可以成为杰出莎剧演员和艺术家的可能。贫寒的家境和坎坷的经历使得James O’Neill富裕后依然勤俭节约,但又喜欢胡乱投资。他深爱妻子,又因贪图省钱为产后的妻子聘请廉价庸医,间接造成妻子吸食吗啡上瘾。James O’Neill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在外又有私生子。James O’Neill自身的种种自我矛盾直接或间接造成儿子的离经叛道,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愧疚感和失败感。
如果说奥尼尔在《驱魔》中对内德父子冲突的表现还只是浅尝辄止,那么在《进入》中,内德父子的冲突,也就是奥尼尔父子的冲突,便十分形象化地表现为埃德蒙和蒂龙的冲突了。也就是说,尽管这两部剧的父子冲突都是奥尼尔对其与父亲关系的两次不同书写,书写的内容如出一辙,但从青涩之作《驱魔》到炉火纯青之作《进入》,其同样的父子冲突主题造成的戏剧性和艺术性,自然有着很大的区别。尽管如此,就作为戏剧艺术创作的父子冲突主题而言,《进入》却是对《驱魔》的续写,这不仅是因为两部剧都是写1912年的故事,而且两部剧在剧情时间以及情节方面都具有直接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父子冲突主题在《驱魔》中只是具备了题材和情节功能,那么,在《进入》中,由于此剧的父子冲突主题既涉及实实在在的父与子的关系,也牵涉父子二人对待玛丽吸毒行为的态度问题,甚至他们由生活琐事到文学艺术趣味的争论以及所引发的对于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争执,使得其造成的父子冲突深度也远远突破了在《驱魔》中的题材性层面而获得了作为严肃戏剧主题的艺术价值。在《送冰》中,尽管此剧并未涉及直接的父子关系,但奥尼尔通过对拉里和帕里特关系的构造,从而形成了一对隐形父子关系的冲突,同样表现了父子冲突主题。
奥尼尔在《驱魔》中较早表现婚姻难题,把内德的婚姻不幸归于妻子的不是,把吉米的失败婚姻归于吉米的酗酒和不忠。奥尼尔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后,跟朋友弗兰克·贝斯特在纽约西区85号大街租了一套公寓。期间,他与Kathleen Jenkins恋爱,当两人把结婚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遭到反对。他们在1909年9月2日跑到新泽西州霍博肯城的一个教堂举行婚礼。James O’Neill得知后暴跳如雷,他认为不在天主教教堂举行的婚礼是非法的,也无法接受儿媳未婚先孕。事态的发展很快也证明了奥尼尔还不具备当好丈夫和父亲的能力。《驱魔》中,内德表示根本不在乎妻子,“一点也不!完全地,彻底地,毫不在乎!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内德把结婚归为“一个绅士的理由”,“一个顽固的魔鬼在我耳朵里嘀咕,说结婚是为数不多的我从没干过的事之一”(O’Neill 2011:76)。按照当时纽约州的法律,只有一方通奸才能判离婚。Kathleen Jenkins的律师跟奥尼尔合谋了一桩交易,让奥尼尔在1911年12月29日晚假装召妓,然后被捉奸在床,于是律师获得充分证据指证他通奸。《驱魔》讲述了这件荒唐事。奥尼尔夫妇的离婚请求在1912年10月11日得到批准,Eugene O’Neill Jr.判给 Kathleen Jenkins监护和抚养,奥尼尔没有被要求承担抚养费,连离婚费用都由Kathleen Jenkins的母亲支付。奥尼尔没有出席法庭宣判。事实上,当1909年奥尼尔在纽约火车站同Kathleen Jenkins告别、转道加州前往洪都拉斯探险时,那就是他与她的诀别,此后他们不再见面。
奥尼尔认为吉米的失败在于他自己。谈到吉米这个角色,应该谈谈奥尼尔的《热爱生活的妻子》(1913)。剧中,老人和年轻人杰克在亚利桑那沙漠淘金,老人的妻子伊薇特跟他的朋友杰克相爱,却又对丈夫保持忠贞。老人自知年轻貌美的妻子不爱自己,常常借酒浇愁。弗洛伊德认为,杰克是奥尼尔的部分自画像,是他笔下第一个性格分裂的主人公。但实际上此剧情节却取材于前面提到过的詹姆斯·拜斯。拜斯是James O’Neill的广告宣传人,奥尼尔的朋友,1911年至1912年间两人一同住在吉米牧师酒店的一个房间。1913年6月6日,即奥尼尔从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出院三天后,拜斯跳楼自杀,奥尼尔在7月写了《热爱生活的妻子》,在后来的剧作中也不断塑造过他,在不同剧中讲述婚姻的忠贞和背叛问题。前面谈到,拜斯是《驱魔》中的吉米,也是《送冰》中的詹姆斯·卡梅伦,绰号吉米·托莫罗。《送冰》中,吉米把酗酒的原因归于妻子,说是布尔战争期间当他从前线回到开普敦的家时,看到妻子跟他一个好朋友睡觉。在最后一幕,吉米又说这只是借口,他早在妻子通奸前便开始酗酒。奥尼尔在许多剧中表现了不如意的爱情和失欢的丈夫,类似人物还包括《榆树下的欲望》(1925)中的伊弗雷姆·凯勃特、《悲悼》(1931)中的艾斯拉·孟南。
值得一提的是,奥尼尔终生与结交的朋友保持友谊:一方面是他在做水手时结交的朋友,他们不断出现在早期航海剧中;另一方面是1912年前后在吉米牧师酒店结交的朋友,奥尼尔在《驱魔》中初步讲述了这类友谊。内德对吉米的态度有时比较粗暴,但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友情。到了晚年写《送冰》时,他对友情的珍视再次升华。弗洛伊德指出,奥尼尔在剧中“赞美那些他心爱的程度仅次于他的家人的人”(1993:505)。从《驱魔》到《送冰》,我们既看到底层群像的形象化呈现,又因这些角色自身的复杂故事,不仅丰富了奥尼尔戏剧,也使得奥尼尔在表现婚姻、友谊等主题时更深刻。
四、死亡叙事的绵延与艺术表达
奥尼尔早在《驱魔》之前的剧作中就开始写死亡。《雾》中的“诗人”认为“死亡”是仁慈的,是一种恩赐。《东航卡迪夫》中的杨克认为“死亡”不会比现在更糟。死亡对《天边外》中的罗伯特来说“不是终点,而是自由的开始”。《驱魔》作为奥尼尔表现自杀事件的写实之作,更是直接表现了他对死亡的迷恋及体验。此剧的结局看似光明:内德死里逃生,跟父亲的矛盾缓解,妻子也愿意跟他离婚,内德还打算跟好友结伴到西部旅游。内德一开始鄙视吉米不断提到的“春天”和“新鲜空气”,但等到他获得新生后,也开始憧憬春天。他和醉醺醺的吉米等人举起酒杯,以春天和新鲜空气的名义欢庆新生活的到来,但想要呼吸新鲜空气并非易事,就像《送冰》中霍普所说:“老天爷,哪里会有这种新鲜空气疗法。”(尤金·奥尼尔2006a:430)奥尼尔刚离开吉米牧师酒店,就被查出肺结核,在1912年圣诞夜被送到疗养院。《驱魔》看似驱除了内德的心魔,仍难掩此剧的死气沉沉,并在奥尼尔晚期戏剧中再现。
奥尼尔在《驱魔》中大量使用了有关死亡的词汇。内德悲观厌世,认为活着犹如行尸走肉,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大部分——包括余下的——”。他渴望作长途旅行——死亡。他把房间称作“停尸房”(morgue),他自杀后昏迷不醒,“直挺挺地躺着——像一具死尸(corpse)”;当吉米和马乔站在沉睡的内德面前时,他们“低头站着,肩并肩站成一排,仿佛在对着尸体作最后的祝福”。内德一再强调思考,自杀前在思考,被抢救过来后还要思考。内德接受父亲的疗养建议的前提是,“只要是我可以一个人待的地方——并且可以思考”(O’Neill 2011)。内德在思考生死,以致失去理智,一如《进入》中埃德蒙所说:“我清醒得很,所以才出了乱子。我坐下来思考得太久了。”(尤金·奥尼尔 2006a:430)《送冰》中的“哲学家”拉里,被戏称为“贼学家”,同样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至于《送冰》,“这部剧的剧名毫无疑问暗喻着死——突然的死或者慢性的死——因为死与‘地狱’酒馆从来就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克罗斯韦尔·鲍恩1988:98)。拉里一出场便表示“我眼下感到安慰的是死亡不过是一种美好的长眠,我已经筋疲力尽,只求早些死去”(尤金·奥尼尔 2006a:154),“丧服”“棺材”“陈尸所”“太平间”“死尸”“半死人”“老死人”“死人气味”等词频频从剧中人口中冒出。罗基说霍普酒店“就像一个太平间,这些酒鬼都是些死人”,拉里说这是“埋死人的坟场”,玛吉感叹“这儿真是个太平间,停放了那么多尸首”,科拉说“这地方真像太平间,阴雨天星期日晚上的太平间”,乔·莫特说他不想喝酒时会让帕里特“打电话给太平间,叫他们来把我的尸体弄走”。而推销员希基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欢乐和畅饮,而是死亡。他的“身上带着些死人的气味”,“他身上有一股冰冷的死气”,“死神就是希基请到他自己家里的那个送冰人”。最后,霍普生日晚会“不是在做寿,是守灵”。拉里认为希基想逼大家统统自杀,希基却说自己早就想自杀,他因自己堕落而又受着妻子无比的爱,竟然以解救妻子的名义将她杀死。就像《进入》中詹米所说:“一个人已经麻木不仁,所以他才不得不把他心爱的东西弄死。”剧终,一向被视为最清醒的“绝不想死”的拉里也表示“我是个懦夫,但是我现在真心想死”,与他一开始的“只求早些死去”呼应。
奥尼尔在《驱魔》中对青年内德的自杀和死亡体验的讲述和书写还比较简单,等到他写《送冰》和《进入》时,更多地写出对生命和死亡的哲理体悟。奥尼尔写《进入》时,父亲和母亲已去世,哥哥虽活着,但早已悲观厌世,又染上酗酒,《月照不幸人》中有对他醉酒后的传神描写,“两眼盯着地,活像个死人慢慢走在自己的棺材后面”(尤金·奥尼尔 2006a:505)。奥尼尔在晚年不时听到老友离世的噩耗,大儿子Eugene O’Neill Jr.也在1950年自杀,这些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进入》中,蒂龙对埃德蒙谈起他父亲的死,埃德蒙谈自己的自杀。埃德蒙和杰米常常引用有关死亡的诗歌嘲讽人生,追慕死亡,都使得《进入》笼罩着一层死亡阴影。由于蒂龙节约,他关掉多余电灯后的大厅“黑得就像一间停尸房”。埃德蒙比内德更强调死亡的存在感,认为现实生活“又像牧羊神,见到了他,你就会死——也就是内在的死——然后活着就像行尸走肉一般”,他时不时要“嘲笑人的一生”,“心里总是存在一点儿想死的念头”。詹米也像内德一样把自己一分为二,“这部分的我早已死去了”,死去的部分希望弟弟的结核病治不好,也许还高兴看到母亲又吸上吗啡,因为“这种人想找陪死鬼,他不愿做家里唯一的死尸”(尤金·奥尼尔 2006a:448-449)。
奥尼尔笔下的不少人物往往婚姻不幸,事业无成,信仰失落,常常借酒浇愁。《驱魔》中,醉酒后的吉米忘记了被妻子抛弃的悲伤,马乔也把被家人逼着一周去两次教堂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送冰》中,霍普酒店的房客们用酒精麻醉自己。《进入》中,蒂龙一家在醉意中互相指责、自责、愧疚和体谅,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遥遥无期的“明天”。“春天”之于吉米,“新鲜空气”和“西部之旅”之于内德,霍普酒店中的房客在希基的刺激和推动下,也都各自有明日梦。奥尼尔没有嘲讽白日梦者,而是给予理解和同情。他在剧中展示了这样的信念:人极端需要一种支持生活的幻想,以减轻摧毁灵魂的现实造成的毫无掩饰的绝望,这蕴含着奥尼尔对个人经历和家庭情感的体悟,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理解。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驱魔》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叙事艺术而言,都堪称是奥尼尔的“死亡之作”。此剧以高度写实的方式讲述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死亡体验,剧作对死亡意象及其象征艺术等手法的运用,更使得这部剧作充满浓郁的死亡叙事风格。然而,作为“心里总是存在一点儿想死的念头”,并常常思考生死的青年奥尼尔,敢于以身试法,以死抗争,纵然抗争的对象或目的是逃避婚姻也好,还是对人生的自暴自弃也罢,毕竟展现出果敢和悲壮的一面,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奠定并增强了他后来对悲剧艺术和悲壮风格的青睐。一方面,我们可以说1912年奥尼尔个人、家庭和朋友的故事以及围绕这些故事生发的种种情节,交织营造出《驱魔》的悲戚和阴郁格调,促成此剧的悲剧情调和悲剧风格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一如内德获救后开始意识到责任担当和生命可贵,期待“春天”和新生活的到来,现实中奥尼尔在自杀未遂后,也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剧末,内德和朋友在歌声中欢庆的场景,虽笔墨不多,却是一个重要表征和转折,它在传记层面为剧作家的自杀事件画上句号,在叙事层面达成戏剧性的完结,在象征层面宣告了奥尼尔对新生的乐观和向往。
因此,奥尼尔既会写出《驱魔》,并允许其上演,又在首演后旋即取消演出,并销毁剧本等相关材料。奥尼尔如此彷徨和自相矛盾,既满足了他要以戏剧写作纪念自己的自杀经历一事,实现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而他旋即将这部剧彻底销毁,又不失为他对这部剧以及对这段死亡经历的诀别。的确,奥尼尔此后的生活尤其是创作,在1912年之后,以及他在1919年写完《驱魔》之后,均迎来了新生。仅就创作而言,奥尼尔从1913年起成功创作了《渴》等多部剧作,正式走上戏剧道路,声名渐起。而写完《驱魔》后的1920年,奥尼尔的《天边外》获普利策戏剧奖,《琼斯皇》为他带来世界声誉。1921年《安娜·克里斯蒂》再获普利策戏剧奖。奥尼尔顽强乐观地活着,却倔强执着地书写悲剧,这两方面构成了他的人生与艺术的张力,形成了其戏剧艺术的魅力。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奥尼尔并不接受外界给他的诸如“令人沮丧的”“悲观主义者”等界定,而是直言“尽管我伤痕累累,但是,我对生活依然是乐观的”(Gelb&Gelb 1973:26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驱魔》,它展现了奥尼尔在绝望中萌发新生,在悲戚中生发乐观,在阴郁中激扬斗志。今天我们重获此剧,既要看到它的传记价值和艺术探索,也应正视它体现出的新生和乐观精神。
从《驱魔》到《送冰》和《进入》,刻骨铭心的死亡体验及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痛苦记忆,既让奥尼尔1919年创作的《驱魔》以写实笔法再现了这些经历和体验,又化作无意识的情感沉淀,进而使得它们在多年后仍能召唤他再次回到1912年这个原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尼尔为何在晚年回到现实主义和写实风格,并使得《驱魔》在晚期剧作中得到续写和重写。不论是被奥尼尔销毁的《驱魔》,还是曾被他封禁的《进入》,都只是剧作家漫长人生旅程的一段奇异插曲。而今,《驱魔》失而复得,既打通了奥尼尔早期创作和晚期剧作的关联,也使我们获得了对其早期失传之作及其晚期经典剧作的新的解读。
Eisen,K.2013.O’Neill afterExorcism[C]//W.Davies King(ed.).Eugene O’Neill Review.Philadelphia: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83-86.
Gelb, A.&B.Gelb.1973.O’Neill[M].New York:Harper and Row Publisher.
Kennedy, J.2013.Exorcism:The Context, the Critics, the Creation, and Rediscovery[C]//W.Davies King(ed.).Eugene O’Neill Review.Philadelphia: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8-38.
O’Neill, E.2011.Exorcism[J].The New Yorker87(32):72-79.
O’Neill, E.2012.Exorcism:A Play in One Act[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Sheaffer, L.1973.O’Neill:Son and Artist[M].Boston:Little,Brown.
Woollcott, A.1961. “Exorcism”[C]//O.Cargill,N.B.Fagin&W.J.Fisher (eds.).O’Neill and His Plays: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弗吉尼亚·弗洛伊德.1993.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M].陈良廷,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克罗斯韦尔·鲍恩.1988.尤金·奥尼尔传——坎坷的一生[M].陈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尤金·奥尼尔.2006a.奥尼尔文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尤金·奥尼尔.2006b.奥尼尔文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