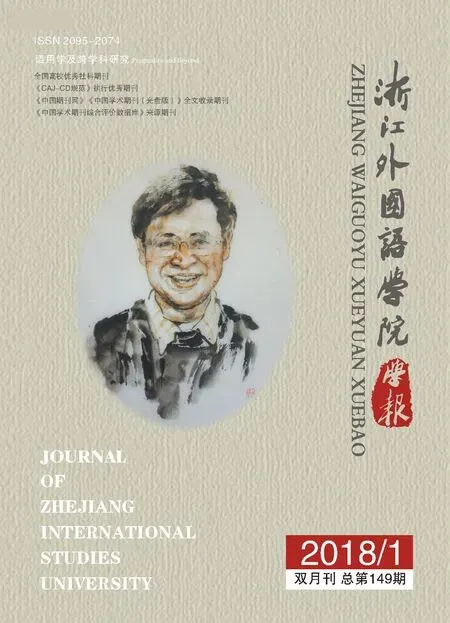剪草坪与人的存在
——从村上春树的“解说”出发解读《下午最后的草坪》
2018-02-11关冰冰杨炳菁
关冰冰,杨炳菁
(1.浙江外国语学院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北京 100089)
一、引言
《下午最后的草坪》(「午後の最後の芝生」,以下简称《草坪》)是日本文学研究界在探讨村上春树短篇小说时涉及较多的一部作品①当前,除了林少华的《“去中国的小船”搭载的是什么》一文(参见村上春树.2008.去中国的小船[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5-17),国内学界对《下午最后的草坪》的译介和研究几乎呈空白状态。。梳理先行研究可以发现,关于《草坪》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聚焦于小说的内容,即通过解读“我”在修剪完草坪后被女雇主带进其女儿房间的场景,对“我”的某种变化进行分析。例如,酒井英行在其专著《村上春树——与分身间的嬉戏》中指出:“可以说,‘我’与‘她’②根据酒井英行的论述,此处的“她”是指已经与“我”分手的前女友。(那个现在不在这里的‘她’)的首次直面相对是在‘中年女性’的引导下发生的。”(2001:22)在酒井看来,女雇主将“我”带进其女儿的房间无异于引领“我”走进了自己从未直面的内心世界。在那里,“我”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从未与已经分手的女友产生过真正的交集。二是针对小说的形式进行研究。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草坪》是一篇具有回忆性质的“手记”,且小说的开头部分出现了关于记忆与小说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因此,他们以小说的表现形式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例如,山根由美惠在其专著《村上春树<物语>的认识系统》中指出,“我”的回忆是“自我认识的过程”,而将回忆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则显示了“我”对“他者关系的一种希求”(2007:258)。三是研究《草坪》在村上小说群中所处的位置。加藤典洋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在《用英语阅读村上春树的短篇1979—2011》中,以态度和写作上的“疏离”(デタッチメント)以及“介入”(コミットメント)为关键词,对《草坪》在村上小说群中的位置进行了分析(2011:181-217)。四是解读小说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例如,高桥龙夫以收录于《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以下简称《全作品》)中的《草坪》版本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小说中美国要素对普通日本民众的影响(2016:136-143)。
在以上四类《草坪》研究中,第一类研究的数量是最多的。由此可见,尽管叙事方式、在村上小说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社会背景同样可以成为解读《草坪》的有效途径,但小说的内容,也就是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无疑是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切入点。既然小说通过“回忆叙事”的方式记叙了“我”最后一次剪草坪的经历,那么发生在“我”和女雇主,即小说中所谓“大女人”③小说是这样描述女雇主形象的:“个子委实高得惊人。我也决不算个小的,但她比我还高出三厘米……年龄五十上下……浓眉毛,方下颏,透出一旦出口决不收回的倔强。”(参见村上春树.2008.去中国的小船[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07)。之间的故事究竟表达了什么便自然成为了研究者解读的焦点。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最后一次剪草坪的经历令“我”发生了某种变化,而此种变化可以用“心灵成长”一词来加以概括。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将这些以故事情节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与村上本人关于《草坪》的解说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尽管两者都涉及了小说内容,但强调的重点却存在较大差异。
《全作品》第三卷的附录《对短篇小说的尝试》中,村上对《草坪》进行了如下解说:“在剪院子里的草坪时,我萌生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念头。不管怎样,我就是想写一个剪草坪的故事。较之故事情节,我更想写剪草坪这一作业。”(1990,3:Ⅷ)这段话透露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在剪院子里的草坪时,我萌生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念头”道出了《草坪》诞生的契机,即没有剪草坪就没有这部小说。第二,“不管怎样,我就是想写一个剪草坪的故事”揭示了村上的创作目的,即他想写的是“剪草坪的故事”而不是“剪草坪时发生的故事”。第三,“较之故事情节,我更想写剪草坪这一作业”则是对“剪草坪的故事”所进行的解说。由此可知,“剪草坪的故事”包含了剪草坪的“作业”和“情节”,且较之“情节”,剪草坪的“作业”更为重要。
结合上面分析来考察先行研究便会发现,聚焦于小说内容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剪草坪的“作业”予以充分重视。他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故事情节上,其研究结果也无法体现作者的创作初衷。那么,以剪草坪的“作业”为切入点是否能够准确解读小说?如果可以,又将得出何种结论?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将做如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梳理并总结《草坪》中出现的剪草坪的“作业”;第二,分析“作业”对“情节”发生所起的作用;第三,分析“作业”对“情节”展开所起的作用。
二、剪草坪的“作业”
虽然村上强调与“情节”相比他更想写剪草坪的“作业”,但是如果仅仅写“作业”本身的话,那么写就的便不是小说,而是说明书。因此,无论怎么重视“作业”,既然是以写小说为前提,那么“作业”就一定会被杂糅到故事情节之中。也就是说,要想梳理村上对“作业”的描写,就必然要从小说的故事情节入手加以抽取和总结。
读后可以发现,《草坪》不仅介绍了剪草坪的一般方式,而且对“我”所采用的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交待。当然,如前所述,此种介绍并非集中书写,而是被杂糅到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之中。小说中,当“我对草坪修剪公司的经理说不想干了”(102)时,他表示了惋惜,并对“我”的工作表示了肯定。继而,“实际上(雇主)对我的反映也极好,因我做事心细”(102)这句话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我”与一般临时工在剪草坪方式上的不同:
一般临时工用大型电动割草机大致割毕,剩下部分的处理相当马虎。那样省时间,又不累。我的做法完全相反。机器用得马虎,而在手工上投入时间,机器割不好的角落都做得一丝不苟,效果当然可观。只是收入不多,因是计件工,工钱取决于院子的大致面积。(102)
由此可知,一方面,“我”剪草坪的方式与一般临时工不同;另一方面,虽然“我”的方式能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从赚钱的角度来讲,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尽管“我”用时更长,花费体力更多。随后,小说对“我”在“大女人”家剪草坪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
早上磨好草坪剪,把割草机放在农用车上开去雇主那里。
我首先拾起掉在院子里的小石块,然后放上割草机。若裹进石块,刀刃就伤了。
割草机开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休息一会,坐在樟树荫下喝冷咖啡。
我用草坪剪剪草,剪到十二点。先把割草机没割均匀的地方剪齐,用耙子拢在一起,接下去剪机器割不到的地方。
十二点半我回到草坪。
我边听FEN的摇滚乐边仔细修剪草坪。用耙子把剪下的草挠了好几次,像理发师那样从各个角度检查有无漏剪之处。到一点半干完三分之二。
两点二十分修剪完毕。我关掉收音机,打赤脚在草坪上转了一圈。结果令人满意,没有漏剪的,没有不均匀的,如地毯一般平滑。(102-111)
剪草坪的“作业”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准备工具阶段,去雇主家前磨好草坪剪;清理草坪阶段,在开始剪前拾起草坪中的小石子以免划伤工具;机械操作阶段,用割草机对草坪进行大致修剪;人工操作阶段,用草坪剪对草坪进行细致修剪;检查效果阶段,剪完后打赤脚在草坪上转一圈以检查效果。由以上几个步骤构成的剪草坪方式虽然可以带来可观的效果,但是更为费时、费力。以“大女人”家的草坪为例,即便不包括准备工具阶段,“我”也大约花费了四个小时,即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开始剪草坪,直至下午“两点二十分修剪完毕”。如果换作一般临时工,估计中午十二点左右便可修剪完毕,因为他们大体会在将“割草机没割均匀的地方剪齐”后便结束工作,而不会“像理发师那样从各个角度检查有无漏剪之处”并进行进一步完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剪草坪的方式因人而异。从赚钱的角度来讲,一般临时工的做法显然更具合理性,但若要追求效果,则需要采用“我”的方式。“我”也是一名临时工,一般来讲,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既然都是赚钱,“我”与一般临时工又有何不同?表面看来,“我”与一般临时工的区别似乎源于自身性格——剪草坪时“可以不必怎么和人说话,正中我下怀”(101)。然而事实上,“我”之所以做得细心只是因为“喜欢剪草坪罢了”(102),“喜欢剪草坪”才是“我”与一般临时工的根本区别。对于一般临时工来讲,剪草坪的目的就是挣钱,其意义也正体现于此。而对“我”来讲,剪草坪确实带来了收入,但其真正意义则在于这一行为本身,与赚钱相比,“我”更注重剪草坪所带来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接到恋人要求分手的信并“注意到一个事实——既然钱派不上用场,再挣派不上用场的钱也就没了意义”(102)的时候,依然选择了到路程相对较远的“大女人”家剪草坪的差使。当从剪草坪中剥离掉“赚钱”这一目的和意义后,剪草坪便表现出一种纯粹性。换句话说,“我”在“大女人”家剪草坪是一项目的与过程高度一致的“作业”,剪草坪就是为了剪草坪。
综上所述,剪草坪的方式会因为操作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决定此种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操作者对目的和过程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两者一致时才会产生最佳效果,反之则不行。从这一点来讲,剪草坪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劳作,采取何种方式其实反映了操作者的心理。一般临时工的目的是赚钱,剪草坪仅仅是赚钱的手段,因此只要是为了赚钱,手段是可以随意改变的;而“我”则是因为喜欢剪草坪而剪草坪,剪草坪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对于“我”来说,手段是唯一的,即要想达到目的就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剪草坪。
三、剪草坪的“作业”与“情节”的发生
考察《村上春树作品研究事典》等先行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普遍认为《草坪》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剪完“大女人”家的草坪后,“我”被“大女人”带到她女儿的房间,并被要求说说对其女儿的感觉这件事(村上春树研究会 2007:67-68)。此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即使单纯从篇幅来讲,小说使用了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该事件,如此高的比例也足以说明其重要性。那么,剪草坪的“作业”究竟对该“情节”的发生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表面上看,“我”在“大女人”家剪草坪的“作业”与小说主要故事情节之间仅仅是时间上的前后关系而已,“作业”对“情节”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即使“我”去“大女人”家做剪草坪以外的其他工作,后面的故事也会产生,而这或许就是一些先行研究没有从“作业”的角度来分析小说的主要原因。该类研究的前提是忽视“作业”本身的重要性,这显然与村上所提供的解读方向相悖。那么,怎样才能准确理解剪草坪的“作业”和“情节”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小说令人费解的标题似乎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在“下午最后的草坪”这一标题中,“草坪”当然是主体,在它前面出现了两个起限定作用的词——“下午”和“最后”。尽管为何要强调“最后”以及因何成为“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单纯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在“大女人”家剪完草坪后的确没有再剪过草坪,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最后”一词的使用应该不会令人产生太多的疑惑。至于另一个限定词“下午”,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在那天上午便开始剪草坪,既然如此,标题为何要使用该词来进行限定?难道上午的草坪与下午的草坪有何不同吗?
很明显,草坪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我”剪的都是同一块草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处的工作阶段却不一样:“我”在上午完成的是准备工具、清理草坪、机械操作和少部分的人工操作,下午完成的则主要是人工操作和最后的检查效果。表面上看,“上午”和“下午”的差异仅仅是工作阶段的不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如果考虑到“情节”的发生便会发现,时间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或许任何人剪草坪都要经历以上几个阶段,但是只有采用“我”的方式才会使发生在“大女人”家的剪草坪“作业”从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也就是说,如果换作一般临时工,根本就不会出现“下午的草坪”。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下午的草坪”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它还带来了“可观的效果”,成为了“作业”与“情节”的连接点。剪完草坪后“大女人”找“我”聊天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剪法与其去世丈夫很相似,她说:“去世的丈夫对草坪很挑剔,总是自己剪得整整齐齐,和你的剪法很相似。”(113)从这一点来说,没有“我”的那种剪草坪方式就没有“下午的草坪”,而如果没有“下午的草坪”带来的效果便也没有了“情节”的发生。因此,小说的标题之所以被设定为“下午最后的草坪”或许就是为了凸显“我”剪草坪方式的重要性——“情节”的发生必须而且只能来自于“我”的那种剪草坪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村上解说中所谓的“作业”便没有“情节”的发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情节”发生的前提必须且只能来自于“我”的那种剪草坪方式,但“大女人”才是“情节”的真正主导者。因为如果“大女人”不把“我”领入房间,那么后面的故事也就不可能发生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到各类女雇主家中剪草坪,虽然剪草坪的方式始终如一,但是绝大多数女雇主却并没有将“我”请入房间。有一次,“年龄三十一二”的女雇主请“我”进入房间,并在“全部关合木板套窗熄掉灯盏的漆黑房间”(103),与“我”发生了关系,但是这并非是因剪草坪行为本身而发生的。与其他将“我”请入房间的女雇主不同,“大女人”那样做纯粹是因为“我”剪草坪的方式与其丈夫相似。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剪法的相似性,那么无论剪草坪的效果有多么可观,“大女人”都未必会继续与“我”聊天。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女人”和“我”聊天并非是由于“我”而是由于其丈夫,“我”的剪法、剪完后的草坪给“大女人”提供了一个遐想的空间,使得她将本没有关联的两个事物——“我”剪的草坪与其丈夫所剪的草坪联系到了一起,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给事物赋予意义的、类似于移情的过程。虽说“情节”发生的前提必须且只能是“我”剪草坪的方式,但如果没有给事物赋予意义的、类似于移情的过程,那么“作业”始终仅仅是“作业”,永远无法与“情节”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类似于催化反应,剪草坪的“作业”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而具有给事物赋予某种意义特质的“大女人”则是“催化剂”,反应的结果便是“情节”发生、小说成立。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第一,对于《草坪》来讲,“我”和“大女人”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我”的剪草坪“作业”,便没有“情节”发生的基础;如果“大女人”不由“作业”想到其丈夫,那么“作业”仅仅就是“作业”,无法对“情节”的发生起作用。第二,“我”和“大女人”之所以缺一不可是由两者所具有的截然相反的特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我”不赋予剪草坪“作业”特定的意义,而使“作业”的目的与过程高度契合,所以才能使“作业”为“情节”的发生提供基础;与此相反,“大女人”具有赋予事物某种意义的特质,因此才会使“作业”对“情节”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第三,虽然两个人存在差异,但是“我”与“大女人”的特质都是通过剪草坪的“作业”而显现出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作业”的重要性。
四、剪草坪的“作业”与“情节”的展开
如前文所述,剪草坪“作业”对“情节”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它对“情节”的发展是否也有作用呢?如果有,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先行研究之所以把《草坪》视为“我”在“大女人”引导下完成“心灵成长”的故事是由于没有重视“作业”,那么注重“作业”,小说又将被解读为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根据小说中的描写,由“作业”而引发的“情节”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女人”将“我”带到她女儿的房间,之后让“我”打开立柜并拉出一个个抽屉,问“对她(女雇主的女儿)”是“怎么看的”(119)。“我”立刻答道:“见都没见过,不清楚。”(119)然而,“大女人”却没有放弃提问,她给出了一个看似充分的理由——“看衣服可以大致了解女人”(119)。于是,“我”开始试图回忆自己以前的恋人,但“全然回忆不起来”,只好再次以“不清楚”(119)来作答。从两个人所具有的特质来看,出现上述情况是非常合理的。“大女人”因为具有赋予事物某种意义的特质,所以才认为“衣如其人”,并要求“我”说说对其女儿的看法。然而,“我”不是那样的人,因此,即便试图通过回忆先前的恋人来回答“大女人”的提问,却依然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重复说“不清楚”。
尽管“我”重复说“不清楚”,但是“大女人”依旧不死心,继续说道:“感觉即可。什么都行,让我听什么都行,哪怕一点点也好。”“为了争取时间,我喝了一口伏特加。”(119)然后,毫无把握地说了一些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口中语句的含义我明白,但我不明白指的是谁和谁”(120-121)。这应该就是“情节”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我”试图满足“大女人”的要求,但已“筋疲力尽,直想睡觉”(121)。对第二阶段的具体描写进一步凸显了两个人的特质。“大女人”的执拗表明,她或许认为赋予事物某种意义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的疲惫却说明,尽管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与“大女人”的不同,因此很难与她进行真正的交流。
第三阶段,或许“大女人”也意识到无法与“我”进行沟通,两个人的谈话陷入了僵局——“往下她久久地缄口不语,我也没作声”(121)。最后,“大女人”以对“我”的歉意结束谈话,而“我”在离开“大女人”家后依然困意十足。为了驱除困意,“我”在回程途中进了路旁的饮食店,要了可口可乐和意大利面条。当女侍者撤去餐具后,“我坐在塑料椅上迷糊了过去”(122)。醒来后,“我终于觉得自己是很累了”,吸了一支烟后“我”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我想我需求的无非是好好修剪草坪”(123)。第三阶段的描写真实地刻画出两个无法沟通之人交流时的窘境,同时,最终结论的获得也表明,“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赋予事物某种意义的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草坪》其实并非是一个“我”在“大女人”的引导下完成“心灵成长”的故事,而是一个“我”与“大女人”无法沟通和交流的故事,这也正是以“作业”为基点分析该小说后所得出的结果。不论是“情节”的发生还是“我”和“大女人”的特质,其背后都可以看到“作业”所具有的重要性,那么,村上为何要写这样一个“作业”具有重要作用的故事呢?笔者认为,联系小说开篇有关“小说”与“记忆”的议论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不过,倘若将人的存在视为一种受比较纯粹的动机驱使的颇为滑稽的行为,那么正确不正确云云便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记忆从中产生,小说由此问世,这类似任何人都无法抑制的永动机。它喀喀作响地满世界走来走去,在地表划出一条永无尽头的线。(99)
上面这段话表明,人的存在与剪草坪的“作业”有着共通之处:剪草坪本应是一项目的与过程高度统一的纯粹“作业”,从本质上讲,人也是因为存在而存在。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对错,人不需要与存在之外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然而,正如“大女人”赋予剪草坪的“作业”某种意义,从而将“作业”与“情节”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主导了“情节”一样,人们亦会将各种意义赋予到人的存在之中,由此,作为意义的载体——记忆得以诞生,而记录这些记忆的小说便也随之出现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小说表现的不过是被赋予了意义的人的存在,它是剪草坪的“情节”,但绝非其本身。
论述至此,我们便可以明白,村上其实是想通过对一个“我”与“大女人”无法沟通的故事的描写来阐述人的存在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在“我”的特质规定下所展现出来的“作业”相当于人的存在,当此种“作业”被“大女人”赋予意义后便有了“情节”,而“我”与“大女人”无法沟通的故事则成为了作为记忆载体的小说无法反映真正意义上人的存在的一个写照。
五、结语
“在剪院子里的草坪时”(村上春树 1990,3:Ⅷ),村上萌生了创作《草坪》的念头。表面上看,小说记录的似乎是作者对十四五年前最后一次剪草坪经历的回忆,但实际上是他对人的存在、记忆以及小说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通过“剪草坪的故事”的创作,作者试图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从本质上讲,作为记忆载体的小说是无法反映人的存在的。这是作者的无奈,也是《草坪》中开始写小说的“我”“不时深感羞愧,甚至认真地脸红”(99)的根本原因。然而,正像小说在最后一段对未来可能重操旧业的“我”所进行的描写那样,村上在此依然表达了一种希望——小说或许可以在将来从本质上表现人的存在。
加藤典洋.2011.村上春樹の短編を英語でむ1979-2011[M].東京:講談社.
酒井英行.2001.村上春樹分身とのれ[M].東京:翰林書房.
高橋龍夫.2016.午後の最後の芝生論―日常の秩序に潜むアメリカの影―[C]//2016年第5届村上春树国际研讨会予稿集.台北:致良出版社,136-143.
村上春樹.1990.村上春樹全作品1979~1989③自作を語る短編小説への試み[M].東京:講談社.
村上春樹研究会.2007.村上春樹作品研究事典(補版)[M].東京:鼎書房.
山根由美恵.2007.村上春樹<物語>の認識のシステム[M].東京:若草書房.
村上春树.2008.去中国的小船[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