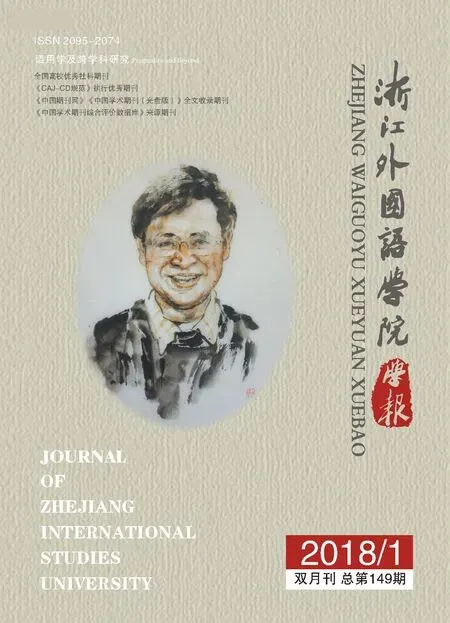《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中的疾病隐喻与关怀伦理
2018-02-11赖丹琪
赖丹琪
(浙江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7)
一、引言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指出:“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2003:5)。作为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疾病和与其相关的死亡、身体诸因素一起,构成了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两部自传体小说《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Angel,1929)、《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1935)①沃尔夫四部长篇小说都具有自传性质。《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中的尤金、《蛛网与磐石》《你不能再回家》中的乔治都是作家塑造的自传性主人公。《天使,望故乡》叙述尤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的经历;《时间与河流》叙述尤金在哈佛、纽约及在欧洲游历的历程。《时间与河流》有诸多主要人物如尤金、尤金父亲母亲、尤金哥哥本、尤金姐姐海伦等与《天使,望故乡》相同,几乎可以看作《天使,望故乡》的续篇。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名字的相似也突出了沃尔夫小说的自传性。沃尔夫父亲名为William Oliver Wolfe,母亲名为Julia Elizabeth Westall。《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中尤金父亲名为W.O.Gant,母亲名为Eliza Pentland(在本文引用的译本中,《天使,望故乡》译作“伊丽莎”,《时间与河流》译作“伊莱扎”,论述时从译文)。尤金两个兄弟的名字Benjamin、Grove也和作家兄弟名字相同。沃尔夫家庭成员及其与小说人物的对应关系可参看 Idol,J.L.Jr.1987.A Thomas Wolfe Companion[M].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pp.175-180。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小说叙述者和小说人物对疾病的叙述、描绘与想象均明显带有桑塔格所说的隐喻特征。不仅如此,这些疾病的隐喻也影响了照顾者与病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将结合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揭示沃尔夫两部小说中所包含的疾病的隐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的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探讨小说所凸现的关怀伦理中他者的具体化、异质化和关系的情境性问题,以透视小说所表达的理想关怀伦理。
二、疾病的隐喻:浪漫化及抵制
沃尔夫作品的自传性(Idol 1987:175-180)使我们知道,《天使,望故乡》(以下简称《天使》)、《时间与河流》(以下简称《时间》)里所叙述的尤金家庭遭受的一些变故都来源于沃尔夫的亲身经历。他的哥哥本杰明死于1918年至1920年间肆虐的流感大流行,而小说中尤金的哥哥本则死于肺炎。他还有个哥哥格罗夫很小就死于疾病,小说中也叙述了这一事件。沃尔夫的家乡阿什维尔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最有名的结核病疗养地(Eckard 2010:8)。而小说中写W·O·甘特初到阿尔塔蒙镇时,“这里不仅是避暑胜地,也成为疗养肺病的好地方”②本文对两本小说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托马斯·沃尔夫:《天使,望故乡: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朱小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及托马斯·沃尔夫:《时间与河流:青年渴望的传奇故事》(颜学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为节省篇幅,本文只随文标出出版年(区分两部小说)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2010:7-8)。沃尔夫1938年死于肺部疾病。沃尔夫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诺埃尔(Elizabeth Nowell)提到,肺结核的阴影一直萦绕着沃尔夫,远远在他1938年右肺发现肺部病变之前就影响了他的写作(qtd.in Eckard 2010:9)。在1920年9月的一封信里,他写到自己得了重感冒,咳嗽多痰,还在手帕上发现了血迹。沃尔夫叙述道,在那一刻,他看见了“我的梦想和诗歌——还有我自己……绝对的毁灭”。但这一事件似乎更坚定了他对写作的信念:“我的信仰中有了一种新的宿命论,无论什么可能到来,我已准备好。但是,无论怎样,我都要竭尽最后一丝力气表达自己。”(Eckard 2010:10)保拉·加仑特·埃卡德(Paula Gallant Eckard)因而认为,沃尔夫对肺结核的高度意识可能影响了他的写作和他的旅行癖(2010:9)。按桑塔格的说法,肺结核长久以来被视为“艺术家的疾病”。有关结核病的神话不仅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还提供了一种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寻找有益于健康地方的流浪者。结核病成为自我放逐和旅行生活的新理由(2003: 31-32)。
沃尔夫家乡成为著名肺结核疗养地,哥哥格罗夫、本杰明和父亲的因病去世,自身疾病的预兆与阴影,促成疾病叙述在沃尔夫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篇幅。而小说中,“疾病的景观布满了隐喻和矛盾。疾病和尤金周边的地理一样,是他个人成长环境的重要部分”(Eckard 2010:6)。
在沃尔夫的时代,对于疾病的原因有一种遗传论的观点,即某些人的体质因为遗传容易受某些疾病的感染。遗传论和 20世纪早期兴起的优生学相关。“Eugenic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ugenes”(“优生”)(Eckard 2010: 11)。伊丽莎给最小的儿子取名“尤金”(Eugene),意即为“优育”。然而,叙述者紧接着就说:“不过,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也从未体现出‘优育’的含义。”(2010:28)甘特的父亲是得肺痨去世的(2010:234)。伊丽莎是她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她的一个妹妹病死了,最小的弟弟智力迟钝,患有淋巴结核(2010:12)。伊丽莎自己的头三个小孩则都没有存活(2010:16)。伊丽莎要生尤金时,甘特对患肺痨而死的前妻辛西亚的回忆被唤醒了(2010:22)。辛西亚的死和父母亲家族的疾病似乎都作为一种阴影预兆着尤金此生与疾病的密切纠缠。
疾病与死亡深刻地影响了尤金的童年经验:尤金三岁时,他的哥哥格罗夫就死于伤寒。姐姐海伦带他去停尸房看格罗夫。小说写道:“尤金望着,恐惧像毒液一样灌注到血液里。透过躺在那里的被遗弃的小小躯壳,他突然想起了那张温暖的棕色脸庞、那曾经注视过自己的柔和目光……”在此处,小说使用了巫术仪式般的呼语:“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2010:49)《天使》原来版本的题名为“失落啊”(“O Lost”),而“失落啊”这句话在小说里反复出现,尤其常与家人的疾病和死亡对尤金造成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相联系。
沃尔夫的哥哥本杰明实际死于流感大流行,然而小说里的本死于肺炎。并且,小说里,肺病专家柯克说他“第一眼”见到本就知道他得了肺病(2010:469)。沃尔夫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曾专门研究过柯勒律治)。而沃尔夫的这一情节安排显示他对疾病具有浪漫化的想象。桑塔格提到,作为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进行的安慰,雪莱在一封致济慈的信里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面容”。桑塔格评价说,这里“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2003:27)。本的疾病与死亡在小说前面(第十章)就以浪漫化的隐喻进行了预示:本抑郁、沉默、内向、独来独往,“像个幽灵”。“他带着这家人悲惨的特征出生:孤身一人在黑暗中行走,死亡与黑暗天使在头顶上盘旋,根本没有人注意他。”(2010:95)而本的临终及死亡场景构成了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小说先是描述了本临终前的可怖景象,但在本临死之际,小说却写了死亡之美和它对旁观者精神的洗礼:
……他躺在那里,就像他自己的影子,尽显出他那不羁而灰暗的孤独之美。大家望着他,看见他明亮的眼神已经被死亡所模糊,看到他瘦弱的胸膛微微起伏搏动,看到一种美妙的景象,他的生命那幽暗而博大的奇迹用它无与伦比的动人美妙征服了众人。他们变得安静而平和,他们穿过了生命中所有的残渣琐屑,他们凝聚成为爱和坚毅的牢固结合,超越了恐惧与迷茫,超越了死亡。(2010: 469)
桑塔格指出,浪漫派通过美化结核病导致的死亡,“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2003:19)。而对本的死亡的叙述,正包含了这种浪漫化隐喻。
尤金对癌症所作的譬喻和叙述从另一面显示出小说对疾病的浪漫化。在《天使》里,尤金将癌症比作一株可怕而美丽的植物,它在父亲的身体里绽开花朵(2010:418)。在《时间》里,关于癌症的类似隐喻又出现了:“癌的大树首先在他内脏快速生长,然后在他整个生命的肌体里扎根、蔓延。”(2011:69)在叙述者和尤金看来,癌症这种疾病似乎就是一种有自身意志的生命体。小说如此叙述甘特的死:
在那一刻,他咳嗽得厉害,感到撕心裂肺,痛苦万分,某种东西在他体内挣脱了束缚,垂死的喘息搅动着他的血液,一大堆绿色的泡沫从他的唇间涌出。接着,世界变得漆黑一团,黑雾涌来,笼罩着他的头顶,……他的头脑遁入了黑夜。(2011:238)
桑塔格认为,疾病隐喻的传统将肺病视为一种灵魂病,而将癌症视为一种身体病。癌症“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2003:18)。她认为《时间》中癌症患者甘特的死是一种“卑贱、痛苦的死”(2003:17)。对本的临死场景的叙述,虽然也包含疾病与死亡的可怖,却也描绘了死亡之美和死亡给众人带来的精神上的超越与灵悟。然而,甘特的疾病与死亡却只有肉身的卑贱与痛楚。这种精神/身体的二元对立以及贬低肉体的浪漫化倾向在沃尔夫小说的疾病隐喻中十分明显。
作为沃尔夫的“另一自我”(alter ego),尤金对疾病的态度与隐喻及其变化至少折射了沃尔夫特定时期对疾病所持的观点。尤金十一岁左右时,“开始无休止地幻想着有魔力的泉水”,它能够“彻底铲除身体里一切疾病的肌体组织,重新赋予他一个完美无瑕的纯洁身躯”(2010:133)。此时的尤金对疾病带有抗拒的态度。尤金成人以后,去找了妓女。小说里只写尤金“腰胯饱受病害的侵蚀”,并未交待具体的病症,但从尤金和本的对话来看,肯定和尤金嫖妓有关。然而这之后,尤金的“情绪再一次恢复了”,“不再害怕了”。面对学校富家子弟的嘲笑,他能反唇相讥(2010:353-356)。疾病在此处被赋予一种成长仪式般的隐喻。实际上,《天使》原来的版本《失落啊》(O Lost)里直接写尤金得了性病,并写麦圭尔医生安慰尤金说:“孩子,我们都是腰部以下的兄弟姐妹。”(Mauldin 2010:38)在《天使》这个版本里,麦圭尔医生的这句话被删掉了。这种编辑处理也体现了某种权力话语对疾病的控制。性病一直以来就被赋予与道德相关的隐喻。性病意味着“羞于启齿”、意味着“道德败坏”,其疾病隐喻包含了强烈的权力规训色彩。然而,《天使》中尤金的话却道破了这种疾病隐喻的虚伪性质:“我所做的事,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做过的。噢,我知道他们会假装没做过。”(2010:353)沃尔夫像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所做的那样,不避讳写主人公嫖妓的经历。对自传性主人公这段“不洁”历史的披露,以一种现代主义的反道德讽刺了虚伪的现存道德秩序。
事实上,随着尤金的成长,他对疾病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尤金上大学时,像其他青少年一样,也一度对自己的身体有特别的关注:他会因嫉妒其他人的整洁牙齿而拼命刷牙一直刷到牙龈出血。然而,渐渐地,尤金开始接受自己身体的缺陷并对之进行了浪漫化的想象。他将脖子上的疹子“当做自己血液中那种悲剧气质的体现”;“通过哥哥的死和扎根在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尤金逐渐领会了以前全然不懂的更加深奥、更加黑暗的智慧。他开始发现,人生的动人与美丽之处恰恰在于一种高贵的珍珠般的病态。……他注视着世界上那些称尊为王者的面孔——发现他们无不被思想与激情的美丽病态所耗尽、所吞噬”。小说紧接着所列的具有美丽病态的王者面孔的清单里就包含了柯勒律治(2010:496-498)。
然而,尤金对于疾病与缺陷却又具有超越浪漫派隐喻的认识。小说写尤金开始认识到:电影和广告中的美丽、英俊脸庞“都像是从一个莹润而空虚的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全国普遍需求的洁白闪亮的马桶、牙膏、贴着瓷砖的快餐馆、理发店、整形牙科、角质眼镜、温泉浴场,在发泄兽欲之后跑到药店老板那里窃窃私语的对疾病的疯狂恐惧——这一切都污秽无比。外表的洁净成为本质败坏的标志”(2010:499)。尤金看到了所谓“洁净、美好、健康”的实质是消费社会到来时个性的消失和个体的均质化。人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复杂的审美感受性,只知追求表面的“漂亮健康”,却在沿用大众媒介、宣传(propaganda)这些单向度的话语系统时不加批判与反思③参见马尔库塞.2006.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疾病、缺陷”以及关于它们的“罪恶”隐喻体现的不过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规训④参见米歇尔·福柯.2012.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关怀伦理:情境性、“具体的”他者与隐喻的消除
疾病的隐喻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疾病的认知,也影响了照顾者关怀、照顾病人的态度、行为、方式,从而参与进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区别于传统伦理学对正义等核心概念的强调,关怀伦理学重视关系与情境,将伦理视为实践、具体的行为而非理论、抽象的逻辑,将他者看作异质的、具体化的、特殊的他者而非普遍化的他者,强调关怀、同情、尊重、爱等情感因素在伦理关系中的重要性⑤See Bowden,P.1997.Caring:Gender-Sensitive Eth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ollins,S.2015.The Core of Care Ethics[M].Basingstoke, 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UK。。后文笔者便将进一步考察《天使》与《时间》不同类型的关怀者与被关怀者所体现的关怀伦理以及疾病的隐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安卡·盖奥斯(Anca Gheaus)认为,关怀伦理学的前提是人类有一种根本的需要——以个人的、有意义的、有益的方式与他人相联系(qtd.in Collins 2015:36)。在尤金家庭中,在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最饱受诟病的是尤金的母亲伊丽莎/伊莱扎。她醉心于房地产投资,将很多精力都花在上面,对丈夫和子女的关怀、照顾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本和伊丽莎的抵牾沟壑最深,以至于他临死的时候都不愿见母亲,不让她进房间。在本看来,伊丽莎宁愿将钱财投在房地产上,也舍不得花钱给尤金买合脚的鞋,对孩子缺乏应有的关怀。海伦和伊丽莎的关系也非常对立。海伦总会生气地提醒伊丽莎,甘特才是真正需要得到照顾的病人。本得肺病而死,海伦、卢克都说,要不是珀特太太(本的恋人)和海伦的照顾,根本没有人来管本的死活,也是在影射伊丽莎只知赚钱、本发高烧时都没有给予其应有的照顾。甘特得病以后,伊丽莎对甘特身体的漠不关心导致甘特对同情的无限渴望。他甚至有几次喝得大醉后试图装死吓唬伊丽莎,希望引起伊丽莎对他的关注(2010:232)。一次甘特喝醉酒后,尤金扶他却被醉酒的父亲打了,因而手上受了伤。当时,尤金的恋人劳拉也在场。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劳拉照顾尤金的过程:劳拉用碘酒为尤金涂抹伤口,还撕下自己的旧白衬衫,用布条包扎伤口。等到伊丽莎过来关注到儿子的手伤时,尤金心里却想,“她的好办法总是来得太晚”(2010:370)。可见尤金对伊丽莎缺乏对他的关注、照顾也是有埋怨的。因而劳拉帮助尤金一起照顾醉酒的甘特并且温柔照料尤金的伤口时,尤金和劳拉的关系更亲密了。佩塔·鲍登(Peta Bowden)认为,母子关系象征着关怀的原型(1997:21)。本和尤金都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某种程度上也是母爱缺失后的一种补偿性行为。
然而,在关怀伦理中,应当注意到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并非绝对不变,而应随着情境进行定义。塞拉·本哈比伯(Seyla Benhabib)区分了“普遍的”和“具体的”他者。他指出,将他人视为“普遍的”他者忽略了个人生活的具体现实,没有认识到他者的个性。而将他人视为“具体的”他者则能将他人当作一个特殊的个体来关怀(qtd.in Parks 2003:40)。应当看到,伊丽莎也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具体化“他者”。伊丽莎对尤金吐露的心声显示关怀伦理的情境性:“我也想给你们一个家呀。自从格罗夫死后,我忍受了一切,但是他却从没让我有过一刻安宁。”“没有人知道。我也需要有个人来安慰我。我的日子过得真苦,儿子,全是痛苦和艰难。”(2010:375)伊丽莎的健康、坚强、乐观让人容易忽略她也需要照顾、安慰。她是一个遭遇数次丧子之痛的母亲,她的丈夫酗酒、嫖妓、患病,她操持各种家务,是家里睡得最晚的人。这些都说明伊丽莎实际上非常操劳辛苦。当时,在沃尔夫的家乡阿什维尔,房地产投资非常兴盛,小说里的阿尔塔蒙镇也是如此。她热衷房地产投资很有可能只是受环境影响,其本意也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家。只是,手段变成了目的,她已经有些迷失了。
伊丽莎/伊莱扎对病人缺乏照顾某种程度上和她对疾病的观念有关。她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很多疾病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伊丽莎和甘特初遇时,伊丽莎看到甘特萎靡不振,便说他的病一半都是想象出来的。伊丽莎说自己三年前得过肺炎,大家都觉得没救了,可她就是挺过来了(2010:9-10)。伊丽莎得伤寒病、风湿病时,就去佛罗里达等地旅行休养(2010:16,128)。上了年纪之后,甘特在疾病中日益沉沦,她却身体越来越健康。可见,伊丽莎身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甘特病入膏肓后,有一次不小心摔倒后流血不止,绝望已经笼罩了甘特和其他人。伊莱扎却对海伦说,有些病树看起来好像整棵树被疾病蛀空,它们却又能不治自愈,在腐烂的地方长出新树皮,渐渐它们又能旺盛生长。她坚信甘特也是如此(2011:215)。伊莱扎对疾病的认识违背了科学话语,而她对疾病所持的这种过分乐观态度既让她能坚强地面对自己的疾病,又使她对他人的疾病相对较少共情。当然,从关怀伦理来看,她的确不是一个理想的关怀者。“认识和接受他人的他者性(otherness)是关怀关系重要的一个方面。”(Bowden 1997:29)而伊丽莎/伊莱扎却将自己对疾病的隐喻——“病树能不治自愈”强加在了病人身上,忽略了他者/病人的具体处境。
海伦则是小说里一个典型的“关怀者/照顾者”形象。海伦“强烈地希望照顾别人,因为只有付出多于回报才能使她感到满足”(2010:112)。甘特生病后,是海伦在长期照顾他。在沃尔夫的时代,家庭护理非常普遍。伊丽莎和甘特初遇时向甘特推销的两本书里就有一本《拉金家庭医生及居家治疗手册》,“里面介绍了五百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2010:9-10)。正如詹妮弗·A·帕克斯 (Jennifer A.Parks)所说,家庭护理是一项女性主义议题,因为女性被定义为照顾者(2003:4)。她在专著《没有一个地方像家?女性主义伦理和家庭护理》一书中特地使用术语“caretaking”而非“caregiving”,以提醒读者:照顾不应仅仅被视为由女性给予的馈赠(a“gift”to be given by women),而是一种工作(2003:7)。家庭护理实际上是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家庭护理的假定就是‘家庭’(读作:女性)将会出于责任感提供她们免费的(或廉价的)劳动。”(2003: 3)
在海伦与甘特的关怀与被关怀关系中,容易遭到忽略的依然是关怀伦理学所强调的具体情境与差异化的他者。由于长期照顾患病父亲导致的身心压力、死亡的阴影所造成的恐惧、自身长期不孕的痛苦,“海伦生活在一种压抑的歇斯底里状态中”。小说写道:“她现在频繁生病,……她的病有各种表现——有时是胸乳部的剧烈疼痛,有时是神经极度衰弱,有时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崩溃,时哭时笑,多半是由于甘特的病,还有就是因为自己一直没能怀孕而万念俱灰。她总是偷着喝酒——小口小口地喝上一点鼓鼓精神,从来不至于喝醉。”(2010:412)海伦出于责任感、爱与同情照顾父亲,耗费了绝大部分精力,以至完全失去了个人生活。她的遭遇呈现了女性照顾者因繁重的家庭护理工作而致身体过劳与精神重压的处境。
对于自己总是充当关怀者角色,海伦并非毫无怨言。按照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说法,建立或维护关怀关系的人总是被自私的(自我关注的)和利他的(关怀的)动机的结合所驱动(2007:118)。海伦嫁给休·巴顿后,也曾对母亲说:“我这辈子光为别人忙活了。现在也轮到他们为我做点什么了。我可不愿意再伺候他的什么亲戚啦。不,绝不!”(2010:321)然而,就在休和海伦打算去蜜月旅行的前天夜里,巴顿老夫人(海伦的婆婆)突然得了疾病,呕吐不止。“海伦抖擞精神,奋力投入对病人的照料;发号施令,雷厉风行,事无巨细,她把病人救了回来。”然而,由于照料巴顿太太,海伦的蜜月被耽搁。海伦对此也表达了情绪:“我天天光围着她擦洗收拾了。你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2010:327)海伦的处境揭示了女性关怀者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女性如何在一个鼓励和颂扬女性无私奉献的文化里平衡他者的要求和自我的保存?”(DeFalco 2012:377)女性常出于爱、同情、责任关怀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然而这种关怀却常常超过了限度,占据了女性关怀者过多的时间、精力,甚至牺牲了女性关怀者的所有自我。人们常常没有将女性关怀者本人当作一个具体的、同样需要关怀的他者来看待。
鲍登认为关怀涉及到“协调尊严与依赖、责任与控制之间的冲突”(1997:104)。海伦与甘特之间的关怀关系则并没有很好地协调这一冲突。甘特过分依赖海伦,在海伦面前如孩子一般,而丝毫不会去考虑所谓尊严问题。海伦对甘特的照顾也变得控制多过责任。阿米莉亚·德法尔科(Amelia DeFalco)对“caretaker”和“caregiver”这两个词的辨析⑥与詹妮弗·A·帕克斯的视角不同,阿米莉亚·德法尔科考察了“caretaker”和“caregiver”这两个词的差别:“caretaker”这个词比“caregiver”至少早出现一百年。“caretaker”有明显的权力暗示,“take care”就是掌管——对被照看的人或事物采取一种权力立场。“caretaking”的接受者可以是事物,而“caregiving”的接受者只能是人。“caregiver”不像“caretaker”那样“掌管任何事物”,而是照看其他人的需要,尤其是那些无法完全照顾自己的人。See DeFalco,A.2012.Caretakers/Caregivers:Economies of Affection in Alice Munro[DB/OL].[2016-08-12].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329084539&v=2.1&u=jiang&it=r&p=LitRC&sw=w&asid=3fc1b5d313c 1629f72efa5400aa88fac.提醒我们:在照顾过程中,照顾者对被照顾者可能会产生一种权力。海伦才十岁的时候,家里便只有她才能让醉酒的甘特老实下来。她“把滚烫的热汤一勺勺喂到他嘴里,只要他胆敢顽抗,就用小手狠狠地抽他的耳光。‘把汤喝了!老实点!’”(2010:21)尤金对父亲的照顾不受醉酒的父亲待见,父亲还要打“这个迫害自己的人”。而海伦进来后,甘特哭了起来:“他们想害死我呢。”海伦一声令下,甘特就老老实实地由女儿扶到床上,喝了热汤。海伦给他喂汤时,他还“羞怯地咧嘴一笑”(2010:368)。甘特病重时,一天,卢克带甘特去街上。回家的时候,甘特却执意要自己一个人走,结果却摔倒在地,流血不止。海伦走进房间时,他“以孩子般的乞求目光看着她”。在甘特心里,海伦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救他的人”(2011:211)。
在海伦与甘特的关怀关系中,被关怀者对关怀者过度依赖,关怀者失去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海伦对麦圭尔医生说,父亲是她活着的唯一支柱。照顾父亲、让他活着已成为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因而,海伦无法接受父亲即将死亡的事实。麦圭尔医生却回答说,那不是她自己的生命,她不应摧毁她体内的伟大生命力——要唤醒它,让它复苏。“垂死的死亡并不可怕,像死一样活着才真正可怕。”(2011:191-192)麦圭尔医生透彻地看出海伦和甘特的关怀关系并不理想,因为海伦已经将照顾父亲视为唯一的生活目的与价值所在,提前埋葬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中的麦圭尔医生和病人甘特及其家属的关系构成了关怀伦理的另一透视视角。麦圭尔对疾病与死亡持一种消除隐喻的态度。他对海伦说:“在你看来,死亡好像可怕得不得了,这是因为你对死亡了解很少,可我跟死亡打过多次交道,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人死去——但是,我知道,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怕之处,对于饱受疾病摧残的老人来说,死亡根本不可怕。”“老人去世,就像钟表停止走动一样——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失去了生存意志,他想死,他只是停止了走动。”(2011:190)区别于傲慢地把持医学权力话语不放的医生,麦圭尔承认医学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的局限性、医生作为个体和其他人一样具有的必死性。他对海伦说:“我可怜的孩子,我救不了任何人——我无能为力——我甚至自身难保。”(2011:193)“我是个医生,不是创造奇迹的人。”“延长他的生命是残忍的行为;我究竟为什么要努力那样做呢?”(2011:208)甘特病情危急,海伦对麦圭尔医生说:“你必须止住流血!”“你必须做到!”麦圭尔却回答说:“止住什么?你究竟认为我是什么人——耶和华?”(2011:212)麦圭尔呈现了医生和病人之间关怀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多年前甘特就成为麦圭尔的病人,他们之间存在超越病患关系的情分。然而,麦圭尔却说延长甘特的生命是残忍的行为。麦圭尔的话提示了医生的伦理困境:是否延长痛苦病人的生命一定最符合医学伦理?麦圭尔看到了医学权力话语过度自信的外表下掩藏着作为必死个体的医生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的局限性。就在甘特葬礼的那天早晨,人们发现麦圭尔医生死在他办公桌的旁边。这之前,人们发现,甘特葬礼上,送来的花圈里,有一个花圈上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有麦圭尔医生的名字。叙述者强调这卡片给人带来的奇怪之感(2011:241)。麦圭尔医生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阿什维尔的医生尤金·格伦(Mauldin 2010:35)。而尤金·格伦实际死于沃尔夫父亲去世两年之后,而非如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死于甘特葬礼同一天(Mauldin 2010:48)。《时间》此处对巧合的虚构,应和了小说前面叙述的麦圭尔作为医生和作为人类普通一员在死亡面前同样感到的无能为力。麦圭尔医生与甘特的关系说明医生与病人的关怀关系也并非定义单一、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具体伦理情境而变化。麦圭尔说延长甘特的生命是“残忍”的行为,恰恰体现他将甘特当作“具体化”的他者——和他一样能感受痛苦、具有必死性的个体,而非“普遍化”的他者——一个符号化的“病人”。
四、结语
《天使》与《时间》体现了疾病的隐喻特征:疾病与遗传论相联系,被赋予浪漫化的宿命感。本的肺炎和甘特的癌症被归属于精神/身体的二元对立:前者能带来精神上的灵悟,后者却只有肉体的卑贱与痛苦。这些都体现了沃尔夫受浪漫派影响的疾病隐喻。然而,小说中也有对疾病浪漫化隐喻的超越之处。尤金对统一化的“健康”的轻蔑和对疾病、缺陷的接受,体现的是对单向度权力话语系统中的疾病的定义与隐喻的抵制,以现代主义的反道德揭示了既有道德秩序的虚伪。而疾病的隐喻渗透到小说的关怀伦理关系中,影响了关怀者对待被关怀者的关怀态度与方式。通过对具体情境的考察,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关怀关系、关怀者、被关怀者并非一成不变:总被定义为关怀者的女性也可能是需要关怀的被关怀者;医生对病人的关怀也可能存在差异化的方式。沃尔夫的小说呈现了关怀伦理的复杂情境。小说提醒我们:理想的关怀关系,既不是海伦与甘特那种过度的控制-依赖关系,也不是伊丽莎/伊莱扎和家人那种缺乏足够关怀的冷漠关系,而是麦圭尔医生和甘特及其家属之间的关怀关系——他者被视为具体化的、异质的。在这种关怀关系中,疾病的隐喻被消除,疾病及死亡不再是“以他物之物名此物”⑦即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义:“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49页。,而是回归为疾病及死亡本身,如其所是。
Bowden, P.1997.Caring:Gender-Sensitive Ethic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llins, S.2015.The Core of Care Ethics[M].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DeFalco, A.2012.Caretakers/Caregivers: Economies of Affection in Alice Munro[DB/OL]. [2016-08-12].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329084539&v=2.1&u=jiang&it=r&p=LitRC&sw=w&asid=3fc1b5d313c1629 f72efa5400aa88fac.
Eckard, P.G.2010.“A Flash of Fire”: Illness and the Body inLook Homeward,Angel[J].Thomas Wolfe Review34:6-24.
Idol, J.L.Jr.1987.AThomas Wolfe Companion[M].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Mauldin, J.M.2010.The Doctor and His Wife: Might There Have Been a Kinder, Gentler Wolfe?[J].Thomas WolfeReview34:35-53.
Parks, J.A.2003.No Place Like Home?Feminist Ethics and Home Health Care[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Slote, M.2007.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马尔库塞.2006.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12.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珊·桑塔格.2003.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托马斯·沃尔夫.2011.时间与河流:青年渴望的传奇故事[M].颜学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托马斯·沃尔夫.2010.天使,望故乡:被埋葬的生活的故事[M].朱小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1996.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