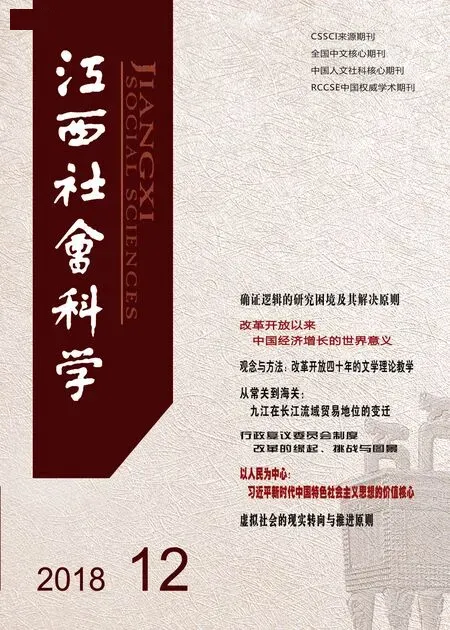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的支点:深层历史、叙事、符码转换
2018-02-11
深层历史、叙事和符码转换是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中有机联系的三个支点。透过这三个支点,詹姆逊阐述了“政治无意识”的实质和形成机制、“政治无意识”的文本投射途径以及文本中潜藏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分析方法。基于以上支点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阐释的理论基础,有效回应了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冲击,并提出了从文本结构回归历史总体、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交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模式。该理论的相关论述在文学自治性、文学对现实的能动反作用、作家主观能动作用及其表现方式多样性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
历史化阐释将作品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途径。早期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主张通过“客体分析”即考察作品内容的历史渊源或创作历史背景来进行批评阐释。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批评模式的理论基础——“客观存在的历史”受到重大冲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所谓历史其实是历史叙事(historiography),人们接触到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关于历史的叙述”。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是根据特定的“深层结构”将一系列历史事实贯穿起来的叙事话语。面对这种困境,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吸收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合理成分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容纳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学说,提出了“政治无意识”理论,从个别主体、社会历史与文学叙事三者间的关系入手,探究社会历史的认知、社会历史在叙事(文本)中的投射及叙事(文本)潜藏的社会历史痕迹的阐释方法。该理论一经提出即在欧美文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奠定了詹姆逊美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英语世界里最主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的地位”[1],对该理论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文艺理论研究的显学。然而,由于詹姆逊未对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无意识”进行清晰界定,学界对该理论的理解差异甚大,甚至导致概念指称泛化、理论应用零乱的现象,这种现象需要我们探求符合詹姆逊原意的理解。目前,学者们从“政治”和“无意识”等符码出发,对“政治无意识”的关键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但对于各关键词间的理论勾连以及詹姆逊对相关学说如何进行辩证改造和融通的思想脉络,所述不多。因此,本文尝试以“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历史化阐释目标为出发点,结合詹姆逊早期学术思想,从深层历史的个体认知、深层历史的语言重现,深层历史的分析途径三个角度,剖析“政治无意识”概念的理论支点,进而梳理该概念所勾连的基本理论脉络。
一、深层历史:“政治无意识”的形成和实质
“政治无意识”包含“政治”和“无意识”两个概念。关于“政治”,詹姆逊曾解释道:“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的。”[2](P20)换言之,在政治无意识理论中,“政治”总是跟社会历史相联系的,“政治”无意识就是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无意识。①
“无意识”原本是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术语。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是本我所处的层面,其中涌动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拉康则跳出家庭和性的视域,从社会性、交流性的语言符号/象征秩序来探讨无意识的起源。他认为:主体(“我”)的形成要经历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种秩序。个体必须在象征界确立自身在语言符号系统或者说象征界中的位置,才能最终获得主体性(成为“我”),未能进入象征秩序的内容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即无意识。换言之,无意识是语言符号(或象征界)压抑的产物,其根源是“大写的他者的话语”。[3]在詹姆逊看来,“无意识”概念具有某种唯物性质。他在《拉康的想象界与真实界》一文中曾指出了精神分析学说对主体进行了去中心化,否定了唯心主体(我思),尽管其去中心化的方向是性或者语言,但两者都是物质性的,因此,精神分析概念(包括“无意识”)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所借鉴和吸收。[3]在理论操作上,詹姆逊认为拉康的“无意识”术语暗示的社会属性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可以选择为“政治无意识”的理论渊源。
“政治”(即社会历史)与“无意识”的结合,则源于阐述人(主体)、历史与叙事(文本)关系的需要。詹姆逊反对“历史即叙事(文本)”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但承认历史通过叙事(文本)才能被人们认识:“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4]这就产生一系列问题:历史是否能够全面充分的再现?什么因素决定历史受到再现或者受到压抑?受到压抑的部分是否能以某种变形的方式重现在叙事(文本)中?我们又如何在叙事(文本)中辨别被压抑的历史的痕迹?这样,需要对个别主体、历史与叙事(文本)三者之间关系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詹姆逊认为吸收了精神分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可望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在詹姆逊之前已有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说相融合的尝试,这位学者就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其成果就是其极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生存状况之想象关系的再现。”[5](P162)在这个定义中,“真实生存条件”“想象性关系”和“(语言)再现”与拉康的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有着密切的对应联系。詹姆逊分析相关学说后认为,永远无法直接体验的“真实界”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因此,所谓的“真实生存条件”,就是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3]这样,个别主体在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功能为历史与文本再现搭建了一座桥梁。詹姆逊写道:“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解释为阿尔都塞所言的表征结构,那么,这个表征结构就允许个别主体构思或想象他或她所经历过的、与超个人的现实(如社会结构或历史的集体逻辑)的关系.”[2](P29)换言之,超个人的历史永远无法被个体直接经验,但可以被个体想象。由于这种想象是个体的、不可通约的,无法为外界所直接了解,所以还需要上升到象征界,通过语言/文本进行再现。这样,借助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詹姆逊解释了历史如何得到文本再现。
不过,阿尔都塞的理论忽略了一个问题:历史是不能得到完全再现的。在詹姆逊看来,历史的再现必须经过一个过滤机制,即意识形态遏制。首先,个别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并非自由的,而是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阿尔都塞此前曾指出,个体通过类型化被(既有的)意识形态询唤为具体的主体(subject),个别主体是(既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5](P180)因此,为了成功询唤个体,意识形态必然对个体与其所生活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力图使个体与历史的真实关系成为这种关系的镜像。个体在接受意识形态询唤从而成为的主体的过程,也是根据自我/个体与历史/总体关系确立自我位置的过程:“意识形态是把个人的自我(想象界)放在这个自我同包围着它的种种集体性和制度性现实的总体的关系中,放在它同这个复杂的并且实际上是无法表征的总体的关系中来给这个自我定位的.”[6]所以,个别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只能筑基于既有意识形态的定位网络,与这个网络的不相符的历史事实往往被排除在个别主体的想象之外。其次,对个别主体的历史想象进行再现的象征界也具有意识形态r 性质。[3]象征界产生在语言符号层面,语言符号的使用并非中立的,而是与使用该语言的特定社会集团相关联。某个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必然受到这个社会集团在社会历史生活的界限所框定,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一个阶级的思想不能越出其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7](P152).因此,个别主体所属的社会集团决定了他其对历史想象进行再现的语言界限,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界限。这样,意识形态具有一种“遏制策略”的功能(strategy of containment),它在帮助个体的主体了解部分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又遮蔽了另一部分的历史真实。这种“遏制策略”功能被詹姆逊称为“意识形态封闭”,被“意识形态封闭”遮蔽的历史真实是未被说出的深层历史。深层历史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类似于拉康所言的未能进入象征秩序的“无意识”。[4]因此,深层历史就是意识形态封闭产生的“无意识”,是“政治无意识”。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深层历史即“政治无意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对此,詹姆逊未作明确阐述,但在解释个体所想象的“超个人的现实”时,他提及两个名词——“社会结构或历史的集体逻辑”[2](P29),换言之,历史中最本质、最根本的层面。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乃是矛盾,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矛盾。伴随着这些矛盾的是迄今人类历史中存在的剥削与压迫境况,这种境况让压迫者和受压迫者都感到难以忍受(压迫者对于压迫导致的反抗和可能的暴力革命充满恐惧,而受压迫者则为短时间无力改变境况而感到痛苦),因而必须加以遮蔽。[8](P131)可以说,这种被遮蔽的矛盾是“政治无意识”的基本内涵。
二、叙事:“政治无意识”的文本投射
受到压抑的深层历史(即“政治无意识”)如何重现于文本,这是“政治无意识”理论需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詹姆逊将解题的关键放在“叙事”上。
在詹姆逊看来,意识形态有消极和积极并存的辩证法:它既是虚假意识,也是一种乌托邦,它虽然压抑历史真实,同时也反映集体对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2](P289)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属性为深层历史的重现提供了可能。深层历史的“缺场”造成一种匮乏,引发主体接触历史真实、回归完满的欲望。为了让这种欲望得到释放,同时又维持根本社会矛盾的遮蔽状态,意识形态必然驱动主体寻找替代性想象,重构个体——历史的关系,从而让被遮蔽社会矛盾获得“解决”。对替代性想象进行表征的途径就是叙事。②在这里,叙事成为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socially symbolic act)[2](P17),它表达集体对于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反映了集体的意志或欲望,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同时,它作为“对现实矛盾的想象解决”实施了解决矛盾的行为,但这种“解决”又是语言上的、想象中的,只具有象征性。正由于叙事的“社会象征性”,社会矛盾不能得到真正解决,主体对回归完满历史真实的渴望无法得到真正缓解,并不断催生着(再)叙事的冲动。
叙事在 “解决”现实矛盾时,不可避免地涉及现实矛盾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前文本(social paratext)即社会历史,并且在叙述“事件”的具体范畴中,将这种前文本积极投射出来。[2](P44)跟精神分析学说中“被压抑者终将回归”相似,被意识形态压抑的深层历史的痕迹终将投射于叙事过程,或隐或现地重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这样,叙事成为具有辩证意味的悖论,它既帮助意识形态压抑历史真实,让根本的社会矛盾处于遮蔽状态,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投射深层历史的痕迹,在文本中重现无法直接体验的深层历史和社会矛盾。因此,叙事成为“政治无意识”文本投射的途径,“正是在发现未中断的叙事痕迹的过程中,在这一将被压抑、被掩盖的基本历史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学说才找到其功能和必要性”[2](P20)。
不过,并非所有叙事都直接投射被压抑的深层历史。在“政治无意识”理论中,叙事包括主叙事与个体叙事两种类型,主叙事关注历史总体,个体叙事聚焦于个别的历史事件。这种两分法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宏大叙事”和“小叙事”之说。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关注超验的、普世的真理,小叙事聚焦于局部语境和个别事件,宏大叙事是不可靠的,在后现代语境应该以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9](Pxxiv-xxv)詹姆逊借鉴了这种区分,但认为“宏大”与“小”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将宏大叙事视为主叙事,那它必然存在于局部、微观的个体叙事中:“宏大的主叙事不是消失了,而是进入了潜藏的状态,它们继续以一种‘思考’的方式在我们的当代境遇中无意识地发生作用。被掩盖的主叙事这种持续存在于我所称的‘政治无意识’中。”[10](Pxxii)因此,关于历史的主叙事与个体叙事构成辩证关系——主叙事潜藏在个体叙事中,个体叙事蕴藏主叙事的因子。
关于历史的主叙事与个体叙事辩证关系还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问题。与整个人类历史相比,个别的历史事件延续时间极短。如果说人类迄今的历史是历时性总体,那个别历史事件只是共时性片段。要确立个体叙事与主叙事的辩证关系,还须证明共时性片段蕴含历时性总体的因子。詹姆逊认为此处“蕴含”的是一种结构因果性。一方面,个别事件与历史总体有结构相关性,个别事件的历史意义由它在历史总体结构上的位置决定,因为“个别时期的形态总是潜在地按时或投射历史序列——叙事或“故事”(即叙事性的再现),而个别时期在这种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衍生意义”[2](P28);另一方面,个别事件与历史总体有结构相似性,如果“放大个体叙事的主符码,个体叙事就会成为一个自身独立的宏大叙事”[2](P33)。
因此,主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联系转化不是源于内容的相似性,而是因为个体叙事的“所指”折射主叙事表征深层历史时采用的基本范畴:“宏大叙事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因为这些寓言中的叙事所指……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2](P33)
文学反映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作为个体叙事的文学文本必然蕴藏着关于历史总体的主叙事因子,反映他们关于理想世界的想象,投射这种想象中潜藏的深层历史的痕迹,折射集体的意志、希望或者怀念。由此,詹姆逊得出结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无论它多么微弱),一切文学都可以理解为对共同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2](P70)该论断从根本上论证了对文学文本进行“历史化阐释”可能性,可谓“政治无意识”理论的重要支点。
三、符码转换:“政治无意识”的结构分析
如何分析作为个体叙事的文学文本,追踪文本中潜藏的深层历史的痕迹,将文学叙事、集体愿望表达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化阐释”,是“政治无意识”理论有待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詹姆逊提出了“符码转换”的方法。
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曾提出直观反映和典型表现等观点。詹姆逊认为:第一种观点秉持的是机械因果律,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独立地位;第二种观点秉持的是表现因果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容易让人误解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有“同源”(homology)特质,导致人们将文艺批评当成历史主叙事发掘,致使批评结论趋同。在遭受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冲击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如果承认叙事(文本)对历史再现的作用,就不能忽略文学作为叙事的能动作用,需要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找出新的论述。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阿尔都塞主张的“结构因果律”。在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之间不存在所谓上层建筑(upper structure)与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之分,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结构的组成部分。结构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各部分组成共时的体系,彼此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在结构中的位置,因此各部分既受结构的影响,又具有一定的“半自治性”。历史不存在于结构中,只是作为“不在场的原因”发挥作用。[11](P186-189)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理论只有一个“结构”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社会历史总体,而非仅限于经济层面。[2](P35)如此,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就具有结构性:一方面,文学文本是总体结构(生产方式)的一个部分或层面,具有自身的规律即“半自治性”;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总体结构(生产方式)的影响,具有与总体结构的同一性。为了将文学文本与总体结构(生产方式)联结起来进行历史化阐释,需要一套符码和术语来“分析表达两种相当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者说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2](P40)。这种沟通不同结构层面的术语操作被詹姆逊称为“符码转换”(transcoding)。
在术语操作上,詹姆逊选择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矛盾”与结构主义文论的基本理念“二元对立”联结起来。对于这两个术语联结的可能性,詹姆逊早年在《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著作中曾从三个方面进行过论证。首先,“二元对立”与“矛盾”在内涵上具有相通性。二元对立必然强调相互关系而非某一个实体,对立中双方是相互牵制的力量,失去一方,另一方也无法存在,而且对立还暗示着整体或者系统的存在。因此,“二元对立”可以看做“静止的辩证法”,其蕴含的对立性与“矛盾”内涵相近,而其暗示的体系性则与“总体性”相近。[12](P27,P98)其次,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理论根源——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主张共时分析,但视共时分析对象为语言一个时间截面的投射,并未排除进行历时观察的可能。[12](P19)最后,文本形式结构并非中立的,而是与内容密切相关,换言之,文本形式与社会结构是相联系的:“任何作品形式的文本化或者抽象化,最终必然表达出其内容的某种深刻的内部逻辑,而且这种文体化自身的存在,最终必然依赖于社会原材料本身的结构。”[13](P342)基于这些观察,詹姆逊认为“二元对立”组成的文本结构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概念性反射和象征性表达,通过“二元对立”“矛盾”的符码转换,可以将作品批评从文本结构分析导向社会历史阐释,在共时分析中寻找一定历时的元素。[2](P73)
基于这种“符码转换”操作,詹姆逊提出了三重视域阐释框架,从文学文本的三种不同性质(作为文学叙事、集体愿望表达和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的投射)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第一重视域是政治历史观。在这个视域内,个体叙事与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被解作社会矛盾在文本内部的表达。该领域的阐释从文本形式结构分析开始,剖析其中折射的“被想象解决的社会矛盾”,追溯先在的社会前文本,即“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第二重视域是社会观。在该视域,个体叙事与文学文本被解作“阶级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论辩策略采取的象征性手段”,即阶级话语(“语言”)的个体叙事表达(“言语”)。由于阶级话语(“语言”)难以在个体叙事(“话语”)充分呈现,该领域的分析旨在发现阶级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最后一重视域是历史观。在该视域,文本形式被当作自身独立的历史积淀内容,个体叙事与文学文本都被当作“形式意识形态”,即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递的象征性信息来解读,而这些符号系统本身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痕迹。由于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同时存在数种生产方式的重叠和共存,因此对符号系统共存(生产方式共存的痕迹)所传递的象征性信息进行分析,可让文学作品结构以辩证的方式向历史开放。[2](P77-95)
四、结 语
通过深层历史、叙事和符码转换的论述,詹姆逊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吸收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合理成分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容纳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学说,从个别主体、社会历史与文学叙事三者间的关系入手,建构主体路线的“历史化阐释”路径。筑基于这三个支点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重新巩固了历史化阐释的理论基础,有效回应了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冲击,并提出了“从结构回归(历史)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演进维度上,该理论以叙事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之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一,它借鉴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认为文学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元素处于共时的生产方式宏观结构中,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并非机械对应,而只是有某种程度的联动关系,这样承认了文学的半自治性;其二,它从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意识和乌托邦两方面的辩证关系这一判断出发,提出“现实矛盾的想象解决”之论,表明文学叙事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现实,指出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打破了关于现实与文学之间逻辑顺序的固定看法;其三,它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引入“无意识”和“愿望满足”等精神分析学说概念,认为文学叙事是一种集体愿望的表达手段,因此,在坚持社会历史总体性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主观能动作用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以上观念有助于文艺批评跳出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窠臼。在阐释方法上,该理论提出三重视域阐释框架,将文学作品放置在历时(社会历史观)、共时(社会观)和共时中的历时成分(历史观)三个视域进行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确实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理论推至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然而,“政治无意识”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政治无意识”概念没有清晰界定,概念阐释也有些语焉不详,因而让该术语显得模棱两可,既像一种被压抑的精神层面,又像一种文本压抑的机制。概念的模糊导致许多不同截然的解读,如集体心理状态、被压抑的社会现实、未明示的意识形态、潜藏的政治欲望等。这种模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理论误读留下空间,扩大“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可能应用范围;另一方面也导致该概念的内涵被不断虚化和泛化。其次,詹姆逊融多种学说为一炉的辩证论述方式也让“政治无意识”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进而导致略显尴尬的状况:对该理论的梳理和分析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但该理论在文学作品批评实践中的应用则相对不多。以国内为例,在“政治无意识”理论为数不多的批评应用中,学者多引用该理论对叙事和文学本质的论断,或者援用其文学作品分析框架,但很少运用特定话语揭示、阐发和诠释作品的主旨、内涵或意识形态立场。应该说,这些情况与“政治无意识”理论的模糊和复杂是有密切联系的。
注释:
①关于“政治无意识”概念中“政治”的含义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详见:张开焱《“政治无意识”基本构成再探》(《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
②詹姆逊并未对叙事何以成为替代性想象的再现途径进行深入阐述。但解读他的相关著作,可以大致发现两条线索:(一)替代性想象关系到想象界和象征界,而叙事是“想象”中的主体尝试与“自我”认同的一种心理功能;(二)文本是人们接触历史的唯一方式,文本是叙事的产物,因此叙事可谓是对替代性想象进行表征的理想途径。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曾将“历史的事先文本化”补充说明为“即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