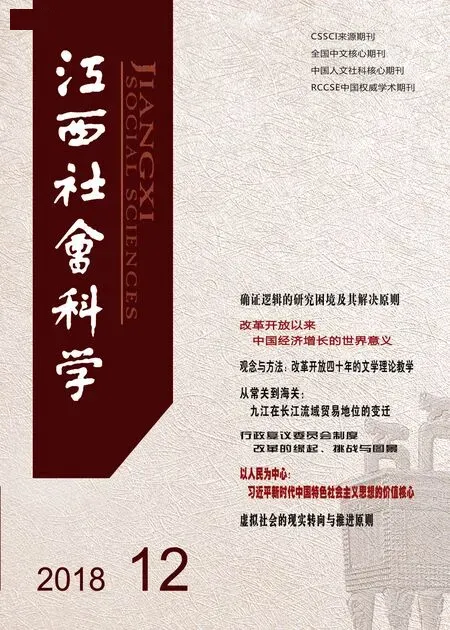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儒家式权利”是权利吗?
2018-02-11
“儒家式权利”思想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好处”“人的尊严”和“义务”三个方面考察“儒家式权利”的基本预设或哲学基础,可以发现,“儒家式权利”不能直接等同于权利,但可以成为对发展现代中国权利有益的“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努力试图从各个层面重构儒学,接榫权利,产生了丰富的“儒家式权利”话语。综观这些权利,有的学者把一个人享有的“好处”等于权利;有的学者把“人的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如李明辉;而有的学者则从“义务”角度思考“作为义务的权利”或者是“通过义务表述的权利”,如赫伯特·芬格莱特、余英时。虽然这些学者对“儒家式权利”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思考,但对这种权利仍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本文拟以“好处”“人的尊严”和“义务”三个方面分析“儒家式权利”,并指出“儒家式权利”不能等同于权利,但可以为发展现代中国的权利理论提供思想资源。
一、作为“好处”的“儒家式权利”的反思
“儒家式权利”的基础,首先涉及“好处”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即享有一项“好处”等于拥有一种“权利”吗?享有一项“好处”与拥有一项权利之间到底有无区别呢?又是何种区别呢?无疑,正如“权利”一词所显示的,“权利”包含了一种“利益”,是一项“好处”,但问题是,它仅仅是一项“好处”吗?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导言”开篇的话就颇具启发:“人权是权利,而不仅仅是一些良好的愿望或主张。称人权为权利不是说,人权所代表的利益仅是愿望或需要;或者这种权利仅是个人应享有的那些利益,或者这种权利仅是社会尊重这种‘豁免’或提供利益的义务。称人权为‘权利’是指人权‘始自权利的’要求,而不是仁慈、博爱、友情或爱的要求;人权无需谋取,也不是奖赏。权利概念意味着,根据一些可适用的规范按照某种秩序应赋予权利所有人的权利;人权概念则意味着,根据道德准则按照一定的道德秩序应赋予的权利被转化并被确认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法律秩序中的法律权利。”[1](P3)另一学者唐纳利也提醒人们要注意享有一项“好处”与拥有一项“权利”这两者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强调拥有一项权利和仅仅享有一项权利的内容,比如拥有食物和拥有食物权或者言论自由和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2](P88)正如拥有食物与拥有食物权不同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在享有某种好处或某些利益时,这种“好处”或“利益”可能并非取决于我们自己,它可能要么作为某种“恩典”或“奖赏”而存在,要么它作为某种不是基于权利的“义务”而存在,因而这种享有就可能会因为随心所欲地给予而随心所欲地收回。
因此,“权利”并非仅仅是“好处”,就在于它具有一种源自“权利”而来的“特殊控制能力”。正如唐纳利所说:“一个人并不拥有由于拥有一项权利而带来的特殊控制能力,一个人享有这些利益的要求也并不具有人权的力量”,“这就是说,他人或政府给一个人提供的好处、利益,不等于这个人享有权利”。[2](P88)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法意》“按语”中精辟地总结过权利的“精义”,所谓权利就是“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3](P971)。
由反观“儒家式权利”的研究,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都将儒家思想关于“民”享有的“好处”解释为拥有“权利”,如《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把对生命的“关切”解释为重视人的生命权或生存权益;孔子、孟子的“庶富教”和“制民之产”等对百姓“厚待”或者“仁政”也被解释为“民”或百姓的经济权利、文化权和受教育权等;“儒家要求统治阶级‘爱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济民’、‘利民’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并明确要求为政者要‘施仁政’。而要‘爱民’、‘济民’、‘利民’和‘施仁政’,就要尊重人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格权、物质生活权等”[4]。这些素朴的看法实质上混淆了享有一个好处与拥有一项权利的区别,唐纳利在评述罗树春(Shu-Chung Lo)的观点时指出:“中国人是拥有这些权利,行使并维护这些权利呢?还是仅仅‘享有’这些权利呢?人们怀疑,充其量也只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罗氏的主张就混淆了享有一个好处同拥有一项权利两者的区别。”[2](P56)
此外,儒家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权利”的实施和实现建立在“不在我、而在彼”的“仁君”“仁政”之“境界”上,因而这些极富“民本”思想的话,看似对“民”的某种“权利”的申论,但在实质上与权利“终究还隔着一层尚待穿透的逻辑上和意志上的膜”[5]。
二、作为“人的尊严”的“儒家式权利”的反思
如果说权利不仅仅是一项“好处”,而是一项“必在我,无在彼”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与“人的尊严”相同吗?根据布鲁姆(Irene Bloom)的研究,“尊严”一词在欧洲出现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人的尊严”这一复合词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在欧洲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民主思潮日益高涨,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仅仅属于少数人的贵族尊严形成对比。[6](P220)可见,人的尊严与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唐纳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这两个概念确实存在着密切的理论联系”[2](P51)。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密切的理论联系”到底是什么?二者能等同吗,即尊重人的尊严就是在主张或支持人的权利吗?
从权利的角度看,拥有权利必然会肯定和尊重人的尊严,国际人权公约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肯定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开宗明义就说:“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第一条也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德国联邦宪法第一条同样写道:“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它。因此,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害与不可让渡的人权是每一人类社群、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7](P47-65)可见,人的权利本身与人的尊严紧密相连,是人的尊严的一种表现方式,拥有人的权利无疑就必然要求尊重人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观念是以对人的尊严的理解为基础的,正如《国际人权公约》所说,人权“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对人的尊严的理解为基础人的权利并非宽泛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而是一种特定的理解。换言之,人的权利是且仅是一种特定的理解人的尊严的方式,其中蕴含的对人独特理解就是“将每个人都视为平等的宝贵的人,并拥有某种从权利与要求的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可剥夺的,甚至可以此反对整个社会的权利。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人而拥有权利”[2](P51)。因此,“人权代表着一系列与人的尊严的特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独特的社会实践”[2](P52)。
反之,从人的尊严的角度看,尊重人的尊严就意味着拥有权利吗?关于人的尊严的概念就含有人的权利的意思吗?又如何来理解“人的尊严”呢?通常而言,所谓人的尊严是指人具有的内在价值人格。就此而言,只要有文明,如希腊哲学、希伯来神学、中国先秦文明、印度文明,就都有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肯认,也就是对人的尊严的敬重。当然,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明都尊重人的尊严,但彼此之间的方式却各不一样。因此,承认和尊重人的尊严从某种意义来说不过是人类文明的表现。正如古希腊的哲学对人的尊严理解与中国儒家对人的尊严理解不同一样,人的权利作为理解人的尊严的特定方式之一,也不同于这些轴心文明的理解方式。虽然都是尊重人的尊严,但不同的人的尊严观却可能对人的权利观念之下的人的尊严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甚至处于相互冲突之中。[5]也就是说,“有许多关于人的尊严的概念并不含有人权的意思,有许多社会制度在实现人的尊严时完全不受人权观念或实践的影响”,“像前现代的西方一样,大部分非西方文化和政治传统,不仅缺乏人权实践,而且缺乏人权观念”。[2](P52)
因此,“伊斯兰教中的‘人权’”“传统非洲和古代中国的‘人权’”等话语或概念的实质主要就是将“人的权利”等同于“人的尊严”。对此唐纳利的考察极具洞见,他指出:“在伊斯兰教中,人权是作为人的尊严讲的”,伊斯兰教“所说的每一种‘人权’或者只是一种没有权利的义务,或者是权利,但拥有者拥有这种权利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人,而是因为他有某种法律或宗教地位”[2](P54)。因此,他在总结伊斯兰教中的”人权”时说:伊斯兰教的社会和政治戒律,的确反映了对人的福祉和人的尊严的强烈关怀,这种关怀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人权概念的一个前提,但决不等于对人的权利的关怀或承认。[2](P54)
厘清了“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的上述关系之后,也就不难分辨儒家“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关系。一方面,正如前文的分析,儒家思想中包涵丰富的“人的尊严”思想,但是,这些儒家“人的尊严”并不理所当然就是人的权利思想。那么,儒家“人的尊严”可以作为“儒家式权利”的哲学基础或者基本预设吗?
李明辉在引用《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西方国家宪法关于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之间关系后,径直得出结论认为:“‘人的尊严’的确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7](P47-65)从表面看,李明辉的结论没有问题。但如果对照我们上述的分析,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把李明辉的结论反过来说,即现代“人权”概念预设了“人的尊严”概念,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李明辉的解释,这一结论就未必正确了。如果只是非常宽泛笼统来说,“‘人的尊严’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深入地追问,“‘人的尊严’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是不是就意味着等于“所有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都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呢?或者换一种问法,具体到儒家“人的尊严”,即儒家“人的尊严”是现代“人的权利”概念的基本预设吗?显然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那么肯定。与上文分析伊斯兰教人的权利类似,儒家“仁—人学”以伦理的方式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因而也就包含着丰富的人的尊严思想。
然而,儒家人的尊严却未必等于人的权利。李明辉在《儒家传统与人权》一文中谈及,他的“目的并非要证明儒家传统中包含现代的人权思想”,这就印证了我们上述的疑惑。儒家人的尊严思想并不能成为人权的基本预设,更遑论儒家人的尊严思想包含现代人的权利思想。在这一点上,金春峰的看法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中国古代“人为贵”的观念引导出来的是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近代意义下的人的权利和个人尊严。[8]因此,“‘人的尊严’是现代‘人权’概念的基本预设”“儒学传统中有关注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其内涵极为宏富,要皆可以成为现代人权意识的哲学基础”等相似的观点,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三、作为“义务”的“儒家式权利”的反思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但未发展出“人权”的概念,连“权利”的概念也付诸阙如。“人权”与“权利”这两个语词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透过翻译而引进的。[9]如果说“权利”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本无”,那么,“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国人怎么能在没有提出这种用语要求的情况下来要求权利呢?”[2](P56)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来致思现代西方通过“权利”概念思考的那部分内容的呢?主流的看法就是通过“义务”。梁漱溟在概括中国文化“要义”时就指出:“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10](P89)更有甚者提出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西方文化则以权利为本位的论断。
结合上文儒家“人的尊严”思想与人的权利之关系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从人的权利来表现人的尊严,它表现的方式正是此处要论述的“义务”。因此,想从弥漫着义务观念的儒家思想中发现人的权利就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正如陈来清醒指出的,如果从作为人的权利或通过权利表达的人权视角去思考“儒家人权思想”,那么,“儒家永远不可能认可此种权利优先的态度”,并因此肯认人的权利。然而,恰恰在这困难的地方,许多学者发现了肯认权利的方式,他们指出,要想发现人的权利,就必须转换视角,即不是直接从权利的视角,而是从“义务”的视角来论证“儒家式权利”,如赫伯特·芬格莱特的“作为义务的权利”、余英时的“通过义务表述的权利”等。然而,问题是,这样可能吗?
芬格莱特通过反思西方人的权利思想,切入“儒家式权利”,认为西方的人权说因把社会界定为一种由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的个体组成的东西而严重地疏远了人的关系:“将人权视为一种自主个体普遍不可侵犯之所有物的立场,的确看起来与孔子的人性观念极不相容。”[11](P146)所以,为了正确地理解儒家式权利,同时也为了解决人权普遍性与非普遍性的两难选择,他提出:“需要‘一种对人权性质的正确解读’。”[11](P147)这种正确的解读就是将权利变成义务。
按照芬格莱特的解释,人的权利概念是与“各种义务”处于一种必然的关系之中。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如果不与各种义务参照并举,一个人权概念便空空如也,毫无内容可言。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任何人都有不得干涉我言论的义务’来替换‘我有自由言论权’,对于这后一句的意思,我们无疑会理解得更为深入透彻。……结果,这就将权利变成了义务。……关于我的‘言论自由权’,它可以反以为‘每个人都负有不得干涉他人言论的义务’”,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赋予权利以独立的存在。我的观点是,问题远比那简单得多。只要提到某个人的权利,就必然意味着他人对其所承担的义务”。[11](P147-14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表达方式的不同蕴含:从权利角度看,人权说使每一个人彼此疏远。我的权利实际上便是一道防范别人侵入我的“空间”的屏障。但是,“如果我们将权利看成是每个人必须对其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便会呈现出来。从作为义务的权利这样一种立场出发,个人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如此诠释的人权学说,肯定每一个人都受制于对他人所必须承担的各种义务的综体(complex)”[11](P149)。
因此,“人权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关乎人的义务的学说。它意味着所有人就其天性来说均处在一个复杂的交互义务网络之中……而把权利看做义务的正确解读,则揭示这一学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社群主义的”[11](P154)。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权利学说完全可以融入儒家思想,进而建立起具有社群主义性质的儒家式权利学说。
余英时和陈来的论述与芬格莱特的看法基本相同。余英时引用西方人权理论史上的一个著名论断为基础,把“义务表述翻译为权利表述”,这一著名论断就是:“用语言难以直白浅显地表述权利……拥有一种权利意味着受益人同时承担对别人的责任,所有关于权利的命题都可直白浅显的翻译成所有关于义务的命题。如果承认这一点,如何表述权利就显得无关宏旨,关键是当我们谈到人权时,便是提出了我们对他人应负有何种义务这一问题,而不是向我们提供任何独立的伦理上的洞见。”[12]据此,余英时认为:“如果可以这样完整地表示权利,即对权利的拥有者而言,权利多少是对他人承担义务的一种复杂约定,而那些义务能够反过来被更高层次的道德律法所解释,那么权利是一种独立的表述的观点显然已经被抛弃,权利涵义拥有了解释性和证明性的道德力量。”[12]
陈来没有解释“通过义务表述权利”的理论基础的问题,而是直接预设了这种可能性:“尽管我们在古代儒家思想中找不到与‘人权’类似的概念表达,但如果把上述了解的重点移向政府或统治者对人民所应承担的义务,那么,类似的关切在中国儒家政治思想中便俯拾皆是了。可以说,在古典儒家思想中是以‘政府义务’而不是‘个人权利’来表达近代人权观念的某些要求的,而这些要求又比较集中在基本生存权利的方面。”[13](P29)因为整个儒学史用义务的表述代替对权利的表述,这也解释了权利概念在儒家传统中缺位的原因。
然而,根据上述的看法,“通过义务表述权利”在逻辑上真的可能吗?首先仍以芬格莱特所举的“我有自由言论权”为例。在逻辑上,如果“我没有自由言论权”,就不可能设立“任何人都有不得干涉我言论的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权利”概念存在时,对“权利”的义务表述,或“将权利概念看成义务”,才能成为“权利”。唐纳利说:义务只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尽管统治者身上的确有许多精心设计的义务,但是,如果不以权利为基础,义务本身也不表明统治者有义务为之采取行动的那些人就一定拥有权利,更不要说证实这些权利存在的了。
另一位学者贾斯汀·蒂瓦尔德(Justin Tiwald)也指出二者关系的不同。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对真正的权利占统治地位的理解是权利的存在本身是使一个行动成为道德的组成成分,而义务或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如果为我兄弟的教育作贡献是我的责任,那么,我仅仅对他有义务。但是,如果帮助他是我的责任,并且道德上允许他通过强制或落实补偿来要求,他就拥有权利。这表明权利的一个核心特点:它是可以被要求的。所以,诉诸责任而非权利,我们就不能说一个受益人可以以他天生的或天赋的权利来要求给予利益。这就是说,他人或政府给一个人提供的好处、利益,不等于这个人享有权利。
其次,“通过义务表述权利”是通过“谁的义务”表述的“谁的权利”呢?具体到儒家思想,根据上述学者的看法,就是通过把“统治者”的“义务”表述为“民”的“权利”。对此,陈来说道:在中国古代,现代人表达的权利并不表达为个人向政府要求的权利,而是表达为主政者必须为人民承担的根本义务和责任。这里保障的“民”,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指人民的集体。如果说统治者的“义务”不是来自“民”之“权利”,它又是来自哪里呢?根据儒家的看法,它最终来自儒家特有的“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进一步又归结为统治者之“仁政”。而一旦排除了源于“民”之“权利”的统治者仁政“义务”,其最终结果就如梁启超分析的,非但不会产生权利,相反“治人者‘其权无限’、治于人者毫无权力,人民也就只有义务而无权利了”[14]。
四、结 语
通过前文从“好处”“人的尊严”和“义务”三个关键词分析“儒家式权利”,笔者认为,三者不能直接作为“儒家式权利”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儒家思想本身及其在建设和发展中国权利时的积极价值,“儒家式权利”仍可以成为对发展现代中国权利理论的有益“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