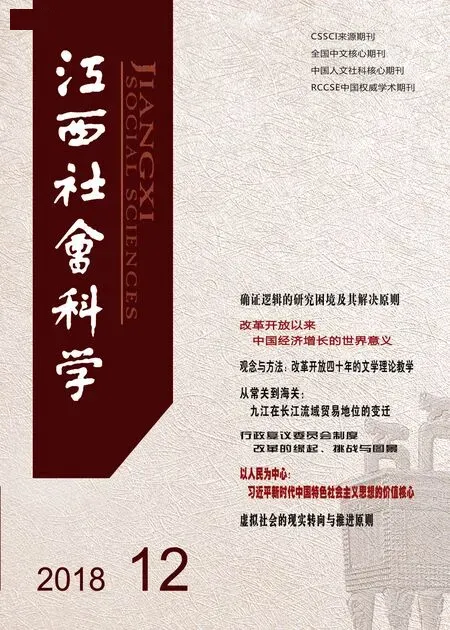确证逻辑的研究困境及其解决原则
2018-02-11
归纳逻辑在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从科学发现向度到归纳确证向度的转变。考察这一转变历程可以发现,归纳确证本质上是关于合理相信的确证逻辑研究。现有主要确证逻辑理论都遇到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难题,要克服这些难题,需要从方法论层面对确证逻辑研究进行系统反思,构建研究需遵循的一些合理性原则,包括:确证研究的行动论视角,避免方法论上的演绎主义,强调证据和假说的相关主题要保持同一,在假说的真理性和解释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聚焦证据的认识论本性和逻辑性质的研究。
自休谟提出归纳问题以来,对归纳的逻辑与哲学研究一直是归纳逻辑和知识论的一个热点领域。归纳逻辑以归纳问题的提出为转折点,逐步从传统向现代演进,其现代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引入概率论和数理逻辑;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研究内容上实现从对作为科学发现方法的研究到对信念确证与辩护研究的转变,即从“归纳发现”向度逐步转向“归纳确证”向度。归纳确证向度的研究在以卡尔纳普和亨佩尔等人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时期达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好的确证定义。由于在代表性确证定义中陆续发现了以确证悖论、绿蓝悖论、彩票悖论为代表的归纳悖论,归纳确证研究的焦点转向归纳悖论的解决,从而掀起了归纳确证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随着葛梯尔问题引发的知识论研究在知识和信念辩护维度的复兴以及21世纪初形式知识论的兴起,作为形式知识论研究主题之一的确证理论研究,有望在合理相信和辩护视角下掀起第三次研究热潮,对这一趋向下的确证逻辑研究进行方法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价值。这些思考主要包括确证逻辑的本性、构建确证逻辑的原则以及研究的重心等方面。
一、确证逻辑的本性是关于合理相信的确证理论
人类最根本的认知目的是形成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因而对理性认知主体至关重要的是,作为认识活动结果的假说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为真?或者说,理性认知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多大程度地)合理相信这些假说?
对这一根本性问题,很多哲学家都进行过讨论。莱布尼兹明确提出,从感觉和经验获得的关于事实的可能真理,要通过先验猜想法,即作为科学发现或形成认识的假说-演绎法。笛卡尔进一步将莱布尼兹作为科学发现的假说演绎法发展为关于归纳确证的假说演绎模型,他认为,关于同一个现象必定有多个相竞争的假说,这些假说都具有猜测性质,它们没有一个是确定的,但有一些是可以合理地相信的。笛卡尔指出,科学家有权力接受那些能成功地解释广泛现象的假说,因为能演绎出所有现象的那个假说不太可能为假。而只要从假说中演绎出来的结论与被解释现象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们是真的。这里,笛卡尔强调的是可以合理相信一个假说的解释原则:如果一个假说能够解释它所衍推的某个现象,那么该假说是可以合理相信的。笛卡尔的这一思想具有从归纳发现到归纳确证的特质,是后来作为确证逻辑的假说-演绎模型的雏形。
现代经验主义者把作为科学发现方法的假说演绎法改造为一种归纳确证的方法。他们认为,通过猜想得出来的假说虽然可以演绎出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但这些假说本身没有经验基础,没有得到证实,因此,要根据假说演绎出推论或预言,然后用经验来决定这些推论或预言是否是对该假说的一种支持或确证。惠更斯在《光论》的序言中对作为确证理论的假说-演绎法的本质给了一个很清晰的表述:“原理是由它们引出的结论来检验的……当用假定的原理论证了的东西与观察中的实验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致时……那么,这当是对我探究成功的强有力的确证。”[1](Pviii)惠威尔认为,假说是运用归纳进行猜测获得的,一个假说提出后,也要按归纳一致加以检验,演绎的作用在于从假说中推出现象,从而确证或检验假说。他说:“假说应当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只有当能预测与构想假说时不同类的事物时,该假说的真实性才能得到确实的证据。”[2](P159)当今确证的假说-演绎模型正是在惠威尔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来的。
从上述关于确证逻辑的早期发展来看,确证逻辑(理论)在其萌芽阶段就关心合理相信问题、假说或信念辩护的理论。在归纳逻辑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归纳确证向度更加明显。
凯恩斯认为,他的《论概率》处理的是两组命题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这种关系是:“在我们认为知道并称之为证据的一组命题和另一组称之为结论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前者所提供的理由,我们指派给结论或多或少的权重……可以把这称之为概率关系。”[3](P5-6)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没有任何命题其自身是可几或者不可几的,同一个陈述的概率随它面对的证据而变化。”[3](P7)对概率的这种说明恰好表明他关注的焦点是信念的合理性问题,即基于一定的证据,相应假说为真的概率是多少。凯恩斯进一步对概率作信念度解释:“设前提由任意一组命题h构成,结论由任意一组命题a构成,那么,如果知道h为合理相信a到程度α提供了辩护,则可以说a和h之间有程度α的概率关系。”[3](P4)由此可见,作为现代归纳逻辑创始人之一,凯恩斯认为,归纳逻辑研究的是认知主体基于一定证据该对相应假说具有多高的信念度。
在归纳逻辑的“归纳确证”向度研究中,以卡尔纳普和亨佩尔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利用其卓越的逻辑分析能力,力图用严格的形式语言就经验证据对假说的支持关系(他们称之为确证关系)进行精密的逻辑句法或语义刻画,以期为某种形式的陈述是否确证某种形式的假说提供一个纯形式的判据。也就是说,归纳确证理论家对归纳确证的研究是从形式的角度而不是内容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确证理论就是确证逻辑。
确证的逻辑研究可分为量化和定性两个进路。量化进路以卡尔纳普的确证度逻辑为代表,他利用概率论和现代逻辑,对两个确证度函数给予了较严格的形式公理化刻画。卡尔纳普关于确证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概率的逻辑基础》[4](P10-30)和《归纳方法连续统》[5](P9-41)中,他在这两本书中分别构造了C系统和λ系统。无论C函数确证系统还是连续统λ系统,都是关于以一定的证据为基础,对假说的合理相信进行逻辑刻画。但这些确证系统面临一些难题,譬如,波普尔指出的“全称假说确证度为零”的问题,逻辑因素与经验因素的权重分配的主观性问题等。为了应对卡尔纳普的确证度理论遭遇的难题,贝叶斯主义者从经验对信念度更新的影响这一维度,利用作主观主义解释的概率,对认知主体为什么可以在经验基础上某种程度地相信假说进行辩护,这就是当今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观贝叶斯确证理论。
定性进路的确证逻辑研究主要以亨佩尔的事例确证逻辑为代表,其主要成果体现在《确证的纯句法定义》[6](P122-143)《“确证度”的定义》[7](P98-115)以及《确证之逻辑研究》[8](P1-26)[9](P97-121)等论著中。整体说来说,亨佩尔的确证逻辑以尼柯德(Jean Nicod)的事例确证概念为基础,力图为经验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确证关系构造一个纯逻辑句法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的核心内容是确证的适当性条件和满足性标准,集中体现在亨佩尔关于直接确证和间接确证的两个定义中。亨佩尔的事例确证逻辑在归纳确证理论中具有经典地位,正如哈勃(Franz Huber)所说:“自此以后,在发展确证逻辑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10](P181)正是在构建其关于确证的逻辑标准时,亨佩尔发现了作为确证非相关难题之集中体现的确证悖论,从而掀起了关于确证逻辑研究第二次高潮的序幕。
上述对归纳确证发展简史的考察表明,确证逻辑本质上是关于合理相信或信念确证的逻辑研究。这种意义上的确证逻辑是指“确证的逻辑”, 而不是“确证性逻辑”。前者是关于确证活动的逻辑机理研究,是对确证活动中体现出的确证概念的精确描述;后者属于类似阿特莫夫(Sergel Artemov)辩护逻辑[11](P477-513)的广义认知逻辑,是以确证为模态算子构造的形式系统。在笔者看来,关于后者的研究以对“确证”算子本身涵义的精确把握为基础,只有合理而精确地把握确证概念,才能构建令人满意的确证形式系统,因此,对第一种意义上的“确证的逻辑”的研究更为迫切。
二、构建确证逻辑的合理性原则
已有的确证逻辑理论主要包括卡尔纳普的确证度理论、亨佩尔的事例确证逻辑、贝叶斯确证理论、确证的各种假说-演绎模型、格莱默尔的拔靴带模型等。这些理论分别遭遇到全称假说确证度为零、确证悖论、旧证据难题、非相干性难题等严峻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题,在准确把握确证逻辑本性的基础上,构建好的确证逻辑还应遵循一些合理性原则。
(一)确证的行动论视角
确证本质上是一项有目的和意向性的认知活动,是科学家和日常主体为其科学假说或信念进行评估和辩护的行动。在构造确证逻辑时,我们应引入行动论视角,将确证看作认知主体有目的地对其认知结果进行评估和辩护的行动。好的确证逻辑应该是一种行动逻辑,它应是对归纳确证这一认知行动的静态描述、近似表征或规范性要求,从而有望避免与认知主体实际认知活动不太吻合的问题。
这种行动论视角在亨佩尔关于假说确证思想中有所体现,但他未自觉地在其确证逻辑中表达这一点。亨佩尔明确指出:
一般说来,对于给定假说的科学检验我们可以区别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执行适当的实验或观察,并随之接受陈述所得结果的观察报告;第二阶段将所给的假说与已接受的观察报告对照,也就是说,确定该观察报告是否对该假说构成确认、否认或无关的证据;最后的阶段或者是根据该确认证据或否认证据而接受或否定该假说,或者不作决定而等待确立进一步的证据。[12](P502)
这里,亨佩尔明显将确证看作科学检验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并且确证活动这一阶段与其他两个阶段不可截然分开。执行第一阶段实际上是寻找相干证据或相干数据,相干是一个相对概念,实验数据只有相对给定假说才可以说相干或不相干。而判断相干实验数据(观察报告)是否确证给定假说是下一步采取相应认知行动的根据,即决定接受、否定还是悬置相应假说。
认知行动与认知主体的意向性、所处认知情境密切相关,在执行确证这种认知行动时应遵行一定的合理性原则。因此,对确证这种认知行动的衡量和评价标准应是合理性,而不是“形式”有效性。如果将确证逻辑看作对确证活动的静态描述,好的确证逻辑应该反映认知主体在实际确证行动中体现出的合理性原则;如果将确证逻辑看作对确证活动的规范性要求,好的确证逻辑需要制定一些认知主体在从事确证活动时应遵守的原则或标准。因此,无论确证逻辑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它需要做的是给出一些合理性原则或标准。
(二)方法论上摒弃演绎主义
确证活动的目标是通过检验和辩护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规律性和解释性的认识。主体的辩护行动涉及主体实际如何看待观察报告与待辩护假说之间的支持关系,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我们不能设定一些纯形式有效的规范,要求认知主体在关于世界的真理性和解释性的认识活动中去执行它们。演绎逻辑是外延性逻辑,它研究的是个体(类)和个体(类)之间的集合论上的属于等关系。而本质上是归纳逻辑的确证逻辑研究的是个体和属性之间关系,也就是说,确证逻辑关注的是某类个体是否具有认知主体在认知上关心的某种属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认知主体可以合理地相信某类个体具有他所关心的那种属性。因此,用纯演绎逻辑来规范确证活动实际上犯了“范畴”错误。
这一点在亨佩尔的确证逻辑和确证悖论中体现得很明显。亨佩尔的确证逻辑的目标是给出一个形式判据,进行确证活动的认知主体根据这一判据来确定观察报告是否确证待检验或待辩护假说。根据亨佩尔的确证逻辑,由于H1“所有乌鸦是黑的”与H2“所有非黑的都是非乌鸦”逻辑等价,它们得到观察报告“个体a是乌鸦也是黑的”同样的确证。但对进行确证活动的认知主体来说,对于H1,他关心的是乌鸦这个类中的个体是否都具有黑色这种属性,而不是任意的个体在是乌鸦的情况下是否也属于黑色这个类,更不是非黑色的个体类和非乌鸦的个体类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演绎要求是不恰当的。
另外,贝叶斯确证逻辑以概率论为工具来刻画确证活动,概率论是一门形式演绎科学,因此,贝叶斯确证逻辑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演绎主义诉求。但是,认知主体在考量某观察报告是否支持待辩护的假说时,并不是通过概率计算来决断。即便对实际认知主体提出这样“严苛”的要求,贝叶斯确证逻辑还必须诉诸一系列经验假定[13](P102-111),而不能仅凭纯形式的概率演算。而作这些经验假定之后,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难题。因此,构建确证逻辑时应摒弃演绎主义倾向,这是由确证活动的本质决定的。
(三)证据和假说的关于性(aboutness)同一性原则
确证悖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不相干证据进入确证程序是确证悖论产生的根源。我们直觉上认为,白粉笔与是否所有乌鸦是黑色的不相干。占主导地位的贝叶斯标准解决方案实质是通过表明白粉笔与待辩护假说“所有乌鸦是黑的”在概率上的非独立性消解悖论。这里隐藏的一个预设是:如果一个观察报告与待辩护假说概率上不独立,那么,该观察报告是该假说的相干证据。但是,这里的“直觉上的相干”与“概率上的相干”是两个不同的“相干”概念。前者要求假说和相应证据(经验内容上)所关于的东西相同,而后者显然没有这种认知上的经验性要求,而只是“形式”上的要求。这可能是为什么贝叶斯确证逻辑在解决确证悖论时尽管形式技术上“令人信服”,但同时会遇到“黑色的非乌鸦”不确证而“非黑色的非乌鸦”确证假说“所有乌鸦是黑的”这一反直观的严峻难题。这一难题似乎意味着一个不是黑色的东西在乌鸦假说的确证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假说-演绎确证逻辑也遇到非相干证据的困扰。提出假说-演绎确证模型的各种修正版,主要是为了应对证据的非相干合取问题和非相干析取问题。[14](P61-65)作为该模型最高成就的自然公理化模型重点关注假说的“内容”,但它对假说内容的刻画是形式的,即假说的内容就是该假说的逻辑后承集,而不是将假说的内容理解为假说表达的经验信息或经验内容,但确证活动关心的却正是这种经验内容,这就注定了该类模型必然会遭遇非相干性和其他难题。
因此,在构建新的确证逻辑时,要重点刻画作为证据的观察报告和待辩护假说在经验内容上的相干性。更具体地,要关注它们两者谈论的主题(subject matter)、它们涉及的内容是一样的。当然,这需要对如何确定命题涉及的内容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是语义或语用学研究而不是逻辑句法学的研究。亚布罗已经这方面做了很出色的工作。[15]
(四)包容真理性和解释性
人类在认识世界时追求的是对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一方面,这种规律性认识最好是真理,即最好是反应世界本身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最好能解释世界上的某类现象。科学家常说科学始于问题。人类有探知世界奥秘和反常现象的本能,对反常现象作出科学和合理的解释是科学活动的重要目标,从而也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目标。因此,构造假说有两大主要目的:发现关于世界的未知规律和解释世界中的反常现象。从而,执行归纳确证活动的认知主体对假说的评价与辩护应该有这两个维度的考量。有的确证主体更关注假说的真理性,有的更关心假说是否能解释他所想解释的现象,而有的则同时看重这两者。
在科学方法论研究当中,真理性、解释力、简单性、逻辑一致性等是公认的假说选择与评价的方法论原则。作为确证主要理论之一的假说-演绎模型,早期是关于科学发现和科学解释的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反常或令人惊讶的现象能从某假说演绎地推出,那么,该现象就得到了该假说的解释,这实质是亨佩尔提出的科学解释的演绎-律则模型。而强调假说的解释功能的早期假说-演绎模型则是由笛卡尔提出的,他将假说的解释性功能与假说的真理性关联在一起:“如果一个假说能解释这些现象,那么它是假的是不太可能的。”[16](P33)亦即该假说很可能是真的,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该假说。利普顿继承了笛卡尔的这一思想,他提出的最佳解释模型是通过确定相互竞争的假说对现象的解释程度来确定该现象最好地支持哪一个假说。[17]也就是说,把假说解释现象的能力看作该假说真理性的标示。好的确证逻辑应该适当吸收这些被广泛承认的方法论成果,在构建评价证据对假说的确证力(确证度)的标准时应结合确证主体的认知意图给予这两者相应的权重。
三、确证逻辑研究重心的证据转向
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确证逻辑研究都遭遇到证据问题。事例确证逻辑面临不相干证据问题,假说-演绎确证逻辑遇到证据的非相干合取和非相干析取问题,而贝叶斯确证逻辑则饱受旧证据问题的折磨。
关于归纳确证的研究现状是,无论代表性确证逻辑还是代表性悖论解决方案,都没有给予证据研究足够的关注。确证逻辑的研究范式基本是确证关系范式,即力图为证据和假说之间的“支持关系”构建一个精确的说明。进一步,它们将这种支持关系理解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亨佩尔明确说证据和假说之间是逻辑关系,他构建的确证逻辑旨在为这种逻辑关系给予精确的形式说明;假说-演绎确证逻辑旨在通过某些限制用逻辑衍推关系来刻画确证关系;贝叶斯确证逻辑是利用概率论这种数学形式科学来刻画这种支持关系。正因为它们都没有证据视角,都遭遇证据方面的难题。作为归纳确证第二次研究高潮的主要议题,归纳悖论的解悖方案也大都没有证据视角。例如,确证悖论标准解决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概率工具来说明白粉笔和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有概率上的依赖关系,并将这种概率论上的依赖关系解释为支持关系或确证关系。绿蓝悖论的研究范式是作为确证关系之关系项“假说”的范式。这种范式之下的解悖方案关注的是假说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不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鉴于没有证据视角的确证逻辑和归纳悖论解悖方案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将研究重心转向作为确证关系之关系项的“证据”可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证据的多维研究对解决归纳悖论、构建确证逻辑和更一般的信念辩护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对证据的较全面研究包括对证据的本体研究、认识论研究、逻辑研究。对证据的本体研究主要讨论哪些本体论“成员”可以作为证据。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证据的命题观,即只有命题可以作为证据。认知主体的感觉经验或知觉能否作为证据?具体实物,譬如一把带血的尖刀,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证据是否是心智状态?证据的认识论研究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是否只有知识才能作为证据?主体对具有很高信念度的命题(或通常所说的信念)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证据的新颖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论意义和功能何在?回答这些问题对归纳悖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证据的逻辑研究对确证逻辑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证据是否具有传递性或逆传递性、对称性?例如,从证据的视角来看,亨佩尔确证逻辑中的等值条件和特殊推论条件衍推证据具有传递性。证据是否在合取、析取和蕴涵等逻辑运算下封闭?证据的证据是否是证据?等等。
四、结 语
归纳逻辑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归纳确证本质上是关于合理相信的逻辑研究。由于现有研究成果都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从方法论层面上对确证逻辑的研究进行系统反思尤显重要。这种反思的启示是:确证的研究需引入行动论视角,在方法论上避免演绎主义诉求,强调证据和假说涉及的主题要保持同一,在假说的真理性和解释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聚焦证据的认识论本性和逻辑性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