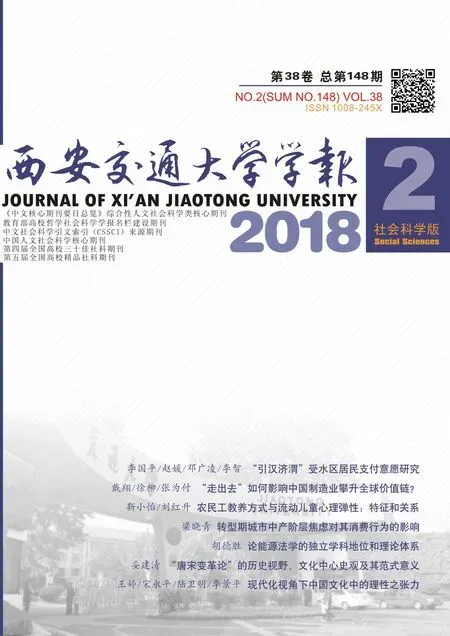霍布斯论绝对主权及其挑战
2018-02-10唐学亮王保民
唐学亮, 王保民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19—20世纪之交,诸多学者掀起了一股持续至今的霍布斯研究热潮,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虽然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以及诸如人性论、自然状态论、权利论、义务论、契约论、国家论、宗教论、语言论甚至形而上学论等研究主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而言,柯利(Curley)的判断是切中要害的,“他(霍布斯)的最伟大的著作经常得到引用而不是细致、彻底的阅读”[1]8,其中对他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以及以讹传讹的成分并非少见,尤以他的绝对主权理论等为甚。无论是霍布斯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学者,由于方法、态度、意识形态等原因,大都无法接受这种主权绝对性的主张,典型者莫如洛克,“这就是认为人们竟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2]。许多学者认为他的主张无法解释诸如三权分立宪制以及现代世界普适性的法律之治等类似的现实政法问题,然而问题真是这样的吗?霍布斯绝对主权理论的完整内涵是什么?他是如何论证的?该理论能否回应现代法律理论和制度对其提出的挑战?无论为了专门的霍布斯研究,还是为了厘清现代一些基本公法学命题,以上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本文在综合原典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还原霍布斯绝对主权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及其论证路线,进而站在霍布斯主义(Hobbesian)的立场上,尝试回应和反诘对该理论的几个主要挑战。
一、主权绝对性及其论证
著名的霍布斯学者哥德斯密斯(Goldsmith)、马克内利(McNeilly)和汉普顿(Hampton)等曾讨论过霍布斯的主权绝对性理论所包含的内涵及其论证思路,但是在笔者看来,他们只把握到了该理论所涵括的部分维度,比如永恒性、不受限制性、不可分割性等,而这些研究对于深刻理解整全的霍布斯绝对主权理论是不够的。通观霍布斯的前后期著作可以发现,其绝对主权理论中所谓的“绝对”(absolute)主要指的是主权者意志的不受外在限制性和自由性,这种外在限制包括权力、法律和宗教等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本文将其含义及论证归纳为六个方面*学术界一般认为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在根本的意义上源自主权者的绝对代表身份,本文之所以没有阐释霍布斯的授权、人格、代表等蕴含主权绝对性的概念,一是因为这在中外学术界已得到较为成熟的研究,二是因为霍布斯的授权概念受到他的自然权利学说的宰制,存在一个不能放弃、不能授权的一个权利缺口,如此一来,在国家人格的拟制以及代表绝对性的设置上也就相应存在某种不完满性和张力,因此按照这个思路论证主权绝对性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主权的最高性及其论证
霍布斯在不同的著作中都表达了主权不受限制性的观点,这也是许多学者批评其主权绝对论的焦点所在,那么,他的这种观点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这种不受限制性所要表达的第一个意思即是主权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最高性和末端性。霍布斯在《法律原理》中做了一个著名的类比,即“主权在一国之中的绝对性就像国家成立之前每个人都拥有的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绝对性一样”[3]114。这一类比所要传达的意思主要有两个:一是主权具有自然性,这点将在下文中予以详细阐释;二是主权在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性,正因为它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受到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在这点上它是自由的。在《论公民》中,霍布斯进一步补充了这个类比,他说,“显然,在每个国家都有某个人、委员会或议事会(court)根据权利对其公民拥有的权力和他们在国家之外对他们自身拥有的权力一样大,也就是,是最高的和绝对的”[4]187。这与上段引文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霍布斯补充了一个关于主权自由性的重要说明,即主权“仅受国家的力量和武力自身而不受任何其它的限制”,因为在《论公民》里霍布斯明确地把自由定义为“不存在运动的障碍和妨害”[4]216,而仅受运动物体自身内在限制的这种限制并不是霍布斯所说的“运动的障碍和妨害”,因此它就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是自由的。从以上两段的类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霍布斯所指的不受限制性,并非如许多学者根据概念所设想的主权者可以恣意妄为、为非作歹等,而首先是指主权的最高性和自由性。
那么,霍布斯是如何论证这种主权最高性的呢?他除了根据授权理论从正面阐释该项特征之外,还额外地采用了一种假设性、否定性的“倒退”(regress)论证路线。在前述《论公民》的引文之后,霍布斯紧接着说,“如果他的权力受到限制,那么这种限制必然来自某种更高的权力。因为规定这种限制的人必然比受他们限制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这种限制权力的权力要不是不受限制的,要不是再受到更大的权力的限制。这样一来,我们将能推出一个除了受全体公民的力量之和外不受其它限制的权力。这一权力就被称作最高的命令”[4]187。这一推导出来的最高权力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主权,所以严格来说,霍布斯并不反对限制权力,但是根据这种形式主义的论证思路以及他独特的定义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根据我的定义,主权是位于权力巅峰上的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所以那些受到限制的权力不是我所说的主权。但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所采用的论证方式是纯形式直线主义的。霍布斯学者哥德斯密斯总结这种路线具备两大特征,即“等级性(hierarchy)”和“闭合性(closure)”[5]。按照这种论证理路,如果我们把各项权力排列起来,它们就会形成一条存在等差秩序的直线形状,这条直线存在刻度上的高下之分,一个权力要么大于另一个权力,要么小于另一个权力,而不可能出现相等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分立与制衡,对霍布斯来讲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三权之间并不呈现直线排列状态,与此同时,这条权力的直线并不是无限的,因为人类的权力不可能是无限的,其必然存在一个直线的顶端或末梢,这个顶端或末梢就是权力的巅峰,而这个巅峰就是霍布斯定义的主权概念。所以从纯粹形式和事物的定义上说,霍布斯的这种论证是合理的,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据霍布斯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直线型的论证思路,在主权前面加上“绝对”二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多余的,“绝对仅仅在于确保符合主权的核心概念(等级与闭合)”[6]423。
(二)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及其论证
对霍布斯来说,主权绝对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绝对主权的一个含义所在[7]。霍布斯极力反对和不能理解主权意义上所谓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思想,认为这会导致主权的分裂与国家的解体,“分割国家权力就等于分解国家,因为分立的权力相互摧毁”[1]214。那么,这种论断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根据霍布斯的主权定义,如果存在三种最高权力的话,那么就存在三个主权。霍布斯并不否认存在三个主权的可能性,但是在他的理论谱系中,三个主权就是三个国家,“事实是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三个独立的宗派,不是一个代表,而是三个”[1]217。这从前述关于主权的纯形式的直线等级式的定义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主权体系之内不可能存在三种相等或者不存在高下之分的权力,如果有的话,那就说明这三种权力分别都是最高权力,也就是三个主权,三个主权也就是三个国家,但在一国之内存在三国,实际上就是政出多门,国将不国,就是国家的解体,回到了自然状态。其次,从技术层面看,这三种权力完全可能甚至必然会出现冲突,因为根据霍布斯的人性论,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人类的一般倾向就是对一个个权力的经久不息的追逐,至死方休”[1]58,而权力在霍布斯那里不是一个绝对性而是一个相对性和比较性的概念,“一个人的权力抵抗和阻碍另一个人的权力的效果:权力就是一个人超过另一个人的权力盈余。因为平等的权力相互对抗和摧毁;它们的相互对抗就被称作竞争”[3]48。因此,人们或出于安全,或出于虚荣等需要,就会出现人人争相扩大自己的权力以求得权力比较中的盈余,也就会出现冲突[8]102,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一种权力来解决这种冲突,而这种权力,或者是凌驾于那三种权力之上,或者属于三者之一,如此一来,这个解决冲突的权力才是最高权力。根据霍布斯的定义,这才是主权,其它三种或者两种权力就不是主权。第三,从实效性上讲,自然状态之所以人人为战,根本原因是因为缺少一个大家都畏惧的共同权力,也正因如此,才有通过相互信约建立主权的契约建国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建立的主权又被分割,进而被弱化的话,人类的悲剧将很可能因为没有强大的公共权力的保护而重演。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地说,“如果他(主权者)转让了国民军事权的话,那么他保留的司法权就会因为缺乏法律的执行而成为无效的(in vain);或者如果他放弃征税(raising money)权的话,那么国民军事权就会成为无效的;或者如果他放弃对学说的统治权的话,那么人们将会因为害怕魂灵(spirits)而起反抗”[1]115,由此不难看出,在霍布斯看来,权力的分割首先意味着权力的弱化,伴随这种弱化而来的是主权者所保留的权力因为缺乏其它相关权力的支撑而导致的虚无,所以在主权的层面,霍布斯认为完全的三权分立至少会导致主权的弱化乃至解体,在这一点上,霍布斯步博丹的后尘,后者明确提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9]146。
(三)主权的自然性及其论证
根据霍布斯的理论,自然状态之所以是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一个“孤独、贫穷、猥琐、残忍和短命”[1]76的状态,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不关联任何义务并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所以他们要想获得和平的生活,必得通过信约放下自然权利以建立代表性的主权来保障公共安全。这是霍布斯契约建国的基本程序,如此一来,主权似乎就只是通过授权程序而出现的,实则并非如此,因为霍布斯曾在多个地方指出,主权是主权者享有的自然权利,并且也正是因为主权不仅是授权的结果,它本身还是一个自然权利,所以这个维度的主权就更能体现其绝对性。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权利是“每个人为了保存他自己的本性即生命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运用自己的权力的自由”[1]79,它具有自治性、不受限制性以及无义务相关性等特征,因此是绝对的。
那么,霍布斯是如何论证主权自然性的呢?他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并且在正面论证里充分运用了其方法论中的证明法和经验例证法。关于正面论证,其有两个主要依据。一是契约法理:霍布斯所设计的社会契约的基本结构是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作为契约的当事方,未来的主权者作为第三方受益人,正因为未来的主权者不作为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受权利转让的影响,也就是说其在自然状态中原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受到触动和影响,因此,在进入政治社会后该自然权利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主权者享有自然权利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法理依据。二是主权者惩罚权的性质:主权者惩罚权不可能来自公民的授权,因为惩罚、伤害的权利属于霍布斯所谓的基本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具有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属性,正因如此,在建国契约里就不可能包含转让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的条款,所以人们不可能授权主权者惩罚自身。霍布斯学者高希尔为了霍布斯授权理论的圆融,天才般地提出一种修正的授权理论,认为“每个人所授权的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其他人的惩罚。当主权者惩罚一个具体的人时,他的行为不是基于该人而是基于所有其他人的授权”[10]148。这虽然是一个精致的设想,但是它一方面直接违背了霍布斯的意图,缺乏文本的支持;另一方面会造成社会契约的结构出现裂缝,因为在主权者每实施一个惩罚行为时,契约的当事方至少会出现一个缺口,并且每次出现的缺口还不一致,这样一来,似乎每一次惩罚都在新订一个新约,这与霍布斯所设想的一劳永逸的社会契约法理是相悖的。与此同时,霍布斯还从相反的方面进行否定性的论证。假如主权者不享有这种自然权利,而是像洛克一样,把主权者作为契约的一方,并接受人民设置的各种条件,这是现代学者普遍青睐的宪政模式,即主权是有条件的,受到约束的,那么对霍布斯来说,至少将出现两方面的困难。首先,假如主权者与作为整体人格的公民,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民签约的话,这种契约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为在主权者出现之前,人民集体的人格由于缺少承载者而成为空中楼阁,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人民的人格是由主权者承担的,或者说主权者就是人民。其次,假如主权者与其公民分别签约的话,姑且不论该主权者是如何产生出来的,结果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或更多的人)主张在主权成立时,主权者违反了信约,而其他一些人(或一个人)或者主权者自己却主张没有违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法官来裁决这个争议,所以就再次返回到了自然状态”[1]111-112。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在主权者和公民之间存在一个对主权者的约束条款或者条件的话,那么该条款在发生争议时,要么无人出来解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返回到自然状态的情况;要么出现权威性的解释者和裁决者,此时这个解释者和裁决人对霍布斯来说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因此,对霍布斯来说,对主权者的约束性条款或条件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无效的。当然,这里享有自然权利的主权者只可能是公共人格意义上的主权者或者主权者的公共人格而不可能是其自然人格,因为作为主权者的自然人或者说主权者的自然人格是参与契约过程的,其在被根据多数决定原则选举出来承载公共人格之前无法被独立出来。
(四)主权的永恒性及其论证
主权绝对性的第四个内涵即是主权的永恒性。主权的永恒性不是指主权是永远不朽的,因为“可朽的人所造的东西没有不朽的”[1]210,而是指除非主权者自己抛弃主权或指定接班人,否则其他任何的人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主权,变更政府形式,废除主权者或另立接班人。关于主权的永恒性,霍布斯与其前辈博丹也是如出一辙。因为主权者能够合法地处理继承问题,因此,只有主权者才能通过赠与或者出售等方式将主权赋予其他人[1]126,也只有在此时才会发生主权的变更。这就是说,主权相对于主权者来说,未必是永恒的,相反,它是可处理、可抛弃甚至可交易的,但是对于公民来说,主权却是永恒不能擅自变动的,主权并不受制于他们的意志。假如公民可以通过新约自行变动主权的话,那么,站在霍布斯的角度将出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的层次,即一个、几个或者多个公民能否另立新约,更改主权;二是全体的层次,即全体公民能否经由全体一致原则,更改主权。
第一,个体的层次。假如作为个体的一个、几个或多个公民试图通过新约变更主权的话,那么从规范性的层面讲,他或者他们将违反相应的义务,行不义之事。霍布斯意义上的公民承担双重的义务,一是对其他公民的,一是对主权者的。如果他们另立新约的话,首先将破坏公民之间的契约义务,构成己方或者《利维坦》中所说的他方的违约,那么根据霍布斯的定义,违约即是不义行为。其次将违背对于主权者的义务,因为“他们已经把主权给予承当他们人格的人,因此,如果他们废除他的话,他们就是取走属于他的东西,这也是不义的”[1]111。再者,如果因这种变更主权的行为而被惩罚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是这种惩罚的原作者,而“一个人因其所做之事,根据自己的权威而被惩罚的话,他就在行不义之事,根据这一点,他同样是不义的”[1]111。所以,从规范性的层面上讲,公民有永远服从一个既定的主权者的义务。从实然性的层面看,公民能否废除主权者呢?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权威,其包含权力的层面,带有一定实效性的维度,如果公民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致可以推翻主权者的话,那么,根据这种权力的实效性,他们是可能变更主权的。但是,这种权力至少要比主权权力大,而主权的力量依赖公民特别是科层制官僚的协助,因此,从实然层面讲,参与新约反叛或者革命的人,在数量上必须要大于协助主权者的人,如此,变动主权的行为才有可能。
第二,全体的层次。如果从规范性层面看的话,即使公民通过全体一致原则另立新约,变更主权,废除既有主权者,他们也仍然如个体公民一样,行三重不义之事。但是,如果从实然层面讲,全体公民经由一致原则——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可以废除主权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全体的力量必然大于主权者的力量,有能力变更主权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全体一致原则”视为主权者没有能力继续保护其公民的情况,按照霍布斯的保护—服从理论,此时,公民可以弃暗投明,另投明主以求保护。虽然这将出现权利与义务的吊诡现象,因为霍布斯明确说过,即使在这个时候,主权者的权利依然具有规范性,但与此同时,公民却没有义务服从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反对革命的权利,但是承认革命的事实,这中间的断裂由实然性的权力进行链接,并且也只能如此,因为根据霍布斯所设计的契约模型,该契约只有生效时间,必定缺乏规范性的失效或可撤销时间,后者只能依赖实然性的保护现状进行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学说中含有一定的“事实”(defacto)理论的因子[11]。
(五)主权的吸附性及其论证
主权绝对性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即是主权的吸附性。所谓主权的吸附性,指的是在主权国家之内,私人的良心、判断、价值观等被主权的公共性所吸纳并由其权威地予以表达,私人空间受到公共空间的极大挤压。根据霍布斯的理论,自然状态之所以是一个战争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对自由,也即绝对私人性的缘故。自然状态是一个绝对私人的状态,每个人只服从和品鉴自己的价值观、良心、判断乃至人格倾向,没有任何义务和兴趣关照他者以及与他者或者公共生活相协调,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即使自然状态中存在自然法,也就是道德,但对霍布斯来说无论成文还是不成文的法都需要解释,而未经规训的自然人基于各自的激情和私人理性,必然得出各自不同的解释,因此必然会形成道德相对主义。霍布斯的解决途径是建构强大的公共性的利维坦,由它来代替私人做出判断和进行理性的推理。所以,霍布斯的利维坦的目的不仅在于吸附分散的私人力量,更是要吸附私人的意志、理性、观念、判断等等以消弭差异,实现和平与和谐,这突出地体现在《比希莫特》一书中。
此处主要以《利维坦》为例来集中阐释这种吸附性。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以下学说都属于妖言惑众的歪理邪说,易使国家发生病变甚至解体。第一,“每一个私人都是善恶行为的法官”[1]212。这一理论是霍布斯分析过的典型的自然状态的理论,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案件的法官,他们没有任何义务服从别人,但在政治社会中,情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在这里,公共性的市民法是一切善恶行为的判断标准,法官则是作为国家代表的立法者,从他关于国家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正面地得出这种结论,但霍布斯往往并不满足于正面的推论,还要从反面演绎其恶果。霍布斯说,“根据这一错误的学说,人们易于相互争辩,并对国家命令提出质疑,然后再根据他们认为的合适的私人判断来决定服从还是不服从这些命令。因此,国家遭到分离和削弱”[1]212。实际上霍布斯要说的是,这样一来国家又复入自然状态,正因如此,在一个价值相对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国家的整合亟需公民宗教的支持,否则,国家必然走向一盘散沙甚至衰亡。第二,“违背良心的所有行为都是罪恶(sin)”[1]212。霍布斯反对这种私人良心的论证思路与前述反对私人判断的论证思路是一样的,即这一教义适用于自然状态而不是政治社会,因为在那里私人良心是罪与非罪的标准,但是在政治社会,私人良心没有用武之地,作为公共理性的法律才是统一的标准。第三,“信仰和神圣不是通过研究与理性,而是通过超自然灵感或注入(infusion)而获得”[1]212。如果个人可以声称通过神秘的超自然灵感获得信仰与神圣的话,那么,根据交互理性的自然法,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做如此的声称,这样必然陷入人人为战的状态。而且更令霍布斯担心的是,既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声称获得信仰与神圣,那么作为公共性的法律的功能必将受到削弱甚至被虚无化,人人将按照自己声称的信仰和神圣进行行动,一如当下的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这样的话,自然状态必将再次出现在眼前。所以,霍布斯必须极力转化这种私人性的超自然神启,这也是《利维坦》整个下半部分的任务,他期望把主权者,特别是其市民法,立为圣俗两界的共同标准。
根据主权的吸附性可以看出,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意图或者说理想存在一个吊诡现象:一方面他要通过自然权利论的理性和激情的启蒙,确立现代自由政制的个体根基[12];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膨胀公共性,萎缩私人性,使人民大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无思的一大堆,并且惟其如此,他的类似于柏拉图言辞建国的利维坦的乌托邦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品性。
(六)主权的统一性及其论证
在霍布斯看来,主权绝对性一个重要且迫切的方面即是其统一性。所谓主权的统一性,指的是圣、俗的统一,即世俗主权与宗教主权的统一。霍布斯的宗教观可谓是霍布斯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我们无法彻底廓清霍布斯究竟的宗教观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主张主权的统一,由世俗的主权者一体代表圣、俗两界。通览霍布斯整个哲学体系可以发现,其政治与法律哲学主要针对的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以长老派、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宗教神学和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法学,其中反传统宗教神学的部分尤其显著,不但在其主要著作中都有所阐释,更是占据《利维坦》整整一半的篇幅。其实,建构涵摄教权在内的一体化的世俗主权,不仅是霍布斯的主要理论关切,也是自博丹以降的学者们共同的重大关切,在霍布斯主要的政治哲学出版之前,类似完整的主张既已见于1632年罗马法法学家唐宁(Downing)的著作之中,他宣称“宗教必须和‘世俗(civil)国家’一样认可英格兰国王为‘最高的政治(civil)领袖’”[13]。
霍布斯虽然宣称“利维坦”拥有人类所能创造的最伟大的力量,但就其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言,世俗国家比起教会来说要逊色得多,因为人们比起可见的力量,更畏惧不可见的力量,比起眼前的惩罚,更畏惧永恒的惩罚。霍布斯引用《圣经》中“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来指明教权可能对世俗主权构成的威胁或教权与俗权的分裂,因为这种威胁和分裂将造成权力的分割,进而对国家的健康发展构成致命的威胁,“这种俗权与灵权的分离只是言辞而已。通过与另一个间接权力分享与同一个直接权力分享是一样的,权力在实际上都被分割了,并且对任何目的来说都是一样危险的”[1]392。以惩罚权为例,世俗主权者的极端惩罚无非是死刑而已,但是宗教中所宣扬的永恒的折磨(eternal torture)比死亡更恐怖,所以人们更害怕的是牧师而不是国王[14]。既然教权与俗权不可分割,那么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因为根据前述形式的直线型权力论证思路,没有人能同时服从两个主人[1]128,教会派人士主张俗权从属于教权,而霍布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教权从属于俗权。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对于宗教与政治之间张力的解决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实现君权和神权的分离:事实上恰恰相反,霍布斯重新将其一体化,使‘上帝之国’和‘尘世之国’在神学上统一起来,同时在‘尘世之国’或在‘现今世界’这个阶段,实现神权服从君权”[15]。
那么,他是如何实现这种统一以及教权对俗权的服从呢?首先,霍布斯把宗教自然化和政治化。在宗教的起源上,霍布斯消解了其神圣和神秘的元素,他认为就上帝作为永恒、无限和全能的存在而言,其是自然或哲学推理中的第一个原始的推动者或者第一因,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人格神,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上帝就是一个哲学化的上帝。就宗教的具体起源来说,他认为鬼的观念、对第二因的无知、对人们恐惧的事物的投入以及把偶然现象当作前兆,是宗教产生的自然种子[1]66。如此一来,宗教就成了人的一种发明,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是人们内心恐惧的产物,如果联系霍布斯对政治的定义的话,就能明显地看出,在霍布斯那里宗教与政治具有同构性,因为二者都是人为的现象和恐惧的结果。第二,霍布斯把“上帝之国”世俗化。霍布斯把上帝的王国分为自然的王国和先知的王国:在前者之中,上帝因为不可抗拒的权力,经由自然理性和自然法进行统治,而自然法本身具有“自我谦抑性”[16],其要求服从市民法,也就是服从世俗主权者;在后者之中,上帝因为契约的缘故,经由诸如摩西这样的代治者进行统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上帝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如此一来,摩西这样的代治者享有的权力就不是教权,而是世俗意义上的王权或主权。所以,在上帝的王国里,俗权是高于教权的。第三,霍布斯把《圣经》政治化。关于《圣经》根据什么权威才能成为律法这个问题,霍布斯明确认为是主权者的权威使得《圣经》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其它的无论公共还是私人的权威都不可能使之实效化。因此,《圣经》篇章的确定以及解释等等,都由主权者进行权威决断。第四,霍布斯把基督的职分空虚化。霍布斯把作为上帝独子基督的职分分为三个阶段,而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即基督在将来的荣耀中重新降临人间,对所有人进行最后审判时,基督才切实地实行统治的职能,也即作为主权者存在,但是他的这个荣耀的国不是现今的世界,因为基督明确宣称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并明确说在这个世界,即现今的世界,要服从世俗的主权者,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教权至上的论证理路。第五,霍布斯把教会和教皇附庸化。霍布斯重新对教会进行定义,“宣誓认信基督教并结合在一个主权者的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其在主权者的命令下,应当聚集起来,没有这种命令,其就不应当聚集”[1]316。正因为教会附庸于主权,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服从的教会。教会附庸化,必然会导致教皇的附庸化,因为教皇是基督教的头,没有普遍教会,那么教皇也就不再可能凌驾于主权者之上,恰恰相反,教皇权力却来自主权者,霍布斯具体地考察了罗马帝国时期教皇权力对于主权的依赖性。第六,霍布斯简化人类得救的条件和解构“黑暗的王国”。霍布斯大大地简化了人类得救的条件,他认为只要遵守神法和相信耶稣是基督,人们就可得救[1]407,并在《利维坦》中“论黑暗的王国”部分,着重解构经由对《圣经》的误解、外邦的魔鬼学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导致的撒旦的王国,这就从反面解除了公民由于恐惧该“黑暗的王国”而对世俗主权的背弃。霍布斯正是通过以上程序和方法,步步为营地解除教权对于俗权的威胁,并把其归附于世俗主权之下,至此,实现了主权的统一。
二、对几个主要理论挑战的回应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甫一面世即遭至大量的批评,很多学者或者试图对其进行柔化甚至阉割化处理,要么让主权者接受法律的约束,要么干脆杀死主权者,把国家改造成一个无头的、去政治化和中立性的规范性法律体系;或者对其提出严峻的挑战,声称该理论无法回应现代社会一个决定性和常识性的诸如美国的三权分立这样的宪政体制,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在本节中,笔者将根据霍布斯的理论,试图站在他的立场上考察其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回应这些改造和挑战。
(一)主权是超越法律的吗?
许多学者,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下的学者,反对绝对主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主权者的超越法律性,他们要做的就是给主权设置一个羁绊,使主权者戴着镣铐跳舞。实际上霍布斯早期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他在《论法律》一文中说,人法就是“直接(straight)和完美的规则,经由其适用,正确与错误得以发现并相互区分……所有法律的真正目的都在于在我们之间规定和树立秩序和政府,我们有义务服从而不是挑战其管辖;一如过去,法律是我们要服务的国王,是我们要服从的首领,是那些使我们生活中所有行为得以和谐和安顿的规则”[17]105。并且还明确地说,“法律应该成为人的统治者,而不是人应该成为法律的主人”[17]111。这是一个多么政治正确的法治概念!但是到了成熟期,霍布斯一改从前,把法律视作主权者的命令,“法律就是那些拥有主权的人或人们对他或他们的公民所公开、明确地宣布的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命令”[18]7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法律与主权的地位在前后期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契约论思想。把法律视作人为的产物、意志的表现以及人定的命令与规则,在现代是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观念,霍布斯想要了解的关键问题是这里的“人”是谁?不是所有人的意志都可立法,只有权威的意志才可立法,而权威的意志只有通过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主权建国这样的途径才可确立,因此,对霍布斯来说,这里的“人”只可能是拥有人造权威的人,也就是主权者,只有主权者的意志才可立法,也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服从,所以他在《利维坦》的法律定义中才明确地说,“从总体上说,法律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也不是任何人对任何人的命令,而是他对一个先前就有义务服从他的人所发布的命令”[1]173。根据霍布斯的契约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引文中“他”指的只可能是主权者,那些服从的人是公民或臣民,而先前义务则是规范性的契约义务。
正是由于只有权威的主权者的意志才能立法,那么顺理成章,主权者从根本上就处于法律之上,因为说一个人受制于自身的意志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意志不过是“在斟酌中,直接导致行动或者不行动的最后一个爱好或者嫌恶”[1]33而已,既然人不受自身的束缚,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受到意志表现的法律的束缚,“因为有权制定和废除法律,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废除令他烦恼的法律和另立新法的方式使自己摆脱这种束缚”[1]174。然而,主权者在实体上和本质上不受制于其立法,并不意味着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不受其法律的约束,因为霍布斯意义上的立法和法律不是瞬时万变、捉摸不定的任意行为,而是要遵从一定程序和形式的要求,“法律是一种命令,命令存在于发命人通过声音、文字或其它的同等充分的证据的形式对其意志的宣布或明示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只有对那些有能力注意到它的人,国家的命令才是法律”[1]177,“法律一旦被制定出来,轻易地不要改变它”[17]113等等。这也就是说,霍布斯意义上的法律本身要经受一定的程序甚至实质合法性的检验[19],这尤其体现在其关于惩罚的理论上。由此可以看出,主权者在根本的意义上,在法律的立、改、废的意义上,不可能受制于市民法的约束,但是在法律变动或者通过一定程序对其进行变动之前,主权者自身却必须甚至示范性地遵守其市民法,因此在市民法变动之前,如若主权者违背法律侵犯了公民的财产等权利的话,后者可以依据法律对其提起类似于现代行政诉讼的诉讼以寻求赔偿,所以抽象地讲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者是在法律之上还是之下,都是不准确的。
(二)主权是必须的吗?
自博丹以降,在现代主权理论的大语境下,把法律界定为主权者的命令是法理学中一条显明的具有实证主义特性的线索,但是在这一谱系之内,随着时间的演进,在自由民主政制的时代氛围下,以凯尔森、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法学人越来越觉得主权是多余乃至有害的,对以奥斯丁为典型代表并可追溯到霍布斯的主权法学理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砍下利维坦的头颅,把现代国家改造成一套无头或者霍布斯所说的无灵魂的规范性法律体系,以法律吸纳政治,最终使得去政治化的国家被化约为一个封闭的、自循环的法律体系。现在就让我们深入他们的理论之中,以霍布斯的眼光去查看这种主张是否站得住脚以及是否可行。
对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而言,国家和法律不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共同体不是一个和它的法律秩序分开的东西,正如社团并非不同于它的构成秩序一样”[20]271,就像个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对凯尔森来说只是隐喻性的说法一样,国家对他而言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于法律秩序的实体,而是国家本身就是一套构成性的法律秩序,如此一来,国家或者说政治就被法律所吸纳,国家成为一个技术中立性的装置。而对该法律秩序,凯尔森采用了类似于上文中所说的霍布斯的“倒退”论证法,其经由渐次授权和逻辑演绎而形成一个等级性和封闭化的金字塔体系,一个具体规范只可能源于一个更高位阶的规范,然后以此类推追溯到第一个宪法规范。如此追问迫使凯尔森不得不在一个独立的法律等级体系上设置一个规范的顶点,该顶点是他做出的一个先验假设,是一个“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20]175,也即基础规范。无独有偶,哈特也甚看不惯奥斯丁的主权法学,《法律的概念》一书主要批判了法律命令说、现实主义法学以及自然法学等,但是其核心理论是通过批判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命令说”这种主权法学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把法律视为强制性命令只是简单社会的法律模型,在现代社会,法律由强制性义务这种初级规则和其它一些次级规则所构成,而次级规则包含承认、变更和审判规则,其中以承认规则最为关键和特殊,是一个法律体系中确定何种规则是法律规则的标准性规则,也即原规则,一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承认规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体系实效性的假定,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在一个已发展的法律体系中,承认规则当然是更复杂的;它们可能不是通过单独一份文本或列表来鉴别初级规则,而是通过初级规则所拥有某一般特征来鉴别规则。这个特征可能是以下的事实,即这些初级规则是由特定机构制定出来的,或者它们被作为习惯长期地实践,或者它们与司法裁判有相关性”[21]86。
那么,站在霍布斯的立场上,该如何回应诸如此类的挑战呢?对凯尔森来说,至少有三点霍布斯可以对其理论展开回应。第一,霍布斯哲学的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确立理性化和普适性的政治科学、政治法学[22],其规划的政治形态一体适用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而凯尔森、哈特以及包括为其主权理论进行辩护的施密特和卡恩等人,都只是在自由民主制、议会民主制的语境中讨论他们的主权概念,这样不但萎缩了主权概念的外延,还进一步薄化了主权的内涵,把其仅仅视作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连接性概念*凯尔森把主权问题仅置于法律领域进行考察,把其转换成一国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关系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传统的主权概念,笔者认为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尤其是对霍布斯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在前文中我们看到,霍布斯的主权概念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牵涉宗教、司法、价值判断等维度。。第二,凯尔森法律秩序体系论所采用的论证路线实际上酷似于霍布斯的“倒退”论证法,而只要能够成功地把前者的基础规范替换为主权者的意志,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论就依然是能够成立的。凯尔森虽然属于实证主义法学传统中人,但是因其基础规范的先验性和形而上学性使得其实证性明显弱于奥斯丁等人,因为奥斯丁明确地把其理论限定在“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中[23],因此,如果我们更加实证地看待法律规范并把其置于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霍布斯依然会追问基础规范是什么?并追问对凯尔森来说不可追问的基础规范的效力根据是什么的问题?结合凯尔森和霍布斯的理论可以得出,凯尔森的作为法律规范最终根据的基础规范实际上就是霍布斯在前述法律定义中所提出的先前义务,正是这一先前义务确保了所有公民的规范性服从义务并把其命令视作法律,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这一义务的根据是什么的话,霍布斯会明确地告诉你,这一义务来源于公民的同意和授权。如果我们把基础规范等同于霍布斯的先前义务的论证是合理的话,那么,这并没有解决具体政治社会的实证性法律概念问题,因为一如基础规范具有假设的性质一样,先前义务也具有假设的性质,它只是用于解决对主权者的规范性服从义务问题,而接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即服从主权者的意志,而法律就是其意志的表现,是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主权者的命令,如此一来,主权者的意志依然是绝对的,亦即主权是绝对的。第三,即使在自由民主制条件下,国家由一套官僚体系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运营,主权因其沉默而被误认为不存在,但是正如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所展示的,非常状态是现代国家理论中的一个普遍概念而伴随国家的始终,而“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24],决断非常状态的人显然就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只有一种能力:意志”[25],因此,即使在一般状态下,主权看似沉默,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在非常状态下一跃而起显示其巨大的威力,此时主权者的意志无疑是最高的和绝对的,其命令也无疑将中止凯尔森的规范性法律秩序的自运行而彰显国家的意志品质。因此,至少在这一决断时刻,凯尔森根本无法用其纯粹法理论挑战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
对哈特来说,除了以上对凯尔森的回应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也适用于他之外,针对其最为核心的承认规则,霍布斯也可能这样予以回应。哈特的承认规则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成文法,二是习惯法,三是法官法。就成文法而言,对霍布斯来说,不存在问题,因为这符合其标准的命令说模型,但是对于习惯法和法官法来说,需要进一步追问习惯以及先例作为法律渊源的正当性根据。第一,就习惯而言,其要成为具有约束性的法律,并非因为长期的实践,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很多,但是只有一部分进入法律成为习惯法,其中的差别在于主权者的意志作用,“当因长期使用而获得法律的权威时,不是因为时间的长度,而是因为在沉默中所表达的主权者的意志使其获得权威”[1]174,并且不但主权者的意志可以使习惯确立为法律,而且还可以废除习惯法使其成为单纯的社会习惯。第二,就法官法或者普通法而言,更是霍布斯批判的标靶,并因此促成《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书。首先,关于智慧或者法律理性,霍布斯认可柯克的观点,即理性是法律的灵魂和生命,普通法即理性,但是坚决否定柯克所谓的这种理性是通过长期的研习和践行而获得并由法官垄断的“技艺理性”。霍布斯虽然认可法律的知识是一种技艺(art),是通过一定的学习获得的,但是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我们不可能分门别类地都把它们称作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物理理性、化学理性等,它们都不过是人的自然理性的运用而已[18]54-55。翻开《对话》一书,迎面而来的就是上述霍布斯从知识论上对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法官优越感的痛击,他甚至声称通过一两个月的研习即可胜任法官一职,一如现实中许多人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即可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官队伍一样,这并不是霍布斯狂傲或痴人说梦,而是一些法官或法学院为了荣誉或利益而对理性视而不见的生活现实。其次,霍布斯旗帜鲜明地指出,“权威而非智慧创制(make)法律”[18]55,这是一种典型的契约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对这种法律观而言,所有的法律,无论成文还是不成文的,都只能出自于主权者的权威意志,习惯不会自动成为法,判例亦是。再次,关于法院和法官,霍布斯指出,法官盖由主权者任命,但法官无论职级高低,他们都有可能犯错误[1]181,而错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而是必须得到纠正的,那么,谁来纠正普通法法官的错误呢?“正义执行(fulfil)法律,衡平解释法律,并纠正根据同一法律所作出的判决”[18]101,霍布斯把这里的“衡平”与主权者,也就是国王的衡平法院联系在一起,由国王特派的大法官代表国王纠正普通法院的错误判决。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普通法并非独立于主权之外,其依然要受制于主权者的绝对主权。
(三)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吗?
有很多学者批评王权时代的霍布斯没有能力预测或者无法想象诸如美国三权分立之类的现代宪制安排,这是对其绝对主权理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挑战,实际上该观点是错误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定义问题。根据霍布斯的论证思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的主权叙事,这就是说,三权分立并不是主权层次上的分立而只是政府执行机制上的分立。虽然霍布斯并不像博丹那样明确地提出国家形式与政府形式的分立问题,但是可以设想的是,在民主政体下,其并不设想直接民主模式,因为这在他看来无异于自然状态模式,人们基于私人理性或者激情复又滑入战争状态,而是主张间接政府、代议制政府[26],那么,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就不是主权意义上的,而是治权和具体政府形式上的,因为三权之上有宪法,宪法之上还有人民,而人民,根据前述线性定义,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者[6]423,这也正是美国建国者们的观点[27]。所以,利用现代三权分立的宪政安排并不能否认霍布斯主权理论的合理性。以美国为例,它是一个宪治国,但是作为规则的宪法不可能享有主权或者不可能成为主权者,只有其背后的人民才享有主权,所以,著名宪法学者阿克曼才可以顺理成章地在“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找回人民[28]。二是解释问题。除了权力的冲突这个技术性问题之外,还存在解释这个技术性难题。因为三权分立的宪制安排背后必然存在一个宪法的文本,而这个“纸上的法”要转化为活法或行动中的法,必经一个解释的环节,如果三个部门都进行解释的话,必然会出现冲突甚至国家解体问题,如果由其中一个部门,比如美国最高法院进行解释的话,那么这个部门实际上就凌驾于其它两个部门之上,成为主权部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对霍布斯来说,主权之上的宪法是不可能的[8]101。由于宪法文本与其它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一样存在解释的需求,因此美国往往被称作“九个人统治的国度”。在日常宪治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享有垄断的宪法解释权,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美国的国家主权是由最高法院行使的。综合霍布斯的理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美国主权的二重性问题,即日常宪治的最高法院主权与“宪法时刻”的人民主权,但是无论日常政治还是非常政治,都无法否定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原理。
三、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虽然遭到普遍误解和激烈批判,但鲜有学者心平气和地勘定霍布斯绝对主权的含义并与其一道论理,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重述霍布斯绝对主权理论,进而站在霍布斯的立场,试图回应对该理论的三个被认为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挑战。现代法治理论强调法律之治而非人之治,但霍布斯恰恰要揭穿这个谎言,经验性、实证性地揭示出法律背后人的要素,并在契约论的武装下找到背后那个权威性的人,即主权者。现代实证主义者,如凯尔森和哈特等人,认定国家是一套规范性秩序,基础规范和承认规则可以代替主权者的决断,他们试图砍下利维坦的头而使其成为一个纯形式和去政治化的自循环的规则体系,然而不但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此构成致命一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霍布斯的思路去追问该基础规范和承认规则的性质的话,依然可以看到主权者的影子。三权分立的现代宪制安排被认为是对霍布斯绝对主权理论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攻击,然而就在许多民主思想家洋洋得意之际,霍布斯则可以从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成功的反击。总而言之,霍布斯虽持绝对主权理论,但因为其自然权利论、契约论的个人主义因子以及主权者对于自然法和形式意义上市民法的服从,甚至一定意义上司法对他的制约[29],使得他绝不可能是一个专制主义者、集权主义者。然而,霍布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如施特劳斯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中道主义的思想家,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其守持一种辩证的平衡,即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上,霍布斯强调的是主权权威的绝对性;在其他事务上,霍布斯强调的则是公民自由。与此同时,即使在强调主权权威的地方,这个权威依然要受到公民从自然状态中保留下来的基本自然权利的制约,这可称之为自由的权威。无独有偶,即使在强调公民自由的地方,这个自由也必须要受到自然法或契约目的的约束,这可称之为权威的自由。
[1] HOBBES T. Leviathan[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 洛克. 政府论(下)[M]. 叶启芳, 瞿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57.
[3] HOBBES T. Human Nature and De Corpore Politic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HOBBES T. Man and Citizen[M].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5] GOLDSMITH M M. Hobbes′s ″Mortal God″: Is There a Fallacy in Hobbes Theory of Sovereignty?[J].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980, 1(1): 33-50.
[6] COURTLAND S D. A Prima Facie Defense of Hobbesian Absolutism[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9, 90(4).
[7] MCNEILY F S. The Anatomy of Leviatha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235.
[8] HAMPTON J. Hobbe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让·博丹. 主权论[M]. 李卫海, 钱俊文,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GAUTHIER D P. The Logic of Leviathan: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obb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 HOEKSTRA K. The defacto Turn in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M]∥SORELL T, FOISNEAU L. Leviathan After 350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73.
[12] 列奥施特劳斯.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基础与起源[M]. 申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3] KALMO H, SKINNER Q. Sovereignty in Fragment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0.
[14] HOBBES T. Behemoth[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4-15.
[15] 孙向晨. 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116-124.
[16] LLOYD S A. Hobbes′s Self-Effacing Natural Law Theory[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1, 82(3/4): 285-308.
[17] HOBBES T. Three Discourses: A Critical Modern Edition of Newly Identified Work of the Yong Hobbe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 HOBBES T.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9] DYZENHAUS D. Hobb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Law[J]. Law and Philosophy, 2001, 20(5): 461-498.
[20]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沈宗灵,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1] 哈特. 法律的概念[M]. 许家馨, 李冠宜,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22] LOUGHLIN M. The Political Jurisprudence of Thomas Hobbes[M]∥DYZENHAUS D, POOLE T. Hobbes and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21.
[23] 约翰·奥斯丁. 法理学的范围[M]. 刘星,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13.
[24] 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神学[M]. 刘宗坤,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4.
[25] 保罗·卡恩. 政治神学[M]. 郑琪,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114.
[26] MANSFIELD H C. Hobbs and the Science of Indirect Govern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 65(1): 97-110.
[27] HAMILTON A, MADISON J,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313.
[28] 布鲁斯·阿克曼. 我们人民: 奠基[M]. 汪庆华,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29] MAY L. Limiting Leviatha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