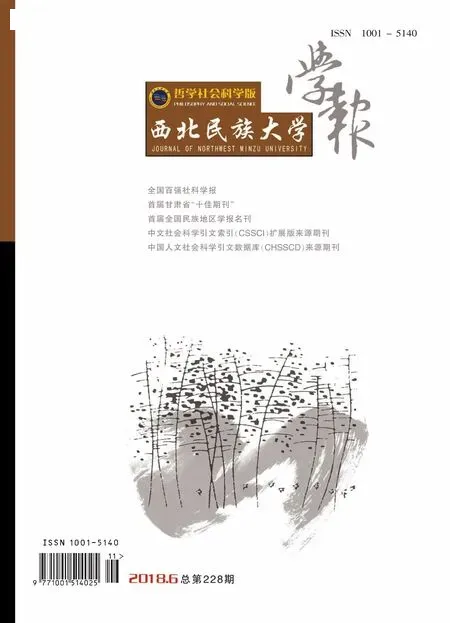困难的宽恕:大屠杀事件的宽恕问题探究
2018-02-10王霞
王 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蕴含着难以言说的创痛。但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历史事件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其传播情况也不容乐观。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创伤经历,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媒体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与再现。而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批判式思考,无疑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重要理论参考。作为对于南京大屠杀进行再现的一种重要方式,《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五月八月》《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表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残酷暴行与中国人的沉重创伤,表现了部分中国官兵、民众的无畏反抗精神,也表现了对于战争中复杂人性的反思。但是,遗憾的是,目前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宽恕问题的表现与探索还很匮乏。而纳粹大屠杀题材电影中已有相关的探究,比如根据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改编的同名电影,表现了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罪过问题,表现了战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于父辈之罪的批判与宽恕困境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国内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表现深度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思考是密不可分的。由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于宽恕问题的相关思考,为国内“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提供某些思路与借鉴。
一、宽恕是否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有计划的迫害与灭绝,目的是要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日本在中国南京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包括斩首比赛、活埋、狗咬、人体试验、强奸等,这些行为被称为“野兽机器”的暴行。犹太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作为极端的灾难性与创伤性事件,在反映人性之恶的同时,也在引发我们思考:对于这样一种人性之恶,是否能够宽恕?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与西方的犹太大屠杀一样,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起最大的人间惨案,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永远都无法愈合,也永远不能宽恕他们的罪行[1]。正如美国学者李彼得所提出的:“在饱受日本的折磨和摧残之后,能够做到克服痛苦和忘记仇恨吗?”[2]对于大屠杀进行宽恕如此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屠杀的行为极为残忍、灭绝人性,让人们难以宽恕,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宽恕大屠杀的罪行就等于默认甚至助长大屠杀。正如刘文瑾所指出的:“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作为代名词的反人类罪,之所以对宽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不仅是由于其残忍的手段以及所制造的深重苦难超出了任何能够衡量人类罪行的尺度,更是由于施害者在拒绝受害者的人性时,亦拒绝了自身的人性。”[3]
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讲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一次亲身经历。一位纳粹党卫队成员在将要死去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并请求威森塔尔来宽恕他。当时,威森塔尔还是集中营中的一名犹太囚犯,他拒绝宽恕这位党卫队成员,沉默地离开了。作者描写了集中营里的悲惨场景,纳粹挑选不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进毒气室,“虽然毒气室在全力运转使用,但是仍赶不上等待送进毒气室的人数的急剧增加。从早到晚,焚尸炉上空总悬挂着一大团烟云,证明死亡工业在全力进行”[4]81。纳粹还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鞭打他们、践踏他们、放驯犬咬他们、羞辱他们……因此,当那位党卫队员说自己仅仅21岁,还没有生活过,请求宽恕时,西蒙·威森塔尔感到愤怒,“21岁就死去,确实也死得太早了些。但是纳粹在把我们的孩子送进毒气室时,是否问过他们是不是死得太早了些?他们是否问过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认真生活过了?”[4]32西蒙·威森塔尔认为,作为一个被纳粹残忍迫害的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义务去接受这名年轻的纳粹党卫队员的忏悔,纳粹士兵没有权利去寻求犹太人的同情,也不值得同情。
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让·阿迈里认为,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不想听到任何有关宽恕的问题,拒绝宽恕大屠杀的施害者,也拒绝和那些大屠杀的助长者、推动者、冷漠的旁观者和解。因为犹太大屠杀这样的行为永远都不应该再发生,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来惩罚如此残忍的大屠杀行为,才可能阻止潜在的犯罪行为[4]115。苏珊娜·赫舍尔指出,在犹太教中,宽恕要求既赎罪又补偿,对于大屠杀的罪恶行为,是不可能补偿的,因此也不可能宽恕[4]198。罗伯特·麦克阿费·布朗也指出,如果我们宽恕了大屠杀的暴行,就可能会助长纳粹的罪恶,他们会因此不再畏惧惩罚,宽恕就会成为一种“软弱”的品质,如果我们宽恕而非抵抗和惩罚纳粹的罪恶行为,就意味着我们也成为纳粹行动的同谋。假如一个纳粹把无辜的犹太孩子扔进火里并使其烧死、成为灰烬,而我们宽恕了他,那么我们自己也和这个纳粹无异。
也有学者认为,大屠杀事件是可以实现和解的。李彼得以埃里克·洛马克斯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名英国士兵,埃里克·洛马克斯在战场被日军所俘,遭受了两年非人的残酷折磨,不断地被英语审讯官永濑武志及其下属毒打。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埃里克·洛马克斯所承受的痛苦并没有结束,他仍然受到种种战争后遗症的折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痛苦。他对永濑武志恨之入骨,根本不相信日本人在战后的悔意。机缘巧合,洛马克斯和永濑武志在泰国见面了,洛马克斯知道了永濑武志的忏悔。永濑武志在战后捐建桥梁、和平寺庙,谴责日本皇室应该为战争罪行负责,发表言论抨击军国主义等。这些实际行动说明了永濑武志的忏悔是真诚的,因此,洛马克斯表示,尽管他不能够忘记那段残酷的历史,但他愿意宽恕永濑武志。可以看出,洛马克斯宽恕永濑武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后者的真诚忏悔,不仅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而且愿意承担相应的惩罚,并努力去赎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彼得指出:“对于东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来说,痛苦的记忆依然如新。因此,日本对此作出真诚而毫不含糊的道歉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这些赔偿并不能减轻受害者的痛苦。”[2]
关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不可宽恕之恶行与不可宽恕之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与其女儿默福·图图认为,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禽兽般的邪恶暴行,但做出这些邪恶行为的人却并非禽兽。如果把一个人看成是禽兽,那么就等于否定了这个人有向善转变的能力,也否定了这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举止所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尽管一些施害者确实犯下泯灭人性、禽兽不如的恶行,但是施害者并非禽兽,“以禽兽来称呼他实际上是轻纵了他,因为禽兽没有是非对错的道德观,也就不能在道德上被定罪,不能被认为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5]55。可以看出,施害者有向善转变的可能性,有悔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谴责恐怖暴行的同时,也不要放弃宽恕与和解的希望。
此外,在现实语境中,宽恕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比如:如果受害者甚或施害者都已不再人世,以谁的名义去宽恕?这样的宽恕是否还有意义,意义何在?宽恕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施害者拒不认罪,宽恕无从谈起。
二、以谁的名义宽恕
宽恕如果存在可能性,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以谁的名义宽恕。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大屠杀的受害者来说,谈论宽恕已经不再可能。那么,大屠杀的幸存者、后代以及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本民族本国家的民众是否可以代表那些受害者去宽恕施害者?
阿兰·L.伯格曾设想,假如他处于西蒙·威森塔尔的位置,他该怎么做,他是否有权利代表被杀害的人去宽恕那些做恶的人。伯格认为,西蒙·威森塔尔不应该也不能够代表那些被如此惨无人道地杀死的犹太人去宽恕,“犹太教教导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罪恶。一种是由于人犯神而做下的。另一种是人犯人而做下的。我或许可以宽恕针对我而犯下的罪。我却不能宽恕因夺走别人的生命而犯下的罪过”[4]128。因此,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不应该也不能够代表那些被惨无人道地杀死的所有犹太人去宽恕。也就是说,饱受创伤的幸存者可以宽恕,但不能代替所有的受害者去宽恕,尤其当受害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时。对于施害者来说,他们的罪行在于迫害、屠杀受害者,而只能向受害者请求宽恕。即,只有当施害者请求受害者的宽恕时,宽恕才能成立,这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恕。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指出,宽恕只能存在于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与第三方没有任何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在‘一个人对一个人’,‘单独面对面’,或可以说只有在犯下不可补救或不可以逆转的罪恶的人和受到这罪行伤害的男人或女人之间,宽恕才能够被要求或者被允许,后者是唯一能够听到宽恕请求,同意或拒绝这种请求的人。”[6]宽恕的这种一对一的特性决定了它与法律、处罚、罪行,与公共机构、司法量刑统治等等不相关联。也就是说,大屠杀的幸存者、后代以及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本民族本国家的民众没有权利代表那些受害者去宽恕战争罪犯,人们不应该以受害者的名义去宽恕,尤其当受害者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时。对于施害者来说,他们也不应该向活着的人、幸存者请求宽恕那些受害者被迫害致死的罪恶。只有当施害者请求受害者的宽恕时,宽恕才能成立,这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宽恕。德里达认为,谁宽恕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唯有有罪者可以请求宽恕,也唯有受害者才能给人以宽恕。第三者不能为之”[7]。当宽恕被用于政治、外交等目的时,就变得不纯粹,比如政府或者教会首脑的悔过场面,往往是有条件性的,是为了改善外交关系、改善市场环境等,这不属于纯粹的宽恕。德里达以南非一位黑人妇女为例,讲述了宽恕的条件以及宽恕在实践中的困境。一位黑人妇女的丈夫被警察的酷刑折磨而死,但是她表示政府或者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都不能宽恕施害者,只有她有权利去宽恕,而她不准备宽恕。这无疑表明了,宽恕与第三方无关。斯迈尔·巴雷克指出:“改正不良行为是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事。第三者团体至多能充当一个调解人的身份。若无真正的悔悟,恶是不可能被善所抵消的。”[4]119国家、法律、司法机关等都不能够代表受害者去宽恕施害者,“国家的代表可以审判,但宽恕与审判不相干。它甚至与公共政治领域不相干,即便它是‘公正的’,宽恕的那种公正性也许与司法的公正性、与法律无涉。法院处理的是司法公正问题,但严格说来它从不宽恕”[8]。可以看出,如果有人以某种名义去宽恕,那么只能由受害人而非第三方去宽恕,但这也由此带来宽恕在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即严格来说,那位黑人妇女尽管也是受害者,但不算是绝对意义上的受害者。绝对的受害者应该是她死去的丈夫,那么,幸存者是否可以以死者的名义去宽恕施害者?电影《朗读者》表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电影中,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汉娜在临死之前,将自己毕生的积蓄装在一个茶叶罐中,希望由米夏转交给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当米夏找到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她却拒绝接受汉娜的钱。她认为如果接受这笔钱,就意味着宽恕,而她是没有权利也不能够去如此宽恕汉娜的。因此,就犹太大屠杀来说,幸存者没有权利以死去的犹太人的名义去宽恕。我们不能够代替受害者去宽恕罪行,更不能轻易地将宽恕廉价地给予施害者,因为如果施害者并没有真正地认清自己的罪行,没有表示忏悔、改过,此时给予其廉价的宽恕不但不可能引起施害者的悔悟、弃恶从善,反而会助长罪恶行径。
综上所述,伯格和德里达等学者强调受害者和施害者作为个体的一对一的关系。这种观点有其特定的意义,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把受害者与施害者作为个体,那么,在现实语境中,如果受害者或施害者都已不在人世,宽恕问题就不再具有意义。笔者认为,大屠杀的受害者和施害者双方不仅仅是某个个体,也是群体的一员。大屠杀事件的罪责问题关系到集体犯罪还是个体犯罪。与之相对应,宽恕问题也应该区分集体恕罪与个体恕罪。就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来说,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受害者是无数的中国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集体记忆,受害者所承受的苦难已成为一种民族创伤。因此,宽恕问题不仅仅是受害者和施害者个体的问题,这一问题也不应随着受害者和施害者个体的离世而被淡忘、无视。就此来说,当今仍需要讨论宽恕问题,其意义在于为了更好地记住历史,记住大屠杀受害者所承受的无法言说的创伤,更是为了反思历史,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个体罪责与集体罪责
大屠杀事件的罪责问题关系到个体罪责还是集体罪责。一方面,宽恕问题不仅仅是受害者和施害者双方个体的问题。大屠杀的创伤已经成为一种集体创伤,这种创伤不随某个个体的受害者或施害者的离世而消失。另一方面,宽恕问题涉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屈从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并且默认罪恶行为的普通民众,涉及到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服从上级命令的无名士兵的罪行等问题。西蒙·威森塔尔讲述了行人看到犹太人被迫害时的冷漠表情,他们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家畜一样看待犹太人。为此,西蒙·威森塔尔提出,迫害犹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纳粹。那些冷漠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犹太人遭受如此非人的折磨、迫害与杀戮,但是这些旁观者既没有用语言来表达不满、抗议,也没有阻止杀戮。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人也是不道德的[4]59。
斯迈尔·巴雷克认为,那些表面上没有犯罪,却容忍罪行的发生,对犯罪行为袖手旁观,漠然地看着施害者对受害者进行羞辱、毒打和杀戮行为的人,实际上也犯了罪[4]119。齐格蒙·鲍曼也指出,在纳粹大屠杀事件中,最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进行屠杀”[9]。此外,在执行大屠杀的政策过程中,不负有直接责任、服从命令的士兵、看守等也不能够免责。如果有了犯罪的事实,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电影《朗读者》体现了对于二战时期德国罪责问题的反思与探究。在电影中,汉娜作为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女看守,忠于职守,服从上级命令,但是缺乏思考力,眼睁睁地看着30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当时的纳粹德国,像汉娜这样缺乏思考力与判断力的人很多,导致平庸之恶盛行。汉娜·阿伦特认为,也许他们只是某一个官僚体系中的工具,只是庞大的行政体制中的一个单纯的齿轮,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和借口,“机器上的任何一只齿轮,也不管被押上法庭与否,都要还原成人”[10]。
问题是,那些施害者的后裔没有参与大屠杀,也没有犯罪事实,他们是否有罪?德波拉·E.李普斯达特认为,纳粹大屠杀之后出生的参加过纳粹大屠杀的国家的公民,可能承担着民族的责任,但对发生的事不承担直接罪责。也就是说,施害者的后裔并不承担施害者的罪责。电影《朗读者》中的米夏由于爱上曾经的纳粹女看守汉娜,而怀有一种难以抹去的罪感。米夏对于汉娜的复杂情感代表了德国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于父辈罪责的矛盾情感。尽管战后一代德国人并没有经历纳粹大屠杀,不承担直接的罪责,但是,由于对有罪的父辈的爱而怀有一种民族责任与道德罪责。刘文瑾指出:“每个人都将独自面对终极审判。”[3]尽管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创伤记忆传递、延续下来。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要牢记历史的真相,不能忘记这一历史;其次,要对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进行哀悼和纪念,不能陷入遗忘和道德冷漠之中。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进行一种有限的“宽恕”,也就是承认“关于罪恶,不存在父债子还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施害者的后裔并不必然继承施害者的罪性”[3]。
四、宽恕的条件
讨论宽恕问题能够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避免发生类似的悲剧,这需要受害者和施害者双方的共同努力。当受害者愿意说出真相、进行和解,施害者获得宽恕需要一些条件。
德斯蒙德·图图、默福·图图认为,施害者获得宽恕的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错误并不容易,但却是获得宽恕的必要条件。施害者只有诚实地面对真相,谦卑而坦诚地面对受害者,表示愿意痛改前非并且尽一切力量来修复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宽恕。不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犹太大屠杀,都是人类历史上极端残忍的灾难性事件,是反人类罪行、反人性罪行。只有当施害者真正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补救,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赎罪时,宽恕才是可能的。玛里·戈登指出,请求西蒙·威森塔尔原谅的那个纳粹党卫队员误解了悔罪。因为,如果一个人公开犯下了某种罪行,就不能够在私下里对他进行赦免,也就是说,作为施害者的犯罪者只有公开地承认罪行,才可以寻求赦免。另外,纳粹党卫队员错误地将西蒙·威森塔尔一个人作为整个犹太群体的公共象征来请求宽恕,“没有人可以私下以他人名义给予宽恕,因为那将意味着窃取受伤害者的宽恕或不宽恕的权利”[4]171。斯万·阿尔卡拉日也认为,西蒙·威森塔尔确实不能代表死去的犹太人去宽恕那个党卫队员。如果认识不到发生了什么罪行,就永远不能宽恕。对战犯的判决十分重要,通过对于罪犯的惩罚不仅能够伸张正义,还能够重温过去的历史。也就是说,惩治犯罪不仅可以彰显正义,还能够避免世人遗忘战争的罪行,而遗忘就意味着二次屠杀。
因此,宽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真正认识到了罪行。请求西蒙·威森塔尔宽恕的纳粹党卫队员无疑是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然而,正如玛里·戈登所指出的,那个纳粹党卫队员误解了悔罪。只有双方都承认了罪的存在,并且通过公开悔罪的仪式才可能保证类似的罪恶不会发生,避免重复同样的历史悲剧。而且,那位党卫队员只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行,还没有完全理解、认清这些罪行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仍将存在。“假如他真的意识到了其罪过的巨大,他就永远不敢去寻求宽恕。绝对不敢!真正看清他的罪过意味着意识到他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去寻求宽恕。……或许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只有在他知道了自己绝对不可被宽恕时,才有可能考虑他被宽恕……”[4]169
此外,宽恕不是一种廉价的恩典,单纯地悔悟本身并不能够得到宽恕,并不能够让受害者忘记他们的罪行。除了真诚地悔悟,公开地悔罪,还要有改过自新的行动。德波拉·E.李普斯达特认为,悔改之人首先应该面对面地请求受害者个人或者团体的宽恕,不仅要口头上表达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羞耻与忏悔,还要决心以后不能够再犯下同样的罪行。“彻底的悔改应表现在遇到同样的犯罪环境时能选择不再重复过去的罪恶行为。这个人还有能力再次犯罪;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丧失。但是,他选择不再重复犯罪。”[4]227也就是说,单纯地悔改并不能被宽恕,更为重要的是承担起自己所犯罪行的后果、责任与惩罚,积极地补赎。与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所讲的故事不同,在埃里克·洛马克斯的案例中,永濑武志不仅认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惩罚,而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战后谴责日本皇室应该为战争罪行负责,发表言论抨击军国主义等,以积极的行动去赎罪。正因此,作为受害者的埃里克·洛马克斯愿意去宽恕作为施害者的永濑武志。
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中日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宽恕难题,只有日本真正地承认自己的罪行,真诚地公开悔罪,并且以积极行动去赎罪,才谈得上宽恕。美籍华人张纯如指出:“日本不仅要向世界承认,更应该自我坦白,它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恶劣,否则日本文化就不会向前发展。”[11]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由于朗读而获得启蒙与良知的苏醒,选择了认罪、赎罪。这种良知的复苏是谈论宽恕问题的基本前提。张悦指出,《朗读者》这部电影不论对道德还是对人性都有所思考,并且引发的不仅仅是对于第三帝国的思考,还有其他国家、地域的人的反思,比如日文版《朗读者》的译者就曾经感叹说:“这是一篇让日本人羞愧欲死的艺术檄文。”[12]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首先不能遗忘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对这段历史、受害者进行哀悼和纪念,因为遗忘等于二次屠杀,“忘记罪行就贬损了死于这场暴行的人们”[4]108。其次,避免非理性的仇恨或者廉价的宽恕,以理性、反思的态度面对历史的创伤,而直面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正如王炜在一篇访谈中所说的:“解释历史是和未来相关的,如果不向着未来,历史和你毫无关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