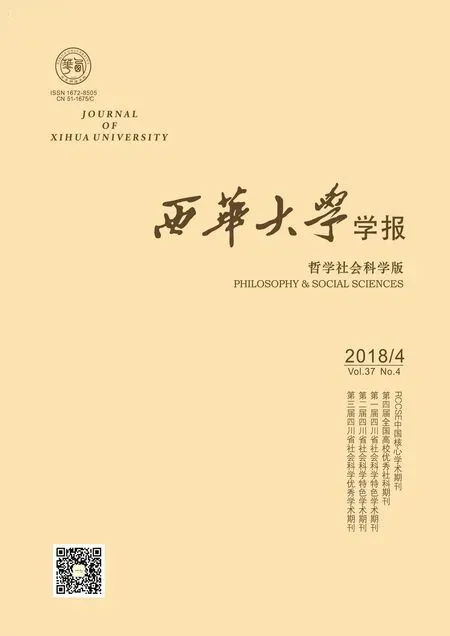回归先秦原典视野,以地理观整体解读屈辞
——《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述评
2018-02-10任敬文林春萍
任敬文 林春萍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先秦典籍中的地理地名,反映出先秦时代特有的地理观念,屈辞中瑰丽的域外地名及文化更是文学方面最突出之代表。自《禹贡》“九州”观念形成后,正史关于地理记载散见于《史记》的“河渠书”“大宛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后代正史便将“地理志”“郡县制”或“四夷列传”等纳入官修史书编撰范围内,后又增加“外国列传”,如《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此外,中国历代地理类杂史、方志、游记等著作亦不胜枚举,如《穆天子传》《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考察地理著述的大致脉络,则时代愈近愈清晰精确;如同上古神话逐渐附会为史传,先秦典籍中的地理坐标也逐渐被坐实或内缩,这无形中限制了文学作品的地域空间想象力;就屈辞而言,则限制了对其中域外地名及文化的整体考察与解读。“《楚辞》地理地名研究,历来为注解《楚辞》者所涉及,但旧注家们大都着眼于单个语词本身,对地名做封闭式的文字训解,从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宏观的空间地理认识。”[1]12旧时注疏者多集中于屈原的行踪考证,对其辞作中的域外地名、神话地理或存而不论,或曲为之解,有意无意地忽视屈原的域外视野,殊不知“文学作品中这一类词通常表明作者创作时,其头脑中活动的空间内容,因而它们具有指明作者创作时知识渊源的意义”[2]150。于屈辞研究者而言,“我们观照屈辞古地名,强调对屈辞原始文本进行整体全面的宏观研究,置一系列地名于屈原整体连贯的逻辑游踪的时空之中以及整体世界性的地理观念之下加以考察。”[1]241这正是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以下简称《屈辞》)一书的突出特色。
一、反思:历代地理观下的屈辞地名误读
我国古代地理观念的形成源头可上溯至《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典籍,有学者认为:“从‘九州’自然地理区划,‘畿服’政治地理构想,《山海经》以‘中山经’为中心的‘海内’和依次向外扩展的‘海外’、‘大荒’三个层次的地理世界模式,可以推知两书不晚于东周时代。”[3]何以在交通不便的先秦时代,先民能有如此宏大开放的地理观念,而汉代以后反而逐渐萎缩?除历代受“大一统”政治追求影响的屈辞注疏者的曲解外,也有神话中地理地名逐渐实化或史化的内趋因素。“我注六经”式的注书理念在中国古代颇为流行,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反观屈辞研究,“为什么历来楚辞注疏者对这些地理语词的注疏如此分歧?分歧的原因何在?为什么置注家们的注疏于屈辞文本,屈辞不能有前后照应的逻辑关联?……楚辞注疏者为什么总是将视域锁定在楚国或者中国?……屈原使用这些外来地理素材有无特别的思想情感寄托?是屈原无意识的选择还是反映了屈原自觉的世界地理观念?……屈原利用域外地理素材创作的《旷世绝响》为后世乃至中华文化又留有怎样的启示?”[1]15-16汤洪的这一系列反思,也是当下研究屈辞乃至先秦原典所必需的反思。
中国历代统治者极为关心疆域的界定,盛世的开疆拓土,衰世的志在恢复,都已成为仁人志士反复歌咏的题材。春秋战国虽战乱频繁,然而各国间来往相对自由,也无碍人民的迁徙,这是后代“华夷”对峙时期所难以达到的。与屈原大致同期的邹衍倡言“大九州”理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有三驺子……其次驺衍……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4]2344-2346这与其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观截然不同。
《汉书·地理志》将地理观念的形成追溯到黄帝时期,所谓“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5]1523。《地理志》还记载了一些海外地理,如“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不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3]1671。在汉代,史官记载域外地名已相对准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6]831汤洪梳理历代“西极”注疏提到,先秦时“西极”本指大地极西,然而从汉代起,就被逐渐缩短视距,不断东渐,从帕米尔一直东缩至长安以西。郭璞注《尔雅》,已把先秦的“西极”缩小到中土长安之西的邠国(邠即豳也),南朝裴骃也沿袭郭璞注《尔雅》“西极”的地理观念。逮及盛唐,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更为开放和包容,如《新唐书·地理志》对域外各国国名及道路里程记载甚详,此外,《大唐西域记》等文献资料也可窥见一斑。宋代疆域远小于汉唐,且南宋又偏安江南一隅,当时文人对屈辞中的域外地名或多靠想象,或认作不稽之谈。《宋史·外国列传》所言“外国”,很大区域在汉唐皆为中国所有或控制,而宋代已视其为外国矣;且有《蛮夷列传》四卷,所记中原以西、以南的极远之地已远不及汉唐。洪兴祖《楚辞补注》注解“西极”时,引用《尔雅》“西至于豳国,为西极”[7]44,屈辞中极远之“西极”东渐到了“豳”地,可见宋人眼中的“极西之地”不过也在中国之内。《元史·地理志》六卷,又有《外夷列传》三卷,所记疆域甚为广大。直至明清,人们的认识又重回归到先秦地理视域之西方极远之地。《明史·地理志》之外又对西南“土司”记载甚详,又“外国列传”九卷、“西域列传”四卷,其时已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中国与域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学者的学术视野自然也随之拓宽。明清《楚辞》研究者能提出与前人不同的地域见解,而汤洪在考察蒋骥、戴震的学术成就时,赞同他们能以新视角和新眼光去体察被大家早已熟视无睹的典籍,这也是著者与已放宽视野的明清学者会心之处。
当然,史书所记地理揭示的是不同时代的疆域观念,绝不等同于文学作品中的地域观,但这却极大影响历代文人对屈辞域外地名的理解,甚者以管窥蠡测之见来理解屈辞宏大地域观,如前所述屈辞域外地名逐渐坐实内缩便是明证。汤洪《屈辞》“绪论”中言“屈原的行踪范围并不能就等同于屈辞地理语词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范围,这是解读屈辞极关键的问题。”[1]12《屈辞》一书揭示了先秦以来地域观逐渐内缩的深层原因,提示我们在理解屈辞时不可为史传或后世文人的注疏所拘束,应当回归屈辞原典视野,以地理观整体解读屈辞,同时也激发我们回归原典视野的深深反思。
二、回归:屈辞原典视野下的整体观照
汤洪《屈辞》正是突破传统注疏者注解《楚辞》的封闭视域,而将屈辞的研究安置在屈原所处时代的宏大地域观中加以考察,其研究方法正是从研究对象自身(即屈辞原典文本)而来。著者对研究对象的选取甚为精审:一则集中于先秦文化,故舍去汉人拟骚之作;二则在先秦“楚辞”作品中只选屈原,以“宋玉《九辩》亦极少涉及历史、神话、传说、外来文化和宗教等内容”。此外,著者专章论述“研究范围屈辞篇目之认定”,最大程度上精确研究范围。屈辞的篇章问题始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近现代,学者都有认真而翔实的考辨。汤洪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艺文志》谨慎地提出所要研究的屈辞篇目。该书《绪论》言:“故笔者置假设于先秦广阔时代语境之下……用屈原的交游、先秦交通、先秦民族迁徙及南北丝绸之路等旁证材料对假设的结论进行了多维度旁证。”[1]18正如作者所言:“研究悬圃共使用了65条材料,研究昆仑共使用了128条材料,研究流沙共使用了46条材料……屈辞古地名的主体研究部分共使用了546条文献材料。”[1]236此外,著者对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广为参考取舍:考古类文献如《殷周金文集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选》《西亚考古史》等,中西交通史文献如历代史书记载、《中西交通史》、《中国古代航海史》等,泛文化研究文献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青铜时代》《比较神话学》《金枝》等。真正做到既不迷信《楚辞》研究权威和传统阐释,又不局限于楚国或中国。
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地理观念及“华夷之辨”,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在团结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无形中拘囿着学者的视野。若仅依史官记载,则很难理解屈辞中那些想象丰富瑰丽、异域色彩浓厚的艺术形象。汤洪始终将视野投向整个先秦时代、投向屈辞原典,并专辟一节“上古地名中包含大量外来地理语词(音译词与意译词)成分”[1]229,将屈辞置于先秦地域观中进行讨论,力证屈辞域外地名存在及来源的可信。时至今日,屈辞中部分域外地名依然很难定位到具体坐标,但这无疑体现出屈原宏大、开放的地理观念。随着文化的发展、史官的记录、学者的阐释,地理学著作逐渐清晰精确,文学作品中的地理观逐渐固化或内缩。如汤洪在书中所言“昆仑”“三危”“崦嵫”等地名由“承载模糊语义者可能为音译外来词”逐渐汉化、坐实为中国疆域内的具体地名,可见后世学者注解屈辞的地域观念变化轨迹。
如前所言,屈辞域外地名的研究需“置屈辞于先秦广阔时代语境之下”,也可借此窥探先秦的整体地域观。第八章“西极”的考辨,汤洪提出疑问:“‘北极’‘西极’同为屈原作品中的地理名词,一个创作者用词当有一定规律,既然‘北极’指北方极远之地,‘西极’也应当指西方极远之地……为什么汉代以后的学者对‘北极’尚有今天意义上的地理观念,而于‘西极’却远远落后于先秦博达之士的地理眼光呢?”[1]132-133又如“两汉以降,国人地理、世界观念逐渐呈现收缩内倾态势”一节中,大力批判纠正了今人迷信古人楚辞注疏之弊,认为“国人对于地理地名的认识、理解与时代、政治和历史密切相关。”[1]228此外,第十五章“由屈辞古地名研究所发现的中国地理文化之特点”,著者对中国地理观念的演变脉络梳理得极为清晰,从屈辞中地名所体现的宏大地理空间到后世注疏者的拘迂,进行细致梳理。著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材料丰富,论证精密,做到了既大胆假设,又小心求证,正如汤洪自言:“置屈辞于先秦广阔时代语境之下,对屈辞蕴含的丰富文化因子做进一步探寻。”[1]15好的作品不仅是知识或思想的传播,更应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该书于此着力甚多,此略举以上几例。
由此可知,汤洪对屈辞所体现的宏大地域观并非单纯因感情而发,亦非泛泛而谈,实为对屈辞地理名词精审考辨的原典视野回归,以屈辞域外地名的历代训释的详实材料为媒介,此外,对目前尚存争议的问题,也秉承阙疑学术规范,体现出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超越:回归原典视野的文化启示
中国历代疆域版图变更甚繁,然而如前所言,疆域观绝非地理观,地理观念包括直接或间接闻知的广大地域空间,而疆域观则狭隘得多,如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夷狄”之辨。汤洪首先抛弃了狭隘的疆域观念,代之以屈原辞赋中的宏大开放的文学地域观,这是对先秦时代地理观的回归,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文化的博大厚重,更能借以窥探先秦时中国和域外的文化交流情形。屈辞中的地理观极为宏大,要综合特定时代的所有因素,尤其是屈辞原典,不能以汉代以后的地理观念或今人的主观臆测来蠡测屈原往观四荒、周游天地的浪漫思想。正如著者所言:“后世学者对于屈辞域外地名的解释充满着大量的主观性、随意性、当下性和不确定色彩(当下性)。……从表面上虽然只是寻常普遍的学术探讨,然而其深层处却无不关涉着不同时期学者和学术所处时代、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宏大背景。”[1]228关于此论断,汤洪凭借“昆仑”地名的考证做了非常精彩的演绎和阐述。《屈辞》提示我们,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时,不能局限于后世阐释者之视野,应回归到先秦的文化视域中来。又如汤洪《从邹衍到屈原:“大九州”理论对屈辞的影响》所谈到的,“屈原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已在总体性知识背景和知识框架下奠定了屈原及其同代更多学者、思想家们一种开放的、广阔的、世界性的视域和眼界,这些世界性思想观念形诸笔端,见诸文字,存诸版册,由此形成众多文化典籍中有关山川地理、名物风光的生动神奇之记载,屈辞所示只不过是其中一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先秦时代知识者群体之中,有关亚欧大陆及其世界性的地理知识,有关‘大九州’的思想观念,或许本如当今时代人们对于‘七大洲’‘四大洋’之类的常识一样,本已深入人心,无可置疑。只不过经由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观念、时代思想的更替之后,在中华民族心灵历程经由大开放、大碰撞进入到2000余年总体性沉寂和禁锢的历史阶段之后,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鲜活的思想、开放的胸襟、壮阔豪迈的气度以及自由不羁的性情却都不由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以至于今天看来竟然显得如此陌生和难以置信。”[8]
加强文化考察力度是《屈辞》又一特色。《屈辞》“结语”中提出“研究先秦文献典籍,研究屈辞并指出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异域外来词汇和地理名称,由此进一步展现先秦时期包括屈原等众多文化大家在内的人们普遍性的世界地理观念,并从侧面揭示先秦乃至更早时期发生在中国与欧亚大陆土地上频繁密集的文化交流。”[1]225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瞩目的“南方丝绸之路”,串起了中国西南尤其是巴蜀地区与南亚交流与融会的脉络;文化交流往往是间接的,正如屈原经由古代巴蜀了解到南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理空间。屈原未涉足域外甚明,然其胸中已有世界性的地理观念,这是先秦时人地理观的文学再现。如后世于“兰台”或“史馆”中挦摘史书、日志、起居注的史官们,是难以想象屈辞中瑰丽多彩的域外地名的。研究屈辞,亦当“知人论世”,若不回归屈辞原典视野整体考察,岂不是方枘圆凿、缘木求鱼?
结语
文学是民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只有把作家及其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正确理解其特有的价值。现代西方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说于阐释都不过是对于当代社会思想的一种曲折反映与折射,“国人对于地理地名的认识、理解与时代、政治和历史也密切相关。”[1]228汤洪《屈辞》一书,或许还未能得出屈辞中域外地名的全部明确结论,但“重要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过程”[1]1。正如刘跃进评价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时说:“从当时的学术状况看,王国维的传统学术根基也许不是最雄厚的,但是他目光如炬,这里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推动学术进步的根本因素还是观念的问题。”[9]同样,《屈辞》给予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观念的开拓、学术视野的扩展、回归原典视域的研究范式。不可否认,目前仍有部分学者局限于“传统学术规范”,而忽视原典的时代环境。“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鴃之先鸣”,中国古代文学回归原典视野的研究时不我待,唯有回归原典时代的整体地域观,才能准确理解屈辞域外地名与域外文化,从而将中国优秀文化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