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儿
2018-02-10文/杨绛
文/杨 绛
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一只两只,而且只因为它们不像一般的猫而似乎超出了猫类。
我从前苏州的家里养过许多猫。我喜欢一只名叫大白的。它大概是波斯种,个儿比一般的猫大,浑身白毛,圆脸,一对蓝眼睛非常妩媚灵秀,性情又很温和。我常胡想,童话里美女变的猫,或者能变美女的猫,大概就像大白。大白如果在户外玩够了想进屋来,就跳上我父亲书桌横侧窗台,一只爪子软软地扶着玻璃,轻轻叫唤一声;看见父亲抬头看见它了,就跳下地,跑到门外蹲着静静等候。饭桌上尽管摆着它爱吃的鱼肉,它绝不擅自取食,只是匆匆地跳上桌子又跳下地,仰头等着。跳上桌子是说:“我也要吃。”跳下地是说:“我在这儿等着呢。”
默存(即作者的丈夫钱锺书——编者注)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过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却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而且,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睛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我们的老李妈爱猫。她说:“带气儿的我都爱。”小猫来了,我只会抱着,喂小猫的是她。“花花儿”也是她起的名字。那天傍晚她对我说:“我已经给它把了一泡屎,我再给它把一泡尿,教会了它,以后就不脏屋子了。”我不知道李妈是怎么“把”、怎么教的,花花儿从来没有弄脏过屋子。
我们让花花儿睡在客厅沙发上一个白布垫子上。那个垫子就算是它的领域。一次我把垫子对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儿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出垫子的范围。一次它聚精会神地蹲在一叠箱子旁,忽然伸出爪子一捞,就逮了一只耗子。那时候它还很小呢。李妈得意地说:“这猫儿就是灵。”它很早就懂得不能上饭桌,只伏在我的座后等候。李妈常说:“这猫儿可仁义。”
花花儿早上见了李妈就要她抱。它用一只前爪勾着李妈的脖子,像小孩儿那样直着身子坐在李妈臂上。李妈笑说:“瞧它!这猫儿敢情是小孩子变的,我就没见过这种样儿。”它早上第一次见我,总把冷鼻子在我脸上碰碰。清华的温德先生最爱猫,家里养着好几只。他曾对我说:“猫儿有时候会闻闻你。可它不是吻你,只是闻闻你吃了什么东西。”我拿定花花儿不是要闻我吃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什么都没吃呢。即便我刚吃了鱼,它也并不再闻我;花花儿只是对我行个“早安”礼。我们有一罐结成团的陈奶粉,那是花花儿的零食。一次默存要花花儿也闻闻他,就拿些奶粉作贿赂。花花儿很懂事,也很无耻。我们夫妇分站在书桌的两头,猫儿站在书桌正中。它对我俩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要往我这边走,一转念,却又决然走到拿奶粉罐的默存那边去,闻了一下他的脸。我们都大笑说:“花花儿真无耻,有奶便是娘。”而这充分说明,温德先生的话并不对。
一次,我们早起不见花花儿。李妈指指茶几底下说:“给我拍了一下,躲在那儿委屈呢。我忙着要扫地,它直绕着我要我抱,绕得我眼睛都花了。我拍了它一下,瞧它!赌气了!”花花儿缩在茶几底下,一只前爪遮着脑门子,满脸气苦,我们叫它也不出来。还是李妈把它抱了出来,抚慰了一下,它又照常抱着李妈的脖子,挨在她怀里。我们还没看见过猫儿会委屈,那副气苦的神情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它第一次上了树不会下来,默存设法救了它下来。它把爪子软软地在默存臂上搭两下,表示感激。
花花儿清早常从户外到我们卧房窗前来窥望。我睡在靠窗的一边。它也和大白一样,前爪软软地扶着玻璃,只是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守着。假如我不回脸,它绝不叫唤;要等我已经看见它了,才叫唤两声,然后也像大白那样跑到门口去蹲着,仰头等候。我开了门,它就进来,跳上桌子闻闻我,并不要求我抱。它偶尔也闻闻默存和圆圆,不过不是经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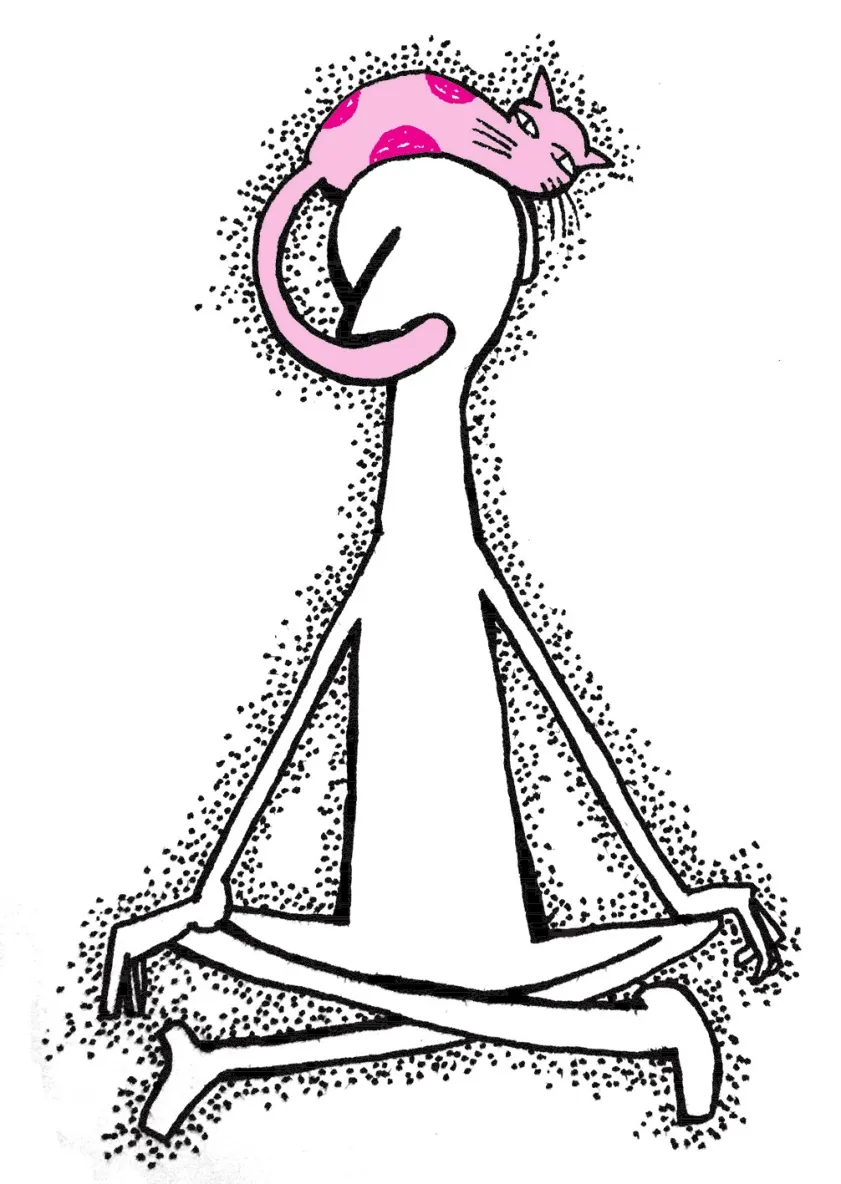
它渐渐不服管教,晚上要跟进卧房。我们把它按在沙发上,可是一松手,它就蹿进卧房。捉出来,又蹿进去,两只眼睛只顾看着我们,表情是恳求。我们三个都心软了,就让它进屋,看它进来了怎么样。我们的卧房是一长间,南北各有大窗,中间放个大衣橱,把屋子隔成前后两间,圆圆睡后间。大衣橱的左侧上方是个小橱。花花儿白天常进卧房,大约看中了那个小橱。它仰头对着小橱叫。我开了小橱的门,它就一下蹿进去,蜷伏在内,不肯出来。我们都笑它找到了一个安适的好窝儿,就开着小橱的门,让它睡在里面。可是它又不安分,一会儿又跳到床上,要钻被窝。它好像知道默存最依顺它,就往他那里钻,可是一会儿又嫌闷,又要出门去。我们给它折腾了一顿,只好狠狠心把它赶走。经过两三次严厉的管教,它也就听话了。
一次我们吃禾花雀。它吃了些脖子、爪子之类,快活得发疯似的从椅子上跳到桌上,又跳回地上,欢腾跳跃,逗得我们大笑不止。它爱吃的东西很特别,如老玉米、水果糖、花生米,好像别的猫不爱吃这些。转眼由春天到了冬天。有时大雪,我怕李妈滑倒(她年已六十),就自己买菜。我买菜,总为李妈买一包香烟,一包花生米。下午没事,李妈坐在自己床上,抱着花花儿,喂它吃花生。花花儿站在她怀里,前脚搭在她肩上,那副模样煞是滑稽。
花花儿一岁左右还不闹猫,不过外面猫儿叫闹的时候,总爱出去看热闹。它一般总找最依顺它的默存,要他开门。它用两只前爪抱着他的手腕子轻轻咬一口,然后叼着他的衣服往门口跑,前脚扒门,抬头看着门上的把手,两只眼睛里全是恳求。它这一出去,就彻夜不归。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区猫儿中的一霸……
花花儿毕竟只是一只猫。“三反运动”后,院系调整,我们被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儿依恋旧屋,由我们捉住装入布袋,搬入新居,拴了三天才渐渐习惯些。可是我偶一开门,它便电光似的向邻近树木繁密的果园蹿去,跑得无影无踪,一去不返。我们费尽心力也找不到它了。我们伤心得从此不再养猫。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他的诗集《容安室休沐杂咏》中有一首提到它:“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
写 法 探 讨
写动物和写人一样,都需要塑造“形象”;只有尽可能地让“形象”鲜明、生动起来,才能够出彩。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是怎么塑造花花儿的形象的呢?作者先是声明她喜欢的猫都不同一般,是“超出了猫类”的,然后写到她喜欢的一只叫大白的猫,用它来为花花儿的出场作铺垫。大白的特点是出奇地漂亮,“我常胡想,童话里美女变的猫,或者能变美女的猫,大概就像大白”。而接下来介绍花花儿,则说它虽然没有大白漂亮,智力却远在它之上。在后面的篇幅里,作者便着重塑造花花儿“聪明”的形象。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描述做到了这一点,精彩的比如:
“一次我把垫子对折着忘了打开,花花儿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一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越出垫子的范围。”
“它对我们俩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要往我这边走,一转念,却又决然走到拿奶粉罐的默存那边去,闻了一下他的脸。”
“它第一次上了树不会下来,默存设法救了它下来。它把爪子软软地在默存臂上搭两下,表示感激。”
“假如我不回脸,它绝不叫唤;要等我已经看见它了,才叫唤两声……”
……
真是不胜枚举。这样的一只猫,何止是聪明,简直可以说是“成精”了。这样的一只猫的形象,又怎么会不鲜明、生动,让人印象深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