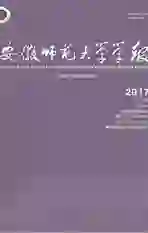大学生创新素质养成与创新人才造就
2018-02-09陶富源
陶富源
关键词: 创新人才;创新能力;创新素质;社会支持系统;创新活动;大学教育改革
摘要: 创新人才是在知行领域中有所发现和发明,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人。创新人才造就于社会支持系统中。作为创新人才成就条件之一的创新能力,主要是由知识、智力和人格等创新素质有机构成的,成功完成某种创新活动的能力。它生发于创新活动中。人的知识、智力和人格等创新素质养成于融“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教育训练中,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大学教育中。为此,要提倡和坚持高校关于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全员面向、志向优先、个性放飞和双向参与。要革新大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4044506
Key words: Innovation talent; innovation ability; innovation quality;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novative activities;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Abstract: Innovative talent is the man whose have found and invented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and discovery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people. Innovative talents are created in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As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innovation,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is mainly composed of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ccomplish some innovative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It is generated in innovative activities. The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people is develop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practice" trinit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specially in schoo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this end, we must advocate and adhere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oriented, ambition priority, individuality flying and two-way participation. We must reform the idea and method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学校,特别是一些高校为自己确立了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定位。对这一目标定位,实际有相去甚远的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创新人才的造就,是其社会支持系统的总体目标,因而作为这个系统构成要素的大学,自然要以这个总体目标为自己的目标;二是认为,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独立力量,因而要以这个目标为要求,去落实教师责任,和对学校进行问责管理。近十多年来,在关于“钱学森之问”①
如何解答的讨论中,有不少论者所持的,就是這样一种理解。在我看来,前一种理解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后一种理解,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确实有些偏颇。即它夸大了大学在创新人才造就中的作用。因而这种理解也就缺乏操作性,弄不好,还会事与愿违。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偏颇的理解呢?在笔者看来,其在理论上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对创新人才、创新能力、创新素质等概念的运用,没有讲究。于是大而化之地认为,创新素质的培养,就是创新能力的生发,同时也就是创新人才的造就。殊不知,此三者并不等同。与此相联系,创新人才必是造就于社会支持系统中;创新能力只能生于创新活动中;创新素质则是养成于教育训练中,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大学教育中。
下面就此来谈四点认识。
一、 创新人才造就于社会支持系统中
关于什么是创新?有人粗略估计,其定义有几十种之多。这是因为,创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关于创新概念,也就有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不过,这多中有一、异中有同。也就是说,在这多种不同的理解中,包含有共同的本质内涵。即“创新”标示着破除或打破旧的观念或事物,发现和发明新的观念或事物。“创”在中国语言中,本来就兼有“破”、“立”二义。在“破”的意义上,如“重创敌人”之“创”;在“立”的意义上,如“开创未来”之“创”。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往往用“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等,来对创新活动进行指谓或表述。不过,从总体来看,在“创新”概念中,“破”只是其隐内涵,“立”才是其显内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创新,也就是在知行领域中有所发现和发明,或简曰,发现和发明就是创新。在知的领域中的发现和发明,可称之为观念创新;在行的领域中的发现和发明,可称之为实践创新。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人类创新的两大方面。此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创新活动的主体无疑是人。但这里的人,非通常之人,而是创新之人,或曰创新人才。所谓创新人才,也就是在知行领域有所发现和发明,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人。这里的贡献,即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endprint
在当今社会,创新人才的宝贵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创新人才是何以造就的呢?这里涉及多种条件。大体说来,有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两大方面。就主体条件来说,它是指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主体要素之和。其中,包括主体所具有的生理、财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等要素。就客体条件来说,它是指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社会支持系统。其中,包括社会需求、人脉、社会资金、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水平、人生机遇、国家意志、制度保障,以及舆论支持等要素。
不难看出,离开了主体条件或客体条件,创新人才的造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诚然,比较而言,客体条件相对于主体条件,乃是居于基础的层面。因为创新人才,不论是作为创新个人,还是由创新个人所构成的创新团队,他们的生存,其才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才能的发挥,都是以社会为基础实现的,都是以社会的一定发展为条件的。这一道理,对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及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在内的社会工作者等,提出创新观念,成就创新事业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知行的对象,原本就是社会的人和事;同样,这一道理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技术工作者、生产者等,提出创新观念,成就创新事业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
任何一位科学家、发明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他们的任何一项发现、发明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拿牛顿来说,如果没有当时英国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简单工具结合为机器这一经济技术要求的推动;没有那时工业发展所提供的观察仪器和设备;没有伽利略和开普勒等先辈的理论贡献;没有同时代著名学者包波勒力、虎克、哈雷等的出色工作和对他的启迪,那末牛顿是不可能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
随着科技发展愈是走向现代,科技创新人才得以造就的社会决定性这一性质,还会愈加突出、愈加显著。具体说来,也就是,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从古代主要作为一种个人事业。即凭借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力量、运用身边材料所进行的事业,到现代愈来愈成为一项社会事业。即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依靠社会力量、体现国家乃至人类意志,并得到各种社会制度保障的事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技发展日益深刻化、复杂化、综合化;科技的经济社会文化作用日益突出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化;科技产品的社会需求日益人性化、生活化、个性化。而这一切,都是任何创新个人力不能逮,而只能依靠团队和企业的集体作用,以及国家的组织引导功能。
就国家来说,也就要求既要重奖创新个人,更要重在增加创新投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培育创新文化;以及进行包括信息系统、培训系统、孵化系统和评价、推介系统等在内的创新支持系统建设。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科研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成型和完善,我国必将迎来一个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灿若群星的时代。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
总之,创新人才造就于社会支持系统中。因为这个系统不仅为创新主体施展创新能力提供了舞台,而且还因为创新能力本身就是在以这个系统为根本前提的创新活动中生发的。这里的前一点,上文已作讨论,下面来重点关注后一点。
二、 创新能力生发于创新活动中
如上所说,创新能力是创新人才得以成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那么人如何才能具有创新能力,从而成为创新人才呢?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才能观的意义上,思索着这个问题,于是,先后形成了“神启说”、“先天说”、“环境说”、“实践说”等的观点。
“神启说”认为,人的才能来源于上帝的启示或神的恩赐。这种观点是一种蒙昧主义的猜测。取代“神启说”的,是“天生说”。“天生说”认为,人的才能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然秉赋”。或曰生而有之。人的生理素质无疑具有自然性、先天性。但再好的生理素质也要通过后天的滋养,才能发育成长起来。另外,它作为能力构成的一个潜在因素,也须待后天开发,即加以“锻炼、捶打、形塑”,才能作为一个现实因素而发挥作用。由于“天生说”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因而它被后来提出的“环境说”所取代。“环境说”认为,人的才能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
这里的“环境说”,有两种形态:其一,是以18世纪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地理环境说”,或“地理环境决定论”。即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性格和气质的差异。但这一观点无法說明,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不同时代、不同的个人,何以会在性格和气质上存在差异。作为对这一难题的一种破解,于是,其二,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环境说”,即“社会环境决定论”,则应运而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环境说”所言的“社会环境”,并不是指社会的经济物质环境,而是政治文化环境,特别是法律和教育环境。比如,爱尔维修认为,人的才能和美德的来源,“既取决于支配人们生活的法律,也取决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 [1]478不过,在此二者中,他更看重教育的作用。他说:“世人中间伟大的人才很少,这是他们的教育的结果。” [1]540由此不难看出,当代流行的,通过学校教育可以造就创新人才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或多或少是18世纪爱尔维修为代表的“教育环境决定论”的一种再现。
爱尔维修的这一观点,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就已进行过批判。认为这种教育环境决定论之不能成立,在理论上,它失足于无效的循环论证。即这种观点认为,教育环境决定人,而它忘记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实践说”。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2]500就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历史的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34]234“在再生产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4]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创新人才而立论的,但其道理对人的创新能力的生成也是完全适用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创新能力不是天生或通过后天教育,作为既有的前提,表现或展现在创新活动中,而是作为产物或结果生发于创新活动中。正如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56]258259这一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的道理,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敏而求之”;或用瓦特的话说,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血汗”的结晶。endprint
总之,一切人的创新能力都生发于创新活动中。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创新能力的生成需要多种创新素质的支撑,也不否认学校教育在创新素质养成中的作用。毋宁说,这种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三、 创新素质养成于教育训练中
创新素质,也就是构成创新能力的要素。其中主要有知识、智力和人格等三个方面。
1.知识要素。知识要素是创新能力的子系统。它是由知识数量、知识种类、知识层次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是创新能力所依存的基础层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做基础,或孤陋寡闻,或一知半解,那是谈不上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的。首先,只有广阔的知识背景,才能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这里的“见同”或“见异”,都是一种创新。其次,只有关于某一事物的系统知识,才能把握该事物的来龙去脉,进而从中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运用规律去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在这里,发现规律和预见趋势,也是一种创新。再次,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可以产生新的联想,可以创造不同的组合,从而形成种种新的可能。特别是在科学发展呈现大分化、大综合特点的今天,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贝弗里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知识的宝藏越丰富,产生重要设想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如果具有有关学科或者甚至边缘学科的广博知识,那么独创的见解就更可能产生。”[6]58最后,具有广博的知识,才能了解别人取得了哪些创新成果,同时又有哪些不足,从而不仅可以避免做无效劳动,而且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前进。
2.智力要素。智力要素是创新能力的又一个子系统。它是由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智力系统。这个智力系统是创新能力所依存的核心层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全面而细致的观察力、敏锐而灵活的思考力,以及丰富而通透的想象力,那末也就沒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首先,只有具有全面而细致的观察力,才能获得丰富而真实的信息,才能捕捉到观察对象的细节。瑞典植物学家林耐说过:“自然界的伟大最清楚地显示在他微小的细节上。” [7]49其次,只有具有敏锐而灵活的思考力,才能对信息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加工、处理。这种加工、处理有两种形式:一是显意识形式,即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二是潜意识形式,即表现为顿悟、直觉、灵感。顿悟是指猛然领悟到问题的关键所在;顿悟作为一种认知能力被称之为直觉,即透过表象,直奔本质的能力;而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心理过程又被称之为灵感。即某种偶然激发,从而使思路豁然贯通。被用来加工的信息有两类:一是内在信息,即大脑中的储备信息;二是外来信息,即关于新的外部客体的信息。这两种信息或一致或冲突,经过加工,其结果或是使认识走向深化和丰富,或是使认识发生变革或飞跃,而这二者都是创新的表现和结果。再次,只有具有丰富而通透的想象力,才能利用真实世界所呈供的素材,在头脑中去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爱因斯坦曾高度肯定想象力在创新中的作用。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8]98
3.人格要素。人格要素是创新能力的又一个子系统。它是由志向性、独立性、探索性和应变性等精神品格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人格系统。这个人格系统是创新能力所依存的主导层次。首先,志向性,是一种把创新视为人生目标,敢想敢干、勇于担当、舍我其谁的精神品格。一切创新者,都是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其次,独立性,是一种不惧怕权贵、不迷信权威、不盲从传统、不屈从私念,用审视的眼睛看世界,用求真的脑袋想问题,用务实的双手辟新径的那种精神品格。不难理解,那些唯书、唯上、唯我者,是不可能有创新能力的。再次,探索性,是一种通过不断追寻以求得真相、通过不断试错以争取成功的精神品格。可以说,一切创新都是在无数次失败后,仍坚持探索才取得成功的。最后,应变性,是一种针对新情况、新特点、新态势和掌握的新信息,以及产生的新需求,调整思路、变换方案、改进方法,包括运用各种手段,随机应变,以求成功的精神品格。有了这种品格,才能有效迎接挑战,进而引领潮流,以至重塑生活。
由此可见,创新能力并非等同于创新素质。它不是知识、智力、人格等创新因素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的,由知识、智力和人格所支撑,并获得优化整合的动力体系。那么,这些创新素质是如何养成的呢?它是在融“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教育训练中养成的。
这里的“教”,是传授。即韩愈所言的“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传授天人之道,培养人格精神。授业,是传授生活的知识技能。解惑,是指解答难题迷惑。这里的“学”,是继承。是指向前人、别人,包括向书本和向老师请教。学什么呢?一是学做人的道理;二是学做事的本领。这里的“习”,是训练。即把所学的东西,加以运用。通过运用来巩固、深化,以及升华所学的东西。
融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其中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创新素质的养成教育中,学校教育是主渠道。这是因为学校教育有专职的老师,系统的、集约化的分门别类的教学内容,比较健全的教学设备。因而在关于学生创新素质的养成方面,学校,特别是高校也就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承载着更为殷切的民众期望。
四、 提升高校对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水平
为了提升高校对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水平,必须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即要提倡和坚持关于大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全员面向、志向优先、个性放飞和双向参与。
1.关于全员面向。创新素质的养成依赖于学校培养,而创新素质能否被调动、汇集并优化整合为创新能力,这主要取决于社会需要和可能。创新能力的发挥,需要包括公平竞争的环境、适合的平台,以及大胆放手和容忍失败的观念和制度等在内的社会支持系统。那种把培养创新人才定格为依靠高校本身的力量所实现的直接目标,那是不妥的。时下某些高校把“高分尖子”视为创新人才的观念和做法,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著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曾就此撰文说,他教过好几个得奥数金奖的中国学生,知识面太窄,考试有能力,但研究没能力,有的甚至还不能毕业。大学不仅要重视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而且这种培养还要面向全体学生,要为他们每个人设定“创新遗传代码”,即为他们在未来成为创新人才提供内在的根据。那种只关注少数所谓“尖子”的做法,之所以不可取,一是它剥夺了多数大学生的上述可能;二是对这个“少数”的过度投入和百般呵护,也是一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而那是没有好结果的。endprint
2.关于志向优先。大学教育要为大学生设定“创新遗传代码”。在这个代码中,最重要的数字应该是“人格”,头一个字符应该是“志向"。一个人的素质像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容易被人看到的是学历和专业知识,乃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真正决定个人成功的,则是其具有的人格精神。就创新人才来说,其人格精神就是上文论及的志向性、独立性、探索性、应变性等精神品质。这其中,作为首要和深层动因的则是志向性。人生志向的最高境界是奉献爱心的人间情怀。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对人类和其命运的关心肯定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9]70被誉为我国当代仓颉的已故院士王选也曾说:“只要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有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10]为此,要对大学生进行关于创新的感恩、责任、欲望和荣耀的教育。要教育大学生对父母、家庭、教师和社会的养育之恩予以回报。即更应该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善于总结、善于创新。要教育大学生树立创新的欲望和自信。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赞扬他们任何微小的“创意”。使他们逐渐树立“一切皆有可能”;“我能行”等的理念和信心。要教育大学生认识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创新事业中。这样,有限也就获得了永恒的光辉,如同牛顿、爱因斯坦那样。这是人生的最大价值实现和美丽所在。
3.关于个性放飞。一切创新人才都是在最能发挥自己优势,即最能适合自己个性,包括性格、气质、潜能等特点的领域中,成就创新事业的。有个性,才会有创新。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个性,有人主张“因材施教”,认为这是教学的第一要义。也有人不表赞同。认为应该超越“因材施教”。再高明的老师也无以判定学生之材,因而也无从进行因材施教,在我看来,教师虽然不能从学生现在的起点去预知他能否成为人才,以及能否成为创新人才这一终点。另外,教师对學生现有材质的认知,确实难免失准失误。但由此走向极端,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材质不可能有所认知,那就偏颇了。在古代,当教育还是一种民间的、私人事务的情况下,一个老师所教的只有几个学生,有时还是一对一的教学,因此,在那时,对学生个人而言,因材施教大体还是可行的。大教育家孔子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近代以来,当教育从以往作为民间的、私人的事务,逐渐变成满足公民享受教育权利,从而成为受国家统管的社会事务以后,建制化的班级成为实施教学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学生个人因材施教,对教师来说,无疑增加了难度。但在班级意义上,对不同的班级因材施教,还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往往比较强调统一化、标准化,以至陷入刻板化,结果压抑了个性,压抑了创新素质的养成。那么怎么办呢?可以从学校制度设置上进行改革。即高校要给大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比如,适当减少硬性的标准化考试,代之以调查报告、研究报告、读书心得、专业论文等作为考核对象。创设大量假期研究项目,支持学生开展自主研究。鼓励学生参加高校教师主导的团队研究,支持大学生的自主创新活动,为其专利发明申请以及创业项目的实施提供制度与条件保障。在大学生个性的养成上,要通过制度安排,实现从侧重于教师“因材施教”,到侧重于学生自我放飞的转变,把放飞个性的决定权还给学生。
4.关于双向参与。融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教育,其中包含老师教什么、如何教,以及学生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是“教师中心论”。即认为,教师是先行的觉悟者,知识和真理的掌握者,因而学生要以教师为中心,求得教师对自己的开悟和传授;二是“学生中心论”。即认为,真理是学生自我发现的,而非教师所教。教师只是助产士,而非智慧的生育者。因而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从旁予以帮助和协助。其实,这两种观点各有所见,亦各有所偏。所谓各有所见,即它们分别肯定了教师在“教授”中的主体作用,和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所谓各有所偏,即偏离了各自的维度,或各自的边界。老师在“教授”中发挥主体作用,其目的在于,指导、引导、激发学生在“学习”中主体作用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中发挥主体作用,也正在于,内化、强化和优化教师在“教授”中主体作用对自己的效用。
所谓双向参与,即老师要创造条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教授”的过程;学生也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听取和争取老师的指导,营造亲密的师生交往关系。这种私下的、非正式的交往,往往会使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难以忘怀的教益。就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来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参与,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反思意识和探索意识。在双向参与中,课堂教学的关键是问题的设置。老师可以提问题,学生也可以提问题;在问题的解答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可以一起讨论,共同寻找答案。在这里,一定要克服那种老师说学生听的“独断式”教学方式,而代之以一种以理性为基准的“探究式”教学方式。这其中,也就少不了不同意见的相互问难,你争我辩。正是在这种争辩中,提高了反思和探索能力,深化了认识层次,激发了思想火花。
总之,“钱学森之问”须由包括成长中的个人、家庭、学校和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来共同加以回答。大学的职责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创新素质教育,并不断提高其水平。这也是大学在创新人才造就这一社会支撑系统中的具体目标定位。必须以这个定位为基准,来进行大学教育,实施大学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威廉·伊恩·比德莫尔·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陈捷,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7]翟焕民,徐秋英.说明文写作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8]王通迅.学海泛舟[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
[9]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M].仲维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10]孙慕天.最委屈的科学家和科学的非功利性[J].民主与科学,2011(1):510.
责任编辑:马陵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