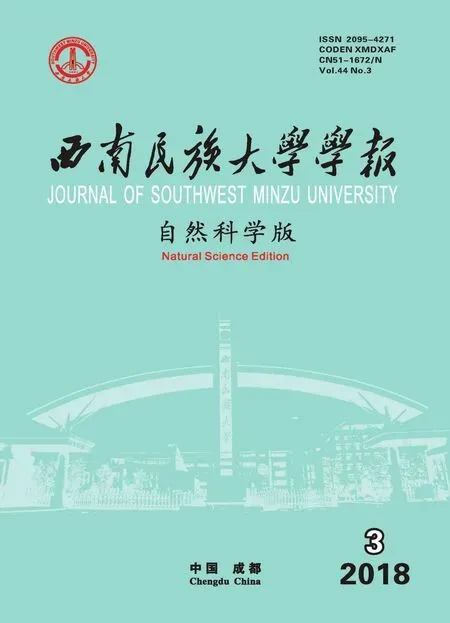西藏阿里地区物种多样性
2018-02-09刘彦宏根呷羊批
杨 孔,刘 伟,刘彦宏,根呷羊批
(1.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2.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阿里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西藏自治区西部,海拔高、气候多变、生态脆弱,是多种高原特有濒危物种的栖息地.然而,目前国内对阿里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系统性科学考察仅见于青海省生物研究所在1974年开展的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近几十年来,阿里地区受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改善等影响,当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也必然随之变化.作为国家精准扶贫的地区之一,如何在阿里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保护和利用其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是当前重要科学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对已经报道的阿里地区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综述与分析,不仅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等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该地区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1 区域概况
阿里地区东起杂美山,与那曲地区相连;东南与日喀则市接壤;北倚昆仑山脉南麓,与新疆喀什、和田地区相邻;西南连接喜马拉雅山西段,与克什米尔及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毗邻.阿里地区是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等山脉相聚的地方,被称之为“万山之祖”;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故又称为“百川之源”.该地区最高海拔7 694 m,最低海拔2 800 m,平均海拔约4 500 m,地貌有高山、沟谷、土林、冰蚀、冲击扇、冰碛和火山等类型,主要河流有朗钦藏布(象泉河)、森格藏布(狮泉河)、马甲藏布(孔雀河)等外流水系和措勤藏布等内流河,湖泊多为咸水湖,较大的湖泊有扎日南木错、班公湖、玛旁雍错(圣湖)、拉昂错等.全地区分为高原温带季风干旱气候区、高原寒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和高原寒带季风气候区,仅有冬夏两季之分,冬长夏短,年无霜期仅为120天,年均大风天气达115天,年均日照3 545.5 h(狮泉河镇),年均降水量74.4 mm(狮泉河镇),年均蒸发量2445.1 mm.阿里地区土壤类型分为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高山荒漠土等14种[1],主要农作物有青稞(Hordeum vulgare)、小麦(Triticum aestivum)、油菜(Brassica napus)等;阿里辖域总面积34.5万km2,为西藏第二大地区,年生产总值37.4亿元,行政区划包括7县、7镇、37个乡、141个村(居)委会,人口10余万,包括21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93%.
2 脊椎动物多样性
2.1 兽类生物多样性
阿里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极具高山高原特色的兽类区系组成.郑昌琳[2]调查表明,阿里地区共有兽类6目12科26种,全属古北区种类,其中青藏高原特有种12种,占该地区兽类总种数的46.2%.阿里地区有蹄类、兔形目和啮齿类动物相对丰富,共计16种,占该地区总种数的64%.其中,有蹄类的优势种为藏野驴(Equus kiang)、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等,常3~5只集群活动于开阔草地,偶见数十只集群.兔形目优势种为西藏鼠兔(Ochotona thibetana)和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前者是针茅、变色锦鸡儿灌丛化草原的优势种,后者是真草原优势种之一,密度高达25~80个洞口/亩,在局部地区数量很多(如阿里地区西南部孔雀河流域的普兰县巴噶区),最高达200个洞口/亩.据测定,每只高原鼠兔日食鲜草77.3 g,52只鼠兔采食量即相当于1个绵羊单位.在鼠害猖獗的日土县德汝草地调查时,鼠洞密集区已寸草不生,草场消失殆尽[3-4].党荣理[5]的调查表明阿里地区有啮齿类动物5科8属13种,其中青藏高原特有成份占总种数的53.8%,主要分布于河谷、湖盆阶地上发育的草甸、灌丛群落中.啮齿类优势种为白尾松田鼠(Phaiomys leucurus)和藏仓鼠(Cricetulus kamensis),均为常见种,前者在沼泽化区域密度较高(如班公湖湖滨阶地的日土县日松区),后者常见侵入屋内.大型啮齿动物主要为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多分布于噶尔县、措勤县和改则县,常栖息于向阳坡,体形健壮,挖掘能力极强,洞穴大而深,每挖掘一个洞穴要破坏1~2 m2的草地.旱獭喜日采食量1.5kg,3只旱獭即相当1个绵羊单位的采食量[3-4].为适应阿里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兽类演化出了相应的身体特征和行为模式.如喜马拉雅旱獭和西藏棕熊(Ursus arctos)具有假冬眠习性,有利于度过漫长的严冬;由于昼夜温差很大,夜间温度急剧下降,几乎所有兽类均为昼间活动,甚至啮齿类动物也极少在午夜以后活动,如藏仓鼠;为适应高寒环境,兽类在体温调节方面表现出体表被毛浓密厚绒、皮下脂肪发达的特点,如野牦牛(Bos mutus);在高原开阔的草原上,掩蔽条件不良,兽类演化出了其他有利于躲避天敌的特征,有蹄类动物具有迅速奔跑的能力和相应的身体特征,如藏羚羊宽阔的鼻腔和轻捷的体型,而高原鼠兔大而隆起的听泡能提升听觉能力,向上翘起的眶上突能提升视觉能力.此外,据《西藏自治区志·动物志》和相关资料记载,阿里地区还有灰狼(Canis lupus)、雪豹(Uncia uncia)、赤狐(Vulpes vulpes)和西藏黄鼬(Mustela sibirica)等[6-7].
阿里地区分布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兽类有野牦牛、金丝野牦牛(Bos grunniens)、藏羚羊、藏野驴、雪豹、北山羊(Capra sibirica)等;国家二级保护兽类有藏原羚、岩羊(Pseudois nayaur)、盘羊(Ovis ammon)、猞猁(Felis lynx)、兔狲(Felis manul)、棕熊、荒漠猫(Felis bieti)、藏狐(Vulpes ferrilata)等;国家三级保护动物有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该地区地处偏远,人为干扰相对较少,国家级保护动物较多,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
2.2 鸟类生物多样性
在鸟类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严酷的自然环境,种类相对贫乏.李德浩和王祖祥[8]在阿里地区的调查共采集到鸟类13目27科71种,分布于多种生境中.在湖泊、河流、沼泽、湖岸等水域分布有斑头雁(Anser indicus)、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凤头潜鸭(Aythya fuligula)、普通秋沙鸭(Mergus merganser)等;在高山旷野生境中分布有草原雕(Aquila nipalensis)、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等;在高山裸岩生境中分布有高山雪鸡(Tetraogallus himalayensis)、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等;在沟谷、农田和居民点分布有石鸡(Alectoris chukar)、高原山鹑(Perdix hodgsoniae)和岩鸽(Columba rupestris)等;在戈壁荒漠则分布有大量西藏毛腿沙鸡(Syrrhaptes tibetanus)等.其中,约2/3的鸟类为食虫鸟类,捕食农林牧业害虫,如蝗虫、草原毛虫等,具有积极意义.在鸟类行为方面,张国钢等[9]在班公错鸟岛发现斑头雁(Anser indicus)将卵产于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的巢中,推测这是由于繁殖地巢址和巢材短缺而引发的种间巢寄生行为.
阿里地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黑颈鹤、白尾海雕(Haliaeetus albicilla)、玉带海雕(Haliaeetus leu-coryphus)、胡兀鹫、金雕(Aquila chrysaetos)、黑头角雉(Tragopan melanocephalus)、高原山鹑、西藏毛腿沙鸡等;属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猎隼(Falco cherrug)、秃鹫(Aegypius monachus)、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红隼(Falco tinnunculus)、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草原雕、秃鹫(Aegypius monachus)、黑鸢(Milvus Korschun)、白尾鹞(Circus cyaneus)等;其它常见鸟类还有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鱼鸥(Larus ichthyaetus)、斑头雁(Anser indicus)、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针尾鸭(Anas acuta)、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白眼潜鸭(Aythya nyroca)、白头鹞(Circus aeruginosus)、草原鹞(Circus macrourus)、高原山鹑、石鸡、红脚鹬(Tringa totanus)、白腰草鹬(Tringa ochropus)、海鸥(Larus canus)等[10].阿里地区鸟类中有多种猛禽以高原鼠兔为主要食物,正确认识高原鼠兔在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科学开展灭鼠工作,是维持鸟类多样性的基础.此外,对当地湿地生境的保护,能保证迁徙水禽的多样性.
2.3 两栖和爬行动物生物多样性
由于两栖和爬行类动物为变温动物,阿里地区干旱寒冷的自然环境极不利于其生存繁殖,相应的研究亦很少开展.在极少的研究成果中,费梁等[11]对新疆和西藏27个地理居群原定名为绿蟾蜍(Bufo viridis)的形态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分布于西藏阿里札达者应为一新种,即札达蟾蜍(Bufo zamdaensis).在爬行类方面,黄永昭[12]于1974年7~9月在阿里地区采集到爬行动物1目2科2属2种,分别为西藏沙蜥(Phrynocephalus theobaldi)和拉达克滑蜥(Scincella ladacensis).西藏沙蜥广泛分布于阿里各地,海拔4 800m处尚可见到,主要栖息在山麓冲积或洪积的倾斜沙砾地带、丘陵缓坡、河湖沿岸的干燥沙砾地或沙丘上,以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主要食物.拉达克滑蜥从海拔3 700 m到5 000 m均有分布,主要栖息在河岸阶地、沟谷斜坡、农田隙地、有灌丛砾石的湿润地段,筑巢于土隙石缝中,以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食.
2.4 鱼类生物多样性
在鱼类方面,虽然阿里地区河流、湖泊较多,但是由于海拔较高,源自于高山冰雪融水,河水温度较低,鱼类种类丰富度较低.武云飞和朱松泉[13]在阿里地区的鱼类资源调查共获得12种(亚种),其中鲤科(Cyprinidae)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7种(亚种),鳅科(Cobitidae)条鳅属(Nemacheilus)5种,包括横口裂腹鱼(Schizothorax plagiostomus)、西藏弓鱼(Racoma tibetanus)、斑重唇鱼(Diptychus maculatus)、锥吻叶须鱼(Ptychobarbus conirostris)、高原裸裂尻鱼指名亚种(Schizopygopsis stoliczkae stoliczkae)、高原裸裂尻鱼班公湖亚种(Schizopygopsis stoliczkae bangongensis)、高原裸裂尻鱼玛法木湖亚种(Schizopygopsis stoliczkae maphamyumensis)、班公湖条鳅(Nemachilus deterrai)、高原条鳅(Nemachilus stoliczkae)、小眼条鳅(Nemachilus microps)、窄尾条鳅(Nemachilus tenuicauda)和阿里条鳅(Nemachilus aliensis).万法江[14]和严莉等[15]在狮泉河流域还捕获了长丝裂腹鱼(Schizothorax dolichonema)、双须叶须鱼(Ptychobarbus dipogon)、异尾高原鳅(Triplo stewarti)、窄尾高原鳅(Triplo tenuicauda)、小眼高原鳅(Triplo microps)、西藏高原鳅(Triplo tibetana)、斯氏高原鳅(Triplo stoliczkae),其中裂腹鱼类主要分布于狮泉河中下游,条鳅主要分布于中游水流较缓、砾石较多的石缝中.该地区鱼类区系组成简单,全部属中亚高山鱼类,均分布于海拔3 500m以上、辐射强烈的高海拔地区.以上鱼类生长缓慢,性成熟迟,繁殖力低,蛰居杂食,具有能适应高原高寒水域的特征,如裸裂尻鱼属(Schizopygopsis)鳞片退化、皮肤和皮下脂肪增厚、体表粘液腺发达[13,16].作为该地区优势种,高原裸裂尻鱼体重和体长较大,食性能随食物环境改变,具有较强可塑性.班公湖水生动物丰富,特别是浅水区,湖中高原裸裂尻鱼主要以水生昆虫和有机碎屑为食,偏肉食性的[14].得益于阿里地区严寒和相对封闭的水域环境、藏区不杀生的习俗,较好的保存了独具特色的鱼类物种多样性,保护当地鱼类资源,深入研究其适应恶劣环境的生理机制,是下一步工作的大致方向.
3 水生无脊椎动物生物多样性
阿里地区水域宽广,水温较低,生产力较弱,水生无脊椎动物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但却是鱼类生存的必需饵料,需进一步调查其种类、数量和分布.万法江[14]在狮泉河流域共检出底栖无脊椎动物26种,主要包括环节动物的寡毛类(Oligochaeta)、软体动物的螺类(Gastropoda)、甲壳动物的虾类和水生昆虫等.水生昆虫以寡毛类和摇蚊幼虫(Chironomid)分布最为广泛,其中摇蚊幼虫为主,如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等齿多足摇蚊(Polypedilum fallax)和直突摇蚊(Orthocladius spp.)等.寡毛类偏好淤泥底质,摇蚊幼虫偏好多碎屑的底质,螺类、钩虾(Gammaridea)、水生昆虫等偏好流速较大的石砾底质.在浮游动物方面,袁显春等[17]在阿里地区21个湖泊的调查得到浮游动物3门11属14种,其中原生动物4属4种,轮虫1属1种,桡足类5属7种,枝角类1属1种.其中有经济种西藏拟溞(Daphniopsis tibetana)和卤虫(Brine shrimp)分布的湖泊数分别为5和12个,生物量较大的有卤虫、桡足类(Copepods)和枝角类(Cladocera),并首次在西藏范围内记录到了亚洲后镖水蚤(Metadiaptomus asiaticus).此外,万法江[14]在狮泉河流域共检出原生动物29属59种,其中肉足虫类(Sarcodina)11属37种,如盘状表壳虫(Arcella discoides)、褐砂壳虫(Difflugia avellana)等,纤毛虫类(Ciliated protozoa)包括简裸口虫(Holophrya simplex)小长吻虫(Lacrymaria minbna)等18属22种;检出轮虫(rotifer)7科19属35种,包括宿轮科(Habrotrochidae)、旋轮科(Philodinidae)、臂尾轮虫科(Brachionidae)、腔轮科(Lecanidae)、椎轮科(Notommatidae)、疣毛轮科(Synchaetidae)和镜轮科(Testudinellidae),其中以臂尾轮虫科种类最多,计14种,如无角狭甲轮虫(Colurella colurus)、盘状鞍甲轮虫(Lepadella patella)等;共检出枝角类5科(薄皮溞科(Leptodoridae)、仙达溞科(Sididae)、盘肠溞科(Chydoridae)、溞科(Daphniidae)和粗毛溞科(Macrothricidae)8属18种,优势种类为尖额溞和盘肠溞;检出桡足类2目(猛水蚤目(Harpaticoida)和剑水蚤目(Cydopoida)8种,如隆脊异足猛水蚤(Canthocamptus carlnatus)、锯缘真剑水蚤(Eucyclops erruiatus)等.在浮游动物分布上,以狮泉河流域例,主河道中以革吉段的生物量最高,支流中以加木河的生物量最高[14].
4 藻类生物多样性
在浮游植物方面,袁显春等[17]调查了阿里地区21个湖泊,采得44个浮游生物样品和22个水化学样品.经鉴定分析得浮游植物5门(硅藻门(Bacillariophyta)、蓝藻门(Cyanophyta)、金藻门(Chrysophyta)、甲藻门(Pyrrophyta)和绿藻门(Chlorophyta))49属105种(变种),其中硅藻门19属63种(变种),占总种数的60%,蓝藻门15属25种,占23.8%.此外,万法江[14]调查了狮泉河流域浮游植物,由于河水流速较缓,河谷开阔,河漫滩、歧流和曲流发育,为狮泉河水生生物提供了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条件,共检出浮游植物5门53属106种,其中硅藻门21属67种,占总种数的63.2%,密度占95.6%,生物量占95%,是绝对的优势种类,包括颗粒直链藻(Melosira granulata)、弯羽纹藻(Pinnularia gibba)等;绿藻门19属24种,占22.6%,包括短棘盘星藻(Pediastrum boryanum)、双射盘星藻(Pediastrum biradiatum)等;蓝藻门11属13种,占 12.3%,包括水华微囊藻(Microcystis flosaquae)、优美平列藻(Merismopedia elegans)等;裸藻门(Euglenophyta)的尾裸藻(Euglena caudata)和隐藻门(Cryptophyta)的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各1属1种.在阿里地区相对贫瘠的水域生态系统中,藻类是最主要的生产者,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有必要更深入的调查其种类和资源.
5 维管植物
受调查条件所限,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阿里地区植物种类调查结果有所不同.刘尚武等[18]于阿里地区采集到维管植物共计46科181属349种,标本1200多号,其中菊科(Asteraceae)53种,禾本科(Poaceae)37种,豆科(Leguminosae)22种.周家福等[19]基于样线、样地调查资料,鉴定记录到阿里地区西部共有种子植物53科159属319种(裸子植物1科1属2种,被子植物52科158属317种).另有研究表明,阿里地区维管植物有670种,其中种子植物663种,隶属于51科225属,藓蕨类共5科7种.草地建群种和主要伴生种主要是禾本科、莎草科(Cyperaceae)、菊科、藜科(Chenopodiaceae)、豆科、十字花科(Brassicaceae)等34科177种[20-21].在水生植物方面,万法江[14]在狮泉河流域共采集到7科14种,主要为湿生植物和沉水植物,如扁水毛莨(Batrachium bungei)、帕米尔眼子菜(Potamogeton pamiricus)、红线草(Potamogeton pectinatus)和短柱角果藻(Zannicheilia palustris)等,几乎扎西岗以上河道均有分布.总体而言,由于阿里地区平均海拔高,气候寒冷、干旱、多风、降水稀少,植物种类相对较少.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景天科(Crassulaceae)[22]、龙胆科(Gentianaceae)[23]、裸子植物[24]种类数量均为最少的.
阿里地区资源植物有淀粉植物、油料植物、有药用植物等类型.淀粉植物有蕨麻(Potentilla anserina)、萎陵菜(Potentilla chinensis)等;油料植物有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及西藏白皮松(Pinus gerardiana),但资源数量较少,经济意义不大;药用植物资源有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红景天(Rhodiola rosea)、麻黄(Ephedra sinica)、当归(Angelica sinensis)、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e)、龙胆(Elephantopus scaber)、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大黄(Rheum palmatum)、报春花(Primula malacoides)等;纤维植物以新疆杨(Populus bolleana)、班公柳(Salix bangongensis)、西藏白皮松等乔木为主,分布区窄,数量少,经济意义不大.班公柳分布于海拔3 600~4 600 m,其人工林主要分布在普兰县城、札达县城、日土县城和狮泉河镇等地,原始林主要分布于日土县.西藏白皮松仅分布于札达县的什不奇与楚鲁松杰等地的河谷山地,是喜马拉雅地区西部稀有的针叶树种,以群聚为主或与椒状白蜡、高山栎(Quercus semecarpifolia)等混交[10,25].阿里地区维管植物生长缓慢,不适宜于大量开发利用,应对其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和科学保护.
6 植被类型和分布
阿里地区森林覆盖率极低,仅仅在札达、普兰和日土县等低海拔谷地有很少量疏林,且主要树种为班公柳和西藏白皮松.沙棘林在低海拔地带为小乔木,当海拔达到4 200 m以上时,只有垫状灌木丛.天然灌木林主要常见种为秀丽水柏枝(Myricaria elegans)、变色锦鸡儿等,主要分布于噶尔县、札达县和普兰县[10,25].
相对于贫瘠的森林植被,阿里地区有复杂多样的草地植被:温性草地类型有三种(草原、荒漠草原、荒漠)、高寒草地类型也有三种(草原、荒漠、草甸)、其余为低平地草甸、沼泽.其中,高寒草原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由寒旱生的丛生禾草(针茅属(Stipa)、羊茅属(Festuca)等)为主要优势层片[4,25].由此,阿里地区虽然草原面积大,但是质量很低,不适合放牧的草原比例高达73.85%,而适合放牧的草原仅有2.71%[26].
植被具有显著的垂直分布特征,高山冰雪带分布于6 000 m以上,高山寒冻垫状植被带分布于5 000~6 000m,山地高寒草原分布于4 000~5 000 m,其中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高山蒿草(Kobresia pygmaea)和青藏苔草(CareJc moorcroftii)为优势种.山地荒漠草原主要分布于4 000 m以下的广大宽谷、盆地和山麓地带,其中沙生针茅(Stipa glareosa)、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和灌木亚菊(Aania fruticulosa)为优势种[27].
在植被水平分布方面,主要取决于温度和湿度,具有如下特点:(1)在地形平坦开阔、排水良好、海拔4 300~4 700 m的地区主要以针茅为主的高寒草原;(2)针茅、变色锦鸡儿灌丛化草原仅狭条状分布于冈底斯山南麓[28];(3)秀丽水柏枝、垫状驼绒藜(Ceratoides compacta)寒荒漠仅见于阿里地区西北隅[29];(4)灌丛群落物种组成较为单一,优势树种在群落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常常形成单优群落[30].
在植被时间演替方面,肖洪浪[31]研究表明,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资源不合理利用(如将大量红柳(Tamarix ramosissima)连根拔起作为薪柴使用),狮泉河宽谷区呈现出旱化、盐化和沙化的退化趋势,具体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为:秀丽水柏枝、赖草(Leymus secalinus)灌丛草甸→变色锦鸡儿、秀丽水柏枝荒漠化灌丛草甸→驼绒藜(Ceratoides)、变色锦鸡儿荒漠、蒿草(Artemisia)草甸→藏沙蒿(Artemisia wellbyi)、嵩草荒漠化草甸→驼绒黎、灌木亚菊沙化荒漠.在退化最为明显的革吉县、改则县和措勤县,随着草地退化,过去一段时间有毒伴生种或偶见种演变成了优势种,草地生态逆向演变明显.比如60年代以前改则县麻米湖周围主要是灌丛草场,如今演变为蓝翠雀花(Delphinium caeruleum)、狼毒、酸模(Rumex acetosa)等有毒有害杂类草的沙化地.据相关统计,阿里地区分布毒草接近100种,毒草面积已占改则县冬融河流域草地总面积的20%左右[4,25].
7 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寄生虫和昆虫
阿里地区一些生物是重要的人兽共患病宿主,与当地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党荣理等[32]对5种自然疫性疫病羊血清学的调查结果表明,野兔热、Q热、斑点热、斑疹伤寒和恙虫病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21.2%、40.3%、52.2%、32.9%和42.2%,其中斑点热和斑疹伤害在整个阿里地区均有检出,而恙虫病则集中分布于普兰县城以南一带.此外,格桑曲珍[33]于2007~2010年在阿里地区采集到鼠疫宿主动物喜马拉雅旱獭 107只,检出鼠疫菌 54株,检出率为50.47%,密度调查表明期间喜马拉雅旱獭种群平均密度为0.31只/hm2.顿珠[34]梳检喜马拉雅旱獭132只,平均密度达1.04只/hm2,测定鼠疫F1抗体血清211份,阳性125份,阳性率为59.3%,鼠疫F1抗原69份,阳性31份,阳性率为44.9%.以上数据说明近十年来阿里地区动物间鼠疫频发,检出率、宿主密度和血清阳性率均很高.
在寄生虫方面,在阿里地区措勤县、改则县和革吉县的调查共采集到18种家畜寄生虫标本:肝片吸虫(Fasciola hepatica)、前后盘吸虫(Paramphistomum cervi)、细粒棘球蚴(Echinococcosis granulosa)、细颈囊尾蚴(Cysticercus tenuicollis)、多头蚴(Coenurosis cerebralis)、盖氏曲子宫绦虫(Helictrometa giardi)、无中点无卵黄腺绦虫(Avitellna centripunctata)、丝网状网尾线虫(Dictyocaulus filaria)、粗纹食道口线虫(Oesophagostomum asperum)、毛首线虫(Trichuris spp.)、旋毛形线虫(Trichinella spiralis)、硬蜱(Ixodidae)、软蜱(Argasidae)、山羊疥螨(Sarcoptes scabiei)、马红尾胃蝇(Gasterophilus haemorrhoidalis)、羊狂蝇(Oestrus ovis)、锯齿状舌形虫(Linguatula serrata)、绵羊虱蝇(Melophagus ovis),其中13种的感染率在45%以上[35].党荣理[32]的调查证实了阿里地区家畜体外寄生虫蚤3种(花蠕形蚤(Vermipsylla alakurt)、犬栉首蚤(Ctrnocephalides canis)和人蚤(Pulex itritans)、蜱4种(银盾革蜱(Dermacentor niveus)、猛突血蜱(Haemaphysalis montgomeryi)、西藏革蜱(Dermacentor everestianus)和微小牛蜱(Boophilus microplus),其中银盾革蜱栖息孽生于畜群转场路线附近场所,为优势种.张桂林等[3]等采集到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蚤计4科8属11种,其中冰武蚤宽指亚种(Hoplopsyllus glacialis)、方指双蚤(Amphipsylla quadratedigita)为优势种,寄生于白尾松田鼠、拉达克鼠兔(Ochotona ladacensis)、喜马拉雅旱獭和高原鼠兔,其中高原鼠兔带蚤率最高,为67.6%,蚤指数3.01.阿里地区啮齿动物、蜱、蚤的大量存在,为自然疫源性疫病提供了宿主和媒介条件,并随着放牧的迁徙而移动或扩散.有专家对阿里地区西藏革蜱在土拉菌病自然疫源地中的媒介作用进行了研究,证实该蜱类是土拉菌病主要传播媒介,并能经卵传递至下一代,使媒介、病原、宿主在该自然疫源地中周而复始的循环[36].由于该地区人、畜、啮齿动物三者间接触密切,以上寄生虫及其所带自然疫源性疾病对人畜威胁较大.
在农牧业害虫方面,蝗虫是阿里地区最主要的害虫,分布于河边草地和农田等生境,危害农牧业生产.印象初[37]在阿里地区采集到蝗虫标本2科8属9种,分别为异距五刺蝗(Pentaspinula calcara)、红足皱背蝗(Ruganotus rufipes)、断线缺耳蝗(Atympanum carinotus)、暗纹缺耳蝗(Atympanum nigrofasciatus)、蚍蝗(Eremippus persicus)、西藏飞蝗(Locusta migratoria)、白边痂蝗(Bryodema luctuosum)、丽色小屏蝗(Auriobulus splendens)和环角蓝尾蝗(Cyanicaudata annulicornea).其中,西藏飞蝗分布广,数量多,危害大.苏红田[38]研究表明西藏飞蝗危害从2003年逐年加重,2006年危害面积达到25万hm2,是有详细记载以来西藏飞蝗危害面积最大的年份,分布范围从金沙江沿岸东扩到大渡河沿岸,危害严重区域从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到噶尔河和金沙江流域.对草原影响较大的害虫还有黄斑草毒蛾(Gynaephora alpherakii)、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银钩夜蛾(Panchrysia ornate)、白边地老虎(Euxoa oberthuri)、八字地老虎(Xestia cnigrum)及蚜虫等[39],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黄斑草毒蛾(Gynaephora alpherakii),俗称草原毛虫、红头黑毛虫[40-41],隶属鳞翅目(Lepidoptera)毒蛾科(Lymantridae)草毒蛾属(Gynaephora),为青藏高原特有的草地害虫,喜食嵩草、羊茅、披碱草(Elymus nutans)、珠芽蓼(Polygoum viviparum)等牧草,在受害区一般10~30条/m2,最严重的区域密度高达500~600条/m2,危害区主要在温度较高的阿里南部地区[4].
8 结论
综上所述,阿里地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自然地理条件特殊,战略意义重大,其海拔高,气候干旱、寒冷、多风、少降水,整体环境条件不适宜于大多数动植物生存繁殖.因此,一方面阿里地区动植物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生态脆弱,破坏后很难恢复;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阿里地区独具特色的高原生物物种,尤其是大量具有指示性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如藏野驴等)和在维护当地生态系统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物种(如高原鼠兔等),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物种对象.随着当地经济发展,交通条件改善,人流物流来往频繁,阿里地区正发生重大变化,其生物多样性及其利用开发也面临新的问题,对人类干扰日益增加的区域(如狮泉河镇等)及其周边进行重点调查和动态监测,研究人类开发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维持高原生态系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针对阿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系统科学考察仅见于1974年青海省生物研究所开展的工作,而数十年来,阿里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变化巨大,急需再次进行系统性综合科学考察,这既是完善我国动植物资源数据库的基础性科学工作,也是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 张斌,常青.西藏阿里地区土种的划分[J].干旱区研究,1993,10(1):67-73.
[2] 郑昌琳.西藏阿里兽类区系的研究及其关于青藏高原兽类区系演变的初步探讨.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91-226.
[3] 张桂林,马德新,窦君,等.西藏阿里地区啮齿动物及其体外寄生蚤生态调查[J].医学动物防治,2000,16(4):184-185.
[4] 杨汝荣.西藏阿里草地退化现状与防治措施[J].中国草地,2002,24(1):61-67.
[5] 党荣理,马德新,王天祥,等.西藏阿里地区啮齿类动物调查[J].地方病通报,1995,10(3):61-63.
[6] 柏志明.藏北高原野生动物览胜[J].野生动物,1986:17-20.
[7] 普布,李丹,朱映久.西藏不同海拔梯度及地区哺乳动物属种数量分析[J].动植物研究,2012,3:68-70.
[8] 李德浩,王祖祥.西藏阿里地区的鸟类.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39-72.
[9] 张国钢,孙戈,孙静,等.西藏阿里班公错斑头雁的种间巢寄生行为[J].动物学杂志,2017,52(4):664-667.
[10] 邓坤枚.西藏阿里地区的林业资源及其发展方向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2):240-245.
[11] 费梁,叶昌媛,黄永昭,等.中国西部地区绿蟾蜍的分类研究[J].动物学研究,1999,20(4):294-300.
[12] 黄永昭.西藏阿里地区的爬行动物.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73-79.
[13] 武云飞,朱松泉.西藏阿里鱼类分类、区系研究及资源概况.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3-38.
[14] 万法江.狮泉河水生生物资源和高原裸尻鱼的生物学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4:15-39.
[15] 严莉,陈大庆,张信,等.西藏狮泉河鱼道设计初探[J].淡水渔业,2005,35(4):31-33.
[16] 扎西次仁,其美多吉.浅析西藏鱼类资源及渔业经济[J].西藏大学学报,1993,8(3):83-86.
[17] 袁显春,郑绵平,赵文,等.西藏阿里地区盐湖浮游生物生态调查[J].地质学报,2007,81(12):1754-1763.
[18] 刘尚武,潘锦堂,张盍曾.西藏阿里地区植物区系.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83-134.
[19] 周家福,张锦华,刘淑珍,等.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J].山地学报,2007,25(5):608-616.
[20] 西藏阿里地区农牧局.西藏阿里土地资源[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1991:191-279.
[21] 马琳雅,黄晓东,方金,等.青藏高原草地植被指数时空变化特征[J].草业科学,2011,28(6):1108-1116.
[22] 德吉,任建材,郭小芳.西藏不同海拔梯度和地区景天科植物属种数量分析[J].西藏科技,2014,5:66-70.
[23] 吴丹,郭小芳,德吉等.西藏不同海拔梯度和地区龙胆科植物属种数量分析[J].西藏科技,2010,5:65-66.
[24] 郭小芳.西藏不同海拔梯度及地区裸子植物属种数量分析[J].西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4(1):24-28.
[25] 畅慧勤,徐文勇,袁杰,等.西藏阿里草地资源现状及载畜量[J].草业科学,2012,29(11):1660-1664.
[26]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草原[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60-76.
[27] 李森,杨萍,董玉翔,等.西藏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87-407.
[28] 张新时.西藏阿里植物群落的间接梯度分析、数量分类与环境解释[J].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91,15(2):101-113.
[29] 潘锦堂,张盍曾,刘尚武.西藏阿里地区的植被.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48-164.
[30] 黄清麟,张超,张晓红,等.西藏灌木林群落结构特征[J].山地学报,2010,28(5):566-571.
[31] 肖洪浪.青藏高原西部狮泉河宽谷区的荒漠化进程[J].干旱区研究,1994,11(2):41-46.
[32] 党荣理,王天祥,周新荣,等.西藏阿里地区家畜与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调查[J].医学动物防治,2000,16(2):85-86.
[33] 格桑曲珍,尼玛次仁,王智.2007-2010年西藏阿里地区鼠疫监测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1,26(5):51-52.
[34] 顿珠,格桑曲珍,才旺加措,等.2007年西藏阿里地区鼠间鼠疫监测分析[J].地方病通报,2008,23(1):58-59.
[35] 尼玛次仁.西藏阿里地区家畜寄生虫病调查[J].中国畜牧业,1998:19-19.
[36] 马德新,张桂林,王天祥,等.阿里土拉菌病疫源地中西藏革蜱的媒介作用[J].地方病通报,1997,12(1):60-61.
[37] 印象初.西藏阿里地区的蝗虫.西藏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77-190.
[38] 苏红田,白松,姚勇.近几年西藏飞蝗的发生与分布[J].草业科学,2007,24(1):78-80.
[39] 王保海,林大武.西藏植保研究[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4:23-204.
[40] 陈一心,王保海,林大武.西藏夜蛾志[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1:267-268.
[41] 王保海,袁维红,王成明.西藏昆虫区系及其演化[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2:230-236,24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