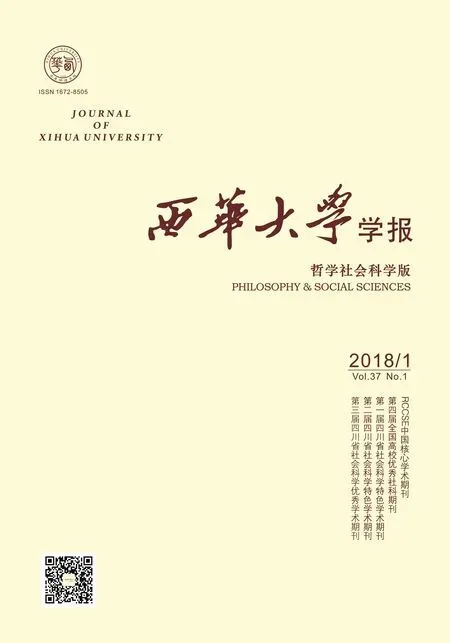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2018-02-09曹顺庆吴结评
曹顺庆 吴结评
吴结评(以下简称吴):随着海外汉学内涵与外延的扩展,海外汉学的名称问题倍受争议。从发展阶段及其研究内容来看,有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之分。sinology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指西方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对中国古典人文科学知识的研究。它是以法国为研究中心的对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主要探讨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方面的问题。Chinese Studies是现代中国学,是指西方各国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的研究,它更多地注重对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近30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学界对海外汉学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如王晓路指出的有“海外汉学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logy)、“海外汉学的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 of Sinology)、“海外汉学的再研究”(Re-study of Sinology)和“海外中国学研究”(Research on Chinese Studies)等。因此,如要找到一个合理、简明、兼顾内涵和外延的术语,他提出可行的命名是“国际中国学研究”(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这样,无论从时间跨越还是从空间范围都能将其涵盖其中,并且兼顾民族国家多元族群概念,同时表明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在这一知识推进的平台上同属一个学术共同体。请问曹师顺庆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名称命名的呢?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汉学”在中文里一指汉代经学研究,它强调考据与训诂的治学方法;二指清代“乾嘉学派”以严谨朴实的考据学风而形成的汉学,与“宋学”相对。英语中的“sinology”,其前缀“sino-”指中国的“秦”,后指代中国,“sinology”即指有关中国的学问或学说。而在早期的“sinology”研究中,西方传教士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中国经典文献,且主要的学术方式是语文学,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和对文献的考证与注疏来进行研究,然后将其翻译为西文。从学者身份、研究内容和学术范式来看,将其学术称为海外汉学(sinology)有其合理性。
吴:那关于兼顾民族国家多元族群概念呢?
曹:我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多民族的历史构成的——中国正史二十五史中有少数民族主导政权的朝代专史,如《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辽史》《金史》等。在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也多注重从“史”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如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篇文体论,还有南宋时期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到“正史”,中国的文学史观约等于汉文学史观,它几乎不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桩几多争论的公案——中国是否有史诗?答案是:中国没有史诗。事实上呢,中国不仅有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史诗,还有成千的史诗在少数民族中间流传,如彝族的《梅葛》、纳西族和白族的《创世纪》、哈尼族的《十二奴局》等等。为什么上百年的“中国是否有史诗”的争论到今天才尘埃落定?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文学史观是以汉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史观。
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文学界掀起一股“重写文学史”的风潮。
曹:是的,在其后的十年间,陆续推出了六、七种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新版本,将之前只字未提或一带而过的作家设专节进行讲解,如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还有就是对以前作为“封资修”的代表作被扫出文学史大门的通俗小说,现在有专章讲述。但是,这些文学史主要从政治历史和文学本体论两方面考虑如何“重写文学史”,而完全没有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文学史观的角度去思考,我要说,这样的中国文学史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是残缺的中国文学史。
吴:面对残缺的中国文学史,我们该如何作为呢?
曹: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从不同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来观察其文学实践,选取从古代到现当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重写中国文学教材。其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包含的八个二级学科中就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可以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院校开设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活动,推进“多民族文学史观”建构的进程。
吴:嗯,您觉得中外学术界在“中国学”这一领域是否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曹:海外汉学从发生起就成为了中外学者互动的桥梁,从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吴注,以下同)与徐光启、李之藻的合作(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和《同文指算》),清朝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与王韬的合作(共同翻译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传》和《礼记》),到民国时期罗常培、赵元任、李芳桂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陈寅恪在清华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传统的小学。
吴:对,早在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不仅开设汉学课程,而且设置汉学教授席位,汉学家雷慕莎(Abel Remusat)为第一任汉文教授。19世纪7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开设了汉文讲座,理雅各出任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民国时期,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也曾受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主讲西方哲学、佛教和梵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受聘于北京大学。同时,陈寅恪也在牛津、剑桥任教。不过,在此之前,学术共同体中三位一体的期刊、学会、年会的“公共学术空间”早已建立起来了。
曹:学会、年会使成员之间具有相对于其他学术共同体以外的“我们感”,建立起一种学科身份的共同体意识,而学术期刊在学者各自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分工和共享规范、原则的共有知识中更多地体现着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吴:早在晚清时期,就有“上海文理学会”创办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①、“美国卫理公会”创办的《教务杂志》②等。民国时期,有《东亚杂志》③和《新中国评论》④等。
曹:提到《新中国评论》,不得不讨论更为重要的《中国评论》⑤。这是理雅各所称的“西方世界最早的真正汉学期刊”,也是《字林西报》所评的中国南方汉学界的代表性刊物。
吴:那么,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您将如何评价《中国评论》呢?
曹:首先,从学术自治方面看,《中国评论》从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而是向所有汉学研究者开放,且把“业余汉学家”⑥拒之门外,使那些关注中国的读者,在官方或某个阶层媒介之外,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其次,把握学术前沿,在语言学、神话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拓土开疆,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在这些新学科领域使中国的语言、神话、族群等研究有了新的向度,从方法论上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成功范例。如艾约瑟(J.Edkins)⑦运用语言学研究汉语方言、语音和字体的演变以及语法、词汇、古今汉语比较等;丹尼斯通过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中国和雅利安种族的神话与传说进行了比较研究;欧德里在《中国评论》发表的《客家历史纲要》,利用族谱和在当地所做的田野调查,从移民史的角度对客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第三,在其内部有了明确的分工,并且有充分的交流。如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⑧对艾约瑟将各种语言与汉语拉上亲缘关系的做法颇有微词,而主编欧德里热情地欢迎福兰阁加入到这样的学术讨论中,共同去澄清事实,了解真相⑨。
吴:被称为民国四大学术期刊⑩之一的《燕京学报》,是以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术期刊,它以其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北方学术重镇,并且辐射至整个汉学界,您认为它在学术共同体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曹:这是一个学术阵容了得的群体,三任主编容庚、顾颉刚、齐思和,一为古文字领域一代宗师,一为“古史辨派”创始人,一为现代史学理论开山人。作者群中,除了国内知名学者,如许地山、冯友兰、陈垣、郭绍虞等,还有国外知名学者,如鸟居龙藏、钢和泰等⑪。从这个学术群体中既可以看到其学术凝聚力,也可以看到其开放的态度。从学术范式上看,也有革新之意,如在论文中增加英文摘要以及横排、标点和文体多样化的要求⑫。从学术自律和监督方面看,它强调学术的原创性和知识生产中的深度加工,杜绝抄袭以及学术上的浅陋和重复生产⑬。
吴:《燕京学报》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英雄不问出处。著名学者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时,他还是一个中学老师,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且内容与主编顾颉刚的观点相左,可其论文不仅被刊物接纳了,顾颉刚还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
无论作者是否是已成学者,还是是否出自学术名门,只要你的论文达到了刊物要求的品质,你都会得到刊物的接纳和承认。刊物从学术自律开始,从学术原创与学术价值出发,搭建起一个真正的学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促成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自发生成,自觉构建,这在当今对我们太有现实意义了。
从理想回到现实,从历史走到今天,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国际中国学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2017年8月17日至20日在河南开封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正式批准了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一级学会下增设海外汉学研究会二级学会。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您对此有何看法?
曹: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国内对海外汉学多有关注,对各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献做了汇编。80年代呢,主要是对海外汉学著作进行翻译。到90年代,学界的研究日益高涨,这一时期有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写了《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阎纯德编写了《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第二件是1995年1月,首次“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由中科院牵头,在海口市召开;第三件是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相继建立起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⑭,不仅开展相关研究,而且还开设相关课程。进入21世纪,在学界倡导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背景下,海外汉学研究开始在反思中回归到对自己的认识,在研究中开展双向阐释的文化对话,在对话中重新建构,包括自己与对方。这期间,有中科院、国家图书馆和海内外共同发起成立的学术机构⑮。目前已有七、八个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连续性学术刊物,除《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之外,还有《法国汉学》(龙巴尔、李学勤主编)、《世界汉学》(刘梦溪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朱政惠主编)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⑯的建成。由上可见,海外汉学从研究模式、学术洞察与知识共享等层面都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好了准备。有具学界影响力的刊物、专著、网络数据库、学术队伍、学术研究会,中国学者将会在世界汉学之林发挥其必有的作用,在学术共同体中搭建起更多、更好的学术平台。
从海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化)与研究主体(国外学者)以及海外汉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海外汉学)与研究主体(中国学者)来看,两者都是跨民族、跨文化语境、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从研究理论来看,“形象学”“主题学”“类型学”“译介学”等都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有重叠交叉。当然,他们在重叠中有差异,关联中又各有其独立性,在互通、互动中形成一种“间性互生”关系。
吴:这样的话,海外汉学及海外汉学研究应该走进比较文学的课堂。
曹:对,教材中也应该有相应的章节。其实,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高旭东)中已有“国际中国学研究”⑰。在这一章中,首先把海外汉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然后对相关概念、学术史、研究内容和学科地位都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有利于比较文学的学生和研究者了解海外汉学的学术谱系、治学理路与特征、历史与现状等。
吴:2013年1月,四川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西部第一个本土中国学研究中心,该中心具有跨文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不仅从中国内部去考察中国,也从世界外部去研究中国。
曹:说起“本土”,它并不是要“与世隔绝”,相反,它是指某个地域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并在这个关联中“自我”与“他者”具有可比性与交互性。换句话说,就是将中国的学问与国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空间中展开,在积极的交流对话中书写自己的本土知识与学术思想,尊重他者的文化理论与差异,反思“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同的文化以及在此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思想与学说,在比较中发现知识生长点,在反思中进行跨文化双向阐释。
吴:在当今新媒体时代,学术生产更加侧重于沿着群体路径,以世界为学术大舞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建构。2007年,美国翻译家Eric Abrahamsen创建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际传播的民间网络翻译组织。通过Paper Republic(纸托邦)这个网站组织,将散居在世界各地爱好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该网站栏目分为四个部分,据我统计,截至今日,在Database一栏Authors以字母顺序列出了该网站已翻译了1171个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如阿来、巴金、北岛、毕飞宇、曹雪芹、曹禺、韩少功、老舍、鲁迅、莫言、钱钟书、王安忆、西川、阎连科(在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中位列第五)、杨绛、叶圣陶、张爱玲等。Translators列出翻译人员358名,其中不乏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如英国著名汉学家Nicky Harman⑱、美国著名汉学家Howard Goldblatt⑲等。在 Publishers一栏里,列出了中国出版社58个,国外出版社170个。在Works一栏列出中文翻译作品423部,外文翻译作品349部。在For Publishers一栏里,还有为英语国家出版社提供中国文学翻译服务信息、译员信息、图书市场信息、中国政治文化信息等。For Translators向译者提供与中国出版商打交道、洽谈翻译业务、参加翻译培训、申请翻译资助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Paper Republic把英语国家甚至非英语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都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一股翻译、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合力。
曹先生,您认为中国汉学界应该如何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新媒体时代的知识共享平台呢?
曹:我认为,通过海外汉学研究会,可以集结一批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对汉学发展通史、国别史、专题研究(如各个时期的汉学家代表的学术旨意、研究方法、范围、成就,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组织,汉籍翻译代表作的流传、流变,汉学研究方法,还有中华多民族文化研究,如藏、蒙、满、彝等等)、学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汉学史上的大事记、汉学论著文献书目等进行梳理,将海量的学术资源与信息建成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知识共享平台。其次,利用相关各级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培养外语能力强、学术有专工并且具有跨学科意识的知识性人才,使其积蓄能量,成为学术后备人才。
吴:今天和恩师畅聊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与现状,受益匪浅,谢谢您!
注释:
① 1857年9月,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汉璧礼(Sir Thomas Hanbury,1832—1907)等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次年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同年出版《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8年停刊,共出版了75卷,109册。
② 1867年1月,由当时在中国成立的“美国卫理公会”的裴来尔(L.N.Wheeler,1839—1893)在福州创办了《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872年5月停刊,1874年1月又由英国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担任主编,由月刊改为双月刊,最终于1941年停刊,历时74年。
③ 《东亚杂志》(East of Asia Magazine)在上海创刊,历时4年多(1902—1906)。
④ 1919年3月,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1919—1922),该刊旨在继承1901年停刊的汉学刊物《中国评论》,撰稿人包括翟里斯、庄延龄等汉学家,使刊物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
⑤ 1872年7月,丹尼斯(N.B.Dennys)在香港创办了《中国评论》(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隔月发行,由“德臣报印字馆”“Trübner&Co.”和别发银行三家共同出版发行,1901年6—7月出刊后停刊(参看《“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王国强,《清史研究》,2007年11月,第4期)。
⑥ 1873年,德国汉学家欧德里(E.J.Eitel,1876年担任《中国评论》主编)在《中国评论》第1卷第4期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业余汉学家》一文,批评业余汉学家们无视经典,肤浅地解读原始文献,叙述中充满臆测和武断。
⑦ 艾约瑟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余篇研究汉语的论文,并著有《上海方言词汇集》专著。
⑧ 福兰阁,曾在中国生活近20年,一生著述颇丰,有300多篇(部)学术著作与文章,代表作有《中国历史》(五卷,1930—1952)、《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讲演和论文集》(1902—1942)。
⑨ 欧德里在《业余汉学家》(见注释6)一文中指出,“我们在接触中国文献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未知领域还很广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掌握全部内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取一个分支,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们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当然也包括诸如注疏、传记和百科全书这样的二手材料,并利用哲学思维历史地、思辨地检验和批评这些材料。不对任何东西想当然,也不依赖于潮流和传统的力量,而是严格地检验那些被称为确凿和古典的事物的真实性,公正地就事论事,就像我们坐在检验法庭的凳子上一样”。
⑩ 民国四大学术期刊:《国学集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燕京学报》。
⑪ 《燕京学报》编辑成员名单:许地山、冯友兰、黄子通、洪业、吴雷川、陈垣、郭绍虞、刘廷芳、陆志韦、张东荪、翁独健、高明凯、林耀华等。时有供稿的著名学者有:王国维、陈寅恪、俞平伯、裴文中、张星烺、夏承焘、聂崇岐、侯仁之、谭其骧、冯家昇、王钟翰等。也有外国作者:鸟居龙藏、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orrlee Glessner Greel)、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钢和泰、羽溪了谛等(参看《〈燕京学报〉对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及对当下学术期刊的启示》,陈义报,《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2期)。
⑫ 《燕京学报》第一期中《简章》规定:“本报文体,不拘文言白话;但格式一律横行,并用新式标点。”
⑬ 《燕京学报》曾经刊登过两篇翻译论文,经自查发现后,郑重刊载启事,强调论文必须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才能发表,之后,该刊再也没出现过翻译论文。
⑭ 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国际中国学研究专门机构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外语学院、苏州大学等。
⑮ 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9年9月,国家图书馆成立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2010年3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在香港注册成立,该学会是由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邀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等地的汉学研究机构共同协商筹备成立的。
⑯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0年10月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特别委托而承担的大型项目,已于2014年3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网站平台发布。该网站平台显示有三个子项目数据库:新中国出版外文图书目录数据库、中国主题外文出版物目录数据库、国外中国主题出版机构数据库。据项目承担者称:“该数据库的建立,旨在通过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总结中国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基本情况、规律、经验和方法,为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文化‘走出去’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咨询。”
⑰ 《比较文学实用教程》第九章内容:国际中国学研究。第一节内容: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国际中国学研究。第二节内容:国际中国学研究案例分析。
⑱ Nicky Harman曾是英国文学翻译中心(British Center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的负责人,英国有名的翻译竞赛Harvill Secker Young Translators’Prize的评委,在伦敦创办“中国小说读书俱乐部”。她翻译过虹影的《K》、韩东的《扎根》、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张翎的《金山》等中国文学作品。
⑲ 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是中文小说翻译的高产翻译家,翻译作品多达60余部,目前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