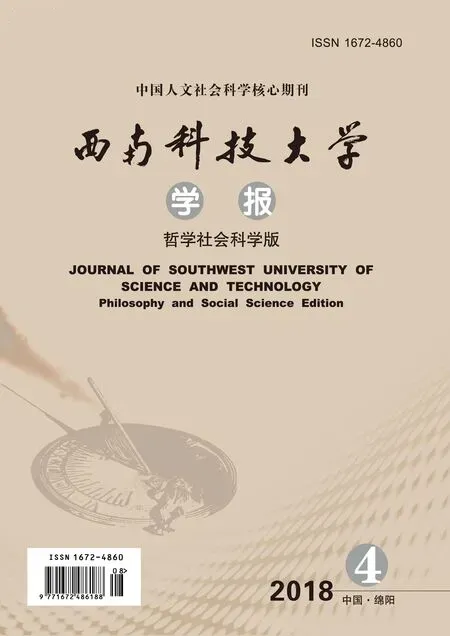“女性行侠复仇”故事新变研究
——从唐代文献到《聊斋志异·侠女》
2018-02-09李雨薇
李雨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山东青岛 266580)
《聊斋志异》内容驳杂,其取材来源也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假借前人故事复加改制点染的,也有采自当时的社会传闻、直录友人的舌笔的,还有完全或基本上出自作者虚构的篇章。《聊斋志异·侠女》正是源自于唐代文献中对“女性行侠复仇”故事的记载。蒲松龄在原有的文献记载上进行革新,使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故事面貌。结合时代背景影响下的侠文化、女性观以及作者的创作心理对《聊斋志异·侠女》中的新变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这些新变背后深层的文化机制和作者内在的心理机制。
一、 “女性行侠复仇”故事的新变
《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故事源于唐代文献中记载的蜀妇人为父复仇后,杀子弃夫而去的侠义事。其源头应为李端言的《蜀妇人传》。此外,唐代还有崔蠡的《义激》、李肇的《妾报父冤事》、薛用弱的《贾人妻》、皇甫氏《崔慎思》等版本,宋代的《翰苑名谈》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形式各异,既有杂传、杂文也有小说。①
但这些文献记载应是同一事源。其依据有二:(1)《义激》中提及崔蠡读李端言的《蜀妇人传》而作《义激》,《蜀妇人传》中女侠复仇发生于贞元(785-805)中,《义激》中则提及“蜀妇人在长安,凡三年,来于贞元(804)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805),去于元和(806-820)初。”[1]54据《旧唐书》卷一一七记载“蠡,字越卿,元和五年(810)擢第,累辟使府。”[2]按时间推算,女侠复仇之事发生在崔蠡生平期间,且崔蠡在《义激》中将其做真实事件记载。由此推断,女侠复仇之事为真实事件的可能性很高。此外,《义激》中将蜀妇人与高愍女、庚义妇、杨烈妇并列,其中高、杨二人因李翱撰碑、传而著名,《新唐书》卷二百五也记载二人相关事迹。《高愍女碑》 云:“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高)彦昭时为颖州刺史,昌黎韩愈始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3]《杨烈妇传》云:“若高女、杨烈妇者,虽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湮灭而不传,故皆叙之,将告于史官。”[3]由此推断高、杨二人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蜀妇人与二人并列,其事迹也应为真。(2)在记载这一事件的《蜀妇人传》《义激》《妾报父冤事》《贾人妻》《崔慎思》等文献中,女侠复仇故事发生时间和地点均集中于贞元末、元和初的长安,在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长安不可能发生多起女侠复仇之事,因此这些文献应为同一事源。据卞孝萱先生考证《义激》应创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唐国史补》的成书在《义激》之后,《集异记》《原化记》的成书又在这二者之后。[2]这些故事,彼此之间的叙述虽存在出入,但差异不大,应是对同一事源的因袭记载。
将《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一文与之前的唐代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女侠复仇故事的新变主要有三:一是女侠由“杀子绝念”转变为“生子报恩”;二是增添了女侠事母至孝的情节。这二者体现了女侠行侠手段的转变,由暴力走向非暴力,同时为女侠形象增添了世俗化色彩。三是男主人公形象进一步丰满,由故事边缘走向故事中心,与女侠的交集增多。
首先是女侠杀子行为的变化。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源自李端言的《蜀妇人传》,它以女侠“断所生二子喉而去”[1]54为结尾,并未对女侠的行为做出解释。崔蠡的《义激》、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的《贾人妻》亦均是发源于李端言的《蜀妇人传》,其中女侠杀子的行为有了初步的解释,被视为侠义行为的象征。在《义激》中,崔蠡从孝义出发,对其杀子行为予以宽容,并在篇末推之云“杀其子,捐其夫,子不得为恩,夫不得为累推之于义,斯义矣”[1]54在崔蠡看来,女侠为父报仇是为“孝”,杀子而使其免受辱是为“义”,这二者既是女侠的侠义行为,又集中体现了女侠既孝且义的侠客品质。在《崔慎思》中,皇甫氏对女侠亦未表现出否定的态度,并认为“杀其子者”是为了“以绝其念也”,甚至将女侠的行为视为“古之侠莫能过焉”。[1]56薛用弱的《贾人妻》亦是与此类似。在这一系列文献记载中,“女性行侠复仇”故事中的杀子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视为女侠侠义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到了宋代的《翰苑名谈·文叔遇侠》中,女侠虽生子但并未杀子,相较于同一故事类型,唐代文献记载中女侠的淡漠与侠性色彩浓厚,《文叔遇侠》中的女侠则展现了更浓厚的世俗性与人情味。随后,在《聊斋志异·侠女》的故事情节中,女侠形象又进一步呈现出女性化、世俗化、伦理化的新变特征。蒲松龄将唐代文献记载中的女侠杀子,变为《聊斋志异·侠女》中的“以子报恩”。 《聊斋》故事中的女侠与孤母相依为命,邻居顾生以卖画为生,虽家贫,但怜悯女侠的孝心,常负粟上门接济母女生计。顾母过世后,女侠替顾生产下一子以报其恩。“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今君德既酬,妾愿亦遂,无憾矣。”[4]216
蒲松龄写女侠用自己的身体为恩人“延续香火”,一方面是为了塑造女侠重情重义恩仇必报的形象,另一方面,相对于唐代文献中的杀子行为,生子报恩更符合儒家伦理道德下的侠义观。
除此之外,《侠女》所呈现的另一新变是增添了女侠奉养老母直至其逝去的相关情节。《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冷淡的性格、高超的剑术、缥缈的行踪使其形象更为神秘,这与唐代相关篇章中所呈现的神异性色彩类似。但女侠奉母至孝的相关情节又为其增添了人情味与世俗化色彩。
从唐代文献,到宋代的《翰苑名谈·文叔遇侠》,再到《聊斋志异·侠女》这一篇章,女侠形象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其侠义行为的变化,兼及女性气质的增强。侠义行为是侠客之所以为侠的根本,可以说,“义”是侠的灵魂。唐人李德裕在其《豪侠论》中曾说“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5]5325“义”与“侠”是紧密相连的。女侠之所以为侠,亦在其“义”。女侠的行侠方式则成为女侠之“义”的外在显现,也影响了女侠形象的呈现。关于女性气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女侠外貌描写的变化及女侠对待儿女之情、男女之私的态度转变。
从整体上看,唐女侠在行侠过程中,采取的是为父报仇,杀子绝念的暴力手段,她们的侠义精神呈现出尚武任侠的特征。并且在行侠过程中,女侠们的女性特质被削弱,整体上缺乏女性柔情。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描写都很少,《唐国史补》中没有对女侠外貌的描写,《义激》中对其貌的描写是“常人也”,《崔慎思》《贾人妻》则以“有容色”“美妇人”寥寥数语概括其貌。而她们对待丈夫与儿子的态度更是缺乏妻子的柔情和母亲的慈爱。“无情”“无性”应是唐代女侠所呈现的整体特征。在《聂隐娘》中,聂隐娘因要杀之人的小儿可爱而不忍下手,尼却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斩其所爱,然后决之。”[6]隐娘听后拜谢;荆十三娘为友人夺回爱妾,并且将爱妾嫌贫爱富的父母杀死;车中女子足智多谋,为盗贼团伙的首领,对文中的吴郡士人并未一见倾心,反而设计陷害,借此盗取宫中财物。类似的女侠,还有三鬟女子、红线女等。在唐传奇中,虽有红拂慧眼识李靖,冯梦龙在《情史》中将她归为情侠,但在《虬髯客传》中,着重突出的还是她乱世中慧眼识俊才的不凡眼光。这实际上反映了唐代作者在塑造女侠形象时,主要还是把她们当作“异人”对待,缺乏女性意识,并未突出她们的女性形象特征,而她们在行侠过程中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与以往的男侠也并无不同。
到了《聊斋志异·侠女》中,蒲松龄塑造的女侠则是呈现了奉母到老,生子报恩的非暴力行侠手段,同时女性化、世俗化色彩加强。不仅加强了对女侠外貌的描写“年约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4]215“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4]215,而且有意减少了她的言行举止神异色彩,通过“便代缝纫,出入堂中,操作如妇”[4]215,为顾生之母“洗创敷药”增添了女侠的女性化和世俗化色彩,女侠的行侠复仇中又带有女性的柔情,遵循世俗的礼教。唐女侠是豪放任侠、断情绝爱,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则是在符合伦理道德的情的驱使下做出侠义事。这一转变涉及到明清之际,侠的内涵的变化的问题。明清之际,儒家伦理道德进一步巩固发展,明代修订的《古今列女传》进一步规范妇女行为,有清一代大树贞节牌坊,规范女德,朱熹的地位在明清两朝空前提高,理学占据主流思想领域,维护封建礼教。明代出现的《女侠传》,是第一部女性侠客的专集。邹之麟将女侠分为六大类,除了豪侠、义侠、任侠、游侠、剑侠以外,还有绿珠、虞姬等一批以贞烈之举被归为节侠的女子。侠的内涵范围被进一步扩大,传统的纲常礼教与女教女德也被归为其中。这极大地造就了《聊斋志异·侠女》女侠形象的新变,使女侠的形象向着更为人情化、伦理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在女侠形象之外,男性主人公从边缘走向故事中心,是《聊斋志异》的女侠故事所呈现的又一新变。在《蜀妇人传》《义激》《妾报父冤事》《贾人妻》及《崔慎思》等“女性行侠复仇”的记载中,女侠之夫的形象都十分单薄,或是未作交代,或是仅以仕途失意、落难困窘概括其平生。《义激》中关于女侠之夫的笔墨甚少,只推测其为女侠同里。而在《崔慎思》中,面对妻子夜半失踪,女侠之夫的表现是“意其有奸,颇发忿怒”。[1]56在这些篇章中,女侠之夫并不是作为正面角色出场,只是女侠隐藏身份的配角。在《聊斋志异·侠女》中,男主人公的形象已丰满起来,小说开篇即点明其身份,“顾生,金陵人。博于材艺,而家摹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赞以自给。”[4]210男主人的身份明确为落魄书生,他的籍贯和家庭也有了初步的介绍。同时,顾生虽为贫寒子弟,但才高德重。女侠言“郎子大孝,胜我寡母孤女什百矣”“君敬我母,我勿谢也,君何谢焉?”[4]216女侠十分敬重顾生的品行表现,感其大孝与养母之恩,甘愿侍奉其母并为其生子。顾生在女侠行侠复仇过程中作为参与者出现,甚至成为女侠行侠报恩的对象,从一个隐藏女侠身份的配角走向了“女性行侠复仇故事”的中心。
从唐代文献记载到《聊斋志异·侠女》“女性行侠复仇”故事新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女侠行侠方式改变后女侠形象的新变,这涉及到中国古代侠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呈现及不同时代女性观的差异;一为女侠之夫在故事中角色地位的变化,唐代小说家与蒲松龄这些不同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与其联系密切。
二、 具有时代风貌的侠文化和女性观
“女侠”作为侠客的一部分,具有侠的精神品格,作为女性,又具有女性的特质。“女性行侠复仇”故事中的女侠在不同时期被书写的过程中,受具有时代风貌的侠文化和女性观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了解不同时代的侠文化,首先要明确侠文化的内涵。最早提到“侠”这一概念的是韩非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6]656他在《八说》中又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6]617“人臣肆意陈欲曰‘侠’”[6]627。其中,韩非认为“侠”的特征是“以武犯禁、弃官宠交、肆意陈欲”。其中的“禁”是指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设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武犯禁”即用武力方式与统治者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对抗;“弃官宠交”是指侠客可以为了友情、恩情而放弃官位;“肆意欲陈”指的是侠不曾或不愿“敬上畏法”,不愿受世俗的束缚而是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意愿。
其后,西汉的司马迁做《史记·游侠列传》,侠进入正史视野。陈平原说“只有司马迁为游侠做传,才为古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7]1后世对于“侠”内涵的讨论,多半始于此: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8]124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侠”往往一诺千金,为了拯救他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并且不夸耀自己,施恩于人从来不求对方的报答。
东汉班固追随司马迁,继续为“游侠”作传。一方面他认同司马迁,承认游侠具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9]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9]深致不满。出于维护封建政权的需要,两汉的统治阶级对游侠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所以,自班固《汉书》之后史学家们不再为游侠作传,也就是说自汉代之后,游侠不再进入正统史学家的视野。但是“游侠”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而是以另一种形象在诗、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中出现。
纵观“侠”的内涵演变,贯穿始终的并不是具有固定的社会家庭背景或属于特殊阶层的人群,而是一种精神气质,是弥漫在各类不同形象中的那种情操、人格力量、不受现实束缚向往自由的愿望和尚任求义的思想境界。因此,人们通过侠客形象与侠义行为对侠文化做出阐释时,易赋予其强烈的主观性色彩,特别是自东汉后,对侠的记述逐渐从历史记载走入文学想象。这样使得侠文化在传承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离不开其固有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深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形象相对于唐代文献记载中所呈现的新变,正是受侠文化内涵的演变的影响。
在《蜀妇人传》《义激》《妾报父冤事》《贾人妻》及《崔慎思》等唐代文献中,女侠呈现的是恩仇必报、果敢决绝、仗剑行侠的形象,这与唐代侠文化的内涵密不可分。
唐代的侠文化呈现出“任侠尚武”的倾向。汪聚应先生指出:“与魏晋六朝相比,唐代任侠的社会面是极其广泛的。”[10]24任侠则源于尚武。武则天公元702年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设置了“武举”,这给武人提供了晋身之阶,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习武风气的活跃。杜甫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则记载了唐代女子巾帼英雄般的雄浑武风。当时的“草圣”张旭曾自己总结说:“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而得其神。”[11]公孙氏舞剑被视为艺术和武术的巧妙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联想。由此可见,女子习武也得到社会的认可。唐代的尚武风气使得唐代文献中对女侠的武力行侠表现出明显的推崇倾向。
除了侠文化内涵的演变影响女侠形象的演变,具有时代风貌的女性观也对女侠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呈现有所影响。
在宋传奇《文叔遇侠》与《聊斋志异·侠女》中,女侠在临走前对其夫进行了殷殷的劝诫与关怀,是封建伦理对女性贤德要求的体现。而在《蜀妇人传》《义激》《妾报父冤事》《贾人妻》等这些记载女侠复仇故事的唐代文献中,女侠并没有呈现封建社会中受夫权束缚的妻子对丈夫敬畏仰慕的心理,这主要体现在女侠复仇之后果决的杀子与辞别行为。特别是女侠杀子,是考虑到避免自己的孩子因其母杀人而受辱以及断绝自己对孩子的感念,并没有考虑其丈夫的感想,甚至明显将妻妾需为丈夫延续香火这一伦理纲常排除其外。
这些都与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对女子较少的封建礼教束缚有关。唐代妇女可以广泛地参加社会交往,公开地与男子联袂出游、同席宴饮。张鷟《朝野佥载》卷3记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12]参加的人中有“宫女千数”和“长安少女妇人千余人”。而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的主人公虽为女性,却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她不仅不是男性的附庸,反而是团体的首领。礼教松弛、女性地位提高是唐代女性观的具体呈现,也使得唐代文学家对蜀妇人武力行侠、杀子弃夫的行为有了更多的宽容。
相对于任侠尚武、独立果决又具有神异色彩的唐女侠,《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形象则呈现出女性化、世俗化、伦理化的新变特征。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儒家文化对侠文化的影响。
《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遵循了“恩仇必报”的侠文化的固有内涵,但女侠的行侠方式却出现了新变,从武力走向了非武力。在为父报仇之外,表现女侠行侠的是“养母送终”与“生子报恩”两处行为,这与清代侠文化的内涵有关。
相对于唐代的侠文化,清代的侠文化不仅更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也更具有世俗化色彩。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唐代道教的传播对唐人的生活理想、审美意识及自由脱俗的精神追求都有影响。体现在“女侠行侠复仇”故事中女侠形象的塑造上,女侠在为父报仇之后杀死孩子以绝念想,出门后就消失了行踪。“她并没有回归于伦理而是逃遁于一种空廓虚无的寂静状态,求取一种新的恬淡无为、清心寡欲的人生境界。”[13]32在任侠的背后,也体现了道教所追求的神仙道法,斩断世俗羁绊。但自宋明理学崛起后,佛道二家虽仍不断流传,却已失去往日与儒学并肩的声势和影响。有清一代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推崇程朱理学。“小说中的正统话语与晚期帝国的理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的实践系统,在明清时期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就像空气,无所不在。”[14]5因此,《聊斋志异·侠女》除了讲述女侠为父报仇外,还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事母至孝的场景。当对女侠有恩的顾生因家贫无法娶妻时,女侠选择为其生子报恩。这些都符合面向现实的宗法伦常。相对于唐代女侠身上自由洒脱的个性色彩,清女侠身上带有更明显的劝世教化意味。
除此之外,聊斋中的女侠私下与顾生结合生子,并不意味着封建礼教对女性束缚的松弛及对贞洁观念的否定。这正是侠文化与程朱理学中的女教女德混合下的产物。侠客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子·经上》解释任侠的“任”:“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15]《墨子·经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15]侠客为“义”所驱,能够“不爱其躯”,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险。《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献身为顾生延续后代,被视为大义行为,是因为在当时的礼教环境下,女子的贞节比生命还贵重。女侠献身报恩主要是为了体现其侠义精神,但也暗示了清代儒家文化对女性贞节的重视。
从唐代到清代,“女性行侠复仇”故事中的女侠形象始终传承着追求自由、尚任求义的侠文化内涵,但这一内涵因不同时代风貌的影响也有所差异,这也造就了故事中女侠形象的新变。同时,女侠因其女性特质,自清至唐女性观的差异也影响了女侠形象的新变。唐代宽松自由、任侠尚武的社会风气使得唐女侠选择武力行侠,而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宽松的社会风气使得唐女侠身上呈现出豪迈洒脱、任侠果敢的精神气质;清代的侠文化则深受儒家宗法伦常与劝世教化理念的影响,因而“女性行侠复仇”故事中的清女侠选择更与世俗贴近的非武力行侠,同时,清代程朱理学中的女教与女德观念在清女侠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 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
具有时代风貌的侠文化、女性观与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都对“女性行侠复仇”故事的新变有重要影响。相对于前者对故事中女侠形象新变的影响,故事的男主人公从边缘走向叙事中心则主要受不同创作主体内在心理的影响。
在描述“女性行侠复仇”故事的唐传奇中,女侠的配偶都处于边缘地位,只是为女侠隐匿身份提供庇护场所,唐代文人记载此事的主要目的则是表现女侠的孝与义。以《义激》为例。据《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记载,崔宁因对宰相卢杞表示不满,被其设计构陷。“杞因诬奏曰‘崔宁初无葵藿向日之心,闻于城中与朱泚坚为盟约奸臣内谋,则大事去矣。’俄有中人引宁于幕后,二力士自后缢杀之。”[2]崔蠡痛于伯祖崔宁被冤杀,在观《蜀妇人传》一文后心有所感,另撰一文,取名《义激》,极力突出女侠的孝与义,借此倾泻自己的胸中积郁。《唐国史补》《集异记》《原化记》中的女侠复仇、杀子弃夫的故事也延续了《义激》的记载。
到了《聊斋志异·侠女》,对男主人公的描写增多,身份与籍贯也有了明确交代。除此之外,他与女侠的交流也增加,成为女侠行侠报恩的对象,在女侠的帮助下他得以延续香火。《侠女》篇章中的这一新变与其创作主体蒲松龄的内在心理密不可分。因为《聊斋志异》虽多记载狐鬼神异之事,但在本质上则是一部作者自抒心声的文言小说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云:“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后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16]可见蒲松龄虚拟狐鬼花妖故事以抒发情怀,寄托忧愤,已成为主导的创作意识。《侠女》篇章的新变与蒲松龄寄寓抒怀的创作观密不可分,自然也深受其忧虑孤愤的创作心理的影响。
蒲松龄的孤愤源自于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自身经历的忧愤。他迷恋科举却屡遭颠簸,直到七十多岁才获得岁贡生的功名,一生落魄。包括蒲松龄在内的这些落魄士子都属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寒士阶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寒士阶层大都是科举之途上的失败者。这种失败造成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低下,这又导致其在婚姻领域中的低下地位,使之无力与富贵者竞争而倍受压抑,往往难以获得满意的婚姻,其中一部分人更是落到无力婚娶,后嗣难继的窘迫境地。”[17]167朱熹在《近思录》中说“寒士之妻,弱国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择势而从,则恶之大者,不容于世矣。”[18]朱熹将寒士之妻与弱国之臣并列,认为二者同居艰难处境,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寒士在婚姻领域中低下的地位。
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蒲松龄对落魄士子的困境和内心渴求有着深刻的认知,便自然成为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言人。他在《聊斋志异》中多写为寒士张目之作,其中尤多描写寒士婚姻遭际的作品。除《侠女》外,《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篇章讲述美女解救寒士婚姻、子嗣困厄的故事。在《姊妹易嫁》《青梅》《胡四娘》《封三娘》等篇中,蒲松龄塑造了一批蔑视富贵而独钟情于寒士的女子形象,并发出了“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王公,乃留意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青梅》)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极力突出的是寒士的品德、才能、学问,以此来同富贵者的地位、财产相抗衡,正是这些吸引了美女的倾慕或同情。因此,可以看出在《聊斋志异·侠女》这一篇章中体现的也是以蒲松龄为代表的寒士阶层既自卑又自尊的意识。
在《侠女》篇章中,蒲松龄丰满了男主人公顾生的形象,使其和女侠共同成为故事的主角。从女侠的角度,该故事讲述的是女侠恩仇必报、行侠仗义之事;从顾生的角度,则是贫寒之士因其学识与品性而子嗣有继的故事。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女侠以自我献身的方式直接解救顾生婚姻子嗣的困厄,在这一过程中顾生与女侠之间的社会地位、财产等诸条件的制约都不复存在,于是作者、寒士的心理便在这一幻想中得到满足。
结语
女侠由“侠”与“女”组成,涉及到侠文化与女性观。唐代的时代风貌造就了任侠尚武的侠文化内涵,也使得唐代文学家对蜀妇人为父报仇、杀子弃夫的侠义事呈现出明显的推崇态度。蒲松龄的创作则是在唐代文献的基础上,自觉地用更为严苛的儒家伦理道德对女侠的行为进行规范,并进一步重塑女侠的形象。但他凭借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并没有让《聊斋志异·侠女》中的女侠成为僵化的道德典范,反而使其更接近时代背景与生活,具有高度的世俗化、生活化色彩。蒲松龄对女侠故事中男主人公形象的突出与丰满,则涉及到潜藏于他心中的寒士心理,既自尊又自卑,蔑视纨绔,却又对自己当下的地位与财产感到窘迫。侠文化内涵的演变和蒲松龄的创作心理都是隐藏在《聊斋志异·侠女》新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和内在心理因素。
注释
① 《一个故事,五种记载——唐人杂传、杂文、轶事、传奇》一文对记载这一故事的文献进行分类。李端言所撰《蜀妇人传》属于杂传,区别于史传。崔蠡所撰《义激》《文苑英华》置于《杂文·纪事》,属杂文。《贾人妻》与《崔慎思》所属的《集异记》与《原化记》均属晚唐小说集。
② 卞孝萱先生考证《义激》中又有“自国初到于今,仅二百年”之语,从武德元年(618)下推二百年为元和十二年(817),推断《义激》撰于元和十二年前后。《唐国史补》的写作时间在《义激》后,“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可以为证。《集异记》、《原化记》的成书年代又在《国史补》之后。《集异记·石吴》《高元裕》《李佐文》《裴用》《嘉陵江巨木》有大和年号(《太平广记》卷七十八、二七八、三四七、三九四、四百五引),《原化记·光禄屠者》亦有大和年号(同书卷四三四引),均晚唐之小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