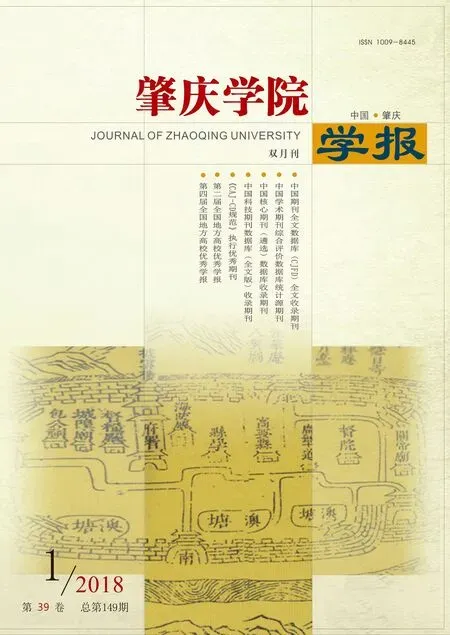从三僧谋生方式看清初广东寺院经济形态
2018-02-09钟玉发
钟玉发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在佛教产生地印度,僧侣主要以乞食纳衣为生,但是汉传佛教却打破了单纯依赖施舍为生的传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布,佛门不仅开展农业生产,而且从事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等社会经济活动,逐渐形成了颇具个性特点的寺院经济。其中,唐代高僧百丈怀海(720—814)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经济”,对后世佛门生计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佛门实际生活中,其经济形态并不整齐划一。比如,明清易代之际广东出现大量不愿与清朝合作的所谓“遗民”,他们中有部分人遁入佛门,成为所谓“逃禅”者(或曰“遗民僧”)。他们在寺庙修建、衣食筹措以及寺产经营等方面既有相同的一面,又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研究清初广东佛门生计问题,不仅能够加深对寺院经济形态多样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探明在明清易代之际“逃禅”者作为一个特殊政治阶层的生存实态。本文拟以颇具代表意义的丹霞山别传寺、广州长寿寺和鼎湖山庆云寺及其住持今释澹归、石濂大汕和成鹫迹删的谋生行为为个案,探析清初广东寺院经济的具体形态和特点。
一、今释澹归:从“沿门抄化”到置产兴业
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侣托钵化缘为生的情况比较少见,官府拨款、社会捐助和民众施舍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寺院有时也主动募施,其目的有二:一是募集建寺资金,二是筹措日常衣食。清初,众多遗民“逃禅”,因事出突然,寺院生计压力增大,主持者不得不各施其能,想方设法化解生存危机。例如,丹霞山别传寺的创建者今释澹归最初就是依靠“沿门抄化”的方式主动募施的,但是他后来又转而购置田产,推行农禅经济。
今释澹归(1614—1680),俗名金堡,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授临清知州,颇有政声。甲、乙之变①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明王朝覆亡。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攻入南京城,南明福王政权灭亡。1644年为甲申年,1645年为乙酉年,因此史称这先后发生的两次事件为“甲、乙之变”。后,他于永历二年(1648年)辗转来到广东肇庆,出任永历政权兵科给事中,因陷入党争而被逮下狱,遭受酷刑。他在谪戍途中于桂林削发为僧,并于顺治九年(1652年)赴广州礼曹洞宗三十四世天然函罡为师,成为“逃禅”者。据释成鹫《舵石翁传》称,澹归初入师门,“入厨下亲涤碗器,隆寒龟手不废服勤,器有衅缺,典衣偿之”[1]552,显示了勇于担当、任劳任怨的优秀品格。为了安置易代之际产生的诸多遗民,澹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接受了明遗臣李充茂兄弟施舍的丹霞山,着手修建别传寺。为了筹措到足够的钱粮,他最初采取的方式是“沿门抄化”。
据释成鹫《舵石翁传》记载,澹归自充监院,为筹建别传寺而“胼手胝足,运水搬柴,露面抛头,躐州过郡,送往迎来,人事轇轕,五官并用”[1]552。澹归《与李鑑湖祠部》说,由于民生凋敝,建寺资金极端匮乏,僧众生计维艰,因此自己不得不“穿州撞府,沿门抄化,忍辱耐劳”[2]185。澹归为此四处奔波,常年在外,其《与南雄常别驾月生》记述说:“僧家为三宝经营,直是脚跟无线,去年坐卧山中不满五十日,归来无一日闲,今又当下山矣。”[2]241其《与李鑑湖祠部》又说:“奔走丹霞七载,计在山中仅及一年”[2]186。澹归《与李鑑湖祠部》说,自己有时甚至带病坚持:“此月初一日,忽吐血十余口,体中至今不佳,然不敢言病,盖修造钱粮甚急,无歇手处”[2]226。后来,他将自己的诗文结集付梓,《徧行堂集缘起》自述说:“(予)充化主,未免以诗文为酬应……阅之自笑,登歌清庙,与街头市尾唱莲花落并行千古”[3]8。可见,《徧行堂集》中既有与官绅文士酬唱的高雅之作,也有沿门乞讨之文,是澹归为建寺而不得不广泛“募缘”的实录。
丹霞的岁入和岁出并无完整记录。澹归《与萧柔以参戎》曾说:“但一山二百人,止是澹归一人募缘,每月讨得百金,尚不济事”[2]209。其《与海幢阿字无和尚》又说:“每年非千金不能支遣,今年挂脚南雄,仅得五百金,目前无卒岁之谋,甚仓皇也。”[2]108据此推测,丹霞大约有僧200人,每年须支出1000两银。因此,为了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和物资,澹归设法广结“俗缘”,其募施对象上至达官显贵下及普通信众。例如,平南王尚可喜自顺治七年(1650年)攻占广州后便停止屠戮,开始礼僧问道,并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重修了光孝寺,因此,澹归设法通过平南王府得宠幕宾、同乡金光获得资助,其《为公绚礼忏疏》称赞说:“捐财劝众,曾讲一家之好,兼行四事(即寺僧伽衣、食、住、药)之檀。”[4]111据其《丹霞新建韦驮殿碑记》记载,康熙八年(1669年)秋,他谒见两广总督周有德,获捐五百金助修韦驮殿[3]290。《华藏庄严阁记》则说,康熙九年(1670年)秋,华藏庄严阁的修建又获得广东巡抚刘秉权的资助[3]292。此外,澹归还获得诸多府县官的护法、捐助。例如,其《送陆孝山太守持服归当湖序》说,陆世楷为南雄太守19年,护法丹霞13年[3]166。他于康熙五年(1666年)捐俸建成丹霞山门[3]288。澹归《准提阁记》还提到,康熙七年(1668年),别传寺修建供奉菩萨像的楼阁,于是“南雄陆使君孝山,以学使者冯公苍心静檀五十金至,即自捐五十金;故司李今莱阳令万公松溪,濒行留二十金;而南海令陈公试庵于初夏远寄一百五十金”[3]287-288。
康熙时期修成的《丹霞山志》具体记载了别传寺的捐施情况:初建时的捐款者既有两广总督、各府县官,也有普通信众,施舍银两从1200两至1两不等,共计51人(其中24人捐款合计2445两,其余27人具体捐款数目不详,仅记作诸如“太守杨万春同募建大殿”“文宗冯标同募建準提阁”等);其重建大殿檀越共有46人(其中41人施舍银1137.5两,其余5人施舍银两数目不详);向寺院施舍饭僧田者共计15人(具体田亩数不详);施舍代坡田者4人;施净檀者22人[5]74-78。此外,澹归辑刻《徧行堂集》也曾获得过护法和信众资助,其《助刻徧行堂集檀越姓氏》记载有22人捐资320两[6]14。
“沿门抄化”和社会捐助毕竟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于是澹归不得不改变谋生方式,转而购置田产,推行农禅经济,妥善地解决了别传寺的生计压力问题。
别传寺最初恪守佛门原始戒律,曾有“辞田”之举。据澹归《辞田说》载,“韶州郡守赵公、郡丞傅公,新创关帝祠,谋置田为久远计,于是越人沈氏以其田租一千一百一十五石应,两公许之”。澹归却指出:一方面,“田为关帝祠香火设,而丹霞之僧享之,其名未正,适足开异日争端”;另一方面,“如来立教,比丘托钵而已。丹霞虽无田,而尚有钵,乞士家风,固未见有得失也。”因此,他辞退了沈氏所捐田产[3]61-62。但是,随着僧众的不断增多,“乞食自活”难以维持,澹归不得已转而“乞(饭僧)田”,规模如其《募僧田疏》自称:“某初开丹霞,即有置田千亩饭僧之愿。每僧一岁食田之入约五亩,仅二百人而止。”不过,为了供养更多的寺僧,他乞求“诸大福德檀越随力助成”[3]234。
别传寺的田产分布在韶州府仁化县、曲江县、乐昌县和南雄府保昌县,其田产主要来源于私家施舍,但也有部分是利用赢余经费自行购置的。例如,澹归《施田碑记之二》记述说,康熙七年(1668年),南雄太守陆世楷就利用官方身份协助职事僧购买仁化田庄(计租1200石,价值860金)[3]290。至于丹霞置田数量并无直接统计资料,澹归曾说,“近刻《丹霞建制》一册,内募饭僧田千亩,事未必便成,成亦须一番布置”,可知其计划置产数量为一千亩(但实际购置数量缺乏确切记载)。就经营模式而言,丹霞施行农、禅并重,澹归就曾在《上书本师天然函罡和上》中说:“秋间有人施田,复成画饼,今当一意料理,使常住有千石之租,以为根本,更劝诸行门兄弟尽心种作”[2]94-95。
此外,澹归还设法获准在曲江设立会龙庵、仁化准提阁、始兴新庵、南雄龙护园四个下院,拓展了别传寺的基业[5]96。例如,其《龙护园碑记》说,康熙六年(1667年),他设法将位于雄州荒野中原梅谷禅师掩关修持的龙护园归并为丹霞之下院[3]319。其《龙护园乞米引》说,龙护园类似于客栈,免费供过往僧众“一宿两餐”。虽然其经济来源同样依靠施舍,但因措置得当,这些下院为往来僧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272。及至雍正七年(1729年),别传寺还购置了广州府南海县庞芳琪铺、庞大朝承继父遗下铺各一间,涉足商业经营活动[5]96。
澹归戮力化缘,苦心经营,其《与强佑人居士》自称目的在于“决不忍使大众各鸟兽散,委梵刹于草莽也”[2]314。因此,他的词作《满江红》总结自己经营别传寺的情形说:“十载丹霞,没两载、偎松依竹。全受用,穿州撞府,抗尘走俗。游客生涯诗与字,丛林大计钱和谷。”[7]295
据释成鹫《舵石翁传》记载说,别传寺开山后,“四方闻风,瓶笠云集,堂室几不能容。”[1]553寺院香火如此兴旺,想必与澹归和尚谋生有方、措置得当密不可分。
二、石濂大汕:海外弘法兼以通洋贸易
广东濒临大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与世界各地往来的前沿之地,位于珠江口的广州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享有无法取代的航海、通商优势,这甚至在清初寺院经济中也得到了显著体现。比如,广州长寿寺住持石濂大汕就借助应邀赴越南弘法之良机,大力开展通洋贸易,集聚了巨额财富。
石濂大汕(1633—1705),又称厂翁和尚,俗姓徐,浙江吴县(一说嘉兴)人,是清代广州五大丛林之一长寿寺的著名住持。他16岁时礼江宁(今南京)曹洞宗著名高僧觉浪道盛为师,20岁以后在江南一带传法弘道。约在康熙二年(1663年),他游方岭南并定居广州,与著名文士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结为密友。在屈大均的帮助下,他通过平南王府得宠幕宾、浙江同乡金光的关系,先后入住广州大佛寺、长寿寺。
大汕出身寒苦,虽未曾获得功名,但“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接纳名士”[8]342。《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记载说:“明季清人入帝中国,(石)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9]139。因此,徐釚《离六堂集序》称大汕出家为僧“殆有托而逃于禅者也”[10]488。不过,大汕因善于结交各方人士和不惜手段聚敛钱财而饱受诟病。潘耒《与梁药亭庶常书》称:“渠(大汕)又谄事平南王之幕客金公绚,得见平南及俺达公(案指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广州长寿、清远飞来二寺,皆实行和尚所住持,实行没,公绚言于俺达,以石濂住长寿。长寿无产业,飞来有租七千余石,乃于诸当事请以飞来为下院,尽逐实行之徒,而并吞其租”[11]56-57。长寿寺的前身是长寿庵,明朝万历丙午(1606年)巡抚沈正隆在广州城西五里的旧顺母桥故址所建,一度成为“名刹。”[12]260但是,久经风雨,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冬大汕受请入住时,该寺“倾颓过半”,亟待大力重修[13]315。于是,如何获得修寺钱物成为大汕必须解决的难题。
大汕在广东僧俗两界交游极为广泛,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八月初四日,大越国王阮福週专使到长寿寺,呈上国书,力邀大汕前往该国弘法。这是大越国王第三次以国书敦请大汕,并附有南金、花藤、黄绢、齐南等重礼[9]1。大汕有感其诚意,于次年(1695年)春从广州启程赴越,随行僧众百余人。
至越南顺化后,大汕发现,当地少壮健者皆须从军,为了逃避服役,出家为僧者众多,结果佛法由此而混滥。于是,他设法在当地多方布道,传授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等。为了改变当地僧侣不知戒律为何事的现象,他还介绍了慧能以下青原、南岳二派以及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宗分化与“所谓何其自性,本来清净”的禅宗主旨,并着力提倡“老实修行”[9]16-19。因此,他很快赢得了越南国王和王公贵族的信任,“俱求摄受为菩萨戒弟子”[9]21。
大汕于第二年(1696年)秋天才顺风乘船回到广州,他将自己在越南弘法期间的所见所闻著成《海外纪事》一书,刊刻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但是,不久,他与顾炎武之徒潘耒交恶而遭受到严厉指责[9]3。潘耒撰成《救狂砭语》一书,揭露大汕种种不法之事,其中不乏偏激之词,但是对其“干禁”开展通洋贸易的披露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汕赴越弘法之际,正值康熙海禁初开、洋船贸易急剧上升的时期,这给处事机敏的大汕带来了生财良机,其方法有二:一是募施,二是通过采办、进献礼品等方式赚取回报。
阮福週师事大汕,言必称“弟子”,有心施舍。大汕借机上疏曰:“广东乃四海五湖云水来龙口,长寿系十州三岛沙门总码头。是释迦,是弥勒,莫不向这里停机。若羽士,若禅人,皆要从此方着足。放下折袋,圣同参凡亦同参;打开钵盂,朝要吃暮也要吃。拄杖子只好各与一顿餬饼话,争奈不疗众饥……吴丝越粟,在中华自有中华施主,圆顶方袍,化外国岂无外国英贤。”[9]60后来,阮福週询问长寿寺修建进展以及费用问题,大汕回答说,大雄宝殿的重修尚缺五千金。阮福週当即慷慨地表示:“今大殿钱粮,某欢喜肩任,明年归时如意创建费,不我惜也。”[9]109于是,大汕作成《重建长寿因缘疏》,援引宋朝时高丽国王捐建浙江法相寺故事,接受了阮王的布施。因此,《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记载说,大汕从越南满载而归,不仅获得大越国王阮福週布施的五千金,而且带回其所回赠的名木、齐南、轮珠、金银等[9]140。黄登也记述说:“今复鼎建藏经阁、大雄殿,飞甍画栋,甲于诸方,历费数万,皆大檀越乐为捐俸。”[13]315
不仅如此,大汕还以采办、赠与阮氏王府礼物的名义在江宁苏杭等地购买大量高级织物,且绣上“王府用,长寿定”字样,输送到越南,以换取高额回赠,也即潘耒《致粤东当事书》所称“多将干禁之物致诸交人,以邀厚利”[11]116,“送礼与交人,每次所获厚报,悉干没入己”[11]117,以及《与长寿院主石濂书》所指责“贩贱卖贵,逐什一而操奇赢。”[11]19
大汕这次海外传法轰动一时,其通洋贸易也颇为有成。但是,大汕违背佛门清规戒律以及颇为铺张奢侈的私生活遭到了部分人的嫉恨,其旅粤同乡潘耒在《致粤东当事书》中就猛烈攻击他“讪上”、通洋敛财、图谋不轨等[11]117-119。当时堪称长寿寺最为有力的护法者平南王府已经开始失势,屈大均等名士也与大汕交恶。在此背景下,广东按察使许嗣兴将大汕投入监狱,并于康熙四十一年(1792年)将其押解至赣州。两年后,江西巡抚李基和再度驱逐他,并将他押解回浙江原籍。结果,客死于押解途中的常州。
从潘耒《救狂砭语》来看,大汕最为严重的劣迹便是私自开展通洋贸易。但是,无论怎么说,大汕的确借此筹措到丰厚的资金,改善了长寿寺的生计状况,不失为谋生有术。
三、成鹫迹删:游方乞食与恪守“祖约”
清初广东佛门并不都像澹归和大汕那样积极募施、生财有道,也有恪守原始佛教戒律、不置田产、依靠施舍为生者。比如,释成鹫的游方乞食以及他作为第七代住持入主鼎湖山庆云寺时生计上的不作为就属此类典型。
成鹫(1637—1722),俗名方颛恺,番禺人,明诸生。生长于丧乱之中,饱经天灾人祸。及至平南王尚可喜攻占广州,他誓死不赴清廷试,结果遭除籍。康熙丁巳(1677年)五月,41岁的方颛恺毅然告别世俗生活,自行断发为僧[14]125。恰逢罗浮山石洞禅院方丈离幻元觉和尚至,遂礼其受法,名光鹫,字迹删,号东樵,后再改名成鹫[15]75。成鹫入道后,居无定所,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出云游,成为名副其实的游方僧,足迹踏遍了岭南的众多名山大寺。根据成鹫本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80岁时所作自传《纪梦编年》可知,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44岁时起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86岁示寂为止,他先后栖身西宁(今郁南)翠林僧舍、罗浮山石洞禅院、琼州府灵泉寺、佛山仁寿寺、香山东林庵、韶州丹霞山别传寺、端州鼎湖山庆云寺、广州大通寺等[14]131-157,长期飘泊不定,到处募缘乞食。
在长期游方生涯之中,成鹫应众请担任端州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期间其生计上的不作为以及由此而遭到排斥之事值得特别关注。此事发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当时成鹫72岁,“鼎湖虚席,主法无人,合山大众强以主持,却之不获”,于是他不得已勉强就任[1]695。
庆云寺修建于明崇祯时期。当时,新会人朱子仁(1611—1685)有志出家,他来到端州鼎湖山莲花峰,结成莲花庵修行,后往庐山参道独和尚,法号弘赞,字在犙。在犙于崇祯九年(1636年)与当地人陈清波、梁少川迎请高僧栖壑和尚(1586—1658)入住莲花庵,并于次年改庵名为庆云寺。栖壑入住庆云寺之后,制定了《祖约》,其中关于寺院生计方面就规定“本院不置田”、僧众以“乞食”为生[16]60。据载,庆云寺一度有僧数百人,却无“担石之储”,所需衣食均依靠诸护法者捐施。肇庆知府胡某与监寺云俦曾设法募金千余两,准备以之购置田产。但是,栖壑予以拒绝,他说:“释子修行,‘龙天拥护’四字自足,何用田为?”[17]1133-1134庆云寺由此确立了不置田产、“乞食”为生的清规戒律,堪称遵奉原始教义的典范。
成鹫就任第七代住持之后,严格遵守丛林轨范和栖壑和尚所定《祖约》,不仅生计上毫不作为(既不主动募施,又不置产兴业),而且反对僧侣私蓄财物和颓废放荡。成鹫曾表示,金钱利益是争端、祸乱之源,其作《诫蓄财》云:“古人作字,利旁有刀,钱一金而二戈,谓利少害多,旁有劫夺之患也。多积聚、长悭贪为我辈生众种子,如法比丘,不蓄秽财,必令净人知是,所以尚廉耻而惩贪吝也。学者实宜遵守,毋为孔方先生所惑。”[1]695因此,他极力反对僧侣从事商贾活动,认为那是“玷辱如来门庭”[1]694。但是,因受世俗风尚的不良影响,庆云寺部分僧人热衷于聚敛钱财,私设小灶,颓风弥漫。于是成鹫“期之以佛法,绳之以祖训”,“痛心疾首,奋臂大呼,领众巡寮,掀翻窠臼,私造饮食炉釜一空。”[14]160但是,“不数月,鹤唳风声,接于耳目。松楸墓域,遽起戈矛。”[14]161成鹫成为众矢之的,受到众僧的排斥。在此过程中,他与前监寺智觉之徒等航、等解等“相水火”之事颇令人关注。据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栖壑和尚圆寂后,能够遵守《祖约》的弘赞继任住持,而庆云寺创建过程中长期担任监寺、为募集钱物贡献巨大的智觉和尚则在鼎湖东北创法云寺为退休之地。至弘赞示寂后,一机、成鹫先后住山,结果他们与智觉之徒等航、等解等发生激烈冲突。后来,成鹫撰成《鼎湖山志》,“凡开山碑状有稍及智觉劳勋者悉为窜易,志末山中难事一卷,尤极谰诋。”[17]1135可见,双方就庆云寺的谋生方式问题曾展开过剧烈的争持。成鹫为了维护《祖约》,不仅生计上不作为,甚至不惜窜改乃至诋毁智觉和尚在庆云寺创建过程中募施得力的“劳勋”。不过,成鹫试图整肃庆云寺僧众纪律的努力并未奏效,反而因此受到围攻、排斥。他只能自叹游方乞食生涯为“梦”,不得不带着满腹的遗憾于次年三月退居大通寺,从此“掩关谢客”[14]167,直至示寂。
成鹫的游方生涯堪称是易代之际广东“逃禅”者生计维艰的典型,而他曾一度主持鼎湖山庆云寺,秉承该寺第一代主持栖壑禅师不置田产的规约,并为维护该规约与违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鲜明地体现了有别于别传寺和长寿寺置产兴业、通洋贸易的谋生行为。因此,有学者称:“在清初岭南佛门中,他(案指成鹫)的道路具有最典型的遗民僧的特征”[18]98。人们在称赞成鹫诗文成就的同时,由衷地钦佩他“戒律精严,道范高峻,与贵人游,道话外公私一无所及。”[17]1135-1136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初广东佛门生计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这在寺院修建资金筹措、僧众衣食来源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今释澹归为了修建丹霞山别传寺,戮力募施,“沿门抄化”,并且由最初的“辞田”转而为后来的大力置办田产,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保障了僧众的生计。广州长寿寺住持石濂大汕利用海外弘法之机开展通洋贸易,其募施方式在寺院经济史上堪称独特无匹,体现了明清之际岭南禅文化的“俗世化”倾向和“近世商人精神”[19]584。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鹫迹删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游方为生,及至其出任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后又遵循《祖约》不置田产,提倡乞食为生,表达了汉传佛教对原始教义的遵从。因此,清初佛门谋生方式异彩纷呈,反映了古代中国寺院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尤其是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澹归、大汕和成鹫作为所谓“逃禅”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立场和忠孝节操等文化观念的制约,他们作为寺院住持因生计问题而不得不与社会各界交涉,这使得他们更易遭受谴责,问题性质也变得更加复杂。澹归对修建、经营别传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时人及后人却颇多微词。邵廷采指责他以“山人”身份为平南王“称颂功德”[20]420。全祖望也嘲讽曰:“辛苦何来笑澹翁,《徧行堂集》玷宗风。丹霞精舍成年谱,又在平南珠履中。”[21]2296今人则指责他为只知募缘的“俗汉”[22]386。石濂大汕则因其通洋贸易行为以及奢靡的生活方式而被屈大均贬斥为“花怪”[23]490,被王士桢称为“妖僧”[9]137。成鹫迹删虽然能够恪守庆云寺不置田产和乞食为生的《祖约》,但是佛门内部对于他在生计问题上的不作为以及过于严守清规戒律颇为不满,甚至最终将其排挤出院。这一方面反映了晨钟暮鼓、遁世修行的高远理想与人间烟火、世俗生计的沉重压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折射出王朝更迭时期广东佛门生计的艰辛困苦和寺院经济形态的复杂多样。
当然,澹归、大汕和成鹫的遭际也有相同之点,这就是他们作为遗民僧均不为“当道”所容,甚至他们的著作也被打入禁毁之列,这更为清初广东佛门谋生行为烙下了特殊的时代和政治印记。
[1]释成鹫.咸陟堂文集:卷六[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澹归和尚.徧行堂集:第2册[M].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
[3]澹归和尚.徧行堂集:第1册[M].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
[4]澹归和尚.徧行堂集:第4册[M].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
[5]陈世英,释古如.丹霞山志:卷六[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澹归和尚.徧行堂集:卷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澹归和尚.徧行堂集:第3册[M].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
[8]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大汕.海外纪事[M].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释大汕.离六堂集:卷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1]潘耒.救狂砭语;救狂后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仇巨川.羊城古钞:卷3[M].陈宪猷,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3]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卷3[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释成鹫迹删.纪梦编年[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5]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6]释成鹫.鼎湖山志[M].李福标,仇江,点校.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
[17]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20[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8]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9]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0]邵廷采.西南纪事:卷7[M]//丛书集成续编:第27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21]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10[M]//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陈垣.清初僧铮记[M]//陈垣全集:第18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23]屈大均.翁山佚文:花怪[M]//屈大均全集: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