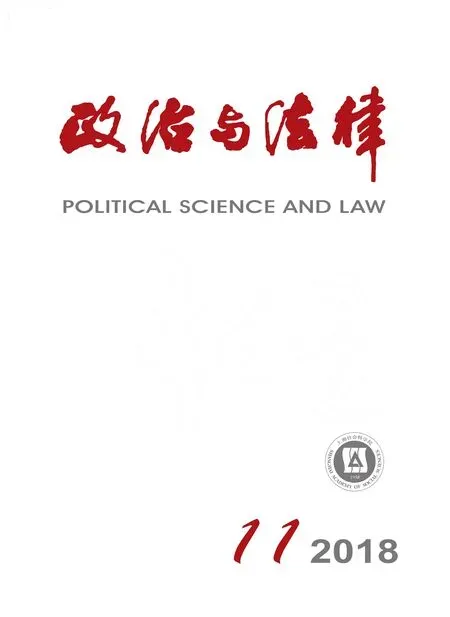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原告资格论*
——以诉的种类为秩序框架
2018-02-07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确认亲子关系这项重要的身份制度在我国制定法上长期缺位,当下的司法运作全然诉诸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第二条,即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的推定规则,学理研究大多也是围绕该条款来讨论事实认定层面的问题。不过,究竟谁有权提起确认亲子关系诉讼这一上游命题却很少受到关注。以何种观念和标准判断原告适格性,直接关系到法院事实审理及实体判决所面临的问题场域的宽窄。如今,就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原告资格,司法实务中的裁量空间很大,相关论理含混跳跃,结论也时有矛盾,亟需适当的分析工具来规范和厘清。为回应这种需求,有必要分两个阶段来构建思考研究的体系:第一阶段是依托诉的种类理论来确立原告资格认定的秩序框架,主要是分析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诉讼对象,以便将不同内容的诉讼正确归入形成之诉或确认之诉的范畴;第二阶段则是在不同的秩序框架下,通过利益衡量来探寻原告资格认定的具体规则,也就是考察形成之诉的原告资格应在何种范围内形成封闭,而确认之诉的原告范围又如何在确认利益的统领下保持开放。
一、现状透视:原告资格认定的秩序需求分析
特定主体的原告资格属法院职权审查的事项,不当禁止起诉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侵害,不当准入既有违诉讼法理,也容易给后续的审理判决造成疑难。就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适格原告,《解释三》第二条虽有涉及,但实质指导力微弱,司法判断在无章可循的背景下陷入无序。
(一)谁有权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
出于维护身份及家庭关系稳定等考虑,《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采用了“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措辞,以限制这一否认权的主体。不过“夫妻一方”这一主体范围可否放宽,或者说能放宽到什么程度,还未形成定见。[注]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之际,曾考虑将提起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权利人限制为夫或妻,尔后基于经验及现实的考虑,认为不能机械地理解“夫妻一方”,而应肯定当事人在离婚后或者子女在成年后的诉权。因此,《解释三》最后未对提起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权利人限制为夫或妻。参见杜万华、程新文、吴晓芳:《〈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11年第17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实务中,法院的立场往往取决于对个案案情的实质衡量,只是这种个别化衡量难免造成差别待遇,有违裁判的稳定性。
1.婚生子女否认诉讼
案例一:张某(法律父)与刘某(生母)婚内生育一子,二人离婚后张某因事故死亡,张某的兄弟姐妹请求确认张某与其婚生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而刘某在之前的离婚诉讼以及该案诉讼中均承认婚生子并非张某亲生,但拒绝亲子鉴定。法院认为,虽然《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将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主体表述为“夫妻一方”,但在夫妻一方死亡等特殊情形下,根据我国婚姻法和继承法等相关规定的精神,应当认可继承人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权利,这也是人伦道德的体现。[注]参见吴可征、殷春昱:《继承人是否有权利确认非亲子关系——河南洛阳西工区法院判决张建水等诉张玉龙确认非亲子关系纠纷案》,《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17日第六版。
案例一将继承权人纳入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主体范围,构成了对通常认知的突破,相当于认可了继承利益可超越身份关系稳定等法益设置的防线。依此逻辑,祖父母、叔父姑母、兄弟姐妹等享有继承利益的人均可成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适格原告,而夫或妻作为原告只是诉讼的通常情况,而非惟一情况。不过,实践中亦有裁判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祖父母无权请求否认婚生子女,即便案件直接涉及到继承或分割死亡赔偿金,其理由便是《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原告应为“夫妻一方”。[注]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2851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中法民申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民终369号民事判决书。实质上,法院否定祖父母等人的原告资格,更像是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公序良俗等考量,更像是得出否定性结论后才搬出司法解释的条款。若法院倾向于肯定祖父母等人的原告资格——像案例一反映的那样——则会强调实体法精神、道德人伦等因素,以论证“破格”的合理性。不难发现,司法解释在现实中处于一种可用可不用的境地,其对主体资格的规制事实上被虚化。
2.非婚生子女否认诉讼
案例二:被告(生母)与原告(可能的生父)交往中生下一女,原告诉称,被告将女儿带走并提出多种要求,原告曾希望协商解决抚养问题,但被告多次到原告工作单位闹事,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并拒绝接受亲子鉴定,故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的非婚生女儿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法院认为,根据《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诉的主体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中的“夫”或“妻”,而该案原告与被告并非夫妻关系,原告提起本诉不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主体身份条件,故裁定驳回起诉。[注]参见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7民初257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0民终1192号民事裁定书。
案例二属于非婚生子女否认诉讼,原告提出了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请求,但并非针对婚生子女,而是针对非婚生子女。就此而言,法院以《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来排除原告的主体资格的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无论是司法解释制定者还是理论界,均认为《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是对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规定,或者说,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被等同于请求否认婚生子女身份。[注]参见前注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书,第48页;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民法基础》,《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其次,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限制婚生子女否认权的主体是为了维护身份及家庭关系的稳定,可是此种“稳定”在该案的情形下原本就不存在,那么有何理由将原告的确认需求拒之门外呢?
(二)谁有权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
相对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而言,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的原告问题,似乎总徘徊在研究者的视线之外,《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也未从语义上对其作出任何限定,因此该问题实际未被纳入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中,司法任意化的隐患也由之而生。
1.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
案例三:黄某(生母)在与陈某1(法律父)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同陈某2(可能的生父、原告)同居并生下陈某3(现已成年、被告)。陈某2诉称,陈某1早年将陈某3抢走并误导其认为陈某1为其生父,现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与陈某3的亲子关系。陈某3在诉讼中拒绝进行亲子鉴定,辩称自己与没有抚养关系的原告陈某2并无感情,且从小接受陈某1的照料,也不愿伤害一直伴随生活的陈某1的感情。法院认为,在缺少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原告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否定陈某3与陈某1之间基于婚生推定而成立的亲子关系。鉴于陈某3已经成年而原告未对其进行抚养,若缺乏必要证据而推定亲子关系成立,不利于社会风气、公序良俗,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民终字第1675号民事判决书。
虽然该案中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推定亲子关系存在,但实务中,同居事实通常足以成为推定亲子关系存在的“必要证据”,[注]参见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2015)八民一初字第0056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2014)鄂南漳少民一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而该案的证据评价及实体判决应该说是价值平衡之后的决定。毕竟,“一味地追求血缘真实而忽略当事人在常年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亲情,损坏当事人现存家庭模式和现实生活利益,裁判者应当极力避免产生如此消极的裁判后果”。[注]同前注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书,第57页。正是考虑到这种社会价值观,该案中法官除了拒绝适用推定,别无其它选择,即使原告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证据也应如此。进一步来看,哪怕已经存在支持原告主张的亲子鉴定,法院认可原告与被告的亲子关系依然面临障碍,因为胜诉判决将导致被告同时拥有两个父亲。这里,亲子鉴定虽能表明婚生推定不符合事实上的血缘关系,但婚生推定的父亲身份必须经过适格主体行使撤销权方可消灭。由此看来,至少在该案情形下,可能的生父的原告资格是值得怀疑的,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的主体不应毫不设限。
2.婚生子女确认诉讼
案例四:原告(生母)与被告(法律父)婚内生育一子,因被告怀疑婚生子并非自己亲生,原告和被告的夫妻感情受到影响。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其婚生子之间具有亲子关系,以消除被告疑虑,但被告在诉讼中拒绝配合亲子鉴定。法院认为,被告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反驳原告的主张,也不能合理解释拒绝亲子鉴定的原因,故根据《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推定婚生子与被告之间存在亲子关系。[注]参见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5)绵竹民初字第653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四属于婚生子女确认诉讼,原告在已经成立婚生推定的场合下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其诉讼的本意虽是澄清血缘,但在不能强制鉴定的背景下,法院能认定的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于是以法律视角观之,原告是要求对一种本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这可能给原告的起诉资格带来疑问,原因在于,首先,《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指向的是非婚生子女认领的情况,并不是婚生子女确认诉讼的规范依据;其次,原告与被告仍在婚姻关系内,原告的诉讼不附随给付或其他请求,就此纯粹的确认请求有无司法保护的必要,仍有讨论的余地。
(三)小结
整体观之,谁能成为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原告,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找不到清楚的答案,甚至找不到清晰的解题思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法官直接诉诸家事审判的一般原则,就个案的案件事实做出价值选择,再决定是否准予诉讼。然而,缺少中层理论指导的价值衡量容易带来裁判的分歧,尤其是作为法官推导前提的宏观原则极抽象,且原则与原则之间时常表现出对立(比如血缘真实原则与身份关系稳定原则)。此外,这种粗放型的价值衡量还引起法官说理论证的单薄与跳跃,有损裁判的形式合理性,并足以引起合理性危机。有鉴于此,原告资格认定需要更科学的理论梳理和制度支撑,将散漫的价值判断纳入秩序化的轨道,以提升裁判的安定性及规范性。
二、诉的归类:建立原告资格认定的秩序框架
在原告资格的实务认定陷于困惑的同时,学术界提供的理论支持也非常有限,然而实际上,诉的种类理论本是可以为把握原告资格指明方向的。在民事诉讼法视野下,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该“直接利害关系”在各种类的诉中有不同的表现:给付之诉的适格原告是具有给付请求权的当事人;确认之诉的适格原告是对诉讼标的有确认利益的人;形成之诉的适格原告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一般而言是指按照法律可以通过形成判决加以救济的人。[注]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沿此逻辑,确认亲子关系诉讼属于何种诉,便依相应法理确定原告即可。然而在国内文献中,有关诉讼种类归属的只言片语却呈现出分歧状态,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为形成之诉,[注]参见李春景:《关于亲子关系否认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评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之规定》,《河北法学》2016年第12期。这其实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说保持了一致;[注]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页;[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另一方面,更多研究者笼统地将确认亲子关系诉讼视为确认之诉,[注]参见杨立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第137页;刘哲玮:《确认之诉的限缩及其路径》,《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认为能够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告必须有确认利益,反过来说,有确认利益的主体均可起诉。[注]参见刘敏、陈爱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28-229页。由是观之,依托诉的种类理论建构原告资格的秩序框架,还得从诉的正确归类着手,即辨明确认亲子关系诉讼属于确认之诉还是形成之诉。
(一)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的区分标准
通说认为,形成之诉是指原告要求法院变动一定法律状态(权利义务关系)的请求,而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要求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请求。[注]参见前注⑩,张卫平书,第186页、第188页。就制度表现而言,两种诉的公认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形成之诉由法律明定,[注]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笔者于本文内所称的形成之诉单指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不包括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形式上的形成之诉。假如没有相应的实体法规范,或者没有满足实体法规范内的要件,则形成之诉不被许可,[注]MüKoZPO/Becker-Eberhard, 5. Aufl. 2016, ZPO Vor § 253 Rn. 28.而确认之诉不要求实体法依据;第二,从判决的主观范围上看,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效力,而确认判决的效力只及于当事人双方;[注]Saenger, ZPO, 7. Aufl. 2017, Vor § 253 Rn. 5 ff.第三,从判决的时间效力上看,确认之诉的判决面向过去,而形成之诉的判决面向未来。[注]参见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任重:《形成判决的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第 28 条》,《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
然而,这些外在差异更像是区别形成之诉与确认之诉的结果,而非进行区分的原因,以其为区分两者的标准只会使两者的边界愈发难以捉摸。一来,有无法律规定不足以界分两种诉,因为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制定确认之诉的规范,况且形成之诉的规范总是从无到有被人为制定出来的,现实中的形成之诉可能还先于规范出现。[注]还有观点认为,并非所有形成之诉都必须在实体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才合法,对于某一诉讼的性质是否为形成之诉,可以用类推解释方法判断之。参见陈桂明、李仕春:《形成之诉独立存在吗——对诉讼类型传统理论的质疑》,《法学家》2007年第4期。二来,判决的主观范围及时间效力均可由法律灵活规定,形成之诉与确认之诉在此不必然有异。比如在德国,确认判决的效力通常及于当事人双方,但其《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FamFG)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血缘关系事件的裁定均具有对世效力,于是确认裁定与形成裁定的效力差别就被消除了。[注]Saenger, a. a. O. , Vor § 253 Rn. 5; MüKoFamFG/Coester-Waltjen/Hilbig-Lugani, 2. Aufl. 2013, FamFG § 184 Rn. 7.此外,日本学者也指出,形成判决是否具有溯及力是立法论及解释论的议题,“是一项旨在谋求该法律关系的安定性要求与彻底实现效果的必要性之间协调的活动”,若需要彻底变动的效果即可承认判决具有溯及力(比如否认亲子关系),反之则可以规定权利变动只面向将来(比如解除婚姻)。[注]同前注,新堂幸司书,第154页.
归根结底,形成之诉与确认之诉的区别在于诉讼目的——形成之诉以变动为目的,确认之诉以固定为目的。具体而言,提起形成之诉旨在实现法律关系的变动,当事人的请求可能是消灭或变更既存法律关系,或者是建立新的法律关系。[注]参见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Klappstein, Die drei verschiedenen Klagearten im Zivilprozess - Systematik,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JA 2012, 611.正因为变动法律关系往往对当事人权利影响巨大,所以为谋求社会关系的安定,才规定当事人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形成效果。[注]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无论是要求形成之诉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定要件,还是限制提出诉讼的主体及期间,都旨在制约这种变动法律关系的可能性。相对而言,确认之诉的目的是消除当事人之间法律状态的不安定,[注]MüKoZPO/Becker-Eberhard, a. a. O. , ZPO § 256 Rn. 1.是“通过裁判来对现状予以确定之诉,以此达到防止变更现状之目的”。[注]同前注,新堂幸司书,第148页。于是,不改变法律关系原有状态的确认之诉,也就不像形成之诉那般始终存在着被限制的需要。
(二)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种类二分
基于笔者此前的分析,一种诉讼是形成之诉还是确认之诉,纯粹由诉讼目的这种诉讼的内因决定,原告意图变动还是固定既有的法律状态,可通过考察诉讼对象和具体请求得出结论。就待归类的确认亲子关系诉讼而言,既不能因为我国缺少对应的法律规范而将其认作确认之诉,也不能因为亲子关系判决理应具有对世效力和溯及效力而将其视为形成之诉。确认亲子关系诉讼须得一分为二地看待,其中的婚生子女否认诉讼和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为形成之诉,非婚生子女否认、婚生子女确认等诉讼则归于确认之诉。
1.形成之诉:婚生子女否认与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
我国学者普遍认可婚生子女否认权的形成权性质,[注]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30页。可仍将婚生子女否认诉讼归为确认之诉,其症结在于混淆了“客观事实的不确定”与“法律关系的不确定”这对概念,即误以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是为了“确认夫与婚生子女无血缘关系的事实”。[注]张红:《婚生子女推定之撤销——最高人民法院法(研)复[1987]20号之解释适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4期。在我国,现实中当事人主要是因为不确定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而起诉,希望法院判断的也是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如此,诉讼似乎符合确认之诉消除不确定性的主旨。然而,这一认识忽视了法院判决只能针对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诉讼能够变动或固定的也只是法律上的亲子关系,血缘关系即便经由亲子鉴定得到澄清,也只构成认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理由。因此从法律角度考察婚生子女否认诉讼,不管血缘关系如何,婚生推定的亲子关系在诉讼时是明确成立的,当事人主张法律推定不合于客观事实而请求否定亲子关系,目的是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这完全符合形成之诉的含义。同理可知,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也是形成之诉。因为在法律视阈下,子女与特定主体之间在诉讼前本无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原告虽意图消除血缘关系不明的状态,但请求认领是希望通过判决将子女与特定主体间的亲子关系建立起来,期待的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新设效果。并且,与婚生子女否认类似,非婚生子女认领所指向的法律关系的变动,在我国也必须经由法院判决方可实现。所以整体观之,婚生子女否认和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虽无法律明定,但不影响其形成之诉的性质,其原告资格问题也当按照形成之诉的逻辑处理。
2.确认之诉:非婚生子女否认诉讼和婚生子女确认诉讼
现有研究倾向于把婚生子女否认与非婚生子女认领两类诉讼当作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的全部,但如果把诉讼请求与待确认的身份关系的法律状态结合起来,确认亲子关系诉讼还可包括非婚生子女否认诉讼(如案例二)与婚生子女确认诉讼(如案例四)。这两类诉讼的原告均抱有固定现有法律地位的目的,其中,非婚生子女否认诉讼是在不存在婚生推定的情况下,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这合乎消极确认之诉的内涵;至于婚生子女确认诉讼,请求确认的是特定主体与其婚生子女间存在亲子关系,是典型的积极确认之诉。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情况是当事人在诉讼时便不清楚其身份关系的法律评价,故请求法院进行确认,这也属于确认之诉的范畴。比如,在婚生推定的法律规则比较复杂的国家,起诉人不能确定自身情况是否符合婚生推定条款,故请求法院判断婚生推定是否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确认之诉带有一种兜底色彩,有些诉讼虽无规范上或理论上的依据,但当事人仍可能具有权利保护需求,因而特定场合下,“法院正是通过对诉的利益的把握……可以将该纠纷引入程序,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法的合理解释,明确新的权利规范”。[注]张卫平:《诉的利益:内涵、功用与制度设计》,《法学评论》2017年第4期。
三、利益衡量:探寻原告资格认定的秩序规则
如果说确定秩序框架是对诉讼种类的正本清源,那么后一阶段寻找原告资格认定的具体规则,则很大程度上属于利益衡量的工作,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在形成之诉框架内,确定原告本是个“法律规定了什么”的问题,但是我国相关法律的制定工作尚未完成,问题于是转化成为“法律应当怎么规定”,这就需要立法者进行实质化的利益衡量。在确认之诉框架内,原告的适格性全然立足在确认利益上,这就需要裁判者基于确认利益的识别理论做出具体判断。
(一)形成之诉的封闭式原告资格
形成之诉以封闭原告范围的方法限制司法的裁量自由,意味着法院不能单纯因为起诉人具有法律明确规定之外的正当的权利保护需求就许可其诉讼。法律上划定封闭的范围,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利益权衡:正面是“起诉的价值”,即允许诉讼保障了原告的血缘知悉权,在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中还有解决子女抚养教育问题的意义;反面是“禁诉的价值”,也就是说,禁止诉讼包括了维护家庭关系和谐及身份关系稳定,维护个人隐私及名誉,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等考虑。以下,笔者将结合案例一、案例三中的问题,梳理婚生子女否认及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
1.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适格原告
就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适格原告,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一定共识,不过各方措辞仍有差异,有的认为夫妻一方或子女成年后均有起诉资格;[注]参见前注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书,第58页。有的将原告资格限于生母、生母的丈夫、子女;[注]参见前注,刘敏、陈爱武书,第221页。有的将否认权人限于被推定的父亲、母亲及成年子女。[注]参见前注,梁慧星书,第230页。总体上,封闭式的立法结构大致是无争议的,但法律规范的行文表述及具体含义尚待统一。
第一,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原告应限定为法律上的父亲、母亲及子女。首先,如果立法采用“夫、妻及子女”的表述,则有失严谨,这也是《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的缺陷之一。因为实践中不乏夫妻一方在离婚后请求撤销亲子关系的案例,此时起诉人已经不具有夫或妻的法律身份,法官则需就其原告资格再为论证。[注]参见赵英颖:《否认亲子关系诉讼的必要证据认定——四川阆中法院判决廖某诉廖姓二子女婚姻家庭纠纷案》,《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8日,第六版。其次,如果立法采用“父、母及子女”的表述,则未明确可能的生父是否被囊括在内便存在疑问(而这类主体理当被排除在外)。现实中的法律父、母亲及子女可能已经组建家庭,并在家庭生活中产生亲情,在这三方当事人未行使否认权的情况下,允许可能的生父起诉势必损害现存家庭和身份关系的和谐稳定,还可能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造成不利。最后,子女有权作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的原告,其血缘知悉权和切身利益的维护不因其成年与否而有差异,在原告为未成年子女时,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由法院指定的代理人代为诉讼。
第二,其他主体无权提起婚生子女否认诉讼。这里值得讨论的,是案例一引出的继承权人可否起诉的问题。就此,比较法上通常持否定态度,比如德国通说指出,孙子女有机会代位继承祖父母的遗产并不构成祖父母享有撤销权的决定性理由,祖父母也不能因血缘关系阻止子女继承父亲的遗产。[注]MüKoBGB/Wellenhofer, 7. Aufl. 2017, BGB § 1600 Rn. 4.此外,哪怕是在继承案件中,其他继承权人也无权附随性地要求血缘澄清,因为继承权本来也不完全取决于血缘关系,比如法律父默认撤销亲子关系的期间流逝的情况。[注]Vgl. OLG Koblenz ZEV 2013, 389.从我国法上看,继承权同样不完全以血缘关系为依据,养父母子女以及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均可发生继承,所以澄清亲子关系并非处理继承权纠纷的必经之路,[注]参见代贞奎、向蕻:《裁判继承权纠纷不以亲子关系鉴定为依据》,《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4期。整体上也没有充分理由肯定祖父母等继承权主体拥有血缘知悉权。案例一中法官以起诉人享有继承利益来认可其起诉资格,更接近确认之诉下认定原告的路径,结果带来了原告范围的扩张。若按形成之诉的思路,继承利益不属于确定该类诉讼原告的考虑因素,即不属于“起诉的价值”,继承权的争执应诉诸其他救济途径(例如提起确认继承权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
2.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的适格原告
相比之下,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的研究远未成熟,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未提到原告资格的限定性,有学者认为子女的生母或成年子女可以起诉;[注]参见前注,王利明书,第305页。有学者认为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有权起诉;[注]参见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还有学者区分了原告的顺位,即“确认非婚生子女生父诉讼,由子女提起的,以生父为被告。子女死亡的,可以由其近亲属提起”。[注]同前注,刘敏、陈爱武书,第225-226页。故在此,封闭式的原告资格及具体主体的适格性都有待明确。
第一,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的原告应限于母亲、子女以及可能的生父。首先,这里所说的子女包括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现实中的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也多以未成年子女为原告、母亲为法定代理人。[注]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哈民一再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4)宁民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德民一终字第805号民事判决书。若是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怠于向生父请求,也可考虑由未成年子女的其他法定代理人或由法院指定的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其次,鉴于我国未设置自愿认领制度,当事人必须依靠判决来确立与非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故有必要赋予可能的生父以请求权。只不过,可能的生父行使诉权应附有前提,即待认领的子女在诉讼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如果不设这个限制条件,无条件允许可能的生父作为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的原告,加之可能的生父又无权提起婚生子女否认诉讼,那么支持认领的判决将导致子女拥有两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注]不过,这一理由不能实质阻碍子女或母亲的诉权,因为这两类主体本有请求婚生子女否认的权利。若子女或母亲提出非婚生子女认领之诉时,子女依婚生推定已有法律父,则原告应先行提出或同时提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可能的生父提出认领诉讼,不利于维持子女与母亲、法律父业已建立的家庭关系。有鉴于此,对案例三中的情形,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自陷于证据评价等实体审理的疑难之中。
第二,其他主体无权提起非婚生子女认领诉讼。比如法律父是无权请求可能的生父为认领的,实践中曾出现的案例,是法律父以子女的母亲及可能的生父为被告,请求可能的生父认领子女,并请求可能的生父与母亲连带承担其抚养费支出。[注]参见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04)南民初字第1324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渝一中民终字3683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了认领的诉讼请求,但更妥当的做法,是以原告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这里,应承认法律父对于认领的诉讼请求具有利害关系,因为他同时提出了连带赔偿的请求,而连带责任要以可能的生父与子女之间成立亲子关系为前提。[注]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人民法院(2000)六民初字第731号民事判决书。只不过,形成之诉的框架下,直接利害关系本就不足以证成原告资格,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既不在“起诉的价值”范畴内,也就更不能与“禁诉的价值”相抗衡了。
(二)确认之诉的开放式原告资格
确认之诉是一种为克服法律状态不安定而设置的纯粹程序法制度,其原告适格性需要法官以确认利益为标准作具体审查,审查的关键在于原告的权利或者法律地位是否受到了现实危险之威胁而处于不安定状态。[注]MüKoZPO/Becker-Eberhard, a. a. O. , ZPO § 256 Rn. 39.通说认为,允许主张的确认利益除了财产性质的利益,还可包括诸如职业利益、信誉度、社会地位或名誉声望等内容。当事人的确认请求不仅可以针对既存的法律关系,也可能针对并不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此外,确认之诉的原告甚至不必是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他还可以请求对诉讼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甚至是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注]MüKoZPO/Becker-Eberhard, a. a. O. , ZPO § 256 Rn. 35.所以,确认利益的广泛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司法判断通常具有情境化依赖,这也导致法律难以预先划定确认之诉的原告范围。
就亲子关系事件而言,控制原告范围以限制起诉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这来源于“维稳”的考虑,然而这种考虑不能被照搬到确认之诉中。因为,原告请求确认的是现有身份关系的法律状态,并非要求法律关系的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用确认之诉来固定或澄清法律关系,反而有助于消除认知差异,进而平复当事人权益或地位的不安。所以,即便敏感如亲子关系事件,非婚生子女否认、婚生子女确认等确认之诉的原告也应当是开放式的,委诸法院以确认利益为标准判断之。由此审视案例二中的非婚生子女否认纠纷,可能的生父的原告资格应当得到肯定。对此,虽有观点认为否认之诉的前提是婚生推定的亲子关系成立,不然当事人根本不需要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注]参见前注,杨立新书,第132页。但案例二现实地表明了可能的生父具有确认利益,因为亲子关系存否的争议使其法律地位不明,进而其财产权益、名誉声望等利益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同理,也应认可案例四中生母请求确认婚生子女法律关系成立的权利,因为原告感到个人名誉及家庭关系受到威胁,所以有提出婚生子女确认诉讼的确认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确认之诉的原告范围是开放的,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任意的,因为认可确认利益也有其前提条件。首先,只有在确认之诉是排除该危险的适宜方法,并最终能够澄清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时,才存在确认利益。[注]参见王洪亮:《实体请求权与诉讼请求权之辨——从物权确认请求权谈起》,《法律科学》2009年第2期。例如,在前述案例二和案例四中,原告因为现有身份状态不安定或存争议而感到自身利益受威胁,法院就其身份关系应受到何种法律评价做出认定,就是代表国家给予该种关系以确定性的评价,这样,身份关系的法律状态虽未变动,但请求人的权利保护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其次,确认之诉的适用还具有居后性,也就是说,如果原告能提起给付之诉或者不作为之诉,一般就不存在确认之利益。除非确认之诉可以使争议问题有意义地、符合事实地被解决,那么在有提起给付之诉的可能之际,也例外地准许确认之诉。[注]vgl. BGH NJW 1996, 918; NJW 2001, 445.最后,法官在判断确认利益有无时,还应当加入对亲子关系事件的特殊价值考量,比如,在诉讼有违公序良俗和道德人伦之际,应认为特定主体的起诉不存在确认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