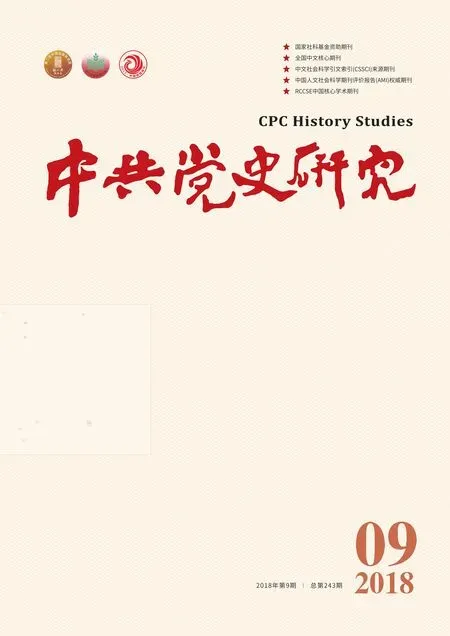归侨知青史研究中的若干思考
2018-02-07叶青
叶 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历时20多年、涉及1700多万青年的大规模政治和社会运动,由于有着毋庸置疑的历史深度和社会意义,近40年来,有关知青的文学作品、学术成果一直长盛不衰。然而在重新检视和反思知青史研究时,笔者却发现,归侨知青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华侨学生归国求学,国家给予妥善安置照顾。1968年,侨生群体也被卷入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但对于归侨知青这一特殊群体,学术成果暂付阙如。
笔者认为,归侨知青是与普通知青有过一段相同人生际遇的特殊知青群体,在知青史研究的版图上应当拥有一席之地。对归侨知青群体的个案微观考察,可以为多角度、多层次推进知青史研究、华侨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实证基础。归侨知青史研究无疑亟待挖掘和拓展,其中的重点地区当属福建、广东、广西等侨乡大省(自治区)。近一年来,笔者带领福建知青史研究团队初步展开归侨知青史研究。拓荒的路途是艰难的,但筚路蓝缕之中,我们也有了一些收获与思考。
一、特定群体研究应有整体关怀,与时代“同频共振”
归侨知青、“老三届”、回乡知青、兵团知青,以及知青先进人物都堪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其中每一个群体的特殊性都很明显,例如归侨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方式、返城时间、双重生活经历影响下的心路历程,以及特殊身份影响下的待遇、境况等,与普通知青都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我们研究这些特殊群体,首先还是应该有整体关怀,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群体都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具体到归侨知青,其身份主体是参与上山下乡的侨生。二战后,海外华侨子弟在居住地升学受挫,华侨纷纷将子女送回中国求学。妥善安置侨生,并对之加以适当照顾,是新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但随着五六十年代东南亚“排华”浪潮高涨,归国侨生数量逐年增加,国家无法负担源源不断的侨生,开始动员他们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政治动员形成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的外部氛围,冲击或感染着归侨知青,驱使他们奔向农村“广阔天地”。
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相对落后,没有劳动经历的归侨知青不得不面对艰苦的劳作和无亲无故的“不安全感”,而且国内“左”倾错误加剧,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归侨知青大多在农村备受身份歧视。在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归侨知青比普通知青更容易焦躁,一方面希望自己积极融入群体,“炼一颗红心”,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就这样日复一日,部分归侨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在艰难困苦坎坷挫折中……知难而进,以不折不挠的精神……超越这些困难”[注]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更多的归侨知青则认定前途渺茫,选择逃离。不难发现,归侨知青的心态和上山下乡经历,总体而言与普通知青并无太多差别,都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其中不乏渴望和激情,更有茫然、困顿、无奈和悲苦。由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下乡生活遭遇诸多困难,知青群体包括归侨知青的思想状态更趋离散化。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知青运动的终结乃是一种历史必然。由此观之,归侨知青的命运同样与祖国的政治、社会生态“同频共振”,考察归侨知青,同样离不开对他们所处时代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的分析,离不开对有关历史语境的探讨。因此,我们团队尝试通过考察归侨知青这一特定群体,来反映和理解整个知青运动,并力图总结出知青运动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
二、应该注意揭示差异,关照分层,展开比较研究
目前,区域知青史课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历史的心境(知青上山下乡的心态、知青家长的态度)、人口与安置(人员迁移与城市化、地点选择、经费使用、日用品与粮油供应、安置的组织模式)、物质生活(劳动收支、住房、日常伙食)、精神生活(自发学习、读书、看电影、文体活动)、恋爱婚姻、疾病、事故与事件、回城(招工、病退、困退、返城、遗留问题)等。对这些不同角度论题的透彻描述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面相的历史场景,丰富了我们对知青运动全貌的了解,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地域性知青史研究成果同质化的问题——尽管研究的省份不同,但基本都围绕上述主题范式、依据中央政策落实情况而展开,因此研究成果大多平铺直叙、千篇一律。实际上,东南西北中,各省市职能部门分别负责知青工作的筹谋和执行,行政区划、政策举措不同,自然环境、文化生态、人口分布、生产方式以及知青个人经历、家庭背景、价值取向也都不同,而且“文化大革命”过程复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知青运动体现在地域、时间段、个体等方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不能一概而论。研究者在透彻梳理某一区域情况并推导一般结论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探寻其间的差异性。这既需要脚踏实地的扎实研究,又要具备放眼全国乃至全球的思维和视野。目前来看,学界还比较缺乏对全国知青运动区域性差异的揭示,以及对各种差异原因的比较研究。
以福建归侨知青上山下乡安置为例,“文化大革命”时期,归侨知青因海外身份而遭受政治歧视,生活上遇到很大困扰。但是,不同区域的民风民情不同,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同,归侨知青的感受当然也各有差异。不仅福建、广东、广西存有差异,即使是福建的不同地区也不尽相同。我们发现,福建龙岩永定归侨知青的住房条件、生活待遇比其他地区好,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永定是福建省安置侨生插队最多的一个县,档案资料显示,1960年至1969年,该县先后接受来自厦门的侨生1553人[注]《关于永定县插队侨生问题座谈会的报告》(1973年3月20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48-007-0085-0061。。我们以为,促使厦门、永定革委会重视归侨知青的主要因素是侨生的海内外影响力。客家人好客、亲切热情的传统和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归侨知青的“异乡感”。举例来说,落户永定的厦门归侨知青林瑞蓉不仅成为知青的先进典型,还被推举出席中共十大。还有不少在永定插队的知青被安排看管“牛鬼蛇神”,或担任代课教师等。侨生们也能发挥专长,被允许开办夜校,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还担任了大队干部。不过,相比于永定,福建其他地区归侨知青的生存环境总体却是艰难的,在招工、招干、评工分方面遭受歧视,以至一些地区的归侨知青不敢领侨汇,或是急于同海外亲属“断绝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归侨知青群体参加运动的心态也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个体差异,即使具有相同的心态,其程度、表现也不尽一致。因此,笔者以为,特定知青群体的研究应当深化到专题史层面,并对研究对象进行分层解构,分区、分段地观察,在理性分析具体特征的基础上,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关问题作比较、参照和印证,最后揭示隐匿在差异背后的历史普遍逻辑。就福建归侨知青而言,我们力图以分专题、分时段的形式梳理出该群体上山下乡的历史脉络,并比较归侨知青与普通知青,以及广东、广西两省归侨知青在安置、生产、生活、心境、返城等方面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解读不同个体或人群命运起伏的生存轨迹及其深层原因,以期弥补目前知青史研究之缺憾。
三、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挖掘和抢救史料
几年来,我们团队几乎走遍八闽大地各市、县档案馆、方志办、党史办,努力搜集、研读知青史料。因为知青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所重合,相关文献资料的获取变得十分困难。一年来,我们开展归侨知青专题研究,特地走访了福建省侨联、侨办和省、市政协等单位,皆毫无所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归侨知青在历史记录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我们还多次赴泉州、龙岩、厦门、漳州、南安等地,实地考察当年安置归侨知青的农场,目前仅在农场修订的志书里翻检出改革开放后几位重访农场的归侨知青的名录。我们几乎穷尽了形形色色的正式、非正式知青出版物,仍然难觅归侨知青群体个人书写的文本之踪影。福建省档案馆、永定县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收藏了有关归侨知青政策的文件和档案,虽然三家档案馆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开放程度都不高,近来更是愈发难以查阅。
我们在基层收集文献资料的同时,努力与时间赛跑,对归侨知青当事人或家属进行口述访谈。当代史研究一个独特的优势是能够与研究对象近距离互动交流,口述史料的抢救和挖掘也是在保留那些曾经无法发声的人们的记忆,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与其互补互证。同时,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可以展示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禁忌、人际关系和个人心路历程,有助于我们复原历史现场之原貌,揭示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动荡、特殊、非常的时期,口述访谈资料无疑显得尤其宝贵。但是,我们在遍寻归侨知青的过程中发现,福建省可以访谈的当事人并不多,不少当年的归侨知青或返回出生地,或移居港澳,目前大都年事已高,甚至体弱多病,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抓紧寻找、抢救“活字典”“活资料”。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言:“苦心盘算、犹豫不决和推托耽搁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受访者可能等不及访谈便去世了——口述史家永远都必须和寿命做现实竞赛。”[注]〔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Ⅷ页。
四、知青研究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关键所在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一场延续时间如此之久、卷入人口如此之多、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前所未有的运动,目前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更不用说充分展开对这场运动的分析和评价了。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知青个人或集体的回忆录、访谈录、纪实文学著作等出版,这些著作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个时代,但是,它们显然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因为对知青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感受上。笔者以为,目前的知青研究需要构建史料与问题结合得恰如其分的研究范式,需要理论方面的凝练和探索,需要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综合考察,需要数据化手段的介入和多学科的联合探讨,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知青运动的来龙去脉,并探寻其因果规律。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随着上山下乡的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对知青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有知青经历的学者已经步入老年,培养一支成规模、训练有素的以历史学为主,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专业研究队伍,应是知青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地方知青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少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都把知青史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这些年轻学者为知青史研究的细化和拓展作出了贡献。与有知青经历的老一辈学者相比,他们在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字资料时,有可能无法抓住关键点,但也正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可以完全摆脱个人经历和情感的羁绊,比知青一代更冷静、更客观地评说这段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高校知青史研究的晚生后学,在学成毕业后,有的因为不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而无法继续研究,有的苦于知青档案资料获取困难、学术成果难以转化而无法应对体制内的评价考核,最终大都无奈地离开了辛勤耕耘几年的知青史领域,或者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副业”。因此,除了希望国家尽可能多地公布档案资料之外,还要呼吁有关方面在科研成果上为有志于知青史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推进知青史研究并使之持续发展的最实在的路径。试想,如果归侨知青史研究能够有广东、广西高校学者共同参与,寻求史实上的相互支持和佐证,并对相关论题逐一展开深入探讨,那么,这一研究的进程无疑将大大加快。遗憾的是,仅凭现有研究队伍,还不太可能实现学者间的互动与协作。
五、关于知青与非知青两代学者的衔接与继承
文末特别回应郑谦研究员关于知青与非知青两代学者的衔接与继承问题。他在此次笔谈中谈及“后知青时代的研究与写作”,并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老知青当年那段生活经历是无法替代的。在他们记忆深处,农村生活不仅仅是艰苦的劳作,还有那些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的错误而弥漫在整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中的、难以言说的压抑和迷茫。”金光耀教授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们对自己作为知青的经历有着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因此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担待,摆脱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陈见,以史家之笔来书写这段特殊的历史。作为知青史的研究者,这些学者的优势是明显的,也是独特的。”[注]金光耀:《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应该说,他们的评析是中肯、精当的,很客观地道出了知青个人感受和体悟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然而,时光如白驹过隙,知青研究终归要由知青学者那里传到新一代非知青学者手里,两代学人如何做好衔接与继承?笔者以为,没有知青经历,没有体验过知青所处的历史场景,而是依靠搜集、爬梳浩如烟海的各种史料,努力还原知青生活的原貌,并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逻辑,这对非知青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除了需要拥有不畏困难的胆识、勇气和韧劲之外,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阅读资料,尽可能多地开展口述访谈,努力提升自己还原历史的感觉和能力。同时,在解读史料时,要注意对比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尤其要将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相互印证,花时间做“沙里淘金”的补正、考辨工作,以免误读。实际上,我们每次近距离访问归侨知青或作细微的史料互证时,都感到颇有收获,不仅更多地了解了他们当年的物质生活、劳动生活和心理世界等被宏观研究所忽略的鲜活历史细节,进一步体会了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生态场景,而且更深刻地领悟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外,新一代非知青学者开拓、借鉴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方法,这是很值得提倡和鼓励的。由于两代学者所处时代和所受学术训练的微妙差异,非知青学者更具史学方法论意识,更讲究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运用,然而年轻学者也必须注意规避刻意地、华而不实地借鉴甚至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现象。
人们对知青史研究尚有许多期待,而知青史研究想要拓展和深化,离不开年轻学者的加盟。两代学者之间的衔接、继承和发展的确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知青学者们非常重视年轻一代非知青学者的学术发展,努力做好“传、帮、带”,例如,知青史研究重镇——复旦大学今年拟举办“新一代知青学者学术沙龙”,邀请前辈学者指导、评点年轻人的学术论文或著作,这无疑是一项可以帮助年轻学者快速成长的很有意义的举措。
总之,尽管知青史研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而且仍有许多分歧和暂未深入涉及的领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知青史研究一定是在不断进步着的,因为毕竟研究者已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知青运动属于“一代人的经历,几代人的话题”,它与“十七年”教育相关,与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关,与四十年改革开放相关,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甚或关系未来。推进和坚守是艰辛的,学者们任重道远,因为拓荒是我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