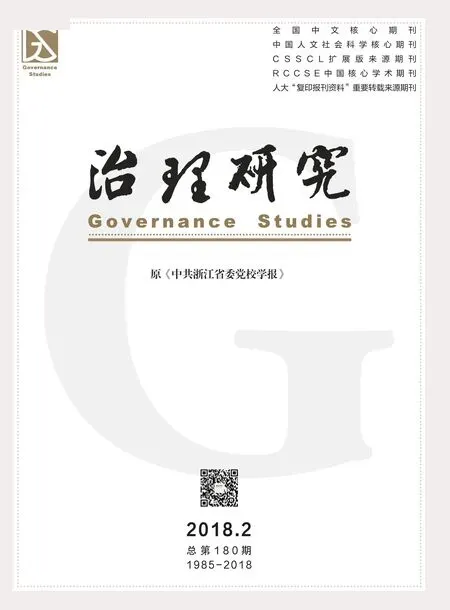秦汉政制构造原理榷论
2018-02-07□李霞
□ 李 霞
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古代政制,定型始自秦汉,功用完善于唐宋,弊端显现于明清。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政制之肇始与定型阶段。*参见劳榦:“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页(“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受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甚至于新的法律,其中还保有固有的法律精神,这仍是从秦汉沿袭而来”)。一般认为,春秋战国系中国古代历史之一大变局,除“礼坏乐崩”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一种全新类型的政制之塑造提供了契机。秦始皇虽“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开启了统一大帝国背景下古代政制模式的创建与尝试,但古代政制模式的真正定型实完成于汉代。因此,钱穆先生说“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钱穆:《国史大纲》(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否认秦在中国古代政制之创建与尝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政制定型化的过程中,既无经验可循,亦无理论、逻辑之指引,此一古代政制实在是社会之变迁、文化之积淀、情势之所趋、一时之权变等因素混合作用之结果。
一、古代帝国早期的历史困局
在地域与政权组织空前的大帝国里,如何“永久地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不仅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也是汉高祖仓促间无从应对而汉武帝继“文景之治”后仍在不断尝试解决的问题。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汉高祖在即帝位之初,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局:新生政权及其稳定性受到内外诸多势力或因素的严酷威胁。面对如此危机,首要之举是找到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予以迅速化解。假如仓促之间的选择只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还需要在危机化解之后,继续在现实情势的基础上寻求更为稳定而有效的控制模式,即(1)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古代帝国直接而有效的控制。
接着,依据历史的逻辑与现实的形势,新生政权的执掌者总要面对来自旧有政治势力及其统治下社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挑战与质疑,从而不得不从思想或者观念上(2)为新生政权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进而,在论证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加强对帝国的控制,又需要(3)创建或编造一套适于时宜的理论或者学说,应对原有政治势力的挑战,化解社会民众的质疑,推动并磨合帝国政权机构的运转。
然而,维持一个空前庞大的古代帝国秩序,除了强力的控制、思想与文化的统一之外,至少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4)中央朝廷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5)如何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治国策略,如何实现以及在实现过程中如何修正预选的治国策略。也只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才会使“实现帝国的有效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在认识、辩明上述诸问题并且尝试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仍然不得不认真对待“人”发挥的作用。
在中华帝国早期(公元前3世纪后期至公元前1世纪中期)约170余年间,上述这些问题纠葛在一起,使这个空前庞大的古代帝国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现实困境,在挑战古代帝王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决断的同时,也为构造一个举世瞩目的古代政制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缘。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或许可以将“古代政制构造”作为一种认识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暗码,通过对这一暗码的解读,尝试分析并理解深埋在帝王将相的荒冢与浩如烟海的史册之间古代政制赖以建构的社会基础及其基本原理。
二、古代政制的构造及修正
上述胪列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帝国早期面临的历史困局,而作为统治集团核心的帝王将相,将如何在政治实践中面对与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完成对古代政制模式的选择、构造与修正。
(一)通过强力的控制
无论是秦始皇嬴政还是汉高祖刘邦,在亲掌政权或者即皇帝位之时,均是在经过连年兵革战乱后而求其内政之宁息,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政局或者帝国秩序的完全控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尽可能直接而有效的策略与措施。具体包括:(1)禁止民间私藏兵器,“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避免或压制地方反抗;(2)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以迅速掌握各地信息,及时处理地方事务;(3)略取边地,修筑长城、亭障等军事要塞,以防御或者驱逐匈奴、戎胡之人;(4)严刑峻罚,强行甲兵,以防止或者镇压朝廷内外诸侯大臣的反叛。*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206、216页;以及《史记·高祖本纪》卷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1-331页。通过这些极具强制性的武力措施,秦汉初期的统治者比较有效地实现了对整个帝国的直接控制。
(二)“终始五德之传”
为了应对此前的政治势力及其统治下社会民众的挑战与质疑,秦代及汉代初期的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思想观念上论证自身政权及其对帝国控制的正当性。鉴于此,公元前221年,天下初定之际,秦王嬴政便以“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为由,下令丞相、御史、诸博士及群臣“议帝号”,百官议定帝号为“泰皇”,嬴政更为“皇帝”,自称“始皇帝”,甚至企望“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1-203页。
在“名正言顺”之后,秦始皇开始选用齐国士人“终始五德之传”的学说,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论证“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然后合五德之数”。为了进一步论证秦政权的正当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紧接着,又先后在之罘、琅邪、碣石、云梦、会稽等地祭祀虞舜、大禹,并“立石刻,颂秦德”。*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7-222页。
至汉代,据史载“高祖斩白蛇”之故事,借老妪之口称,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对此,应劭解释为,秦祠白帝,“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随后,沛县起兵之际,“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页。可见,汉初统治者也在尝试运用“终始五德之传”来论证其政权的正当性,恰如班固赞语所言,“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第59页。
公元前166年,鲁人公孙臣与丞相张苍围绕“终始五德之传”展开辩驳。公孙臣上书陈请“终始传五德事”,声称“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建议“当改正朔服色制度”;而丞相张苍却“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表示反对。次年,“黄龙见成纪”,应验了公孙臣之说,故而汉文帝“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下诏“亲郊祀上帝诸神”。*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卷十,第363页。
可见,秦始皇和汉初诸帝均不约而同地借用“终始五德之传”来论证自身政权及其对帝国控制的正当性,在社会心理层面迅速赢得了较为普遍的社会信任,或者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民众的怀疑,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三)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在依凭武力控制帝国秩序,借用“阴阳五行”与“封禅祭祀”证明自身政权的正当性之后,秦汉初期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套完整而适于时宜的理论或学说,作为其控制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理。公元前213年,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围绕“封建”与“郡县”展开辩论,秦始皇令群臣商议,李斯趁机主张“焚书”,一方面,强调遵守和维系中央朝廷政令的权威;另一方面,强化和巩固“事皆决于法”的政制构造。*参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218页。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发“焚书令”。次年,因侯生、卢生等诽谤逃亡,秦始皇“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扶苏谏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不仅未予采纳,反而命扶苏随蒙恬戍守边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20页。至此,在李斯等人的努力下,法家哲学高居庙堂之上,而儒家思想及其他诸子学说暂隐于江湖。
西汉初期,高祖刘邦对先秦诸子学说既没有明显偏好,也从未想从中选取一种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略显吊诡的是,从个人本性看,刘邦将“竖儒”挂在嘴边,明显对儒士有一种厌恶心理;但从治国角度看,他又对儒家学者及其政治思想与政制方案另眼相待。例如,公元前195年,经鲁国而“以大牢祠孔子”。*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第56页。之后,虽然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卷十,第366页。,武帝“乡儒术,招贤良”,甚至准备依据儒家思想建构古代政制,但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甚至因赵绾、王臧等儒者“欲议古立明堂”及“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而案杀之,以致“诸所兴为者皆废”。*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卷二,第382页;亦可参见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10页。从政制构造的主导思想看,这一时期大体上是黄老之术对儒家思想的压抑。
迄窦太后崩,武帝发布征贤良文学诏,旨在察问“古今王事之体”,“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以致“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卷二,第382页;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15页;以及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07、2709页。然而,武帝并不限于将贤良文学之士笼络于庙堂之上,以论证“古今王事之体”,而是还想方设法扭转自商鞅变法以来整个社会形成的功利的、无信无义的人际关系。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尝试通过法律手段推行教化,强令官吏察举孝廉*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19页。,以期移转民间风俗,为政权之巩固奠定相当的社会基础。
在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参见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第1901-1918页。,不仅回复了武帝关于“古今王事之体”的察问,更为之草拟了一幅由“正心—任德—教化—均布—更化”构成的古代政制蓝图,而构造这一政制的前提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在“隆儒”的基础上,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册”,“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50页。
(四)“封建”与“郡县”之辩
在借“推终始五德之传”及“封禅祭祀”论证政权正当性的过程中,帝国统治者仍然要面对如何处理中央朝廷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元前221年,丞相卫绾建议采用周制,立国封王,镇治地方。秦始皇下令群臣商议,多数大臣表示赞同。廷尉李斯却提出异议,认为“置诸侯不便”。*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4页。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并且指明导致东周列国纷争的原因正在于分封诸侯。故而,秦始皇分天下以为郡县,企图通过委派官吏和巡行郡县实现对帝国的控制与治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颂赞秦政以及始皇之威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然而,博士齐人淳于越却亢意直言,接卫绾之踵,再次提出效法殷周封建之制。*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页。对于周青臣与淳于越围绕“郡县”与“封建”而展开的驳难,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强制要求遵守先前推行郡县的法令,而是下令群臣商议。对此,丞相李斯重申推行郡县制的立场,并强调遵守法令的意义: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17页。
至汉代立国之初,摆在统治者面前的至少有两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及经验:殷周的封建制与秦的郡县制。但在他们看来,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秦行“郡县”历十五年而亡,偌大一个历史教训,无论是刘邦还是他的谋臣,似乎都不得不选择“封建”。即位之初,刘邦先后分封了诸多异姓诸侯王及列侯,实际上,这也是高祖的“权宜之计”,毕竟“与天下同利”*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321页。是其获得并维系帝位的基础。此时,汉“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随后,异姓诸侯王逐渐被刘氏宗亲替代,不仅实现了“王同姓以填天下”*班固:《汉书·荆王刘贾传》卷三十五,第1481页。的初期政制架构,还订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卷九,第337页。的“白马之盟”。
在汉高祖的政制谋划中,经过血亲网络过滤而成的“家族封建”政制模式显然优于宗亲异姓杂封的“殷周封建”政制模式,然而,这也是刘邦政治幼稚的表现,未能看清在庞大帝国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血缘纽带根本无力维系中央对地方诸侯王国的控制与约束,因而必须寻求其他更为稳定而有效的政制模式与制约方法。二十年后,贾谊洞察到刘邦未能看清的这一问题,谏告文帝“患之兴自此起”,力陈“封建之患”的根由,甚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概言之,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分化”政策。*参见《新书》“藩伤”、“藩彊”、“五美”诸篇,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页、第39-40页、第67-68页;亦可参见班固:《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第1718-1719页。此处所引疏文即通常所称的《陈政事疏》,亦称“治安策”,是贾谊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虽然文帝在政治实践中部分实践了贾谊的方案,但未能有效解决问题,以致这一始终未能消解的矛盾终于激化而成“七国之乱”。在这一矛盾从潜隐到爆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位与贾谊具有相当的政治洞察力,且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制改革方案的人物——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
为了推行“削藩”政策,晁错向景帝上书力陈“封建之弊”,指出封诸侯“分天下半”而“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根据晁错的建议,景帝先后下诏削楚东海郡、吴豫章郡及会稽郡、赵河间郡及胶西六县。此后,武帝继续推行贾谊、晁错等人秉持的“分化”政策,虽留分封王侯之事,但在诸多限制下已形同虚设,根本无力对抗中央朝廷,从而使地方治理之权事全部纳入郡县制度之内。因此,张荫麟先生将“七国之乱”称为“汉朝政制的大转机”*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是相当允当的。
(五)从“事皆决于法”至“德主刑辅”
自商鞅变法以降,秦以法家思想立国,至平定天下,“始定刑名,显陈旧章”,“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任用李斯,厉行法治,“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以至于“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及至秦二世,“遵用赵高,申法令”,“用法益刻深”。*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03-223、227、228页。然而在厉行法治的过程中,却“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班固:《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页。概言之,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秦朝选择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并作最严厉之推行,从而在“专任刑罚”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古代帝国的政制模式。
尽管汉高祖初入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307页。,但其后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班固:《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页。,实际上,从政制初步构造的角度讲,主张“汉承秦制”是比较恰当的。惠帝、高后时,用萧何、曹参为相,“以无为之法填安百姓”,以致“依食滋殖,刑罚用稀”。及至文帝即位,反思“亡秦之政”,改革刑制,以“恺弟君子”、“为民父母”之意“化行天下”。*班固:《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931页。
公元前156年,景帝下诏,命廷尉与丞相商议修订律令,于是,提出了一套由“计偿费,勿论”、“坐臧为盗”、“夺爵免官”以及“罚金”“没入所受[臧]”等阶梯式刑罚构成的吏治律令的修订方案。然而可惜的是,这一修订律令方案是否被采行,史籍未载。但有史书明确记载的是,自公元前145年起,景帝连续五年颁发诏令,要求吏民遵行法令,尤其强调依法治狱、治吏的重要意义。*参见班固:《汉书·景帝纪》卷五,第101页、106-109页。
至汉武帝时,无论是基于政治实践的现实需求,还是受到儒家学说的观念影响,开始将“百姓之未洽于教化”*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22页。作为政制构造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从而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运用先秦诸子学说——当然,核心是儒家思想——修正已初具模型的古代政制。显然,这些修正举措绝非单纯向世人宣扬所谓的“仁圣之心”,更重要的是,借儒家学者倡导的殷周礼制之名变革或修正秦及汉初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家的法治主义政制模式。
三、“士”在古代政制构造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古代政制构造及其修正的过程中,帝王在重大事件或困境中的政治决断与选择当然至关重要,但影响或促使帝王做出政治决断的因素却是复杂而多元的,除了帝王自身的主观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面对重大事件或者困境时,究竟是哪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古代帝王的政治决断与选择,以及这些人在古代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思想传统、文化特征等。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钱穆先生的观点——汉代政府是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并且“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的“士人政府”*参见钱穆:《国史大纲》(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或可呈现一条值得深入的路径。
(一)李斯及其对古代政制的初步建构
为实现对统一帝国的有效统治,秦始皇在平定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乏在政制建构层面上的尝试与努力,在这一政制建构过程中,李斯既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极具代表性。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少时,为郡小吏”,追随荀况“学帝王之术”,在分析战国形势之后,认为“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且“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故而选择辅佐秦王建功立业。随着为“天下一统”之“帝业”的谋划计策的铺展与实现,李斯逐渐受到秦王的重用,由郎而为长史,为客卿,为廷尉,及至平定天下后,官至丞相。公元前213年,李斯借评议淳于越谏言效法殷周封建之机,建议禁私学、去诗书、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而颁发了“焚书令”。此外,在“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以及“巡狩,外攘四夷”等政制建构与帝国控制方面,李斯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第2231-2237页。
从楚国小吏跻身帝国公卿之列,李斯审时度势,运用“帝王之术”实践了个人建功立业的雄心。然而,秦始皇死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身居丞相位的李斯却与赵高合谋矫诏赐死扶苏,立胡亥为太子,即二世皇帝位。随后,秦二世采纳赵高的意见,“更为法律”,案杀群臣诸公子,以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此时,在政制构造的理念上,李斯虽然与赵高存在决然的分歧,但在政治的高压下,迫不得已上言“独制督责之术”,以“阿二世意,欲求容”,而朝廷“事皆决于赵高”。李斯又不甘数十年营造之功亏一篑,尝作最后一搏,“上书言赵高之短”,却被赵高诬以“谋反”之名,“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参见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第2238-2250页。
(二)贾谊及其关于古代政制的理想与阐释
经历秦末战乱之后,汉初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天下和洽,但同时,汉家王朝也面临着四伏的危机。无论是为了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辙,还是为了实现刘氏政权对帝国的有效控制,汉文帝开始尝试逐步修正奠基于秦代而为汉代继承的古代政制。在这一社会与政治背景下,除了具体的制度变革外,迫切需要有深刻洞察力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统治者指明潜伏的危机与症结所在,并为之提供更具长远眼光的政制改革方案。从历史上看,足以堪此重任者正是贾谊。*关于贾谊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司马迁:《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页。
文帝时,河南郡守吴公(曾学事李斯,而李斯与韩非一起共事荀子)因贾谊少时“能诵诗属书”且“通诸子百家之书”而“幸爱”之,或可推断,贾谊的政治思想与荀子的学说可能有某些共通之处,甚至一脉相承,从而有别于孔孟传统的儒学思想。例如,在分析汉初封建诸侯问题及解决方案时,贾谊指出“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贾谊:《新书·制不定》卷二,第71页。
在诏议对策之时,贾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司马迁:《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页。文帝虽未予直接采纳,却“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后因列侯周勃、灌婴、张相如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人构陷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疏离贾谊,適以为长沙王太傅。此后,文帝仍欲重用贾谊,但在封侯建国的问题上,两人或有分歧,贾谊数次上疏谏言削藩,文帝不听,以致贾谊郁郁不得志而终。*参见司马迁:《史记·贾谊传》卷八十四,第2192、2201-2202页。尽管如此,但贾谊构造帝国政制的理念及策略却得到后世的沿袭与实践。
(三)晁错及其对古代政制构造理论的实践
与贾谊的“郁郁不得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同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晁错*关于晁错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司马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399-2400页。,后者的政治生涯始终处在文景时期最激烈的政治旋涡中心。晁错身为太子家令时即已看清“封侯建国之弊”及“更定法令之需”,故而“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虽然文帝未予采纳,却因“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及至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经常与其商讨政事并采纳其建议,“法令多所更定”。随后,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因而与公卿列侯宗室之间产生极端的矛盾。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以诛错为名”起兵反叛,景帝在两难之间采信窦婴、袁盎的建议,“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400-2401页;亦可参见班固:《汉书·吴王刘濞传》卷三十五。
晁错早年“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后“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又“受《尚书》伏生所”,其中,“申商刑名”是以申不害、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伏生所讲《尚书》实为儒家思想在齐鲁之间的流传,由此推断,晁错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或可兼备儒法两家之论。然而,晁错“为人陗直刻深”,虽然在对汉初“封建之弊”的判断上与贾谊同样是正确的,但在推行“削藩策”时,“更令三十章”,试图用严刑峻法“侵削诸侯”,以致“诸侯皆喧哗”。*司马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399-2401页。结果,不幸沦为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政治博弈祭坛上的牺牲。至于对晁错及其建言的评价,诚如谒者仆射邓公所言,“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司马迁:《史记·晁错传》卷一百一,第2401页。
(四)董仲舒及其对古代政制的哲学构建
在秦汉政制构造过程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如何创建一套合于时宜的理论学说,既可镇治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又可化解社会民众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并磨合帝国政权机构的有效运转。无论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还是思想文化的积累,抑或政治现实的需求,迄至汉武帝时,历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而最终站在这个关节点上且抓住了这一契机的人,就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的汉儒董仲舒。*关于董仲舒早年经历的简介,可参见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第2714-2715页。
秦时初创的古代帝国政制,至汉武帝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了相当的问题与弊端,无论是实践者,还是思想者,在对现实的观察过程中也积累了相当的洞察与反思,并且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等学说注入儒家思想之中,建构起了一个以“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希望能通过“更化”或者“改制”来修正既有政制之不足,从而将此前的“法家政治”转化成理想中的“儒家政治”。*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页。
相对于“秦政权缺乏社会基础”来说,至两汉时期,“中国真正地熔铸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一段熔铸的过程,不在汉初的郡国并建,不在武帝的权力膨胀,而在于昭、宣以后逐渐建立起政权的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恰恰是“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拔而参与其政治结构”。*参见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6、355页。然而,无论从“士人”阶层形成的渐进过程,还是秦汉帝国建构的政治实践来看,恰如前文所述,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时,具有独特政治哲学思想与治国理论的“士人”,已经开始在选择重大政治决策的历史时刻突显其重要意义,并且开始于古代帝国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