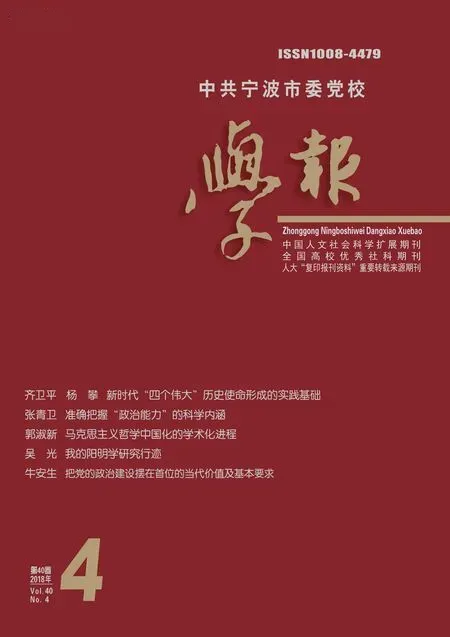“格物”之异
——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2018-02-06胡发贵
胡发贵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4;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6)
据《明史》记载,明代学术史上,王阳明与罗钦顺是“心学”与“宋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他们俩生前是好友,多有交际,但学术观点却相左。在一封给阳明的信中,罗钦顺曾这样说过:“去年尝辱手书,预订文会,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与偕之大道。……窃恐异同之论有非一会晤间之所能决也。”(《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又》)一次见面晤谈难以解决观点分歧,可见罗、王之间的“异同之论”不是个小问题。其实不仅罗钦顺是这样看,王阳明也有类似的感觉。在给罗钦顺的信中,阳明就如此说道:“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彼此观点的出入非通信所能廓清,必须见面长谈才能道出个眉目,也足见差异是很大的。对罗、王两人间的观点对峙,当时学者就很困惑:为什么同为大儒,彼此的学术思想会如此方圆枘凿呢?一次弟子问高攀龙:“整庵、阳明俱是儒者,何议论相反?曰: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宋之朱、陆亦然。……学问并无别法,只依古圣贤成法做去,体贴得上身来,虽是圣贤之言行,即我之行矣。”(《明儒学案》卷58)按高氏的意思,是因为学者有不同的师承,故即便同是儒者,议论也会相反的。其后的清人就直揭罗是王的论敌了:“钦顺平生专力于穷理格物之学,而力斥王守仁讲良知之非。”(《四库全书》本《整庵存稿》案语)不论是何种原因所致,罗、王两人“议论相反”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我们就从格物问题上试窥其一斑。
一、阳明格物学要义——“默坐澄心为学的”
早年阳明曾一度信奉朱熹哲学,倾心于格物求理。十八岁那年他曾问学于吴与弼的弟子娄谅,“过广信,谒娄一斋谅,语格物之学,先生甚喜,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后遍读考亭(朱熹)遗书,思诸儒谓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年谱》)年轻气盛并急于求道的阳明遂去格竹子。理未求到,反而大病了一场,后来阳明对此十分后悔:“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
格竹子失败的经验使阳明对格物求理的求知路径深感怀疑。后因被贬谪贵州龙场三年,万山之中无书可读,只能默诵已往读过的书,然后冥思苦想地求解其中的微言大义,一日忽然恍然大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这样阳明也就更加坚信于事物上求理是大错而特错了,主张格物“只在身心上做”:“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下》)
王阳明被谪贵州龙场的时间是正德二年(1507),三年之后、即正德五年(1510)才予以平反昭雪,阳明对格物观念的彻底改变也就在此期间完成。自此以后,阳明对格物的理解完全“心学”化了,照黄宗羲的评论即是“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了:“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明儒学案》卷十)
经此根本性的转变后,阳明坚决摈斥外向的格物求知:“先生曰:先儒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在阳明看来宇宙万物是不可穷尽的,因此一草一木的去格首先是做不到的。其次,即使“格得”草木,如果未能反身而诚,还是难说已求得物理。由此阳明认为格物只能在“自家意”上做工夫:“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传习录下》)
下面这段话中,其“格物”的“澄心”意向则更为明显: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阳明这里已将“格物”之“物”变成了意念的投影,即“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事物反而只成了观念(意)的表现和证明了。他的这一说法,自然会令人想起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判断。“物”既然只是精神活动的一种投射,那么“格物”自然也就只要在“心”上、即意念之内做工夫了。
二、罗钦顺的忧虑与批评——“局于内而遗其外”
罗钦顺对“格物”问题十分关注,曾进行过长期的深入研究,“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明儒学案·师说》)也因此,就阳明对格物的诠解,钦顺甚感忧虑,也坚决不赞成。其间的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是阳明格物之学有“启禅学”之隐忧。他在写给阳明的信中强调指出,学“溺于外”固不妥,但“局于内而遗其外”则更不当,因为这有“禅学化”的嫌疑了:“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于内外乎?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见乎理之一,无彼无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会,夫然后谓之知至。……外此或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遗其外。溺于外而遗其内,俗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今欲援俗学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禅学之萌,使夫有志于学圣贤者,将或昧于所从,恐不可不过为之虑也。”(《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罗钦顺虽然也不满沉溺于词章的“俗学”,但“局于内”更令他不满,因为这会导致诱发根本为异端的“禅学”;而更使他不安的是,阳明“格物”之学的内向性,会使得有志于圣贤之学的后来者有滑向禅学的隐忧。
其二,阳明的“格物”说没有正解物之观念。罗钦顺认为:“近时格物之说,亦未必故欲求异于先儒也。只缘误认知觉为性,才干涉事物,便说不行,既以道学名,置格物而不讲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与其所见相似,难得来做个题目,所以别造一般说话,要将物字牵拽向里来。然而,毕竟牵拽不得,分定故也。向里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两无归着,盍于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见者,虚心一意,恳求其所未见者,性与天道未必终不可见,何苦费尽许多气力,左笼右罩,以重为诚意正心之累哉。”(《困知记》续录卷上)
罗这里可谓是一语中的。阳明在诠解格物观念时,正是竭力企图将“物”字“拽向里来”,即消解“物”的客观实在性,使其成为一种精神意念的投影,从而使得格物化为“默坐澄心”就可以了。罗钦顺以为孔孟之圣学,是与此断然相反的:“盖必穷事物之理,通古今之变,然后可以扩充其猷为,必明义利之分,秉固穷之节,然后可以坚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贵乎博学而尚志也。”(《整庵存稿》卷三)文中“必穷事物之理”、“贵乎博学”就显示出,在罗这里,“格物”既是外向的实践,也是“致知”的开始与知识的本源。
与阳明的理解相反,罗对“格物”的解释尤其重视其“工夫”、即实践品格。他说:“格字古注或训为至,如格于上下之类;或训为正,如格其非心之类。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训之,因文生义,惟其当而已矣。吕东莱释天寿平格之格,又以为通彻三极而无间。愚按通彻无间亦至字之义,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为明白而深长。试以训格于上下曰通彻上下而无间,其孰曰不然。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困知记》续录卷上)从这段话也可见出,罗钦顺对“格物致知”命题的历史源流是曾下过一番求索功夫的,罗的刻意描述,似意着揭示阳明“格物”之“格”于史无据。
罗钦顺还明确指出,王阳明的“格物”解释不符合经典本意:
“切详《大学古本》之复,盖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圣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直以支离目之,曾无所用。夫当仁之让可谓勇矣,窃惟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颜渊称夫子之善诱,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邪外邪,是固无难辨者。凡程朱之所为说,有戾于此者乎?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王阳明)则从而为之训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其为训如此,要使之内而不外以会归一处。亦尝就以此训推之,如曰: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而格之,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以归于正,而必尽夫天理,盖犹未及知字,已见其缴绕迂曲而难明矣。审如所训,兹惟《大学》之始,苟能即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皆尽夫天理,则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诚矣,继此诚意正心之目无乃重复堆叠而无用乎。”(《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
文意表明,罗以为阳明实是臆解儒家经典以为自己的心学张目。在罗看来“圣门设教”,是“文行兼资”的;而历史语境中的“文”就是“博学”,就是“资外以求理”,绝无一味反观内省的意思。其次,经典强调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一个统一的认识、修身的过程,而阳明的“格物”则否认这种连续过程性,只要“格物”就一了百了,下面致知、正心、诚意都成为多余的了。所以罗钦顺论定阳明的“格物”为“缴绕迂曲”,实即强词夺理、牵强附会。
三、阳明的反驳
对于罗的批评,王阳明则大不以为然。他申辩并反驳说: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于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从文中反诘的句势和口气来看,阳明是断然拒绝罗指责自己专事“反观内省”的,而且坚信自己的“格物”论涵括了朱子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论的全部内容,只是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为明己意,阳明又继续申论道: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诚然诚然。……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这里阳明一是将认识论的“格物”,引向修身道德论范畴,“物”演变成“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二是从其心本论入手,将世界化为“心”的表象和摹写,于是“物”自然变成“心”之“明觉之感应”,且与“意、知”一样,同属精神活动的意念而已,所以“格物”在阳明那里必然就是格“心之物”、“意之物”了。
四、罗钦顺再献三点疑问
对于阳明的辩解,罗又提出了三点疑问。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此执事格物之训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自有《大学》以来无此议论,此高明独得之妙,夫岂浅陋之所能窥也邪。然诲谕之勤,两端既竭,固尝反复推寻不敢忽也。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无疑者一也。
又执事尝谓意在于事亲,即事亲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诸如此类不妨说得行矣,有如《论语》川上之叹,《中庸》鸢飞鱼跃之旨,皆圣贤吃紧为人处,学者如未能深达其义,未可谓之知学也。试以吾意著于川之流、鸢之飞、鱼之跃,若之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邪?此愚之所不能无疑者二也。
又执事答人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当云知至而后物格,不当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则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后乎?此愚之所不能无疑者三也。”(《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又》)
罗这里虽不否定阳明将物定义为“意之用”、训格物为“正其不正心归于正”,是为秦汉以后的“独得之妙”,是一大新“发现”,但又严正地指出其说有背于经典的本旨,并给出了自己的三点疑问:
一是阳明一方面将物析成“三物”,一方面又讨论“一物”,那么此“一物”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是指“意之用”,此“三物”中的“物”又当何解呢?罗钦顺意在强调不论阳明如何善说,终究是方圆枘凿的,亦即阳明释物为“意之用”是说不通的。
二是阳明训格物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罗所举例“川之流、鸢之飞、鱼之跃”,就不同于“事亲”、“事君”,因为后者确有所指,而前者不论是“流”,还是“飞、跃”,所描述的都是某种心态与意境,而且是深含微言大义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如此又如何来“正其不正”呢?
三是阳明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先后顺序。按照经典的表述,致知是格物的结果,所以《大学》的说法是“致知在格物”;而阳明把“致知”理解成“致吾心之良知”,“格物”为“事事物物各得其理”,于是“格物”也就成为“致知”的衍生物。在罗钦顺看来,这显然是有违于《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的;而且阳明“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与“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之论,有含混和矛盾处,到底是先“精察”还是先“致良知”呢,故罗钦顺反问“察也,致也,果孰先乎?”罗氏的发问确实也揭示了阳明格物中一些见解的未臻圆融。
四、余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格物致知是个古老的命题了。单一个“格”字出现得很早,金文中就已有其字形了,但作为一对概念,“格物”却是晚出。它首见于《礼记·大学》篇中,原文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对此“格”,汉儒郑玄注解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礼记注疏》卷六十)这显然是从道德视角来解读的。唐代孔颖达则给出了认识论的诠说:“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礼记注疏》卷六十)从即物穷理的意义上注解格物致知的,则开始于二程:“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河南程氏外书》卷二)朱熹则进一步完善了二程的观点,并强化了格物的实践认知倾向:“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卷一)又说:“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也。”(《朱子语类》卷十八)朱子这里所强调的都是对客观对象、即事物之理的认识,其格物之训的唯物和实践倾向是很明显的。下面这两段话则更为鲜明地体现明了这一点:
“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大学或问》卷二)
“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朱子语类》卷十五)
前段话强调的是格物的具体实践性,后一段话所突出的是格物的客观性和外在性,而其宗旨都是肯定格物即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包含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性。
当然,历史上的格物论也存有许多争议。对朱熹的上述格物说,同时代的陆九渊就不同意,他们俩曾在江西信州的鹅湖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即“鹅湖之会”。陆不喜言“格物”,他指斥朱熹的格物致知为“支离事业”,“诸公上殿,多好说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会,何必别言格物。”(《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他宣扬“尊德性”的“易简工夫”,实即反身而诚的体认本心:“所谓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易》之穷理,穷此理也,故能尽性至命。《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陆九渊集》卷十九)文中所谓的“格此”、“致此”之“此”,均指“心”而言。王阳明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上,显然继承了陆九渊的理路,且更为鲜明地将“格物”予以主观化的解释,阳明弟子的这段评说可谓一语中的:“心犹镜也。……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传习录》)所谓“磨上用功”,亦即“心上用功”,这就与“照物”的客观求知迥异了。所以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说也多有不满之词,如指斥之为“玩物丧志”,是“无轻重”,“少头脑”(《传习录下》)等等,对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心学家轻议、甚至诋毁朱熹的言论,罗钦顺在情理和学理上都很难接受,甚为不满,也多有反诘。当然,这是需要专文讨论的另一个话题了。
要之,钦顺的“格物”说继承并坚持了“宋学”的实践倾向,也吸收了同代人——如湛若水的“格物”思想,并突出了“格物”论中所固有的认识论内涵。罗、王之间在“格物”问题上的论争,实质上是“物本”与“心本”之争的一种表现。王以“心”化解世界万物,故推论出“格物即格此心”;罗则认为这种理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处也,岂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困知记》附录《答允恕弟》)。王阳明的“格物”说实也是为其“致良知”说作铺垫,其旨意是指向主观精神的张扬与舒展,即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如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而罗的“格物”说,在学理上严守经典,在学统上固守“宋学”、尤其是程朱之见;在致用层面则着意于利国利民的实际绩效,“君子之学有以明其体,必有以周其用;礼乐法制工虞教养钱谷甲兵,其为事虽有精有粗,或巨或细,无非一理而已,能于此而不能于彼,能其一而不能其二,其为用有所不周,则其体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则君子之学岂易言哉。……其所学岂记诵词章之谓哉。”(《整庵存稿》卷六)
从整个认识过程来看,“格物”实是认知之路的起点,开始即如此纷争,也预示着罗、王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是难以妥协的。可惜的是,天不假年。罗钦顺的《与王阳明书·又》写完未及发出,就传来了阳明下世的消息。罗所提出的“三疑”再也得不到王阳明的亲自回音了,这也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如果阳明也能与钦顺一样的高寿,罗、王两人关于“格物”问题的辩论,以及其他话题上的对话,肯定更精彩、更丰富,当然这也定会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留下更多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