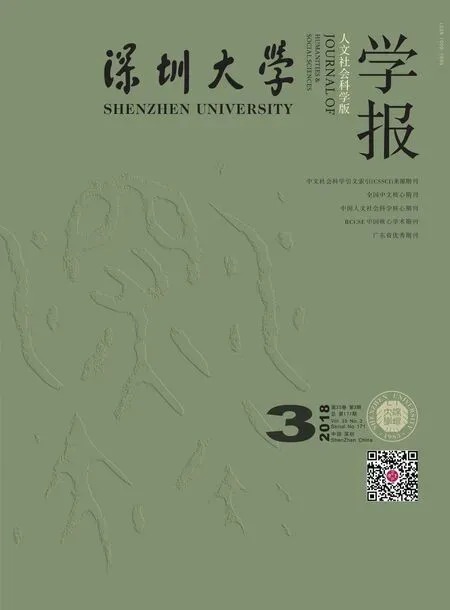从现实主义到古典主义:中国百年文艺思潮的价值转向
2018-02-01潘水萍
潘水萍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细而察之,20世纪中国批评视野中伏着一股以“现实主义”而非“古典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一特殊而诡秘的文艺思潮回响及脉流症候。从另一侧面的根本关节点上看,此一吊异文艺迹象之频繁涌现、高扬,恰恰正是“古典主义在20世纪中国”研究话题的缺席、蒙尘、遮蔽甚至被边缘化迹象之明证。这是被当下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的、颇为令人反思的学术疑点问题。若探究并揭开以“现实主义”而非“古典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所投射出来的种种片面性、隐患性和机械性,自然要将近年学界对“古典主义”要义进行自觉辨析或描述式考察逐步纳入概观,甚至也要溯源到20世纪中国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细致的辨析及悉心的考量,才可以从整体上看出造成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历史时代语境及政治意识因素。诚然,探讨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局限性因缘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之流变迹象,显然有着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及其现代学术价值投射,特别是透过把握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之本然原样的精神资源张力、文化意味表征及审美理想内质,更是有助于人们对20世纪文艺史上某些话语之病态套用之文学现象作一弹性的了解和较为成熟的自省。有学者很是独到地谈及:“文化传统与文学经典有其自身的稳定性与恒久价值,对单向度的社会现代化起着反思与纠偏作用。”[1]需要正视的是,从学术角度对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相去甚远此一命题展开解读与探析,包括学界对此议题之忽视与尘蔽的端倪予以正本溯源、矫枉和纠偏,这显然需要秉持一种警觉与审视的学术态度。若就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实质局限性、越位性和乏力性而稍加整理与阐发,将从以下三大内隐性要略问题展开意义深远的会诊、破解与辨识。
一、被遮蔽的视域:“现实主义”的高扬与“古典主义”的蒙尘
20世纪以来,多元文艺思潮的新旧嬗替对中国创作思维的鲜活独特之面貌和脉动可谓影响深远。然而,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终究应该以“现实主义”来解读,还是应该以“古典主义”审美理想进行解读更为贴切?如何从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根基脉络里仔细界定、分疏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种局限性失误的缘起,重审“古典主义”之内蕴意涵、特质底色和精神要义,重点发掘并揭发古典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新文艺建构之隐而不彰的影响张力,藉此溯源并把握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生发的古典主义文化底蕴与审美样态。从另一侧面上看,这无疑也是潜在地考察古典主义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度被抽离、轻忽、断裂、规避、障蔽而遂变得冷寂、沉沦与隐没无声的重要因由。盘而点之,以“现实主义”置换“古典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无疑是越位的、背离的、变异的、偏失的、乏力的、瓶颈的、令人费解的甚至是相去甚远的。沿此一怪异的文学现象余响,回望并追溯到20世纪中国具体的民族情感特质和思想理论渊源中,剥离多重缘起之层层面纱而展开一一细密学理的印认、考量、还原与挖掘,则可心领神会地发现一种被屡次误解及扭曲了的文学现象——频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潜在内涵的偏误。这也正是学术界尚没有充分作出概要说明与阐发的文艺症候。究其原因,这倒令人想起似乎过分耽于20世纪某一特定历史语境之多重内在张力及大量相关主流话语细节在迥然作怪。这一文艺症候之学术盲视点固然需要作出独特感知与关联窥探。
应该承认、直面与重思以“现实主义”理论景象整体理解与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有着诸多的盲目而偏狭的不妥之处,在此很有必要做出高度理性的质询、修正与重释。细察则可发现,无论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还是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Realism)与古典主义(Classicisme)两个词的丰富性所呈现出来的内涵意蕴是截然不同的,更是不能相互替代与任性置换的。因为现实主义又称“写实主义”,强调对自然的直接复现、认知、理解与感知,它摒弃理想化的想象,而主张细密观察和据实摹写。就概念意涵之秘蕴而言,古典主义可称“唯理主义”。它主要指对希腊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文化的高度认同之余脉涵蕴,力主模仿其和谐、均衡、克制、理性、静穆、启蒙的人文深旨及文风基调。推本溯源,“古典主义”这一审美理想在传统民族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的中心位置和确凿性的辐射根源。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历程诚然也从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古典主义”以独特的“古典新义”。可以说,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一脉是中国乃至世界漫长的古典文学实践及其古典性意涵理论思想的结晶。毕竟,近现代的文艺书写创作依然印刻着某种前现代的总体特征。不管其审美理想内核是推崇“动荡”、“激情”、“神性”、“感性”等概念的刻画,抑或是持守“和谐”、“理性”、“静穆”、“克制”等理念的经典化书写,或多或少地烙印着某种挥之不去的古典情怀、审美理想和生命精神的记忆。朱立元尤以为要地指称:“我们应该指出,一些概念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最初表示的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文化事件等,但在后来的使用中,它已远远超出了这种内涵,成了一种文化范式、审美范式的代名词了,我们不能局限于它最初的意义了。”[2]在这一点上,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坛,人们再次以一种折中、古典、稳健的古典主义审美理论思维向度,强调可持续发展之和谐社会建构正向合力。毋庸置疑,走向比照、融通和糅合的世界文艺批评话语的今天,“古典主义”此一审美理想与文艺思潮,其所承载与阐扬的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批评的担当使命与新时代观念启蒙本色的意义彰显。梁实秋有更深入的唤醒:“可是居今之世,以文学的传统精神相倡导,至少在印象主义者看来可谓不识时务已达极点。但在印象的世界里,事事是相对的,生活像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的活动,生活没有稳健的基础,艺术文学于是也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在重理性的古典主义者看来,必感异常的不安。我们可以不必诉诸传统精神,但是我们可以诉诸理性。”[3]其实,中国古典文学究竟应以“现实主义”展开贴标签式的释读与概观,还是应借重与归趋于“古典主义”进行本真性的认定与阐扬?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反思并加以呼吁、反思与修正的文艺症候。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频频以“现实主义”而非“古典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自然是不甚妥当的。其中有一点原因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主流思潮的一度滥加高歌、张扬和哄抬,正是当时文坛对众多“主义”的一片唱和中造成学界对“古典主义”思潮一度展开深不以为然的盲目诋毁、屏蔽、挤压而使其被后人扭曲的缘起,暂时处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冷寂消歇,这恰恰是问题的真正要害之所在。若进一步厘析造成这一彼此唱和、鼓吹喧嚣声中的不可忽视之诸多原因,则绝然不能不追溯到这一独特历史语境下颇为悬殊的政治意识形态风向标的根本性深意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典主义在中国哑语、骤衰及边缘化,还有主因生成的另一脉——那就是因为20世纪早期学衡派代表吴宓、梁实秋等人倡导新人文主义,被当时学界文坛肤浅地甚至一棍子打死般地贴上了保守、落后、传统的眼光取向,从而受到了学界文坛前所未有、不加思辨甚至混淆概念嫌疑般的攻击开撕和毁誉诘难。以事实推理而言,很少有人静心反思到学衡派所宣扬的新人文古典主义思想背后,对“传统”如何跃进“现代”之维这一时代性价值预设的先知先觉另一种对话意味、触遇理解与本真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周来祥较早就开始注重“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问题论辩,特别是他的两篇别开生面的论文中言及此种较为奇特的文艺现象[4][5]。周来祥怀有一种宽厚的传统文化情感较早地开启了评述“古典主义”一词丰富的精神内涵,这确可谓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且最值得重视。刘绍瑾在很早的时候就针对“中国艺术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审美特征”和“儒家的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之学理做出了敞明的论证[6](P69-106)。以上这两位学者深刻的言论鲜见背后,启明性地提示出了藏蕴丰实而思涵深远的中国古典文学更应以“古典主义”而非“现实主义”进行解读的这一学理说法。毕竟,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似乎颇难用“现实主义”来加以暧昧性甚至笼统性概括的。恰恰相反,从百年文艺兴替思潮问题中可读出,无论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抑或是一种审美理想,古典主义对中国历代文艺叙事格调、书写实践、民族意识、审美趣味、美学渊源、文学想象、现代构筑、意义视域等,着实交织着甚深的审美流风影射。鉴于此,任何套用、高扬或标榜“现实主义”一词来解读“古典主义”,诚然都是越位、粗暴、牵强、乏力、格格不入甚至是面目模糊的。在此不可不置辩。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是另一问题——主流意识嬗变造成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因缘。
综而观之,“古典主义”这一命题在中国文学批评现象和文艺思想语境中未曾彰显,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百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演进、流变、衍生与重释中,学界文坛不少学者从“现实主义”出发做出的跟风式的解读,很可能是占据了中国人文精神生发的主流。关于这一点,大约可以从胡适、郑振铎、游国恩等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系统性诠说中所呈示的一个严重问题更多地影射、印证甚至确认以“现实主义”解读、概观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这一文学现象症候的弊病所在。这是需要重新反思、明鉴、批评与纠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条以“现实主义”这一至上地位的标准,往往以是否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劳苦大众生活)、表达人民或大众的感情、是否批判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为几大特征。然而,相较于“古典主义”这一审美理想来说,“现实主义”毕竟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诠释的唯一标准,更不是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贴切的期待及理想。此后,章培恒、骆玉明、袁行霈等的文学史书写就并非完全是以“现实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是开始质疑“现实主义”而转向深度“古典”之美的特殊标准。继之,周来祥、刘绍瑾、杨春时、俞兆平等的文艺思想表达,则完全抛弃、剔除“现实主义”的标签帽子,而是全面地接受、认同并肯定以“古典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这一文化眼光的价值取向。他们以尤为新锐思维与独到视野颇为稀见性地俨然暗示了以“现实主义”解读、概括及重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本身局限、模糊、弊病、危害、疏离、脱节与越位。换言之,就“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相对应的古典性意涵的问题,他们几个人曾不约而同地把“古典主义”的概念内涵作为一个文艺批评的切入点做出过相应的空间表述与内涵透视①。实际上,以“古典主义”作为审美理想与批评尺度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有着别样的认知视角立场甚至重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毕竟,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漫长的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某种内在生命元素之价值意蕴、经典定位及张力因子,需要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有效的激活与全新的阐发。藉此视之,那么,以“古典主义”这一命题重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意义就将得到充分显现。其实,溯其根源,古典主义在中国百年来的消长沉浮与蒙尘遮蔽,与20世纪早中期多元文艺思潮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的涌现、植入、热捧、传播等密切相关。其中,“古典主义”作为一股文艺思潮得以在中国20世纪植入与传播的土壤根基,恰恰是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那种推崇和谐、节制、均衡、中庸、和合、情味的审美理想之精神内核是颇为暗地吻合、对接而相契的。相较于“现实主义”,以“古典主义”来重释、概观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概念内涵无疑更接地气。凭此而观之,就中西文化审美理想的可通约性与可融通性而言,“古典主义”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西方的某种审美理想,而是有了落脚于中国漫长的古典文学实践及其理论思想的结晶。这恰恰是明示了“古典主义”这股文艺思潮得以于20世纪植入中国的内缘。可以说,“古典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抑或是一种审美理想,都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对其作出具体的个案分析与现代性重释。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对此问题视点图景的深度关注及辨惑还是有所欠缺的。
二、主流意识嬗变:造成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因缘
不可否认,任何历史时代主流文化之更迭推延,始终更为深刻地烙印着“革新”与“守成”、“分离”与“回归”、“借鉴”与“批评”、“继承”与“反叛”、“现代”与“传统”的时代启蒙、意识洗礼和视野诉求等独特内联性。这也应合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7]从历史事实语境的文化传承与对话的各要素来看,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就是过分照搬、套用“外来”文化观念,其病症在于忽略或屏蔽“本土”历史渊源文化涵蕴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建构史上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颇为丰厚的古典传统文学也许更应是一种透明得多的“古典主义”而并非“现实主义”进行超然而理性的对照性解读。人们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将“古典主义在中国”这一个极富时代话语的学术问题纳入当下的研究领域。毕竟,从现代性视野审视古典主义在20世纪中国消长沉浮的历史命运之关注远远不够。对此,杨春时有所思地指出:“20世纪前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属于古典主义传统。……中国文学自汉、唐以来,就形成了古典主义传统(其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它在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支援下,延续两千余年,影响至今未绝。”[8]这段文字轻轻地提到并点出了以“现实主义”一词来从根本上戛然地取代甚至置换“古典主义”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明显过于疏离、晦涩、谐谑而有悖于其原义。若要更进一步推论说,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学衡派、新月社等因对“传统之秉承与持守”而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也一度遭受冷遇,连“古典主义”一词都成为当时文人作家们急于回避忌讳的字眼,而当时的学者自然而然地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一时隆起、脉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元性主流思潮话语。这亦更进一步助推、催生甚至滋长了文坛学界对主流思潮之隐含性的吹捧、宣扬、独张、抬高并获得了随处可见的运思与凸显效应。与此恰恰相对的是,“古典主义”一词则被贬损地认为是对“现代”的失败反抗而受尽子虚乌有的敌意诟病与褒贬不一的批驳关注,以致导引并造成的对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古典主义在20世纪中国”话语在学界遭遇低视与失语的缘起,这是需要引起注目的事实。
回顾中国百年文艺思潮,“传统”与“现代”的接引、“古今”与“中外”的鉴照、“大众”与“精英”的折中、“人”与“自然世界”的谐调等成为现当代整个社会文化构筑古典“和谐美”的思想内核。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生成,源自20世纪中国文坛呈显出来的“外来”与“本土”同化而旁生的某种套用、迎合的话语变异及心理抗衡。朱光潜曾发表这样的意见:“互相影响原是文化交流所必有的现象,中国文学接受西方的影响势所必然,理所固然的。便是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生不息,前浪推后浪,前因产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一代,却仍是前一代的子孙。”[9](P79)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精神旨向建构,对古典传统文化曾一度出现厌离、嘲谑、摧残、贬抑与抛弃之现象端倪,诚然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近年来,人们渐已意识到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重新审视了古典传统和民族情感的学术问题。这显然更能丰富并加深人们对中国古典传统意蕴文化内涵的深入解读与思维找寻。余光中发人深思地表述过:“传统并不仅指中国的古典。浪子们不但要反中国的古典传统,还要反西洋浪漫主义以前的传统。浪子们的错误,在于不明白文学的潮流是发展而成,不是可以强行分割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文学之流亦复如此。现代诗似乎使诗人们患了一种‘主义狂’(Ismania),一时作者们似乎不使自己属于某种主义便不快乐。人们轮流模仿达达、超现实、存在等派别,好像换几种不同牌子的洋烟一样方便。事实上,千变万化,恐怕仍然跳不出古典与浪漫两种基本的气质。”[10]从文学思潮史此起彼伏的文化传播及意义庞杂的文化热点看,作为现代性视野中一种文艺思潮的“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坛上切实呈显出彼此价值标尺的影响作用及各自审美风尚的历史局限性。然而,人们亦不应忽视另一方面:学界的喜“新”厌“旧”及“现代”急需从“传统”中华丽的转身与换装所造成的隐然伏沉,即是时疏时密地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后果——“外来”的极力彰显、宣扬与“本土”的尖刻障蔽、扔弃。
从国内总体的文化环境和知识资源来看,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中国现代文坛上生发出这样一种颇为畸形而又极为诡谲的文学现象——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进行症候解读。正是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写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主流新思潮脉流框架所标举、独尊与崇奉,恰恰在客观上致使、引发了精纯、圆熟的“古典主义”一度被人们扭曲性、片面性甚至偏执性地理解为 “腐儒”、“落后”、“保守”、“封建”及“传统”,而遭受到显而易见的致命排挤、遮蔽、分割、贬损、扼杀及挤压,从而滑向尘蔽蒙尘的时代命运际遇深渊之嬗变及转向,甚为悲哀可惜。对此,俞兆平曾这样说起:“但在中国思想界的实际现象表现中,对‘自由意志’的奉从、对民族文化的谨慎守成等这些特质,并不只是新儒学派,如张君劢、梁漱溟等所独具的;像在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中取折中调和的梁启超;像竭力推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像出国留学后却想‘勒马回缰作旧诗’的闻一多,以及梁实秋、朱光潜等现代文学作家、诗人等,均有此倾向。因此,只能从异中取从,把他们纳入‘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概念趋向中。”[11]这些大有意味的文字言论,显然夹着文化政治话语枷锁和时代语境屏障的深层机理批评。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扣上“现实主义”这顶帽子进行解读,其间的干枯、幼稚、无知、拘板、浅显、矫揉与造作之“误”也就渐趋一一浮上水面,不经意间让人贻笑大方甚且嘲讽其“奴”般的酸腐。诚然,这仍有待时间为其辩白、梳证与澄清。总而言之,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扬言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现象毛病与图景流弊。这种奋然而起的标举式论说、解读或推理显然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且对号入座的嫌疑。范曾具有代表性地暗示:“为什么20世纪会出现这么多以反传统为标志的艺术流派,这么集中,这么极端,而且前仆后继,愈演愈烈?我想,这绝对和20世纪政治、经济、社会的心态,有直接关系。”[12]于此,不难看出造成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因缘,恰恰正是审美意识嬗变、时代风尚的交接、文化批评角度、时代精神力量、审美心理郁结及主流文化霸权使然的结果及写照。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著述颇多,如“实用主义在中国”、“现代主义在中国”、“浪漫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女性主义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进化主义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等,其中不少在国内较具影响力的学者之著述惟独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遗忘了对古典主义这股文艺思潮的关注声音、影迹及踪径,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史的价值与意义。不过,事实就是如此,不用复述。
三、视界融合:以“古典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切近
倘若回眸中国蕴涵丰富、根基渊博、文气贯通而存思绵延的千年流变之古典文化传统之内在本色,不难看出以“古典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切近。接下来,不妨探讨一下用“古典主义”进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适用性与操作性。若追根溯源或刨根问底,西欧的“古典”往往指涉的是对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复归及回响。作为文学流派的古典主义追求一种生命存在主义之平衡、传统、理性、摹仿、生态、规范、适宜、整一等美学精神主导原则。从整体上看,“古典”作为历史性的概念与思潮样态理想的流变衍迁,似乎是一个流淌于古今中外文艺史上具有普遍审美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审美范式,一直未曾淡出文艺创作与批评标准的审美视野。“古典主义”一词中的“古典”就是要以古希腊罗马经典的审美范式为美的榜样和规律,研习“古典”即学习古希腊罗马历史时期的拉丁文文艺作品的“经典”,并要求符合固有的规则范式进行创作。西方推崇和谐、均衡、节制、比例、秩序、静穆、单纯之古典美;而中国以儒道为内核的文化精神更是推崇和为贵、天人合一、自然、中庸、克制等所包涵的贯注生气和极致美感之审美理想。鉴于此,古典文艺实践要求创作表现出一种 “古典主义”式的内在冷静、优雅含蓄、品性良善、高贵克制、纯净永恒与单纯静穆的美的规律。换言之,古典主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地倾重于倡导常态、健康、自由的美学原则创作论,同时也一脉相承地隐然彰显出一种和谐、理性、均衡和穆美的艺术创作新义。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审美理想及精神实质上有着很大的可通约性、融通性及吻合性。显然,从概念内涵的传承、流衍与发展的视域看,古典主义作为一种中西文化共通性的“和谐美”审美理想,自始至终都一以贯之地影响着各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中国千百年以来的古典传统文学浸染、熏陶、感化的内在文化意蕴之精神学理。其实,“古典”传统于现当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在中国现当代语境中,如何坚守、弘扬古典传统的审美向度,并挖掘、透视其新时期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历史意蕴内涵及其启示,显然需要做出合乎事实的导出、定位与反思。
不可疑议的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更接近、更相通甚至更吻合于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之概念意蕴、精神内核、艺术色彩、心理基础、模式原型和主调立场,这一点几成文坛学界的共识。以“现实主义”解读具有不凡历史血脉沿续、诗性智慧生成和内在品性悠远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学,是牵强附会和不合情理的,亦是脱节错位的。细而思之,20世纪中国学界文坛上铺天盖地的频频出现标榜 “现实主义”一词而甚少有人触涉到“古典主义”一词的文艺现象,其在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相关的著论中是有所反映的②。实质上,这些论著措辞口吻言之凿凿地以“现实主义”置换、否定甚至屏蔽“古典主义”解读涵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现象论调,是极为浅薄、背离与偏倚的。朱光潜见解独到地重申:“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先研究它的起源;犹如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9](P7)综观中国百年文艺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中国文艺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且影响很大的转折点。然而,随后由于文艺界过于强调“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等卓然高标的文化政治批判维度的机械宣扬,并把其作为衡量文艺创作与发展的话语标准。如白石言辞明确地强调:“古典文学的人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深入探讨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内容,对于开展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继承与发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3]两相对比,对“古典主义”的针砭讽刺与遮蔽掩盖相对应的则是对“现实主义”的无上称誉与一片唱和,甚至日益助长了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这种相当畸形、拘限的转向轨迹事实现象,实质上亦正与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的时局潮流相清晰唱和及时代主流话语措辞的鲜明看齐。然而这一学术镜像实相、空间话语秘蕴及文艺越界症候,尚且未能为当前学者所重而献疑。
表面上看,“古典主义”本身亦沉潜甚至映射着一种近似揭露现实社会复杂矛盾一面的 “现实主义”内在的书写表达倾向。然却,细而思之,若以此就笼统地以“现实主义”单纯地以一锤定音的方式解读“古典主义”之特质,无疑缺少了对“古典主义”深层了悟的思想锐气,实在难以接受,而应给予否定与修正。不过,把此一文艺症候归化于20世纪中国文艺迈向现代转型、更新、再生、复兴等百年命运的诸多层面上,做出以史实为证的内在关联的视点重释,溯源此一文艺症候生成的历史因素并阐明其衍化变迁的脉络,似乎很有必要。刘再复这样凸显:“当社会进入这样的转变时期,古典传统的完整形态就会发生蜕变。”[14]此外,也有学者做出以下概述:“30年代以后,随着日趋严峻的救亡时局和政治斗争的挤压,它(古典主义)的生存空间也日益萎缩。50年代之后,这种空间完全被取消,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或受其影响的文学群体,不是被斥为‘复古派’、‘反动文人’,就是被视为‘逆流’。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抬头,随着文化热、‘后现代’热及由此展开的对五四以来‘反传统’倾向的反思,新古典主义才逐渐浮出海面,它所主张的那种传统文化本位观和‘融化中西’的理想在近十多年的文学论争中也渐有了市场。”[15]问题的症结在于,正是在这种独特政治条件要素的历史语境下,“现实主义”自然而然地如虎添翼般被学界文坛最为频繁地援引征用而始终操持着相当高的出镜频率,而被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则如打了死结般日趋招致非议而显得曲高和寡,于此则可见一斑。有学者一度暗示了这种意味及感受:“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其他思潮相比,古典主义文学的传统底蕴和本土意识更浓重一些。”[16]此外,朱自清也曾总结:“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这并非空话。”[17]不能忽视,古典主义之审美理想不仅暗合、应和了20世纪现代中国新文学思想理论建构过程中对人文精神特质层面的实相要求,而且也切实地契合、会通并应合了中国千百年以来历史深邃的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理论建构视域、生命情怀寄存、精神话语想象和文艺书写思维。
综上所述,较之以“现实主义”,纵然还是应该以 “古典主义”来解读和映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尤其是以古雅生香的情、味、意、境为内核基因之诗性智慧的思想和多元而独特的人文精神意蕴)更为趋近、空灵、亲切、丰赡和切近,也显得更为不隔、无碍、宽博和厚实,同时也愈加深得文理而令人信服。对此,刘绍瑾却能独见:“‘温柔敦厚’的艺术审美理想,与西方古典主义的特点在精神上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6](P112)此一见解述要的回响,显然独具慧眼地照见了20世纪中国杂乱纷纭的文坛这样一种原貌:较之以牵强附会的“现实主义”,以“古典主义”来解读有着深层相通性、相似性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必然更为迹近、活脱、审慎与贴切。然却,20世纪中国学界文坛上曾一度浮现大量以“现实主义”置换甚至取代“古典主义”解读中国古典传统文学的论著言说③。无独有偶,中国近现代文坛甚至还频频裸现出以 “古典现实主义”一词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系列论文④。以上学者论著之话语措辞恐怕受到20世纪社会主流文风的助力趋附、仿效熏染、一味迎合、特意遵循等等历史语境之缘域场合,显然更值得审视、质询与盘点。若对这些甚不清畅的著论言说、话语界定展开细读慢味,于学理反思深处总有一种相去甚远的“隔”与“碍”。对此,余光中有一段文字说得好:“在精神上,我们是古典的。在一切的纷扰之后,古典的坚定和静观是何等的可靠!这种古典,不是力的取消,而是力的内敛,不是生命的松弛,而是生命的凝聚。”[18]亦有学者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散文的古典主义传统特别强大。”[19]关于“古典主义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批评的切入点、贴切性和可行性”及“古典主义的批评维度在中国被遮蔽的因缘探讨”两大问题的阐释,可参见本人近些年发表的“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为主题的相关论文⑤,在此不再重复展开细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间最终可以见证优胜劣汰。很多因历史时代政治造成的问题,等到多年后的某天回首与前瞻时,孰优孰劣、孰契孰疏或孰是孰非,往往就灼然可见的了。需要坦诚的是,上述所论只是大致地勾勒出以“现实主义”解读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此一文艺症候之不全不粹且不近情理的局限,藉此力图唤醒与辨证此一文艺症候现象尚且需要做出更为深层的多维性凸显这一学理问题。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旁及到诸多相关性纠偏补弊问题的流脉表述、深究与新诠,还有待日后再续。
注:
①周来祥、杨春时、俞兆平、刘绍瑾等人较早发表的论著谈及到“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参考。如周来祥《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从意境谈起》(1980)、周来祥,陈炎《古典主义艺术的美学原则》(1992)、周来祥 《论古典主义的类型性典型》(1981)、周来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彻底解决了文学和现实的矛盾》(1959)、杨春时《老舍创作的多向性——现实主义、启蒙主义与革命古典主义》(2010)、杨春时《样板戏——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2008)、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2007)、杨春时,刘连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误读与误判》(2007)、杨春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2003)、杨春时 《走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1995)、俞兆平《古典主义思潮的排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欠缺》(2010)、俞兆平《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2006)、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2004)、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八章节谈及 “中国艺术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审美特征”(1989)。
②如呂美生《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959)、奚姗姗,吕美生《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1960)、朱光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1963)、朱明雄《略论鲁迅开拓的现实主义传统》(1979)、秦裕权《要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1979)等。
③如殷孟伦 《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1955)、郭晋稀《试从诗、骚的创作方法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1957)、澥浛《读“元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后的几点不同意见》(1958)、罗根泽《曹雪芹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社会背景》(1958)、郭豫适《关于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1962)、陆侃如,牟世金《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1962)、袁世硕《〈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1963)、刘建军《为什么必须重视现实主义传统》(1978)、吴文治 《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1979)、陈伯海《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初探》(1980)、刁云展 《关于两种 〈后水浒〉的现实主义》(1981)、周中明《论〈金瓶梅〉的近代现实主义特色》(1989)、朱恩彬 《儒家思想与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1996)等等。
④纪川 《试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本体论的形成与发展》(1980)、高文超 《〈文心雕龙〉古典现实主义比较论》(1985)、王向峰《中国古典文艺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1981)、毕万忱《论杜诗对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1990、郁沅《中西古典现实主义之比较》(1996)、韩经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古典现实主义》(2011)等。
⑤ 如《古典主义在中国消长沉浮的现代命运》(2011)、《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2011)、《古典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综述》(2011)、《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 “古典主义”阐释》(2011)、《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与反思》(2011)、《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失语与重估》(2011)、《“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历史境遇》(2012)、《古典主义在中国之现代命运及当下解读——兼谈吴宓、梁实秋对白璧德的时代接受》(2012)、《历史际遇与审美暗示:再评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012年第7期)、《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2012)、《古典主义在中国的植入与辐射——对20世纪文学思潮论的一种考察》(2013)等。
[1]李钧.中和与重构,归心与返魅——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纲[J].文艺争鸣,2010,(7):75-79.
[2]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卷3)[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266.
[3]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2.
[4]周来祥.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从意境谈起[J].文学遗产,1980,(3):111-116.
[5]周来祥.古典和谐美的理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模式[J].江汉论坛,1983,(10):44-49.
[6]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中国复古文学理论的美学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意大利)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
[8]杨春时.走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2):1-4+46.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0]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62.
[11]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3.
[12]范曾.范曾谈美[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63.
[13]白石.关于古典文学的人民性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57,(3):63-70.
[14]刘再复,林岗.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J].福建论坛,1988,(5):6-12.
[15]张林杰.守旧与开新——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摭谈[J].社会科学辑刊,1999,(6):147-150.
[16]白春超.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3.
[17]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M].凌云岚考释.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4.
[18]余光中.余光中集(第四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26.
[19]马茂军.论中国古典主义散文的强势传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26-31+3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