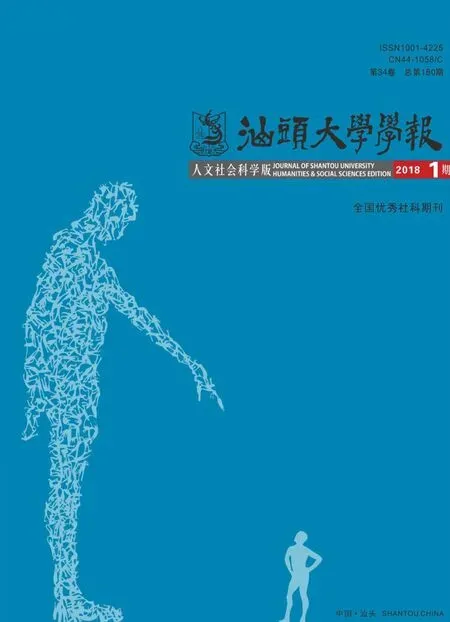试论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价值
2018-02-01倪晶晶
倪晶晶
(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近年来,国内“医闹”事件屡禁不止,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医患矛盾愈演愈烈,即使社会一直呼吁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但不和谐现象依旧大行其道。2016年1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王玲玲教授介绍,2016年全国暴力伤医案呈上升趋势,全国发生典型暴力伤医案例42起,共导致60余名医务人员受伤或死亡。因而,建立新型和谐的医患关系刻不容缓。本文立足于传统医疗父爱主义,分析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呼吁给予医生适度干预权①医生适度干预权是指:医生在特定情况下,限制病人的自主权利,实现自己意志以达到对病人应尽责任的目地。,实现传统医疗父爱关怀的现代回归。
一、传统医疗父爱主义和近代医疗自由主义
(一)传统医疗父爱主义
“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来自拉丁语pater,意指“家长式的管理原则和做法。像一位父亲一样来统治政府;像一位父亲对待其子女一样为一个民族或共同体提供需要或支配生命的要求或尝试。”[1]简言之,就是为了他人益处而干预他人的行为。父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广泛,如法律父爱主义、教育父爱主义。而医疗父爱主义,是指运用在医疗这个特殊领域中的父爱主义,通常表现为——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医生凭借专业知识,为患者的最大利益作出最优选择,甚至在患者及其家属无法作出正确判断时,帮助患者做出选择,并强行要求患者接受。
传统医疗父爱主义在中国流传千年,成为传统医学的主导思想。究其原因,与它两个明显的特征有关。首先,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仁者爱人”。“仁”的粗浅解释是指一种感通、关切、融合的精神状态。“仁者,爱人”,因此对个体之外发生的痛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受到了创伤,十分关切他人伤痛,甚至与他人情感相互融合,这便是“仁”。“医乃仁术”,因此医生施行仁术时,要保持一种“医者父母心”的人文关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爱患者,将患者之痛当成自身之痛,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天职,树立“人命之重贵于千金”的基本理念。同时,医学仁术还表现在医生治病的态度上,要求医生以温和、同情、关爱的态度抚慰患者身心伤痛,对患者充满关爱和耐心,并且不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对患者做到诚信不欺,按病下药。这种博爱济众的仁爱思想,是传统医学的普遍思想,良医无不如此。
此外,传统医疗父爱主义还有一个明显特征——父权至上。在传统的医疗实践中,医生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医生以仁爱之心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患者,这也就意味着医生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例如,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患者及家属经受身体伤痛、心理紧张和医疗专业知识欠缺方面的桎梏,无法作出清醒判断。此时,医生就会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根据自身经验及专业知识,为患者健康作出最优选择,强行进行救治,即使这些选择有违患者意愿。
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上述两个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仁爱主义及家国一体的伦理本位模式。以仁爱和父权为核心的医疗父爱主义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主导原则。但也因其极度推崇父权至上,即以医生单方决定为主,不顾患者意愿,使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因而,随着近代患者人权运动,强调医患平等、医疗自由等理念的发展,传统医疗父爱主义逐渐式微,并最终被以尊重患者知情同意为核心的医疗自由主义所取代。[2]
(二)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医疗自由主义
医疗自由主义以“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作为核心,字面意思就是基于说明的同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医疗行业迅速发展,医疗行业中出现了诸多不端现象,如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过分追求利益收受红包、医生态度冷漠等,使整个医疗行业陷入信任危机。因此,人们开始呼吁病人人权,要求“视患者为人”的权利运动蓬勃发展。此时,患者不再像过去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医生,而是试图实现与医生的平等。特别在手术前,要求医生告知实际病情及治疗手段,从而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手术,患者知情同意的观念悄然兴起。而作为法律概念上的“知情同意”权,是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1946)中出现的,为了严厉谴责纳粹医生在集中营强迫受害者进行人体试验的行为,作为对纳粹分子轻视、践踏人权的反思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认可。我国出于对患者的保护,顺理成章地引入知情同意权,并使其成为我国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显性原则。
(三)医疗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遭遇的挑战
出于对患者生命尊重的知情同意权被引入我国,本该是历史的进步,但却在医疗实践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和质疑。可以说,以尊重患者知情同意为核心的医疗原则,并未能为我国医疗领域频发的道德问题提供有效指导。不论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孕妇李丽云事件,还是引发公众热议的周发芝事件,都与过分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密切相关。纵观近年频发的医闹事件,其实就是片面强调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折射。
片面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诸多瓶颈和质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医疗行业本身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医生群体在对病理成因、病情程度、治疗手段的选择等方面,具有先天不容置疑的专业优势。由于患者受专业知识的桎梏,即使医生告知相关病理和治疗方案,也可能存在患者及家属不能完全接受的情况。此时,医学专业知识的不对称,就成了患者知情同意权利的天然屏障。其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医生为避免医疗非技术因素可能对病人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影响病人康复,会采取父爱式医疗手段以保护病人利益,如善意欺骗、使用模糊用语等方式。这种出于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善意保密做法,也在叩问着片面强调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合理性。再次,我国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本身并不健全,如知情同意制度不充分、法律条文太笼统不具操作性、法律规范相互抵触、知情同意权适用例外规定不完善等[3]。2010年出台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规定:“对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字;患者因病无法签字时,应当由其授权的人员签字;为抢救患者,在法定代理人或被授权人无法及时签字的情况下,可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签字。”该规定旨在保护患者的生命权利,解决医生在紧急状态下进行手术治疗的后顾之忧,但充其量只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出现,因此法律效力极为有限;最后,将患者的知情同意拔高到至高地位,严重限制了医生进行正常的医疗救治活动。例如,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医生不约而同地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理解为手术签字制度,直接表现为“不签字,不手术”现象,因而可能严重耽误最佳救治时机。若患者或其家属不签字,医生出于对救治风险的担忧和恐惧,很可能酿成从见死难救到见死不救的悲剧,此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就异化成了医生免责的护身符。
因此,将医疗决策权力完全交给患者,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模式的选择问题,它涉及医学伦理的基本价值标准:是选择以医生仁爱为核心的父爱主义,还是倡导患者自主权利的自由主义,抑或调和患者知情同意权和医生干预权各自裨益后的综合。从古今医患关系的明显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医患关系总体而言是和谐的,而现代医患关系总体而言是对立的。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父爱之心悬壶济世,本着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主导医疗活动,施行“仁术”;而对患者而言,医生像父亲一样,是值得信任和托付生命的。因此,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模式在今天仍具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挖掘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为化解当前医疗行业的实践困境提供有效指导。
二、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
传统的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以仁爱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传统医学父爱主义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利他的爱。因此,其当代价值必须保留这一维度,当代医生也需以人为本,尊重患者,以有利患者的原则主导医疗活动。另一方面,在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中,医生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拥有完全自主权。因此,其当代价值的另一维度,就是要给予医生适当医疗干预权。并且,医生适当干预权需以父爱主义为德性前提,医生需本着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实施“仁术”。
(一)以人为本,尊重患者
中国传统医学父爱主义以仁爱为基。仁爱的目的是为了病人利益,方式上要求一视同仁,而态度则要求温和亲切。
以人为本,体现在医生的利他医德中。表现为医生会把“患者福祉优先”当成行医的基本信条,将治病救人看做自己应尽的义务和美德,将患者健康的最大化视作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中国古代良医提出的“易地以观”的观点,其实就是利他医德的表现,因为关心患者,所以站在患者的角度看问题。如清代名医徐延柞在《医粹精言》中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故医虽小道,而所系甚重,略一举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惧乎哉”。[4]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敬畏,让医生站在病人角度关怀病人,使得病人完全相信医生,甚至毫无保留地将生命托付给医生。
与利他医德相对立的,是充斥在今天医患关系中的利己主义,表现在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医生对患者而言是功利的,因此,患者试图通过送红包的方式贿赂医生,以求医生尽力,即使有德性的医生表示会竭尽全力,如不收红包,患者依旧难以心安。而患者对医生而言,仅是医疗对象,是自己职业收入的来源。但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相关。市场经济滋生出的拜金主义,对医疗行业逐步侵蚀,造成部分医生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使本该施行“仁术”的职业沦为商业的附庸。在以药养医的体制缺陷的掩护下,部分医生昧着良心,以收取患者额外钱财为目的,使患者处境雪上加霜,加剧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局面。此时,父爱主义的利他医德被精致的利己主义完全取代;一视同仁的为医之道被乱收患者红包的现象蚕食不见;温和亲切的人文关怀被急功近利的服务态度冲刷殆尽。久而久之,造成医生失去本该有的“医者父母心”的关怀。传统的医疗父爱主义为当代医疗工作者提供了一种价值视角,教育医者敬畏生命、救死扶伤,本着利他原则关爱患者,而不是一味金钱至上、利益至上,忘记从医初心、离弃医道良心。
以人为本的利他医德,还应该表现在医疗服务态度上。近代以来,医疗技术迅速发展,部分医学工作者将医疗活动看成单纯的技术活动,把对患者的医疗服务简单还原为药物、手术或者各种技术手段的实施,从而淡化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在医生看来,患者只是试管里、显微镜下的血液、尿液、细胞和各种形态的标本,而活生生的完整人的形象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样疾病便从患者身上分离出来,作为医生研究的对象,医术也从医生身上分离出来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5]。因此,本该是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医术与疾病关系,本该是服务便民的医疗行业,退变为需看脸色的行业。但是,正如马克思认为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任何片面地把病人物化、异化的行为都严重背离仁爱思想。
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以仁爱为核心,仁爱的前提就是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人的价值的全面尊重。病人是具有生理、心理和社会属性的有机整体,尊重病人就是尊重病人的全部属性。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生更应重拾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中的仁爱关怀,尊重病人,一视同仁地进行医疗活动。
当然,仅强调以人为本,尊重患者还不够,医疗父爱主义还需给予医生适当干预权。给予医生适当干预权的主张,来源于古今医患关系的对比变化。但是,不论是今天片面强调患者知情同意权,还是古代片面强调医生自主权,都有局限性。片面强调患者权利,医生被动,以致医生无法按照最佳医治手段进行救治;片面强调医生权利,患者被动,易造成医生专断,患者讳疾就医。因此,和谐医患关系的现代重建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一方面,实现传统医疗父爱医德的现代性回归;另一方面,需在父爱医德的基础上,给予医生适当的医疗干预权。
(二)医生适当干预权
2007年11月21日,因丈夫肖志军拒绝手术签字,坚持要求医生给妻子治感冒,而不是生孩子,导致医生束手无策,眼看李丽云及其腹中胎儿死亡。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有人站在患者家属立场上,控诉医院不作为。也有人站在医院角度,指责家属愚昧无知。其实事件的关键,在于对手术签字制度和医生适度干预权的理解。
众所周知,彰显现代社会文明特征之一的是契约制,现代医学默认了这种模式,甚至将此覆盖到医疗行业的方方面面。现代医学将尊重患者自主权看成医学的道德原则,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患者权利的体现。因此,现代医疗机构顺理成章地将手术签字制度,看成是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表现。医生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都必须暗含在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契约之中,医生需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否则构成医疗过失。[6]这就做法看似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其实忽略了医生的德性。因为此时医生的治疗活动,与其说是自觉实施“仁术”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活动。作为谋生的职业,医生无需将父爱看作医疗活动的关怀维度,更不需为患者利益最大化,冒着风险违背患者意愿。医生仅需按部就班完成工作,获得相应报酬,长此以往,造成医生渐失人本医德,医疗干预要么成为天方夜谭,要么成为免责的护身符。从这个方面而言,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患者权利,其实某种程度上,为之后医疗道德频发问题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患者权利,难保有部分患者及家属,利用法律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假借医疗事故之名,弄虚作假,以图高额赔偿金,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医生群体被推至道德的风口浪尖,面对严重的医疗风险,直接导致医生的职业品行每况愈下。因此,给予医生适当干预权十分有必要。
其实,我国早已关注到医生特殊干预权的问题,但所谓的干预权,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如精神病患者、自杀未遂者拒绝治疗、传染病患者的强制隔离等,而日常的医疗道德争议问题,却没得到足够重视。目前,医生特殊干预权还不能像患者知情同意权那样,得到普遍的支持与认可。只有当极具争议性的个案发生时,才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思考。正因如此,使医患关系时至今日也得不到有效缓和,甚至愈演愈烈。
传统医患关系推崇父权至上,医生拥有完全的医疗决策权,因此,医生可无后顾之忧,纯粹为患者最大利益进行救治。但今天和过去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当今对患者权利的尊重乃是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今时今日,整个医疗行业的道德水平,在拜金主义弊病侵蚀下,与传统相比大相径庭,因而难保有些无良医生,会打着医疗干预权的旗号,做出某些越界出格的行为。所以,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
三、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
造成当前医疗纠纷、互不信任等现象是多方原因的综合,不仅有观念思想原因,也有法律、机制原因。因此,缓解医患矛盾、建立新型和谐的医患关系,实现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性回归,需进行多方面的对接转型。并且在转型中,建立医患互信的沟通模式,平衡双方权利,使医患关系始终处于和谐稳定状态。
(一)建立医患互信的思维方式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1年对全国326所医院调查显示,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其中90%是非医疗过错引起的纠纷。[7]对于原因解释,医生群体普遍认为是患者为私利无理取闹、对医疗活动认识不足、维权意识增强造成的。但患者却认为医生唯利是图、缺乏责任心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医患之间缺乏基本信任和必要沟通。因此,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亟需转变医患互不信任的思维方式,建立双向互动的沟通机制,这要求医患双方共同努力。
就医生而言,现代医师需在恪守传统医家良训的同时,培养新型职业道德,将传统医道的仁爱精髓融入现代医学职业道德之中,增强从医责任心,实现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传统医德的仁爱精髓包括人本、诚信、有利、公平等原则。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说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①孙思邈:《大医精诚》。由此可见,孙思邈认为医生需敬畏生命,常怀恻隐之心,并树立“济世活人”的职业理想,这与现代社会对医生医德的要求不谋而合。也正因如此,古医才有“临病人问所便”②《黄帝内经》,《灵枢·师传第二十九》。的温和亲善做法。反观当今,虽也强调尊重患者权利,但却与初衷大相径庭,医患之间似乎成为彼此道德的异乡人,罕见相互关心体谅。时至今日,“临病人问所便”的做法,仅是医生问诊的工作程序,甚至演变为“只见病不见人”的就诊方式,更别说无形中沦为冗长复杂,或枯燥无物的手术签字同意书。多数医生似乎没有正确领会签字前提是详细了解患者文化背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后,帮助患者权衡利弊,在其充分了解同意书的基础上互动交流,为患者生命健康施行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罗列一个有关风险、利益的清单,摊在患者及家属面前,任其决定。“临病人问所便”的做法其实就是医学人本、尊重、有利患者医德的集中体现。古代良医从职业良心出发,对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故此,“医者精诚,志存救济”,患者深信,以命相托。由此可见,古医恪守的医学仁术,和现代社会要求培养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职业要求一脉相承。
当然,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还需权衡传统人道医德和医生合法收益之间的关系,培养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传统医德的仁爱精髓,在当今医疗市场化大背景下相得益彰,真正实现医疗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的统一。正如清代名医徐大椿所云,为谋生计而学医实不可取,但却认同医者通过医术水平而获“利”的做法。“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③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之“医家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95页。这种把提高医疗水平作为获取名利的方法,无疑对现代医学价值观具有深刻意义。
就患者而言,转变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思维模式也需患者参与其中。患者需打破传统医患之间相互沉默的历史,改变不信任的就医心理,在医生询问病情时,主动提供病史资料,坦言相关病症,积极配合治疗,并在尽量了解疾病发展规律、治疗手段和程序之后,与医生积极互动沟通,尽量避免不合作或冲突状况。只有这样,医患之间才能增加彼此互谅,为互信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正确起点,使医患关系重回正途。此外,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还需对接相关法律,保障父爱干预权,真正为实现医疗父爱主义回归保驾护航。
(二)引权入法,对接法律与父爱
众所周知,道德和法律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两个重要维度,医德医风属于道德范畴,而权利义务则属于法律制度范畴。传统社会中,礼扮演法的角色,医生克己复礼,严于律己;患者以礼相待,恭谦礼让。因而总体而言,医患和睦、休戚与共。然而,在个人权利凸显的今天,传统的礼乐教化作用已日渐消退,因此,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亟需实现医生父爱关怀和相关成文法制的对接。法律既要给医生适当干预权提供保障,也需隐含对医生医德的要求。
因孕妇李丽云案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56条,可以说是传统医疗父爱主义实现法律对接的体现。《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较之前,此规定更加明确了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况下的医疗权。立法者试图通过《侵权责任法》的规范化,实现医疗救治法律与医疗父爱道德的现代“对接”。我们可这样理解此项规定:当遇紧急情况,医生无法获得患者或其家属的意见时,具有推定其同意进行手术救治的权利,甚至可根据危险程度,不顾患者及其家属意见,强行进行救治。即使不能得到患者及家属意见,适当的救治方案仍可执行,这似乎隐含着患者或其家属可能不同意,医疗机构仍可“忽略”“不顾”而进行救治。由此看见,该规定其实赋予了医疗机构父爱式治疗救助权[8]。此项规定综合考虑了当前的医患关系,试图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干预权的平衡统一,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同时,发挥医疗机构的主动性,为实施利他性的父爱救治提供法律保障,虽有不顾患方意愿之嫌,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患者生命健康。
此外,对于恶性医闹事件,立法者也试图通过修正原有法规,为保障医生适当干预权,实现医疗父爱主义关怀的回归保驾护航。例如,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第31条,将“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包括“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此项修订意味着“医闹”现象今后将载入刑法。同时,该刑种的处罚级别也被提高,从原本的“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提高为“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也就意味着,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保障大大提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方努力,医患关系的改善已取得明显效果。2017年2月23日,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马岩介绍,2016年,全国医疗纠纷数量较2015年下降6.7%,涉医违法犯罪案件下降14.1%。由此可见,用引权入法的方式来保障医疗父爱干预初见成效。
当然,也需注意到,现存的成文法虽明确赋予医疗机构一定的父爱救治权,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救治程序不甚合理、责任界定模糊等。特别对医疗卫生领域而言,单纯的法律规范不仅无益于医德医风的改善,甚至还暗藏医疗道德滑坡的隐忧,使医患博弈愈演愈烈。可见,医疗父爱主义现代转型关键,还是医德和权利的对接转型。这就要求在当前医德医风建设中,既发挥传统医德的文化培育和道德示范作用,又发挥法律规范的监督保障功能。
综上所述,医疗父爱主义的现代转型,既需良好医德为适当干预权提供道德价码,也需相关成文法律为医家道德保驾护航。在今天复杂的医患关系中,不加选择地将病人的自主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已滋生出一系列棘手的道德问题。面对今天临床医疗实践中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病人至高无上的权利,重新挖掘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为实现传统医学的父爱主义回归提供可行之道。
参考文献:
[1]H·T·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M].范瑞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2.
[2]周奕.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3]陈燕红.困境与出路: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法律保护与适用的完善建议[J].河北法学,2014(2):132-137.
[4]费伯雄.医方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6.
[5]李东临,李志宏.对现代医患关系的初步探讨[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39.
[6]彭红.医患博弈及其沟通调适[D].长沙:中南大学,2008.
[7]梅海岚.全国326所医院调查: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法制日报[N/OL].(2002-02-21).http://english,hanban.edu.cn/Chinese/2002/Feb/110040.htm.
[8]郭春镇,林海.“对接”的“父爱”——评《侵权责任法》第 56 条中的“医疗权”[J].私法,2011(2):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