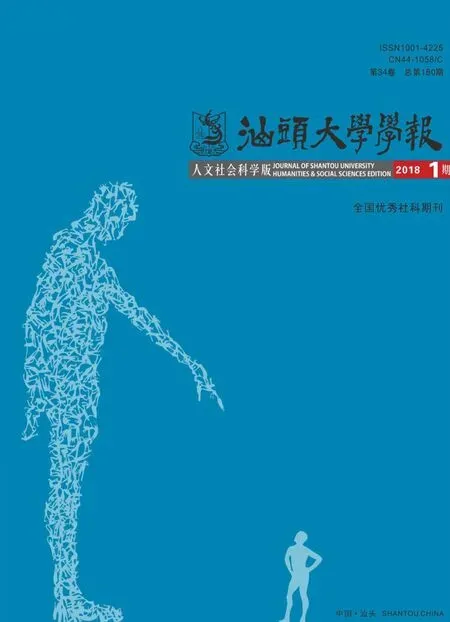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
——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2018-02-01宫陈
宫 陈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史德者,史家之德行品质。中国传统史学素称发达,举世闻名;究其原因,这与自古以来众多讲求史德的史家之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史家修养的一个重要范畴,史德的高下好坏往往会对史书记载的可信程度产生极大影响;反之,一本载之可信的史书背后往往能反映出著史者个人史德的修养。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史家为客观纪史不惜殒命的事例: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1]1099
其后,秉笔直书、实录修史者代不乏人,可以说历代史家都在将德行的修养作为一个崇高使命来追求,同时也丰富了其内涵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认识到:“文非泛论,按实而书”[2]286,所以他提出史家在修史过程中要秉持“素心”:
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287
至于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书中围绕史家修养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论,他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3]185所以他指出,史家在修史时一定要“直书其事”,只有这样才能“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同时他还对德行高尚的史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3]180
其后,元朝史家揭傒斯围绕史家德行修养进一步指出,修史的根本在于心术,若是心术不正,即便是其他方面有着显著才能也不能用以修史。明朝的胡应麟继承前人,补充了“公心”与“直笔”两点要求,要求著史者需出于公心,下笔所书必依据事实、还原其本。明确提出“史德”二字概念的则是清代的章学诚,他在氏著《文史通义》中专辟《史德》与《文德》两章来谈史家在修史过程中的德行品质问题。可以说章氏将中国传统史德观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代以来,虽然史界风气与治史观念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于以史德为主体的史家修养观的探索与研究仍在继续,较早对传统史德观进行近代阐释的是梁启超,1926-1927年间,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专门讨论“史家的四长”,而四长之首,即为史德。紧随其后,刘咸炘在其出版的《治史绪论》一书中也就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观进行了探讨。梁、刘二人的著述发行后在当时的学界亦引发回响,1942年,柳诒徵在重庆为受抗战影响内迁至此的中央大学研究院的“教授进修课程”讲授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时就列出“史德”一节加以讲解,一方面就章学诚的史德观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回应梁启超、刘咸炘等人的观点,后该讲义整理成书,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定名《国史要义》。
以往学界对于“史德”这一概念以及章学诚、柳诒徵等人的史德观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成果①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有:关于“史德”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周文玖《论“史德”》,《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该文论述了史德概念的由来及其在史学活动中的地位,指出了中国史学重视史德的传统和相关局限;刘开军《“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的深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该文系统梳理了“史德”这一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史德”的孕育和诞生是史学批评走向深入的一个缩影。关于章学诚的史德观研究,可参见朱政惠、陈勇《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该文指出章学诚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了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章氏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对当下有着借鉴意义;章益国《章学诚“史德”说新解》,《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该文梳理了以往对“史德”的惯常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史德”是指史家要对自己诚实,要发扬“天性”,不能屈从“他人”,章学诚的“史德”说不是主张“客观主义”,他是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彭忠德《章学诚“史德”说新解》,《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关于柳诒徵的史德观研究,可参见范红霞《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作者指出了柳诒徵的“史德”观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另有一些学位论文等也都有所涉及,如孙文阁《柳诒徵史学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2006年;施昱丞《“本史迹以导政术”:柳诒徵的文化史书写》,台湾大学历史系,2013年。;但大都围绕其中某一史家或某一问题进行讨论,较少将之贯通比较。本文试图对章学诚的史德观进行再梳理,在此基础上展示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民国学者对于章氏史德观的讨论与评价;通过考察传统史德观在近代的不同阐释借以管窥民初以降,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一、“心术”与“敬恕”
章学诚的史德观并非无中生有,一家独创,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章学诚在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前首先简要回顾了前代学者关于史家修养问题的论述,尤其对刘知几所提倡的史家三长论予以肯定,他认为“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4]265但他同时也指出刘知几观点的不足之处,认为“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4]265在章学诚看来把识记背诵当作史学,将著述文采当作史才,视专断为史识并不是良史所应具备的才学识,所以在他眼中,刘知几所提倡的才学识不过是想让人在识记背诵之间知道应如何选择判断借以成文罢了,是故他虽然肯定刘氏,但也指出“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4]265章学诚在这里所言固然有其道理,但他实际上误解了刘知几关于才学识的比喻。刘知几对于才学识的看法是:
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 ,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 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②《新唐书》《旧唐书》所载刘知幾之传亦收录该文。[5]507
可见,刘知几之本意是有史学而无史才,有如坐拥良田财宝却不知如何巧妙生财,最终难免贫乏;有史才而无史学,有如空怀良技,但却无地用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章学诚的比喻则是将史识与史才混淆了。不过,“章学诚从并非完全正确的引证中,却阐说了正确的理论,而他明确地提出以‘史德’来丰富‘史识’的内涵,并进而以‘史德’来补充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毕竟显示了他的卓识。”[6]724
在章学诚看来,“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4]265如何理解这句话,学界有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句话表明章学诚的“史德”已经包含在“史识”之中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如仓修良就不赞成此说,他认为“‘识’是指史家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这是观点问题,识断问题;而‘史德’则是指能否忠于史实的品德,是史家的思想修养问题,还包含立场在内。”①仓修良另撰有《“史德”、“史识”辨》(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139页)一文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可为参考。[4]265仓氏立论有其道理,但未免有些以今度古,拿当下概念去套古人成说之嫌,且过于纠结字词本身的文本含义,忽略了其历史背景;如何理解二者关系,在笔者看来还应以古度古、回到历史。欲探究二者关系,首先要明了二者之概念。何为“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5]265何为“史识”?有人认为刘知几本人并未直接给出解释,实则不然,“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5]507即为刘氏对于“史识”的回答。因为这段话“正好紧扣着郑惟忠提出‘自古以来,文史多而史才少,何也?’的问题,此句应该即是刘知几‘史识’的正面叙述。”[7]106无论是公正客观,还是善善恶恶,其背后都蕴含着史家在著史时秉持公心、躬身德行的道德选择,反映了史家心术之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识”当中的确包含有“史德”的成分,所以完全否定两者密切关系的观点似有偏颇。但如果说“史德”完全就是“史识”,亦不正确。章学诚的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从“识”中抽离出“德”并将之放大,使之由从属地位上升为并列关系,这不仅是对史家的个人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客观上反映了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上的深化。同时也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自省在这一时期发展至高峰。
在修史过程中,史家心术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章学诚将之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心术本就不正,在著史中多有秽谤,这样的史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4]265由于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他们的劣迹,所以不会受其干扰,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对也就较小。第二种是“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4]265这类人心术虽正,但个人修养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他们虽有向善致臻之心,但却很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这是令章氏更为担心的。针对如何提高这类人的史德修养这一问题,章学诚给出的答案是: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4]265
他认为在修史过程中能够小心谨慎地辨别天道与人道,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情感因素在其中,即便最终不能完全达到理想效果,但如果有心按此去做就可以说做到心术端正,史德高尚了。
但是,章学诚在这里更多的是侧重于宏观层面上的思考,他所给定的要求与其说是进行经验传授毋宁看作是描绘了一种理想境地。具体落脚到实践操作层面,修史者该如何进行心术的修养呢?章学诚引入了“气”“情”与“敬恕”的概念。
章学诚认识到史事最终要见诸于史书,而史书又以文字为载体,文字又需文采来修饰,所以他很看重“史”与“文”的关系,他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4]266所以他认为“良史莫不工文。”[4]266好的史书必定也是史笔飞动、文采上乘的佳作,但是他反对过分追究文采以至于以文害史的舍本逐末的行为。他还认为,史家笔下的文章本身并不能打动读史之人,之所以动人之处,在于文章字里行间所饱含的史家之“气”和“情”,所谓“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4]266也就是说,在章学诚眼里,天下间可称得上大美文章的一定是感情真挚、生气勃勃的。但是无论是“气”还是“情”都应平和中正,不可被史家内心与外部世界所扰乱,倘若不能够做到这点,则写出的文字“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4]266而且往往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史家尚不自知,所以在史德心术的修养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怎样去保持“气”“情”的中正平和,使史家自身的心术不致于偏离?章学诚要求修史者在下笔之前务要保持“敬恕”。他说“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4]136意思就是“气”太过张扬放纵必然不合适,要有所收束,而“恕”则要求我们不要过分苛责古人,要设身处地地理解前人往事。对于“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4]136章学诚的这种修史态度在今天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也应当努力做到临文必敬,知人论世,这不仅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史家的自我负责,而这种负责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一个史家的正直心术与崇高品德。章学诚所倡导的“敬恕”态度在后世被接受并发扬,近代以来,很多史家都表达过与章氏类似的观点,其中为大众所熟知的莫过于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同情理解”说:
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8]279
要而言之,章学诚以著史者心术为核心的史德观是中国史家在传统史学理论的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极大进步,较之前人,他明确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并且丰富了其内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意识到了修史过程中的史家主体与史实客体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触及到了历史学的本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章学诚的史德观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虽然其观念思维中存有较为明显的名教痕迹,但其仍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大建树。”[9]213
二、“治史之必本于德”
章学诚去而后百年间,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即是传统的四部之学逐渐向现代学科体系过度;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史学?而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的史德观又与现代学术有着怎样的关系?近代以来率先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是梁启超,紧随其后的是刘咸炘,而集大成者则应属柳诒徵。
众所周知,梁启超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实践者,他对于传统史学的思考和现代史学的设想集中体现在氏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含《补编》)一书中。对于章学诚及其思想,他多有肯定,认为“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10]27而且,梁启超还认为“自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10]27虽然梁氏承认章学诚在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理论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并且认为他的很多思想已经具备现代意味,与西方史家颇有契合之处,但就其史德观而言,倘用现代眼光加以审视,仍“亦说的不圆满”,[10]130所以他需“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10]130与梁启超认为章学诚在史德方面阐之未尽的观点不同,刘咸炘则是对章氏大加褒扬,他于1927年草成《治史绪论》一书,开篇即称:“吾于史学宗章实斋。”[11]229他认为“章先生书,久读乃能贯通”“章先生《史德》一篇,最为精深”[11]232,所以刘咸炘谦逊地称他所讲授的内容“不啻为章先生书作一总疏矣。”[11]232相较于刘氏对章学诚及其史德观饱含感情,推崇备至,柳诒徵的态度则更为客观公允,虽然“从学术风格上看,柳诒徵和刘咸炘实为同道中人。”[12]柳氏溯源而上,将章学诚的史德观置于整个传统史学的大环境下加以审视,指出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同为治史学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刘氏自以所志不遂,郁怏孤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论,主于敬恕,故著《史德》《文德》二篇,畅论其旨。”[13]108他认为刘知几受个人经历影响,在立论著说方面存有偏颇,这点章似好于刘。所以章学诚批评刘知几为文史之儒,只讲技巧方法,不讲心术品德。这一点,“世之诵习章氏之学者,似皆未悟其所指。”[13]108对于梁启超与刘咸炘关于章学诚及其史德观的评价,柳诒徵亦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氏“未尝切究章氏所谓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诸语”[13]108;而梁氏的观点“其陈义甚高,第似未甚虚心体察章氏之意,忠实及鉴空衡平,非养心术使底于粹之谓乎?”[13]109
梁启超将章学诚的史德概念定义为“乃是对于过去好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10]130而且他认为章氏所坚持的史家必须心术端正这一点固然重要,但仅仅就此来涵盖史德还是不够的,在梁启超看来史家修德的首要任务在于忠实。如何才算得上是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10]130为什么要强调忠实?因为梁氏认为我们在修史过程中无论是扬是贬都很容易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借古喻今,在很大程度上把历史研究作为一种手段,使之成为宣传工具,并且存在受材料所限、不加甄别、随意判断的现象。概言之,梁启超认为史家修史多存有夸大、附会、武断等弊病,所以非忠实不可补救之。那么在忠实的基础上还需如何?存疑。梁启超说:“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10]132总的来说,梁启超对章学诚的史德观的补充即是要求“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10]132,也就是说要史家修史乃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要将自我的主观心理摒斥在外。通过对前文章学诚的史德观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梁氏自认于章氏学说有所增补,然而实际上其所说内容章氏皆已谈及,反观柳诒徵对梁氏评价,更觉公允。梁启超阐说章氏史德观时,认为史家修史的客观性应包含两个方面,过程的客观和目的的客观,也即,修史者不仅在著述过程中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据实而书,同时不要预设目标,不应期望通过修史来达到某种目的;也就是说,梁启超赞同的是纯粹的历史记录和研究。他发现:“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10]33即便是历史学亦是如此:
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10]33
在梁氏看来,预设目的式的历史研究只会削足适履,于真实历史多有损害,其结果必然是史无信史、史家无德,只有自觉地将这两方面的客观态度贯穿于修史始终,方能得出有益国民且经得起考验的良史。所以他极力呼吁:
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绝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10]35
梁启超之所以持此观点,盖由于其接受了西方学科观念,视史学为一门现代科学,理应秉持科学态度,以现代视角进行历史研究;然就这段话而言,梁氏虽意在引导修史者朝向信史与良史的方向努力,但他首先即承认了良史对于国民自觉的促进之效,下意识中点出了历史研究之目的与作用,前后比较,不免生自相矛盾之感;推而观之,无论是作为维新变法的先锋还是新史学的巨擘,梁氏个人的历史研究都带有浓重的古为今用的色彩,所以,梁氏虽竭力呼吁治史应纯粹客观,可一旦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往往会陷入自我否定的窠臼。
与梁启超在史德方面强调目的与手段的双重客观不同,柳诒徵认为:“则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13]109意思是说修史者不应先培育德行,再去治史,等到德行完备才进行历史研究,而应当把修史本身看作是培养德行的一种方式,并通过修史使得自己品行完善。柳氏的这一观点是对章学诚史德观的一种修正,章学诚强调“临文必敬”,柳诒徵认为这样做易使人产生误解,使修史者平时不必过分追求德行的修养,只需在治史前注意到这点即可,明显此种做法不能达到正其心术的目的。如何畜德?柳诒徵引用《易》中的话进行回答:“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即,畜德的根本做法仍是从读史治史中得来。为何柳诒徵对历史如此看重?盖“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彝,惟史之功用最大。”[13]109显然,柳诒徵不赞同梁启超“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的观点,作为典型的经世致用史学观的持见者,他认为历史有着很好的教化垂训功能,所以修史必先立德,立德则先讲求心术,这也正是史德的重要性所在。再之,历史的这种教化垂训功能既能够作用于个体也能够作用于社会,“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无存,且无先哲垂训,诏之以特立独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盖环境与个人相互影响”[13]111,既可以作用于外部环境也可以作用于史家自身,所以“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13]110再进一步,这种教化垂训功能的产生并非是先前预设,而是读史者或修史者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然得出的,用柳诒徵的话来说就是“人盖由于好学而且深思,能从历代史事及史籍之高下得失,比勘推究,而有以见前哲之精神,非好为崇拜古人也。”[13]127
近代以来,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除了围绕治史心术和史家主体性与历史客观性的相互关系以及治史与修德等方面提出不同讨论外,对于其史德观的另一内容,“敬恕”亦多有阐发,除了上文已经涉及到的“临文必敬”外,其“知人论世”与“同情理解”等观点亦受到近代学者的认可。梁启超说:“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10]78他也举了魏收修撰《魏书》的例子,认为虽然魏收距所修历史的时间距离较近,但对于他的记载不可轻信,盖由于其人心术不端,修史多秽之故①关于魏收所作《魏书》是否为秽史的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看法,读者可参见李凭、瞿林东等人的论著,该问题不在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之列,此处从略。;这是典型的知人论世。刘咸炘对于章学诚的“敬恕”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11]232他认为做到这点才称得上“能入”。因为前人旧事修史者未曾亲历,其中回环曲折,真相如何,很难尽知,在这种情况下史家不应妄下断语,更不应随意臧否。只有做到“统观始终源流,乃能定其高下,其别甚为细微。”[11]231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亦十分不易,所以刘咸炘建议修史者要“温柔敦厚”,这一看法与章学诚的“同情理解”可谓如出一辙。与梁、刘不同的是,柳诒徵将“敬恕”与心术结合起来考察,补充了“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观点,做到了这点“乃真史德也。”[13]130在柳氏看来,一味地强调“敬恕”其实并未理解历史本原,终不免玩物丧志。在“敬恕”二字中,柳诒徵更为看重的是“敬”,所谓“动莫若敬”[13]113,“敬”是一切之根本,“吾国族之能萃大群而成统一之国家,端由于此。”[13]113
柳诒徵对于章学诚史德观的申说其目的何在?在笔者看来,柳氏希望论证中国传统史学讲求“史德”借以证明中国历史是真实可信的,进而驳斥同时期流行学界的疑古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后,以其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式登上学界舞台,其后影响渐大。作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的柳诒徵对于“古史辨”派怀疑本民族历史的这种自我否定态度十分反对,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史家秉笔,又必慎重考订,存信阙疑,乃德勒成一代之史”[13]121,所以“吾国史籍,自古相承,昭信核实,以示群德。”[13]12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柳诒徵就认为中国古史全盘可信,他也承认作史过程中会出现矫饰造假的现象,但是忠实重信是修史的主流,那些造假之作是很难流传下来的,所以“治吾国史书,必先知吾自古史官之重信而不敢为非,而后世史家之重视心术,实其源远流长之验也。”[13]114而且柳诒徵在这里所说的史并不单单指代君王之史,而是整个民族集体的历史。这些历史之所以可靠,所凭借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修史者的史德高尚,注重修德;是他们的素养保证了史书的质量。因此,柳诒徵认为那些怀疑抹杀本国历史的史学家在道德修养方面有所欠缺,认为他们“积于德也不素,则其临文也无本。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13]134而且,针对当时这种仿效国外,以“求真”为名行“疑古”之实的做法,柳氏特别指出,在历史研究中不要丧失民族本位,不要“因为外国人不信他们从前相传的神话,也就将中国的人事疑做一种神话”[14]501,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妄自菲薄。
海通以还,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史学也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过渡,在此过程中,近代学者争相发掘新兴材料,扩大研究范围,援引西方治史方法,推出现代史学著作,努力从外部入手将传统史学与西方规范进行调适,而对于史德观等传统史学的内部因素的考察,关注者并不甚多。梁启超受西方“新史学”思潮影响将“史德”赋予现代含义,试图对章学诚的观点进行补充,但究其内容仍是在重复章氏之成说,且在这一过程中凸显自相矛盾之处;刘咸炘对章氏观点极为赞同但却未能结合近代治学风气的变化加以反思;柳诒徵吸收同时期诸家观点,站位本土,以民族文化的视角申说章学诚所倡之史德观,重建国史内在理路,借以凸显民族本位立场,力求达到昌明传统文化的效果。他的这一实践或许显露出一些保守色彩,但其在这一过程中所坚守的以我为主的研究立场,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亲敬态度等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浦起龙撰,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唐会要:卷63[Z]//刘占召.史通评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林时民.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主义——刘知几与章学诚[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3.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
[9]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1]刘咸炘.治史绪论·序论[M]//刘咸炘论史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12]刘开军.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5(2):27-36.
[13]柳诒徵.国史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4]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C]//柳曾符,柳定生.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