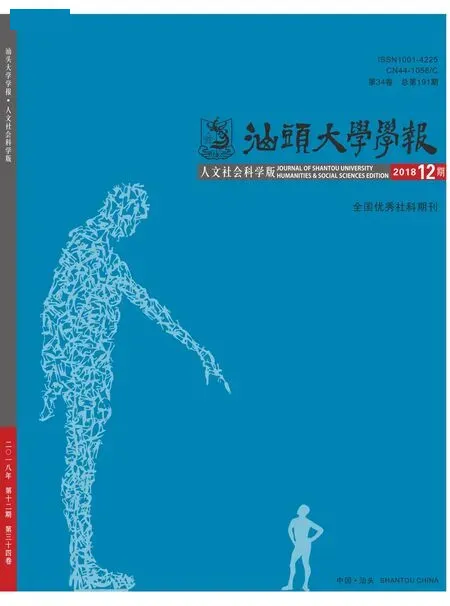鲁迅与编辑出版
2018-01-30孙郁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6)
王富仁先生曾经说过:“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也没有新文学四大文体形式的确立以及四大文体内部关系的新的调整。”这是一个共识,现代文学研究不能不关顾的就有传播学的话题。不过,由于目前学科的设立,人们对于作家的看法有时是局限于自己的学科背景的,这自然影响了一些问题的判断。如今人们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其实是试图在出离这样的困局。在个体化的思考里体现整体性思维,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不能不做的工作。
有学者已经指出,我们在文学之外的视域里,方能够把握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现代艺术的诞生纠缠着许多因素,它与民族国家、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存在大有关系。不仅西方如此,东方亦带有此种特征。我们反观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群落的奋斗史,当感到此现象的耐人寻味。回望那时候的历史可以发现,传统经典的普及受到了新传媒的影响,新思想也诞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现代性之门的打开,靠的是多种学理与精神之力的推动。知识分子如何借用传媒从事启蒙与社会变革活动,其实有着文化史中诱人的内容。
早有人从五四那代人的精神实践里看到了此点。以鲁迅为例,他与报刊、出版社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编辑活动,牵扯着文化史的诸多神经。鲁迅给我们的难度是,不能够在单一的文学思维里观照其生命行迹,他一生从事的工作横跨数个领域,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就带出了诸多背景:教育环境、舆论空间、政治氛围、书写习惯……文学家与出版体系的互动关系,倒是能够看出时代的立体性的一面。
李金龙所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当看到他的书稿的时候,感受到深切的思考里的快慰。在作者大量史料的梳理里,昨日历史纷乱的一页被进行了有趣的注解。
现代传媒给知识界带来的最大的便利是,与时代的对话去掉了围墙。不仅藏在深宫里的作品可以直接展示在读者面前,人们对于时局瞬间的感受也很快传递出来。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近代知识人从书斋里走到媒体里,具有了直接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所以与传统士大夫不同,就在于他们具有认识论的革命性、方法的革命性、传播工具的革命性。这三者缺一不可,恰恰是借助工具的革命性,他们把现代性的精神光泽,辐射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从李金龙的研究中发现,作者对于鲁迅的文化精神的流动渠道的认识颇为深入,不仅看到了精神本色的一面,也对于其社会活动的方式特点做了详细的梳理和思考。鲁迅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艺术工具推陈出新,被其一一点染出来。
这是一个用单一认知模式难以解释的存在。思考鲁迅这样的人物需要历史的整体感和细节的真实还原。纵观鲁迅一生,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除了译介域外的作品,还有编辑杂志的冲动。这自然与章太炎、梁启超的影响有关,但在根本层面,也存有寻找自我的选择。我们从周氏兄弟早期活动看他们的思想,能够感受到新旧知识人的界限。而在五四前后的创作实践里,鲁迅与媒介的多种交织也折射出其与同代人不同的个性。这个角度提供的景观有思想的另一面。我们看彼时的知识界的分分合合,也会知道新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而后来,当鲁迅与青年作家一起编辑出版左翼意味较浓的杂志时,其生命中迷人的一面也渐渐显露出来。相对于象牙塔里激进知识人的选择,鲁迅更知道拓展艺术平台的重要性。
在鲁迅看来,新的思想与艺术的出现,必须有属于自己的载体。知识人不应只具备审美的沉思,还应有在世间耕耘的辛苦。编辑对于鲁迅而言,像农民种地一样,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出喜爱的果实。但又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引领大众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也是精神的设计者和思想的导演。我们如果从这个层面看他的选择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在纯粹理性中面对世界的人,而是在对话中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的战士。从他积极介绍尼采、契诃夫、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高尔基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他精神的渴念。而这些作品的翻译、编校、设计、出版,他多以己身之力为之,那些艺术品的诞生,看得出编者的智性之高。这里留下了精神图谱里重要的线索,也为我们了解其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参考数据。
在鲁迅编辑的图书、杂志里,有日本读物的影子,俄国与德国的理念也跃然纸上。但有时候也有中国明清印刷品的底色,传统士大夫的影子也是有的。他给自己的杂感集起书名,都有明清士大夫作品集的味道,书籍装帧带有古朴之气。在培育新的艺术产品里,保留最古老的东西,其实是鲁迅的梦想。他年轻的时候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后来的实践里都得以证实了。
鲁迅一生做了许多跨行当的工作,所以亲自参加编辑实践,是自己的使命感和价值态度所决定的。当《新青年》分裂后,他意识到寻找自己的平台的重要性。一个不依附于他人的媒介,可以传播出自己最希望传播的声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就写道:“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1]无法认同别人的时候,一切只能靠自己,否则就成了无所事事的旧式人物。而那时候能够给他快慰的大多是青年。他后来与青年们一起打造新的刊物和出版社,成了选择的重点。这种集创作、翻译、编辑、出版于一体的工作,能够看出鲁迅能量的非凡。
李金龙在研究中尽量照顾到了鲁迅编辑生涯的方方面面。既看到了编辑意图中深处的隐含,也发现了出版策略。而对于商业运作与思想抵抗间的复杂联系,也做了有趣的说明。重要的是,文学社团与流派的活动空间在这里是以复杂性的方式出现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鲁迅的独立性与丰富性。
如果我们对比同代的许多出版物可以看到,鲁迅经营的杂志和图书,带有精神的前沿性和审美的先锋性。就眼光而言,他所译介的作品都非平庸之作,多为国人难见的有创造性的文字。而又能够启示知识人对于当下文化发声。重要的是,他在编辑过程,不忘的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使命,扶植了大量青年进入文学领域,那些鲜活的作品因为他的支持得以与读者见面。以出版而推出新人,这也是他深切的父爱精神的体现吧。
我们的作者在叙述里对于鲁迅的编辑思想做了多方面的梳理。许多篇章阐发出幽微中深广的情思,其中关怀意识、出版的期刊品质、内在导向、审美风格、衍生的话题殊多。沿着这些思路,也发现了许多难点。比如鲁迅的编辑逻辑和传播悖论,比如独断性的选择可能导致的误读与误判,比如对抗性的思维可能带来的对于异己的群落的忽略等等。在面对这些难点的时候就会发现,鲁迅的思想是在各种对抗和对话中诞生的。他不仅面对政治的压力,也有商业的压力。在泛意识形态与泛商业化的环境里,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十分艰难。从出版业的角度看鲁迅那时候的选择,当感到战斗的不易。可以说,鲁迅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鲁迅给出版界带来了万花筒般的景观,他在选题、风格和审美方面独步业界,数量与质量都让人刮目相待。从文学领域看,他最早介绍了摩罗诗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达达主义作品;在美术界,敏锐地将表现主义、立体派艺术引入出版物中;理论方面,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籍;而创作方面,推出一批有活力的青年作品,萧军、萧红、叶紫、柔石等人都因其提携而被读者记住。从无到有,从陌生到熟悉,要填补的是一种精神的空白。在一个缺少人道与爱意的国度,知识分子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输进新鲜的思想,改造国民的精神。细看他在媒体界的出出进进,其表达的格式是有创造性的。拿来主义的因素颇多,而精神底色里,重要的是对于本土的创作的渴念。在鲁迅看来,思想不得畅达表达的时候,中国还不能算一个文化大国。而在引进外来艺术品的时候,也重新激发了其对于中国固有文明的认识,他后来把汉代造像的元素带进版画运动中,说明了他对另一种失去的国故的自信。
这是有趣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各种精神合力的作用。在摸索新路的时候,既有新风的吹拂,也有旧语的翻新,其工具性的存在也可以看出文化的连续性。即便是左翼文化建设时期,鲁迅对于前卫艺术的介绍和现实的沉思,除了有传统工具所没有的亮点外,汉唐气魄也暗含其间。研究鲁迅的这种实践和探索,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审视,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凝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五四那代人丰富了我们固有文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里,鲁迅就认为,躲在象牙塔里是安全的,但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而要做一些事情。鲁迅从事编辑活动的过程,看得出其精神之梦的闪动。这是许多京派的学人们做不了的工作,因为要付出,要自我牺牲。但在那时候做编辑,要保持知识分子本色,不免要受到重重压迫。所以,在编辑的日子里,也是自己独战的日子。在介绍自己与《语丝》的关系时,鲁迅这样写道: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警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由来,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说吧。[2]
从一个人与一个刊物的关系,散出如此多的信息,便知道现代文学与现代艺术滋长的艰辛。而在有限的空间里,知识分子要拓展精神之路,就要横眉冷对旧的势力。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忆那段历史,当惊心于那时候的现实的残酷。不了解鲁迅的这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对于现代文化的本然的存在将是隔膜的。
和平时期的青年,不太易理解鲁迅那代人的苦心,研究那段历史,不能够忽略的恰是那逆俗的阔达的情怀。这在鲁迅的文字里随处可见。1934年1月,在编辑了《引玉集》后,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狸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3]
文学艺术生产的过程,要克服盲点和政治禁忌,对抗风气和传统习惯,而且还具有精神灯火的作用。在讨论这些片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鲁迅提供的话题,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作家。从李金龙展示的脉络看,鲁迅一个人就覆盖了现代精神的许多领域。他在翻译、编辑、出版策划与展览策划里,催促出难得的艺术之花。可以说,鲁迅是现代艺术舞台一位伟大的设计者,在艺术天地里涂抹出让人惊艳的思想光点。在这里,旧的表达失去力量,而现代人的价值与理想,被定格在时光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这一丰富的现象,我们的精神也因之得以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