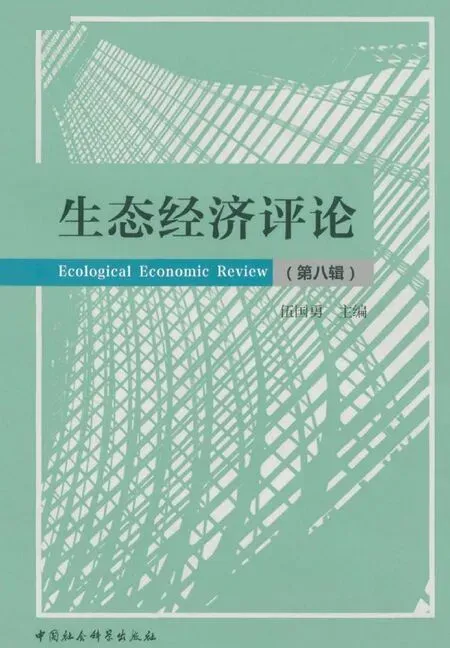茶与边疆:明代弘治年间西北民族贸易与边防体制*
2018-01-30李曼曼
王 君 李曼曼
内容提要: 茶作为中国饮食的重要部分、生活的必需品,不只利润颇丰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交流之用,早在秦汉之际,国家就开始了对茶的管控,此后历代从未放弃对茶利的盘剥。国家以榷茶制度在王朝内部获得巨额利润,补充国家财政。明时期不只注重茶利,更重视茶安靖地方的功用。茶马贸易作为民族贸易的一种,实为边防体制的经济管控措施。弘治年间杨一清在西北地区重整茶马,恢复茶马旧制,为安靖西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问题的提出
《礼记·礼运》 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人类的生存发展与食物息息相关,贯穿于整个繁衍过程之中。“摄取营养作为一种生物过程,比之性活动更为根本,在有机个体的生命过程中,它是一种更为基本、周而复始的更快需求; 相对于其他生理机能,从更为广泛的人类社会角度来说,它更能决定社会群体的特性,以及其所采取的活动方式。”①[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建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 页。茶亦如是,“茶者,南方嘉木也……茶之为永宁,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苦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②(唐)陆羽:《陆羽茶经译注》,傅树勤、欧阳勋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古时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佳品、珍品,每每以马换茶。
然而茶叶作为一种国家管控的物资,对外输出由国家掌控。边疆民族地区不产茶叶,但又需要茶叶,在国家允许合法贸易的情况下,多采取贸易的形式获得所需。但是,当不愿为其付出成本又想获得所需的时候,在群体对于某种切身共同利益的追求下攻击其他群体以获得自身发展的所需的战争就会爆发。为了避免战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规范民族贸易,“事实上每个朝代都力求控制诸如盐铁等攸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商品的税收的征缴和再分配。所以这些商品不但被看作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被国家实施专营,而且政府还将这些商品的专营看作确保公平销售,保障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的关键举措。”③[美]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 页。
有明一代大多数政府机构的设置在沿袭唐、宋、元各代之旧制的同时构成自己的特色,当然明帝国的财政管理亦不例外。“由监察官员审核财政,设立六部,政府发行纸币,利用大运河作为南北交流的主干线,与游牧部族进行茶马贸易,实行开中盐法以充裕边防,以上这些做法多是效仿前朝。”④[美]黄仁宇:《16 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 页。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开始往西南用兵,行羁縻之制,力图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相较于对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而言,西北则显得相对平静,民族贸易正常进行,严禁私贩,对“通番夷”者以重典处罚。
此后,对西北地区的贸易因练兵和防卫等原因使得正常的官方贸易终止,私贩严重,西北地方不稳,这种情况在明代弘治年间极为明显。西北边防急需治理,弘治十五年(1502年),因刘大夏之荐,杨一清被任命为督理西北马政的全权御史,开始了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其中对西北茶、马政的管理尤为突出,使得西北地方安靖,一改以前马政荒废之象。在《关中奏折》 中,杨一清详细论述了茶马贸易对于安靖地方的重要性,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实施了一系列恢复此前被荒废的“金牌信符制”,使得西北各族前来“差发”“中给纳马”,各取所需,有效贯彻羁縻之制,地方得以安定。
“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发展一套非个人的法律实施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由于法律的发展是一种公共产品,便具有与之有关的重要规模经济。如果有一套法律存在,谈判和履行的费用便可以大大减少,因为基本的交易规则早已清楚。”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4 页。但是,古代中国的国家政府往往不是以第三方的角色出现,作为主要的管控者,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相应的国家经济秩序,交易规则亦是为国家服务。本文将以弘治年间,杨一清重整西北马政,呈给朝廷的茶马类奏折为材料,从茶马贸易切入,分析明朝的茶法与茶马民族贸易的情况,民族贸易对国家边防体制的影响,即民族贸易对于国家边防安靖的重要功用。
二 明弘治年间的茶马贸易
“早期的中国军队设法对边疆的军队和边疆地区政府提供物资供给,而不向边疆地区征赋税和徭役。不管为边疆地区提供了多少从教育到经济方面的援助,中央政府对边疆却一无所取。相反,中央王朝实施了诸多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通过从内地征收和募集来满足边疆地区统治之需求。”②[美]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 页。其中,茶马贸易一项在边疆地区常设,国家榷茶制度建立,茶法的设置,均是保障此种贸易顺利进行,进而意图稳定边疆。明弘治年间的茶法在延续前朝的同时并对其进行不断调整,茶马贸易在西北地区的交易。
(一)明以前的茶马贸易
《汉书·食货志》 记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者也。”山川之利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茶之收入。《封氏闻见记》 记载:开元以后,“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颇甚多。……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①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 页。
可见,唐朝茶马交易便用于民族地区的交流,两者互通有无,有利于唐与回鹘等周边地区交好。宋元时期,西北地区的回鹘、龟兹、于阗等国尚与中国有朝贡关系,大量商队往来中国贸易,以美玉、名马、镔铁剑、琉璃器、象牙及各种香料等交换中国的丝绸、茶叶等货物。元政府更是重商人之利,在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繁盛。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渐成规模,此后各朝代在自身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均没有放弃对这条经济路线的经营,以输入国外的奇珍异宝,输出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珍贵物品为主,支撑着西北地区的经济线。
李埏先生曾言:“茶是经济作物,适于小农生产。地主茶园可以种它,一家一户的农民也可以种它。这和种桑养蚕是相似的。但制为成品投入市场时,绢帛不可以尺寸裂,茶叶则可以斤两计,多少都可以售出。尤其不同的是进入消费过程以后,茶,无贵贱都得而饮用,绢帛则非富贵之家是不能服御的。在塞外游牧社会里,这种情况更为显著。绢帛,只有安坐帐幕中的贵族酋长们能够享有,至于广大牧民和战士们,诚如汉人中行说劝告老上单于说的,‘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 至若茶叶,那就很不同。贵族们、牧民们都是‘羶肉酪浆,以充饥渴’,非茶不可,因而茶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显然,茶的市场较绢更为广阔,绢马贸易自然不能不逊于茶马贸易了。至此(指唐代),茶在内外市场上已执商品界的牛耳。到宋代,茶业更兴旺了。”①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可知茶叶不同于丝绸的一大优势就是茶叶市场更加广阔,不同的人群可以饮用不同品种的,只有价格高低之别,在古时的边境民族地区交易量比丝绸更多,茶马互换关乎地方稳定。
(二)明时期的茶马贸易
明代继承了前代由政府向西番少数民族地区供应茶叶,并与之交换马匹以控制西番的做法,仍然官营垄断茶叶贸易,在陕西汉中与四川地区设立茶课司,以征税形式获取大量茶叶,然后运往甘肃河州、洮州、岷州、湟州等地,通过茶马司换取藏族及其他民族的马匹。②田培栋:《陕西商帮》,万象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9 页。明朝的时候将前代的“茶马互市”这种官方管控下的商业贸易,国家作为第三者通过相关法律规范贸易之举,直接转变为官控的像田赋一样的“差发”,茶马贸易不再是商人的参与,中央政府在此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纥入贡,巳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乃有以茶易番马之制。所谓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者,宜无出此。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我体既尊,彼欲亦遂。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轻重得失,较然可知。③(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 页。
“差发”直接受政府管控,“互市”“交易”虽然受政府监控但是并不是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之内,商人在西北地区自由贸易,所得之利并没有直接进入国家的财政税收系统之内。明朝统治者和官员均认为边防稳定的重要一环是控制好该地区的茶马交易。
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责番夷以差发,非若秦、汉喜功好大勤远略者之所为也,亦非中国果无良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葢西番之为中国藩篱久矣。汉武帝图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而幕南无王庭。今金城之西,绵亘数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终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为之世雠,恐议其后,此天所以限别区域,绝内外者也。不然则犬羊长驱,宁、河、岷、陇之区,鲜不为其蹂践,欲晏然无事,得乎?①(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 页。
可知自明代边防重患在于西北,以“差发”的形式与中国的藩篱进行贸易原因不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也不是中国无良驹,而是番人是明代的屏障,对明代的西北边防极为重要,也是防止西北被夷狄蹂践的良策。
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住札,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敌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②同上。
可知,茶在明代对于西北番夷来说极为重要,以茶作为控制地区安靖的重要物资,以茶易马,增强军队的实力的同时也减少军队的畜马成本,故而杨一清将茶马差发作为制西番以控北敌的上策。
“国家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所入以目奉。凡前代所谓榷务,贴射交引茶由诸种名色,今皆无之。惟四川置茶马司四间于关津要害置数批验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赍榜于行茶地方张挂,俾民知禁。又于西番入贡为之禁,限每人许顺带有定数,所以然者,只欲资外国之马以备边。岂若前代夺民生日用之资以为经费哉?”③(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征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7 页。明时期茶叶的严格控制并不是夺民之利,而是在边疆地区实行的特殊贸易政策。对待番夷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茶马互易,以期治国安邦,安靖西南、西北。“明朝二百多年中,西藏地方一直服从明朝的政府的管辖,使明朝‘西陲宴然’,人民之间往来频繁,茶马等贸易也始终不断,茶马贸易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①南炳文、汤纲:《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 页。
正是因为茶马贸易的繁盛,就更需要对茶严格管理。早在洪武、永乐年间茶法就在逐步确立。洪武初年规定:“凡引由,官给茶引付产茶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贴付之,仍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其有茶引不相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拿问。卖茶毕,即以原引由赴住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具各委官一员管理。”②(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重修本)卷之三七课程六·茶课》,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6 页。以茶引的方式严格控制国内茶叶的运输与贩卖。
《国朝典汇》 记载:“辛丑正月,中书省始议榷茶之法。官给引令商赴产茶郡县,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贸易,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郡县籍记姓名以凭勾稽,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贴付之茶,无由引者,听人告捕,令府州县委官一员掌其事。”③(明)徐学聚编撰:《国朝典汇(下册)卷九五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6 页。所有的出境贸易必须有官方的凭证,对茶商登记名录,所有行事均以茶引为依据,每府州县都有专门的掌事人员负责专职管理。
在明代,有边茶与内地茶之别,边茶主要是陕西和四川所产的茶叶,系明代政府为控制四夷进行茶马互市时所用。边茶与内地茶,“二者在植茶及焙制上皆有甚大的差别,前者主要以粗茶制成茶砖大量外输边族,以交换马匹,此即明史上所谓‘茶马法’。由政府在边地关卡设官司来进行交易,所谓:‘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者无比于此。’ 边茶攸关政治、经济至重,故立法至严,犯者罪至死。明代政府为交易,在沿边陕西一带与四川、湖广等地区招民植茶,由官方茶课司征茶课,因茶利至厚,私茶出关者多,及官吏舞弊,致茶马法后多不行。”①吴智和:《明代职业户的初步研究》,《明清史研究专刊(第四期)》,大立出版社(台湾)1981年版,第68—69 页。早在洪武年间为进行“差发”而实行的“金牌信符制”已几近废除。
杨一清在受命督办西北马政时呈奏折曰:臣受命督理茶马亲至、西宁洮州等卫地方,督同兵备、守备等官陕西按察司副使萧翀、署都指挥佥事蒋昂等,选差抚夷官员,带领通事,分投抚调各族番夷,中纳茶马。随据差去人员,陆续抚调各族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偕其国师、禅师,各赍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观焉。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臣奉宣皇上恩威,抚且谕之,责其近年不肯输纳茶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这是我西番认定的差发,合当办纳,近年并不曾赍金牌来调,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将马来换茶。今后来调时,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违了。臣于是乃知我圣祖神宗,睿谋英略,度越前代远矣。”②(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 页。
可知,明初有效控制番夷的策略就是以金牌信符的方式合理地规定了每一地区应该茶马交易的数额,根据不同的地区发放不同数目的金牌,持金牌每三年进行一次茶马交易,所获之马均用于西北军事操练。
明朝的统治者深知茶叶贸易可获得丰厚利润,以官控的形式给商人以茶引,采取开中茶法、召商运茶、召商买茶等措施,在国家人力、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商人的财力实行政府的职责,一方面对边境地区或者灾害地区补给物资,弥补国家财政的短缺以及资源不足的缺憾; 另一方面通过茶马互市抑制西番的军事力量,保障明边境的安全,茶马互市安靖地方的功用在明统治者看来极为重要,也是实施这一措施的根本目的,远远超乎元代统治者只为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为此,明朝为了更好地控制茶利,与茶相关的一切都在明政府的管辖之下,明初通过法律规定茶户、茶商、茶律对其严格管理。此后因种种原因对茶的控制日渐松弛,弘治年间杨一清督理西北马政的马政重整茶业。
三 明时期的茶户、茶园、茶商、茶律与边防
(一)茶户、茶园、茶商
在明代,茶户由其所在的地方政府管理,他们负责国家茶课的定期征收,当地方发生灾异不能及时完纳茶课时,负责向上级政府直至最高统治者皇帝汇报,并对茶户的清查与登记负有管理责任。这种责任同管理普通农户相似,为了方便对茶户的管理,明代还比照粮长制度,选定了各地区的里长和解茶大户协助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工作,而对茶课的征收、解运能否按时完成也是对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①魏志静:《明代茶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2007年,第30 页。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御蒙古及藏族贵族入侵,明统治者在嘉峪关外设立罕东、曲先、阿端、安定、赤斤、哈密六卫。又在甘肃、青海、宁夏境内设置了二十余卫及十余个千户所,驻军十二三万人,军粮的供应,除军屯和陕西布政司的供应外,还有一部分依赖盐的开中法及茶马法换取的粮食来补充。这些制度的施行为陕西商人提供了从事盐业和茶业经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其中游刃有余。”②田培栋:《陕西商帮》,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8 页。
然而明政府明确规定凡外出经商,必须经过官府批准,领取官府签发的“官券”,才能进行商业活动。史称:“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官券。”这种“官券”,又叫作“商引”“路引”或“物引”。如无商引,即属非法,“坊厢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黯窜化外”③李龙潜:《明清经济探微初编》,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 页。。商引的内容,载明货物种类、重量以及道里远近。史称:“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引间。”④同上书,第522 页。目的是明确掌握商人的动向,防止其摆脱政府的监控,做非法之事或者成为“游民”。
明代对商引、路引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允许地方官府随便发放商引、路引,对擅自涂改商引、路引的,也要进行刑事处罚。景泰年间加强对茶引制度的规定,要求商人在申报茶引时必须要由批验茶引所对其姓名、贯址、引由数目、发卖地点等进行明确登记,茶商在路途中要随时接受盘验,地方政府要对收缴的茶引情况每年登记造册,对于那些不按时交还茶引的茶商要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及时交由司处理。可见当时商人在从事茶货经营时所要接受的监督和管理要远远多于从事普通货物的经营。
明中叶后实行招商中茶。这种招商散引的办法,是由商人运茶交甘肃各地茶马司,政府给以盐引,商人领到盐引再去扬州等地支盐。①田培栋:《陕西商帮》,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9 页。此去路程艰险,但是实力雄厚的茶商不惧危险,从官府取引贩鬻四方,获资无算。商人从中获得巨额利益,严重影响了西北茶马互市的正常运转,使得私茶泛滥。
为此杨一清在办理西北马政提议要求:“但今停止商茶,户部题奉准依,许将例前报中者,照旧发卖,其数几二百万,是又一厄也。诚使私茶商贩,一切禁绝,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无茶,不抚亦将自来,调之宁敢不至? 臣仰承任使,恒惧无补,以速罪尤,深虑却顾,辄罄一得之愚如此。至于兴废补敝之宜,谨条陈五事于后,伏维圣明省觉。”②(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 页。可知,商人贩运私茶至番夷,严重影响了国家对边境的管控,认为一旦茶叶得到禁止,番夷无茶之后,自会来臣服。
因此,更应该严格控制茶商,言明茶律。乞勅户、兵二部,议其可否,覆奏行之。仍乞断自宸衷,今后有以开中商茶为言者,无赐施行。该部该科查照不许招商中茶前旨,举奏惩泊。庶几番人坚内附之诚,边方无意外之患,不止有禆三边马政而已。臣不胜惓惓体国之至等因开坐奏。③同上书,第76 页。为保边方无外患,明初对边茶、茶引的控制极为严厉。
(二)茶律
陕西、四川的茶户种植的茶主要为控制番夷,茶马互市所用,所以为边茶户。而内地茶为民生日用所需,由除陕西和四川两省之外的产茶州县供应,因此这些茶户为内地茶户。而内地茶则主要是供应内地的消费,明政府主要通过征收榷税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在法律的惩处方面并没有边茶那么严厉。①吴智和:《明代职业户的初步研究》,《明清史研究专刊(第四期)》,大立出版社(台湾)1981年版,第68—69 页。
明初规定:“出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没官。客商贩到茶货经过批验所,须要依例批验,将引由截角,别无夹带方许放行,违越者,笞二十。伪造茶引者,处死,籍没当房家产,告捉人赏银二十两。”②(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重修本)卷之三七课程六·茶课》,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6 页。可知,明初对伪造茶引的行为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犯罪人本人处死,并处没收财产,因为茶引作为茶法中最为重要的官方凭证,其作用十分重要。后来《大明律》 明确将伪造茶引的行为作为诈伪罪的重要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凡伪造衙门印信及历日符验、夜巡铜牌、茶盐引者,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③《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 页。茶律对于茶引的控制极为严苛,使得很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又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的利润以及不会被查处的侥幸,对茶利趋之若鹜。
各番虽不中马,未尝一日无茶。彼既坐得之,何求于我? 且中国之人,明知禁例,肆行无忌,于番夷乎何诛? 臣乃申严禁令,严督所司,缉捕私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敛迹,茶价顿增。已而招调番人,远近毕集,稔恶如朵工、黑章咂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国之茶,真足以系番人之心而制其命。④(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 页。
可知,明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番夷不来中马,但依旧有茶可饮,故而番夷不听调遣,实为私贩严重,杨一清在西北缉捕私贩,使得招调番人,远近毕集,看到茶叶对于番夷的重要作用,将严格控制茶业贸易作为边防的重中之重。
弘治年间,西北都御史杨一清再次提出:“严私贩之禁。查得律内,凡犯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及查见行事例,私茶有兴贩五百斤的,照见行私盐监例,发充军陕西等处。但有汉人结交夷人,互相买卖借代,诓骗财物,引惹边衅者,问发边卫,永远充军。近准兵部咨,为从宜处置边务事,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玑奏前事,本部咨行臣处,查访议处,应奏请者奏请定夺。内一件止通番。访得西宁、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邻番族,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巨万,通番买马。雇佣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住不出。不特军民,而已军职自将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当通番。番人受其恐吓,马牛任其计取,变诈渐萌含愤未发。诚恐一旦不受束约,患可胜言? 且通番之人,明知事例,犯该充军,乃互相嘻谓:‘无故亦要投军,有甚打紧。’ 似此欺玩,若不重加法典,则通番起衅,兹其渐也。又一件禁约私茶,查得洪武、永乐年间兴贩私茶者处死,以故,当时少有蹈之者。间有一二私贩者,包藏裹挟不过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岂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积聚如丘; 外境夷方,载行如蚁。明知禁轻,相谓兴贩私茶与兴贩私盐同律,事发,止理见在,不许攀指。例则五百斤以上方才充军。计使一人出本,百人为伙,毎人止负五十斤,百人总负五千斤。各执兵器,昼止夜行,遇捕并力。万一捉去一人,只是一人认罪,数不及五百斤以上,不过充徒,余茶总收其利,以此得计。群聚势凶,莫之敢捕。官兵遥见,预为潜躲。乞将兴贩私茶者,合无照永乐年间旧例处死,通番并把隘卖放之人亦如之。如圣慈不忍寘之重典,合无将私茶十斤以上与一应通番并把隘纵放之人,俱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等因。”①(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0—81 页。
弘治年间,将私贩茶者处死,重申贩私茶之禁律。之所以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严厉的处罚,是因为茶与边境的安全息息相关。茶马互市作为明代边防体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府从事茶叶贸易的生产到销售各环节进行严格的掌控,以期通过控制经济贸易安靖地方。
四 茶马“差发”与杨一清的西北边防体制
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一书中提出:“国家将规定章程,以便统治者以及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后在其约束下,将发明一些章程来降低交易费用。非自愿的组织形式如果对统治者有利(如非资源的奴隶制)将会存在; 如果比较有效的组织形式从内部或外部威胁着统治者的生存(如果今天苏联的集体村庄,或古典世界雅典谷物贸易的组织),相对低效的组织形式也会存在。”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1 页。诚然如此,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谋求,明洪武年间初行金牌、信符之制,严格控制西北边防的茶马贸易,将其视为边防体制的一部分。
窃照洪武年间,钦降金牌数目,各卫典籍磨灭,多无的据。查得河州地方,原设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原额金牌二十一面,认纳差发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卫地方,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冲、申藏等族金牌一十六面,该纳差发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卫地方,火把哈藏、思曩等族金牌四面,该纳差发马三千五十匹。上号在于内府收贮。每三年一次,钦遣近臣赍捧前来,公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劄营,调聚番夷,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如有拖欠之数,次年前去催收。②(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 页。
可知,洪武年间,针对西北番夷的不同情况,分发数目不同的金牌,按照金牌的面数认纳马匹,给予相应的茶斤。但是,后来因边防多事,陕西军民转输军饷,无暇运茶,腹里卫分官军又各调去甘、凉、宁夏等处征操,别无官军可调,茶马因是停止。西北地区的金牌、信符之制停止之后,历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诸卫,貌不相通,诚恐数十年之后,虽近番亦不复知有茶马矣。
杨一清在西北督办马政,欲照旧例,调军入番征收,非唯病于供亿,且恐激扰番夷,故而呈奏折于朝廷,希望可以查出该衙门将金牌旧额。然后申明各位,原先给应该纳差发马匹番族告知,朝廷修复旧制,各当本等差发,不许生拗违背。为安靖地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茶源的问题,杨一清在奏折中提道:“然招番必先运茶,不然调来番马,无价可偿,失番人之望,亏中国之体。”
合无于弘治十八年、十九年内,如臣后所拟奏,严禁私贩,广积官茶。其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等官,久不袭替,亦令兵备、守备官查出奏请,就彼各袭原职,以为统领,不必令其来京。以弘治二十年为招番之期,乞遣廷臣赍捧上号金牌前来,会同臣及陕西、甘肃二处巡抚官,督同都、布、按三司官员,不须动官军深入番族,止在三卫住劄,差委抚夷官员、通事,分投调取各番,各赍原降下号金牌,牵赶马匹,前来上纳。分别上、中、下三等,给与价茶,厚加赏劳,遣回本族。如不敷原数,听次年征收补还,事完,将收过马数造册,随金牌赍缴,马送陕西行太仆寺印烙,照例给军骑操。以后三年一次举行,中间二年,仍照常差官,赍番字文书前去各族晓谕,有情愿者,听其自来,将马换茶,不愿者不拘。敢有不受约束招调不来者,再三抚谕,如果执迷不悛,量调汉番官兵,问罪诛剿,以警其余,庶几恩威并施,番人怀威永为藩篱之固。①(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关中奏折·茶马类〉》,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78 页。
杨一清将弘治二十年定位招番纳马之期,各番夷按照金牌面数规定的马匹数,将马换茶。根据马匹的好坏程度的不同,给予相应的价茶,三年一期。中间二年如若有自愿来以马换茶的听其自愿,按例照行。中央政府直接管控了茶马贸易,对于招调不来者,再三抚谕后仍执迷不悛,调兵问罪诛剿,以警其余,恩威并施,方可使番人怀威永为藩篱之固。
明政府,对边境的治理一直采取羁縻之制,在这种边防体制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在边境驻扎,操练军马,起威慑之用。每一场战争都需要消耗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无疑能以经济手段控制并安靖地方是绝佳之良策。杨一清以招番纳马,将马换茶之制运用于西北边防体制中有效地控制西北地方稳定。
五 结 论
明初,国家初立,边防重兵以压,军队的极大消耗使得国家财政负担加重,除采取军屯的方式,军队部分自给自足,还加大了对山泽之利、专卖制度的管控。茶作为盐铁等重要物资也在被管辖之列,作为剩余价值极高一件商品,吸引着国家、商人、茶户等竞相逐利。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会坐失巨额利润和其背后的防控机制。尽管此前,私贩茶马极为严重,进而影响国家对西北地区的掌控,但是明孝宗弘治年间,杨一清督理西北马政的时候,复金牌之制,严私贩之禁,巡专察之官,处茶园之课,广茶价之积,使得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一改往日私茶泛滥之象。在官府控制之下的茶马贸易,番人怀威,忌惮王朝权威,从而藩篱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