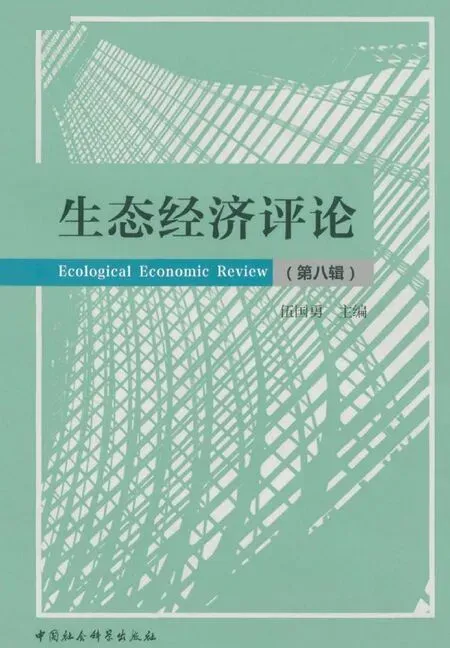社会距离:化工区民众环境风险知觉折扣及其生成
——以湘中X市Z化工区为例*
2018-01-30郑进
郑 进
内容提要: 受环境问题影响核心区域民众的环境风险知觉偏低现象受到学界关注,已有结构化解释虽建树颇多但力有未逮之处。通过对Z 地50年来民众与化工区的互动及变迁历程考察发现,基于化工区的生产后果所产生的社会距离意识对环境风险知觉的折扣起着关键作用。对化工生产结果的感知、个体生活经验和所得、所处结构性位置是影响工农群体调整与化工区空间距离意识的重要变量。因化工生产及排放物对于工农群体的生活具有改善效果而意图进入化工厂及影响场域之中,有益无害的化工认知使得民众的风险意识处于蛰伏之态; 在逐步靠近化工区过程中污染影响日益突出,工农群体采取技术安全认知并调整生活策略从而将化工区的消极后果排斥于生活空间、环境风险意识之外,通过剥离个体与化工负面影响的关系使得风险知觉出现了折扣效应。
一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我国局部地域环境问题突显,雾霾、江河水重金属超标等影响面大的环境事件让数千万城乡居民浸淫在环境恶化的担忧之中。然而除了个别地方因特定原因爆发了邻避运动外,我国绝大部分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民众并没有生成高度的风险知觉并参与到环境抗争行动之中。更为吊诡的是受环境问题影响核心区域民众的风险知觉或对个人居住区域内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相对较低判断程度并不最高,①中国环境意识项目办:《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世界环境》 2008年第2期。反而呈现出类似“心理台风眼”效应②李纾、刘欢坦、白新文:《汶川“5·12”地震中“心理台风眼”效应》,《科技导报》2009年第3 期。(Psychological Tyhpoon Eye effect),即中心区域民众的风险认知并非高于而是明显低于非中心区域民众的认知程度,中心区域民众的风险知觉出现了折扣(Discounting)效应。
目前,除了心理学中认知失调理论、简单暴露效应、个体知识经验等解释外,社会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体制一体化、政治机会结构、强国家弱社会及民众的经济理性计算等视角解释这一折扣困境的发生机制,这些解释工具着眼于宏观制度、经济理性等外在力量对人们的认知与行动所生发出的限制、形塑作用,忽略了对人与污染环境的互动过程的剖析,并且已有环境意识调查大多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个社群,缺乏横贯层面的比较和纵贯层面的跟踪研究。③包智明、陈占江:《中国经验的幻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3 期。整体而言,已有解释框架很好地说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民众整体上环境风险知觉偏低,然而对现实中同一情境下不同人对环境风险产生相异甚至是结构化的理解与行动倾向,特别是中心区域民众的风险知觉偏低及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无风险意识这一吊诡现象则解释乏力。
概观已有研究,由于缺乏对环境风险情境与行动者的互动这一社会维度的讨论,过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都无法解释群体风险认知的非结构化特点,以及特定区域内民众的风险知觉特点及演变历史。因而有学者认为目前风险认知的研究将环境受影响者当作“一个本土情境下的‘他者’”④司开玲:《知识与权力:农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即因为没有考虑受影响者作为积极行动主体的感官体验式知识及与污染因素的互动过程,而使当地一般民众成为审判性知识和污染议题之外的第三者。正因为如此,以自然与社会互动所产生的“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为视角,剖析民众对环境的历史性获得感和感官体验式认知,将作为主体一方的群体放置在风险情境的结构和历史形成过程之中,从情境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长期互动与距离感这一社会“黑匣子”入手探索环境风险知觉折扣的结构特点与生成机制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
二 文献回顾
直到20 世纪末社会学者才开始关注环境风险知觉这一议题,该议题传入我国则迟至最近十年,到目前为止我国环境社会学者将过多的学术热情投入到了对环境抗争策略、出路及困境等问题研究之中而使得环境风险知觉的研究相对薄弱。
20 世纪50年代在对购物心理进行研究的时候,“风险知觉”一词被提出,随后被应用于环境风险研究中。Guedeney 、Mendel 具有开创意义地考察了人们对法国一核电站的风险知觉态度的认知,①Guedeney C.,Mendel G., L'angoisse atomique et l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Contribution psychanalytique et sociopsychanalytique àl’ étude d’ un phenomena collecti.Paris:Payot,1973.此后核反应站、炼油厂、机场、燃气站、监狱、区域供暖设备,甚至精神病院等周围的居民对这些公共设施的风险认知大小及特点也被研究者所关注。此类研究主要想测量特定区域人们的风险值,注意到了特定区域和风险源对人们风险认知的可能影响,不可忽视的这些研究都将调查对象放置于污染距离之外即强调了空间距离和风险类型对认知的影响,没有研究群体对环境,特别是化工生产区不同理解的影响。
进入21 世纪我国环境社会学者在环境风险情境与风险知觉的关联和影响机制上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并对风险情境的影响作用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理解。宏观层面上主要是考察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和文化特点对民众风险知觉的影响,承认了自然影响和知觉之间存在着社会影响因子,如地方文化、政治机会结构、社会结构等。如景军早在2006年提到对乡村环境抗争的社会与文化分析在我国仍处于几乎空白的状态,强调生态问题的文化自觉和家族延续的地方文化形塑人们的风险认知和行动动员形态。①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 期。陈占江等考察了湖南湘江流域易村村民在特定政治机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群体环境风险意识缓慢的觉醒历程及其所受到的限制。②陈占江、包智明:《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 期。王甫勤考虑到我国转型社会的特点而提出民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受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制约。③王甫勤:《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第2 期。不过,除了景军关注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外,陈占江与王甫勤眼中的环境受影响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被动化桎梏之中,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被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所分割。
微观层面则主要依托田野调查展开,在对风险源及与个体互动的梳理上较宏观研究更为细致,对风险源和风险认知的相关关系上亦有所新发现。陈阿江认为“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在一些污染地促使了“癌症—污染”风险认定关系的产生,但由于村民的认知局限而放大了污染与身体疾病之间的关联性。④陈阿江、程鹏立:《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学海》 2011年第3 期。与上述发现相反的是,熊易寒觉察到湘南农村由于村庄和家庭利益嵌入化工厂的发展之中,农民在经济理性面前突破了空间距离的影响以致呈现出无环境风险知觉之态,甚至在化工厂搬迁之际出现了“反脱嵌”心理—社会行为;⑤熊易寒:《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读书》 2007年第9 期。郑蕊等通过某铅锌矿区的调查发现在风险知觉上存在着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应,个体的风险知觉随着采矿卷入度的提高而显著下降,从矿区获益或损失的感知是关键的中介变量。⑥郑蕊、饶俪琳、李纤:《铅锌矿区居民风险知觉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心理学与创新能力提升——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13年。上述两研究者眼中村民仍没有摆脱风险强化心理和在强大利益诱惑面前的被动性色彩,但其研究发现打破了污染与认知之间的正向关联,证明了空间距离难以解释环境风险知觉的非线性特点及个体心理距离的多元性。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对风险情境的研究发现除了空间距离、个体心理距离两个中间影响因素之外,自然影响与风险知觉的形成之间还存在着社会性影响因子,特别是受影响的主体如何处理自身与污染物之间的距离关系,即如何将自己排斥于污染的影响距离之外、生成化工生产的影响与危害等意识之别。对主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之中利用与调整已有资源来影响风险知觉的形成也就成为本文的重要意义和关怀所在。
当然,关于社会主体与风险情境互动对风险知觉生成的影响已经受到了学术界关注。洪鸿智强调一般风险知觉文献,常低估居民与地方环境互动在风险知觉形成的作用,而风险知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奠基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之中。①洪鸿智、黄于芳:《农村工业污染风险知觉的空间特性与决定因素》,《台湾土地研究》2010年第2 期。缺乏对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与环境情境的互动环节研究无疑限制了学术研究的穿透力。在田野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情境的重要中介意义。司开玲提醒到只有关注农民的反抗行动所放置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境,特别是农民对于环境的感官体验,才能展现农民反抗的动态性而不是其必然性,不过她同样没有将研究对象延展到污染制造的农民。陈阿江发现村民们通过迁离污染源、改变食物、改变水源等办法规避风险。我国台湾学者洪鸿智等对情境结构化的分析和认知的空间特征的梳理更具启发意义。其研究发现由于特殊的工农发展环境,受所处生活条件、污染冲击、邻居的风险知觉及地方感等地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台湾农村居民的工业污染风险知觉具有空间分布特性。这些研究重新将环境受影响者纳入风险情境结构之中,关注到风险情境和感官体验所产生的折扣作用。
鉴于此,笔者在湘江流域有着60余年的工业发展史和环境污染史的城乡接合部社区——X市Z地进行田野调查,借用“人在情境中”的视角,通过对Z 化工区发展历史回顾和与工业环境相关生活的挖掘相结合的方法,力图理解历经60 余年的工业发展与当地工农群体环境知觉的折扣环节和影响机制,以期剖析包含着自然情境和社会情境、静态现状和动态历程的环境情境对受影响者的环境风险知觉折扣影响,回答为什么在普遍承认的化工污染区民众不同程度地参与化工生产活动,甚至主动与化工区相邻居住和只觉有影响而不觉有风险存在,以致鲜有集体性抗争行动发生。
三 嵌入式参与和蛰伏的环境风险知觉
(1)化工区的生成
Z地处长沙湘潭腹地,临江且有山丘荒地,1950年湖南省工业厅决定在Z 建立湖南砖瓦厂以支援地区建设,开启了该地工业下乡序幕。此后数年在沿江的荒山空地上有硫酸厂、电化厂、色织染整厂、氮肥厂、树脂厂、第三化工厂、化工研究院等企业相继建成投产。
Z 以国企化工为主,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较高,封闭化程度亦较好,加之国企工人主要从事行政岗和技术岗,雇用临时工从事搬运、投料等工作。因而即使有化工厂使用强酸类原料,但正式工人直接接触它们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他们知道原料及产品的毒性,但整体上认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安全的。即使发生了安全事故,也都是发生在非正常操作的情况之下,他们不认为安全事故属于常态,并且此类事件在当时仍属少见。如1979年有机化工厂工人胡耀丹因反应塔发生紧急故障,在摘除防护装置的情况下连续四次进入反应塔,超出预定工作时间的四倍,最终发现其出现肝功能受损而入院接受治疗,工人们强调他是超量工作所致。
此时由于工厂均刚刚建设,投入规模不大,产量长期都未达到原设计的标准,因而“三废”排放量及其所造成的污染有限。如有机化工厂设计的邻甲苯胺生产能力是1200 吨,由于技术的局限,至20 世纪80年代中期其生产能力平均仍不到400 吨。①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湘潭市志·三·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毗邻的湘江由于环境容量巨大,成为各工厂排放废水的最佳选择,工厂生产产生的废水全部直接排入湘江之中,数座荒山和岸边亦成为堆砌生产废料的绝佳之地。享受单位制福利和身份保护的国企工人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化工生产=身体危害”的意识。
(2)嵌入化工区的村与民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无须自负盈亏,“下乡国企”为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和多元利益输送,化工区对于工农群体而言不是污染之源而是生活提升的助推器。当地农民以积极、正面的方式融入了这一“工—农”情境之中而改变了化工区与生活区的空间距离。
1.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现代工业的植入和发展带动了作为远郊的Z现代公共设施的建设。在工业规划的刺激下,Z 所属公社办公楼、银行、供销社、供水站等纷纷建立。工业用电输入以后,在有机化工厂、硫酸厂等的帮助下,70年代初村民即开始免费使用工业电,成为湘潭市最早通电及农民用电的地区之一。为了方便化工厂与外界的联络和工人上下班,邮电所于1965年7月建成,市第八路公共汽车营运线于1973年9月开通,由板塘区到Z 外围,1976年正在搬迁至此的市第三化工厂利用基建资金自主修建了外围至Z 核心的板竹路,同期公交线路延长至此。①湘潭市经济委员会编志办公室:《湘潭市工业志(1840—198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客观上使Z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个偏僻的农村变成了相对现代化的区域,实现了“旧貌换新颜”的蜕变,当地村民亦从中受益。
2.务工农民:一种主动参与形式。由于下乡工业对劳动力有着较大的需求,相当大的一批劳动力转移到了工业战线,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务工农民”。在1978年之前地方政策规定每征收三亩田地即为生产小队解决一个用工指标,同时还从当地招收一批临时工。
对于村民而言,进入化工企业不仅不是受污染,而是关系到能否跳出农门、享受工人待遇的大事。因为相比较于做农活,“在工厂里,夏天晒不到热不到,冬天冷不到,穿得整整齐齐的,也不要干重体力活”(刘海,2014年11月24日)。每个生产队约4 个人进入化工厂上班,而这4个人都是生产队干部的子女,即使是进入化工厂做临时工,也具有相当的竞争,跟生产队干部没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当年19岁的青年刘海还为生产队同意取消招工名额而与生产队干部争吵了几次,可见当时进入国有工厂的吸引力之大。
这种“农工结合体”的形成,不仅为工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增加了生产队和农民的收入,使工厂与村民之间形成了一体化的共生关系,当地农民则成为“离土不离乡”之民。
3.工业惠及农业。作为承接工业下乡的Z,在集体福利、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得到了国有企业的帮助,工农之间良性互动。1968年市氮肥厂和硫酸厂出资修建了一条输水管道,为了纪念工农合作名为“友谊渡槽”,该渡槽将工厂内的氮肥水引向Z 地各生产队,因此Z 村的农业生产从60年代就开始有免费的化学肥料使用。并且各个生产小队以15 元的低廉价格每两个月一次轮流去氮肥厂拉一个星期的煤渣回生产小队,以供村民们做饭、烤火之用。农忙时,工厂免费为生产队提供抽水的水管、水泵、脱粒的水泥场地和脱粒机,临时工在不扣工资的情况下可以回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组织工人在农忙的时候为劳动力不足的生产队帮忙。由于当时工厂生产产量并不大所以对农业生产并没有负面影响,所以当时Z村的农业生产情况要好于周围各纯农业村庄的生产情况,处于Z 核心区域的易家生产小队曾在1978年湘潭郊区水稻亩产评比中以亩产1050 斤获得过第一名的成绩,一般年份也都是处于前三名好成绩(刘士辉,2014年8月13日)。总体而言,Z 较早享受了工业下乡的好处,并与化工厂保持着良好关系,与化工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在此一时期就开始被社会因素所影响。
(3)蛰伏的污染与无危害的风险认知
从全国来看,政治机会结构是对民众环境风险知觉的出现产生压制作用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忽视局部地区环境自身的自然基础、工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污染的有限性。此一时期尽管工业生产已经开始,但机械化的操作和废物排放量不大,使得Z 地环境污染处于蛰伏之态,对当地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身份制度对工人产生了巨大的保护作用。
经济上的优惠、化工厂的具体生产环境和产生的污染情况、惠农助农措施所营造的“道德经济体制”以及单位制对工人、农民都有巨大诱惑力,村民们极力想将化工生产及其影响纳入自己的生活空间之中。加之此时的化工生产环境和所产生污染的情况亦使化工污染及其危害局限在非常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工农群体没有感受到化工生产对他们生活的威胁。因此,工农互嵌的社会关系与蛰伏的污染及其影响的有限性同样是风险情境的有机社会组成部分,视化工生产及化工区有益无害的意识所生成的社会距离对此一时期内工、农群体环境风险知觉的折扣起到关键作用。
四 距离与规避:低风险的自我建构
前一时期的化工生产整体表现为有益无害,而自21 世纪初开始化工生产对当地负面影响逐步凸显,关于污染的报道时不时出现在各级媒体之上。然而,人们的风险知觉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在经历了短暂的国企衰落期后,此地出现的繁华热闹景象更甚于前。不仅没有出现邻避现象,反而村民们均围绕着化工区大量新建住宅,并想方设法进入工厂务工,外来务工者更是达到了空前数量。
(一)工业下乡及凸显的污染影响
从1992年开始,整个湘潭市的国有化工企业陷入了急速经济下滑期,绝大部分企业由盛转衰。湘潭市政府依托1994年被国家化工部列为全国中小城市14 个精细化工基地之一的政策优势,通过租赁、破产、重组等形式,在已经停产或半停产国企基础之上引进了近20 家私营企业。2000年Z 工业区经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示范区之一; 2003年设立湘潭市高新区新兴材料工业园; 2010年已有大小不等的现代企业60 余家,就业人数最高峰时达10000 余人。随着以先进电池材料、精细化工材料、新型金属材料等为主的新材料生产加工为主业的化工厂数量增多,Z 地化工污染日重,湘江水污染问题先后被“中青在线”、《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等报道过。
(二)规避:一种去风险的技术策略
1.原国企工人:毒在其他工种。已有研究强调我国普通民众采取环境正义框架来看待环境风险,而地方政府则采取技术安全框架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①邱洪峰:《技术安全框架与环境正义框架? ——从东山PX 事件看政府风险传播的困局和破解》,《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 期。其实在逐步发展起来的化工区中同样存在着采用技术安全框架解释环境认知。
尽管化工厂务工者与化工区及其生产空间距离最近,但原国企工人依据个人朴素的知识、工作岗位和经验判定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影响,自己处于危险空间之外。
在原国有企业破产之后,部分国企工厂从事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下岗工人继续在Z 工作。2000年前后进入的一批私企直接购买国有企业的车间、机械设备,并聘请部分国企下岗工人继续从事生产活动。对于这些在国企改革浪潮之中能够顺利找到技术类工作岗位的下岗工人而言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机遇,在略有几分庆幸能找到相关工作发挥所长的同时他们的风险知觉产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更何况他们强调一直以来接触的是机器,而不是直接接触化工原料和产品,有毒的是化工产品而不是化工器械(黄文,2015年8月13日)。确实如黄文所言,他们在化工厂主要从事调度、化验、检验、管理、销售等工种,他们认为并没有接触化工原料,而且在工作中他们都佩戴口罩、手套、选择站在上风口等。调研期间笔者参观了某颜料公司的实验室,该实验室有着一定的隔离空间、封闭反应池、抽风机等。正是如此他们才认为作为技术工人和管理者处于化工危险之外。在生活中,由于工人社区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食用自来水,所以他们更不担心饮水问题。
2.农民工:没有危害的生产。高工资、低强度的工作和相对满意的工作环境使得农民工群体将化工生产的危害放置于自己的安全空间的范围之外。由于私营企业在用人上没有身份制度的限制,各个化工厂开始大量招收农民工从事操作工、搬运工、锅炉工等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工种,以及负责清洁、保卫、厨房等后勤工作。由于Z 的化工属于精细化工类,机械化程度较高,需要手工操作和涉及重体力活的工作并不多,整个生产原料的反应过程和输送过程大都在封闭的管道之中,化工厂内同时安装了大量的电风扇、抽风机以加速空气流通,使得整体工作环境并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化工行业工资较高,工作过程中比较自由,如陈氏化学公司部分工种八小时制的工资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达1000 元。因而,虽然大部分工种的准入要求并不高,化工厂在招人方面却有一定的门槛,部分工厂需要有一定的关系介绍和担保才能够进入。
如50 岁的王海清在其任职于湖南省某知名大学的化学化工学院的弟弟介绍下进入一生产电池材料的化工厂工作,但笔者谈到该工作对身体有害的时候他言道:“难道我的亲弟弟会骗我害我? 真是有毒的话他会让我来做事?”并且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都有意模仿技术工人的自我保护措施。由于对环境及污染影响的乐观判断,尽管化工区对于务工者而言已经不是“有益无害”的感知,但在农民工的意识中并没有形成“化工区=危害”的判断。对化工生产环境的知晓,接触程度和工作时的自我保护,工人们并不觉得在化工厂上班有何不同之处,污染危害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风险意识之中,反而在乐观偏误的认知作用下环境风险知觉度均较低。
3.普通村民:靠近及生活调整。直到21 世纪初当地村民们仍在积极向化工区靠近。20 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化工区出现了建房热,村民的居住地从相对而言距离化工区较远的地方,在再次新建住房的时候朝向靠近化工区的区域聚集。不仅一般村民如此,Z 所在的乡镇府亦在1996年的时候征收化工区核心部分的沿路耕地新建了两排商品房,很快这里形成了商贸中心,村民们亦主动在其商贸中心的边缘部位和沿江地带继续建房而形成了紧挨着化工区的生活区。因此,直到这一时期化工区仍没有进入农民空间意识中“他者”之内。
约从2002年开始,Z 的污染开始加重,村庄开始更多地遭受到生产排放物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污染的部分结果开始显性化,但村民依据居住区位的不同,其环境风险知觉在空间上呈现多元化特征。由于湘潭多南北风,地处化工区南边的村民因受刺激性气体的影响而有较强的风险知觉,然而这一区域非常有限。由于化工区北边的地势略高,尽管距离不到一公里但该块村民普遍不担心地下水受影响,并且化工区500 米以外的北区农民没有农赔款、蔬菜补贴。因而虽然2011年之后免费安装了自来水管,但笔者2015年11月调查发现依旧使用井水作为饮用水的住户比例高达约35%,北区的使用比例更高,调查中他们均觉得隔得远地下水不会被污染。在化工区西边聚居的村民则以所闻气味极少和地势较高而普遍认为自己所在区域没有污染。
认为受化工废气废水影响的民众在生活中也进行一系列调整。如将紧挨着化工区的农田产的稻谷用来作为鸡食猪食或者用来酿白酒,甚至主要用于售卖而非自己食用; 在认为地下水有影响之后食用自来水或桶装水,而井水用来洗漱等。对于晚上较为突出的废气影响,村民们则采取减少晚上外出、安装铝制玻璃窗等办法。村民们觉得刺激性废气对儿童群体十分不利,对中老年群体则没什么影响。
因而,尽管陈占江、包智明认为随着国家政治机会结构的改变,村民们的环境风险知觉得以苏醒。①陈占江、包智明:《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 期。但通过对Z 地区的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转变、传统文化等对村民的影响并不是同质化的。处于不断地苏醒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意识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直接受到了特殊的区位和经历等社会距离的影响。这一情境所产生的社会距离影响远比彭远春所言及的污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产生的麻痹作用②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 期。要复杂,而是部分村民们更相信这些污染物不在其日常生活空间之中,或者将污染风险因素排斥于安全空间之外而形成有影响无风险之态。
五 结 论
尽管Z 地化工污染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不严重到严重的过程,但该地民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并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除了极少数人表现出较高的环境关心度和零星的抗争外,该地一反常态地少有邻避运动发生,化工区核心地带民众的集体沉默和无风险认识曾经让笔者陷入深深的思索和痛苦之中。通过对该地半个世纪的发展史,特别是化工发展史、厂民工农互动史以及工作生活经验的分析,笔者发现化工生产所造成的自然影响与民众的风险知觉折扣之间存在着社会距离这一关键变量,即基于民众的判断所产生的社会距离意识对民众风险知觉生成起着关键的折扣作用。
客观上讲,由于化学物质传播、扩散的特点,民众距离污染源或化工区越近受到的影响越严重。然而,空间距离的大小并不与风险知觉的大小成正比例,民众依据生活经验、对情境历史生成的感知、生存机会成本、在情境中的结构性位置对空间距离进行有意识的处理后生成社会距离,从而对风险知觉的生成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对于工农群体而言化工生产所带来的影响不一定是负面或具有环境危害性的,即化工影响≠环境风险。在20 世纪90年代以前,化工区对于工农极具诱惑力,从生活、工作等方面来看化工生产对他们有益无害,靠近甚至进入化工区具有相当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即使在污染的公共性被人所觉察,但民众可以在工作生活中依旧朴素的生活经验和化工影响的表征而认为自己并不在污染所导致的风险之中,并运用一些办法规避环境风险。
近些年在部分高风险化工项目转移、引入地普通民众因担心化工产业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而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最终导致“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不良后果。群体环境风险认知的生产、传播、扩大在群体性事件之中起着关键性影响。在对抗争运动发生地普通民众的环境风险意识进行深入探究的同时,亦需要关注另一类现象及群体,即“心理台风眼”效应下沉默的多数和积极进入化工生产之中的民众。从自然与社会、群体与环境的积极互动所产生的情境出发理解民众的环境风险知觉特点及“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生成逻辑,对于反向理解目前产业引入与群体性事件频发相伴生以及破解这一困局或许有着积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