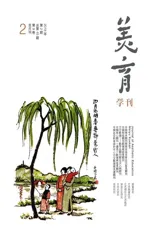“发国人之内曜”:鲁迅文学的美育价值
2018-01-30叶继奋
叶继奋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这个问题在当下显得特别突出。快节奏的生活与繁杂的日常事务,使人忽视自我反省致使内部世界日渐荒芜;日趋激烈的竞争与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应有的联系和关爱而疏远冷漠;世俗生活的盛宴以及一己情欲的过度渲染,使人沉湎其中而意志消沉松懈疲软。鲁迅文学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关注人类历史转型时刻的精神建设问题,预见到物质至上可能给人类带来精神毁灭的恶果,担忧“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1]54鲁迅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变异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重视美育对于人的内部世界建设的重要作用,对艺术的审美功能有过深入研究,认为艺术真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2]52。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其美学思想的具体实践,它以独特的美感作用于人的心灵,能“发国人之内曜”[2]27,并以每个中国人焕发的精神之光凝聚成民族之火。鲁迅文学在构建当代人精神世界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美育价值。
一、灵魂之真:严肃纯洁的内部生活
人的存在和意义是重要的哲学问题。雅思贝尔斯认为,“作为真正的人活着,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内省他自己,对自己进行哲学思维”。鲁迅关注有关人的存在和意义、道德和人性等重大问题,重视人的内部世界建设,认为“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1]57,“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鲁迅所谓真的“人”,即具有“白心”者,“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他们剖白内心直视灵魂,焕发自我精神之光耀,使得“人生之意义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于沉沦于浊水”[2]29。事实上,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熙熙攘攘的日常事务中忙碌周旋,很容易沉沦于非本真状态,经常就人生重大问题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可以从凡庸世俗中暂时超脱出来,并借此确立心灵准则和生活目标。这种带有哲学性质的深度思考,赋予人以尊严和高贵的品质。有关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灵魂对话,在鲁迅小说中是借助“复调”的艺术形式展开的,其主要策略是虚构一个随时存在的叙事者“我”,将主体由完整的实体分裂为几个不同的自我,“通过几个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对话、审视、反思,来探究自我、把握自我、揭示自我的深层结构”[3]。《在酒楼上》主要是叙事者“我”与主人公的对话。“我”的作用不仅在于叙述事件,同时还是个重要的“在场者”。虽然“我”的态度沉静内敛,并没有在言行上表现出与主人公思想的明显对峙,但“我”通过客观打量和追问质疑对主人公造成无形压力,致使主人公不得不反躬自省。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之间构成潜对话,反映出人物灵魂中“形我”与“心我”“真我”与“假我”的分裂和挣扎。由灵魂双音构成的内在主体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张力,能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野草》中有不少作品也充满着灵魂对话,它在揭示人物心理深层结构的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彷徨时期思想和情感的复杂矛盾。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边缘情境”是包围人类生存的一个灰心丧气的“定在”。它使人蜗居其中,失去意义和追求而终至毁灭。然而,毁灭与新生俱在,关键取决于人的态度。人之所以能突破它战胜它,依靠的是主体的自由意志:“人可以通过自我选择,自我超越达到‘自由’的境界。”它的前提是“人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有意识到现实世界的荒谬性和自我存在的无意义,人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本质,走上自由之路”。[4]鲁迅彷徨时期的作品出现了“告别”主题。所谓“告别”,是指人的精神时刻处在生与死的交替中,人通过“告别”以获得死后重生。“告别”是主体自我对话之后的必然选择。作品在写作手法上呈现出规律性特征:先对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状态进行审视比照,继而以自由意志作出选择,最终告别无意义现实而坚定地走向意义世界。散文诗《野草》和小说《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都鲜明地呈现出这一深刻主题。《野草》中《求乞者》展示了同处于灰暗颓败的境遇中“我”与孩子截然两样的生存态度:“我不布施,我但居布施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在“冻灭”和“烧完”的两难境地中,“死火”坚定地选择了“烧完”,死而复燃的生命之火焕发出红彗星般的璀璨光芒。《影的告别》是对“形影不离”说的一种反动。影子对自己的附着体“形”的“告别”蕴含着形与影、灵与肉、现在与过去、高尚与卑鄙、进取与堕落等诀别的丰富内涵。《野草·题辞》充满了生与死、虚无与实有、光明与黑暗、存在与毁灭、过去与未来、痛苦与欢乐的哲学思辨,洋溢着辞旧迎新的坦然与欢欣,展示着通透澄澈的生命境界。小说《长明灯》中的“疯子”与“狂人”是富有存在论意义层面意味的艺术典型,包含着鲁迅特定时期的人生思考。疯子的出身以及发狂、被骗、被治愈的经历与狂人无异,所不同的是他再度“发病”。尽管他喜剧性地被关进了自己为拯救世人而竭力要烧毁的社庙,无奈地生存在一个崇高者被亵渎、被玩耍、被遗忘的孤独境地,但他终于从“候补”的沉沦中超脱出来,他不再“回去”。他发出了“我放火”的强烈心声。这既是对挺立在地面上的封建社庙的破毁,也是对自我绝望的猛烈震荡!疯子是狂人的死后重生。《在酒楼上》,“我”与吕纬甫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我”坚定地与没有“以后”、“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度日的吕纬甫分道扬镳。《孤独者》中“下葬”仪式则蕴含着鲁迅在生死转换方面的深度思考:魏连殳的“活”使“我”认识到什么是虽生犹死,而魏连殳的“死”则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快乐。小说强烈地表达了人对自身沉沦的无比憎厌,是对人自我的本性回归和灵魂救赎。小说所具有的理性思辨,使它超越了社会学阐释和道德训诲的层面,进而呈现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方面的哲学启示。
在宗教意义上,“死亡是波及整个生命的现象。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死亡。生命是不断的死亡,是对一切方面的终点的体验,是永恒对时间的不断的审判。生命是同死亡的不断斗争,是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局部死亡。我们生命内部的死亡是由于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容纳完满而造成的。时间和空间是能够带来死亡的,它们所导致的分裂就是对死亡的局部体验。当人的感情在时间中消失的时候,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5]。人生的不完美无可避免地存在于生命之中,追求完美的天性促使人类自觉地向它告别,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痛苦而又愉悦的死亡感。只有直面死,学会死,才能得到生,得到永恒。它赋予人的生存以形而上智慧,使人类载着不满足的精神之舟驶向理想彼岸。鲁迅的许多篇小说反复出现了哲学意义上的生死轮回。与其说它呈现了鲁迅躁动不安的诗性灵魂,毋宁说在这颗激扬活跃的灵魂里,我们深感到人自身对纯洁和完美永不停息的追求。
二、人性之善:普遍联系的心灵原则
“创作总根于爱。”对故乡的记忆表象和情绪体验是鲁迅文学的创作源泉,它流淌着善良、真挚和悲悯的人性暖流。他所写的都是他曾经亲历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他熟稔于心的。他写家里的长工保姆、世家故友以及乡邻同学,他听得懂他们的每一声叹息。在他的记忆中,故乡蒙着一层由败落、沉沦、灾祸、夭折、丧葬等苦难织成的灰霾。炮烙一般的创伤性记忆,深秋落叶般的往事和细节,在灵魂深处发酵酿成艺术之酒,那厚朴甘醇之味浸入心灵渐渐发散以至产生强烈震撼,你无法抗拒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力量。正如高尔基所言:“一个大师不仅应该熟悉他的材料,而且还应该热爱自己的材料,更准确地说还应该欣赏他的材料。因为唯其对材料怀有这么深厚的欣赏和热爱,他才会进入到这个世界,从中获得那不仅深刻,而且细微、独特的发现。”
鲁迅不但冷峻地再现了人类生命的生存本相,而且他在呈现这些生命困境的同时,表现了人类生命的尊严和力量。究其根底,这种生命的尊严和力量源自伟大的悲悯。鲁迅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像中国人这样遭受无穷尽的不幸。这使鲁迅在面对这个民族时满怀着太多的悲悯。悲悯是鲁迅的爱的底色。过于丰盛的悲悯使他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安然度日,悲悯迫使他要为改变这个民族太多的不幸做点什么”[6]。葛赛尔认为与维克多·雨果一样,罗丹“在诗中倾诉个人的悲欢,他歌唱婴儿摇篮边的母亲,女儿坟上的父亲,幸福的纪念物前面的情人”,他是继维克多·雨果之后,“表现了最幽深、最奥秘的心灵”的雕塑家。[7]鲁迅忠实于心灵深处的乡土记忆,他动情地书写那些卑微到没有姓名的农夫、船工、村妇、保姆,以及他们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命运。他们的生命像蝼蚁一样短暂,像枯草一样低贱。他们像牲口一样劳作,像奴隶一样受人摆布。同尼采一样,鲁迅希望人类走过了由虫豸变为人的道路之后,能够超过动物,跨越深渊,走向更高的文明。但与之不同的是,尼采心仪的超人是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在他看来“怜悯”是“最大的危险”。而鲁迅却毫不吝惜自己的情爱,他的笔端充盈着与底层人感同身受的饱满情愫——那是感伤和仁慈。“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托尔斯泰时时为人类的苦难而忧伤”,稍有不同的是,鲁迅的人道情怀里删去了基督教式的忍从与缄默,增添了为改变民族苦难命运所必需的激奋与呐喊。
鲁迅给予了最大悲悯的是女性和孩子。这首先因为女性与孩子标志着人类生命孕育、繁衍与生长的最古老而本质的关系,是文学艺术母题中的母题;其次,她们又是中国封建等级文化最大的受害者。对女性和孩子题材,欧洲艺术家的表现各有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美丽的女园丁》《金翅雀圣母》等画作中,牧歌情调的大自然,可爱的孩子在慈爱的圣母膝旁嬉戏,有着天国仙界特有的和平、安宁和恬静。在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笔下,则更多地表现出贵族家庭安逸富足的伦理生活。美丽的花园,明媚的春色,年轻漂亮的母亲与伶俐可爱的女儿依偎在一起,一派其乐融融甜美闲适的情调。鲁迅热爱美术,也熟谙美术之道,20世纪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曾引起过他的高度关注,他把珂勒惠支介绍到中国,并特地写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一文。他十分推崇《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认为“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他借了日本批评家永田一修的话来说明,认为珂勒惠支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8]487-488由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妇孺问题普遍关注的时代氛围,以及鲁迅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洞悉和现实人生的印象与体验等因素,他也创作了大量以中国母亲与孩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散文和小说比较经典的有《明天》《药》《祝福》《在酒楼上》《伤逝》《颓败线的颤动》《阿长与〈山海经〉》等篇。在这些作品中,他写很多的村姑寡妇,写与她们命运相关的婚恋悲剧,以及她们枯萎的生命与无奈的叹息。他写孩子们如何在无爱和病态的环境中受到伤害而终遭夭折。他要给出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存是如此贫乏和困顿?在这些作品里,没有天国的光辉与田园的牧歌,没有夜莺与小夜曲,没有孩子的俏皮与嬉闹,进入读者眼中的是:稚嫩的春芽在冷峭的寒风中萎落,娇艳的花苞未及绽放而凋零……从而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抱以始终的博大的悲悯情怀。作者不屑涂饰瑰丽华彩的色调,只用素淡的笔墨和简练的线条勾勒故事轮廓,而文本深层却有着细腻而清晰的情感肌理。在无爱的人间,美丽善良的女性和孩子的生命走向寂灭和死亡。它在激起人们对“为死亡所捕获”的“人间挚爱者”的无限感伤和悲悯的同时,也激发起人们抗争苦难争取新生的信念和力量。在小说《兔和猫》等作品中,鲁迅也将怜悯之情洒向幼小生灵,从人性深处折射出来的正是鲁迅文学的深沉美感。
鲁迅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鲁迅思想锋芒的锐利自有公认,但他对朋友一向真诚挚爱,体现出人性的绵软和温厚。他写过许多追忆师长故友的悼文,从他择友的标准不难看出他自己的为人准则:藤野先生的温厚,范爱农的耿介,韦素园的认真,刘半农的清浅等,在个性各异中共同闪现着人性之善。在小说《社戏》中,平桥村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乡土乐园,村民们的人性如同儿童刚从原始的自然中分娩出来的生命一样朴素单纯。“人性的单纯来自自然”[9],但社会的作用往往使人失去单纯的人性,鲁迅是身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仍然保存单纯天性的诗人。他用心表现和召唤那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逝去的美好人性,借此穿透筑在人与人之间厚重的等级障壁,达到人心相呼应相沟通的美好境界。这是一切精神伟人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类为之向往并终将实现的文明目标。
鲁迅将对人性之善的追求建立在对势利凉薄等人性之恶批判的基础上。在《社戏》中,作者以“城里的戏”和“乡下的戏”相比照来表达理想人性。在其他作品中,他设计了咸亨酒店、华氏茶馆等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用来展示人性的基本事实,生活空间也由绍兴乡镇延伸拓展到了北京、上海等首善之城和繁华都市,《阿金》即是其中一例。他同时也展示了大革命动荡时期偏僻乡村特有的人际关系,小说《风波》对人情的凉薄以及散沙一般的生态样式作了生动精细的表现,是其中典型之作。此外,还采取了精致凝练的小品样式,如《狗的驳诘》以人犬对话形式讽刺势利小人。小说《示众》则以“看——被看”抽象的叙事模式表达深刻的文明批评。鲁迅一生最感寂寞和痛恨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不相通。“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有船上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10]555鲁迅在呼唤人心相通的同时建立了人类普遍联系的心灵原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8]624
三、崇高之美:刚健雄伟的精神骨力
优美对象无论是色彩、声音、空间造型等,都能直接引起人的愉快而纯粹的美感。从价值论角度而言,人生的“平衡是暂时的,矛盾冲突却是永恒的;但人的生命却追求平衡,渴望和谐。这体现在审美中,就是赋予瞬间的和谐自由以永恒的价值。因此,优美成为一切审美形态的基本价值尺度”[11]。然而单一的优美则有可能导致主体精神的平庸萎靡。完整的美育应该体现优美与崇高的双重属性,这样才能使人的天性获得完全的生长与发展。优美与崇高在建构理想人格方面缺一不可。与优美直接从人所观照的对象中获得的纤秀柔媚的美感不同,崇高由于客体数量、体积、形态和力量等方面的无比庞大而与主体发生冲突,使主体产生恐惧感,在经历了瞬间生命力的阻滞之后产生心灵的抗拒和超越的冲动,激发起主体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的喷射,继而获得一种崇高感。如康德所言,崇高感源于“通过道德的原则克服了感性世界的阻碍”而证明了自己人格的崇高。崇高感具有一种扩展胸怀,磨砺意志,激发力量,承受苦难,提升人生境界的作用,使人“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2]29。崇高感“使得美育超越了艺术教育的局限扩展到了整个自然和社会人生的领域,从而使审美与人生趋向统一”[12]。崇高感的培养对中国人尤为重要。由于长期以儒家为代表的父权意识的统治,“加上儒道佛这三种在中国古代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里所具有的女性偏向,使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气质、性格仍保留着深层的女性底蕴”[13],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中庸保守、阴柔谦和的传统气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日益频繁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所带来的不只是和谐,还包括因文化的差异和不平等形成对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的冲击力。只有改善国民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及审美趣味,才能迅速融入人类的文明对话。
对往昔美好的珍藏与吟唱是鲁迅文学的题中之义。从美学角度而言,这些作品属于优美范畴,其主要特征是秀美和谐。但从总体而言,悲凉崇高则是鲁迅文学更为重要而独特的美学特征,“在审美感受上,强调了现代人在纷繁、激烈的社会和人生动荡中,那种痛苦与愉悦、自由与焦灼、束缚与解放等对立的、复杂的情感混合之感受和生命之体验。在审美本质内涵上,突出‘对立’‘崇高’所反映的近现代社会人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呈现出近现代以‘力’、‘悲壮’、‘悲凉’和‘孤独’为特征的审美走向”[14]。鲁迅在作品中很少描写自然景物,即使偶有出现,也绝非柔婉甜腻之趣味。他所选择的物象,更多的是乌鸦恶鸟而非夜莺黄鹂;不是春二三月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而是“毫不以深冬为意”的傲霜斗雪的老梅及“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的“愤怒且傲慢”的山茶花;他写已然遍体鳞伤却仍“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他写朔方的雪伴着旋风,蓬勃地奋飞、旋转而且升腾,“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他在寂寥无边的荒原呐喊,那是被困于铁屋子中不得解放的人从灵魂深处发出的狂呼;他感觉“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那是现代人挣脱孤独缠绕之后的沉重喘息和庆贺新生的粗犷放歌。他的人生态度是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着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10]4他听从“前面的声音”的召唤,在风雪中“走”,在月光下“走”,在无路之路“走”。“走”是人的自由意志对自我和命运的决绝与抗拒,是鲁迅的哲学和宗教。鲁迅赞美虽身处困厄之境,仍坚持为真理和正义抗争鏖战的英雄,疯子、夏瑜、眉间尺等艺术形象都具有坚毅不屈的精神及充沛旺盛的斗志,在他们身上散发着伦理力量之光。鲁迅毫不畏惧苦难、孤独、绝望和死亡,他直接进入人的心灵世界,大胆抒写现代人的喧嚣和躁动,字里行间蒸腾着生命的血气和热量,其激昂张扬酣畅淋漓的风格,与安详平和悠远静穆的传统趣味迥然相悖,从而形成了崇高悲凉的现代美学风格。鲁迅文学所特有的“力之美”,足以“构成对中国人心灵的猛烈闪击”[15]。
鲁迅文学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不辱使命的担当勇气,深刻的孤独意识及超越凡庸的先行者智慧,对人的命运及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精神,对绝望人生的彻悟与奋力反抗的生命热情……鲁迅在表现人生苦难的同时自己也处在精神炼狱之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无私地释放自己的生命能量,以强大的意志力超越苦难,坚定地行进在广袤无际的荒原上,成为罗曼·罗兰所称的“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的强有力的英勇队伍里的一员。鲁迅文学所具有的崇高美感,对构建现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生存于世俗化社会中的当代人,几乎被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那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无形的精神锈蚀,意志日益磨损,身心脆弱无力,既缺乏对浅薄卑俗自觉抵抗的敏锐感觉,更缺乏对挫折的承受力和远大的理想追求。现代人的灵魂需要注入刚健雄伟的崇高之力以作精神支撑。鲁迅文学使人开阔胸襟,激扬精神,充实内心,深化人生意义,更新审美趣味,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席勒曾辩证地论述了美和崇高对人的精神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我们被接连不断的快感弄得虚弱松懈,就会丧失性格的朝气蓬勃,而且我们被存在的这种偶然形式紧紧缚住,我们永恒的使命和我们真正的祖国就会在眼前消逝。只有崇高与美结合起来,而且同等程度地培养我们对二者的敏感性时,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公民,因而不会是自然的奴隶,也就不会在只能靠理性而不能靠感性来认识世界中丧失公民权。”[16]这真是极富见地的论断。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刘再复.关于文学的内在主体间性——与杨春时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2,91(6):14-23.
[4] 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34.
[5]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332.
[6] 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2.
[7] 罗丹.罗丹艺术论[M].葛赛尔,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131.
[8]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周国平.周国平论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209.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杜卫.美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29.
[12] 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56.
[13] 梁一儒,户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420.
[14] 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272.
[15] 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多维视野中的鲁迅[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316.
[16] 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96.